Европейският вицешампион по санда Йордан Янков-Руския: Президентът на федерацията Стефан Колев е измамник!

Искам да предупредя хората, които мислят за в бъдеще да работят с него, просто да не му се доверяват, заяви Един от най-титулуваните бургаски спортисти
Ключови думи:
Йордан Янков, Руския, шампион, санда, Стефан Колев, президент, федерация, общински съветник, ГЕРБ, европейско първенство, Москва, премии, подготовка, разходи, Бургас, Флагман
17 Януари 2017, Вторник, 11:46 ч.
Автор: Петър ПЕТРОВ, снимка: авторътОтказвам да отговарям на такива нападки, всеки може да твърди каквото си поиска, лаконичен бе бургаският общински съветник
Шокиращи разкрития за президента на Българската федерация по санда и общински съветник от Бургас Стефан Колев направи шампионът Йордан Янков-Руския в интервю за Флагман.бг.Един от най-титулуваните бургаски спортисти обяви, че заради неуредици във федерацията се е разминал с премия в размер на хиляди левове з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я първи медал за България от европейското първенство в Москва през май миналата година. Празни са останали и обещанията, че Бургас ще се превърне в център за развитието на изключително атрактивния спорт, който е смесица между кикбос и ММА.
„Самото европейско беше добро преживяване. Аз и моите колеги сме разочаровани от действията на ръководство на Българската федерация по санда в лицето н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тефан Колев. Преди състезанието ни обещаваше едно, но после се отметна от думите си. Той ни каза, че е говорил с министъра на спорта Красен Кралев и той му е обещал, че вземем ли медал, тази година ще отпуснат 100 000 лв. на федерацията за развитието на спорта. В последствие той ни каза, че няма сключен договор с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то на спорта. Тогава разбрахме, че няма да вземем и премии за медала от европейското”, заяви пред Флагман.бг Йордан Янков.
Руския добави, че със съотборника му Васил Симов са били принудени сами да се готвят за европейското първенство в Москва. Сами са търсели и плащали за зали, където да тренират и спаринг-партньори. Получили помощ единствено от Община Бургас. Стефан Колев платил разходите само за самолетни билети и престоя в Москва, но и това, според Йордан Янков Колев направил с мъка.
„Отначалото се опита да ни прекара сами да плащаме всички разходи – пътни, престой и т. н., става въпрос за състезатели и треньори. По принцип всяка една федерация, за която съм се състезавал, покрива тези неща. Стефан Колев до последно се опитваше да ни прекара да платим и тях. След като му казахме, че няма да ходим на състезание, се принуди да поеме и тези разходи”, разкри Руския.
След завръщането им от Русия Стефан Колев буквално се покрил. Не вдигал мобилния си телефон, успели да се свържат с него близо половин година след края на европейското.
„Обадих се от друг номер 4-5 месеца след европейското. Уж имахме идеи да развиваме спорта тук, а какво се случи – изглежда, че строим въздушни замъци. Отидохме с треньорския състав на среща в кабинета му, около половин година след успеха в Москва. Той се държеше изключително нагло. „Аз на никого пари не давам. Хората работят за без пари”, така ни каза тогава. Поискахме поне наполовина да ни компенсира за премиите, да вземем нещо символично”, заяви Янков.
Той добави, че вече е отписал въпросната премия и желае просто да предупреди други хора, които за в бъдеще ще работят със Стефан Колев. Руския се свърза с Флагман.бг, след като прочел статията за съмненията около световното по УШУ, което се проведе в Бургас през есента. (ВИЖ ТУК)
„За мен тези пари не са важни. Искам просто да предупредя хората, които мислят за в бъдеще да работят с него, просто да не му се доверяват. Той е измамник! Заставам на 100% за думите си. Съжалявам, че не успяхме да развием нещо ново, нещо интересно. Този човек не живее за спорта, а от спорта. Самият той си призна, че има интерес. Такива хора не трябва да бъдат близко не само до спорта, но и до длъжности, при които може да се злоупотребява с пари. Разбрах, че искал да оглави комисията по спорт. Според мен подобно нещо ще навреди много на самия спорт в Бургас и ще подрони авторитета на Общината. Един такъв човек може да компрометира цялат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каза Йордан Янков.
Той не пропусна да коментира и въпросното световно първенство по УШУ.
„Видях статията във Флагман.бг преди Нова година и почти на 99% съм сигурен, че нещата са така. За проведеното световно първенство по УШУ в Бургас мога да кажа само, че не съм виждал такава ант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Всяка сутрин, минавайки покрай спирката на зала „Младост”, виждах как отборите пътуваха с градския транспорт. Аз съм бил на над 15 международни състезания и за пръв път виждам такова нещо – да пътуваш до залата с неорганизиран градски транспорт. Когато ни награждаваха в Община Бургас след европейското, Стефан се хвалеше, че ще направи незабравимо световно първенство. Твърдеше, че това ще му струва 1 млн. лв., които самият той ще плати. Аз виждам от тези фактури, че всеки отбор си е плащал сам и парите са минавали през неговия клуб. Но аз не съм някаква институция, просто коментирам видяното”, отбеляза многократният световен и европейски шампион по муай тай.
Флагман.бг потърси и Стефан Колев, за да чуе и неговата позиция. Колев, който освен общински съветник е и солиден бизнесмен с интереси в строителния сектор, категорично отрече твърденията на бургаския шампион.
„Няма какво да коментирам. Това е абсолютна глупост! Няма такова нещо. Водили сме няколко пъти разговори, в които участваха и други хора. Не ставаше въпрос за премии, а по-скоро за някакви възнаграждения. Такива не съм обещавал, защото федерацията няма пари. Отказвам да отговарям на такива нападки, всеки може да твърди каквото си поиска”, лаконичен бе Стефан Колев.





 За какво най-често лъжат хората на първа среща
За какво най-често лъжат хората на първа среща


Младоженец избяга от сватбата с тъща си, сътвори нещо още по-гнусно преди това
21/04/2025, Понеделник 21:40
3

4 зодии, които имат невероятно шесто чувство
21/04/2025, Понеделник 21:20
1

Тайната е в продуктите: сладкиш без печене, любим на цялото семейство
21/04/2025, Понеделник 21:00
0

Бягайте далеч от тези зодии, те се обвързват много трудно
21/04/2025, Понеделник 20:40
0

Жена с трансплантирана матка роди здраво бебе в Англия, българин от Златоград е в екипа
21/04/2025, Понеделник 20:20
0

Невръстно дете падна от шестия етаж в Габрово
21/04/2025, Понеделник 20:00
1

Жените от тези зодии са истински кръвопийки
21/04/2025, Понеделник 19:40
1

Покойният папа отраснал с нашето кисело мляко, което баба му квасела в Аржентина
21/04/2025, Понеделник 19:20
2

Режа 1 картоф и мажа по лицето, отначало всички ми се смееха, но като видяха резултата, останаха без думи
21/04/2025, Понеделник 19:00
0

Зодиите, които ще се къпят в пари в следващите дни
21/04/2025, Понеделник 18:40
0

Вчера направих тази бърза баница с домашни кори, цялата улица ухае на нея, а всички ми искат рецептата
21/04/2025, Понеделник 18:20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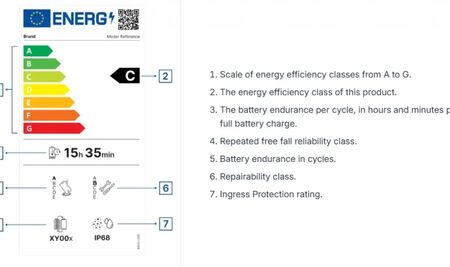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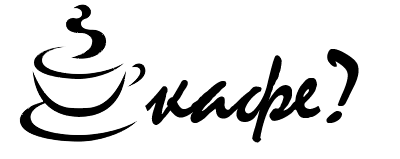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問
道:「爾吃酒麼?」梅氏答道:「因心中寂寞,聊飲三杯以解煩悶。」說罷丫
頭已將酒席排上,二人坐下對飲。
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見了心中氣忿不過,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
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少爺快些回去。」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
「我有一件心事爾可曉得麼?」雙桃道:「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花子能
道:「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又有愛我的心,只恨太師來衝散了,一場好事不
能成就。」雙桃道:「這個使不得的,二夫人年紀雖輕,到底是庶母,不是我
冒犯少爺說,爾不可癡心妄想,紊亂五倫。」花子能道:「什麼五倫?就是十
倫也無要緊,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妗母私通,將母舅謀死,二人猶如夫婦一般
。」雙桃道:「這是畜類,說他怎麼。少爺乃是官家之子,不可無理,快些回
去,免得累我。」花子能道:「爾若說得此事成,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雙
桃想道:「待我騙他出去便了。」乃說道:「今夜太師在此,爾且回去,明日
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花子能道:「我要,在爾身上成事的。」雙桃答道:
「這個自然。」
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到四更時
分就去上朝。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昨日少爺幾時
回去?」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梅氏聽了一發愁悶,恨怒道:「老厭
物衝散我的好事,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只愛他精精壯壯的少年,說的言語甚
是知心,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顧什麼規矩,管什麼五倫?若能夠與他成
其夫婦,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一心想念子能,一心恨著花錦章不提。
且說皇上登殿,兩班文武山呼已畢,皇上傳旨:「命吏部侍郎邱君陛領旨
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邱君陛領旨出朝,兩班文武退朝。花錦章回府大悅道
:「邱君陛乃我好友,此事不妨了。」吩咐備酒伺候。不一時邱君陛前來辭行
,花錦章留住飲酒,邱君陛道:「有勞大人費心。」花錦章道:「爾說那裡話
來,與我摯交,何必客套。只是有一件事相托,不知可肯見許麼?」邱君陛道
:「願聞其詳,小弟無所不依。」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邱君陛道:「這
個做得。」吃了酒,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
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爹爹啊,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誰教爾做
事自佔便宜,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是爾自己不是,不干我事。」睡到天明
爬起身來,梳洗已畢,吃了點心,也不帶花通,恐他多言,獨自一個來到七畝
莊,由後門打門。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只撥兩名花僮在
園內照顧門戶,整理花木,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梅氏與花錦
章說可以不用花僮,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
,花錦章道:「也說得有理。」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不便放他在此,是以
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
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忽聞犬吠,又聞嬰哥叫道:「雙桃
開門。」梅氏道:「雙桃,敢是太師來了?快去開門。」雙桃連忙走去開門,
見是少爺,遂道:「我說是太師爺到此,原來是少爺來。」花子能問道:「二
夫人在那裡?」
雙桃道:「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爾回去罷。」花子能道:「放屁,我
特來謝酒。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什麼反叫我回去?」一邊說一邊
走進。雙桃將門閉了,花子能問道:「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雙桃道:「不
要說起,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還要告訴太
師,是我說少爺酒後之言不必見怪,二夫人才歇。」花子能道:「既如此帶我
去謝罪便了。」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雙桃叫道:「二夫人,少爺來了
。」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裡面來坐。」花子能走上前道:「孩兒今日一
來謝酒,二來請安,三來賠罪。」梅氏問道:「賠什麼罪?到要說個明白。」
花子能道:「雙桃說二夫人動怒,所以我特來謝罪。」梅氏道:「不要聽這賤
人的話。」遂叫:「雙桃、雙杏快去備酒,雙梅去取茶,雙桂去取點心。」將
四個丫頭打發開去。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一手來摸胸乳。梅氏道:「不可如
此,焉有母子成奸的理?」花子能道:「又不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算不得數
的,只好兄妹稱呼罷了。」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摸得梅氏慾火難
禁,說道:「既要如此,奴家從了爾罷。」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說道:
「只是此處不好行事。」梅氏道:「這個不妨,等雙梅、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
可如此說,我便這般應答,豈不瞞了他們?」花子能道:「如此甚妙。」遂走
原位坐下。只見雙梅、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梅氏道:「少爺
吃些點心。」花子能道:「多謝二姨娘,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景致不凡,
意欲看看,不知可肯見許麼?」
梅氏道:「如此我陪爾去看看。雙梅、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若備完可排
在登雲閣內。」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閉了門,二人解帶脫衣,上牀成
其好事。
且說雙梅、雙桂來到廚房,說:「二夫人吩咐,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
伺候。」雙桃道:「二夫人在那裡?」雙桂應道:「同少爺去看景致。」雙桃
心中想道:「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待我去尋尋看。」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
,偶然尋到迎香院,見門是閉的,舉手一推卻推不開,想道:「他二人必在裡
面。」又想道:「此事那個不愛?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況且青天白日在此
取樂,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也罷,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那梅氏與
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穿了衣褲,梅氏道:「若太師有事不能來,爾千萬要來
,不可做無情義的人。」花子能道:「這個自然。」忽聽得雙桃叫聲:「太師
爺,這裡來。」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汗如流水,滿身發抖。花子能忙
趴在牀下躲著,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才放心開了門,問道:「雙桃
,太師爺在那裡?」雙桃應道:「太師爺是不曾來的,我因等得不耐煩了,所
以假叫一聲。」梅氏道:「事已至此,爾切不可多言,我自然另眼相待。」雙
桃道:「這個自然。」那花子能躲在牀下,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梅氏將眼
一丟。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解開裙帶脫下褲來,用
強就弄。雙桃叫道:「做不得的。」花子能道:「做得的。」弄了一回兒。事
畢,雙桃穿了裙褲道:「二夫人,這是少爺用強,不干我事。」梅氏道:「誰
來怪爾?」二人互相整了頭髮,梅氏道:「少爺,爾今如此如此而來,我先去
等爾,免得三個丫頭疑心。」花子能道:「不錯,爾先去,我依計而行便了。
」
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那三個丫頭問道:「少爺為何不來?」梅氏道
:「少爺腹痛走不動,他道腹痛好了就來。」
遂坐下等了一回,只見花子能走到,梅氏道:「少爺,此時腹痛可好了麼
?」花子能道:「此時好些了。」梅氏道:「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二
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如再挨延,倘太師爺到來
如何是好?須當速去,等明日再來罷。」花子能沒奈何,辭別梅氏而去。這花
子能平日作惡作威,今日又與庶母通姦,於禽獸何異?雖是前生孽債,然而罪
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報應昭彰?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屈害忠良,故有
此報。
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一路而來,已到揚州,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接
進知府堂上,開讀詔書已畢,知府備酒款待。
誰知府內有個書辦,姓陳名松,曾受李榮春大恩,未曾報答,念念在心,
今日忽聞此信,驚得冷汗直流,道:「此事怎麼好?
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只是不能出去,如何是好?也罷,我且到後庭
去看可有出路麼。」急急走到後庭,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忽見東南角有一
株樹,遂爬上了樹,立在牆頭望下一跳,跌倒在地,也顧不得疼痛,爬起就走
,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開門一看
,問道:「原來是陳師爺,夤夜到此何事?」陳松道:「爾家大爺睡去也未?
」管門的應道:「尚未睡呢,還在書房看書。」
陳松道:「爾將門閉了,快些進去通報,說我有緊急事要見。」
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李榮春道:「快請他進來。」管門的走出來
道:「大爺有請。」陳松連忙走進,來到書房道:「李兄,不好了。」李榮春
問道:「陳兄為何如此慌張?請坐下說話。」陳松道:「李兄爾不曉得,那花
錦章奏了一本,說爾與蟠蛇山大盜串通謀反,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方
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現在私衙飲酒,酒若飲完便來擒爾。我跳牆而出前來通
報,快些急走。」李榮春笑道:「不必著忙,真的真假的假,怕他何事?若走
不是好漢,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陳松道:「此是奸臣陷害,不可看輕的
事。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爾卻全然不在心上。」李榮春道:「爾難道不
曉我的性情麼?死不怕,生不貪,禍福由天,奸臣陷害我還嫌遲,早已知他要
來害我的。」陳松道:「不是如此說,爾若有差遲,令堂夫人靠著誰來?」李
榮春道:「我自有道理。」
那三元、來貴二人聽了此言,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李夫人聽了此言心
中大怒,罵道:「花錦章,爾這狗男女!老奸賊!聽信兒子讒言,誣害我兒為
盜黨,全然不念同鄉之情。如此害人,良心何在?」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
的哭。施碧霞聞言大怒,大罵奸賊不休,又道:「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為何
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施碧霞如何曉
得?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京報》來看,所以蟠蛇山
大盜童孝貞、施必顯、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已有報到李府,是
以李府人人曉得。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今日果然有是事,恨著哥哥不該
在蟠蛇山落草,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公報私仇,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
這卻如何做得?叫聲:「母親、嫂嫂不必愁悶,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
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也好與
母親出此怨氣。」李夫人道:「胡說,這個如何使得?殺了欽差非是小可,害
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施
碧霞道:「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李夫人道:「爾這句
話到說得有些意思,待我叫我兒來問,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遂叫丫
頭:「快去叫大爺進來。」丫頭領命,連忙來到書房道:「大爺,夫人請爾進
去。」李榮春立起身道:「陳兄請寬坐,我進去就來。」陳松道:「請便。」
李榮春來到內廳,叫聲母親,李夫人應道:「我兒啊,如今花錦章這奸賊
要害爾,說兒是賊黨,聖上差官前來拿問,爾卻如何主意?快些說與為娘的曉
得。」李榮春道:「母親啊,雖然奸賊弄權,只是聖旨如何違拗?我家祖公數
代俱受皇恩,皆食朝廷俸祿,未曾報效,就是朝廷要斬孩兒,孩兒情願將首級
獻上,況且未必就斬,尚要審問,那時真假自然辨出。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
笑,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淡氏大娘眼淚
汪汪,叫聲:「官人,不是如此說的,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如何容爾分辯?
必要將爾害死方休。爾不可執一己之見,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事不三
思終有悔,到那時後悔就遲了。」施碧霞道:「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害哥哥
受賊黨之名。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與我哥哥說明此事,叫他起人馬殺上
長安,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又與我爹爹報仇,豈不是好?」李榮春道
:「賢妹為何說出此言?真不中聽。若是如此做去,豈不弄假成真麼?
我自有道理,爾們不必多言。」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
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李榮春只是不聽,這些家人七嘴八舌
,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老烏龜,罵個不休,一家紛紛大亂。忽見管門的如
飛似的走進。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榮春甘心待戮 李國華置席謝恩
話說管門的如飛一般走進書房報道:「大爺不好了,欽差大人同了府縣官
員帶了兵馬將前後門團團圍住,要捉大爺。」
李榮春道:「唗!老狗才,些小之事如此大驚小怪,快去開正門,待我出
來迎接。」管門的道:「大爺啊!要想定主意啊!」
李榮春道:「我自有主意,爾快快去開門。」遂換了解元衣巾。
那三元、來貴二人扯住衣裙跪下叫道:「大爺啊!千萬不可出去。」李榮
春道:「爾這狗才,誰要爾多言?是非曲直有我在此,誰要爾們拖拖扯扯,成
何景象?」遂頓脫三元、來貴的手,一直走出大廳。爾道欽差前來捉拿犯人就
該隨到隨時捉拿,為何留住私衙飲酒耽擱時候?因恐日裡去拿反被李榮春知風
逃走,故此挨到更深時候悄悄而來。管門家人將大門開了,欽差並文武官員來
到大堂坐著道:「叫李芳出來見我。」那李榮春已走出來大堂,說道:「欽差
大人,我李芳有罪自然應該拿究,只須父母官委一位來足矣,何必大人親臨?
且請後面飲酒。」高文傑道:「誰要吃爾的酒?」回頭問知府道:「這個就是
犯人李芳麼?」知府道:「正是他。」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左右答
應一聲,將李榮春衣巾剝下,上了刑具。那江都縣忙走上前將眼色亂丟,似乎
說他愛財,欲要李榮春行賄免罪。李榮春已知其意,大笑道:「欽差大人到來
,本該不受人情才是,雖有金銀卻送不得,若送他時豈不被人笑說行賄世情?
等待無事回來,那時備些薄禮相送。」高文傑聽了大怒道:「好個賊黨李芳。
」叫左右:「將刑具緊緊收錮,帶回府去。」那三元、來貴連忙走進報與夫人
曉得,夫人聽了又急又苦,只得吩咐三元、來貴:「拿了銀子隨大爺去衙門上
下使用,大爺才不致受苦。」三元、來貴領命而去。那陳松見李榮春被欽差拿
去,自己悄悄走出李府,來到外面想道:「李大爺果然是個好漢,不怕死的人
。今已被他拿去了,我如今怎麼好?如此夜深怎能再跳過牆去?不如且在外面
打聽李大爺的消息便了。」
且說高文傑將李榮春交與揚州府收管,自己又去拿田大修。
再說這些百姓見李榮春被欽差拿去收在揚州府監內,個個不平,人人不願
。有一個年紀老的為頭,招這些人在土地廟計議此事道:「爾們眾人都有受過
李榮春的恩,今日李大爺被奸賊陷為賊黨,若審起來必要受刑,若受不起刑法
認了此事,不但要斬首的,連家眷也難保無事。我們平日受李大爺恩惠,今日
見他遭此冤屈,必要用個計策救他才算知恩報恩。」內中有姓張名能說道:「
今夜我們去放火燒監,他們必然救火要緊,待他忙亂之時,我們打進去救了李
大爺出來,豈不妙哉?」那個老人叫做王德,說道:「這斷使不得,放火燒監
我們都是死的,這個計不妙。」又一個說道:「不如我們伏在要路,等李大爺
起解我們搶了就走,投蟠蛇山去做賊。」王德道:「放爾娘的屁,若如此豈不
害李大爺是真賊黨了?」又一個道:「爾們說的俱不正道,只要我們寫一張連
名保狀到府縣衙門去保出李大爺來。」王德道:「爾在此說夢話麼?奉聖旨拿
的犯人府縣怎做得主?我想此事皆花錦章這個老奸賊害的,我們如今打到花家
去,將花家打得落花流水,先與大爺出個恨氣,然後見機而行便了。」
眾人道:「不錯,還是王老伯說得是。」眾人立起身就要走,王德道:「
且慢,如此去怎麼打得進去?待我先去騙他開門,爾們隨我後面,見我進去爾
們即時亦擁打進去才能有濟。」眾人道:「到底是爾老人家有見識。」遂隨了
王德後面而來。
王德來到花府門口,見大門並耳門俱是閉的,遂舉手打耳門。那管門的見
有人打門遂來開門,王德見門開了用手望後一招,遂走進耳門。那管門的問道
:「爾是何人,到我家何事?」
王德道:「特來與李大爺出氣。」說聲未完,只見眾人一哄走進,喝喊一
聲,一齊動手,見物就打。那管門的吃了一驚,望內便走,這些家人見人圍了
許多進來亂打,眾家人不知何事,卻不敢上前來問,就是門口經過的人見他們
為李大爺打不平,個個歡喜,也各進來幫打,越打人越多,這些家人婦女見人
越打越多一直打進內堂來,驚得望內亂跑亂走。那紅花正在小姐靈幃,忽見眾
人亂走進來,不知何故,問道:「爾們為何如此驚忙,亂走進來?」眾人道:
「不知何故這些百姓打上門來,我們怕了只得走進來。」紅花聽了連忙走出內
廳,只見數百餘人紛紛亂打亂喊,紅花大聲喝道:「爾們何故打上門來?少爺
又不在家,家中無主,勸爾們差不多些罷了。」眾人道:「爾這賤人還敢出來
說話,爾家花子能父子同惡相濟謀害李榮春大爺,欽差將李大爺拿去收在府監
,我們不願,來與李大爺報仇,就打爾一家也不為過。」紅花聽了吃了一驚,
問道:「列位住口,李大爺幾時拿去的?」眾人道,「昨夜拿去的。」紅花叫
聲:「不好了。」回身就走,連忙出了後門要到李家而去。
且說總管見人越打越多,勸又勸不來,只得走去見府縣官將前情說了一遍
,求老爺做主禁住他們。知府聽說此事,連忙帶了衙役打道來到花府來問道:
「爾們何事將花府打得如此模樣?」眾人見知府來到只得住手,大聲叫道:「
老爺救命呵!」
知府道:「爾們聚眾喊打猶如強盜一般,怎麼反稱救命?」眾人道:「只
為李榮春是個好人,揚州一郡誰人不曉得他是濟困扶危的小孟嘗君?那個不受
他的恩惠?如今被著花家陷他為賊黨,我們人人不平、個個不願,所以打上花
門出口怨氣。伏乞老爺作主。」知府想道:「到虧他們有此義氣,但是他們乃
亡命之徒,不便拿捉,況且人有三百多名,如何辦得許多?不免將言語宣化他
們便了。」遂對眾人說道:「那李榮春乃是奉旨捉拿的欽犯,又是他自己情願
出頭的,況且尚未審問,且待審時若是假的自然無事,與花府什麼相干?」眾
人道:「這是花家父子同謀害他的。」知府道:「此乃聖旨,不干花府之事,
爾們休得胡鬧,聚眾成群,白日打家,律有明條,若辦起罪來不但爾們死罪,
而且累及地方官也有罪,爾們不可自取罪狀。」
眾人道:「我們情願死的。」知府道:「此言差矣,自古道螻蟻尚且貪生
,為人豈不惜命?爾眾人就死了,能救得李榮春無事也罷了,只是死了一萬個
也救他不來,何苦自傷其命?爾們既為李大爺之事可稱知恩的人,但他自有本
府本縣照管周全,無用爾等這般做作。各人回去安分生業罷,若再如此,本府
定要嚴辦,那時不但爾們有罪,連地方官的紗帽料也難保,爾們聽本府的話散
回的好。」眾人道:「老爺既如此吩咐,小人們焉敢不聽,只是李大爺全望老
爺周全的。」知府道:「這個自然。」眾人才自散去。總管隨即叩謝知府,知
府也就回去。可憐一個相府門風被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坍的坍、毀的毀,不計
其數。花興這狗奴才生成一片奸惡的心腸,不顧眾人之命,連忙打點起身去見
欽差邱大人,只說李榮春的黨類五百餘猛打到我家搶劫,一盡搶去,這一次事
情一發弄得大了。
且說紅花來到李府,走進內堂拜見夫人道:「此事又是我家太師聽了少爺
之言來害大爺,奴家心中不忍,要去看看大爺。」李夫人道:「爾去恐不便。
」紅花道:「不妨的。」遂一直要去見李大爺,一路走來不表。
且說這揚州府司獄姓李名國華,父親在日曾做過宛平縣知縣,因開空國庫
,收禁天牢,全仗李榮春父親代他彌補才復舊職,所以李國華在揚州做了四年
獄官,一年四季皆備禮物送到李府孝敬李夫人。今日忽見發下李榮春來,吃了
一驚,一夜想到天明,想不出一個計策來救,因他是個欽犯,難以相救,李奶
奶道:「爾有多大的官,怎能救得他來?只好備一桌酒請他,表我們一點心就
是。」李國華道:「爾說得是。」遂吩咐備酒伺候,悄悄將李榮春刑具開了請
進內廳,見禮坐下。李國華道:「不想公子被奸賊陷為賊黨,使我一聞此事急
得肝腸寸斷,沒法可救。恨我官卑職小,不能報公子的恩。」李榮春道:「此
乃花子能的奸計,欲報私仇,故此陷我為賊黨。只是我卻不怕他,到審問時自
然明白的。」李國華道:「公子與花子能有何私仇?乞道其詳。」李榮春遂將
前情說了一遍。李國華聽了心中大怒,道:「公子爾一片好心,卻被奸賊如此
陷害,真正可恨。」忽見屏風後走出一人,高聲大叫道:「反了,反了!花錦
章這老奸賊如此無禮,待我趕到京中拿住這老烏龜一刀兩段,才出我胸中之氣
。」李榮春聞言到吃一驚,問道:「先生,此位何人,如此英雄?」李國華道
:「乃是小兒,名喚元宰,甚是莽撞。」罵聲:「畜生,休得無禮,快來見禮
。」李榮春立起身來與元宰見了禮坐下。李元宰道:「公子不必憂悶,待我趕
到京中殺了這老奸賊,問他可敢害人麼?」李榮春道:「不必如此,生死由天
,到審問時我自有道理。」李國華又罵道:「小畜生,不要呆頭呆腦呆出事來
。」李元宰道:「爹爹如此膽小,到老也不過仍是一個司獄官罷了。」只見家
人將酒席掃上,李國華道:「公子遭難在此,我不能相救,只是備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而已。」李榮春道:「多蒙厚意,使我何以充當?」三人坐下飲酒。
忽見家人報道:「禁子來說有個年少女子自稱王翠兒要來見李大爺,禁子
不敢私自定奪,特來通報。」李國華道:「公子,可有這個人麼?」李榮春道
:「他乃義婢紅花。」李元宰道:「既是義婢紅花,快去放他進來。」家人領
命而去。不一會時只見紅花走進,李榮春立起身來道:「恩姐,我在此並無甚
事,爾為何出頭露面而來?」紅花道:「我如何曉得大爺受此屈禍?只因眾百
姓打上花門而來我才曉得。」李榮春問道:「那百姓如何打上花門?」紅花道
:「那些百姓道我家少爺用計陷害大爺,所以聚眾打上花門來與大爺報仇。」
李榮春聞說,叫聲:「不好了,誰要他們如此多事?看來事情弄的大了。」
紅花道:「大爺,此事非同小可,賊黨二字卻是當不起的,還恐性命難保
,叫夫人靠著誰人?豈不誤了大娘的青春?」李榮春答道:「恩姐太小心了,
我是不怕死不貪生的好漢,豈怕奸臣害我?我若是怕他害我時我早已逃去了,
不〔會〕到此時尚在此處。爾乃女子,排不得事,解不得危,不必掛心。爾速
回去解勸夫人不必憂悶,我是不妨的。」紅花又與李國華父子見過了禮。
李元宰見紅花雖無天姿國色卻有十分丰韻,可惜做了人家丫頭,只是照依
我面貌配他也不辱沒了他。想定主意立起身就走進裡面來,叫聲:「母親,孩
兒有句話要說,不知母親可肯容孩兒說乎?」李奶奶道:「我兒有話但說何妨
,為娘的有甚不依?」李元宰道::外面有個紅花生得十分丰韻,孩兒意欲」
就住口不說了。李奶奶道:「為何不說?」李元宰道:「意欲留他來吃一杯酒
,他與李公子有恩情。」李奶奶道:「此乃小事,我叫丫頭請他進來便了。」
李元宰退了出去。丫頭奉了李奶奶之命來請紅花進內,李奶奶將紅花上下一看
,果然生得娟好,遂笑嘻嘻的說道:「不必如此,行過個常禮罷。」
紅花見了禮,李奶奶叫聲:「紅花請坐。」又叫廚房備酒。紅花卻想不出
這李奶奶為何如此好禮相待,就同入席。及酒吃完日已歸西,紅花謝了李奶奶
辭別欲要回去,李奶奶道:「紅花姐,若閒時可來玩耍。」紅花道:「多謝奶
奶。」來到外面又辭別李國華父於並李大爺。遂回到李府來,將拜望李大爺之
事說了一遍,李夫人道:「多謝爾,辛苦了。」紅花道:「不敢。」又別了李
夫人要回自己家中,誰知來到半路天色已晚錯走路頭,月色已上,買賣的店頭
俱關了,紅花想道:「不好了,錯走了路。欲要向人間路卻又害羞,若不去問
卻又走錯,又不知要從那條路去,如今怎麼好?也罷,再到李府去耽擱一夜便
了。」轉回身依舊路而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女弄父終成呆漢 佞殘忠激動寇心
話說紅花立在路旁,心中甚是著急,要等有人經過問明去路好回家去,誰
知遇著拐子來。這拐子姓史名文,別號一彈,乃安慶府人氏。娶妻張氏,生下
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史慶望,不幸出天花而死,女的取名史蓮姑,年已十六歲
,又生得十分美貌。為何尚未受茶?因人人說他是個拐子的女兒,名聲不好,
所以無人來與他結婚,那下等之人要來求親,史文又嫌他是下等之人無甚出色
名聲,也是不好的,是以不肯許他,所以長成至十六歲尚未許配人家。史文做
拐子又比別個的拐子不同,他因二十一歲時在天仙閣閒耍,偶然見神桌下有一
本破書,史文就拾起來一看,原來就是麻叔謀祖師的咒訣竅法,諸般法術甚多
。他也看不清楚,就拿回家細細的看,用心依法學習,習了半年有餘到學了幾
件。誰知他的妻子張氏見了心中不悅道:「學此則甚?都是傷天理沒良心的事
,學他何用?」就不許丈夫再學。史文不聽妻子言語,道:「爾們婦人家曉得
什麼?學會了不但有趣,也有穿也有吃,豈不是好?」張氏道:「爾若做了沒
天理的事,天地也不容爾,爾也不能好死,我與女兒都是無望的了。」說了就
哭,終日與丈夫啼啼哭哭的吵鬧,史文只是不聽。那日張氏見丈夫出門去了,
遂將那本書拿來用火燒了。
及至史文回來不見此書,問張氏取討原書,張氏道:「爾去問火神爺討罷
了。」史文聽說知是被他燒了,氣得亂喊亂跳,與張氏吵鬧,相打一場,也是
沒奈何他。還虧得記得幾件,是迷人的藥法,遂將藥配好藏在身邊,若遇著豔
麗女子或是美貌小官人,便將藥用指甲挑些望他身上一彈,人若被他彈著便隨
他而去,史文又帶到別處去用法解了迷藥,然後賣人。張氏見他時常拐男拐女
回來,每每勸他不可如此,一則傷天害理,二則若被人聞知,拿去送官如何是
好?史文只是不聽。誰知到了新官到任甚是嚴緊,這些不見了男女的人家都來
新知縣衙門去告,知縣隨差衙役四處查拿,三日一問、五日一比,衙役被打不
過,只得用心四處查拿。史文聞知此事甚是著急,遂同張氏並女兒蓮姑逃到揚
州,尋了一間房屋住下。來到揚州才得三日,遂備酒筵請四鄰同來吃酒,此是
揚州常禮。
這日因被一個與他一黨的朋友請去吃酒,吃到將近二更,酒已醉了,遂辭
別了朋友要回去。來到半路,影影見一個人站著,急走上前一看,卻是一個女
子,想道:「好了,買賣上門了。此處四下無人,待我問他一聲看他如何回答
。」遂叫聲問說:「爾這小娘子,為何夜靜更深獨自一人在此何事?」紅花紅
了面,沒奈何叫聲:「大叔,我是要往黃石街去的,不想走錯了路頭,故立在
此等人問路的。」史文想道:「我到此才得幾日,那裡認得什麼黃石街?如今
不用藥就可以騙他回去。」
乃道:「爾這小娘子,真正是爾的造化,我也是要到黃石街,爾可隨我順
路同去便了。」紅花想道:「男女同行卻是不便。」
乃道:「爾這位大叔指說個路逕與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不必同行。」史
文想道:「這女子到覺乖巧,既不上當,待我用藥來便了。」遂在身邊取出藥
包,解開用指甲挑了望紅花面上一彈,紅花打個寒噤,一時說不出話,只見三
面都是水,只有面前一條路,無水可行。史文用手一招,紅花身不由主就隨他
走。
來到門口,史文將門叩了三下,張氏連忙出來開門,見丈夫又帶一個女子
回來,問道:「爾又做沒天理的事了。」將門閉上,來到房中問道:「官人,
這女子那裡拐來的?」史文遂將前情說了一遍,張氏見紅花生得相貌端嚴甚然
美麗,卻是丫頭打扮,想道:「好個丫頭,可惜被我那沒天理的拐了來,想爾
諒難回去了。」史文就叫張氏道:「娘子,爾去取一杯茶來與我吃。」張氏到
後面去取茶,史文想道:「好個女子,不知可是原封貨否?不要管他,待我試
一試便知好歹。」才要動手,只見張氏取茶進入房來道:「官人,茶在此。」
史文道:「放在桌上。娘子,我有一句話與爾商量,爾是要依我的。」張氏道
:「若說有情理我自然就要依爾的。」史文笑嘻嘻的說道:「我見此女子生得
美貌,所以用藥沫迷了他來,今夜要與他成就好事,爾卻不要吃醋。」張氏聞
言啐啐了一啐,說道:「爾敢說出這樣話來?虧爾羞也不羞,老面皮無廉恥說
出這不肖的話來。我勸爾不可做這傷天滅理的事,休得敗壞人的節行。」
史文道:「我的乖乖好娘子,望爾做件好事,今夜與我同他作樂,明夜就
來與爾開心。」張氏道:「休得胡說,不必癡心迷想。」史文道:」爾當真不
肯麼?」張氏道:「就是不准爾便怎麼?」史文道:「我就殺爾這賤人,怕爾
不肯。」立起身就走往廚房要去取刀。張氏忙了,連忙走入女兒房中躲著,眼
淚汪汪不敢則聲。史丈拿了刀趕入女兒房內,史蓮姑要走來勸,見他手拿一枝
刀又不敢上前,只是叫道:「爹爹,這個使不得的。」誰知史文忽然發了瘋顛
病,跌倒在地亂叫亂跳。張氏見了道:「妙啊,此乃惡人生怪病,從來的作惡
天地不饒。」史蓮姑就拿一支門閂將史文手中的刀打落下未,張氏道:「他如
此亂叫亂跳,卻如何能得他定?」史蓮姑道:「有了。」走去將史文包拿來解
開,用指甲挑些望史文面上彈去。那史文被這藥沫一彈卻呆呆站著,也不會叫
也不會跳,張氏扶他入房睡在牀上。史蓮姑道:「為何爹爹忽然要殺母親?」
張氏道:「因他迷了這個女子回來要圖淫欲,我勸了他幾句的話,他就拿刀要
來殺我。」史蓮姑道:「既是如此,趁爹爹此時不知人事,何不放他出去?」
張氏道:「想他已被藥沫所迷,如醉如癡與爾爹爹一般,放他出去也是無益。
」史蓮姑道:「如此卻怎麼好?」張氏道:「如今只好暫且留在家中,若有人
前來尋覓即便還他,只說本是如此,我們見了留他入來,誰疑是拐來的?他還
要來謝我們。只怨爾爹爹一世,人只好如此罷,莫說不知解法,就是曉得解法
也不敢救他,若是將他救好了,我們母子性命就將難保了。」史蓮姑道:「母
親說得不錯。」幸虧史文平日拐來男女賣來的銀子累積倒有千餘金,母女二人
又做些針指,盡可過日。
且說田大修一路巡察巡到南京,將那惡棍土豪貪官污吏一概除盡,百姓人
人稱好。那日正在升堂審事,忽見中軍跪下稟道:「聖旨到。」田大修見報,
連忙吩咐備辦香案,自己走出轅門迎接聖旨,接入大堂。高文傑立在中堂道:
「聖旨到,跪聽宣讀:今有閣臣花錦章奏稱李芳與蟠蛇山大盜童孝貞、施必顯
、張順等串連一黨,書札為憑,爾田大修亦與他往來,陶天豹左道附從,虞患
無窮。除將李芳拿勘外,朕念爾田大修為官多載,正直無私,聞奏未知虛實,
有無難辯,著即拿下勘明,復旨定奪。欽哉謝恩。」田大修聽罷旨意,三呼萬
歲,兩邊侍衛將田大修冠帶剝下上了刑具。田大修大笑道:「花錦章啊花錦章
,爾果來得好利害了。我做了數年的官,與爾並無冤仇,無非殺了花秦氏,爾
就陷我為賊黨。幸虧朝廷鑒察我的為官清正,這頂紗帽還保得祝」高文傑道:
「陶天豹何在?」田大修正要開口,忽聽得大叫一聲道:「陶天豹在此。」那
陶天豹怒氣沖天,一手拿竹刺、一手拿乾坤鐧走出大堂,大聲罵道:「花錦章
爾這老賊徒,敢來害我田大人,我的田大人乃鐵面無私之官,怎麼陷為賊黨?
大人啊,爾不可做自投入籠之鳥。」
田大修兩目圓睜,大聲喝道:「陶天豹休得胡言,陷我為不忠。」又叫一
聲:「高大人,此人就是陶天豹,快快將他拿下。」
高文傑叫聲:「與我拿下了。」兩邊答應一聲上前來拿,陶天豹大喝一聲
道:「誰人敢來?」舞動乾坤鐧,兩邊侍衛那個敢上前?陶天豹就要去打高文
傑,田大修喝道:「誰敢打高大人?他是奉旨而來,爾敢無禮麼?還不束手受
綁。」陶天豹道:「這是好賊弄權,大人不要上他的當,快些與我去的好。」
田大修道:「我只知忠君,不惜性命,朝廷旨意誰敢違逆?」叫聲:「高大人
,還不將他拿下麼?」高文傑道:「左右與我快快拿下。」兩邊侍衛沒奈何,
只得上前來拿,被陶天豹將竹刺打退眾人。高文傑見了大怒,自己走下來拿,
被陶天豹將竹刺一打,仰面一翻跌倒在地。陶天豹叫道:「大人,爾不隨我去
麼?待我趕到京城殺了那好賊,才消我心中之恨。」說完駕起雲帕而去,又回
頭來叫聲:「高文傑,我將田大人交付與爾,若稍有差遲我就要與爾討人,叫
爾認得我這雙寶鐧的利害。」說完駕雲帕而去。來到半路,卻遇著師父萬花老
祖,叫道:「徒弟爾好莽撞,今日雖然拿了田大修,爾就不該毆官打役,又要
到京中去殺花錦章。不想此行要害多少人等?須等花錦章時日到了,自然叫爾
們去拿他。此時切勿妄動,隨我回山,自有道理。」
陶天豹不敢有違師父,惟以應聲唯唯,即隨萬花老祖而去不表。
且說高文傑怒氣沖天道:「反了、反了,如此無法無天麼?目無王法,敢
打欽差,這還不是賊黨,乃有何說?又駕霧騰雲而去要殺花太師,真是左道惑
眾。待我奏明聖上便了。」遂將田大修交與應天府收管,知府備酒請高文傑在
私衙飲宴。
且說邱君陛奉旨出京,一路官員迎送。那日來到南京,文武官員俱來迎接
,接入應天府,邱君陛即時傳令命中軍:「火速去揚州,立弔李榮春前來聽審
。」中軍領命而去。這裡各文武俱來送禮拜見,高文傑報稱:「陶天豹恃強抗
拒,擅打欽差,駕雲而去,不能拿祝」邱君陛道:「且等李芳到來,審了再作
道理。」不上幾日,揚州府、江都縣押解李榮春前來。邱君陛即時升了公座,
吩咐將人犯帶進。揚州府帶進李榮春,應天府帶進田大修。邱君陛先叫帶出張
環來,侍衛答應一聲,將張環拖出跪在堂下,邱君陛叫聲:「張環,爾將李榮
春並田大修與賊來往之事一一講來。」張環道:「小人因家窮苦,不能度日,
所以上山做個嘍囉。山上有三位大王,一個叫做童孝貞,一個叫做施必顯,一
個叫做張順,三人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田大修、陶天豹、李榮春三人平日與
他俱有書函往來。」邱君陛道:「只這封書是誰寄來?要與那個的?」張環道
:「是施必顯叫小人送與李榮春的,不想來到半路被花少爺攔住搜出這封書函
,遂將小人帶進京去,是故小人不能到揚州。」邱君陛道:「可有委曲在內麼
?」張環道:「並無虛言,大人若是審出虛情,小的甘當死罪。」
邱君陛叫左右:「將李芳帶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李榮春帶上堂來放
下跪著,邱君陛怒目圓睜,大聲喝問道:「李榮春,我看爾小小年紀怎麼如此
大膽?敢與強盜往來。好好據實招來,免受刑罰。」李榮春道:「大人休得聽
信讒言將我陷作盜黨,我祖居揚州,世食王祿,多行善事,並不為非,焉肯與
賊為黨?此乃花虹之計要來害我。」邱君陛道:「胡說,現有書札為憑,又有
張環活口作證,爾還敢強辯麼?」叫聲:「左右,與我將李芳夾起來。」左右
答應一聲將李芳拖倒,脫去鞋襪,將生銅夾棍套上兩邊一收,可憐李芳心如油
煎,痛不能言。邱君陛道:「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心如鐵石,視死如歸
,雖受酷刑,只是忍著不招。邱君陛道:「將他收緊了。」
兩邊答應一聲,將繩收緊。邱君陛道:「再加八十敲頭。」可憐李榮春腳
目也被敲凹了,死去了幾次又還魂來,只是不招。
邱君陛吩咐:「帶在一旁。」又叫:「帶田大修上來。」
左右答應一聲,亦隨帶田大修上來。邱君陛道:「田大人,爾祖公世代居
官,爾又代聖上巡察,怎麼不思報君之恩,敢與大盜串通一黨?實實招來。」
田大修道:「大人豈不知我的為人麼?我身居顯職,安肯與賊為黨?因我巡到
揚州拜望花虹,他有女婢紅花告花秦氏與曹通通姦,謀死花賽金,被我親身上
樓拿組夫淫婦,究出真情,即刻正法,業已拜本上奏。花虹挾此私仇,陷我與
賊為黨。」邱君陛道:「住了,爾說花虹挾仇陷爾為賊黨,不過是爾口外之談
,可曉得張環有書札為證麼?我念爾是個命臣,故爾不加刑罰,如今快些將真
情招來,我好去復旨。」田大修道:「我為官多年,豈不知國法利害?豈肯與
賊往來?這封函乃奸賊假造的,就是張環也是他的家人,使他來做對頭的。」
邱君陛冷笑道:「到辯得乾乾淨淨,那陶天豹何在?」田大修道:「那陶天豹
不伏王法,駕雲而去,那日高大人親身拿他不住,這個與我何干?」邱君陛聞
言大怒,喝道:「好個與爾何干?陶天豹乃爾的門徒,怎說無干?據施必顯函
內所言,真真是旁門左道,快些招來,免受刑罰。」田大修道:「爾不過受花
賊之托,我已將頭丟在身外不要了,爾要我屈招是萬萬不能的。」邱君陛大怒
,吩咐左右:「將田大修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田大修拖倒,脫去靴襪
將銅棍套上,兩邊一收,邱君陛問道:「爾招不招?」田大修咬定牙關,只是
不招。邱君陛吩咐左右:「將他上了腦箍。」田大修死去又還魂,任刑不招。
邱君陛道:「問李芳招也不招?」李榮春道:「邱君陛,爾受了多少金銀
,如此枉法害人?要我屈打成招是萬萬不能的。若要賄賂到也容易,我家金銀
財寶甚多,憑爾要多少我就送來與爾罷。」邱君陛聞言大怒,罵道:「爾這該
死的賊囚,敢來衝犯本部麼?爾與賊通連這且慢說,為何黨邀百姓數百餘人鳴
鑼擂鼓打劫花府?這不是謀叛卻有何說?」李榮春道:「這一發好笑,我已收
在監內,他們做的事我如何曉得?怎說是我招連的?」邱君陛冷笑道:「好個
利口能言的賊徒。」叫左右:」將他上了腦箍。」李榮春忍受酷刑,任他敲打
,只是「不招」二宇。邱君陛一時亦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二人交與府縣收監,
不許一人與他往來,府縣官領命而去。邱君陛將張環交與二府收管,自己退了
堂,悶悶不樂。
且說來貴、三元二人在外面打聽,見主人受此刑法只是不招,二人私下說
道:「大爺果然是個好漢,受此酷刑總是不招。」三元道:「此事原是招不得
的,若招了就要斬首。」來貴道:「只恐第二堂再當不起刑罰了,我們須要照
應才好。」遂到酒館買了熱酒好菜來到監門,禁子不放進去,二人將銀與他,
禁子說道:「酒飯我便代送進去,人是不能進去的。」二人沒奈何,只得將酒
飯交與禁子送進去。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
話說來貴、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
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且說邱君陛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
,沒奈他何,只得寫書一封,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
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聞李榮春不肯承招此事,想道:「此事乃是花
家要陷害他的,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
,屈打成招,性命豈不難保?我曾受過他的大恩,必須報他的恩。我今須當到
京去求母舅,他在刑部衙門辦事,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想定主意要
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也罷,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
罷。」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若說陳松
要救李榮春,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也是無奈何的擺佈,只是盡他的心
而已。
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心中想道:「雖
然頭堂不招,只恐二堂難熬酷刑,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止不住
眼淚汪汪的哭泣。施碧霞對李夫人道:「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奴
家豈可坐視不救?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
叫他來訴明此事,免得恩兄受罪。」李夫人道:「想爾哥哥為人莽撞,猶恐弄
出事來反為不美。」施碧霞道:「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平生是不
肯累人的,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淡
氏大娘道:「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
自送性命?」施碧霞道:「古人有言:一身做事一身當。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
怕死的人,嫂嫂何必如此膽怯?」李夫人道:「爾是個女子,怎好去出乖露醜
到山上去?」施碧霞道:「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何況此地到山東?
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李夫人道:「既然如此,爾去書房改裝便了。」
施碧霞來到書房,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頭戴一頂武巾,身穿一件綠綢戰
衣,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
:「有了。」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又將針線拿來縫了,穿戴打扮起來果與
男人無異,遂走出廳來。
李夫人看了一看,說道:「果然像得緊。」吩咐備馬伺候。施碧霞道:「
母親請上,女兒就此拜別。」遂拜了四拜,又與淡氏大娘拜別。李夫人叮囑道
:「爾執意要去,我也難以阻擋,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到了山上叫爾哥哥
只可婉轉來辯此冤。」施碧霞答道:「女兒遵命。」遂辭別出門,上馬而去不
提。
且說邱君陛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將書密投門上,門上將書獻上與花
太師。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想道:「如今此事如何處置?」即忙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
花錦鳳道:「施必顯在蟠蛇山猖撅,這個不是假的,又有一封書信,總要
算為憑據。陶天豹駕雲而遁,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
我在旁邊也來奏聞,說他們通連一黨,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請旨將此二賊
先除,免了國家之患。」
花錦龍道:「不要性急,且緩數日,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一發情
真事實了。」花錦章道:「二位賢弟說得有理。」
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先來見花太師,花錦章備酒款待,又差人去請花
錦龍、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叫他明白如此
如此、這般這般面奏:「老夫保爾官上加官。」高文傑依允,酒席飲完,辭謝
而去。
次日五更三點,皇上登殿,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黃門官啟奏道:「今
有高指揮回朝復旨,現在午門外伺候,請旨定奪。」皇上傳旨:「宣高文傑見
駕。」高文傑領旨上殿,拜舞山呼已畢,奏道:「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
出京,捉拿李榮春、田大修、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不想拿下李榮春,卻被
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
旨、扯毀詔書,將臣打倒,辱罵不堪。田大修已拿下交與邱君陛勘審外,尚有
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非臣不能拿他,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
。」花錦章出班奏道:「臣想李榮春、田大修與賊寇通連,獲有書札為憑,蒙
恩欽恤田大修,特差邱君陛往勘,當是時拿下。李榮春民多喧哄,而田大修膽
敢抗旨毀詔,罪不容誅,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均各有證有憑,此等巨惡實為
國家之大患。」那花錦鳳、花錦龍亦出班奏道:「臣啟陛下,田大修與李芳通
同賊寇,勢甚猖狂,膽恣橫凶扯毀詔書,毆辱欽差,即是欺君。自古有言:不
除稂萎,難種嘉禾﹔欲斬盜源,先除盜黨。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田大修二人
速行正法,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仍為盛世之良
民。一面嚴拿陶天豹,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伏乞聖裁。」皇上傳旨:「依
卿所奏,即著高文傑齎旨速行,命邱君陛督斬回奏,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
捕,務在盡除賊黨,毋遺國患。」二人領旨,駕退回宮,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
府而去,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
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爾這人好大膽,敢
來我山下探望麼?」施碧霞道:「爾去通報施大王,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
要來見他。」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連忙走上山來到忠義廳跪下稟道:「
啟二大王的知,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是揚州來的,說與大王是朋友,叫小
的特來通報。」施必顯聽了道:「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
即時吩咐大開寨門,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施必顯大叫一聲:「李榮春
我的恩賢弟,爾來了麼?」施碧霞叫聲:「哥哥,是我在此。」施必顯定睛一
看,叫聲:「噯呀!原來是小妹到了,為何這般打扮?快請上山說個明白。」
四人一同上山,來到忠義廳,各見了禮坐下。施必顯問道:「小妹,這二人爾
可認得麼?」施碧霞道:「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施必顯道:「這位姓童名
孝貞,號索命無常,乃我結拜之兄﹔這位姓張名順,號半節蜈蚣,是我結義之
弟,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施碧霞道:「爾到快活,別人卻去受
苦。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卻來在此
落草?」
必顯道:「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有時打劫客商,每嘗出去擄搶民
財,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日日開懷痛飲,爾道好麼?」施碧霞道:「有這樣
的好處麼?咳!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大仇不報,不掛在心,連受恩的朋友
竟亦丟開了,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性命難保?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
累他的。」施必顯聞言叫聲:「住了,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快快
說來。」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
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大罵:「花子能,爾這狗男女,無故謀
害好人,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
童孝貞道:「不要性急,慢慢計議而行,若是去殺了花賊,不但不能救得
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施必顯道:「這
句話說得不錯,只是如今怎樣的好?」施碧霞道:「我此來非為別事,因此事
乃哥哥起的,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自然他們就無事了。」施必顯道:「
爾在此說呆話麼?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我去焉能救得他?猶如蟲飛
入蜘蛛網,自去尋死。」施碧霞道:「如此怕死,做什麼好漢?」施必顯道:
「非我貪生怕死,還要打算才救得來。」張順道:「什麼打算?我們三人即到
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看其能奪回去麼?」施必顯道:「不錯,正是這樣主
見。」童孝貞道:「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豈不害了他的家眷?」
張順道:「不妨,這也容易,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將
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那時還怕怎樣的?」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張順道
:「大哥何故呆呆的想,莫非不敢去麼?」童孝貞道:「怎說我不敢去?只是
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況且各處城門甚多,豈不被人盤問?」
張順道:「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到那時再作道理。」施碧霞
道:「只是凡事要小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可執性而為。」施必顯道:
「我們曉得,爾在此看守山寨,須要小心照顧。」施碧霞道:「我自然曉得照
顧。」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又撥
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八名嘍囉領命而去。
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暗藏器械
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
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
大王。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只見有個涼亭,涼亭內有個義井,旁邊有個
瓦罐,三人走來亭內吃水,正吃得爽快,忽聽得馬鈴響。張順抬頭一看,見那
邊來了八九個人,俱是騎馬的,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施必顯道:「這個人
必是京中來的,那黃包袱必是聖旨。」張順道:「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說
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爾們且慢些走,留下買路錢來。」高文傑聽了大怒道
:「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爾敢攔我去路麼?
」張順道:「住了,爾往南京有何公幹?說得明白放爾過去。」高文傑就說:
「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爾們乃問則甚?」
施必顯聞言喊道:「爾這狗官,休想過去了。」用手一拉拉下馬來。高文
傑大怒,罵道:「爾這該死的狗頭,敢如此大膽麼?」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
來救主人,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又將高文傑一刀
砍為兩段,九個人變作十八段。將黃包解開一看,大笑道:「若是錯過此處,
要救田大修、李榮春是不能的,徒費我的心機麼?」張順道:「虧了此井才能
救得田、李二人,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如何能救田、李二人?如今
將這些物事送他罷。」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此時已是夜深時候
,並無人看見,三人趁著月色趕路,這且不言。
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所以星夜趕路,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誰知
忽然雲起將月迷了,黑暗之間不能行路,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只得歇
歇再走。四處一看並無坐處,影影見有個墳墓,四圍似乎有欄杆,想道:「不
免在此借坐便了。」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通了名姓,道:「我國走路辛苦,
在此借坐一回,望乞莫怪。」遂坐在一塊石板上,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
人,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真正可歎。但我此去
到京求母舅,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那陳松也是呆想,不想花錦章勢惡滔
天誰人不怕,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
榮春。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不知以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陳松遇鬼會英雄 湯隆搬家歸寨主
話說陳松坐在石板上呆呆的想,兩手敲腿,忽聞得吱吱的叫,抬頭四處一
看,只見那邊有個矮鬼。此時月色朦朧,吃了一驚道:「不好了,有有有鬼來
了。」連忙立起身,大聲喝道:「爾這野鬼不必在此怕我,我陳松是不怕鬼的
,還不快些迴避麼?」那鬼似不聽見,甚是不怕人,任爾叫喝只是不聽,慢慢
的走近身來。陳松到退了兩步道:「還不退去,來此則甚?」
說聲未了,又聽得那邊吱吱的又叫起來,陳松復回頭一看,又見一個雪白
的高鬼,足足有一丈五六尺多長,擺也擺擺將近來。
陳松此時心中著忙道:「敢是我今夜命該盡了麼?不然何為長的鬼、矮的
鬼都來了?」遍身寒戰,毛髮倒豎,要走也走不動,心驚腳軟一跤跌倒在地。
那長鬼與矮鬼笑了一聲,忽然二個鬼變出三個人來,一個將陳松挾領抓住就剝
衣服,一個身邊取出白雪的刀來。陳松見了驚得魂不附體,大聲叫道:「救命
啊!」
一個就取出棍來晃一晃道:「爾敢叫麼?若再高聲就打死爾這狗奴才。」
說尚未了,只聽得後面有人喝道:「誰敢在此謀財害命?」三人急回頭一看,
卻好被那人將他一人一刀三人砍做六段。
爾說那殺人的是誰?原來就是施必顯等三人,正走到此處,聽得有人大聲
喊叫救命,上前看時卻見三人圍著打劫,遂拔出刀來一一殺了。扶起陳松,遂
即問他道:「爾這人為何黑夜行路被人打劫?」陳松道:「恩人啊!我因要救
李榮春,所以日夜趕路要進京城,不想到此被劫。多虧恩人相救。」張順問道
:「爾叫甚麼名字,與李榮春是何親故,因何要去救他?」陳松答道:「我姓
陳名松,曾受過李榮春的大恩,薦我在揚州府為幕賓,是以要趕進京城救他性
命。請問三位好漢尊姓大名?」
張順三人各將名姓說明,更言:「爾今不必進京,且到幡蛇山住下,等我
們救了李大爺回來再作道理。」陳松道:「只是我認不得路逕,如何去得?」
正說之間,忽見山後跳出一人,大聲叫道:「我認得皤蛇山的去路。」張
順等四人吃了一驚,定睛一看,見這人面貌猶如尉遲恭一般,體胖身長,甚是
英雄。張順問道:「爾這個人叫甚名字?為何躲閃在此,忽跳出來說認得幡蛇
山的路?」那人道:「我姓湯名隆,號扒山虎,因聽得此位陳相公說不認得路
逕,我故出來要帶他去。」張順道:「爾敢是與這三個死屍一黨麼?」湯隆道
:「不瞞好漢說,他與我雖然同住一處,只是所作不同,我只在此就近做些無
本錢的買賣,常思要來投奔好漢,奈無進路,今夜有緣幸得相遇,」我願與陳
松同去。」
張順道:「爾家中還有何人?」湯隆道「惟有一妻一妹而已。」
施必顯想道:「我妹子在山上沒有一個丫頭使女使用,不免叫他們一起上
山罷。」遂與童張二人計議,張順道:「如此甚好。
」遂說與湯隆曉得,湯隆甚是歡喜。那陳松甚是驚疑,暗想道:「童孝貞
等三人乃是莽撞之人,並不疑他有甚歹意,爾殺他三人他沒奈爾何,騙我到前
面去一刀殺了,那時向誰討命?」湯隆叫道:「陳相公不必遲疑,快快同我回
家去耽擱一夜,明日好走路。」施必顯對陳松道:「我們要趕路到南京去,爾
同湯隆前去便了。」說完就走。湯隆道:「好漢請轉。」張順問道:「還有什
麼話說麼?」湯隆道:「我此去與施小姐兩不相識,倘他不肯收留如何是好?
必須與我們一個憑據去才好。」施必顯道:「不必憑據,爾去只須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得明白自然收留。」說完如飛的去了。湯隆叫道:「陳相公快些拿
起銀包隨我回去罷。」陳松此時沒奈何,硬了頭皮拿起包袱,穿好衣巾隨了湯
隆而行。
走不多路,已來到了一間人家,湯隆打門,只聞裡面答應一聲說:「來了
。」將門一開,叫聲:「官人回來了麼?」湯隆道:「我今夜到有個好買賣,
就是爾的時運到了。」陳松聽了此言驚得面如上色,叫聲「不好了」,回身就
走。湯麓趕上前,將陳松挾領一把抓住道:「爾要走那裡去?」捉回家來,叫
妻子閉了門,將陳松放下道:「我雖做此買賣,也是沒奈何的,如今與爾是朋
友了,豈有害爾的?何故如此懼怕?」方氏道:「官人,爾方才說得不明不白
,怪不得他驚走了。」湯隆道:「果然是我說得不明白。」遂叫方氏:「與陳
松見了禮,免得明日同行不便。」方氏與陳松見了禮,遂叫湯隆進內問明來歷
,即備了酒飯出來款待陳松。陳松此時才放心,想道:「如今是不妨了,只是
我到山上去文質彬彬叫我幹那一件?如若不去又無處安身,卻如何是好?也罷
,到那裡再作道理便了。」
吃完酒飯,湯隆就在廳上打個牀鋪與陳松安睡。那方氏又去向姑娘名叫勝
姑說知此情,那湯勝姑雖是獵戶之女,生成甚是俊俏,更兼力大無窮,每日在
家無事消遣習成兩柄雙刀,閒時舞弄甚然精熟,只有一雙金蓮與男人差不多的
。日日出外打獵,若有人惹著他一句話便打得他半死,所以人人懼怕,叫他做
「女光棍」,亦有人叫他做「女強盜」,所以長成至十八歲尚未配親。姑嫂二
人都是一般勇猛。此時聽嫂嫂說了此話,心中大喜道:「人人叫我女強盜,如
今真正要去做強盜了。」
一夜晚景已過。次日天明,方氏到廚下收拾酒飯,那湯隆叫湯勝姑:「與
陳松見了禮,路上好同行走。」湯勝姑遂與陳松見了禮,回進房中收拾細軟物
件。方氏將酒飯搬出來,各各吃完,即將些細軟物件打了三個包袱,粗重之物
丟下不要。四人出來將門鎖了,一路望皤蛇山而去。爾道這三個假鬼的雖與湯
隆結黨卻另住一處,每至更深夜靜時候即到墳墓兩旁埋伏,若有人從此經過便
出來唬將嚇倒打劫,金銀作四股均分。那知這晚該死,被張順等三人殺了。那
湯氯與他均是一黨,為何不出來卻去躲著哩?他因恐這三人劫不過手便好出來
幫助,誰知此夜卻救不及了。
且說湯隆等四人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非只一日,已到幡蛇山下。只
見一聲鑼響,走出一支唆羅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人留下買路錢來放爾
過去。」湯隆笑道:「我不過是要上山去的,難道也要買路錢麼?」眾嘍囉道
:「爾等是何人?要上山去何干?」湯隆道:「我們是爾三位大王差我來的,
有緊急的事要見女大王,快些與我同上去。」眾嘍囉道:「且慢,待我先去通
報然後來帶爾上去。」說完回身上山,來到忠義堂跪下稟道:「啟稟女大王,
山下來了二男二女,說是三位大王差他來的,有緊急之事要來面稟。」施碧霞
道:「傳他進來。」嘍囉得令,來到山下叫道:「女大王叫爾們進去,須要小
心。」湯隆道:「曉得。」四人隨嘍囉上山來到忠義廳外面,湯隆先隨嘍囉進
廳,跪下道:「女大王在上,湯隆叩見。」施碧霞道:「爾且起來說話,到此
何事?」湯隆遂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施碧霞道:「請陳相公進見。」陳松見
請,遂走進廳來低了頭作了一個揖,施碧霞以賓主之禮相待,回了禮請他坐下
,陳松也將前事說了一遍。施碧霞道
Douglas McKay, Secretary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Glenn L. Emmons, Commissioner
BRANCH OF EDUCATION
Hildegard Thompson, Chief
Single Copy Price 20 cents
Phoenix Indian School Print Shop
Phoenix, Arizona
Third Edition 5,000 copies--September 1953
Little Man's family
diné yázhí ba'áłchíní
pre-primer
[Illustration]
by
J. B. Enochs
illustrated by
Gerald Nailor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FOREWORD
This pre-primer is one of three little books based on material prepared
by J. B. Enochs, who once taught in the sanitarium school at Kayenta. It
deals entirely with typical life experiences among the Navaho, the
largest Indian tribe in the United States, numbering approximately
65,000. Nine out of ten Navahos do not speak English, and the tribe has
never had a written language.
Missionaries and scientists for many years have had alphabets with which
to record this difficult language. But these alphabets have usually
included letters not found in English, and have been peppered with
diacritical marks to indicate inflection, tonal change and nasalization.
Thus they proved too complicated for popular use. Space does not permit
mention of many who have worked with the Navaho language. Finally Dr.
John Harrington,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nd Mr. Oliver LaFarge,
author and linguist, collaborated to produce a simplified alphabet which
might be written with an ordinary typewriter. Mr. Robert W. Young,
associate of Dr. Harrington, experimentally recorded a great deal of
material in this new alphabet. The Navaho portions of later pamphlets in
this bi-lingual series are the joint work of Harrington and Young.
=Little Man's Family= has been expressed in Navaho, using the
Harrington-LaFarge alphabet, by Willetto Antonio, a Navaho teacher on
the reservation, and Dr. Edward Kennard, formerly a specialist in Indian
languages for the Indian Service. Both the recording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in these books have been checked by Chic Sandoval, Howard
Gorman, and Adolph Bitanny, Navaho interpreters, and by Robert W. Young.
Back pages contain an explanation of the sound values represented by the
alphabet, and the indications of tonal change and nasalization which are
used.
These bi-lingual texts are an attempt to speed up Indi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life. Use of native languages to speed up acquisition of
English in Federal schools is a new departure in Indian policy, which
has proved very successful.
The type used for these books has been selected because of its
similarity in design to the alphabet used for manuscript writing. In the
primers, only proper names and the pronoun I have to be capitalized, so
as to further minimize the new learnings often encountered by the
primary child when faced with several different alphabets at once.
Willard W. Beatty
Revised February 1950
[Illustration]
I am a Navaho boy.
diné 'ashkii nishłį́.
[Illustration]
my mother
shimá
[Illustration]
my father
shizhé'é
[Illustration]
my baby brother
'awéé' sitsilí
[Illustration]
our baby's cradle
nihe'awéé' bits'áál
[Illustration]
my big sister
shádí
[Illustration]
my little sister
shideezhí
[Illustration]
our hogan
nihighan
[Illustration]
my father made our hogan
shizhé'é nihighan 'áyiilaa.
[Illustration]
our sweathouse
nihitáchééh
[Illustration]
the soapweed plant
tsá'ászi'
[Illustration]
we wash our hair
nihitsii' tanínádeiigis
[Illustration]
our sheep
nihidibé
[Illustration]
our goats
nihitł'ízí
[Illustration]
our corral
nihidibé bighan
[Illustration]
our horses
nihilį́į́'
[Illustration]
our wagon
nihitsinaabąąs
[Illustration]
my mother's saddle
shimá bilį́į́' biyéél
[Illustration]
my father's saddle
shizhé'é bilį́į́' biyéél
[Illustration]
my little spotted pony
shilé'éyázhí łikizh
[Illustration]
my black dog
shilééchąąshzhiin
[Illustration]
my mother's loom
shimá bidah'iistł'ǫ́
[Illustration]
my mother cleans the wool.
shimá 'aghaa' hasht'eilééh
[Illustration]
my mother cards the wool.
shimá 'aghaa' hanéiniłcha'.
[Illustration]
my mother spins the wool
shimá 'aghaa' hanéiniłdis.
[Illustration]
my mother weaves a rug.
shimá diyogí yitł'ó.
[Illustration]
my sisters help my mother.
shádí dóó shideezhí shimá yíká 'anáhi'nilchééh.
[Illustration]
we sell the rug.
diyogí ninádahiilnih.
THE NAVAHO ALPHABET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Navaho alphabet and its use
should prove helpful to one familiar with the English language.
VOWELS
The vowels have continental values. They are as follows, the first
example being a Navaho word, the second the closest approximation to the
sound in an English word:
a gad (juniper) father
e ké (shoe) met
i sis (belt) or as in sit or as in
dishááh (I'm starting) pique
o doo (not) note
Vowels may be either long or short in duration, the long vowel being
indicated by a doubling of the letter. This never affects the quality of
the vowel, except that long i is always pronounced as in pique.
sis (belt) is short siziiz (my belt) is long
Vowels with a hook beneath the letter are nasalized. That is, some of
the breath passes through the nose in their production. After n, all
vowels are nasalized and are not marked.
tsinaabąąs (wagon)
jį́ (day)
kǫ́ǫ́ (here)
DIPHTHONGS
The diphthongs are as follows:
ai hai (winter) aisle
ei séí (sand) weigh
oi 'ayóí (very) Joey
The diphthongs oi (as in Joey) will frequently be heard as ui (as in
dewy) in certain sections of the reservation. However, since the related
word ayóó is always of one value, this spelling has been standardized.
In a similar way, the diphthongs ei and ai are not universally
distinguished. For example, the word for sand, séí will be pronounced
sáí by some Navahos.
CONSONANTS
The consonants are as follows:
b bá (for him) like p in spot
d díí (this) like t in stop
g gah (rabbit) like k in sky
These sounds are not truly voiced as are the sounds represented by these
letters in English, but are like the wholly unaspirated p, t, and k in
the English words given as examples.
t tó (water) tea
k ké (shoe) kit
The t and k in Navaho are much more heavily aspirated than in the
English words given in the examples, so that the aspiration has a harsh
fricative quality.
' glottal stop yá'át'ééh (it is good) unh unh, oh oh
In the American colloquial negative unh unh, and in the exclamatory
expression oh oh, the glottal stop precedes the u and the o
respectively. Or, in actual speec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Johnny earns
and Johnny yearns, is that the former has a glottal closure between the
two words.
t' yá'át'ééh (it is good)
This letter represents the sound produced by the almost simultaneous
release of the breath from the closure formed by the tip of the tongue
and the teeth and the glottal closure described previously.
k' k'ad (now)
This sound is produced in the same way as the t', except that the k
closure is formed by the back of the tongue and the soft palate.
m mósí (cat) man
n naadą́ą́' (corn) no
s sis (belt) so
sh shash (bear) she
z zas (snow) zebra
zh 'ázhi' (name) azure
l laanaa (would that) let
ł łid (smoke)
This sound is made with the tongue in exactly the same position as in
the ordinary l, but the voice box or larynx does not func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l's is the same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 and p, d and t, or s and z. If one attempts to pronounce th as in
thin followed by l without an intervening vowel a ł is produced. Thus
athłete.
h háadi (where) hot
In Navaho there are two sounds represented by the letter h. The
difference is in the intensity or fricativeness. Where h is the first
letter in a syllable it is by some pronounced like the ch of German.
This harsh pronunciation is the older, bu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Navahos tends to pronounce the sound much as in English.
gh hooghan (hogan)
This is the voiced equivalent of the harshly pronounced variety of h,
the functioning of the voice being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ounds.
j jádí (antelope) jug
This sound is an unaspirated ch, just as d and g represent unaspirated t
and k.
ch chizh (wood) church
ch' ch'il (plant)
This sound is produced in a fashion similar to the t' and k', but with
the release of the breath from the ch position and from the glottal
closure.
dz dził (mountain) adze
ts tsa (awl) hats
ts occurs in the beginning and middle of Navaho words, but only in final
position in English.
ts' ts'in (bone)
This sound is similar to ch', except for the tongue position, and
involves the release of the breath from the glottal closure in the same
way as the other glottalized sounds.
dl beeldléí (blanket)
The dl is produced as one sound, as gl is in the word glow.
tł tła (grease)
This sound is pronounced as unvoiced dl.
tł tł'ízí (goat)
This sound involves the release of the breath from the t position of the
tongue tip and teeth, from the contact of the sides of the tongue inside
the back teeth (normal l position), and the glottal closure. It has a
marked explosive quality. The sound is produced as a unit, as in the gl
of glow, cited above.
y yá (sky) you
w 'awéé' (baby) work
PALATALIZATION AND LABIALIZATION
It is to be noted that the sounds represented by g, t, k, h, gh, and ch,
ts (when heavily aspirated) are palatalized before e, i, and labialized
before o. By this it is meant that such a word as ké (shoe) is
pronounced as though it were written kyé, and tó (water) as though
written twó.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 gh sound, it practically resolves itself into a
w when followed by o. Thus tálághosh (soap) could be written táláwosh,
yishghoł (I'm running) as yishwoł etc.
k and h can also be pronounced as kw and hw before e, i, in which case
the combination is a distinct phoneme. In such cases the w must be
written. Thus kwe'é (here), kwii (here), hwii (satisfaction) etc.
TONE
The present system of writing Navaho employs only one diacritical to
express four tonal variations. This is the acute accent mark (´). If a
short vowel or n, both elements of a long vowel or a diphthong are
marked thus the tone indicated is high. If only the first element of a
long vowel or diphthong is marked the tone is falling from high, and if
only the last element is marked the tone is rising from low. When a
vowel, diphthong or n is unmarked the tone is l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ow and high tone in Navaho is similar to the difference in tone
of "are you" and "going" in the English question "are you going?"
'azee' (medicine) low tone
'azéé' (mouth) high tone
háadish? (where?) falling tone
shínaaí (my elder brother) rising tone
WORD AND SENTENCE STRUCTURE
Teachers will note that the possessive pronouns of Navaho are always
prefixed to the noun. Thus, we have shimá (my mother), nimá (your
mother), bimá (his mother), but never má. The stem -má has no
independent form and never occurs without a prefix.
The structure of the Navaho verb has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but is
more complex. The subject of the sentence is always incorporated in the
verb with a pronominal form, and other verbal elements. Ideas of time
and mode are likewise incorporated in the verb, and auxiliary verbs such
as will, did, have, might, etc. do not occur in Navaho. The ideas
conveyed by these independent words in English are expressed by
different forms of the verb itself in Navaho.
Another point in which Navaho sentence structure differs from English is
that English prepositions are postpositions in Navaho.
with my elder sister shádí bił (my elder sister, with her)
for my mother shimá bá (my mother for)
whereas normal word order in English is subject, verb, and object,
Navaho has subject, object, and verb.
PUBLICATIONS OF THE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INDIAN LIFE READERS
NAVAJO SERIES (bilingual in English and Navajo)
by J. B. Enochs, illustrated by Gerald Nailor
Little Man's family. preprimer, primer and reader
by Hildegard Thompson, illustrated by Van Tsihnahjinnie
Preprimer, Primer
Coyote Tales (reader)
by Ann Clark, illustrated by Hoke Denetsosie
Who Wants to be a Prairie Dog? (A Navajo fairy tale)
by Ann Clark, illustrated by Van Tsihnahjinnie
Little Herder in Autumn, in Winter (single volume)
Little Herder in Spring, in Summer (single volume)
In English only:
Little Navajo Herder (Autumn, Winter, Spring, Summer)
by Cecil S. King, Navajo New World Readers:
1. Away to School. Illustrated by Franklin Kahn
2. The Flag of My Country. Illustrated by Henry Bahe
(Material of mature concept and simple vocabulary for use by recently
non-English-speaking adolescents.)
SIOUX SERIES (in English and Dakota)
by Ann Clark, illustrated by Andrew Standing Soldier
Sioux Cowboy (preprimer)
The Pine Ridge Porcupine
The Grass Mountain Mouse
There Still are Buffalo
Bringer of the Mystery Dog (illustrated by Oscar Howe)
Brave Against the Enemy (photographic illustrations by Helen Post)
Singing Sioux Cowboy (Primer)
The Slim Butte Raccoon
The Hen of Wahpeton
PUEBLO SERIES
by Ann Clark (in English and Spanish)
Little Boy With Three Names (illustrated by Tonita Lujan) Taos
Young Hunter of Picuris (illustrated by Velino Herrera)
Sun Journey (illustrated by Percy Sandy) Zuni
by Edward A. Kennard (in English and Hopi)
Field Mouse Goes to War (illustrated by Fred Kabotie)
Little Hopi (illustrated by Charles Loloma)
ALASKA STORIES
by Edward A. Keithahn, illustrated by George A. Ahgapuk
Igloo Tales
Also pamphlets on Indian Life and Customs, and Indian Handcrafts
for catalog and price list write to
HASKELL INSTITUTE
* * * * *
Transcriber's Notes:
Spelling changes made:
Foreword: "Mr. Robert W. Young, assocate [associate] of Dr. Harrington"
Pg 034: "ts ocurs [occurs] in the beginning"
Pg 034: "final position in Englsh [English]."
Pg 034: "This harsh pronounciation [pronunciation]"
Changes not made - multiple spellings of:
"pre-primer", "preprimer"
"bi-lingual", "bilingual"
End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Little Man's Family, by J. B. Enochs
*** END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LITTLE MAN'S FAMILY ***
***** This file should be named 37829-0.txt or 37829-0.zip *****
This and all associated files of various formats will be found in:
http://www.gutenberg.org/3/7/8/2/37829/
Produced by Juliet Sutherland, Fulvia Hughes and the Online
Distributed Proofreading Team at http://www.pgdp.net
Updated editions will replace the previous one--the old editions
will be renamed.
Creating the works from public domain print editions means that no
one owns a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in these works, so the Foundation
(and you!) can copy and distribute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ermission and without paying copyright royalties. Special rules,
set forth in the General Terms of Use part of this license, apply to
copying and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ncept and trademark.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may not be used if you
charge for the eBooks, unless you receive specific permission. If you
do not charge anything for copies of this eBook, complying with the
rules is very easy. You may use this eBook for nearly any purpose
such as creation of derivative works, reports, performances and
research. They may be modified and printed and given away--you may do
practically ANYTHING with public domain eBooks. Redistribution is
subject to the trademark license, especially commercial
redistribution.
*** START: FULL LICENSE ***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PLEASE READ THIS BEFORE YOU DISTRIBUTE OR USE THIS WORK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by using or distributing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you agree to comply with all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available with this file or online at
http://gutenberg.org/license).
Section 1. General Terms of Use and Re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1.A. By reading or using any part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you indicate that you have read, understand, agree to
and accept all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mark/copyright) agreement. If you do not agree to abide by all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cease using and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n your possession.
If you paid a fee for obtaining a copy of or access to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and you do not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ay obtain a refund from the person or
entity to whom you paid the fee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8.
1.B.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It may only be
used on or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an electronic work by people who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you can do with most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even without complying with the full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See
paragraph 1.C below.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do with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f you follow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and help preserve free future access to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See paragraph 1.E below.
1.C.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or PGLAF), owns a compilation copyright in the collec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Nearly all the individual works in the
collection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an
individual work is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are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do not claim a right to prevent you from
copying, distributing, performing, display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e work as long as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are removed. Of course, we hope that you will suppor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mission of promoting free access to electronic works by
freely sharing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keep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 You can easily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y
keeping this work in the same format with its attached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when you share it without charge with others.
1.D.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located also govern
what you can do with this work. Copyright laws in most countries ar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change. If you ar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check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in addition to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efore downloading, copy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distribut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is work or any other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The Foundation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concerning
the copyright status of any work in any country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1.E. Unless you have removed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1.E.1. The following sentence, with active links to, or othe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must appear prominently
whenever any copy of a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any work on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ppears, or with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is associated) is accessed, displayed, performed, viewed,
copied or distributed: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1.E.2.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is derived
from the public domain (does not contain a notice indicating that it is
pos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the work can be copied
and distributed to an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aying any fees
or charges. If you are redistributing or providing access to a work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ssociated with or appearing on the
work, you must comply either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or obtain permission for the use of the work and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s 1.E.8 or
1.E.9.
1.E.3.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i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your use and distribution
must comply with both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and any additional
terms impos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 Additional terms will be linked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for all work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f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work.
1.E.4. Do not unlink or detach or remov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terms from this work, or any files containing a part of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with Project Gutenberg-tm.
1.E.5. Do not copy, display, perform, distribute or redistribute this
electronic work, or any part of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out
prominently displaying the sentence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1 with
active links o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1.E.6. You may convert to and distribute this work in any binary,
compressed, marked up, nonproprietary or proprietary form, including any
word processing or hypertext form. However, if you provide access to or
distribute copies of a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in a format other than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at used in the official version
posted on the official Project Gutenberg-tm web site (www.gutenberg.org),
you must, at no additional cost, fee or expense to the user, provide a
copy, a means of exporting a copy, or a means of obtaining a copy upon
request, of the work in its original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 Any alternate format must includ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a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1.E.1.
1.E.7. Do not charge a fee for access to, view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copying or distributing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unless you comply with paragraph 1.E.8 or 1.E.9.
1.E.8. You may charge a reasonable fee for copies of or providing
access to or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provided
that
- You pay a royalty fee of 20% of the gross profits you derive from
the use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
you already use to calculate your applicable taxes. The fee is
owed to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but he
has agreed to donate royalties under this paragraph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Royalty payments
must be paid within 60 days following each date on which you
prepare (or are legally required to prepare) your periodic tax
returns. Royalty payments should be clearly marked as such and
sent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t the
address specified in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 You provide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by a user who notifies
you in writing (or by e-mail) within 30 days of receipt that s/he
does not agree to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You must require such a user to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the works possessed in a physical medium
and discontinue all use of and all access to other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 You provide,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F.3,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for a work or a replacement copy, if a defect in the
electronic work is discovered and reported to you within 90 days
of receipt of the work.
- You comply with all other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free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1.E.9. If you wish to charge a fee or distribute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or group of works on different terms than are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obtain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both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Michael
Hart,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Contact the
Foundation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3 below.
1.F.
1.F.1. Project Gutenberg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expend considerable
effort to identify, do copyright research on, transcribe and proofread
public domain works in creat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llection. Despite these efforts,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and the medium on which they may be stored, may contain
"Defect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incomplete, inaccurate or
corrupt data, transcription errors, a copyrigh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a defective or damaged disk or other medium, a
computer virus, or computer codes that damage or cannot be read by
your equipment.
1.F.2. LIMITED WARRANTY, DISCLAIMER OF DAMAGES - Except for the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F.3,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and any other party distributing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under this agreement, disclaim all
liability to you for damages,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YOU AGREE THAT YOU HAVE NO REMEDIES FOR NEGLIGENCE, STRICT
LIABILITY, BREACH OF WARRANTY OR BREACH OF CONTRACT EXCEPT THOSE
PROVIDED IN PARAGRAPH 1.F.3. YOU AGREE THAT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D ANY DISTRIBUTOR UNDER THIS AGREEMENT WILL NOT BE
LIABLE TO YOU FOR ACTUAL, DIRECT, INDIRECT, CONSEQUENTIAL, PUNITIVE OR
INCIDENTAL DAMAGES EVEN IF YOU GIVE NOTICE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1.F.3.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 If you discover a
defect in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in 90 days of receiving it, you can
receive a refund of the money (if any) you paid for it by sending a
written explanation to the person you received the work from.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on a physical medium, you must return the medium with
your written explanation. The person or entity that provided you with
the defective work may elect to provide a replacement cop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the person or entity
providing it to you may choose to give you a second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the second copy
is also defective, you may demand a refund in writing without further
opportunities to fix the problem.
1.F.4. Except for the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F.3, this work is provided to you 'AS-IS' WITH NO OTHER
WARRANTIES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RANTIES OF MERCHANTIBILITY OR FITNESS FOR ANY PURPOSE.
1.F.5. Some states do not allow disclaimers of certain implied
warranties or the exclusion or limitation of certain types of damages.
If any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violates the
law of the state applicable to this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shall be
interpreted to make the maximum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permitted by
the applicable state law. The invalidity or unenforceability of any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void the remaining provisions.
1.F.6. INDEMNITY - You agree to indemnify and hold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y agent or employee of the Foundation, anyone
providing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greement, and any volunteer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promo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harmless from all liability,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that ari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any of the following which you do
or cause to occur: (a) distribution of this or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b) alteration, modification, or additions or deletions to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and (c) any Defect you cause.
Section 2. Information about the Miss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Project Gutenberg-tm is synonymous with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in formats readable by the widest variety of computers
including obsolete, old, middle-aged and new computers. It exists
because of the efforts of hundreds of volunteers and donations from
people in all walks of life.
Volunteers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vide volunteers with the
assistance they need, are critical to reaching Project Gutenberg-tm's
goals and ensuring tha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llection will
remain freely available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In 2001,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was created to provide a secure
and permanent future for Project Gutenberg-tm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how your efforts and donations can help, see Sections 3 and 4
and the Foundation web page at http://www.pglaf.org.
Section 3.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is a non profit
501(c)(3)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nd granted tax exempt status by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The Foundation's EIN or 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is 64-6221541. Its 501(c)(3) letter is posted at
http://pglaf.org/fundrais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re tax deductible to the full extent
permitted by U.S. federal laws and your state's laws.
The Foundation's principal office is located at 4557 Melan Dr. S.
Fairbanks, AK, 99712., but its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are scattered
throughout numerous locations. Its business office is located at
809 North 1500 West, Salt Lake City, UT 84116, (801) 596-1887, email
[email protected]. Email contact links and up to date contac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the Foundation's web site and official
page at http://pglaf.org
For additional contact information:
Dr. Gregory B. Newby
Chief Executive and Director
[email protected]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Project Gutenberg-tm depends upon and cannot survive without wide
spread public support and donations to carry out its mission of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ublic domain and licensed works that can be
freely distributed in machine readable form accessible by the widest
array of equipment including outdated equipment. Many small donations
($1 to $5,000)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aintaining tax exempt
status with the IRS.
The Foundation is committed to complying with the laws regulating
charities and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all 50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are not uniform and it takes a
considerable effort, much paperwork and many fees to meet and keep up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We do not solicit donations in locations
where we have not received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compliance. To
SEND DONATIONS or determine the status of compliance for any
particular state visit http://pglaf.org
While we cannot and do not solicit contributions from states where we
have not met the solicitation requirements, we know of no prohibition
against accepting unsolicited donations from donors in such states who
approach us with offers to donate.
International donations are gratefully accepted, but we cannot make
any statements concerning tax treatment of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U.S. laws alone swamp our small staff.
Please check the Project Gutenberg Web pages for current donation
methods and addresses. Donations are accepted in a number of other
ways including checks, online payments and credit card donations.
To donate, please visit: http://pglaf.org/donate
Section 5.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Professor Michael S. Hart is the originato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ncept of a library of electronic works that could be freely shared
with anyone. For thirty years, he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Project
Gutenberg-tm eBooks with only a loose network of volunteer support.
Project Gutenberg-tm eBooks are often created from several printed
editions, all of which are confirmed as Public Domain in the U.S.
unless a copyright notice is included. Thus, we do not necessarily
keep eBooks in compliance with any particular paper edition.
Douglas McKay, Secretary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Glenn L. Emmons, Commissioner
BRANCH OF EDUCATION
Hildegard Thompson, Chief
Single Copy Price 20 cents
Phoenix Indian School Print Shop
Phoenix, Arizona
Third Edition 5,000 copies--September 1953
Little Man's family
diné yázhí ba'áłchíní
pre-primer
[Illustration]
by
J. B. Enochs
illustrated by
Gerald Nailor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FOREWORD
This pre-primer is one of three little books based on material prepared
by J. B. Enochs, who once taught in the sanitarium school at Kayenta. It
deals entirely with typical life experiences among the Navaho, the
largest Indian tribe in the United States, numbering approximately
65,000. Nine out of ten Navahos do not speak English, and the tribe has
never had a written language.
Missionaries and scientists for many years have had alphabets with which
to record this difficult language. But these alphabets have usually
included letters not found in English, and have been peppered with
diacritical marks to indicate inflection, tonal change and nasalization.
Thus they proved too complicated for popular use. Space does not permit
mention of many who have worked with the Navaho language. Finally Dr.
John Harrington,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nd Mr. Oliver LaFarge,
author and linguist, collaborated to produce a simplified alphabet which
might be written with an ordinary typewriter. Mr. Robert W. Young,
associate of Dr. Harrington, experimentally recorded a great deal of
material in this new alphabet. The Navaho portions of later pamphlets in
this bi-lingual series are the joint work of Harrington and Young.
=Little Man's Family= has been expressed in Navaho, using the
Harrington-LaFarge alphabet, by Willetto Antonio, a Navaho teacher on
the reservation, and Dr. Edward Kennard, formerly a specialist in Indian
languages for the Indian Service. Both the recording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in these books have been checked by Chic Sandoval, Howard
Gorman, and Adolph Bitanny, Navaho interpreters, and by Robert W. Young.
Back pages contain an explanation of the sound values represented by the
alphabet, and the indications of tonal change and nasalization which are
used.
These bi-lingual texts are an attempt to speed up Indi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life. Use of native languages to speed up acquisition of
English in Federal schools is a new departure in Indian policy, which
has proved very successful.
The type used for these books has been selected because of its
similarity in design to the alphabet used for manuscript writing. In the
primers, only proper names and the pronoun I have to be capitalized, so
as to further minimize the new learnings often encountered by the
primary child when faced with several different alphabets at once.
Willard W. Beatty
Revised February 1950
[Illustration]
I am a Navaho boy.
diné 'ashkii nishłį́.
[Illustration]
my mother
shimá
[Illustration]
my father
shizhé'é
[Illustration]
my baby brother
'awéé' sitsilí
[Illustration]
our baby's cradle
nihe'awéé' bits'áál
[Illustration]
my big sister
shádí
[Illustration]
my little sister
shideezhí
[Illustration]
our hogan
nihighan
[Illustration]
my father made our hogan
shizhé'é nihighan 'áyiilaa.
[Illustration]
our sweathouse
nihitáchééh
[Illustration]
the soapweed plant
tsá'ászi'
[Illustration]
we wash our hair
nihitsii' tanínádeiigis
[Illustration]
our sheep
nihidibé
[Illustration]
our goats
nihitł'ízí
[Illustration]
our corral
nihidibé bighan
[Illustration]
our horses
nihilį́į́'
[Illustration]
our wagon
nihitsinaabąąs
[Illustration]
my mother's saddle
shimá bilį́į́' biyéél
[Illustration]
my father's saddle
shizhé'é bilį́į́' biyéél
[Illustration]
my little spotted pony
shilé'éyázhí łikizh
[Illustration]
my black dog
shilééchąąshzhiin
[Illustration]
my mother's loom
shimá bidah'iistł'ǫ́
[Illustration]
my mother cleans the wool.
shimá 'aghaa' hasht'eilééh
[Illustration]
my mother cards the wool.
shimá 'aghaa' hanéiniłcha'.
[Illustration]
my mother spins the wool
shimá 'aghaa' hanéiniłdis.
[Illustration]
my mother weaves a rug.
shimá diyogí yitł'ó.
[Illustration]
my sisters help my mother.
shádí dóó shideezhí shimá yíká 'anáhi'nilchééh.
[Illustration]
we sell the rug.
diyogí ninádahiilnih.
THE NAVAHO ALPHABET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Navaho alphabet and its use
should prove helpful to one familiar with the English language.
VOWELS
The vowels have continental values. They are as follows, the first
example being a Navaho word, the second the closest approximation to the
sound in an English word:
a gad (juniper) father
e ké (shoe) met
i sis (belt) or as in sit or as in
dishááh (I'm starting) pique
o doo (not) note
Vowels may be either long or short in duration, the long vowel being
indicated by a doubling of the letter. This never affects the quality of
the vowel, except that long i is always pronounced as in pique.
sis (belt) is short siziiz (my belt) is long
Vowels with a hook beneath the letter are nasalized. That is, some of
the breath passes through the nose in their production. After n, all
vowels are nasalized and are not marked.
tsinaabąąs (wagon)
jį́ (day)
kǫ́ǫ́ (here)
DIPHTHONGS
The diphthongs are as follows:
ai hai (winter) aisle
ei séí (sand) weigh
oi 'ayóí (very) Joey
The diphthongs oi (as in Joey) will frequently be heard as ui (as in
dewy) in certain sections of the reservation. However, since the related
word ayóó is always of one value, this spelling has been standardized.
In a similar way, the diphthongs ei and ai are not universally
distinguished. For example, the word for sand, séí will be pronounced
sáí by some Navahos.
CONSONANTS
The consonants are as follows:
b bá (for him) like p in spot
d díí (this) like t in stop
g gah (rabbit) like k in sky
These sounds are not truly voiced as are the sounds represented by these
letters in English, but are like the wholly unaspirated p, t, and k in
the English words given as examples.
t tó (water) tea
k ké (shoe) kit
The t and k in Navaho are much more heavily aspirated than in the
English words given in the examples, so that the aspiration has a harsh
fricative quality.
' glottal stop yá'át'ééh (it is good) unh unh, oh oh
In the American colloquial negative unh unh, and in the exclamatory
expression oh oh, the glottal stop precedes the u and the o
respectively. Or, in actual speec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Johnny earns
and Johnny yearns, is that the former has a glottal closure between the
two words.
t' yá'át'ééh (it is good)
This letter represents the sound produced by the almost simultaneous
release of the breath from the closure formed by the tip of the tongue
and the teeth and the glottal closure described previously.
k' k'ad (now)
This sound is produced in the same way as the t', except that the k
closure is formed by the back of the tongue and the soft palate.
m mósí (cat) man
n naadą́ą́' (corn) no
s sis (belt) so
sh shash (bear) she
z zas (snow) zebra
zh 'ázhi' (name) azure
l laanaa (would that) let
ł łid (smoke)
This sound is made with the tongue in exactly the same position as in
the ordinary l, but the voice box or larynx does not func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l's is the same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 and p, d and t, or s and z. If one attempts to pronounce th as in
thin followed by l without an intervening vowel a ł is produced. Thus
athłete.
h háadi (where) hot
In Navaho there are two sounds represented by the letter h. The
difference is in the intensity or fricativeness. Where h is the first
letter in a syllable it is by some pronounced like the ch of German.
This harsh pronunciation is the older, bu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Navahos tends to pronounce the sound much as in English.
gh hooghan (hogan)
This is the voiced equivalent of the harshly pronounced variety of h,
the functioning of the voice being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ounds.
j jádí (antelope) jug
This sound is an unaspirated ch, just as d and g represent unaspirated t
and k.
ch chizh (wood) church
ch' ch'il (plant)
This sound is produced in a fashion similar to the t' and k', but with
the release of the breath from the ch position and from the glottal
closure.
dz dził (mountain) adze
ts tsa (awl) hats
ts occurs in the beginning and middle of Navaho words, but only in final
position in English.
ts' ts'in (bone)
This sound is similar to ch', except for the tongue position, and
involves the release of the breath from the glottal closure in the same
way as the other glottalized sounds.
dl beeldléí (blanket)
The dl is produced as one sound, as gl is in the word glow.
tł tła (grease)
This sound is pronounced as unvoiced dl.
tł tł'ízí (goat)
This sound involves the release of the breath from the t position of the
tongue tip and teeth, from the contact of the sides of the tongue inside
the back teeth (normal l position), and the glottal closure. It has a
marked explosive quality. The sound is produced as a unit, as in the gl
of glow, cited above.
y yá (sky) you
w 'awéé' (baby) work
PALATALIZATION AND LABIALIZATION
It is to be noted that the sounds represented by g, t, k, h, gh, and ch,
ts (when heavily aspirated) are palatalized before e, i, and labialized
before o. By this it is meant that such a word as ké (shoe) is
pronounced as though it were written kyé, and tó (water) as though
written twó.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 gh sound, it practically resolves itself into a
w when followed by o. Thus tálághosh (soap) could be written táláwosh,
yishghoł (I'm running) as yishwoł etc.
k and h can also be pronounced as kw and hw before e, i, in which case
the combination is a distinct phoneme. In such cases the w must be
written. Thus kwe'é (here), kwii (here), hwii (satisfaction) etc.
TONE
The present system of writing Navaho employs only one diacritical to
express four tonal variations. This is the acute accent mark (´). If a
short vowel or n, both elements of a long vowel or a diphthong are
marked thus the tone indicated is high. If only the first element of a
long vowel or diphthong is marked the tone is falling from high, and if
only the last element is marked the tone is rising from low. When a
vowel, diphthong or n is unmarked the tone is l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ow and high tone in Navaho is similar to the difference in tone
of "are you" and "going" in the English question "are you going?"
'azee' (medicine) low tone
'azéé' (mouth) high tone
háadish? (where?) falling tone
shínaaí (my elder brother) rising tone
WORD AND SENTENCE STRUCTURE
Teachers will note that the possessive pronouns of Navaho are always
prefixed to the noun. Thus, we have shimá (my mother), nimá (your
mother), bimá (his mother), but never má. The stem -má has no
independent form and never occurs without a prefix.
The structure of the Navaho verb has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but is
more complex. The subject of the sentence is always incorporated in the
verb with a pronominal form, and other verbal elements. Ideas of time
and mode are likewise incorporated in the verb, and auxiliary verbs such
as will, did, have, might, etc. do not occur in Navaho. The ideas
conveyed by these independent words in English are expressed by
different forms of the verb itself in Navaho.
Another point in which Navaho sentence structure differs from English is
that English prepositions are postpositions in Navaho.
with my elder sister shádí bił (my elder sister, with her)
for my mother shimá bá (my mother for)
whereas normal word order in English is subject, verb, and object,
Navaho has subject, object, and verb.
PUBLICATIONS OF THE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INDIAN LIFE READERS
NAVAJO SERIES (bilingual in English and Navajo)
by J. B. Enochs, illustrated by Gerald Nailor
Little Man's family. preprimer, primer and reader
by Hildegard Thompson, illustrated by Van Tsihnahjinnie
Preprimer, Primer
Coyote Tales (reader)
by Ann Clark, illustrated by Hoke Denetsosie
Who Wants to be a Prairie Dog? (A Navajo fairy tale)
by Ann Clark, illustrated by Van Tsihnahjinnie
Little Herder in Autumn, in Winter (single volume)
Little Herder in Spring, in Summer (single volume)
In English only:
Little Navajo Herder (Autumn, Winter, Spring, Summer)
by Cecil S. King, Navajo New World Readers:
1. Away to School. Illustrated by Franklin Kahn
2. The Flag of My Country. Illustrated by Henry Bahe
(Material of mature concept and simple vocabulary for use by recently
non-English-speaking adolescents.)
SIOUX SERIES (in English and Dakota)
by Ann Clark, illustrated by Andrew Standing Soldier
Sioux Cowboy (preprimer)
The Pine Ridge Porcupine
The Grass Mountain Mouse
There Still are Buffalo
Bringer of the Mystery Dog (illustrated by Oscar Howe)
Brave Against the Enemy (photographic illustrations by Helen Post)
Singing Sioux Cowboy (Primer)
The Slim Butte Raccoon
The Hen of Wahpeton
PUEBLO SERIES
by Ann Clark (in English and Spanish)
Little Boy With Three Names (illustrated by Tonita Lujan) Taos
Young Hunter of Picuris (illustrated by Velino Herrera)
Sun Journey (illustrated by Percy Sandy) Zuni
by Edward A. Kennard (in English and Hopi)
Field Mouse Goes to War (illustrated by Fred Kabotie)
Little Hopi (illustrated by Charles Loloma)
ALASKA STORIES
by Edward A. Keithahn, illustrated by George A. Ahgapuk
Igloo Tales
Also pamphlets on Indian Life and Customs, and Indian Handcrafts
for catalog and price list write to
HASKELL INSTITUTE
* * * * *
Transcriber's Notes:
Spelling changes made:
Foreword: "Mr. Robert W. Young, assocate [associate] of Dr. Harrington"
Pg 034: "ts ocurs [occurs] in the beginning"
Pg 034: "final position in Englsh [English]."
Pg 034: "This harsh pronounciation [pronunciation]"
Changes not made - multiple spellings of:
"pre-primer", "preprimer"
"bi-lingual", "bilingual"
End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Little Man's Family, by J. B. Enochs
*** END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LITTLE MAN'S FAMILY ***
***** This file should be named 37829-0.txt or 37829-0.zip *****
This and all associated files of various formats will be found in:
http://www.gutenberg.org/3/7/8/2/37829/
Produced by Juliet Sutherland, Fulvia Hughes and the Online
Distributed Proofreading Team at http://www.pgdp.net
Updated editions will replace the previous one--the old editions
will be renamed.
Creating the works from public domain print editions means that no
one owns a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in these works, so the Foundation
(and you!) can copy and distribute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ermission and without paying copyright royalties. Special rules,
set forth in the General Terms of Use part of this license, apply to
copying and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ncept and trademark.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may not be used if you
charge for the eBooks, unless you receive specific permission. If you
do not charge anything for copies of this eBook, complying with the
rules is very easy. You may use this eBook for nearly any purpose
such as creation of derivative works, reports, performances and
research. They may be modified and printed and given away--you may do
practically ANYTHING with public domain eBooks. Redistribution is
subject to the trademark license, especially commercial
redistribution.
*** START: FULL LICENSE ***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PLEASE READ THIS BEFORE YOU DISTRIBUTE OR USE THIS WORK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by using or distributing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you agree to comply with all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available with this file or online at
http://gutenberg.org/license).
Section 1. General Terms of Use and Re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1.A. By reading or using any part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you indicate that you have read, understand, agree to
and accept all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mark/copyright) agreement. If you do not agree to abide by all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cease using and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n your possession.
If you paid a fee for obtaining a copy of or access to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and you do not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ay obtain a refund from the person or
entity to whom you paid the fee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8.
1.B.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It may only be
used on or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an electronic work by people who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you can do with most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even without complying with the full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See
paragraph 1.C below.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do with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f you follow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and help preserve free future access to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See paragraph 1.E below.
1.C.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or PGLAF), owns a compilation copyright in the collec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Nearly all the individual works in the
collection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an
individual work is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are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do not claim a right to prevent you from
copying, distributing, performing, display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e work as long as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are removed. Of course, we hope that you will suppor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mission of promoting free access to electronic works by
freely sharing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keep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 You can easily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y
keeping this work in the same format with its attached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when you share it without charge with others.
1.D.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located also govern
what you can do with this work. Copyright laws in most countries ar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change. If you ar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check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in addition to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efore downloading, copy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distribut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is work or any other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The Foundation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concerning
the copyright status of any work in any country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1.E. Unless you have removed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1.E.1. The following sentence, with active links to, or othe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must appear prominently
whenever any copy of a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any work on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ppears, or with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is associated) is accessed, displayed, performed, viewed,
copied or distributed: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1.E.2.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is derived
from the public domain (does not contain a notice indicating that it is
pos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the work can be copied
and distributed to an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aying any fees
or charges. If you are redistributing or providing access to a work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ssociated with or appearing on the
work, you must comply either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or obtain permission for the use of the work and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s 1.E.8 or
1.E.9.
1.E.3.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i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your use and distribution
must comply with both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and any additional
terms impos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 Additional terms will be linked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for all work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f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work.
1.E.4. Do not unlink or detach or remov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terms from this work, or any files containing a part of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with Project Gutenberg-tm.
1.E.5. Do not copy, display, perform, distribute or redistribute this
electronic work, or any part of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out
prominently displaying the sentence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1 with
active links o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1.E.6. You may convert to and distribute this work in any binary,
compressed, marked up, nonproprietary or proprietary form, including any
word processing or hypertext form. However, if you provide access to or
distribute copies of a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in a format other than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at used in the official version
posted on the official Project Gutenberg-tm web site (www.gutenberg.org),
you must, at no additional cost, fee or expense to the user, provide a
copy, a means of exporting a copy, or a means of obtaining a copy upon
request, of the work in its original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 Any alternate format must includ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a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1.E.1.
1.E.7. Do not charge a fee for access to, view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copying or distributing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unless you comply with paragraph 1.E.8 or 1.E.9.
1.E.8. You may charge a reasonable fee for copies of or providing
access to or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provided
that
- You pay a royalty fee of 20% of the gross profits you derive from
the use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
you already use to calculate your applicable taxes. The fee is
owed to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but he
has agreed to donate royalties under this paragraph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Royalty payments
must be paid within 60 days following each date on which you
prepare (or are legally required to prepare) your periodic tax
returns. Royalty payments should be clearly marked as such and
sent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t the
address specified in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 You provide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by a user who notifies
you in writing (or by e-mail) within 30 days of receipt that s/he
does not agree to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You must require such a user to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the works possessed in a physical medium
and discontinue all use of and all access to other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 You provide,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F.3,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for a work or a replacement copy, if a defect in the
electronic work is discovered and reported to you within 90 days
of receipt of the work.
- You comply with all other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free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1.E.9. If you wish to charge a fee or distribute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or group of works on different terms than are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obtain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both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Michael
Hart,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Contact the
Foundation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3 below.
1.F.
1.F.1. Project Gutenberg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expend considerable
effort to identify, do copyright research on, transcribe and proofread
public domain works in creat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llection. Despite these efforts,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and the medium on which they may be stored, may contain
"Defect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incomplete, inaccurate or
corrupt data, transcription errors, a copyrigh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a defective or damaged disk or other medium, a
computer virus, or computer codes that damage or cannot be read by
your equipment.
1.F.2. LIMITED WARRANTY, DISCLAIMER OF DAMAGES - Except for the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F.3,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and any other party distributing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under this agreement, disclaim all
liability to you for damages,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YOU AGREE THAT YOU HAVE NO REMEDIES FOR NEGLIGENCE, STRICT
LIABILITY, BREACH OF WARRANTY OR BREACH OF CONTRACT EXCEPT THOSE
PROVIDED IN PARAGRAPH 1.F.3. YOU AGREE THAT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D ANY DISTRIBUTOR UNDER THIS AGREEMENT WILL NOT BE
LIABLE TO YOU FOR ACTUAL, DIRECT, INDIRECT, CONSEQUENTIAL, PUNITIVE OR
INCIDENTAL DAMAGES EVEN IF YOU GIVE NOTICE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1.F.3.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 If you discover a
defect in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in 90 days of receiving it, you can
receive a refund of the money (if any) you paid for it by sending a
written explanation to the person you received the work from.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on a physical medium, you must return the medium with
your written explanation. The person or entity that provided you with
the defective work may elect to provide a replacement cop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the person or entity
providing it to you may choose to give you a second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the second copy
is also defective, you may demand a refund in writing without further
opportunities to fix the problem.
1.F.4. Except for the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F.3, this work is provided to you 'AS-IS' WITH NO OTHER
WARRANTIES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RANTIES OF MERCHANTIBILITY OR FITNESS FOR ANY PURPOSE.
1.F.5. Some states do not allow disclaimers of certain implied
warranties or the exclusion or limitation of certain types of damages.
If any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violates the
law of the state applicable to this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shall be
interpreted to make the maximum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permitted by
the applicable state law. The invalidity or unenforceability of any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void the remaining provisions.
1.F.6. INDEMNITY - You agree to indemnify and hold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y agent or employee of the Foundation, anyone
providing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greement, and any volunteer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promo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harmless from all liability,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that ari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any of the following which you do
or cause to occur: (a) distribution of this or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b) alteration, modification, or additions or deletions to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and (c) any Defect you cause.
Section 2. Information about the Miss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Project Gutenberg-tm is synonymous with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in formats readable by the widest variety of computers
including obsolete, old, middle-aged and new computers. It exists
because of the efforts of hundreds of volunteers and donations from
people in all walks of life.
Volunteers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vide volunteers with the
assistance they need, are critical to reaching Project Gutenberg-tm's
goals and ensuring tha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llection will
remain freely available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In 2001,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was created to provide a secure
and permanent future for Project Gutenberg-tm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how your efforts and donations can help, see Sections 3 and 4
and the Foundation web page at http://www.pglaf.org.
Section 3.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is a non profit
501(c)(3)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nd granted tax exempt status by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The Foundation's EIN or 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is 64-6221541. Its 501(c)(3) letter is posted at
http://pglaf.org/fundrais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re tax deductible to the full extent
permitted by U.S. federal laws and your state's laws.
The Foundation's principal office is located at 4557 Melan Dr. S.
Fairbanks, AK, 99712., but its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are scattered
throughout numerous locations. Its business office is located at
809 North 1500 West, Salt Lake City, UT 84116, (801) 596-1887, email
[email protected]. Email contact links and up to date contac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the Foundation's web site and official
page at http://pglaf.org
For additional contact information:
Dr. Gregory B. Newby
Chief Executive and Director
[email protected]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Project Gutenberg-tm depends upon and cannot survive without wide
spread public support and donations to carry out its mission of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ublic domain and licensed works that can be
freely distributed in machine readable form accessible by the widest
array of equipment including outdated equipment. Many small donations
($1 to $5,000)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aintaining tax exempt
status with the IRS.
The Foundation is committed to complying with the laws regulating
charities and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all 50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are not uniform and it takes a
considerable effort, much paperwork and many fees to meet and keep up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We do not solicit donations in locations
where we have not received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compliance. To
SEND DONATIONS or determine the status of compliance for any
particular state visit http://pglaf.org
While we cannot and do not solicit contributions from states where we
have not met the solicitation requirements, we know of no prohibition
against accepting unsolicited donations from donors in such states who
approach us with offers to donate.
International donations are gratefully accepted, but we cannot make
any statements concerning tax treatment of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U.S. laws alone swamp our small staff.
Please check the Project Gutenberg Web pages for current donation
methods and addresses. Donations are accepted in a number of other
ways including checks, online payments and credit card donations.
To donate, please visit: http://pglaf.org/donate
Section 5.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Professor Michael S. Hart is the originato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ncept of a library of electronic works that could be freely shared
with anyone. For thirty years, he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Project
Gutenberg-tm eBooks with only a loose network of volunteer support.
Project Gutenberg-tm eBooks are often created from several printed
editions, all of which are confirmed as Public Domain in the U.S.
unless a copyright notice is included. Thus, we do not necessarily
keep eBooks in compliance with any particular paper edition.
Douglas McKay, Secretary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Glenn L. Emmons, Commissioner
BRANCH OF EDUCATION
Hildegard Thompson, Chief
Single Copy Price 20 cents
Phoenix Indian School Print Shop
Phoenix, Arizona
Third Edition 5,000 copies--September 1953
Little Man's family
diné yázhí ba'áłchíní
pre-primer
[Illustration]
by
J. B. Enochs
illustrated by
Gerald Nailor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FOREWORD
This pre-primer is one of three little books based on material prepared
by J. B. Enochs, who once taught in the sanitarium school at Kayenta. It
deals entirely with typical life experiences among the Navaho, the
largest Indian tribe in the United States, numbering approximately
65,000. Nine out of ten Navahos do not speak English, and the tribe has
never had a written language.
Missionaries and scientists for many years have had alphabets with which
to record this difficult language. But these alphabets have usually
included letters not found in English, and have been peppered with
diacritical marks to indicate inflection, tonal change and nasalization.
Thus they proved too complicated for popular use. Space does not permit
mention of many who have worked with the Navaho language. Finally Dr.
John Harrington,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nd Mr. Oliver LaFarge,
author and linguist, collaborated to produce a simplified alphabet which
might be written with an ordinary typewriter. Mr. Robert W. Young,
associate of Dr. Harrington, experimentally recorded a great deal of
material in this new alphabet. The Navaho portions of later pamphlets in
this bi-lingual series are the joint work of Harrington and Young.
=Little Man's Family= has been expressed in Navaho, using the
Harrington-LaFarge alphabet, by Willetto Antonio, a Navaho teacher on
the reservation, and Dr. Edward Kennard, formerly a specialist in Indian
languages for the Indian Service. Both the recording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in these books have been checked by Chic Sandoval, Howard
Gorman, and Adolph Bitanny, Navaho interpreters, and by Robert W. Young.
Back pages contain an explanation of the sound values represented by the
alphabet, and the indications of tonal change and nasalization which are
used.
These bi-lingual texts are an attempt to speed up Indi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life. Use of native languages to speed up acquisition of
English in Federal schools is a new departure in Indian policy, which
has proved very successful.
The type used for these books has been selected because of its
similarity in design to the alphabet used for manuscript writing. In the
primers, only proper names and the pronoun I have to be capitalized, so
as to further minimize the new learnings often encountered by the
primary child when faced with several different alphabets at once.
Willard W. Beatty
Revised February 1950
[Illustration]
I am a Navaho boy.
diné 'ashkii nishłį́.
[Illustration]
my mother
shimá
[Illustration]
my father
shizhé'é
[Illustration]
my baby brother
'awéé' sitsilí
[Illustration]
our baby's cradle
nihe'awéé' bits'áál
[Illustration]
my big sister
shádí
[Illustration]
my little sister
shideezhí
[Illustration]
our hogan
nihighan
[Illustration]
my father made our hogan
shizhé'é nihighan 'áyiilaa.
[Illustration]
our sweathouse
nihitáchééh
[Illustration]
the soapweed plant
tsá'ászi'
[Illustration]
we wash our hair
nihitsii' tanínádeiigis
[Illustration]
our sheep
nihidibé
[Illustration]
our goats
nihitł'ízí
[Illustration]
our corral
nihidibé bighan
[Illustration]
our horses
nihilį́į́'
[Illustration]
our wagon
nihitsinaabąąs
[Illustration]
my mother's saddle
shimá bilį́į́' biyéél
[Illustration]
my father's saddle
shizhé'é bilį́į́' biyéél
[Illustration]
my little spotted pony
shilé'éyázhí łikizh
[Illustration]
my black dog
shilééchąąshzhiin
[Illustration]
my mother's loom
shimá bidah'iistł'ǫ́
[Illustration]
my mother cleans the wool.
shimá 'aghaa' hasht'eilééh
[Illustration]
my mother cards the wool.
shimá 'aghaa' hanéiniłcha'.
[Illustration]
my mother spins the wool
shimá 'aghaa' hanéiniłdis.
[Illustration]
my mother weaves a rug.
shimá diyogí yitł'ó.
[Illustration]
my sisters help my mother.
shádí dóó shideezhí shimá yíká 'anáhi'nilchééh.
[Illustration]
we sell the rug.
diyogí ninádahiilnih.
THE NAVAHO ALPHABET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Navaho alphabet and its use
should prove helpful to one familiar with the English language.
VOWELS
The vowels have continental values. They are as follows, the first
example being a Navaho word, the second the closest approximation to the
sound in an English word:
a gad (juniper) father
e ké (shoe) met
i sis (belt) or as in sit or as in
dishááh (I'm starting) pique
o doo (not) note
Vowels may be either long or short in duration, the long vowel being
indicated by a doubling of the letter. This never affects the quality of
the vowel, except that long i is always pronounced as in pique.
sis (belt) is short siziiz (my belt) is long
Vowels with a hook beneath the letter are nasalized. That is, some of
the breath passes through the nose in their production. After n, all
vowels are nasalized and are not marked.
tsinaabąąs (wagon)
jį́ (day)
kǫ́ǫ́ (here)
DIPHTHONGS
The diphthongs are as follows:
ai hai (winter) aisle
ei séí (sand) weigh
oi 'ayóí (very) Joey
The diphthongs oi (as in Joey) will frequently be heard as ui (as in
dewy) in certain sections of the reservation. However, since the related
word ayóó is always of one value, this spelling has been standardized.
In a similar way, the diphthongs ei and ai are not universally
distinguished. For example, the word for sand, séí will be pronounced
sáí by some Navahos.
CONSONANTS
The consonants are as follows:
b bá (for him) like p in spot
d díí (this) like t in stop
g gah (rabbit) like k in sky
These sounds are not truly voiced as are the sounds represented by these
letters in English, but are like the wholly unaspirated p, t, and k in
the English words given as examples.
t tó (water) tea
k ké (shoe) kit
The t and k in Navaho are much more heavily aspirated than in the
English words given in the examples, so that the aspiration has a harsh
fricative quality.
' glottal stop yá'át'ééh (it is good) unh unh, oh oh
In the American colloquial negative unh unh, and in the exclamatory
expression oh oh, the glottal stop precedes the u and the o
respectively. Or, in actual speec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Johnny earns
and Johnny yearns, is that the former has a glottal closure between the
two words.
t' yá'át'ééh (it is good)
This letter represents the sound produced by the almost simultaneous
release of the breath from the closure formed by the tip of the tongue
and the teeth and the glottal closure described previously.
k' k'ad (now)
This sound is produced in the same way as the t', except that the k
closure is formed by the back of the tongue and the soft palate.
m mósí (cat) man
n naadą́ą́' (corn) no
s sis (belt) so
sh shash (bear) she
z zas (snow) zebra
zh 'ázhi' (name) azure
l laanaa (would that) let
ł łid (smoke)
This sound is made with the tongue in exactly the same position as in
the ordinary l, but the voice box or larynx does not func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l's is the same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 and p, d and t, or s and z. If one attempts to pronounce th as in
thin followed by l without an intervening vowel a ł is produced. Thus
athłete.
h háadi (where) hot
In Navaho there are two sounds represented by the letter h. The
difference is in the intensity or fricativeness. Where h is the first
letter in a syllable it is by some pronounced like the ch of German.
This harsh pronunciation is the older, bu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Navahos tends to pronounce the sound much as in English.
gh hooghan (hogan)
This is the voiced equivalent of the harshly pronounced variety of h,
the functioning of the voice being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ounds.
j jádí (antelope) jug
This sound is an unaspirated ch, just as d and g represent unaspirated t
and k.
ch chizh (wood) church
ch' ch'il (plant)
This sound is produced in a fashion similar to the t' and k', but with
the release of the breath from the ch position and from the glottal
closure.
dz dził (mountain) adze
ts tsa (awl) hats
ts occurs in the beginning and middle of Navaho words, but only in final
position in English.
ts' ts'in (bone)
This sound is similar to ch', except for the tongue position, and
involves the release of the breath from the glottal closure in the same
way as the other glottalized sounds.
dl beeldléí (blanket)
The dl is produced as one sound, as gl is in the word glow.
tł tła (grease)
This sound is pronounced as unvoiced dl.
tł tł'ízí (goat)
This sound involves the release of the breath from the t position of the
tongue tip and teeth, from the contact of the sides of the tongue inside
the back teeth (normal l position), and the glottal closure. It has a
marked explosive quality. The sound is produced as a unit, as in the gl
of glow, cited above.
y yá (sky) you
w 'awéé' (baby) work
PALATALIZATION AND LABIALIZATION
It is to be noted that the sounds represented by g, t, k, h, gh, and ch,
ts (when heavily aspirated) are palatalized before e, i, and labialized
before o. By this it is meant that such a word as ké (shoe) is
pronounced as though it were written kyé, and tó (water) as though
written twó.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 gh sound, it practically resolves itself into a
w when followed by o. Thus tálághosh (soap) could be written táláwosh,
yishghoł (I'm running) as yishwoł etc.
k and h can also be pronounced as kw and hw before e, i, in which case
the combination is a distinct phoneme. In such cases the w must be
written. Thus kwe'é (here), kwii (here), hwii (satisfaction) etc.
TONE
The present system of writing Navaho employs only one diacritical to
express four tonal variations. This is the acute accent mark (´). If a
short vowel or n, both elements of a long vowel or a diphthong are
marked thus the tone indicated is high. If only the first element of a
long vowel or diphthong is marked the tone is falling from high, and if
only the last element is marked the tone is rising from low. When a
vowel, diphthong or n is unmarked the tone is l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ow and high tone in Navaho is similar to the difference in tone
of "are you" and "going" in the English question "are you going?"
'azee' (medicine) low tone
'azéé' (mouth) high tone
háadish? (where?) falling tone
shínaaí (my elder brother) rising tone
WORD AND SENTENCE STRUCTURE
Teachers will note that the possessive pronouns of Navaho are always
prefixed to the noun. Thus, we have shimá (my mother), nimá (your
mother), bimá (his mother), but never má. The stem -má has no
independent form and never occurs without a prefix.
The structure of the Navaho verb has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but is
more complex. The subject of the sentence is always incorporated in the
verb with a pronominal form, and other verbal elements. Ideas of time
and mode are likewise incorporated in the verb, and auxiliary verbs such
as will, did, have, might, etc. do not occur in Navaho. The ideas
conveyed by these independent words in English are expressed by
different forms of the verb itself in Navaho.
Another point in which Navaho sentence structure differs from English is
that English prepositions are postpositions in Navaho.
with my elder sister shádí bił (my elder sister, with her)
for my mother shimá bá (my mother for)
whereas normal word order in English is subject, verb, and object,
Navaho has subject, object, and verb.
PUBLICATIONS OF THE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INDIAN LIFE READERS
NAVAJO SERIES (bilingual in English and Navajo)
by J. B. Enochs, illustrated by Gerald Nailor
Little Man's family. preprimer, primer and reader
by Hildegard Thompson, illustrated by Van Tsihnahjinnie
Preprimer, Primer
Coyote Tales (reader)
by Ann Clark, illustrated by Hoke Denetsosie
Who Wants to be a Prairie Dog? (A Navajo fairy tale)
by Ann Clark, illustrated by Van Tsihnahjinnie
Little Herder in Autumn, in Winter (single volume)
Little Herder in Spring, in Summer (single volume)
In English only:
Little Navajo Herder (Autumn, Winter, Spring, Summer)
by Cecil S. King, Navajo New World Readers:
1. Away to School. Illustrated by Franklin Kahn
2. The Flag of My Country. Illustrated by Henry Bahe
(Material of mature concept and simple vocabulary for use by recently
non-English-speaking adolescents.)
SIOUX SERIES (in English and Dakota)
by Ann Clark, illustrated by Andrew Standing Soldier
Sioux Cowboy (preprimer)
The Pine Ridge Porcupine
The Grass Mountain Mouse
There Still are Buffalo
Bringer of the Mystery Dog (illustrated by Oscar Howe)
Brave Against the Enemy (photographic illustrations by Helen Post)
Singing Sioux Cowboy (Primer)
The Slim Butte Raccoon
The Hen of Wahpeton
PUEBLO SERIES
by Ann Clark (in English and Spanish)
Little Boy With Three Names (illustrated by Tonita Lujan) Taos
Young Hunter of Picuris (illustrated by Velino Herrera)
Sun Journey (illustrated by Percy Sandy) Zuni
by Edward A. Kennard (in English and Hopi)
Field Mouse Goes to War (illustrated by Fred Kabotie)
Little Hopi (illustrated by Charles Loloma)
ALASKA STORIES
by Edward A. Keithahn, illustrated by George A. Ahgapuk
Igloo Tales
Also pamphlets on Indian Life and Customs, and Indian Handcrafts
for catalog and price list write to
HASKELL INSTITUTE
* * * * *
Transcriber's Notes:
Spelling changes made:
Foreword: "Mr. Robert W. Young, assocate [associate] of Dr. Harrington"
Pg 034: "ts ocurs [occurs] in the beginning"
Pg 034: "final position in Englsh [English]."
Pg 034: "This harsh pronounciation [pronunciation]"
Changes not made - multiple spellings of:
"pre-primer", "preprimer"
"bi-lingual", "bilingual"
End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Little Man's Family, by J. B. Enochs
*** END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LITTLE MAN'S FAMILY ***
***** This file should be named 37829-0.txt or 37829-0.zip *****
This and all associated files of various formats will be found in:
http://www.gutenberg.org/3/7/8/2/37829/
Produced by Juliet Sutherland, Fulvia Hughes and the Online
Distributed Proofreading Team at http://www.pgdp.net
Updated editions will replace the previous one--the old editions
will be renamed.
Creating the works from public domain print editions means that no
one owns a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in these works, so the Foundation
(and you!) can copy and distribute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ermission and without paying copyright royalties. Special rules,
set forth in the General Terms of Use part of this license, apply to
copying and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ncept and trademark.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may not be used if you
charge for the eBooks, unless you receive specific permission. If you
do not charge anything for copies of this eBook, complying with the
rules is very easy. You may use this eBook for nearly any purpose
such as creation of derivative works, reports, performances and
research. They may be modified and printed and given away--you may do
practically ANYTHING with public domain eBooks. Redistribution is
subject to the trademark license, especially commercial
redistribution.
*** START: FULL LICENSE ***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PLEASE READ THIS BEFORE YOU DISTRIBUTE OR USE THIS WORK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by using or distributing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you agree to comply with all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available with this file or online at
http://gutenberg.org/license).
Section 1. General Terms of Use and Re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1.A. By reading or using any part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you indicate that you have read, understand, agree to
and accept all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mark/copyright) agreement. If you do not agree to abide by all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cease using and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n your possession.
If you paid a fee for obtaining a copy of or access to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and you do not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ay obtain a refund from the person or
entity to whom you paid the fee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8.
1.B.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It may only be
used on or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an electronic work by people who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you can do with most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even without complying with the full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See
paragraph 1.C below.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do with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f you follow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and help preserve free future access to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See paragraph 1.E below.
1.C.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or PGLAF), owns a compilation copyright in the collec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Nearly all the individual works in the
collection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an
individual work is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are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do not claim a right to prevent you from
copying, distributing, performing, display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e work as long as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are removed. Of course, we hope that you will suppor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mission of promoting free access to electronic works by
freely sharing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keep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 You can easily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y
keeping this work in the same format with its attached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when you share it without charge with others.
1.D.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located also govern
what you can do with this work. Copyright laws in most countries ar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change. If you ar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check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in addition to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efore downloading, copy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distribut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is work or any other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The Foundation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concerning
the copyright status of any work in any country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1.E. Unless you have removed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1.E.1. The following sentence, with active links to, or othe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must appear prominently
whenever any copy of a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any work on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ppears, or with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is associated) is accessed, displayed, performed, viewed,
copied or distributed: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1.E.2.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is derived
from the public domain (does not contain a notice indicating that it is
pos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the work can be copied
and distributed to an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aying any fees
or charges. If you are redistributing or providing access to a work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ssociated with or appearing on the
work, you must comply either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or obtain permission for the use of the work and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s 1.E.8 or
1.E.9.
1.E.3.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i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your use and distribution
must comply with both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and any additional
terms impos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 Additional terms will be linked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for all work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f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work.
1.E.4. Do not unlink or detach or remov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terms from this work, or any files containing a part of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with Project Gutenberg-tm.
1.E.5. Do not copy, display, perform, distribute or redistribute this
electronic work, or any part of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out
prominently displaying the sentence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1 with
active links o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1.E.6. You may convert to and distribute this work in any binary,
compressed, marked up, nonproprietary or proprietary form, including any
word processing or hypertext form. However, if you provide access to or
distribute copies of a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in a format other than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at used in the official version
posted on the official Project Gutenberg-tm web site (www.gutenberg.org),
you must, at no additional cost, fee or expense to the user, provide a
copy, a means of exporting a copy, or a means of obtaining a copy upon
request, of the work in its original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 Any alternate format must includ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a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1.E.1.
1.E.7. Do not charge a fee for access to, view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copying or distributing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unless you comply with paragraph 1.E.8 or 1.E.9.
1.E.8. You may charge a reasonable fee for copies of or providing
access to or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provided
that
- You pay a royalty fee of 20% of the gross profits you derive from
the use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
you already use to calculate your applicable taxes. The fee is
owed to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but he
has agreed to donate royalties under this paragraph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Royalty payments
must be paid within 60 days following each date on which you
prepare (or are legally required to prepare) your periodic tax
returns. Royalty payments should be clearly marked as such and
sent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t the
address specified in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 You provide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by a user who notifies
you in writing (or by e-mail) within 30 days of receipt that s/he
does not agree to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You must require such a user to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the works possessed in a physical medium
and discontinue all use of and all access to other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 You provide,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F.3,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for a work or a replacement copy, if a defect in the
electronic work is discovered and reported to you within 90 days
of receipt of the work.
- You comply with all other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free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1.E.9. If you wish to charge a fee or distribute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or group of works on different terms than are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obtain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both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Michael
Hart,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Contact the
Foundation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3 below.
1.F.
1.F.1. Project Gutenberg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expend considerable
effort to identify, do copyright research on, transcribe and proofread
public domain works in creat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llection. Despite these efforts,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and the medium on which they may be stored, may contain
"Defect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incomplete, inaccurate or
corrupt data, transcription errors, a copyrigh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a defective or damaged disk or other medium, a
computer virus, or computer codes that damage or cannot be read by
your equipment.
1.F.2. LIMITED WARRANTY, DISCLAIMER OF DAMAGES - Except for the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F.3,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and any other party distributing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under this agreement, disclaim all
liability to you for damages,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YOU AGREE THAT YOU HAVE NO REMEDIES FOR NEGLIGENCE, STRICT
LIABILITY, BREACH OF WARRANTY OR BREACH OF CONTRACT EXCEPT THOSE
PROVIDED IN PARAGRAPH 1.F.3. YOU AGREE THAT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D ANY DISTRIBUTOR UNDER THIS AGREEMENT WILL NOT BE
LIABLE TO YOU FOR ACTUAL, DIRECT, INDIRECT, CONSEQUENTIAL, PUNITIVE OR
INCIDENTAL DAMAGES EVEN IF YOU GIVE NOTICE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1.F.3.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 If you discover a
defect in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in 90 days of receiving it, you can
receive a refund of the money (if any) you paid for it by sending a
written explanation to the person you received the work from.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on a physical medium, you must return the medium with
your written explanation. The person or entity that provided you with
the defective work may elect to provide a replacement cop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the person or entity
providing it to you may choose to give you a second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the second copy
is also defective, you may demand a refund in writing without further
opportunities to fix the problem.
1.F.4. Except for the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F.3, this work is provided to you 'AS-IS' WITH NO OTHER
WARRANTIES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RANTIES OF MERCHANTIBILITY OR FITNESS FOR ANY PURPOSE.
1.F.5. Some states do not allow disclaimers of certain implied
warranties or the exclusion or limitation of certain types of damages.
If any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violates the
law of the state applicable to this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shall be
interpreted to make the maximum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permitted by
the applicable state law. The invalidity or unenforceability of any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void the remaining provisions.
1.F.6. INDEMNITY - You agree to indemnify and hold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y agent or employee of the Foundation, anyone
providing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greement, and any volunteer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promo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harmless from all liability,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that ari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any of the following which you do
or cause to occur: (a) distribution of this or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b) alteration, modification, or additions or deletions to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and (c) any Defect you cause.
Section 2. Information about the Miss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Project Gutenberg-tm is synonymous with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in formats readable by the widest variety of computers
including obsolete, old, middle-aged and new computers. It exists
because of the efforts of hundreds of volunteers and donations from
people in all walks of life.
Volunteers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vide volunteers with the
assistance they need, are critical to reaching Project Gutenberg-tm's
goals and ensuring tha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llection will
remain freely available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In 2001,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was created to provide a secure
and permanent future for Project Gutenberg-tm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how your efforts and donations can help, see Sections 3 and 4
and the Foundation web page at http://www.pglaf.org.
Section 3.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is a non profit
501(c)(3)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nd granted tax exempt status by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The Foundation's EIN or 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is 64-6221541. Its 501(c)(3) letter is posted at
http://pglaf.org/fundrais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re tax deductible to the full extent
permitted by U.S. federal laws and your state's laws.
The Foundation's principal office is located at 4557 Melan Dr. S.
Fairbanks, AK, 99712., but its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are scattered
throughout numerous locations. Its business office is located at
809 North 1500 West, Salt Lake City, UT 84116, (801) 596-1887, email
[email protected]. Email contact links and up to date contac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the Foundation's web site and official
page at http://pglaf.org
For additional contact information:
Dr. Gregory B. Newby
Chief Executive and Director
[email protected]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Project Gutenberg-tm depends upon and cannot survive without wide
spread public support and donations to carry out its mission of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ublic domain and licensed works that can be
freely distributed in machine readable form accessible by the widest
array of equipment including outdated equipment. Many small donations
($1 to $5,000)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aintaining tax exempt
status with the IRS.
The Foundation is committed to complying with the laws regulating
charities and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all 50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are not uniform and it takes a
considerable effort, much paperwork and many fees to meet and keep up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We do not solicit donations in locations
where we have not received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compliance. To
SEND DONATIONS or determine the status of compliance for any
particular state visit http://pglaf.org
While we cannot and do not solicit contributions from states where we
have not met the solicitation requirements, we know of no prohibition
against accepting unsolicited donations from donors in such states who
approach us with offers to donate.
International donations are gratefully accepted, but we cannot make
any statements concerning tax treatment of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U.S. laws alone swamp our small staff.
Please check the Project Gutenberg Web pages for current donation
methods and addresses. Donations are accepted in a number of other
ways including checks, online payments and credit card donations.
To donate, please visit: http://pglaf.org/donate
Section 5.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Professor Michael S. Hart is the originato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ncept of a library of electronic works that could be freely shared
with anyone. For thirty years, he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Project
Gutenberg-tm eBooks with only a loose network of volunteer support.
Project Gutenberg-tm eBooks are often created from several printed
editions, all of which are confirmed as Public Domain in the U.S.
unless a copyright notice is included. Thus, we do not necessarily
keep eBooks in compliance with any particular paper edition.
Douglas McKay, Secretary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Glenn L. Emmons, Commissioner
BRANCH OF EDUCATION
Hildegard Thompson, Chief
Single Copy Price 20 cents
Phoenix Indian School Print Shop
Phoenix, Arizona
Third Edition 5,000 copies--September 1953
Little Man's family
diné yázhí ba'áłchíní
pre-primer
[Illustration]
by
J. B. Enochs
illustrated by
Gerald Nailor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FOREWORD
This pre-primer is one of three little books based on material prepared
by J. B. Enochs, who once taught in the sanitarium school at Kayenta. It
deals entirely with typical life experiences among the Navaho, the
largest Indian tribe in the United States, numbering approximately
65,000. Nine out of ten Navahos do not speak English, and the tribe has
never had a written language.
Missionaries and scientists for many years have had alphabets with which
to record this difficult language. But these alphabets have usually
included letters not found in English, and have been peppered with
diacritical marks to indicate inflection, tonal change and nasalization.
Thus they proved too complicated for popular use. Space does not permit
mention of many who have worked with the Navaho language. Finally Dr.
John Harrington,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nd Mr. Oliver LaFarge,
author and linguist, collaborated to produce a simplified alphabet which
might be written with an ordinary typewriter. Mr. Robert W. Young,
associate of Dr. Harrington, experimentally recorded a great deal of
material in this new alphabet. The Navaho portions of later pamphlets in
this bi-lingual series are the joint work of Harrington and Young.
=Little Man's Family= has been expressed in Navaho, using the
Harrington-LaFarge alphabet, by Willetto Antonio, a Navaho teacher on
the reservation, and Dr. Edward Kennard, formerly a specialist in Indian
languages for the Indian Service. Both the recording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in these books have been checked by Chic Sandoval, Howard
Gorman, and Adolph Bitanny, Navaho interpreters, and by Robert W. Young.
Back pages contain an explanation of the sound values represented by the
alphabet, and the indications of tonal change and nasalization which are
used.
These bi-lingual texts are an attempt to speed up Indi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life. Use of native languages to speed up acquisition of
English in Federal schools is a new departure in Indian policy, which
has proved very successful.
The type used for these books has been selected because of its
similarity in design to the alphabet used for manuscript writing. In the
primers, only proper names and the pronoun I have to be capitalized, so
as to further minimize the new learnings often encountered by the
primary child when faced with several different alphabets at once.
Willard W. Beatty
Revised February 1950
[Illustration]
I am a Navaho boy.
diné 'ashkii nishłį́.
[Illustration]
my mother
shimá
[Illustration]
my father
shizhé'é
[Illustration]
my baby brother
'awéé' sitsilí
[Illustration]
our baby's cradle
nihe'awéé' bits'áál
[Illustration]
my big sister
shádí
[Illustration]
my little sister
shideezhí
[Illustration]
our hogan
nihighan
[Illustration]
my father made our hogan
shizhé'é nihighan 'áyiilaa.
[Illustration]
our sweathouse
nihitáchééh
[Illustration]
the soapweed plant
tsá'ászi'
[Illustration]
we wash our hair
nihitsii' tanínádeiigis
[Illustration]
our sheep
nihidibé
[Illustration]
our goats
nihitł'ízí
[Illustration]
our corral
nihidibé bighan
[Illustration]
our horses
nihilį́į́'
[Illustration]
our wagon
nihitsinaabąąs
[Illustration]
my mother's saddle
shimá bilį́į́' biyéél
[Illustration]
my father's saddle
shizhé'é bilį́į́' biyéél
[Illustration]
my little spotted pony
shilé'éyázhí łikizh
[Illustration]
my black dog
shilééchąąshzhiin
[Illustration]
my mother's loom
shimá bidah'iistł'ǫ́
[Illustration]
my mother cleans the wool.
shimá 'aghaa' hasht'eilééh
[Illustration]
my mother cards the wool.
shimá 'aghaa' hanéiniłcha'.
[Illustration]
my mother spins the wool
shimá 'aghaa' hanéiniłdis.
[Illustration]
my mother weaves a rug.
shimá diyogí yitł'ó.
[Illustration]
my sisters help my mother.
shádí dóó shideezhí shimá yíká 'anáhi'nilchééh.
[Illustration]
we sell the rug.
diyogí ninádahiilnih.
THE NAVAHO ALPHABET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Navaho alphabet and its use
should prove helpful to one familiar with the English language.
VOWELS
The vowels have continental values. They are as follows, the first
example being a Navaho word, the second the closest approximation to the
sound in an English word:
a gad (juniper) father
e ké (shoe) met
i sis (belt) or as in sit or as in
dishááh (I'm starting) pique
o doo (not) note
Vowels may be either long or short in duration, the long vowel being
indicated by a doubling of the letter. This never affects the quality of
the vowel, except that long i is always pronounced as in pique.
sis (belt) is short siziiz (my belt) is long
Vowels with a hook beneath the letter are nasalized. That is, some of
the breath passes through the nose in their production. After n, all
vowels are nasalized and are not marked.
tsinaabąąs (wagon)
jį́ (day)
kǫ́ǫ́ (here)
DIPHTHONGS
The diphthongs are as follows:
ai hai (winter) aisle
ei séí (sand) weigh
oi 'ayóí (very) Joey
The diphthongs oi (as in Joey) will frequently be heard as ui (as in
dewy) in certain sections of the reservation. However, since the related
word ayóó is always of one value, this spelling has been standardized.
In a similar way, the diphthongs ei and ai are not universally
distinguished. For example, the word for sand, séí will be pronounced
sáí by some Navahos.
CONSONANTS
The consonants are as follows:
b bá (for him) like p in spot
d díí (this) like t in stop
g gah (rabbit) like k in sky
These sounds are not truly voiced as are the sounds represented by these
letters in English, but are like the wholly unaspirated p, t, and k in
the English words given as examples.
t tó (water) tea
k ké (shoe) kit
The t and k in Navaho are much more heavily aspirated than in the
English words given in the examples, so that the aspiration has a harsh
fricative quality.
' glottal stop yá'át'ééh (it is good) unh unh, oh oh
In the American colloquial negative unh unh, and in the exclamatory
expression oh oh, the glottal stop precedes the u and the o
respectively. Or, in actual speec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Johnny earns
and Johnny yearns, is that the former has a glottal closure between the
two words.
t' yá'át'ééh (it is good)
This letter represents the sound produced by the almost simultaneous
release of the breath from the closure formed by the tip of the tongue
and the teeth and the glottal closure described previously.
k' k'ad (now)
This sound is produced in the same way as the t', except that the k
closure is formed by the back of the tongue and the soft palate.
m mósí (cat) man
n naadą́ą́' (corn) no
s sis (belt) so
sh shash (bear) she
z zas (snow) zebra
zh 'ázhi' (name) azure
l laanaa (would that) let
ł łid (smoke)
This sound is made with the tongue in exactly the same position as in
the ordinary l, but the voice box or larynx does not func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l's is the same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 and p, d and t, or s and z. If one attempts to pronounce th as in
thin followed by l without an intervening vowel a ł is produced. Thus
athłete.
h háadi (where) hot
In Navaho there are two sounds represented by the letter h. The
difference is in the intensity or fricativeness. Where h is the first
letter in a syllable it is by some pronounced like the ch of German.
This harsh pronunciation is the older, bu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Navahos tends to pronounce the sound much as in English.
gh hooghan (hogan)
This is the voiced equivalent of the harshly pronounced variety of h,
the functioning of the voice being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ounds.
j jádí (antelope) jug
This sound is an unaspirated ch, just as d and g represent unaspirated t
and k.
ch chizh (wood) church
ch' ch'il (plant)
This sound is produced in a fashion similar to the t' and k', but with
the release of the breath from the ch position and from the glottal
closure.
dz dził (mountain) adze
ts tsa (awl) hats
ts occurs in the beginning and middle of Navaho words, but only in final
position in English.
ts' ts'in (bone)
This sound is similar to ch', except for the tongue position, and
involves the release of the breath from the glottal closure in the same
way as the other glottalized sounds.
dl beeldléí (blanket)
The dl is produced as one sound, as gl is in the word glow.
tł tła (grease)
This sound is pronounced as unvoiced dl.
tł tł'ízí (goat)
This sound involves the release of the breath from the t position of the
tongue tip and teeth, from the contact of the sides of the tongue inside
the back teeth (normal l position), and the glottal closure. It has a
marked explosive quality. The sound is produced as a unit, as in the gl
of glow, cited above.
y yá (sky) you
w 'awéé' (baby) work
PALATALIZATION AND LABIALIZATION
It is to be noted that the sounds represented by g, t, k, h, gh, and ch,
ts (when heavily aspirated) are palatalized before e, i, and labialized
before o. By this it is meant that such a word as ké (shoe) is
pronounced as though it were written kyé, and tó (water) as though
written twó.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 gh sound, it practically resolves itself into a
w when followed by o. Thus tálághosh (soap) could be written táláwosh,
yishghoł (I'm running) as yishwoł etc.
k and h can also be pronounced as kw and hw before e, i, in which case
the combination is a distinct phoneme. In such cases the w must be
written. Thus kwe'é (here), kwii (here), hwii (satisfaction) etc.
TONE
The present system of writing Navaho employs only one diacritical to
express four tonal variations. This is the acute accent mark (´). If a
short vowel or n, both elements of a long vowel or a diphthong are
marked thus the tone indicated is high. If only the first element of a
long vowel or diphthong is marked the tone is falling from high, and if
only the last element is marked the tone is rising from low. When a
vowel, diphthong or n is unmarked the tone is l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ow and high tone in Navaho is similar to the difference in tone
of "are you" and "going" in the English question "are you going?"
'azee' (medicine) low tone
'azéé' (mouth) high tone
háadish? (where?) falling tone
shínaaí (my elder brother) rising tone
WORD AND SENTENCE STRUCTURE
Teachers will note that the possessive pronouns of Navaho are always
prefixed to the noun. Thus, we have shimá (my mother), nimá (your
mother), bimá (his mother), but never má. The stem -má has no
independent form and never occurs without a prefix.
The structure of the Navaho verb has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but is
more complex. The subject of the sentence is always incorporated in the
verb with a pronominal form, and other verbal elements. Ideas of time
and mode are likewise incorporated in the verb, and auxiliary verbs such
as will, did, have, might, etc. do not occur in Navaho. The ideas
conveyed by these independent words in English are expressed by
different forms of the verb itself in Navaho.
Another point in which Navaho sentence structure differs from English is
that English prepositions are postpositions in Navaho.
with my elder sister shádí bił (my elder sister, with her)
for my mother shimá bá (my mother for)
whereas normal word order in English is subject, verb, and object,
Navaho has subject, object, and verb.
PUBLICATIONS OF THE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INDIAN LIFE READERS
NAVAJO SERIES (bilingual in English and Navajo)
by J. B. Enochs, illustrated by Gerald Nailor
Little Man's family. preprimer, primer and reader
by Hildegard Thompson, illustrated by Van Tsihnahjinnie
Preprimer, Primer
Coyote Tales (reader)
by Ann Clark, illustrated by Hoke Denetsosie
Who Wants to be a Prairie Dog? (A Navajo fairy tale)
by Ann Clark, illustrated by Van Tsihnahjinnie
Little Herder in Autumn, in Winter (single volume)
Little Herder in Spring, in Summer (single volume)
In English only:
Little Navajo Herder (Autumn, Winter, Spring, Summer)
by Cecil S. King, Navajo New World Readers:
1. Away to School. Illustrated by Franklin Kahn
2. The Flag of My Country. Illustrated by Henry Bahe
(Material of mature concept and simple vocabulary for use by recently
non-English-speaking adolescents.)
SIOUX SERIES (in English and Dakota)
by Ann Clark, illustrated by Andrew Standing Soldier
Sioux Cowboy (preprimer)
The Pine Ridge Porcupine
The Grass Mountain Mouse
There Still are Buffalo
Bringer of the Mystery Dog (illustrated by Oscar Howe)
Brave Against the Enemy (photographic illustrations by Helen Post)
Singing Sioux Cowboy (Primer)
The Slim Butte Raccoon
The Hen of Wahpeton
PUEBLO SERIES
by Ann Clark (in English and Spanish)
Little Boy With Three Names (illustrated by Tonita Lujan) Taos
Young Hunter of Picuris (illustrated by Velino Herrera)
Sun Journey (illustrated by Percy Sandy) Zuni
by Edward A. Kennard (in English and Hopi)
Field Mouse Goes to War (illustrated by Fred Kabotie)
Little Hopi (illustrated by Charles Loloma)
ALASKA STORIES
by Edward A. Keithahn, illustrated by George A. Ahgapuk
Igloo Tales
Also pamphlets on Indian Life and Customs, and Indian Handcrafts
for catalog and price list write to
HASKELL INSTITUTE
* * * * *
Transcriber's Notes:
Spelling changes made:
Foreword: "Mr. Robert W. Young, assocate [associate] of Dr. Harrington"
Pg 034: "ts ocurs [occurs] in the beginning"
Pg 034: "final position in Englsh [English]."
Pg 034: "This harsh pronounciation [pronunciation]"
Changes not made - multiple spellings of:
"pre-primer", "preprimer"
"bi-lingual", "bilingual"
End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Little Man's Family, by J. B. Enochs
*** END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LITTLE MAN'S FAMILY ***
***** This file should be named 37829-0.txt or 37829-0.zip *****
This and all associated files of various formats will be found in:
http://www.gutenberg.org/3/7/8/2/37829/
Produced by Juliet Sutherland, Fulvia Hughes and the Online
Distributed Proofreading Team at http://www.pgdp.net
Updated editions will replace the previous one--the old editions
will be renamed.
Creating the works from public domain print editions means that no
one owns a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in these works, so the Foundation
(and you!) can copy and distribute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ermission and without paying copyright royalties. Special rules,
set forth in the General Terms of Use part of this license, apply to
copying and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ncept and trademark.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may not be used if you
charge for the eBooks, unless you receive specific permission. If you
do not charge anything for copies of this eBook, complying with the
rules is very easy. You may use this eBook for nearly any purpose
such as creation of derivative works, reports, performances and
research. They may be modified and printed and given away--you may do
practically ANYTHING with public domain eBooks. Redistribution is
subject to the trademark license, especially commercial
redistribution.
*** START: FULL LICENSE ***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PLEASE READ THIS BEFORE YOU DISTRIBUTE OR USE THIS WORK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by using or distributing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you agree to comply with all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available with this file or online at
http://gutenberg.org/license).
Section 1. General Terms of Use and Re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1.A. By reading or using any part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you indicate that you have read, understand, agree to
and accept all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mark/copyright) agreement. If you do not agree to abide by all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cease using and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n your possession.
If you paid a fee for obtaining a copy of or access to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and you do not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ay obtain a refund from the person or
entity to whom you paid the fee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8.
1.B.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It may only be
used on or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an electronic work by people who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you can do with most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even without complying with the full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See
paragraph 1.C below.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do with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f you follow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and help preserve free future access to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See paragraph 1.E below.
1.C.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or PGLAF), owns a compilation copyright in the collec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Nearly all the individual works in the
collection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an
individual work is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are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do not claim a right to prevent you from
copying, distributing, performing, display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e work as long as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are removed. Of course, we hope that you will suppor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mission of promoting free access to electronic works by
freely sharing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keep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 You can easily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y
keeping this work in the same format with its attached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when you share it without charge with others.
1.D.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located also govern
what you can do with this work. Copyright laws in most countries ar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change. If you ar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check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in addition to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efore downloading, copy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distribut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is work or any other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The Foundation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concerning
the copyright status of any work in any country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1.E. Unless you have removed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1.E.1. The following sentence, with active links to, or othe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must appear prominently
whenever any copy of a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any work on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ppears, or with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is associated) is accessed, displayed, performed, viewed,
copied or distributed: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1.E.2.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is derived
from the public domain (does not contain a notice indicating that it is
pos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the work can be copied
and distributed to an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aying any fees
or charges. If you are redistributing or providing access to a work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ssociated with or appearing on the
work, you must comply either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or obtain permission for the use of the work and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s 1.E.8 or
1.E.9.
1.E.3.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i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your use and distribution
must comply with both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and any additional
terms impos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 Additional terms will be linked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for all work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f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work.
1.E.4. Do not unlink or detach or remov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terms from this work, or any files containing a part of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with Project Gutenberg-tm.
1.E.5. Do not copy, display, perform, distribute or redistribute this
electronic work, or any part of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out
prominently displaying the sentence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1 with
active links o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1.E.6. You may convert to and distribute this work in any binary,
compressed, marked up, nonproprietary or proprietary form, including any
word processing or hypertext form. However, if you provide access to or
distribute copies of a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in a format other than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at used in the official version
posted on the official Project Gutenberg-tm web site (www.gutenberg.org),
you must, at no additional cost, fee or expense to the user, provide a
copy, a means of exporting a copy, or a means of obtaining a copy upon
request, of the work in its original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 Any alternate format must includ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a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1.E.1.
1.E.7. Do not charge a fee for access to, view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copying or distributing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unless you comply with paragraph 1.E.8 or 1.E.9.
1.E.8. You may charge a reasonable fee for copies of or providing
access to or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provided
that
- You pay a royalty fee of 20% of the gross profits you derive from
the use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
you already use to calculate your applicable taxes. The fee is
owed to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but he
has agreed to donate royalties under this paragraph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Royalty payments
must be paid within 60 days following each date on which you
prepare (or are legally required to prepare) your periodic tax
returns. Royalty payments should be clearly marked as such and
sent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t the
address specified in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 You provide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by a user who notifies
you in writing (or by e-mail) within 30 days of receipt that s/he
does not agree to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You must require such a user to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the works possessed in a physical medium
and discontinue all use of and all access to other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 You provide,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F.3,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for a work or a replacement copy, if a defect in the
electronic work is discovered and reported to you within 90 days
of receipt of the work.
- You comply with all other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free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1.E.9. If you wish to charge a fee or distribute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or group of works on different terms than are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obtain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both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Michael
Hart,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Contact the
Foundation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3 below.
1.F.
1.F.1. Project Gutenberg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expend considerable
effort to identify, do copyright research on, transcribe and proofread
public domain works in creat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llection. Despite these efforts,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and the medium on which they may be stored, may contain
"Defect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incomplete, inaccurate or
corrupt data, transcription errors, a copyrigh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a defective or damaged disk or other medium, a
computer virus, or computer codes that damage or cannot be read by
your equipment.
1.F.2. LIMITED WARRANTY, DISCLAIMER OF DAMAGES - Except for the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F.3,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and any other party distributing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under this agreement, disclaim all
liability to you for damages,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YOU AGREE THAT YOU HAVE NO REMEDIES FOR NEGLIGENCE, STRICT
LIABILITY, BREACH OF WARRANTY OR BREACH OF CONTRACT EXCEPT THOSE
PROVIDED IN PARAGRAPH 1.F.3. YOU AGREE THAT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D ANY DISTRIBUTOR UNDER THIS AGREEMENT WILL NOT BE
LIABLE TO YOU FOR ACTUAL, DIRECT, INDIRECT, CONSEQUENTIAL, PUNITIVE OR
INCIDENTAL DAMAGES EVEN IF YOU GIVE NOTICE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1.F.3.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 If you discover a
defect in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in 90 days of receiving it, you can
receive a refund of the money (if any) you paid for it by sending a
written explanation to the person you received the work from.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on a physical medium, you must return the medium with
your written explanation. The person or entity that provided you with
the defective work may elect to provide a replacement cop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the person or entity
providing it to you may choose to give you a second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the second copy
is also defective, you may demand a refund in writing without further
opportunities to fix the problem.
1.F.4. Except for the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F.3, this work is provided to you 'AS-IS' WITH NO OTHER
WARRANTIES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RANTIES OF MERCHANTIBILITY OR FITNESS FOR ANY PURPOSE.
1.F.5. Some states do not allow disclaimers of certain implied
warranties or the exclusion or limitation of certain types of damages.
If any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violates the
law of the state applicable to this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shall be
interpreted to make the maximum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permitted by
the applicable state law. The invalidity or unenforceability of any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void the remaining provisions.
1.F.6. INDEMNITY - You agree to indemnify and hold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y agent or employee of the Foundation, anyone
providing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greement, and any volunteer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promo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harmless from all liability,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that ari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any of the following which you do
or cause to occur: (a) distribution of this or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b) alteration, modification, or additions or deletions to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and (c) any Defect you cause.
Section 2. Information about the Miss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Project Gutenberg-tm is synonymous with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in formats readable by the widest variety of computers
including obsolete, old, middle-aged and new computers. It exists
because of the efforts of hundreds of volunteers and donations from
people in all walks of life.
Volunteers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vide volunteers with the
assistance they need, are critical to reaching Project Gutenberg-tm's
goals and ensuring tha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llection will
remain freely available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In 2001,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was created to provide a secure
and permanent future for Project Gutenberg-tm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how your efforts and donations can help, see Sections 3 and 4
and the Foundation web page at http://www.pglaf.org.
Section 3.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is a non profit
501(c)(3)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nd granted tax exempt status by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The Foundation's EIN or 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is 64-6221541. Its 501(c)(3) letter is posted at
http://pglaf.org/fundrais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re tax deductible to the full extent
permitted by U.S. federal laws and your state's laws.
The Foundation's principal office is located at 4557 Melan Dr. S.
Fairbanks, AK, 99712., but its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are scattered
throughout numerous locations. Its business office is located at
809 North 1500 West, Salt Lake City, UT 84116, (801) 596-1887, email
[email protected]. Email contact links and up to date contac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the Foundation's web site and official
page at http://pglaf.org
For additional contact information:
Dr. Gregory B. Newby
Chief Executive and Director
[email protected]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Project Gutenberg-tm depends upon and cannot survive without wide
spread public support and donations to carry out its mission of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ublic domain and licensed works that can be
freely distributed in machine readable form accessible by the widest
array of equipment including outdated equipment. Many small donations
($1 to $5,000)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aintaining tax exempt
status with the IRS.
The Foundation is committed to complying with the laws regulating
charities and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all 50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are not uniform and it takes a
considerable effort, much paperwork and many fees to meet and keep up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We do not solicit donations in locations
where we have not received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compliance. To
SEND DONATIONS or determine the status of compliance for any
particular state visit http://pglaf.org
While we cannot and do not solicit contributions from states where we
have not met the solicitation requirements, we know of no prohibition
against accepting unsolicited donations from donors in such states who
approach us with offers to donate.
International donations are gratefully accepted, but we cannot make
any statements concerning tax treatment of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U.S. laws alone swamp our small staff.
Please check the Project Gutenberg Web pages for current donation
methods and addresses. Donations are accepted in a number of other
ways including checks, online payments and credit card donations.
To donate, please visit: http://pglaf.org/donate
Section 5.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Professor Michael S. Hart is the originato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ncept of a library of electronic works that could be freely shared
with anyone. For thirty years, he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Project
Gutenberg-tm eBooks with only a loose network of volunteer support.
Project Gutenberg-tm eBooks are often created from several printed
editions, all of which are confirmed as Public Domain in the U.S.
unless a copyright notice is included. Thus, we do not necessarily
keep eBooks in compliance with any particular paper edition.
Most people start at our Web site which has the main PG search facility:
http://www.gutenberg.org
This Web site includes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tm,
including how to make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how to help produce our new eBooks, and how to
subscribe to our email
Douglas McKay, Secretary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Glenn L. Emmons, Commissioner
BRANCH OF EDUCATION
Hildegard Thompson, Chief
Single Copy Price 20 cents
Phoenix Indian School Print Shop
Phoenix, Arizona
Third Edition 5,000 copies--September 1953
Little Man's family
diné yázhí ba'áłchíní
pre-primer
[Illustration]
by
J. B. Enochs
illustrated by
Gerald Nailor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FOREWORD
This pre-primer is one of three little books based on material prepared
by J. B. Enochs, who once taught in the sanitarium school at Kayenta. It
deals entirely with typical life experiences among the Navaho, the
largest Indian tribe in the United States, numbering approximately
65,000. Nine out of ten Navahos do not speak English, and the tribe has
never had a written language.
Missionaries and scientists for many years have had alphabets with which
to record this difficult language. But these alphabets have usually
included letters not found in English, and have been peppered with
diacritical marks to indicate inflection, tonal change and nasalization.
Thus they proved too complicated for popular use. Space does not permit
mention of many who have worked with the Navaho language. Finally Dr.
John Harrington,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nd Mr. Oliver LaFarge,
author and linguist, collaborated to produce a simplified alphabet which
might be written with an ordinary typewriter. Mr. Robert W. Young,
associate of Dr. Harrington, experimentally recorded a great deal of
material in this new alphabet. The Navaho portions of later pamphlets in
this bi-lingual series are the joint work of Harrington and Young.
=Little Man's Family= has been expressed in Navaho, using the
Harrington-LaFarge alphabet, by Willetto Antonio, a Navaho teacher on
the reservation, and Dr. Edward Kennard, formerly a specialist in Indian
languages for the Indian Service. Both the recording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in these books have been checked by Chic Sandoval, Howard
Gorman, and Adolph Bitanny, Navaho interpreters, and by Robert W. Young.
Back pages contain an explanation of the sound values represented by the
alphabet, and the indications of tonal change and nasalization which are
used.
These bi-lingual texts are an attempt to speed up Indi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life. Use of native languages to speed up acquisition of
English in Federal schools is a new departure in Indian policy, which
has proved very successful.
The type used for these books has been selected because of its
similarity in design to the alphabet used for manuscript writing. In the
primers, only proper names and the pronoun I have to be capitalized, so
as to further minimize the new learnings often encountered by the
primary child when faced with several different alphabets at once.
Willard W. Beatty
Revised February 1950
[Illustration]
I am a Navaho boy.
diné 'ashkii nishłį́.
[Illustration]
my mother
shimá
[Illustration]
my father
shizhé'é
[Illustration]
my baby brother
'awéé' sitsilí
[Illustration]
our baby's cradle
nihe'awéé' bits'áál
[Illustration]
my big sister
shádí
[Illustration]
my little sister
shideezhí
[Illustration]
our hogan
nihighan
[Illustration]
my father made our hogan
shizhé'é nihighan 'áyiilaa.
[Illustration]
our sweathouse
nihitáchééh
[Illustration]
the soapweed plant
tsá'ászi'
[Illustration]
we wash our hair
nihitsii' tanínádeiigis
[Illustration]
our sheep
nihidibé
[Illustration]
our goats
nihitł'ízí
[Illustration]
our corral
nihidibé bighan
[Illustration]
our horses
nihilį́į́'
[Illustration]
our wagon
nihitsinaabąąs
[Illustration]
my mother's saddle
shimá bilį́į́' biyéél
[Illustration]
my father's saddle
shizhé'é bilį́į́' biyéél
[Illustration]
my little spotted pony
shilé'éyázhí łikizh
[Illustration]
my black dog
shilééchąąshzhiin
[Illustration]
my mother's loom
shimá bidah'iistł'ǫ́
[Illustration]
my mother cleans the wool.
shimá 'aghaa' hasht'eilééh
[Illustration]
my mother cards the wool.
shimá 'aghaa' hanéiniłcha'.
[Illustration]
my mother spins the wool
shimá 'aghaa' hanéiniłdis.
[Illustration]
my mother weaves a rug.
shimá diyogí yitł'ó.
[Illustration]
my sisters help my mother.
shádí dóó shideezhí shimá yíká 'anáhi'nilchééh.
[Illustration]
we sell the rug.
diyogí ninádahiilnih.
THE NAVAHO ALPHABET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Navaho alphabet and its use
should prove helpful to one familiar with the English language.
VOWELS
The vowels have continental values. They are as follows, the first
example being a Navaho word, the second the closest approximation to the
sound in an English word:
a gad (juniper) father
e ké (shoe) met
i sis (belt) or as in sit or as in
dishááh (I'm starting) pique
o doo (not) note
Vowels may be either long or short in duration, the long vowel being
indicated by a doubling of the letter. This never affects the quality of
the vowel, except that long i is always pronounced as in pique.
sis (belt) is short siziiz (my belt) is long
Vowels with a hook beneath the letter are nasalized. That is, some of
the breath passes through the nose in their production. After n, all
vowels are nasalized and are not marked.
tsinaabąąs (wagon)
jį́ (day)
kǫ́ǫ́ (here)
DIPHTHONGS
The diphthongs are as follows:
ai hai (winter) aisle
ei séí (sand) weigh
oi 'ayóí (very) Joey
The diphthongs oi (as in Joey) will frequently be heard as ui (as in
dewy) in certain sections of the reservation. However, since the related
word ayóó is always of one value, this spelling has been standardized.
In a similar way, the diphthongs ei and ai are not universally
distinguished. For example, the word for sand, séí will be pronounced
sáí by some Navahos.
CONSONANTS
The consonants are as follows:
b bá (for him) like p in spot
d díí (this) like t in stop
g gah (rabbit) like k in sky
These sounds are not truly voiced as are the sounds represented by these
letters in English, but are like the wholly unaspirated p, t, and k in
the English words given as examples.
t tó (water) tea
k ké (shoe) kit
The t and k in Navaho are much more heavily aspirated than in the
English words given in the examples, so that the aspiration has a harsh
fricative quality.
' glottal stop yá'át'ééh (it is good) unh unh, oh oh
In the American colloquial negative unh unh, and in the exclamatory
expression oh oh, the glottal stop precedes the u and the o
respectively. Or, in actual speec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Johnny earns
and Johnny yearns, is that the former has a glottal closure between the
two words.
t' yá'át'ééh (it is good)
This letter represents the sound produced by the almost simultaneous
release of the breath from the closure formed by the tip of the tongue
and the teeth and the glottal closure described previously.
k' k'ad (now)
This sound is produced in the same way as the t', except that the k
closure is formed by the back of the tongue and the soft palate.
m mósí (cat) man
n naadą́ą́' (corn) no
s sis (belt) so
sh shash (bear) she
z zas (snow) zebra
zh 'ázhi' (name) azure
l laanaa (would that) let
ł łid (smoke)
This sound is made with the tongue in exactly the same position as in
the ordinary l, but the voice box or larynx does not func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l's is the same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 and p, d and t, or s and z. If one attempts to pronounce th as in
thin followed by l without an intervening vowel a ł is produced. Thus
athłete.
h háadi (where) hot
In Navaho there are two sounds represented by the letter h. The
difference is in the intensity or fricativeness. Where h is the first
letter in a syllable it is by some pronounced like the ch of German.
This harsh pronunciation is the older, bu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Navahos tends to pronounce the sound much as in English.
gh hooghan (hogan)
This is the voiced equivalent of the harshly pronounced variety of h,
the functioning of the voice being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ounds.
j jádí (antelope) jug
This sound is an unaspirated ch, just as d and g represent unaspirated t
and k.
ch chizh (wood) church
ch' ch'il (plant)
This sound is produced in a fashion similar to the t' and k', but with
the release of the breath from the ch position and from the glottal
closure.
dz dził (mountain) adze
ts tsa (awl) hats
ts occurs in the beginning and middle of Navaho words, but only in final
position in English.
ts' ts'in (bone)
This sound is similar to ch', except for the tongue position, and
involves the release of the breath from the glottal closure in the same
way as the other glottalized sounds.
dl beeldléí (blanket)
The dl is produced as one sound, as gl is in the word glow.
tł tła (grease)
This sound is pronounced as unvoiced dl.
tł tł'ízí (goat)
This sound involves the release of the breath from the t position of the
tongue tip and teeth, from the contact of the sides of the tongue inside
the back teeth (normal l position), and the glottal closure. It has a
marked explosive quality. The sound is produced as a unit, as in the gl
of glow, cited above.
y yá (sky) you
w 'awéé' (baby) work
PALATALIZATION AND LABIALIZATION
It is to be noted that the sounds represented by g, t, k, h, gh, and ch,
ts (when heavily aspirated) are palatalized before e, i, and labialized
before o. By this it is meant that such a word as ké (shoe) is
pronounced as though it were written kyé, and tó (water) as though
written twó.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 gh sound, it practically resolves itself into a
w when followed by o. Thus tálághosh (soap) could be written táláwosh,
yishghoł (I'm running) as yishwoł etc.
k and h can also be pronounced as kw and hw before e, i, in which case
the combination is a distinct phoneme. In such cases the w must be
written. Thus kwe'é (here), kwii (here), hwii (satisfaction) etc.
TONE
The present system of writing Navaho employs only one diacritical to
express four tonal variations. This is the acute accent mark (´). If a
short vowel or n, both elements of a long vowel or a diphthong are
marked thus the tone indicated is high. If only the first element of a
long vowel or diphthong is marked the tone is falling from high, and if
only the last element is marked the tone is rising from low. When a
vowel, diphthong or n is unmarked the tone is l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ow and high tone in Navaho is similar to the difference in tone
of "are you" and "going" in the English question "are you going?"
'azee' (medicine) low tone
'azéé' (mouth) high tone
háadish? (where?) falling tone
shínaaí (my elder brother) rising tone
WORD AND SENTENCE STRUCTURE
Teachers will note that the possessive pronouns of Navaho are always
prefixed to the noun. Thus, we have shimá (my mother), nimá (your
mother), bimá (his mother), but never má. The stem -má has no
independent form and never occurs without a prefix.
The structure of the Navaho verb has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but is
more complex. The subject of the sentence is always incorporated in the
verb with a pronominal form, and other verbal elements. Ideas of time
and mode are likewise incorporated in the verb, and auxiliary verbs such
as will, did, have, might, etc. do not occur in Navaho. The ideas
conveyed by these independent words in English are expressed by
different forms of the verb itself in Navaho.
Another point in which Navaho sentence structure differs from English is
that English prepositions are postpositions in Navaho.
with my elder sister shádí bił (my elder sister, with her)
for my mother shimá bá (my mother for)
whereas normal word order in English is subject, verb, and object,
Navaho has subject, object, and verb.
PUBLICATIONS OF THE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INDIAN LIFE READERS
NAVAJO SERIES (bilingual in English and Navajo)
by J. B. Enochs, illustrated by Gerald Nailor
Little Man's family. preprimer, primer and reader
by Hildegard Thompson, illustrated by Van Tsihnahjinnie
Preprimer, Primer
Coyote Tales (reader)
by Ann Clark, illustrated by Hoke Denetsosie
Who Wants to be a Prairie Dog? (A Navajo fairy tale)
by Ann Clark, illustrated by Van Tsihnahjinnie
Little Herder in Autumn, in Winter (single volume)
Little Herder in Spring, in Summer (single volume)
In English only:
Little Navajo Herder (Autumn, Winter, Spring, Summer)
by Cecil S. King, Navajo New World Readers:
1. Away to School. Illustrated by Franklin Kahn
2. The Flag of My Country. Illustrated by Henry Bahe
(Material of mature concept and simple vocabulary for use by recently
non-English-speaking adolescents.)
SIOUX SERIES (in English and Dakota)
by Ann Clark, illustrated by Andrew Standing Soldier
Sioux Cowboy (preprimer)
The Pine Ridge Porcupine
The Grass Mountain Mouse
There Still are Buffalo
Bringer of the Mystery Dog (illustrated by Oscar Howe)
Brave Against the Enemy (photographic illustrations by Helen Post)
Singing Sioux Cowboy (Primer)
The Slim Butte Raccoon
The Hen of Wahpeton
PUEBLO SERIES
by Ann Clark (in English and Spanish)
Little Boy With Three Names (illustrated by Tonita Lujan) Taos
Young Hunter of Picuris (illustrated by Velino Herrera)
Sun Journey (illustrated by Percy Sandy) Zuni
by Edward A. Kennard (in English and Hopi)
Field Mouse Goes to War (illustrated by Fred Kabotie)
Little Hopi (illustrated by Charles Loloma)
ALASKA STORIES
by Edward A. Keithahn, illustrated by George A. Ahgapuk
Igloo Tales
Also pamphlets on Indian Life and Customs, and Indian Handcrafts
for catalog and price list write to
HASKELL INSTITUTE
* * * * *
Transcriber's Notes:
Spelling changes made:
Foreword: "Mr. Robert W. Young, assocate [associate] of Dr. Harrington"
Pg 034: "ts ocurs [occurs] in the beginning"
Pg 034: "final position in Englsh [English]."
Pg 034: "This harsh pronounciation [pronunciation]"
Changes not made - multiple spellings of:
"pre-primer", "preprimer"
"bi-lingual", "bilingual"
End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Little Man's Family, by J. B. Enochs
*** END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LITTLE MAN'S FAMILY ***
***** This file should be named 37829-0.txt or 37829-0.zip *****
This and all associated files of various formats will be found in:
http://www.gutenberg.org/3/7/8/2/37829/
Produced by Juliet Sutherland, Fulvia Hughes and the Online
Distributed Proofreading Team at http://www.pgdp.net
Updated editions will replace the previous one--the old editions
will be renamed.
Creating the works from public domain print editions means that no
one owns a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in these works, so the Foundation
(and you!) can copy and distribute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ermission and without paying copyright royalties. Special rules,
set forth in the General Terms of Use part of this license, apply to
copying and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ncept and trademark.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may not be used if you
charge for the eBooks, unless you receive specific permission. If you
do not charge anything for copies of this eBook, complying with the
rules is very easy. You may use this eBook for nearly any purpose
such as creation of derivative works, reports, performances and
research. They may be modified and printed and given away--you may do
practically ANYTHING with public domain eBooks. Redistribution is
subject to the trademark license, especially commercial
redistribution.
*** START: FULL LICENSE ***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PLEASE READ THIS BEFORE YOU DISTRIBUTE OR USE THIS WORK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by using or distributing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you agree to comply with all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available with this file or online at
http://gutenberg.org/license).
Section 1. General Terms of Use and Re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1.A. By reading or using any part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you indicate that you have read, understand, agree to
and accept all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mark/copyright) agreement. If you do not agree to abide by all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cease using and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n your possession.
If you paid a fee for obtaining a copy of or access to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and you do not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ay obtain a refund from the person or
entity to whom you paid the fee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8.
1.B.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It may only be
used on or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an electronic work by people who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you can do with most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even without complying with the full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See
paragraph 1.C below.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do with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f you follow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and help preserve free future access to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See paragraph 1.E below.
1.C.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or PGLAF), owns a compilation copyright in the collec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Nearly all the individual works in the
collection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an
individual work is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are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do not claim a right to prevent you from
copying, distributing, performing, display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e work as long as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are removed. Of course, we hope that you will suppor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mission of promoting free access to electronic works by
freely sharing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keep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 You can easily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y
keeping this work in the same format with its attached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when you share it without charge with others.
1.D.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located also govern
what you can do with this work. Copyright laws in most countries ar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change. If you ar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check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in addition to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efore downloading, copy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distribut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is work or any other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The Foundation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concerning
the copyright status of any work in any country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1.E. Unless you have removed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1.E.1. The following sentence, with active links to, or othe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must appear prominently
whenever any copy of a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any work on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ppears, or with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is associated) is accessed, displayed, performed, viewed,
copied or distributed: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1.E.2.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is derived
from the public domain (does not contain a notice indicating that it is
pos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the work can be copied
and distributed to an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aying any fees
or charges. If you are redistributing or providing access to a work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ssociated with or appearing on the
work, you must comply either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or obtain permission for the use of the work and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s 1.E.8 or
1.E.9.
1.E.3.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i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your use and distribution
must comply with both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and any additional
terms impos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 Additional terms will be linked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for all work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f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work.
1.E.4. Do not unlink or detach or remov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terms from this work, or any files containing a part of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with Project Gutenberg-tm.
1.E.5. Do not copy, display, perform, distribute or redistribute this
electronic work, or any part of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out
prominently displaying the sentence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1 with
active links o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1.E.6. You may convert to and distribute this work in any binary,
compressed, marked up, nonproprietary or proprietary form, including any
word processing or hypertext form. However, if you provide access to or
distribute copies of a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in a format other than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at used in the official version
posted on the official Project Gutenberg-tm web site (www.gutenberg.org),
you must, at no additional cost, fee or expense to the user, provide a
copy, a means of exporting a copy, or a means of obtaining a copy upon
request, of the work in its original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 Any alternate format must includ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a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1.E.1.
1.E.7. Do not charge a fee for access to, view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copying or distributing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unless you comply with paragraph 1.E.8 or 1.E.9.
1.E.8. You may charge a reasonable fee for copies of or providing
access to or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provided
that
- You pay a royalty fee of 20% of the gross profits you derive from
the use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
you already use to calculate your applicable taxes. The fee is
owed to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but he
has agreed to donate royalties under this paragraph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Royalty payments
must be paid within 60 days following each date on which you
prepare (or are legally required to prepare) your periodic tax
returns. Royalty payments should be clearly marked as such and
sent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t the
address specified in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 You provide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by a user who notifies
you in writing (or by e-mail) within 30 days of receipt that s/he
does not agree to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You must require such a user to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the works possessed in a physical medium
and discontinue all use of and all access to other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 You provide,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F.3,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for a work or a replacement copy, if a defect in the
electronic work is discovered and reported to you within 90 days
of receipt of the work.
- You comply with all other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free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1.E.9. If you wish to charge a fee or distribute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or group of works on different terms than are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obtain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both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Michael
Hart,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Contact the
Foundation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3 below.
1.F.
1.F.1. Project Gutenberg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expend considerable
effort to identify, do copyright research on, transcribe and proofread
public domain works in creat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llection. Despite these efforts,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and the medium on which they may be stored, may contain
"Defect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incomplete, inaccurate or
corrupt data, transcription errors, a copyrigh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a defective or damaged disk or other medium, a
computer virus, or computer codes that damage or cannot be read by
your equipment.
1.F.2. LIMITED WARRANTY, DISCLAIMER OF DAMAGES - Except for the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F.3,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and any other party distributing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under this agreement, disclaim all
liability to you for damages,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YOU AGREE THAT YOU HAVE NO REMEDIES FOR NEGLIGENCE, STRICT
LIABILITY, BREACH OF WARRANTY OR BREACH OF CONTRACT EXCEPT THOSE
PROVIDED IN PARAGRAPH 1.F.3. YOU AGREE THAT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D ANY DISTRIBUTOR UNDER THIS AGREEMENT WILL NOT BE
LIABLE TO YOU FOR ACTUAL, DIRECT, INDIRECT, CONSEQUENTIAL, PUNITIVE OR
INCIDENTAL DAMAGES EVEN IF YOU GIVE NOTICE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1.F.3.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 If you discover a
defect in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in 90 days of receiving it, you can
receive a refund of the money (if any) you paid for it by sending a
written explanation to the person you received the work from.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on a physical medium, you must return the medium with
your written explanation. The person or entity that provided you with
the defective work may elect to provide a replacement cop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the person or entity
providing it to you may choose to give you a second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the second copy
is also defective, you may demand a refund in writing without further
opportunities to fix the problem.
1.F.4. Except for the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F.3, this work is provided to you 'AS-IS' WITH NO OTHER
WARRANTIES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RANTIES OF MERCHANTIBILITY OR FITNESS FOR ANY PURPOSE.
1.F.5. Some states do not allow disclaimers of certain implied
warranties or the exclusion or limitation of certain types of damages.
If any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violates the
law of the state applicable to this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shall be
interpreted to make the maximum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permitted by
the applicable state law. The invalidity or unenforceability of any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void the remaining provisions.
1.F.6. INDEMNITY - You agree to indemnify and hold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y agent or employee of the Foundation, anyone
providing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greement, and any volunteer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promo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harmless from all liability,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that ari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any of the following which you do
or cause to occur: (a) distribution of this or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b) alteration, modification, or additions or deletions to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and (c) any Defect you cause.
Section 2. Information about the Miss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Project Gutenberg-tm is synonymous with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in formats readable by the widest variety of computers
including obsolete, old, middle-aged and new computers. It exists
because of the efforts of hundreds of volunteers and donations from
people in all walks of life.
Volunteers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vide volunteers with the
assistance they need, are critical to reaching Project Gutenberg-tm's
goals and ensuring tha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llection will
remain freely available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In 2001,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was created to provide a secure
and permanent future for Project Gutenberg-tm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how your efforts and donations can help, see Sections 3 and 4
and the Foundation web page at http://www.pglaf.org.
Section 3.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is a non profit
501(c)(3)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nd granted tax exempt status by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The Foundation's EIN or 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is 64-6221541. Its 501(c)(3) letter is posted at
http://pglaf.org/fundrais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re tax deductible to the full extent
permitted by U.S. federal laws and your state's laws.
The Foundation's principal office is located at 4557 Melan Dr. S.
Fairbanks, AK, 99712., but its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are scattered
throughout numerous locations. Its business office is located at
809 North 1500 West, Salt Lake City, UT 84116, (801) 596-1887, email
[email protected]. Email contact links and up to date contac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the Foundation's web site and official
page at http://pglaf.org
For additional contact information:
Dr. Gregory B. Newby
Chief Executive and Director
[email protected]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Project Gutenberg-tm depends upon and cannot survive without wide
spread public support and donations to carry out its mission of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ublic domain and licensed works that can be
freely distributed in machine readable form accessible by the widest
array of equipment including outdated equipment. Many small donations
($1 to $5,000)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aintaining tax exempt
status with the IRS.
The Foundation is committed to complying with the laws regulating
charities and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all 50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are not uniform and it takes a
considerable effort, much paperwork and many fees to meet and keep up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We do not solicit donations in locations
where we have not received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compliance. To
SEND DONATIONS or determine the status of compliance for any
particular state visit http://pglaf.org
While we cannot and do not solicit contributions from states where we
have not met the solicitation requirements, we know of no prohibition
against accepting unsolicited donations from donors in such states who
approach us with offers to donate.
International donations are gratefully accepted, but we cannot make
any statements concerning tax treatment of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U.S. laws alone swamp our small staff.
Please check the Project Gutenberg Web pages for current donation
methods and addresses. Donations are accepted in a number of other
ways including checks, online payments and credit card donations.
To donate, please visit: http://pglaf.org/donate
Section 5.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Professor Michael S. Hart is the originato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ncept of a library of electronic works that could be freely shared
with anyone. For thirty years, he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Project
Gutenberg-tm eBooks with only a loose network of volunteer support.
Project Gutenberg-tm eBooks are often created from several printed
editions, all of which are confirmed as Public Domain in the U.S.
unless a copyright notice is included. Thus, we do not necessarily
keep eBooks in compliance with any particular paper edition.
Most people start at our Web site which has the main PG search facility:
http://www.gutenberg.org
This Web site includes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tm,
including how to make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how to help produce our new eBooks, and how to
subscribe to our email
small disturbance made by the return of Anton had gradually settled
down. Those first-class treasures of Sabine's had made way for other
specimens of damask, still of a superior kind, it is true, but which
came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e elderly cousin's comprehension. She had
been quite right in prophesying that Anton would never remark those
signs of exuberant gratitude or their withdrawal. However, one change
had been permanently made--the greatest, the best of all changes--the
clerk retained a privileged place in the heart of the young mistress of
the firm, and his tall figure often appeared as one of the circle that
Sabine's fancy loved to gather round her when at her work-table or in
her treasure-chamber.
To-day she was walking restlessly up and down before dinner. The cousin,
who heard every thing, had just told her that a maid from Ehrenthal's
had run into the office to announce Bernhard's death to his friend. "How
will he bear it?" thought she. And the name of Ehrenthal forced her
thoughts back to the past, to one now far away, and to that painful hour
when the struggle going on in her own mind had been suddenly brought to
a close by a letter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parted. And Anton had known
of that conquered feeling of hers. How considerate he had always been,
how chivalrous, how helpful! She wondered if he had any idea of the
completeness of her triumph over a girlish illusion. She shook her head.
"No, he has not. It was here, at this very table, that an accident first
betrayed me to him. That past time still rises like a cloud between us.
Whenever I sit near Wohlfart of an evening, I am conscious of another's
shadow at my side; and when he speaks to me, his tone, his manner always
seem to say, 'You are not alone; he is with you.'" Sabine started, and
lovingly passed her hand over the beautiful flowers on the table before
her, as if to dispel a painful thought. She could not tell him that she
was free from that long-felt sorrow. Now, however, when he had lost a
friend whom he so much loved, she must show him that there were other
hearts that clung to him still. And again she walked up and down, trying
to devise a way of speaking to him alone.
Dinner was announced. Anton came with the rest, and took his place at
once. There was no opportunity of exchanging a word during the meal, but
he often met her sad and sympathizing eye. "He eats nothing at all
to-day," whispered her cousin; "not even any of the roast," she added,
reproachfully. Sabine was much perturbed. Mr. Jordan had already risen;
Anton would leave the room with the rest, and she should not see him
again the whole day through. So she called out, "The great Calla is
fully blown now. You were admiring the buds the other day; will you
remain a moment; I should like to show it you?" Anton bowed and staid
behind. A few more awkward moments, then her brother rose too; and,
hurrying to Anton, she took him to the room where the flowers were.
"You have had sorrowful tidings to-day," she began.
"The tidings themselves did not surprise me," replied Anton. "The doctor
gave no hope. But I lose much in him."
"I never saw him," said Sabine; "but I know from you that his life was
lonely--poor in affection and in enjoyment."
She moved an arm-chair toward Anton, and led him on to talk about his
friend. She listened to every word with warm sympathy, and well knew
what to ask and how to comfort. It was a relief to Anton to speak of the
departed one, to describe his quiet way of life, his erudition, his
poetical enthusiasm. After a pause, Sabine looked up frankly into his
face, and asked, "Have you any tidings of Herr von Fink?"
It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his departure that she had ever breathed his
name. Anton felt how touching her confidence was, given in this hour of
his sadness. In his emotion, he seized her hand, which she was slow in
withdrawing.
"He is not happy in his new life," he gravely replied. "There was a
savage humor in his last letter, from which I gather, even more than
from his actual words, that the business into which his uncle's death
has thrown him does not suit him."
"It is unworthy," cried Sabine.
"At all events, it is not what would be recognized as honorable in this
house," replied Anton. "Fink is upright, and has lived too long with
your brother to take pleasure in the wild speculations so common on the
other side the Atlantic. His partners and colleagues are for the most
part men without a conscience, and his feelings revolt against their
companionship."
"And can Herr von Fink tolerate such relations as these for a day?"
"It is a remarkable thing that he whose own will was ever so arbitrarily
exercised, should now be obliged against that will to obey a pressure
from without, and every where to work with his hands tied. The
organization of such speculations in America is so complicated that one
shareholder can do little to alter it; and, now that Fink has attained
what used to be the goal of his wishes--a large capital, and the
management of immense districts--his condition appears more uncertain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He was always in danger of thinking slightingly
of others, now I am distressed at the bitter contempt he expresses for
his own life. His last letter paints an intolerable state of things, and
seems to point to some decisive resolve."
"There is only one resolve for him," cried Sabine. "May I ask what you
said to him in reply?"
"I entreated him instantly, come what would, to free himself from the
business in which he was entangled. I said that his own strong will
might find a way of extrication, even if that which I pointed out proved
impracticable. Then I begged of him either to carry out his old plan of
becoming a landed proprietor in America, or to return to us."
"I knew that you would write thus," said Sabine, drawing a long breath.
"Yes, Wohlfart, he shall return," said she, gently, "but he shall not
return to us."
Anton was silent.
"And do you think that Herr von Fink will follow your advice?"
"I do not know. My advice was not very American."
"But it was worthy of you," cried Sabine, with proud delight.
"An officer wishes to speak to Mr. Wohlfart," said a servant at the
door.
Anton sprang up. Sabine went to her flowers and bent mournfully over
them. The shadows of others hovered still between her friend and her.
The few words spoken by the servant filled Anton with a vague terror. He
hurried into the ante-room: there stood Eugene von Rothsattel. Anton was
gladly rushing forward to greet him, but the young soldier's face of
agony made him start back. He whispered, "My mother wishes to speak to
you; something dreadful has occurred." Anton caught up his hat, ran into
the office, hurriedly asked Baumann to excuse him to the principal, and
then accompanied the lieutenant to the baron's house.
On the way, Eugene, who had lost all self-command, said unconnectedly to
Anton, "My father last night accidentally wounded himself by a
pistol-shot--a messenger was sent to summon me--when I came, I found my
mother in a swoon--my sister and I do not know what to do--Lenore
implored my mother on her knees to send for you--you are the only one in
whom w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our distress--I understand nothing about
business, but my father's affairs must be in a dreadful state--my mother
is beside herself--the whole house is in the greatest disorder."
From what Eugene said and what he did not say; from his broken sentences
and his look of agony, Anton guessed at the horrors of the previous
evening. In the boudoir of the baroness he found Lenore, weeping and
exhausted.
"Dear Wohlfart!" cried she, taking his hand and beginning again to sob,
while her head sank powerless on his shoulder.
Meanwhile Eugene walked up and down, wringing his hands, and at length
throwing himself on the sofa, he gave himself up to silent tears.
"It is horrible, Mr. Wohlfart," said Lenore, lifting up her head. "No
one may approach my father--Eugene may not, nor I--only my mother and
old John are with him; and early this morning the merchant Ehrenthal was
here, insisting that he must see my father. He screamed at my mother,
and called my father a deceiver, till she fainted away. When I rushed
into the room, the dreadful man went off threatening her with his
clenched fist."
Anton led Lenore to a chair and waited till she had told him all.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comforting in this case, and his own heart was
wrung to the utmost by the misery he witnessed.
"Call my mother, Eugene," said Lenore, at length.
Her brother left the room.
"Do not forsake us," implored Lenore, clasping her hands; "we are at the
last gasp; even your help can not save us."
"He is dead who might perhaps have done so," mournfully replied Anton.
"Whether I can be of any use I know not, but you can not doubt my
willingness to be so."
"No," cried Lenore. "And Eugene, too, thought of you at once."
The baroness now entered. She walked wearily; but, steadying herself by
a chair, she saluted Anton with dignity. "In our position," said she,
"we need a friend who knows more of business than we three do.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prevents the baron--possibly for a long time to
come--from managing his own affairs, and, little as I understand them, I
can see that our interests require prompt measures. My children have
mentioned you to me, but I fear I am unreasonable in asking you to
devote your time to our service."
She sat down, beckoned Anton to take a chair, and said to her children,
"Leave us; I shall be better able to tell Mr. Wohlfart the little that I
know when I do not see your grief."
When they were alone, she motioned him nearer and tried to speak, but
her lips quivered, and she hid her face in her handkerchief.
"Before I can consent, gracious lady," said he, "to your reposing in me
such confidence as this, I must first inquire whether the baron has no
relative or intimate friend to whom you could with less pain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I pray you to remember that my own knowledge of business
is but small, and my position not one to constitute me a proper
counselor to the baron."
"I know no one," said the baroness, hopelessly. "It is less painful to
me to tell you what I can not conceal, than to one of our own circle.
Consider yourself a physician sent for to visit a patient. The baron has
this morning told me some particulars of his present circumstances." And
then she proceeded to relate what she had gathered as to the nature of
his embarrassments, the danger in which the family property was placed,
and the capital needed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Polish estate.
"My husband," continued she, "has given me the key of his desk, and he
wishes Eugene, with the help of a man of business, to go over his
papers. I now request of you to make this examination together with my
son. When you need explanations, I will try to obtain them from the
baron. The question is now, whether you are inclined to undertake this
trouble for us, who are only strangers."
"I am most willing to do so," earnestly replied Anton; "and I hope that
the kindness of my principal will allow me the time needful for the
purpose, if you do not consider it more advisable to depute the baron's
experienced legal adviser to the task."
"There will be an opportunity of asking that gentleman's advice later,"
said the baroness.
Anton rose. "When do you wish to begin?"
"Immediately. I fear there is not a day to lose. I shall do all I can to
help you look the papers over." She led Anton into the next room, called
in Eugene, and unlocked the baron's desk. As she opened it she lost her
self-command for a moment, and moving to the window, the quivering of
the curtains betrayed the anguish that shook her fragile frame.
The mournful task began. Hour after hour passed. Eugene was in no
condition to peruse any thing, but his mother reached letters and
documents to Anton, and, though often obliged to desist a while, she
bravely returned to the task. Anton placed the papers in order, and
sought, by glancing over each, to arrive at least at a superficial view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It was evening, when the old servant opened the door in dismay, and
called out, "He is there again." The baroness could not repress a slight
scream, and made a gesture of aversion.
"I have told him that no one is at home, but he will not be dismissed;
he makes such a noise on the steps. I can not get rid of him."
"It will kill me if I hear his voice again," murmured the baroness.
"If the man be Ehrenthal," said Anton, rising, "I will try to get him
away. We have now done what was most necessary; have the goodness to
lock up these papers, and to allow me to return to-morrow." The baroness
silently assented, and sank back in her chair. Anton hurried off to the
ante-room, whence he could hear Ehrenthal's loudly-raised voi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usurer shocked him. His hat pushed half off his
head, his pale face swelled as if by drinking, his glazed eyes red with
tears, Ehrenthal stood before him, calling in broken sentences for the
baron, wailing and cursing alternately. "He must come! he must come at
once!" cried he; "the wicked man! A nobleman, indeed! he is a vagabond,
after whom I will send the police. Where is my money? Where is my
security? I want my mortgage from this man who is not at home."
Anton went straight up to him, and asked, "Do you know me, Mr.
Ehrenthal?" Ehrenthal turned his glazed eyes upon him, and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 friend of his dead son.
"He loved you!" he cried, in a lamentable voice. "He spoke to you more
than to his father. You were the only friend that he had on earth. Have
you heard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house of Ehrenthal?" continued he, in
a whisper. "Just as they stole the papers he died. He died with a hand
like this," and clenching his fist he struck his forehead. "Oh my son!
my son! why didst not thou forgive thy father!"
"We will go to your son," said Anton, taking the arm of the old man, who
unresistingly allowed himself to be led back to his own house.
From thence Anton hurried to Councilor Horn, with whom he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It was late before he returned home. In the midst of his anxiety about
those whose prosperity had filled his imagination years before,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in their adversity, reposed in him, dilated his
breast with a feeling of pride. He burned with desire to help them, and
hoped that his zealous devotion might yet find some way of rescue. As
yet he saw none. Looking up at the great building before him, so firm
and secure, in the moonlight, a thought flashed into his mind. If any
man could help them, it was his principal. His keen eye would be able to
unravel all the dark secrets in which the baron was entangled, and his
iron strength of will would crush the villains who held the unfortunate
nobleman in their power. And then he had a noble nature; he always
decided on the right, without an effort or a struggle. Anton looked at
the first floor. The whole house-front was dark, but in a corner room a
light still burned. It was the private office of his chief.
With sudden resolve, Anton begged the servant to take him to Mr.
Schröter, who looked with amazement at the unexpected visitor, and asked
what brought him, and whether any thing had happened.
"I implore your counsel--I implore your help," cried Anton.
"For yourself or for others?" inquired the merchant.
"For a family with whom I have accidentally become connected. They are
lost if a strong hand does not ward off the impending catastrophe."
Anton then rapidly related the occurrences of the afternoon, and,
seizing his principal's hand in his emotion, cried, "Have pity upon the
unhappy ladies, and help them."
"Help them!" replied the merchant; "how can I? Have you been
commissioned to apply to me, or are you only following the impulse of
your own feelings?"
"I am not commissioned; it is only the interest that I take in the
baron's fate which leads me to you."
"And what right have you to inform me of facts communicated in strict
confidence to yourself by the baron's lady?" asked the merchant, dryly.
"I am committing no indiscretion in telling you what will, in a few
days, be no secret, even to strangers."
"You are unusually excited, otherwise you would not forget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hatever, does a man of business venture to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without the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Of course, I shall make no wrong use of what you have said, but it was
by no means business-like, Wohlfart, to be so open toward me."
Anton was silent, feeling, indeed, that his principal was right, but yet
it seemed hard to be blamed for reposing confidence at such a time as
this. The merchant walked silently up and down; at length, stopping
before Anton, he said, "I do not now inquire how you come to take so
warm an interest in this family. I fear it is an acquaintance you owe to
Fink."
"You shall hear all," said Anton.
"Not at present. I will now content myself with repeating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interfere in these affairs without being specially
applied to by the parties themselves. I may add that I by no means wish
for such an application, and do not disguise from you that, were it
made, I should probably decline to do any thing for the Baron
Rothsattel."
Anton's feelings were roused to the utmost. "The question is the rescue
of an honorable man, and of lovely and amiable women from the toils of
rogues and impostors. To me, this seems the duty of every one; I, at
least, consider it a sacred obligation which I dare not shrink from. But
without your support I can do nothing."
"And how do you think this embarrassed man can be helped?" inquired the
merchant, seating himself.
With somewhat more composure, Anton repli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an experienced man of business making himself master of the case. There
must be some way of circumventing these villains. Your penetration would
discover it."
"Any attorney would be far more likely to do so, and the baron might
readily engage the services of experienced and upright legal advisers.
If his enemies have done any thing illegal, the quick eye of a lawyer is
the most likely to detect it."
"Alas! the baron's own lawyer gives but little hope," replied Anton.
"Then, my dear Wohlfart, no other is likely to do much good. Show me an
embarrassed man who has strength to grasp an offered hand, and bid me
help him, and for the sake of all I owe you, I will not refuse to do so.
I think you are convinced of this."
"I am," said Anton, dejectedly.
"From all I hear, however," the merchant went on,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the baron. From what I gather from general report, as well as from
you, his embarrassments arise from his having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usurers, which proves him deficient in what alone ennobles the life of
any man--good sense, and the power of steady exertion."
Anton could only sigh his assent.
"To help such a man," inexorably continued the merchant, "is a futile
attempt, against which reason may well protest. We are not to despair of
any, but want of strength is the most hopeless case of all. Our power of
laboring for others being limited, it becomes our duty to inquire,
before we devote our time to the weak, whether we are not thus
diminishing our chances of helping better men."
Anton interrupted him. "Does he not deserve every allowance to be made
for him? He was brought up to exact much; he has not learned, as we
have, to make his way by his own labor."
The merchant laid his hand on the young man's shoulder. "The very
reason. Believe me, a large number of these landed gentry, who pay the
penalty of their old family memories, are beyond help. I am the last to
deny that many worthy and admirable men belong to this class. Indeed,
wherever remarkable talent or nobility of character shoots up among
them, no doubt their position offers peculiar scope for its development,
but for average men it is not a favorable one. He who considers it his
hereditary privilege to enjoy life, and who assumes a distinguished
position in virtue of his family, will very often fail to put forth his
whole strength in order to deserve that position. Accordingly, numbers
of our oldest families are declining, and their fall will be no loss to
the state. Their family associations make them haughty without any
right to be so--limit their perceptions and confuse their judgment."
"Even if all this be true," cried Anton, "it does not absolve us from
helping individuals of the class who have excited our sympathy."
"No," said the principal, "if it be excited. But it does not glow so
rapidly in advancing years as in youth. The baron has endeavored to
isolate his property from the current of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leave it forever to his family. Forever! You, as a merchant, know how to
estimate the attempt. True, every rational man must allow it to be
desirable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same soil should be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We all prize what our forefathers have possessed before
us, and Sabine would unlock every room in this house with pride, because
her great-great-grandmother turned the same keys before her. It is
therefore natural that the landed proprietor should desire to preserve
those familiar scenes, which are the source of his own prosperity, to
those nearest and dearest to him. But there must be means to this end,
and these means are the making his own existence available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increase of his patrimony. Where energy dies in families
or individuals, then it is well that their means die too, that their
money should circulate through other hands, and their plowshare pass to
those who can guide it better. A family that has become effete through
luxury ought to sink down into common life, to make room for the
uprising of fresh energies and faculties. Every one who seeks, at the
cost of free activity for others, to preserve permanent possessions and
privileges for himself or his family, I must look upon as an enemy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social state. And if such a man ruin
himself in his endeavors, I should feel no malicious pleasure in his
downfall, but I should say that he is rightly served, because he has
sinned against a fundamental law of our social being; consequently, I
should consider it doubly wrong to support this man, because I could but
fear that I should thus be supporting an unsound condition of the body
politic."
Anton looked down mournfully. He had expected sympathy and warm
concurrence, and he met with disaffection and coldness that he despaired
of conquering. "I can not gainsay you," he at length replied; "but in
this case I can not feel as you do. I have been witness to the
unspeakable distress in the baron's family, and my whole soul is full
of sadness and sympathy, and of the wish to do something for those who
have opened their heart to me. After what you have said, I dare no
longer ask you to trouble yourself with their affairs, but I have
promised the baroness to assist her as far as my small powers permit,
and your kindness allows. I implore you to grant me permission to do
this. I shall endeavor to be regular in my attendance at the office, but
if during the next few weeks I am occasionally absent, I must ask you to
excuse me."
Once more the merchant walked up and down the room, and then, looking at
Anton's excited face, with deep seriousness and something of regret, he
replied, "Remember, Wohlfart, that every occupation which excites the
mind soon obtains a hold over a man, which may retard as well as advance
his success in life. It is thi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 to agree
to your wishes."
"I know it," said Anton, in a low voice; "but I have now no choice
left."
"Well, then, do what you must," said the merchant, gloomily; "I will lay
no hinderance in your way; and I hope that after a few weeks you will be
able to consider the whole circumstances more calmly." Anton left the
room, and the merchant stood looking long with frowning brow at the
place his clerk had occupied.
Nor was Anton in a more congenial mood. "So cold, so inexorable!"
exclaimed he, as he reached his own room. He began to suspect that his
principal was more selfish and less kindly than he had hitherto
supposed. Many an expression of Fink's recurred to his mind, as well as
that evening when young Rothsattel, in his boyish conceit, had spoken
impertinently to the merchant. "Is it possible," thought he, "that that
rude speech should be unforgotten?" And his chief's keen, deep-furrowed
face lost inexpressibly by contrast with the fair forms of the noble
ladies. "I am not wrong," he cried to himself; "let him say what he
will, my views are more just than his, and henceforth my destiny shall
be to choose for myself the way in which I shall walk." He sat long in
the darkness, and his thoughts were gloomy as it; then he went to the
window to look down into the dark court below. A great white blossom
rose before him like a phantom. Striking a light, he saw that it was the
beautiful Calla out of Sabine's room. It hung down mournfully on its
broken stem. Sabine had had it placed there. This little circumstance
struck him as a mournful omen.
Meanwhile Sabine, taper in hand, entered her brother's room.
"Good-night, Traugott," nodded she. "Wohlfart has been with you this
evening; how long he staid!"
"He will leave us," replied the merchant, gloomily.
Sabine started and dropped her taper on the table. "For God's sake, what
has happened? Has Wohlfart said that he was going away?"
"I do not yet know it, but I see it coming step by step; and I can not,
and still less can you, do any thing to retain him. When he stood before
me here with glowing cheeks and trembling voice, pleading for a ruined
man, I found out what it was that lured him away."
"I do not understand you," said Sabine, looking full at her brother.
"He chooses to become the confidential friend of a decayed noble. A pair
of bright eyes draws him away from us: it seems to him a worthy object
of ambition to become Rothsattel's man of business. This intimacy with
nobility is the legacy bequeathed to him by Fink."
"And you have refused to help him?" inquired Sabine, in a low voice.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said the merchant, harshly; and he
turned to his writing-table.
Sabine slowly withdrew. The taper trembled in her hand as she passed
through the long suite of rooms listening to her own footfall, and
shuddering as the feeling came over her that an invisible companion
glided by her side. This was the revenge of that other. The shadow that
once fell on her innocent life now drove her friend away from their
circle. Anton's affections clung to another. She had but been in his
eyes a mere stranger, who had once loved and languished for one now far
away, and who now, in widow's weeds, looked back regretfully to the
feelings of her youth.
The few next weeks were spent by Anton in over-hard work. He had great
difficulty in keeping up his counting-house duties, while he spent every
spare hour in conference with the baroness and the lawyer.
In the mean time, the misfortunes of the baron ran their course. He had
not been able to pay the interest of the sums with which his estate was
burdened. When last they were due, a whole series of claims was brought
against him, and the estate fell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district authorities. Complicated lawsuits arose. Ehrenthal complained
loudly, claiming the first mortgage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nay, he
was inclined to advance claims on the last mortgage offered by the baron
in the recent fatal hour. Löbel Pinkus also appeared as claimant of the
first mortgage, and asserted that he had paid the whole sum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Ehrenthal had no proof to bring forward, and had been
for some weeks past quite unable to manage his own affairs, while
Pinkus, on the contrary, fought with every weapon a hardened sinner can
devise or employ, and the deeds which the baron had executed at Veitel's
suggestion proved to be so capital a master-stroke of the cunning
advocate, that the baron's man of business had, from the first, little
hope of the case. We may here observe that Pinkus did eventually win it,
and that the mortgage was made over to him.
Anton was now gradually gaining some insight into the baron's
circumstances. But the double sale of the first mortgage was still kept
a secret by the latter, even from his wife. He declared Ehrenthal's
claim unfounded, and even expressed a suspicion that he had himself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robbery in his office. Indeed, he really
believed this. Then the name of Itzig was never broached, and the
suspicion against Ehrenthal, which the baron's lawyer shared, prevented
Anton seeking any explanation from him.
Meanwhile, an estrangement had sprung up between our hero and his
principal, which the whole counting-house remarked with surprise. The
merchant scowled at Anton's vacant seat when the latter chanced to be
absent during office-hours, or looked coldly at his clerk's face, made
pale as it was with excitement of mind and night-work. He took no notice
of his new occupation, and never seemed to remark him. Even to his
sister he maintained a stiff-necked silence; nor could all her attempts
lead him to speak of Anton, who, on his side, felt his heart revolt
against this coldness. After his return, to be treated like a child of
the house, praised, promoted, petted, and now to be treated like a mere
hireling, who is not worth the bread thrown to him; to be a toy of an
incomprehensible caprice--this, at least, he had not deserved; so he
became reserved toward the whole family, and sat silent at his desk; but
he fel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now and the then so keenly, that often,
when alone, he would spring up and stamp on the ground in the bitter
indignation of his heart.
One comfort remained. Sabine was not estranged. True, he saw little of
her, and at dinner she seemed to avoid speaking to him, but he knew that
she was on his side.
A few days after his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the merchant, she came down
stairs as he stood in the hall, and had to pass him by so closely that
her dress touched him. He had retreated, and made a formal bow, but she
looked at him imploringly, and whispered, "You must not be estranged
from me." It was an affair of a moment, but the faces of both were
radiant with a happy understanding.
The time had now arrived when Mr. Jordan was to quit the firm. The
principal again called Anton into his little office, and without any
severity, but also without a trace of his former cordiality, began: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o you my intention of appointing you Jordan's
successor; but,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your time has been more taken
up with other business than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such a post, I
therefore ask you whether you are now at liberty to undertake Jordan's
duties?"
"I am not," replied Anton.
"Can you name any--not very distant--time when you will be free from
your present occupation? In that case I will endeavor to find a
substitute until then."
Anton sorrowfully replied, "I can not at present say when I shall again
be master of my whole time; and, besides, I feel that, even as it is, I
tax your indulgence by many irregularities. Therefore, Mr. Schröter, I
beg that you will fill up this post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me."
The merchant's brow grew furrowed and dark, and he silently bowed
assent. Anton felt as he closed the door that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m was now complete, and, resuming his place, he leaned his throbbing
head on his hand. A moment later Baumann was summoned to the principal,
and Jordan's situation conferred upon him. On returning to the office,
he went up to Anton and whispered, "I refused at first, but Mr. Schröter
insisted. I am doing you an injustice." And that evening Mr. Baumann, in
his own room, read in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the chapters treating of
the unjust Saul (the principal), and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Jonathan
and the persecuted David, and strengthened his heart thereby.
The next day Anton was summoned to the baroness. Lenore and her mother
sat before a large table covered with jewel-boxes and toilette elegances
of every description, while a heavy iron chest stood at their feet. The
curtains were drawn, and the subdued light shone softly into the richly
furnished room. On the carpet glowed wreaths of unfading flowers, and
the clock ticked cheerfully in its alabaster case. Under the shade of
flowering plants sat the two love-birds in their silvered cage, hopping
from perch to perch, screaming ceaselessly, or sitting up quietly close
to each other. The whole room was beauty and perfume. "For how long?"
thought Anton. The baroness rose. "We are already obliged to trouble you
again," said she; "we are engaged in a very painful occupation." On the
table were all manner of ornaments, gold chains, brilliants, rings,
necklaces, gathered into a heap.
"We have been looking out all that we can dispense with," said the
baroness, "and now pray you to undertake to sell these things for us. I
have been told that some of them are of value, and as we are now in much
need of money, we turn here for help."
Anton looked in perplexity at the glittering heap.
"Tell us, Wohlfart," cried Lenore, anxiously, "is this necessary? can it
be of any use? Mamma has insisted upon setting apart for sale all our
ornaments, and whatever plate is not in daily use. What I can give is
not worth talking of, but my mother's jewels are costly; many of them
were presents made to her in youth, which she shall not part with unless
you say that it is necessary."
"I fear," said Anton, gravely, "that it will prove so."
"Take them," said the baroness to Anton; "I shall be calmer when I know
that we have at least done what we could."
"But do you wish to part with all?" inquired Anton, anxiously. "Much
that is dear to you may have but little value in a jeweler's eyes."
"I shall never wear an ornament again," quietly replied the baroness.
"Take them all;" and, holding her hands before her eyes, she turned
away.
"We are torturing my mother," cried Lenore, hastily; "will you lock up
all that is on the table, and get them out of the house as soon as you
can?"
"I can not undertake the charge of these valuables," said Anton,
"without taking some measures to decrease my own responsibility. First
of all, I will in your presence make a short note of all you intrust to
me."
"What useless cruelty!" exclaimed Lenore.
"It will not take long."
Anton took out a few sheets from his pocket-book, and began to note down
the different articles.
"You shall not see it done, mother," said Lenore, drawing her mother
away, and then returning to watch Anton at his task.
"These preparations for the market are horrible," said she. "My mother's
whole life will be sold; some memory of hers is linked with every single
thing. Look, Wohlfart, the princess gave her this diamond ornament when
she married my father."
"They are magnificent brilliants," cried Anton, admiringly.
"This ring was my grandfather's, and these are presents of poor papa's.
Alas! no man can know how we love all these things. It was always a
festival to me when mamma put on her diamonds. Now we come to my
possessions. They are not worth much. Do you think this bracelet good
gold?" She held out her hand as she spoke.
"I do not know."
"It shall go with the rest," said Lenore, taking it off. "Yes, you are a
kind, good man, Wohlfart," continued she, looking trustfully into his
tearful eyes; "do not forsake us. My brother has no experience, and is
more helpless than we are. It is a frightful position for me. Before
mamma I do all I can to be composed, else I could scream and weep the
whole day through." She sank in a chair, still holding his hand. "Dear
Wohlfart, do not forsake us."
Anton bent over her, and looked with passionate emotion at the lovely
face that turned so trustfully to him in the midst of its tears.
"I will be helpful to you when I can," said he, in the fullness of his
heart. "I will be at hand whenever you need me. You have too good an
opinion of my information and my faculties; I can be of less assistance
to you than you suppose, but what I can, that I will do in any and every
possible way."
Their hands parted with a warm pressure; the affair was settled.
The baroness now returned. "Our lawyer was with me this morning," said
she; "and now I must ask for your opinion on another subject. He tells
me that there is no prospect of preserving the baron's family estate."
"At this time, when interest is high, and money difficult to get, none,"
replied Anton.
"And you, too, think that we must turn all our efforts toward preserving
the Polish property?"
"I do," was the answer.
"For that, also, money will be necessary. Perhaps I may be able through
my relatives to intrust you with a small sum, which, with the help of
that"--she pointed to the iron chest--"may suffice to cover the first
necessary expenses. I do not, however, wish to sell the jewels here, and
a journey to the residence would be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cure the
sum to which I have just alluded. The baron's lawyer has spoken most
highly of your capacity for business. It is his wish which now decides
me to make a proposal to you. Will you for the next few years, or, at
all events, until our greatest difficulties are over, devote your whole
time to our affairs? I have consulted my children, and they agree with
me in believing that in your assistance lies our only hope of rescue.
The baron, too, has come in to the plan. The question now is whether
your circumstances allow you to give your support to our unfortunate
family. We shall be grateful to you, whatever conditions you affix; and
if you can find any way of making our great obligations to you apparent
in the position you hold, pray impart it to me."
Anton stood petrified. What the baroness required of him was separation
from the firm, separation from his principal, and from Sabine! Had this
thought occurred to him before, when standing in Lenore's presence or
bending over the baron's papers? At all events, now that the words were
spoken, they shocked him. He looked at Lenore, who stood behind her
mother with hands clasped in supplication. At length he replied, "I
stand in a position which I can not leav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others.
I was not prepared for this proposal, and beg to have time allowed me
for consideration. It is a step which will decide my whole future life."
"I do not press you," said the baroness; "I only request your
consideration. Whatever your decision be, our warmest gratitude will
still be yours; if you are unable to uphold our feeble strength, I fear
that we shall find no one to do so. You will think of that," she added,
beseechingly.
Anton hurried through the street with throbbing pulse. The noble lady's
glance of entreaty, Lenore's folded hands, beckoned him out of the
gloomy counting-house into a sphere of greater liberty, into a new
future, from whose depths bright images flashed out upon his fancy. A
request had been frankly made, and he was strongly inclined to justify
the confidence that prompted it. Those ladies required an unwearied,
self-sacrificing helper to save them from utter ruin, and if he
followed his impulse he should be doing a good work--fulfilling a duty.
In this mood he entered the merchant's dwelling. Alas! all that he saw
around him seemed to stretch out a hand to detain him. As he looked at
the warehouse, the good-humored faces of the porters, the chains of the
great scales, the hieroglyphics of the worthy Pix, again he felt that
this was the place that he belonged to. Sabine's dog kissed his hand,
and ran before him to his room--his and Fink's room. Here the childish
heart of the orphan boy had found a friend, kind companions, a home, a
definite and honorable life-purpose. Looking down through his window on
all the long-familiar objects, he saw a light in Sabine's store-chamber.
How often he had sought for that light, which brightened the whole great
building, and brought a sense of comfort and cheerfulness even into his
room. He now sprang up suddenly, and said to himself, "She shall
decide."
Sabine started in amazement when Anton appeared before her. "I am
irresistibly impelled to seek you," cried he. "I have to decide upon my
future life, and I feel undetermined, and unable to trust to my own
judgment. You have always been a kind friend to me since the day of my
arrival. I am accustomed to look up to you, and to think of you in
connection with all that interests me here. Let me hear your opinion
from your own lips. The Baroness Rothsattel has to-day proposed to me
permanently to undertake the situation of confidential adviser and
manager of the baron's affairs. Shall I accept; or shall I remain here?
I know not--tell me what is right both for myself and others."
"Not I," said Sabine, drawing back and growing very pale. "I can not
venture to decide in the matter. Nor do you wish me to do so, Wohlfart,
for you have already decided."
Anton looked straight before him and was silent.
"You have thought of leaving this house, and a wish to do so has sprung
out of the thought. And I am to justify you, and approve your resolve!
This is what you require of me," continued she, bitterly. "But this,
Wohlfart, I can not do, for I am sorry that you go away from us."
She turned away from him and leaned on the back of a chair.
"Oh, be not angry with me too!" said Anton; "that I can not bear. I have
suffered much of late. Mr. Schröter has suddenly withdrawn from me the
friendly regard that I long held my life's greatest treasure. I have not
deserved his coldness. What I have been doing has not been wrong, and
it was done with his knowledge. I had been spoiled by his kindness; I
have the more deeply felt his displeasure. My only comfort has been that
you did not condemn me. And now, do not you be cold toward me, else I
shall be wretched forever. There is not a soul on earth to whom I can
turn for affectionate comprehension of my difficulties. Had I a sister,
I should seek her heart to-day. You do not know what to me, lonely as I
am, your smile, your kindly shake of the hand has been till now. Do not
turn coldly from me, I beseech you."
Sabine was silent. At length she inquired, still with averted face,
"What draws you to those strangers; is it a joyful hope, is it sympathy
alone? Give this question close consideration before you answer it to
yourself at least."
"What it is that makes it possible for me to leave this house," said
Anton, "I do not myself know. If I can give a name to my motives, it is
gratitude felt toward one. She was the first to speak kindly to the
wandering boy on his way out into the world. I have admired her in the
peaceful brightness of her former life. I have often dreamed childish
dreams about her. There was a time when a tender feeling for her filled
my whole heart, and I then believed myself forever the slave of her
image. But years bring changes, and I learned to look on men and on life
with other eyes. Then I met her again, distressed, unhappy, despairing,
and my compassion became overmastering. When I am away from her, I know
that she is nothing to me; when I am with her, I feel only the spell of
her sorrow. Once, when I had to depart out of her circle like a culprit,
she came to me, and before the whole scornful assembly she gave me her
hand and acknowledged me her friend; and now she comes and asks for my
hand to help her father. Can I refuse it? Is it wrong to feel as I do? I
know not, and no one can tell me--no one but you alone."
Sabine's head had sunk down to the back of the chair on which she bent.
She now suddenly raised it, and with tearful eyes, and a voice full of
love and sorrow, cried, "Follow the voice that calls you. Go, Wohlfart,
go."
CHAPTER XXVII.
On a cold October day, two men were seen driving through the latticed
gate of the town of Rosmin on toward the plain, which stretched out
before them monotonous and boundless. Anton sat wrapped in his fur coat,
his hat low on his forehead, and at his side was young Sturm, in an old
cavalry cloak, with his soldier's cap cocked cheerily on one side. In
front of them a farm-servant, squatted on a heap of straw, flogged on
the small horses. The wind swept the sand and straw from the
stubble-fields, the road was a broad causeway without ditches or hedges,
the horses had to wade alternately through puddles and deep sand. Yellow
sand gleamed through the scanty herbage in all directions wherever a
field-mouse had made her way to her nest or an active mole had done what
he could to diversify the unbroken plain. Wherever the ground sank,
stagnant water lodged, and there hollow willow-trees stretched their
crippled arms in the air, their boughs flapping in the wind, and their
faded leaves fluttering down into the muddy pool below. Here and there
stood a small dwarf pine, a resting-place for the crows, who, scared by
the passing carriage, flew loudly croaking over the travelers' heads.
There was no house to be seen on the road, no pedestrian, and no
conveyance of any kind.
Karl looked every now and then at his silent companion, and said at
last, pointing to the horses, "How rough their coats are, and how pretty
their gray mouse skins! I wonder how many of these beasties would go to
make up my sergeant's horse! When I took leave of my father, the old man
said, 'Perhaps I shall pay you a visit, little one, when they light the
Christmas-tree.' 'You'll never be able,' said I. 'Why not?' asked he.
'You'll never trust yourself in any post-chaise.' Then the old boy
cried, 'Oho! post-chaises are always of a stout build; I shall be sure
to trust myself in one.' But now, Mr. Anton, I see that my father never
can pay us a visit."
"Why not?"
"It is possible that he may reach Rosmin; but, as soon as he sees these
horses and this road, he will instantly turn back. 'Shall I trust
myself,' he'll say, 'in a district where sand runs between one's legs
like water, and where mice are put into harness? The ground is not firm
enough for me.'"
"The horses are not the worst things here," said Anton, absently. "Look!
these go fast enough."
"Yes," replied Karl, "but they don't go like regular horses; they
entangle their legs like two cats playing in a parsley-bed. And what
things they have for shoes--regular webbed hoofs, I declare, which no
blacksmith can ever fit."
"If we could only get on!" returned Anton; "the wind blows cold, and I
am shivering in spite of my fur."
"You have slept but little the last few nights, sir," said Karl. "The
wind blows here as if over a threshing-floor. The earth is not round
hereabouts as elsewhere, but flat as a cake. This is a complete desert;
we have been driving for more than an hour, and there is not a village
to be seen."
"A desert indeed," sighed Anton; "let us hope it may improve." They
relapsed into profound silence. At length the driver stopped near a
pool, unharnessed the horses, and led them to the water's edge, without
noticing the travelers.
"What the deuce does this mean?" cried Karl, jumping down from the
carriage.
"I am going to feed," replied the servant, sulkily, in a foreign accent.
"I am anxious to know how that will be done," said Karl. "There is not
the shadow of a bag of provender."
The horses, however, soon proved that they could live without corn; they
stretched down their shaggy heads, and began to pull the grass and weeds
at the edge of the pool, sometimes taking a draught of the dirty water.
Meanwhile the servant drew a bundle from under his seat, settled himself
under the lee of an alder-bush, and, taking his knife, cut his bread and
cheese without even glancing at the travelers.
"I say, Ignatius or Jacob," cried Karl, sharply, "how long will this
breakfast of yours last?"
"An hour," replied the man, munching away.
"And how far is it from here to the estate?"
"Six miles, or maybe more."
"You can make nothing of him," said Anton; "we must put up with the
customs of the country;" and, leaving the carriage, they went to look on
at the horses feeding.
Anton is on his way to the Polish property. He is now the baron's agent.
Anxious months have the last proved to him. The parting from his
principal and the firm had been painful in the extreme. For some time
before it, indeed, Anton had found himself alone in the midst of his
colleagues. The quiet Baumann still remained his friend, but the others
considered him a castaway. The merchant received his resignation with
icy coldness; and even in the hour of parting, his hand lay impassive as
metal in Anton's grasp. Since then, our hero had undertaken several
journeys to the capital and to creditors in the family's behalf, and now
he was on his way to set the new estate in order, accompanied by Karl,
whom he had induced to become the baron's bailiff.
Ehrenthal had, by the authority conferred on him,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from the time of the sale by auction, and hired the Polish
bailiff for the baron. There had been unfair dealings between them at
the time, and it was well known in Rosmin that the bailiff had sold off
a good deal, and been guilty of all sorts of frauds since, so that Anton
had even now no prospect of a quiet life.
"The hour is come when I may execute my commission," cried Karl, groping
in the straw under the seat. He drew out a large japanned tin case, and
carried it to Anton. "Miss Sabine gave me this in charge for you." He
then joyously opened the lid, produced the materials for an excellent
breakfast, a bottle of wine, and a silver goblet. Anton took hold of the
case.
"It has a very knowing look," said Karl. "Miss Sabine planned it
herself."
Anton examined it on all sides, and placed it carefully on a tuft of
grass; then he took up the goblet, and saw his initials engraved on it,
and underneath the words, "To thy welfare." Whereupon he forgot the
breakfast and all around him, and stood gazing at the goblet, lost in
thought.
"Do not forget the breakfast, sir," suggested Karl, respectfully.
"Sit down by me, my faithful friend; eat and drink with me. Leave off
your absurd politeness. We shall have but little, either of us, but what
we have we will share like brothers. Take the bottle if you have no
glass."
"There's nothing like leather," said Karl, taking a small leathern
drinking-cup out of his pocket. "As for 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t was
kindly meant, and I thank you; but there must be subordination, if it
were but for the sake of the others; and so, sir, be kind enough to let
me shake hands with you now, and then let things be as they were before.
Only look at the horses, Mr. Anton. My faith! the creatures devour
thistles."
Again the horses were harnessed, again they threw out their short legs
in the sand, and again the carriage rolled through the barren
district--first through an empty plain, next through a wretched
fir-wood, then past a row of low sand-hills, then over a tumble-down
bridge crossing a small stream.
"This is the property," said the driver, turning round, and pointing
with his whip to a row of dirty thatched roofs that had just come into
sight.
Anton stood up to look for the group of trees in which the Hall might be
supposed to stand. Nothing of the sort to be seen. The village was
deficient in all that adorns the home of the poorest German peasant--no
orchard, no hedged-in gardens, no lime-trees in the market-place.
"This is wretched," said he, sitting down again; "much worse than they
told us in Rosmin."
"The village looks as if under a curse," cried Karl; "no teams working
in the fields--not a cow or a sheep to be seen."
The farm-servant flogged his horses into an irregular gallop, and so
they passed through the rows of mud huts which constituted the village,
and arrived at the public house. Karl sprang from the carriage, opened
the tavern door, and called for the landlord. A Jew slowly rose from his
seat by the stove and came to the threshold. "Is the gendarme from
Rosmin come?" He is gone into the village. "Which is the way to the
farm-yard?"
The landlord, an elderly man with an intelligent countenance, described
the way in German and Polish, and remained standing at the
door--bewildered, Karl declared, by the sight of two human beings. The
carriage turned into a cross-road, planted on both sides with thick
bushes, the remains of a fallen avenue. Over holes, stones, and puddles,
it rattled on to a group of mud huts, which still had a remnant of
whitewash upon them. "The barns and stables are empty," cried Karl, "for
I see gaps in the roofs large enough to drive our carriage through."
Anton said no more; he was prepared for every thing. They drove through
a break between the stables into the farm-yard, a large irregular space,
surrounded on three sides by tumble-down buildings, and open to the
fields on the fourth. A heap of _débris_ lay there--lime and rotten
timber, the remains of a ruined barn. The yard was empty; no trace of
farm implements or human labor to be seen. "Which is the inspector's
house," inquired Anton, in dismay. The driver looked round, and at last
made up his mind that it was a small one-storied building, with straw
thatch and dirty windows.
At the noise of the wheels a man appeared on the threshold, and waited
phlegmatically till the travelers had dismounted, and were standing
close before him. He was a broad-shouldered fellow, with a bloated,
brandy-drinking face, dressed in a jacket of shaggy cloth, while behind
him peered the muzzle of an equally shaggy dog, who snarled at the
strangers. "Are you the steward of this property?"
"I am," replied the man, in broken German, without stirring from where
he was.
"And I am the agent of the new proprietor," said Anton.
"That does not concern me," growled the shaggy man, turning sharp round,
entering the house, and bolting the door within.
Anton was thoroughly roused. "Break the window in, and help me to catch
the rascal," cried he to Karl, who coolly seized a piece of wood, struck
the panes so as to make the rotten framework give way, and cleared the
opening at one leap. Anton followed him. The room was empty, so was the
next, and in it an open window--the man was gone.
"After him!" cried Karl, and dashed on in pursuit, while Anton looked
about the house and out-buildings. He soon heard the barking of a dog,
and saw Karl capture the fugitive. Hurrying to his help, he held the man
fast, while, with a kick, Karl sent the dog flying. They then contrived
to force the steward back to the house, though he kept striking out
violently all the way.
"Go to the tavern, and bring the gendarme and the landlord," cried Anton
to the driver, who, undisturbed by all that had been going on, had
meanwhile unpacked the carriage. The man accordingly drove leisurely
off, and the fugitive being got into the room, Karl found an old cloth,
and with it bound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I beg your pardon, sir,"
said he; "it is only for an hour or so, till the arrival of the Rosmin
gendarme, whom we have appointed to meet us."
Anton then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house, bu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found but the merest necessaries; no books nor papers of any kind. It
had doubtless been emptied already. A bundle projected from the
coat-pocket of the prisoner, which turned out to be receipts and legal
documents in Polish. In time, the driver returned with the landlord and
the armed policeman. The landlord stood at the door in some perplexity,
and the policeman explained in a few moments what remained to be done.
"You must make a statement to the local judge, and give the man up to
me. He shall go back in your carriage to Rosmin. You will do well to get
rid of him, for this is a wild country, and it will be safer for you to
have him at Rosmin than here, where he has friends and accomplices."
After a long search, a sheet of paper was found in a cupboard, the
statement made and submitted to the policeman, who shook his head a
little over the Polish composition, and the prisoner lifted into the
carriage, the gendarme taking his seat beside him, and saying to Anton,
"I have long expected something of the kind. You may have often occasion
to want me again." The carriage then drove away, and thus the property
came under Anton's administration. He felt as if cast on a desert
island.
His portmanteau and traveling effects were leaning against a mud wall,
and the Polish landlord was the only man who could give him and Karl any
information or advice in their forlorn condition.
Now that the steward was fairly gone, the landlord grew more
communicative, and showed himself serviceable and obliging. A long
conversation ensued, and its purport was what Anton had apprehended from
the warning given by the Commissary Walter and other Rosmin officials.
The inspector had,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done all he could in the
way of spoliation, rendered daring by a report which had found its way
from the town to the village, that the present proprietor would never be
able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estate. At last Anton said, "What that
wretched man has done away with he will have to account for; our first
care must be to preserve what is still to be found on the property. You
must be our guide to-day."
They then examined the empty buildings. Four horses and two
servants--they were gone into the wood--a few old plows, a pair of
harrows, two wagons, a britzska, a cellar full of potatoes, a few
bundles of hay, a little straw--the inventory did not take much time in
drawing up. The buildings were all out of repair, not through age, but
neglect.
"Where is the dwelling-house?" inquired Anton. The landlord led the way
out of the yard to the meadow--a broad plain, gradually sloping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brook. It had been a great pasture. The cattle had
trodden it down into holes; the snouts of greedy swine had rooted it up;
gray molehills and rank tufts of grass rose on all sides.
The landlord stretched out his hand. "There is the castle. This castle
i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he added, reverentially; "no
nobleman in the district has a stone house like that. All the gentry
here live in wood and mud buildings. Herr von Tarow, the richest of
them, has but a poor dwelling."
About three hundred yards from the last out-building rose a great brick
edifice, with a black slate roof and a thick round tower. Its gloomy
walls on this treeless pasture-land, without one trace of life around,
rose beneath the cloudy sky like a phantom fortress which some evil
spirit had evoked from the abyss--a station from which to blight all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The strangers approached it. The castle had fallen into ruins before the
builders had finished their task. The tower had stood there for ages. It
was built of unhewn stone, and had small windows and loop-holes. The
former lords of the land had looked down from its summit on the tops of
the trees, which then stretched far into the plain. They had then ruled
with a rod of iron the serfs who cultivated their land, and toiled and
died for them. Many an arrow had sped through those loop-holes at the
enemy storming below, and many a Tartar horse had been overthrown before
those massive walls. Years ago, a despot of the district had, in
expiation of former sins, begun to add to the gray tower the walls of a
holy monastery; but the monastery never got finished, and the useless
walls had already stood there long, when the late count took it into his
head to convert them into a lordly dwelling for his race, and to raise a
house unparalleled for magnificence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 front of the house was added on to both sides of the tower, which
projected in the middle. The intention had been to have a high
terrace-road up to the castle, and the principal entrance had been made
in the tower, and arched over; but the terrace never having been formed,
the stone threshold of the main door was quite inacce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ladders, and the wide opening was left. The window-spaces of
the lower floor were merely closed up with boards, while on the second
story were some window-frames of beautifully carved wood, in which large
panes had once been placed, but they had got broken. In other windows
were temporary frames of rough deal, with small panes of muddy glass let
into them. A company of jackdaws sat on the top of the tower, looking
down in amazement on the strangers, and every now and then one flew off,
screaming loudly, to contemplate the intruders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A house for crows and bats, not for human beings," said Anton. "At
least, I see no way of getting into it."
The landlord now took them round the building. Behind, where the two
wings made a sort of horse-shoe, there were low entrances to the cellars
and offices; beneath which, again, were stables, great arched kitchens,
and small cells for the serfs. A wooden staircase led to the upper
story. The door turned creaking on its hinges, and a narrow passage took
them through a side wing to the front part of the house. There all was
at least magnificently planned. The circular entrance-hall--an arched
room of the old tower--was painted in mosaic, and through the great
doorway-opening was seen a wide expans
small disturbance made by the return of Anton had gradually settled
down. Those first-class treasures of Sabine's had made way for other
specimens of damask, still of a superior kind, it is true, but which
came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e elderly cousin's comprehension. She had
been quite right in prophesying that Anton would never remark those
signs of exuberant gratitude or their withdrawal. However, one change
had been permanently made--the greatest, the best of all changes--the
clerk retained a privileged place in the heart of the young mistress of
the firm, and his tall figure often appeared as one of the circle that
Sabine's fancy loved to gather round her when at her work-table or in
her treasure-chamber.
To-day she was walking restlessly up and down before dinner. The cousin,
who heard every thing, had just told her that a maid from Ehrenthal's
had run into the office to announce Bernhard's death to his friend. "How
will he bear it?" thought she. And the name of Ehrenthal forced her
thoughts back to the past, to one now far away, and to that painful hour
when the struggle going on in her own mind had been suddenly brought to
a close by a letter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parted. And Anton had known
of that conquered feeling of hers. How considerate he had always been,
how chivalrous, how helpful! She wondered if he had any idea of the
completeness of her triumph over a girlish illusion. She shook her head.
"No, he has not. It was here, at this very table, that an accident first
betrayed me to him. That past time still rises like a cloud between us.
Whenever I sit near Wohlfart of an evening, I am conscious of another's
shadow at my side; and when he speaks to me, his tone, his manner always
seem to say, 'You are not alone; he is with you.'" Sabine started, and
lovingly passed her hand over the beautiful flowers on the table before
her, as if to dispel a painful thought. She could not tell him that she
was free from that long-felt sorrow. Now, however, when he had lost a
friend whom he so much loved, she must show him that there were other
hearts that clung to him still. And again she walked up and down, trying
to devise a way of speaking to him alone.
Dinner was announced. Anton came with the rest, and took his place at
once. There was no opportunity of exchanging a word during the meal, but
he often met her sad and sympathizing eye. "He eats nothing at all
to-day," whispered her cousin; "not even any of the roast," she added,
reproachfully. Sabine was much perturbed. Mr. Jordan had already risen;
Anton would leave the room with the rest, and she should not see him
again the whole day through. So she called out, "The great Calla is
fully blown now. You were admiring the buds the other day; will you
remain a moment; I should like to show it you?" Anton bowed and staid
behind. A few more awkward moments, then her brother rose too; and,
hurrying to Anton, she took him to the room where the flowers were.
"You have had sorrowful tidings to-day," she began.
"The tidings themselves did not surprise me," replied Anton. "The doctor
gave no hope. But I lose much in him."
"I never saw him," said Sabine; "but I know from you that his life was
lonely--poor in affection and in enjoyment."
She moved an arm-chair toward Anton, and led him on to talk about his
friend. She listened to every word with warm sympathy, and well knew
what to ask and how to comfort. It was a relief to Anton to speak of the
departed one, to describe his quiet way of life, his erudition, his
poetical enthusiasm. After a pause, Sabine looked up frankly into his
face, and asked, "Have you any tidings of Herr von Fink?"
It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his departure that she had ever breathed his
name. Anton felt how touching her confidence was, given in this hour of
his sadness. In his emotion, he seized her hand, which she was slow in
withdrawing.
"He is not happy in his new life," he gravely replied. "There was a
savage humor in his last letter, from which I gather, even more than
from his actual words, that the business into which his uncle's death
has thrown him does not suit him."
"It is unworthy," cried Sabine.
"At all events, it is not what would be recognized as honorable in this
house," replied Anton. "Fink is upright, and has lived too long with
your brother to take pleasure in the wild speculations so common on the
other side the Atlantic. His partners and colleagues are for the most
part men without a conscience, and his feelings revolt against their
companionship."
"And can Herr von Fink tolerate such relations as these for a day?"
"It is a remarkable thing that he whose own will was ever so arbitrarily
exercised, should now be obliged against that will to obey a pressure
from without, and every where to work with his hands tied. The
organization of such speculations in America is so complicated that one
shareholder can do little to alter it; and, now that Fink has attained
what used to be the goal of his wishes--a large capital, and the
management of immense districts--his condition appears more uncertain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He was always in danger of thinking slightingly
of others, now I am distressed at the bitter contempt he expresses for
his own life. His last letter paints an intolerable state of things, and
seems to point to some decisive resolve."
"There is only one resolve for him," cried Sabine. "May I ask what you
said to him in reply?"
"I entreated him instantly, come what would, to free himself from the
business in which he was entangled. I said that his own strong will
might find a way of extrication, even if that which I pointed out proved
impracticable. Then I begged of him either to carry out his old plan of
becoming a landed proprietor in America, or to return to us."
"I knew that you would write thus," said Sabine, drawing a long breath.
"Yes, Wohlfart, he shall return," said she, gently, "but he shall not
return to us."
Anton was silent.
"And do you think that Herr von Fink will follow your advice?"
"I do not know. My advice was not very American."
"But it was worthy of you," cried Sabine, with proud delight.
"An officer wishes to speak to Mr. Wohlfart," said a servant at the
door.
Anton sprang up. Sabine went to her flowers and bent mournfully over
them. The shadows of others hovered still between her friend and her.
The few words spoken by the servant filled Anton with a vague terror. He
hurried into the ante-room: there stood Eugene von Rothsattel. Anton was
gladly rushing forward to greet him, but the young soldier's face of
agony made him start back. He whispered, "My mother wishes to speak to
you; something dreadful has occurred." Anton caught up his hat, ran into
the office, hurriedly asked Baumann to excuse him to the principal, and
then accompanied the lieutenant to the baron's house.
On the way, Eugene, who had lost all self-command, said unconnectedly to
Anton, "My father last night accidentally wounded himself by a
pistol-shot--a messenger was sent to summon me--when I came, I found my
mother in a swoon--my sister and I do not know what to do--Lenore
implored my mother on her knees to send for you--you are the only one in
whom w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our distress--I understand nothing about
business, but my father's affairs must be in a dreadful state--my mother
is beside herself--the whole house is in the greatest disorder."
From what Eugene said and what he did not say; from his broken sentences
and his look of agony, Anton guessed at the horrors of the previous
evening. In the boudoir of the baroness he found Lenore, weeping and
exhausted.
"Dear Wohlfart!" cried she, taking his hand and beginning again to sob,
while her head sank powerless on his shoulder.
Meanwhile Eugene walked up and down, wringing his hands, and at length
throwing himself on the sofa, he gave himself up to silent tears.
"It is horrible, Mr. Wohlfart," said Lenore, lifting up her head. "No
one may approach my father--Eugene may not, nor I--only my mother and
old John are with him; and early this morning the merchant Ehrenthal was
here, insisting that he must see my father. He screamed at my mother,
and called my father a deceiver, till she fainted away. When I rushed
into the room, the dreadful man went off threatening her with his
clenched fist."
Anton led Lenore to a chair and waited till she had told him all.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comforting in this case, and his own heart was
wrung to the utmost by the misery he witnessed.
"Call my mother, Eugene," said Lenore, at length.
Her brother left the room.
"Do not forsake us," implored Lenore, clasping her hands; "we are at the
last gasp; even your help can not save us."
"He is dead who might perhaps have done so," mournfully replied Anton.
"Whether I can be of any use I know not, but you can not doubt my
willingness to be so."
"No," cried Lenore. "And Eugene, too, thought of you at once."
The baroness now entered. She walked wearily; but, steadying herself by
a chair, she saluted Anton with dignity. "In our position," said she,
"we need a friend who knows more of business than we three do.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prevents the baron--possibly for a long time to
come--from managing his own affairs, and, little as I understand them, I
can see that our interests require prompt measures. My children have
mentioned you to me, but I fear I am unreasonable in asking you to
devote your time to our service."
She sat down, beckoned Anton to take a chair, and said to her children,
"Leave us; I shall be better able to tell Mr. Wohlfart the little that I
know when I do not see your grief."
When they were alone, she motioned him nearer and tried to speak, but
her lips quivered, and she hid her face in her handkerchief.
"Before I can consent, gracious lady," said he, "to your reposing in me
such confidence as this, I must first inquire whether the baron has no
relative or intimate friend to whom you could with less pain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I pray you to remember that my own knowledge of business
is but small, and my position not one to constitute me a proper
counselor to the baron."
"I know no one," said the baroness, hopelessly. "It is less painful to
me to tell you what I can not conceal, than to one of our own circle.
Consider yourself a physician sent for to visit a patient. The baron has
this morning told me some particulars of his present circumstances." And
then she proceeded to relate what she had gathered as to the nature of
his embarrassments, the danger in which the family property was placed,
and the capital needed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Polish estate.
"My husband," continued she, "has given me the key of his desk, and he
wishes Eugene, with the help of a man of business, to go over his
papers. I now request of you to make this examination together with my
son. When you need explanations, I will try to obtain them from the
baron. The question is now, whether you are inclined to undertake this
trouble for us, who are only strangers."
"I am most willing to do so," earnestly replied Anton; "and I hope that
the kindness of my principal will allow me the time needful for the
purpose, if you do not consider it more advisable to depute the baron's
experienced legal adviser to the task."
"There will be an opportunity of asking that gentleman's advice later,"
said the baroness.
Anton rose. "When do you wish to begin?"
"Immediately. I fear there is not a day to lose. I shall do all I can to
help you look the papers over." She led Anton into the next room, called
in Eugene, and unlocked the baron's desk. As she opened it she lost her
self-command for a moment, and moving to the window, the quivering of
the curtains betrayed the anguish that shook her fragile frame.
The mournful task began. Hour after hour passed. Eugene was in no
condition to peruse any thing, but his mother reached letters and
documents to Anton, and, though often obliged to desist a while, she
bravely returned to the task. Anton placed the papers in order, and
sought, by glancing over each, to arrive at least at a superficial view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It was evening, when the old servant opened the door in dismay, and
called out, "He is there again." The baroness could not repress a slight
scream, and made a gesture of aversion.
"I have told him that no one is at home, but he will not be dismissed;
he makes such a noise on the steps. I can not get rid of him."
"It will kill me if I hear his voice again," murmured the baroness.
"If the man be Ehrenthal," said Anton, rising, "I will try to get him
away. We have now done what was most necessary; have the goodness to
lock up these papers, and to allow me to return to-morrow." The baroness
silently assented, and sank back in her chair. Anton hurried off to the
ante-room, whence he could hear Ehrenthal's loudly-raised voi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usurer shocked him. His hat pushed half off his
head, his pale face swelled as if by drinking, his glazed eyes red with
tears, Ehrenthal stood before him, calling in broken sentences for the
baron, wailing and cursing alternately. "He must come! he must come at
once!" cried he; "the wicked man! A nobleman, indeed! he is a vagabond,
after whom I will send the police. Where is my money? Where is my
security? I want my mortgage from this man who is not at home."
Anton went straight up to him, and asked, "Do you know me, Mr.
Ehrenthal?" Ehrenthal turned his glazed eyes upon him, and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 friend of his dead son.
"He loved you!" he cried, in a lamentable voice. "He spoke to you more
than to his father. You were the only friend that he had on earth. Have
you heard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house of Ehrenthal?" continued he, in
a whisper. "Just as they stole the papers he died. He died with a hand
like this," and clenching his fist he struck his forehead. "Oh my son!
my son! why didst not thou forgive thy father!"
"We will go to your son," said Anton, taking the arm of the old man, who
unresistingly allowed himself to be led back to his own house.
From thence Anton hurried to Councilor Horn, with whom he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It was late before he returned home. In the midst of his anxiety about
those whose prosperity had filled his imagination years before,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in their adversity, reposed in him, dilated his
breast with a feeling of pride. He burned with desire to help them, and
hoped that his zealous devotion might yet find some way of rescue. As
yet he saw none. Looking up at the great building before him, so firm
and secure, in the moonlight, a thought flashed into his mind. If any
man could help them, it was his principal. His keen eye would be able to
unravel all the dark secrets in which the baron was entangled, and his
iron strength of will would crush the villains who held the unfortunate
nobleman in their power. And then he had a noble nature; he always
decided on the right, without an effort or a struggle. Anton looked at
the first floor. The whole house-front was dark, but in a corner room a
light still burned. It was the private office of his chief.
With sudden resolve, Anton begged the servant to take him to Mr.
Schröter, who looked with amazement at the unexpected visitor, and asked
what brought him, and whether any thing had happened.
"I implore your counsel--I implore your help," cried Anton.
"For yourself or for others?" inquired the merchant.
"For a family with whom I have accidentally become connected. They are
lost if a strong hand does not ward off the impending catastrophe."
Anton then rapidly related the occurrences of the afternoon, and,
seizing his principal's hand in his emotion, cried, "Have pity upon the
unhappy ladies, and help them."
"Help them!" replied the merchant; "how can I? Have you been
commissioned to apply to me, or are you only following the impulse of
your own feelings?"
"I am not commissioned; it is only the interest that I take in the
baron's fate which leads me to you."
"And what right have you to inform me of facts communicated in strict
confidence to yourself by the baron's lady?" asked the merchant, dryly.
"I am committing no indiscretion in telling you what will, in a few
days, be no secret, even to strangers."
"You are unusually excited, otherwise you would not forget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hatever, does a man of business venture to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without the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Of course, I shall make no wrong use of what you have said, but it was
by no means business-like, Wohlfart, to be so open toward me."
Anton was silent, feeling, indeed, that his principal was right, but yet
it seemed hard to be blamed for reposing confidence at such a time as
this. The merchant walked silently up and down; at length, stopping
before Anton, he said, "I do not now inquire how you come to take so
warm an interest in this family. I fear it is an acquaintance you owe to
Fink."
"You shall hear all," said Anton.
"Not at present. I will now content myself with repeating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interfere in these affairs without being specially
applied to by the parties themselves. I may add that I by no means wish
for such an application, and do not disguise from you that, were it
made, I should probably decline to do any thing for the Baron
Rothsattel."
Anton's feelings were roused to the utmost. "The question is the rescue
of an honorable man, and of lovely and amiable women from the toils of
rogues and impostors. To me, this seems the duty of every one; I, at
least, consider it a sacred obligation which I dare not shrink from. But
without your support I can do nothing."
"And how do you think this embarrassed man can be helped?" inquired the
merchant, seating himself.
With somewhat more composure, Anton repli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an experienced man of business making himself master of the case. There
must be some way of circumventing these villains. Your penetration would
discover it."
"Any attorney would be far more likely to do so, and the baron might
readily engage the services of experienced and upright legal advisers.
If his enemies have done any thing illegal, the quick eye of a lawyer is
the most likely to detect it."
"Alas! the baron's own lawyer gives but little hope," replied Anton.
"Then, my dear Wohlfart, no other is likely to do much good. Show me an
embarrassed man who has strength to grasp an offered hand, and bid me
help him, and for the sake of all I owe you, I will not refuse to do so.
I think you are convinced of this."
"I am," said Anton, dejectedly.
"From all I hear, however," the merchant went on,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the baron. From what I gather from general report, as well as from
you, his embarrassments arise from his having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usurers, which proves him deficient in what alone ennobles the life of
any man--good sense, and the power of steady exertion."
Anton could only sigh his assent.
"To help such a man," inexorably continued the merchant, "is a futile
attempt, against which reason may well protest. We are not to despair of
any, but want of strength is the most hopeless case of all. Our power of
laboring for others being limited, it becomes our duty to inquire,
before we devote our time to the weak, whether we are not thus
diminishing our chances of helping better men."
Anton interrupted him. "Does he not deserve every allowance to be made
for him? He was brought up to exact much; he has not learned, as we
have, to make his way by his own labor."
The merchant laid his hand on the young man's shoulder. "The very
reason. Believe me, a large number of these landed gentry, who pay the
penalty of their old family memories, are beyond help. I am the last to
deny that many worthy and admirable men belong to this class. Indeed,
wherever remarkable talent or nobility of character shoots up among
them, no doubt their position offers peculiar scope for its development,
but for average men it is not a favorable one. He who considers it his
hereditary privilege to enjoy life, and who assumes a distinguished
position in virtue of his family, will very often fail to put forth his
whole strength in order to deserve that position. Accordingly, numbers
of our oldest families are declining, and their fall will be no loss to
the state. Their family associations make them haughty without any
right to be so--limit their perceptions and confuse their judgment."
"Even if all this be true," cried Anton, "it does not absolve us from
helping individuals of the class who have excited our sympathy."
"No," said the principal, "if it be excited. But it does not glow so
rapidly in advancing years as in youth. The baron has endeavored to
isolate his property from the current of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leave it forever to his family. Forever! You, as a merchant, know how to
estimate the attempt. True, every rational man must allow it to be
desirable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same soil should be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We all prize what our forefathers have possessed before
us, and Sabine would unlock every room in this house with pride, because
her great-great-grandmother turned the same keys before her. It is
therefore natural that the landed proprietor should desire to preserve
those familiar scenes, which are the source of his own prosperity, to
those nearest and dearest to him. But there must be means to this end,
and these means are the making his own existence available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increase of his patrimony. Where energy dies in families
or individuals, then it is well that their means die too, that their
money should circulate through other hands, and their plowshare pass to
those who can guide it better. A family that has become effete through
luxury ought to sink down into common life, to make room for the
uprising of fresh energies and faculties. Every one who seeks, at the
cost of free activity for others, to preserve permanent possessions and
privileges for himself or his family, I must look upon as an enemy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social state. And if such a man ruin
himself in his endeavors, I should feel no malicious pleasure in his
downfall, but I should say that he is rightly served, because he has
sinned against a fundamental law of our social being; consequently, I
should consider it doubly wrong to support this man, because I could but
fear that I should thus be supporting an unsound condition of the body
politic."
Anton looked down mournfully. He had expected sympathy and warm
concurrence, and he met with disaffection and coldness that he despaired
of conquering. "I can not gainsay you," he at length replied; "but in
this case I can not feel as you do. I have been witness to the
unspeakable distress in the baron's family, and my whole soul is full
of sadness and sympathy, and of the wish to do something for those who
have opened their heart to me. After what you have said, I dare no
longer ask you to trouble yourself with their affairs, but I have
promised the baroness to assist her as far as my small powers permit,
and your kindness allows. I implore you to grant me permission to do
this. I shall endeavor to be regular in my attendance at the office, but
if during the next few weeks I am occasionally absent, I must ask you to
excuse me."
Once more the merchant walked up and down the room, and then, looking at
Anton's excited face, with deep seriousness and something of regret, he
replied, "Remember, Wohlfart, that every occupation which excites the
mind soon obtains a hold over a man, which may retard as well as advance
his success in life. It is thi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 to agree
to your wishes."
"I know it," said Anton, in a low voice; "but I have now no choice
left."
"Well, then, do what you must," said the merchant, gloomily; "I will lay
no hinderance in your way; and I hope that after a few weeks you will be
able to consider the whole circumstances more calmly." Anton left the
room, and the merchant stood looking long with frowning brow at the
place his clerk had occupied.
Nor was Anton in a more congenial mood. "So cold, so inexorable!"
exclaimed he, as he reached his own room. He began to suspect that his
principal was more selfish and less kindly than he had hitherto
supposed. Many an expression of Fink's recurred to his mind, as well as
that evening when young Rothsattel, in his boyish conceit, had spoken
impertinently to the merchant. "Is it possible," thought he, "that that
rude speech should be unforgotten?" And his chief's keen, deep-furrowed
face lost inexpressibly by contrast with the fair forms of the noble
ladies. "I am not wrong," he cried to himself; "let him say what he
will, my views are more just than his, and henceforth my destiny shall
be to choose for myself the way in which I shall walk." He sat long in
the darkness, and his thoughts were gloomy as it; then he went to the
window to look down into the dark court below. A great white blossom
rose before him like a phantom. Striking a light, he saw that it was the
beautiful Calla out of Sabine's room. It hung down mournfully on its
broken stem. Sabine had had it placed there. This little circumstance
struck him as a mournful omen.
Meanwhile Sabine, taper in hand, entered her brother's room.
"Good-night, Traugott," nodded she. "Wohlfart has been with you this
evening; how long he staid!"
"He will leave us," replied the merchant, gloomily.
Sabine started and dropped her taper on the table. "For God's sake, what
has happened? Has Wohlfart said that he was going away?"
"I do not yet know it, but I see it coming step by step; and I can not,
and still less can you, do any thing to retain him. When he stood before
me here with glowing cheeks and trembling voice, pleading for a ruined
man, I found out what it was that lured him away."
"I do not understand you," said Sabine, looking full at her brother.
"He chooses to become the confidential friend of a decayed noble. A pair
of bright eyes draws him away from us: it seems to him a worthy object
of ambition to become Rothsattel's man of business. This intimacy with
nobility is the legacy bequeathed to him by Fink."
"And you have refused to help him?" inquired Sabine, in a low voice.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said the merchant, harshly; and he
turned to his writing-table.
Sabine slowly withdrew. The taper trembled in her hand as she passed
through the long suite of rooms listening to her own footfall, and
shuddering as the feeling came over her that an invisible companion
glided by her side. This was the revenge of that other. The shadow that
once fell on her innocent life now drove her friend away from their
circle. Anton's affections clung to another. She had but been in his
eyes a mere stranger, who had once loved and languished for one now far
away, and who now, in widow's weeds, looked back regretfully to the
feelings of her youth.
The few next weeks were spent by Anton in over-hard work. He had great
difficulty in keeping up his counting-house duties, while he spent every
spare hour in conference with the baroness and the lawyer.
In the mean time, the misfortunes of the baron ran their course. He had
not been able to pay the interest of the sums with which his estate was
burdened. When last they were due, a whole series of claims was brought
against him, and the estate fell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district authorities. Complicated lawsuits arose. Ehrenthal complained
loudly, claiming the first mortgage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nay, he
was inclined to advance claims on the last mortgage offered by the baron
in the recent fatal hour. Löbel Pinkus also appeared as claimant of the
first mortgage, and asserted that he had paid the whole sum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Ehrenthal had no proof to bring forward, and had been
for some weeks past quite unable to manage his own affairs, while
Pinkus, on the contrary, fought with every weapon a hardened sinner can
devise or employ, and the deeds which the baron had executed at Veitel's
suggestion proved to be so capital a master-stroke of the cunning
advocate, that the baron's man of business had, from the first, little
hope of the case. We may here observe that Pinkus did eventually win it,
and that the mortgage was made over to him.
Anton was now gradually gaining some insight into the baron's
circumstances. But the double sale of the first mortgage was still kept
a secret by the latter, even from his wife. He declared Ehrenthal's
claim unfounded, and even expressed a suspicion that he had himself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robbery in his office. Indeed, he really
believed this. Then the name of Itzig was never broached, and the
suspicion against Ehrenthal, which the baron's lawyer shared, prevented
Anton seeking any explanation from him.
Meanwhile, an estrangement had sprung up between our hero and his
principal, which the whole counting-house remarked with surprise. The
merchant scowled at Anton's vacant seat when the latter chanced to be
absent during office-hours, or looked coldly at his clerk's face, made
pale as it was with excitement of mind and night-work. He took no notice
of his new occupation, and never seemed to remark him. Even to his
sister he maintained a stiff-necked silence; nor could all her attempts
lead him to speak of Anton, who, on his side, felt his heart revolt
against this coldness. After his return, to be treated like a child of
the house, praised, promoted, petted, and now to be treated like a mere
hireling, who is not worth the bread thrown to him; to be a toy of an
incomprehensible caprice--this, at least, he had not deserved; so he
became reserved toward the whole family, and sat silent at his desk; but
he fel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now and the then so keenly, that often,
when alone, he would spring up and stamp on the ground in the bitter
indignation of his heart.
One comfort remained. Sabine was not estranged. True, he saw little of
her, and at dinner she seemed to avoid speaking to him, but he knew that
she was on his side.
A few days after his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the merchant, she came down
stairs as he stood in the hall, and had to pass him by so closely that
her dress touched him. He had retreated, and made a formal bow, but she
looked at him imploringly, and whispered, "You must not be estranged
from me." It was an affair of a moment, but the faces of both were
radiant with a happy understanding.
The time had now arrived when Mr. Jordan was to quit the firm. The
principal again called Anton into his little office, and without any
severity, but also without a trace of his former cordiality, began: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o you my intention of appointing you Jordan's
successor; but,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your time has been more taken
up with other business than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such a post, I
therefore ask you whether you are now at liberty to undertake Jordan's
duties?"
"I am not," replied Anton.
"Can you name any--not very distant--time when you will be free from
your present occupation? In that case I will endeavor to find a
substitute until then."
Anton sorrowfully replied, "I can not at present say when I shall again
be master of my whole time; and, besides, I feel that, even as it is, I
tax your indulgence by many irregularities. Therefore, Mr. Schröter, I
beg that you will fill up this post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me."
The merchant's brow grew furrowed and dark, and he silently bowed
assent. Anton felt as he closed the door that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m was now complete, and, resuming his place, he leaned his throbbing
head on his hand. A moment later Baumann was summoned to the principal,
and Jordan's situation conferred upon him. On returning to the office,
he went up to Anton and whispered, "I refused at first, but Mr. Schröter
insisted. I am doing you an injustice." And that evening Mr. Baumann, in
his own room, read in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the chapters treating of
the unjust Saul (the principal), and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Jonathan
and the persecuted David, and strengthened his heart thereby.
The next day Anton was summoned to the baroness. Lenore and her mother
sat before a large table covered with jewel-boxes and toilette elegances
of every description, while a heavy iron chest stood at their feet. The
curtains were drawn, and the subdued light shone softly into the richly
furnished room. On the carpet glowed wreaths of unfading flowers, and
the clock ticked cheerfully in its alabaster case. Under the shade of
flowering plants sat the two love-birds in their silvered cage, hopping
from perch to perch, screaming ceaselessly, or sitting up quietly close
to each other. The whole room was beauty and perfume. "For how long?"
thought Anton. The baroness rose. "We are already obliged to trouble you
again," said she; "we are engaged in a very painful occupation." On the
table were all manner of ornaments, gold chains, brilliants, rings,
necklaces, gathered into a heap.
"We have been looking out all that we can dispense with," said the
baroness, "and now pray you to undertake to sell these things for us. I
have been told that some of them are of value, and as we are now in much
need of money, we turn here for help."
Anton looked in perplexity at the glittering heap.
"Tell us, Wohlfart," cried Lenore, anxiously, "is this necessary? can it
be of any use? Mamma has insisted upon setting apart for sale all our
ornaments, and whatever plate is not in daily use. What I can give is
not worth talking of, but my mother's jewels are costly; many of them
were presents made to her in youth, which she shall not part with unless
you say that it is necessary."
"I fear," said Anton, gravely, "that it will prove so."
"Take them," said the baroness to Anton; "I shall be calmer when I know
that we have at least done what we could."
"But do you wish to part with all?" inquired Anton, anxiously. "Much
that is dear to you may have but little value in a jeweler's eyes."
"I shall never wear an ornament again," quietly replied the baroness.
"Take them all;" and, holding her hands before her eyes, she turned
away.
"We are torturing my mother," cried Lenore, hastily; "will you lock up
all that is on the table, and get them out of the house as soon as you
can?"
"I can not undertake the charge of these valuables," said Anton,
"without taking some measures to decrease my own responsibility. First
of all, I will in your presence make a short note of all you intrust to
me."
"What useless cruelty!" exclaimed Lenore.
"It will not take long."
Anton took out a few sheets from his pocket-book, and began to note down
the different articles.
"You shall not see it done, mother," said Lenore, drawing her mother
away, and then returning to watch Anton at his task.
"These preparations for the market are horrible," said she. "My mother's
whole life will be sold; some memory of hers is linked with every single
thing. Look, Wohlfart, the princess gave her this diamond ornament when
she married my father."
"They are magnificent brilliants," cried Anton, admiringly.
"This ring was my grandfather's, and these are presents of poor papa's.
Alas! no man can know how we love all these things. It was always a
festival to me when mamma put on her diamonds. Now we come to my
possessions. They are not worth much. Do you think this bracelet good
gold?" She held out her hand as she spoke.
"I do not know."
"It shall go with the rest," said Lenore, taking it off. "Yes, you are a
kind, good man, Wohlfart," continued she, looking trustfully into his
tearful eyes; "do not forsake us. My brother has no experience, and is
more helpless than we are. It is a frightful position for me. Before
mamma I do all I can to be composed, else I could scream and weep the
whole day through." She sank in a chair, still holding his hand. "Dear
Wohlfart, do not forsake us."
Anton bent over her, and looked with passionate emotion at the lovely
face that turned so trustfully to him in the midst of its tears.
"I will be helpful to you when I can," said he, in the fullness of his
heart. "I will be at hand whenever you need me. You have too good an
opinion of my information and my faculties; I can be of less assistance
to you than you suppose, but what I can, that I will do in any and every
possible way."
Their hands parted with a warm pressure; the affair was settled.
The baroness now returned. "Our lawyer was with me this morning," said
she; "and now I must ask for your opinion on another subject. He tells
me that there is no prospect of preserving the baron's family estate."
"At this time, when interest is high, and money difficult to get, none,"
replied Anton.
"And you, too, think that we must turn all our efforts toward preserving
the Polish property?"
"I do," was the answer.
"For that, also, money will be necessary. Perhaps I may be able through
my relatives to intrust you with a small sum, which, with the help of
that"--she pointed to the iron chest--"may suffice to cover the first
necessary expenses. I do not, however, wish to sell the jewels here, and
a journey to the residence would be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cure the
sum to which I have just alluded. The baron's lawyer has spoken most
highly of your capacity for business. It is his wish which now decides
me to make a proposal to you. Will you for the next few years, or, at
all events, until our greatest difficulties are over, devote your whole
time to our affairs? I have consulted my children, and they agree with
me in believing that in your assistance lies our only hope of rescue.
The baron, too, has come in to the plan. The question now is whether
your circumstances allow you to give your support to our unfortunate
family. We shall be grateful to you, whatever conditions you affix; and
if you can find any way of making our great obligations to you apparent
in the position you hold, pray impart it to me."
Anton stood petrified. What the baroness required of him was separation
from the firm, separation from his principal, and from Sabine! Had this
thought occurred to him before, when standing in Lenore's presence or
bending over the baron's papers? At all events, now that the words were
spoken, they shocked him. He looked at Lenore, who stood behind her
mother with hands clasped in supplication. At length he replied, "I
stand in a position which I can not leav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others.
I was not prepared for this proposal, and beg to have time allowed me
for consideration. It is a step which will decide my whole future life."
"I do not press you," said the baroness; "I only request your
consideration. Whatever your decision be, our warmest gratitude will
still be yours; if you are unable to uphold our feeble strength, I fear
that we shall find no one to do so. You will think of that," she added,
beseechingly.
Anton hurried through the street with throbbing pulse. The noble lady's
glance of entreaty, Lenore's folded hands, beckoned him out of the
gloomy counting-house into a sphere of greater liberty, into a new
future, from whose depths bright images flashed out upon his fancy. A
request had been frankly made, and he was strongly inclined to justify
the confidence that prompted it. Those ladies required an unwearied,
self-sacrificing helper to save them from utter ruin, and if he
followed his impulse he should be doing a good work--fulfilling a duty.
In this mood he entered the merchant's dwelling. Alas! all that he saw
around him seemed to stretch out a hand to detain him. As he looked at
the warehouse, the good-humored faces of the porters, the chains of the
great scales, the hieroglyphics of the worthy Pix, again he felt that
this was the place that he belonged to. Sabine's dog kissed his hand,
and ran before him to his room--his and Fink's room. Here the childish
heart of the orphan boy had found a friend, kind companions, a home, a
definite and honorable life-purpose. Looking down through his window on
all the long-familiar objects, he saw a light in Sabine's store-chamber.
How often he had sought for that light, which brightened the whole great
building, and brought a sense of comfort and cheerfulness even into his
room. He now sprang up suddenly, and said to himself, "She shall
decide."
Sabine started in amazement when Anton appeared before her. "I am
irresistibly impelled to seek you," cried he. "I have to decide upon my
future life, and I feel undetermined, and unable to trust to my own
judgment. You have always been a kind friend to me since the day of my
arrival. I am accustomed to look up to you, and to think of you in
connection with all that interests me here. Let me hear your opinion
from your own lips. The Baroness Rothsattel has to-day proposed to me
permanently to undertake the situation of confidential adviser and
manager of the baron's affairs. Shall I accept; or shall I remain here?
I know not--tell me what is right both for myself and others."
"Not I," said Sabine, drawing back and growing very pale. "I can not
venture to decide in the matter. Nor do you wish me to do so, Wohlfart,
for you have already decided."
Anton looked straight before him and was silent.
"You have thought of leaving this house, and a wish to do so has sprung
out of the thought. And I am to justify you, and approve your resolve!
This is what you require of me," continued she, bitterly. "But this,
Wohlfart, I can not do, for I am sorry that you go away from us."
She turned away from him and leaned on the back of a chair.
"Oh, be not angry with me too!" said Anton; "that I can not bear. I have
suffered much of late. Mr. Schröter has suddenly withdrawn from me the
friendly regard that I long held my life's greatest treasure. I have not
deserved his coldness. What I have been doing has not been wrong, and
it was done with his knowledge. I had been spoiled by his kindness; I
have the more deeply felt his displeasure. My only comfort has been that
you did not condemn me. And now, do not you be cold toward me, else I
shall be wretched forever. There is not a soul on earth to whom I can
turn for affectionate comprehension of my difficulties. Had I a sister,
I should seek her heart to-day. You do not know what to me, lonely as I
am, your smile, your kindly shake of the hand has been till now. Do not
turn coldly from me, I beseech you."
Sabine was silent. At length she inquired, still with averted face,
"What draws you to those strangers; is it a joyful hope, is it sympathy
alone? Give this question close consideration before you answer it to
yourself at least."
"What it is that makes it possible for me to leave this house," said
Anton, "I do not myself know. If I can give a name to my motives, it is
gratitude felt toward one. She was the first to speak kindly to the
wandering boy on his way out into the world. I have admired her in the
peaceful brightness of her former life. I have often dreamed childish
dreams about her. There was a time when a tender feeling for her filled
my whole heart, and I then believed myself forever the slave of her
image. But years bring changes, and I learned to look on men and on life
with other eyes. Then I met her again, distressed, unhappy, despairing,
and my compassion became overmastering. When I am away from her, I know
that she is nothing to me; when I am with her, I feel only the spell of
her sorrow. Once, when I had to depart out of her circle like a culprit,
she came to me, and before the whole scornful assembly she gave me her
hand and acknowledged me her friend; and now she comes and asks for my
hand to help her father. Can I refuse it? Is it wrong to feel as I do? I
know not, and no one can tell me--no one but you alone."
Sabine's head had sunk down to the back of the chair on which she bent.
She now suddenly raised it, and with tearful eyes, and a voice full of
love and sorrow, cried, "Follow the voice that calls you. Go, Wohlfart,
go."
CHAPTER XXVII.
On a cold October day, two men were seen driving through the latticed
gate of the town of Rosmin on toward the plain, which stretched out
before them monotonous and boundless. Anton sat wrapped in his fur coat,
his hat low on his forehead, and at his side was young Sturm, in an old
cavalry cloak, with his soldier's cap cocked cheerily on one side. In
front of them a farm-servant, squatted on a heap of straw, flogged on
the small horses. The wind swept the sand and straw from the
stubble-fields, the road was a broad causeway without ditches or hedges,
the horses had to wade alternately through puddles and deep sand. Yellow
sand gleamed through the scanty herbage in all directions wherever a
field-mouse had made her way to her nest or an active mole had done what
he could to diversify the unbroken plain. Wherever the ground sank,
stagnant water lodged, and there hollow willow-trees stretched their
crippled arms in the air, their boughs flapping in the wind, and their
faded leaves fluttering down into the muddy pool below. Here and there
stood a small dwarf pine, a resting-place for the crows, who, scared by
the passing carriage, flew loudly croaking over the travelers' heads.
There was no house to be seen on the road, no pedestrian, and no
conveyance of any kind.
Karl looked every now and then at his silent companion, and said at
last, pointing to the horses, "How rough their coats are, and how pretty
their gray mouse skins! I wonder how many of these beasties would go to
make up my sergeant's horse! When I took leave of my father, the old man
said, 'Perhaps I shall pay you a visit, little one, when they light the
Christmas-tree.' 'You'll never be able,' said I. 'Why not?' asked he.
'You'll never trust yourself in any post-chaise.' Then the old boy
cried, 'Oho! post-chaises are always of a stout build; I shall be sure
to trust myself in one.' But now, Mr. Anton, I see that my father never
can pay us a visit."
"Why not?"
"It is possible that he may reach Rosmin; but, as soon as he sees these
horses and this road, he will instantly turn back. 'Shall I trust
myself,' he'll say, 'in a district where sand runs between one's legs
like water, and where mice are put into harness? The ground is not firm
enough for me.'"
"The horses are not the worst things here," said Anton, absently. "Look!
these go fast enough."
"Yes," replied Karl, "but they don't go like regular horses; they
entangle their legs like two cats playing in a parsley-bed. And what
things they have for shoes--regular webbed hoofs, I declare, which no
blacksmith can ever fit."
"If we could only get on!" returned Anton; "the wind blows cold, and I
am shivering in spite of my fur."
"You have slept but little the last few nights, sir," said Karl. "The
wind blows here as if over a threshing-floor. The earth is not round
hereabouts as elsewhere, but flat as a cake. This is a complete desert;
we have been driving for more than an hour, and there is not a village
to be seen."
"A desert indeed," sighed Anton; "let us hope it may improve." They
relapsed into profound silence. At length the driver stopped near a
pool, unharnessed the horses, and led them to the water's edge, without
noticing the travelers.
"What the deuce does this mean?" cried Karl, jumping down from the
carriage.
"I am going to feed," replied the servant, sulkily, in a foreign accent.
"I am anxious to know how that will be done," said Karl. "There is not
the shadow of a bag of provender."
The horses, however, soon proved that they could live without corn; they
stretched down their shaggy heads, and began to pull the grass and weeds
at the edge of the pool, sometimes taking a draught of the dirty water.
Meanwhile the servant drew a bundle from under his seat, settled himself
under the lee of an alder-bush, and, taking his knife, cut his bread and
cheese without even glancing at the travelers.
"I say, Ignatius or Jacob," cried Karl, sharply, "how long will this
breakfast of yours last?"
"An hour," replied the man, munching away.
"And how far is it from here to the estate?"
"Six miles, or maybe more."
"You can make nothing of him," said Anton; "we must put up with the
customs of the country;" and, leaving the carriage, they went to look on
at the horses feeding.
Anton is on his way to the Polish property. He is now the baron's agent.
Anxious months have the last proved to him. The parting from his
principal and the firm had been painful in the extreme. For some time
before it, indeed, Anton had found himself alone in the midst of his
colleagues. The quiet Baumann still remained his friend, but the others
considered him a castaway. The merchant received his resignation with
icy coldness; and even in the hour of parting, his hand lay impassive as
metal in Anton's grasp. Since then, our hero had undertaken several
journeys to the capital and to creditors in the family's behalf, and now
he was on his way to set the new estate in order, accompanied by Karl,
whom he had induced to become the baron's bailiff.
Ehrenthal had, by the authority conferred on him,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from the time of the sale by auction, and hired the Polish
bailiff for the baron. There had been unfair dealings between them at
the time, and it was well known in Rosmin that the bailiff had sold off
a good deal, and been guilty of all sorts of frauds since, so that Anton
had even now no prospect of a quiet life.
"The hour is come when I may execute my commission," cried Karl, groping
in the straw under the seat. He drew out a large japanned tin case, and
carried it to Anton. "Miss Sabine gave me this in charge for you." He
then joyously opened the lid, produced the materials for an excellent
breakfast, a bottle of wine, and a silver goblet. Anton took hold of the
case.
"It has a very knowing look," said Karl. "Miss Sabine planned it
herself."
Anton examined it on all sides, and placed it carefully on a tuft of
grass; then he took up the goblet, and saw his initials engraved on it,
and underneath the words, "To thy welfare." Whereupon he forgot the
breakfast and all around him, and stood gazing at the goblet, lost in
thought.
"Do not forget the breakfast, sir," suggested Karl, respectfully.
"Sit down by me, my faithful friend; eat and drink with me. Leave off
your absurd politeness. We shall have but little, either of us, but what
we have we will share like brothers. Take the bottle if you have no
glass."
"There's nothing like leather," said Karl, taking a small leathern
drinking-cup out of his pocket. "As for 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t was
kindly meant, and I thank you; but there must be subordination, if it
were but for the sake of the others; and so, sir, be kind enough to let
me shake hands with you now, and then let things be as they were before.
Only look at the horses, Mr. Anton. My faith! the creatures devour
thistles."
Again the horses were harnessed, again they threw out their short legs
in the sand, and again the carriage rolled through the barren
district--first through an empty plain, next through a wretched
fir-wood, then past a row of low sand-hills, then over a tumble-down
bridge crossing a small stream.
"This is the property," said the driver, turning round, and pointing
with his whip to a row of dirty thatched roofs that had just come into
sight.
Anton stood up to look for the group of trees in which the Hall might be
supposed to stand. Nothing of the sort to be seen. The village was
deficient in all that adorns the home of the poorest German peasant--no
orchard, no hedged-in gardens, no lime-trees in the market-place.
"This is wretched," said he, sitting down again; "much worse than they
told us in Rosmin."
"The village looks as if under a curse," cried Karl; "no teams working
in the fields--not a cow or a sheep to be seen."
The farm-servant flogged his horses into an irregular gallop, and so
they passed through the rows of mud huts which constituted the village,
and arrived at the public house. Karl sprang from the carriage, opened
the tavern door, and called for the landlord. A Jew slowly rose from his
seat by the stove and came to the threshold. "Is the gendarme from
Rosmin come?" He is gone into the village. "Which is the way to the
farm-yard?"
The landlord, an elderly man with an intelligent countenance, described
the way in German and Polish, and remained standing at the
door--bewildered, Karl declared, by the sight of two human beings. The
carriage turned into a cross-road, planted on both sides with thick
bushes, the remains of a fallen avenue. Over holes, stones, and puddles,
it rattled on to a group of mud huts, which still had a remnant of
whitewash upon them. "The barns and stables are empty," cried Karl, "for
I see gaps in the roofs large enough to drive our carriage through."
Anton said no more; he was prepared for every thing. They drove through
a break between the stables into the farm-yard, a large irregular space,
surrounded on three sides by tumble-down buildings, and open to the
fields on the fourth. A heap of _débris_ lay there--lime and rotten
timber, the remains of a ruined barn. The yard was empty; no trace of
farm implements or human labor to be seen. "Which is the inspector's
house," inquired Anton, in dismay. The driver looked round, and at last
made up his mind that it was a small one-storied building, with straw
thatch and dirty windows.
At the noise of the wheels a man appeared on the threshold, and waited
phlegmatically till the travelers had dismounted, and were standing
close before him. He was a broad-shouldered fellow, with a bloated,
brandy-drinking face, dressed in a jacket of shaggy cloth, while behind
him peered the muzzle of an equally shaggy dog, who snarled at the
strangers. "Are you the steward of this property?"
"I am," replied the man, in broken German, without stirring from where
he was.
"And I am the agent of the new proprietor," said Anton.
"That does not concern me," growled the shaggy man, turning sharp round,
entering the house, and bolting the door within.
Anton was thoroughly roused. "Break the window in, and help me to catch
the rascal," cried he to Karl, who coolly seized a piece of wood, struck
the panes so as to make the rotten framework give way, and cleared the
opening at one leap. Anton followed him. The room was empty, so was the
next, and in it an open window--the man was gone.
"After him!" cried Karl, and dashed on in pursuit, while Anton looked
about the house and out-buildings. He soon heard the barking of a dog,
and saw Karl capture the fugitive. Hurrying to his help, he held the man
fast, while, with a kick, Karl sent the dog flying. They then contrived
to force the steward back to the house, though he kept striking out
violently all the way.
"Go to the tavern, and bring the gendarme and the landlord," cried Anton
to the driver, who, undisturbed by all that had been going on, had
meanwhile unpacked the carriage. The man accordingly drove leisurely
off, and the fugitive being got into the room, Karl found an old cloth,
and with it bound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I beg your pardon, sir,"
said he; "it is only for an hour or so, till the arrival of the Rosmin
gendarme, whom we have appointed to meet us."
Anton then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house, bu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found but the merest necessaries; no books nor papers of any kind. It
had doubtless been emptied already. A bundle projected from the
coat-pocket of the prisoner, which turned out to be receipts and legal
documents in Polish. In time, the driver returned with the landlord and
the armed policeman. The landlord stood at the door in some perplexity,
and the policeman explained in a few moments what remained to be done.
"You must make a statement to the local judge, and give the man up to
me. He shall go back in your carriage to Rosmin. You will do well to get
rid of him, for this is a wild country, and it will be safer for you to
have him at Rosmin than here, where he has friends and accomplices."
After a long search, a sheet of paper was found in a cupboard, the
statement made and submitted to the policeman, who shook his head a
little over the Polish composition, and the prisoner lifted into the
carriage, the gendarme taking his seat beside him, and saying to Anton,
"I have long expected something of the kind. You may have often occasion
to want me again." The carriage then drove away, and thus the property
came under Anton's administration. He felt as if cast on a desert
island.
His portmanteau and traveling effects were leaning against a mud wall,
and the Polish landlord was the only man who could give him and Karl any
information or advice in their forlorn condition.
Now that the steward was fairly gone, the landlord grew more
communicative, and showed himself serviceable and obliging. A long
conversation ensued, and its purport was what Anton had apprehended from
the warning given by the Commissary Walter and other Rosmin officials.
The inspector had,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done all he could in the
way of spoliation, rendered daring by a report which had found its way
from the town to the village, that the present proprietor would never be
able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estate. At last Anton said, "What that
wretched man has done away with he will have to account for; our first
care must be to preserve what is still to be found on the property. You
must be our guide to-day."
They then examined the empty buildings. Four horses and two
servants--they were gone into the wood--a few old plows, a pair of
harrows, two wagons, a britzska, a cellar full of potatoes, a few
bundles of hay, a little straw--the inventory did not take much time in
drawing up. The buildings were all out of repair, not through age, but
neglect.
"Where is the dwelling-house?" inquired Anton. The landlord led the way
out of the yard to the meadow--a broad plain, gradually sloping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brook. It had been a great pasture. The cattle had
trodden it down into holes; the snouts of greedy swine had rooted it up;
gray molehills and rank tufts of grass rose on all sides.
The landlord stretched out his hand. "There is the castle. This castle
i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he added, reverentially; "no
nobleman in the district has a stone house like that. All the gentry
here live in wood and mud buildings. Herr von Tarow, the richest of
them, has but a poor dwelling."
About three hundred yards from the last out-building rose a great brick
edifice, with a black slate roof and a thick round tower. Its gloomy
walls on this treeless pasture-land, without one trace of life around,
rose beneath the cloudy sky like a phantom fortress which some evil
spirit had evoked from the abyss--a station from which to blight all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The strangers approached it. The castle had fallen into ruins before the
builders had finished their task. The tower had stood there for ages. It
was built of unhewn stone, and had small windows and loop-holes. The
former lords of the land had looked down from its summit on the tops of
the trees, which then stretched far into the plain. They had then ruled
with a rod of iron the serfs who cultivated their land, and toiled and
died for them. Many an arrow had sped through those loop-holes at the
enemy storming below, and many a Tartar horse had been overthrown before
those massive walls. Years ago, a despot of the district had, in
expiation of former sins, begun to add to the gray tower the walls of a
holy monastery; but the monastery never got finished, and the useless
walls had already stood there long, when the late count took it into his
head to convert them into a lordly dwelling for his race, and to raise a
house unparalleled for magnificence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 front of the house was added on to both sides of the tower, which
projected in the middle. The intention had been to have a high
terrace-road up to the castle, and the principal entrance had been made
in the tower, and arched over; but the terrace never having been formed,
the stone threshold of the main door was quite inacce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ladders, and the wide opening was left. The window-spaces of
the lower floor were merely closed up with boards, while on the second
story were some window-frames of beautifully carved wood, in which large
panes had once been placed, but they had got broken. In other windows
were temporary frames of rough deal, with small panes of muddy glass let
into them. A company of jackdaws sat on the top of the tower, looking
down in amazement on the strangers, and every now and then one flew off,
screaming loudly, to contemplate the intruders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A house for crows and bats, not for human beings," said Anton. "At
least, I see no way of getting into it."
The landlord now took them round the building. Behind, where the two
wings made a sort of horse-shoe, there were low entrances to the cellars
and offices; beneath which, again, were stables, great arched kitchens,
and small cells for the serfs. A wooden staircase led to the upper
story. The door turned creaking on its hinges, and a narrow passage took
them through a side wing to the front part of the house. There all was
at least magnificently planned. The circular entrance-hall--an arched
room of the old tower--was painted in mosaic, and through the great
doorway-opening was seen a wide expans
small disturbance made by the return of Anton had gradually settled
down. Those first-class treasures of Sabine's had made way for other
specimens of damask, still of a superior kind, it is true, but which
came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e elderly cousin's comprehension. She had
been quite right in prophesying that Anton would never remark those
signs of exuberant gratitude or their withdrawal. However, one change
had been permanently made--the greatest, the best of all changes--the
clerk retained a privileged place in the heart of the young mistress of
the firm, and his tall figure often appeared as one of the circle that
Sabine's fancy loved to gather round her when at her work-table or in
her treasure-chamber.
To-day she was walking restlessly up and down before dinner. The cousin,
who heard every thing, had just told her that a maid from Ehrenthal's
had run into the office to announce Bernhard's death to his friend. "How
will he bear it?" thought she. And the name of Ehrenthal forced her
thoughts back to the past, to one now far away, and to that painful hour
when the struggle going on in her own mind had been suddenly brought to
a close by a letter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parted. And Anton had known
of that conquered feeling of hers. How considerate he had always been,
how chivalrous, how helpful! She wondered if he had any idea of the
completeness of her triumph over a girlish illusion. She shook her head.
"No, he has not. It was here, at this very table, that an accident first
betrayed me to him. That past time still rises like a cloud between us.
Whenever I sit near Wohlfart of an evening, I am conscious of another's
shadow at my side; and when he speaks to me, his tone, his manner always
seem to say, 'You are not alone; he is with you.'" Sabine started, and
lovingly passed her hand over the beautiful flowers on the table before
her, as if to dispel a painful thought. She could not tell him that she
was free from that long-felt sorrow. Now, however, when he had lost a
friend whom he so much loved, she must show him that there were other
hearts that clung to him still. And again she walked up and down, trying
to devise a way of speaking to him alone.
Dinner was announced. Anton came with the rest, and took his place at
once. There was no opportunity of exchanging a word during the meal, but
he often met her sad and sympathizing eye. "He eats nothing at all
to-day," whispered her cousin; "not even any of the roast," she added,
reproachfully. Sabine was much perturbed. Mr. Jordan had already risen;
Anton would leave the room with the rest, and she should not see him
again the whole day through. So she called out, "The great Calla is
fully blown now. You were admiring the buds the other day; will you
remain a moment; I should like to show it you?" Anton bowed and staid
behind. A few more awkward moments, then her brother rose too; and,
hurrying to Anton, she took him to the room where the flowers were.
"You have had sorrowful tidings to-day," she began.
"The tidings themselves did not surprise me," replied Anton. "The doctor
gave no hope. But I lose much in him."
"I never saw him," said Sabine; "but I know from you that his life was
lonely--poor in affection and in enjoyment."
She moved an arm-chair toward Anton, and led him on to talk about his
friend. She listened to every word with warm sympathy, and well knew
what to ask and how to comfort. It was a relief to Anton to speak of the
departed one, to describe his quiet way of life, his erudition, his
poetical enthusiasm. After a pause, Sabine looked up frankly into his
face, and asked, "Have you any tidings of Herr von Fink?"
It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his departure that she had ever breathed his
name. Anton felt how touching her confidence was, given in this hour of
his sadness. In his emotion, he seized her hand, which she was slow in
withdrawing.
"He is not happy in his new life," he gravely replied. "There was a
savage humor in his last letter, from which I gather, even more than
from his actual words, that the business into which his uncle's death
has thrown him does not suit him."
"It is unworthy," cried Sabine.
"At all events, it is not what would be recognized as honorable in this
house," replied Anton. "Fink is upright, and has lived too long with
your brother to take pleasure in the wild speculations so common on the
other side the Atlantic. His partners and colleagues are for the most
part men without a conscience, and his feelings revolt against their
companionship."
"And can Herr von Fink tolerate such relations as these for a day?"
"It is a remarkable thing that he whose own will was ever so arbitrarily
exercised, should now be obliged against that will to obey a pressure
from without, and every where to work with his hands tied. The
organization of such speculations in America is so complicated that one
shareholder can do little to alter it; and, now that Fink has attained
what used to be the goal of his wishes--a large capital, and the
management of immense districts--his condition appears more uncertain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He was always in danger of thinking slightingly
of others, now I am distressed at the bitter contempt he expresses for
his own life. His last letter paints an intolerable state of things, and
seems to point to some decisive resolve."
"There is only one resolve for him," cried Sabine. "May I ask what you
said to him in reply?"
"I entreated him instantly, come what would, to free himself from the
business in which he was entangled. I said that his own strong will
might find a way of extrication, even if that which I pointed out proved
impracticable. Then I begged of him either to carry out his old plan of
becoming a landed proprietor in America, or to return to us."
"I knew that you would write thus," said Sabine, drawing a long breath.
"Yes, Wohlfart, he shall return," said she, gently, "but he shall not
return to us."
Anton was silent.
"And do you think that Herr von Fink will follow your advice?"
"I do not know. My advice was not very American."
"But it was worthy of you," cried Sabine, with proud delight.
"An officer wishes to speak to Mr. Wohlfart," said a servant at the
door.
Anton sprang up. Sabine went to her flowers and bent mournfully over
them. The shadows of others hovered still between her friend and her.
The few words spoken by the servant filled Anton with a vague terror. He
hurried into the ante-room: there stood Eugene von Rothsattel. Anton was
gladly rushing forward to greet him, but the young soldier's face of
agony made him start back. He whispered, "My mother wishes to speak to
you; something dreadful has occurred." Anton caught up his hat, ran into
the office, hurriedly asked Baumann to excuse him to the principal, and
then accompanied the lieutenant to the baron's house.
On the way, Eugene, who had lost all self-command, said unconnectedly to
Anton, "My father last night accidentally wounded himself by a
pistol-shot--a messenger was sent to summon me--when I came, I found my
mother in a swoon--my sister and I do not know what to do--Lenore
implored my mother on her knees to send for you--you are the only one in
whom w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our distress--I understand nothing about
business, but my father's affairs must be in a dreadful state--my mother
is beside herself--the whole house is in the greatest disorder."
From what Eugene said and what he did not say; from his broken sentences
and his look of agony, Anton guessed at the horrors of the previous
evening. In the boudoir of the baroness he found Lenore, weeping and
exhausted.
"Dear Wohlfart!" cried she, taking his hand and beginning again to sob,
while her head sank powerless on his shoulder.
Meanwhile Eugene walked up and down, wringing his hands, and at length
throwing himself on the sofa, he gave himself up to silent tears.
"It is horrible, Mr. Wohlfart," said Lenore, lifting up her head. "No
one may approach my father--Eugene may not, nor I--only my mother and
old John are with him; and early this morning the merchant Ehrenthal was
here, insisting that he must see my father. He screamed at my mother,
and called my father a deceiver, till she fainted away. When I rushed
into the room, the dreadful man went off threatening her with his
clenched fist."
Anton led Lenore to a chair and waited till she had told him all.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comforting in this case, and his own heart was
wrung to the utmost by the misery he witnessed.
"Call my mother, Eugene," said Lenore, at length.
Her brother left the room.
"Do not forsake us," implored Lenore, clasping her hands; "we are at the
last gasp; even your help can not save us."
"He is dead who might perhaps have done so," mournfully replied Anton.
"Whether I can be of any use I know not, but you can not doubt my
willingness to be so."
"No," cried Lenore. "And Eugene, too, thought of you at once."
The baroness now entered. She walked wearily; but, steadying herself by
a chair, she saluted Anton with dignity. "In our position," said she,
"we need a friend who knows more of business than we three do.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prevents the baron--possibly for a long time to
come--from managing his own affairs, and, little as I understand them, I
can see that our interests require prompt measures. My children have
mentioned you to me, but I fear I am unreasonable in asking you to
devote your time to our service."
She sat down, beckoned Anton to take a chair, and said to her children,
"Leave us; I shall be better able to tell Mr. Wohlfart the little that I
know when I do not see your grief."
When they were alone, she motioned him nearer and tried to speak, but
her lips quivered, and she hid her face in her handkerchief.
"Before I can consent, gracious lady," said he, "to your reposing in me
such confidence as this, I must first inquire whether the baron has no
relative or intimate friend to whom you could with less pain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I pray you to remember that my own knowledge of business
is but small, and my position not one to constitute me a proper
counselor to the baron."
"I know no one," said the baroness, hopelessly. "It is less painful to
me to tell you what I can not conceal, than to one of our own circle.
Consider yourself a physician sent for to visit a patient. The baron has
this morning told me some particulars of his present circumstances." And
then she proceeded to relate what she had gathered as to the nature of
his embarrassments, the danger in which the family property was placed,
and the capital needed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Polish estate.
"My husband," continued she, "has given me the key of his desk, and he
wishes Eugene, with the help of a man of business, to go over his
papers. I now request of you to make this examination together with my
son. When you need explanations, I will try to obtain them from the
baron. The question is now, whether you are inclined to undertake this
trouble for us, who are only strangers."
"I am most willing to do so," earnestly replied Anton; "and I hope that
the kindness of my principal will allow me the time needful for the
purpose, if you do not consider it more advisable to depute the baron's
experienced legal adviser to the task."
"There will be an opportunity of asking that gentleman's advice later,"
said the baroness.
Anton rose. "When do you wish to begin?"
"Immediately. I fear there is not a day to lose. I shall do all I can to
help you look the papers over." She led Anton into the next room, called
in Eugene, and unlocked the baron's desk. As she opened it she lost her
self-command for a moment, and moving to the window, the quivering of
the curtains betrayed the anguish that shook her fragile frame.
The mournful task began. Hour after hour passed. Eugene was in no
condition to peruse any thing, but his mother reached letters and
documents to Anton, and, though often obliged to desist a while, she
bravely returned to the task. Anton placed the papers in order, and
sought, by glancing over each, to arrive at least at a superficial view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It was evening, when the old servant opened the door in dismay, and
called out, "He is there again." The baroness could not repress a slight
scream, and made a gesture of aversion.
"I have told him that no one is at home, but he will not be dismissed;
he makes such a noise on the steps. I can not get rid of him."
"It will kill me if I hear his voice again," murmured the baroness.
"If the man be Ehrenthal," said Anton, rising, "I will try to get him
away. We have now done what was most necessary; have the goodness to
lock up these papers, and to allow me to return to-morrow." The baroness
silently assented, and sank back in her chair. Anton hurried off to the
ante-room, whence he could hear Ehrenthal's loudly-raised voi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usurer shocked him. His hat pushed half off his
head, his pale face swelled as if by drinking, his glazed eyes red with
tears, Ehrenthal stood before him, calling in broken sentences for the
baron, wailing and cursing alternately. "He must come! he must come at
once!" cried he; "the wicked man! A nobleman, indeed! he is a vagabond,
after whom I will send the police. Where is my money? Where is my
security? I want my mortgage from this man who is not at home."
Anton went straight up to him, and asked, "Do you know me, Mr.
Ehrenthal?" Ehrenthal turned his glazed eyes upon him, and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 friend of his dead son.
"He loved you!" he cried, in a lamentable voice. "He spoke to you more
than to his father. You were the only friend that he had on earth. Have
you heard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house of Ehrenthal?" continued he, in
a whisper. "Just as they stole the papers he died. He died with a hand
like this," and clenching his fist he struck his forehead. "Oh my son!
my son! why didst not thou forgive thy father!"
"We will go to your son," said Anton, taking the arm of the old man, who
unresistingly allowed himself to be led back to his own house.
From thence Anton hurried to Councilor Horn, with whom he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It was late before he returned home. In the midst of his anxiety about
those whose prosperity had filled his imagination years before,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in their adversity, reposed in him, dilated his
breast with a feeling of pride. He burned with desire to help them, and
hoped that his zealous devotion might yet find some way of rescue. As
yet he saw none. Looking up at the great building before him, so firm
and secure, in the moonlight, a thought flashed into his mind. If any
man could help them, it was his principal. His keen eye would be able to
unravel all the dark secrets in which the baron was entangled, and his
iron strength of will would crush the villains who held the unfortunate
nobleman in their power. And then he had a noble nature; he always
decided on the right, without an effort or a struggle. Anton looked at
the first floor. The whole house-front was dark, but in a corner room a
light still burned. It was the private office of his chief.
With sudden resolve, Anton begged the servant to take him to Mr.
Schröter, who looked with amazement at the unexpected visitor, and asked
what brought him, and whether any thing had happened.
"I implore your counsel--I implore your help," cried Anton.
"For yourself or for others?" inquired the merchant.
"For a family with whom I have accidentally become connected. They are
lost if a strong hand does not ward off the impending catastrophe."
Anton then rapidly related the occurrences of the afternoon, and,
seizing his principal's hand in his emotion, cried, "Have pity upon the
unhappy ladies, and help them."
"Help them!" replied the merchant; "how can I? Have you been
commissioned to apply to me, or are you only following the impulse of
your own feelings?"
"I am not commissioned; it is only the interest that I take in the
baron's fate which leads me to you."
"And what right have you to inform me of facts communicated in strict
confidence to yourself by the baron's lady?" asked the merchant, dryly.
"I am committing no indiscretion in telling you what will, in a few
days, be no secret, even to strangers."
"You are unusually excited, otherwise you would not forget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hatever, does a man of business venture to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without the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Of course, I shall make no wrong use of what you have said, but it was
by no means business-like, Wohlfart, to be so open toward me."
Anton was silent, feeling, indeed, that his principal was right, but yet
it seemed hard to be blamed for reposing confidence at such a time as
this. The merchant walked silently up and down; at length, stopping
before Anton, he said, "I do not now inquire how you come to take so
warm an interest in this family. I fear it is an acquaintance you owe to
Fink."
"You shall hear all," said Anton.
"Not at present. I will now content myself with repeating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interfere in these affairs without being specially
applied to by the parties themselves. I may add that I by no means wish
for such an application, and do not disguise from you that, were it
made, I should probably decline to do any thing for the Baron
Rothsattel."
Anton's feelings were roused to the utmost. "The question is the rescue
of an honorable man, and of lovely and amiable women from the toils of
rogues and impostors. To me, this seems the duty of every one; I, at
least, consider it a sacred obligation which I dare not shrink from. But
without your support I can do nothing."
"And how do you think this embarrassed man can be helped?" inquired the
merchant, seating himself.
With somewhat more composure, Anton repli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an experienced man of business making himself master of the case. There
must be some way of circumventing these villains. Your penetration would
discover it."
"Any attorney would be far more likely to do so, and the baron might
readily engage the services of experienced and upright legal advisers.
If his enemies have done any thing illegal, the quick eye of a lawyer is
the most likely to detect it."
"Alas! the baron's own lawyer gives but little hope," replied Anton.
"Then, my dear Wohlfart, no other is likely to do much good. Show me an
embarrassed man who has strength to grasp an offered hand, and bid me
help him, and for the sake of all I owe you, I will not refuse to do so.
I think you are convinced of this."
"I am," said Anton, dejectedly.
"From all I hear, however," the merchant went on,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the baron. From what I gather from general report, as well as from
you, his embarrassments arise from his having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usurers, which proves him deficient in what alone ennobles the life of
any man--good sense, and the power of steady exertion."
Anton could only sigh his assent.
"To help such a man," inexorably continued the merchant, "is a futile
attempt, against which reason may well protest. We are not to despair of
any, but want of strength is the most hopeless case of all. Our power of
laboring for others being limited, it becomes our duty to inquire,
before we devote our time to the weak, whether we are not thus
diminishing our chances of helping better men."
Anton interrupted him. "Does he not deserve every allowance to be made
for him? He was brought up to exact much; he has not learned, as we
have, to make his way by his own labor."
The merchant laid his hand on the young man's shoulder. "The very
reason. Believe me, a large number of these landed gentry, who pay the
penalty of their old family memories, are beyond help. I am the last to
deny that many worthy and admirable men belong to this class. Indeed,
wherever remarkable talent or nobility of character shoots up among
them, no doubt their position offers peculiar scope for its development,
but for average men it is not a favorable one. He who considers it his
hereditary privilege to enjoy life, and who assumes a distinguished
position in virtue of his family, will very often fail to put forth his
whole strength in order to deserve that position. Accordingly, numbers
of our oldest families are declining, and their fall will be no loss to
the state. Their family associations make them haughty without any
right to be so--limit their perceptions and confuse their judgment."
"Even if all this be true," cried Anton, "it does not absolve us from
helping individuals of the class who have excited our sympathy."
"No," said the principal, "if it be excited. But it does not glow so
rapidly in advancing years as in youth. The baron has endeavored to
isolate his property from the current of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leave it forever to his family. Forever! You, as a merchant, know how to
estimate the attempt. True, every rational man must allow it to be
desirable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same soil should be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We all prize what our forefathers have possessed before
us, and Sabine would unlock every room in this house with pride, because
her great-great-grandmother turned the same keys before her. It is
therefore natural that the landed proprietor should desire to preserve
those familiar scenes, which are the source of his own prosperity, to
those nearest and dearest to him. But there must be means to this end,
and these means are the making his own existence available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increase of his patrimony. Where energy dies in families
or individuals, then it is well that their means die too, that their
money should circulate through other hands, and their plowshare pass to
those who can guide it better. A family that has become effete through
luxury ought to sink down into common life, to make room for the
uprising of fresh energies and faculties. Every one who seeks, at the
cost of free activity for others, to preserve permanent possessions and
privileges for himself or his family, I must look upon as an enemy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social state. And if such a man ruin
himself in his endeavors, I should feel no malicious pleasure in his
downfall, but I should say that he is rightly served, because he has
sinned against a fundamental law of our social being; consequently, I
should consider it doubly wrong to support this man, because I could but
fear that I should thus be supporting an unsound condition of the body
politic."
Anton looked down mournfully. He had expected sympathy and warm
concurrence, and he met with disaffection and coldness that he despaired
of conquering. "I can not gainsay you," he at length replied; "but in
this case I can not feel as you do. I have been witness to the
unspeakable distress in the baron's family, and my whole soul is full
of sadness and sympathy, and of the wish to do something for those who
have opened their heart to me. After what you have said, I dare no
longer ask you to trouble yourself with their affairs, but I have
promised the baroness to assist her as far as my small powers permit,
and your kindness allows. I implore you to grant me permission to do
this. I shall endeavor to be regular in my attendance at the office, but
if during the next few weeks I am occasionally absent, I must ask you to
excuse me."
Once more the merchant walked up and down the room, and then, looking at
Anton's excited face, with deep seriousness and something of regret, he
replied, "Remember, Wohlfart, that every occupation which excites the
mind soon obtains a hold over a man, which may retard as well as advance
his success in life. It is thi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 to agree
to your wishes."
"I know it," said Anton, in a low voice; "but I have now no choice
left."
"Well, then, do what you must," said the merchant, gloomily; "I will lay
no hinderance in your way; and I hope that after a few weeks you will be
able to consider the whole circumstances more calmly." Anton left the
room, and the merchant stood looking long with frowning brow at the
place his clerk had occupied.
Nor was Anton in a more congenial mood. "So cold, so inexorable!"
exclaimed he, as he reached his own room. He began to suspect that his
principal was more selfish and less kindly than he had hitherto
supposed. Many an expression of Fink's recurred to his mind, as well as
that evening when young Rothsattel, in his boyish conceit, had spoken
impertinently to the merchant. "Is it possible," thought he, "that that
rude speech should be unforgotten?" And his chief's keen, deep-furrowed
face lost inexpressibly by contrast with the fair forms of the noble
ladies. "I am not wrong," he cried to himself; "let him say what he
will, my views are more just than his, and henceforth my destiny shall
be to choose for myself the way in which I shall walk." He sat long in
the darkness, and his thoughts were gloomy as it; then he went to the
window to look down into the dark court below. A great white blossom
rose before him like a phantom. Striking a light, he saw that it was the
beautiful Calla out of Sabine's room. It hung down mournfully on its
broken stem. Sabine had had it placed there. This little circumstance
struck him as a mournful omen.
Meanwhile Sabine, taper in hand, entered her brother's room.
"Good-night, Traugott," nodded she. "Wohlfart has been with you this
evening; how long he staid!"
"He will leave us," replied the merchant, gloomily.
Sabine started and dropped her taper on the table. "For God's sake, what
has happened? Has Wohlfart said that he was going away?"
"I do not yet know it, but I see it coming step by step; and I can not,
and still less can you, do any thing to retain him. When he stood before
me here with glowing cheeks and trembling voice, pleading for a ruined
man, I found out what it was that lured him away."
"I do not understand you," said Sabine, looking full at her brother.
"He chooses to become the confidential friend of a decayed noble. A pair
of bright eyes draws him away from us: it seems to him a worthy object
of ambition to become Rothsattel's man of business. This intimacy with
nobility is the legacy bequeathed to him by Fink."
"And you have refused to help him?" inquired Sabine, in a low voice.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said the merchant, harshly; and he
turned to his writing-table.
Sabine slowly withdrew. The taper trembled in her hand as she passed
through the long suite of rooms listening to her own footfall, and
shuddering as the feeling came over her that an invisible companion
glided by her side. This was the revenge of that other. The shadow that
once fell on her innocent life now drove her friend away from their
circle. Anton's affections clung to another. She had but been in his
eyes a mere stranger, who had once loved and languished for one now far
away, and who now, in widow's weeds, looked back regretfully to the
feelings of her youth.
The few next weeks were spent by Anton in over-hard work. He had great
difficulty in keeping up his counting-house duties, while he spent every
spare hour in conference with the baroness and the lawyer.
In the mean time, the misfortunes of the baron ran their course. He had
not been able to pay the interest of the sums with which his estate was
burdened. When last they were due, a whole series of claims was brought
against him, and the estate fell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district authorities. Complicated lawsuits arose. Ehrenthal complained
loudly, claiming the first mortgage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nay, he
was inclined to advance claims on the last mortgage offered by the baron
in the recent fatal hour. Löbel Pinkus also appeared as claimant of the
first mortgage, and asserted that he had paid the whole sum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Ehrenthal had no proof to bring forward, and had been
for some weeks past quite unable to manage his own affairs, while
Pinkus, on the contrary, fought with every weapon a hardened sinner can
devise or employ, and the deeds which the baron had executed at Veitel's
suggestion proved to be so capital a master-stroke of the cunning
advocate, that the baron's man of business had, from the first, little
hope of the case. We may here observe that Pinkus did eventually win it,
and that the mortgage was made over to him.
Anton was now gradually gaining some insight into the baron's
circumstances. But the double sale of the first mortgage was still kept
a secret by the latter, even from his wife. He declared Ehrenthal's
claim unfounded, and even expressed a suspicion that he had himself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robbery in his office. Indeed, he really
believed this. Then the name of Itzig was never broached, and the
suspicion against Ehrenthal, which the baron's lawyer shared, prevented
Anton seeking any explanation from him.
Meanwhile, an estrangement had sprung up between our hero and his
principal, which the whole counting-house remarked with surprise. The
merchant scowled at Anton's vacant seat when the latter chanced to be
absent during office-hours, or looked coldly at his clerk's face, made
pale as it was with excitement of mind and night-work. He took no notice
of his new occupation, and never seemed to remark him. Even to his
sister he maintained a stiff-necked silence; nor could all her attempts
lead him to speak of Anton, who, on his side, felt his heart revolt
against this coldness. After his return, to be treated like a child of
the house, praised, promoted, petted, and now to be treated like a mere
hireling, who is not worth the bread thrown to him; to be a toy of an
incomprehensible caprice--this, at least, he had not deserved; so he
became reserved toward the whole family, and sat silent at his desk; but
he fel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now and the then so keenly, that often,
when alone, he would spring up and stamp on the ground in the bitter
indignation of his heart.
One comfort remained. Sabine was not estranged. True, he saw little of
her, and at dinner she seemed to avoid speaking to him, but he knew that
she was on his side.
A few days after his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the merchant, she came down
stairs as he stood in the hall, and had to pass him by so closely that
her dress touched him. He had retreated, and made a formal bow, but she
looked at him imploringly, and whispered, "You must not be estranged
from me." It was an affair of a moment, but the faces of both were
radiant with a happy understanding.
The time had now arrived when Mr. Jordan was to quit the firm. The
principal again called Anton into his little office, and without any
severity, but also without a trace of his former cordiality, began: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o you my intention of appointing you Jordan's
successor; but,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your time has been more taken
up with other business than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such a post, I
therefore ask you whether you are now at liberty to undertake Jordan's
duties?"
"I am not," replied Anton.
"Can you name any--not very distant--time when you will be free from
your present occupation? In that case I will endeavor to find a
substitute until then."
Anton sorrowfully replied, "I can not at present say when I shall again
be master of my whole time; and, besides, I feel that, even as it is, I
tax your indulgence by many irregularities. Therefore, Mr. Schröter, I
beg that you will fill up this post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me."
The merchant's brow grew furrowed and dark, and he silently bowed
assent. Anton felt as he closed the door that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m was now complete, and, resuming his place, he leaned his throbbing
head on his hand. A moment later Baumann was summoned to the principal,
and Jordan's situation conferred upon him. On returning to the office,
he went up to Anton and whispered, "I refused at first, but Mr. Schröter
insisted. I am doing you an injustice." And that evening Mr. Baumann, in
his own room, read in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the chapters treating of
the unjust Saul (the principal), and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Jonathan
and the persecuted David, and strengthened his heart thereby.
The next day Anton was summoned to the baroness. Lenore and her mother
sat before a large table covered with jewel-boxes and toilette elegances
of every description, while a heavy iron chest stood at their feet. The
curtains were drawn, and the subdued light shone softly into the richly
furnished room. On the carpet glowed wreaths of unfading flowers, and
the clock ticked cheerfully in its alabaster case. Under the shade of
flowering plants sat the two love-birds in their silvered cage, hopping
from perch to perch, screaming ceaselessly, or sitting up quietly close
to each other. The whole room was beauty and perfume. "For how long?"
thought Anton. The baroness rose. "We are already obliged to trouble you
again," said she; "we are engaged in a very painful occupation." On the
table were all manner of ornaments, gold chains, brilliants, rings,
necklaces, gathered into a heap.
"We have been looking out all that we can dispense with," said the
baroness, "and now pray you to undertake to sell these things for us. I
have been told that some of them are of value, and as we are now in much
need of money, we turn here for help."
Anton looked in perplexity at the glittering heap.
"Tell us, Wohlfart," cried Lenore, anxiously, "is this necessary? can it
be of any use? Mamma has insisted upon setting apart for sale all our
ornaments, and whatever plate is not in daily use. What I can give is
not worth talking of, but my mother's jewels are costly; many of them
were presents made to her in youth, which she shall not part with unless
you say that it is necessary."
"I fear," said Anton, gravely, "that it will prove so."
"Take them," said the baroness to Anton; "I shall be calmer when I know
that we have at least done what we could."
"But do you wish to part with all?" inquired Anton, anxiously. "Much
that is dear to you may have but little value in a jeweler's eyes."
"I shall never wear an ornament again," quietly replied the baroness.
"Take them all;" and, holding her hands before her eyes, she turned
away.
"We are torturing my mother," cried Lenore, hastily; "will you lock up
all that is on the table, and get them out of the house as soon as you
can?"
"I can not undertake the charge of these valuables," said Anton,
"without taking some measures to decrease my own responsibility. First
of all, I will in your presence make a short note of all you intrust to
me."
"What useless cruelty!" exclaimed Lenore.
"It will not take long."
Anton took out a few sheets from his pocket-book, and began to note down
the different articles.
"You shall not see it done, mother," said Lenore, drawing her mother
away, and then returning to watch Anton at his task.
"These preparations for the market are horrible," said she. "My mother's
whole life will be sold; some memory of hers is linked with every single
thing. Look, Wohlfart, the princess gave her this diamond ornament when
she married my father."
"They are magnificent brilliants," cried Anton, admiringly.
"This ring was my grandfather's, and these are presents of poor papa's.
Alas! no man can know how we love all these things. It was always a
festival to me when mamma put on her diamonds. Now we come to my
possessions. They are not worth much. Do you think this bracelet good
gold?" She held out her hand as she spoke.
"I do not know."
"It shall go with the rest," said Lenore, taking it off. "Yes, you are a
kind, good man, Wohlfart," continued she, looking trustfully into his
tearful eyes; "do not forsake us. My brother has no experience, and is
more helpless than we are. It is a frightful position for me. Before
mamma I do all I can to be composed, else I could scream and weep the
whole day through." She sank in a chair, still holding his hand. "Dear
Wohlfart, do not forsake us."
Anton bent over her, and looked with passionate emotion at the lovely
face that turned so trustfully to him in the midst of its tears.
"I will be helpful to you when I can," said he, in the fullness of his
heart. "I will be at hand whenever you need me. You have too good an
opinion of my information and my faculties; I can be of less assistance
to you than you suppose, but what I can, that I will do in any and every
possible way."
Their hands parted with a warm pressure; the affair was settled.
The baroness now returned. "Our lawyer was with me this morning," said
she; "and now I must ask for your opinion on another subject. He tells
me that there is no prospect of preserving the baron's family estate."
"At this time, when interest is high, and money difficult to get, none,"
replied Anton.
"And you, too, think that we must turn all our efforts toward preserving
the Polish property?"
"I do," was the answer.
"For that, also, money will be necessary. Perhaps I may be able through
my relatives to intrust you with a small sum, which, with the help of
that"--she pointed to the iron chest--"may suffice to cover the first
necessary expenses. I do not, however, wish to sell the jewels here, and
a journey to the residence would be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cure the
sum to which I have just alluded. The baron's lawyer has spoken most
highly of your capacity for business. It is his wish which now decides
me to make a proposal to you. Will you for the next few years, or, at
all events, until our greatest difficulties are over, devote your whole
time to our affairs? I have consulted my children, and they agree with
me in believing that in your assistance lies our only hope of rescue.
The baron, too, has come in to the plan. The question now is whether
your circumstances allow you to give your support to our unfortunate
family. We shall be grateful to you, whatever conditions you affix; and
if you can find any way of making our great obligations to you apparent
in the position you hold, pray impart it to me."
Anton stood petrified. What the baroness required of him was separation
from the firm, separation from his principal, and from Sabine! Had this
thought occurred to him before, when standing in Lenore's presence or
bending over the baron's papers? At all events, now that the words were
spoken, they shocked him. He looked at Lenore, who stood behind her
mother with hands clasped in supplication. At length he replied, "I
stand in a position which I can not leav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others.
I was not prepared for this proposal, and beg to have time allowed me
for consideration. It is a step which will decide my whole future life."
"I do not press you," said the baroness; "I only request your
consideration. Whatever your decision be, our warmest gratitude will
still be yours; if you are unable to uphold our feeble strength, I fear
that we shall find no one to do so. You will think of that," she added,
beseechingly.
Anton hurried through the street with throbbing pulse. The noble lady's
glance of entreaty, Lenore's folded hands, beckoned him out of the
gloomy counting-house into a sphere of greater liberty, into a new
future, from whose depths bright images flashed out upon his fancy. A
request had been frankly made, and he was strongly inclined to justify
the confidence that prompted it. Those ladies required an unwearied,
self-sacrificing helper to save them from utter ruin, and if he
followed his impulse he should be doing a good work--fulfilling a duty.
In this mood he entered the merchant's dwelling. Alas! all that he saw
around him seemed to stretch out a hand to detain him. As he looked at
the warehouse, the good-humored faces of the porters, the chains of the
great scales, the hieroglyphics of the worthy Pix, again he felt that
this was the place that he belonged to. Sabine's dog kissed his hand,
and ran before him to his room--his and Fink's room. Here the childish
heart of the orphan boy had found a friend, kind companions, a home, a
definite and honorable life-purpose. Looking down through his window on
all the long-familiar objects, he saw a light in Sabine's store-chamber.
How often he had sought for that light, which brightened the whole great
building, and brought a sense of comfort and cheerfulness even into his
room. He now sprang up suddenly, and said to himself, "She shall
decide."
Sabine started in amazement when Anton appeared before her. "I am
irresistibly impelled to seek you," cried he. "I have to decide upon my
future life, and I feel undetermined, and unable to trust to my own
judgment. You have always been a kind friend to me since the day of my
arrival. I am accustomed to look up to you, and to think of you in
connection with all that interests me here. Let me hear your opinion
from your own lips. The Baroness Rothsattel has to-day proposed to me
permanently to undertake the situation of confidential adviser and
manager of the baron's affairs. Shall I accept; or shall I remain here?
I know not--tell me what is right both for myself and others."
"Not I," said Sabine, drawing back and growing very pale. "I can not
venture to decide in the matter. Nor do you wish me to do so, Wohlfart,
for you have already decided."
Anton looked straight before him and was silent.
"You have thought of leaving this house, and a wish to do so has sprung
out of the thought. And I am to justify you, and approve your resolve!
This is what you require of me," continued she, bitterly. "But this,
Wohlfart, I can not do, for I am sorry that you go away from us."
She turned away from him and leaned on the back of a chair.
"Oh, be not angry with me too!" said Anton; "that I can not bear. I have
suffered much of late. Mr. Schröter has suddenly withdrawn from me the
friendly regard that I long held my life's greatest treasure. I have not
deserved his coldness. What I have been doing has not been wrong, and
it was done with his knowledge. I had been spoiled by his kindness; I
have the more deeply felt his displeasure. My only comfort has been that
you did not condemn me. And now, do not you be cold toward me, else I
shall be wretched forever. There is not a soul on earth to whom I can
turn for affectionate comprehension of my difficulties. Had I a sister,
I should seek her heart to-day. You do not know what to me, lonely as I
am, your smile, your kindly shake of the hand has been till now. Do not
turn coldly from me, I beseech you."
Sabine was silent. At length she inquired, still with averted face,
"What draws you to those strangers; is it a joyful hope, is it sympathy
alone? Give this question close consideration before you answer it to
yourself at least."
"What it is that makes it possible for me to leave this house," said
Anton, "I do not myself know. If I can give a name to my motives, it is
gratitude felt toward one. She was the first to speak kindly to the
wandering boy on his way out into the world. I have admired her in the
peaceful brightness of her former life. I have often dreamed childish
dreams about her. There was a time when a tender feeling for her filled
my whole heart, and I then believed myself forever the slave of her
image. But years bring changes, and I learned to look on men and on life
with other eyes. Then I met her again, distressed, unhappy, despairing,
and my compassion became overmastering. When I am away from her, I know
that she is nothing to me; when I am with her, I feel only the spell of
her sorrow. Once, when I had to depart out of her circle like a culprit,
she came to me, and before the whole scornful assembly she gave me her
hand and acknowledged me her friend; and now she comes and asks for my
hand to help her father. Can I refuse it? Is it wrong to feel as I do? I
know not, and no one can tell me--no one but you alone."
Sabine's head had sunk down to the back of the chair on which she bent.
She now suddenly raised it, and with tearful eyes, and a voice full of
love and sorrow, cried, "Follow the voice that calls you. Go, Wohlfart,
go."
CHAPTER XXVII.
On a cold October day, two men were seen driving through the latticed
gate of the town of Rosmin on toward the plain, which stretched out
before them monotonous and boundless. Anton sat wrapped in his fur coat,
his hat low on his forehead, and at his side was young Sturm, in an old
cavalry cloak, with his soldier's cap cocked cheerily on one side. In
front of them a farm-servant, squatted on a heap of straw, flogged on
the small horses. The wind swept the sand and straw from the
stubble-fields, the road was a broad causeway without ditches or hedges,
the horses had to wade alternately through puddles and deep sand. Yellow
sand gleamed through the scanty herbage in all directions wherever a
field-mouse had made her way to her nest or an active mole had done what
he could to diversify the unbroken plain. Wherever the ground sank,
stagnant water lodged, and there hollow willow-trees stretched their
crippled arms in the air, their boughs flapping in the wind, and their
faded leaves fluttering down into the muddy pool below. Here and there
stood a small dwarf pine, a resting-place for the crows, who, scared by
the passing carriage, flew loudly croaking over the travelers' heads.
There was no house to be seen on the road, no pedestrian, and no
conveyance of any kind.
Karl looked every now and then at his silent companion, and said at
last, pointing to the horses, "How rough their coats are, and how pretty
their gray mouse skins! I wonder how many of these beasties would go to
make up my sergeant's horse! When I took leave of my father, the old man
said, 'Perhaps I shall pay you a visit, little one, when they light the
Christmas-tree.' 'You'll never be able,' said I. 'Why not?' asked he.
'You'll never trust yourself in any post-chaise.' Then the old boy
cried, 'Oho! post-chaises are always of a stout build; I shall be sure
to trust myself in one.' But now, Mr. Anton, I see that my father never
can pay us a visit."
"Why not?"
"It is possible that he may reach Rosmin; but, as soon as he sees these
horses and this road, he will instantly turn back. 'Shall I trust
myself,' he'll say, 'in a district where sand runs between one's legs
like water, and where mice are put into harness? The ground is not firm
enough for me.'"
"The horses are not the worst things here," said Anton, absently. "Look!
these go fast enough."
"Yes," replied Karl, "but they don't go like regular horses; they
entangle their legs like two cats playing in a parsley-bed. And what
things they have for shoes--regular webbed hoofs, I declare, which no
blacksmith can ever fit."
"If we could only get on!" returned Anton; "the wind blows cold, and I
am shivering in spite of my fur."
"You have slept but little the last few nights, sir," said Karl. "The
wind blows here as if over a threshing-floor. The earth is not round
hereabouts as elsewhere, but flat as a cake. This is a complete desert;
we have been driving for more than an hour, and there is not a village
to be seen."
"A desert indeed," sighed Anton; "let us hope it may improve." They
relapsed into profound silence. At length the driver stopped near a
pool, unharnessed the horses, and led them to the water's edge, without
noticing the travelers.
"What the deuce does this mean?" cried Karl, jumping down from the
carriage.
"I am going to feed," replied the servant, sulkily, in a foreign accent.
"I am anxious to know how that will be done," said Karl. "There is not
the shadow of a bag of provender."
The horses, however, soon proved that they could live without corn; they
stretched down their shaggy heads, and began to pull the grass and weeds
at the edge of the pool, sometimes taking a draught of the dirty water.
Meanwhile the servant drew a bundle from under his seat, settled himself
under the lee of an alder-bush, and, taking his knife, cut his bread and
cheese without even glancing at the travelers.
"I say, Ignatius or Jacob," cried Karl, sharply, "how long will this
breakfast of yours last?"
"An hour," replied the man, munching away.
"And how far is it from here to the estate?"
"Six miles, or maybe more."
"You can make nothing of him," said Anton; "we must put up with the
customs of the country;" and, leaving the carriage, they went to look on
at the horses feeding.
Anton is on his way to the Polish property. He is now the baron's agent.
Anxious months have the last proved to him. The parting from his
principal and the firm had been painful in the extreme. For some time
before it, indeed, Anton had found himself alone in the midst of his
colleagues. The quiet Baumann still remained his friend, but the others
considered him a castaway. The merchant received his resignation with
icy coldness; and even in the hour of parting, his hand lay impassive as
metal in Anton's grasp. Since then, our hero had undertaken several
journeys to the capital and to creditors in the family's behalf, and now
he was on his way to set the new estate in order, accompanied by Karl,
whom he had induced to become the baron's bailiff.
Ehrenthal had, by the authority conferred on him,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from the time of the sale by auction, and hired the Polish
bailiff for the baron. There had been unfair dealings between them at
the time, and it was well known in Rosmin that the bailiff had sold off
a good deal, and been guilty of all sorts of frauds since, so that Anton
had even now no prospect of a quiet life.
"The hour is come when I may execute my commission," cried Karl, groping
in the straw under the seat. He drew out a large japanned tin case, and
carried it to Anton. "Miss Sabine gave me this in charge for you." He
then joyously opened the lid, produced the materials for an excellent
breakfast, a bottle of wine, and a silver goblet. Anton took hold of the
case.
"It has a very knowing look," said Karl. "Miss Sabine planned it
herself."
Anton examined it on all sides, and placed it carefully on a tuft of
grass; then he took up the goblet, and saw his initials engraved on it,
and underneath the words, "To thy welfare." Whereupon he forgot the
breakfast and all around him, and stood gazing at the goblet, lost in
thought.
"Do not forget the breakfast, sir," suggested Karl, respectfully.
"Sit down by me, my faithful friend; eat and drink with me. Leave off
your absurd politeness. We shall have but little, either of us, but what
we have we will share like brothers. Take the bottle if you have no
glass."
"There's nothing like leather," said Karl, taking a small leathern
drinking-cup out of his pocket. "As for 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t was
kindly meant, and I thank you; but there must be subordination, if it
were but for the sake of the others; and so, sir, be kind enough to let
me shake hands with you now, and then let things be as they were before.
Only look at the horses, Mr. Anton. My faith! the creatures devour
thistles."
Again the horses were harnessed, again they threw out their short legs
in the sand, and again the carriage rolled through the barren
district--first through an empty plain, next through a wretched
fir-wood, then past a row of low sand-hills, then over a tumble-down
bridge crossing a small stream.
"This is the property," said the driver, turning round, and pointing
with his whip to a row of dirty thatched roofs that had just come into
sight.
Anton stood up to look for the group of trees in which the Hall might be
supposed to stand. Nothing of the sort to be seen. The village was
deficient in all that adorns the home of the poorest German peasant--no
orchard, no hedged-in gardens, no lime-trees in the market-place.
"This is wretched," said he, sitting down again; "much worse than they
told us in Rosmin."
"The village looks as if under a curse," cried Karl; "no teams working
in the fields--not a cow or a sheep to be seen."
The farm-servant flogged his horses into an irregular gallop, and so
they passed through the rows of mud huts which constituted the village,
and arrived at the public house. Karl sprang from the carriage, opened
the tavern door, and called for the landlord. A Jew slowly rose from his
seat by the stove and came to the threshold. "Is the gendarme from
Rosmin come?" He is gone into the village. "Which is the way to the
farm-yard?"
The landlord, an elderly man with an intelligent countenance, described
the way in German and Polish, and remained standing at the
door--bewildered, Karl declared, by the sight of two human beings. The
carriage turned into a cross-road, planted on both sides with thick
bushes, the remains of a fallen avenue. Over holes, stones, and puddles,
it rattled on to a group of mud huts, which still had a remnant of
whitewash upon them. "The barns and stables are empty," cried Karl, "for
I see gaps in the roofs large enough to drive our carriage through."
Anton said no more; he was prepared for every thing. They drove through
a break between the stables into the farm-yard, a large irregular space,
surrounded on three sides by tumble-down buildings, and open to the
fields on the fourth. A heap of _débris_ lay there--lime and rotten
timber, the remains of a ruined barn. The yard was empty; no trace of
farm implements or human labor to be seen. "Which is the inspector's
house," inquired Anton, in dismay. The driver looked round, and at last
made up his mind that it was a small one-storied building, with straw
thatch and dirty windows.
At the noise of the wheels a man appeared on the threshold, and waited
phlegmatically till the travelers had dismounted, and were standing
close before him. He was a broad-shouldered fellow, with a bloated,
brandy-drinking face, dressed in a jacket of shaggy cloth, while behind
him peered the muzzle of an equally shaggy dog, who snarled at the
strangers. "Are you the steward of this property?"
"I am," replied the man, in broken German, without stirring from where
he was.
"And I am the agent of the new proprietor," said Anton.
"That does not concern me," growled the shaggy man, turning sharp round,
entering the house, and bolting the door within.
Anton was thoroughly roused. "Break the window in, and help me to catch
the rascal," cried he to Karl, who coolly seized a piece of wood, struck
the panes so as to make the rotten framework give way, and cleared the
opening at one leap. Anton followed him. The room was empty, so was the
next, and in it an open window--the man was gone.
"After him!" cried Karl, and dashed on in pursuit, while Anton looked
about the house and out-buildings. He soon heard the barking of a dog,
and saw Karl capture the fugitive. Hurrying to his help, he held the man
fast, while, with a kick, Karl sent the dog flying. They then contrived
to force the steward back to the house, though he kept striking out
violently all the way.
"Go to the tavern, and bring the gendarme and the landlord," cried Anton
to the driver, who, undisturbed by all that had been going on, had
meanwhile unpacked the carriage. The man accordingly drove leisurely
off, and the fugitive being got into the room, Karl found an old cloth,
and with it bound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I beg your pardon, sir,"
said he; "it is only for an hour or so, till the arrival of the Rosmin
gendarme, whom we have appointed to meet us."
Anton then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house, bu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found but the merest necessaries; no books nor papers of any kind. It
had doubtless been emptied already. A bundle projected from the
coat-pocket of the prisoner, which turned out to be receipts and legal
documents in Polish. In time, the driver returned with the landlord and
the armed policeman. The landlord stood at the door in some perplexity,
and the policeman explained in a few moments what remained to be done.
"You must make a statement to the local judge, and give the man up to
me. He shall go back in your carriage to Rosmin. You will do well to get
rid of him, for this is a wild country, and it will be safer for you to
have him at Rosmin than here, where he has friends and accomplices."
After a long search, a sheet of paper was found in a cupboard, the
statement made and submitted to the policeman, who shook his head a
little over the Polish composition, and the prisoner lifted into the
carriage, the gendarme taking his seat beside him, and saying to Anton,
"I have long expected something of the kind. You may have often occasion
to want me again." The carriage then drove away, and thus the property
came under Anton's administration. He felt as if cast on a desert
island.
His portmanteau and traveling effects were leaning against a mud wall,
and the Polish landlord was the only man who could give him and Karl any
information or advice in their forlorn condition.
Now that the steward was fairly gone, the landlord grew more
communicative, and showed himself serviceable and obliging. A long
conversation ensued, and its purport was what Anton had apprehended from
the warning given by the Commissary Walter and other Rosmin officials.
The inspector had,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done all he could in the
way of spoliation, rendered daring by a report which had found its way
from the town to the village, that the present proprietor would never be
able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estate. At last Anton said, "What that
wretched man has done away with he will have to account for; our first
care must be to preserve what is still to be found on the property. You
must be our guide to-day."
They then examined the empty buildings. Four horses and two
servants--they were gone into the wood--a few old plows, a pair of
harrows, two wagons, a britzska, a cellar full of potatoes, a few
bundles of hay, a little straw--the inventory did not take much time in
drawing up. The buildings were all out of repair, not through age, but
neglect.
"Where is the dwelling-house?" inquired Anton. The landlord led the way
out of the yard to the meadow--a broad plain, gradually sloping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brook. It had been a great pasture. The cattle had
trodden it down into holes; the snouts of greedy swine had rooted it up;
gray molehills and rank tufts of grass rose on all sides.
The landlord stretched out his hand. "There is the castle. This castle
i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he added, reverentially; "no
nobleman in the district has a stone house like that. All the gentry
here live in wood and mud buildings. Herr von Tarow, the richest of
them, has but a poor dwelling."
About three hundred yards from the last out-building rose a great brick
edifice, with a black slate roof and a thick round tower. Its gloomy
walls on this treeless pasture-land, without one trace of life around,
rose beneath the cloudy sky like a phantom fortress which some evil
spirit had evoked from the abyss--a station from which to blight all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The strangers approached it. The castle had fallen into ruins before the
builders had finished their task. The tower had stood there for ages. It
was built of unhewn stone, and had small windows and loop-holes. The
former lords of the land had looked down from its summit on the tops of
the trees, which then stretched far into the plain. They had then ruled
with a rod of iron the serfs who cultivated their land, and toiled and
died for them. Many an arrow had sped through those loop-holes at the
enemy storming below, and many a Tartar horse had been overthrown before
those massive walls. Years ago, a despot of the district had, in
expiation of former sins, begun to add to the gray tower the walls of a
holy monastery; but the monastery never got finished, and the useless
walls had already stood there long, when the late count took it into his
head to convert them into a lordly dwelling for his race, and to raise a
house unparalleled for magnificence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 front of the house was added on to both sides of the tower, which
projected in the middle. The intention had been to have a high
terrace-road up to the castle, and the principal entrance had been made
in the tower, and arched over; but the terrace never having been formed,
the stone threshold of the main door was quite inacce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ladders, and the wide opening was left. The window-spaces of
the lower floor were merely closed up with boards, while on the second
story were some window-frames of beautifully carved wood, in which large
panes had once been placed, but they had got broken. In other windows
were temporary frames of rough deal, with small panes of muddy glass let
into them. A company of jackdaws sat on the top of the tower, looking
down in amazement on the strangers, and every now and then one flew off,
screaming loudly, to contemplate the intruders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A house for crows and bats, not for human beings," said Anton. "At
least, I see no way of getting into it."
The landlord now took them round the building. Behind, where the two
wings made a sort of horse-shoe, there were low entrances to the cellars
and offices; beneath which, again, were stables, great arched kitchens,
and small cells for the serfs. A wooden staircase led to the upper
story. The door turned creaking on its hinges, and a narrow passage took
them through a side wing to the front part of the house. There all was
at least magnificently planned. The circular entrance-hall--an arched
room of the old tower--was painted in mosaic, and through the great
doorway-opening was seen a wide expans
small disturbance made by the return of Anton had gradually settled
down. Those first-class treasures of Sabine's had made way for other
specimens of damask, still of a superior kind, it is true, but which
came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e elderly cousin's comprehension. She had
been quite right in prophesying that Anton would never remark those
signs of exuberant gratitude or their withdrawal. However, one change
had been permanently made--the greatest, the best of all changes--the
clerk retained a privileged place in the heart of the young mistress of
the firm, and his tall figure often appeared as one of the circle that
Sabine's fancy loved to gather round her when at her work-table or in
her treasure-chamber.
To-day she was walking restlessly up and down before dinner. The cousin,
who heard every thing, had just told her that a maid from Ehrenthal's
had run into the office to announce Bernhard's death to his friend. "How
will he bear it?" thought she. And the name of Ehrenthal forced her
thoughts back to the past, to one now far away, and to that painful hour
when the struggle going on in her own mind had been suddenly brought to
a close by a letter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parted. And Anton had known
of that conquered feeling of hers. How considerate he had always been,
how chivalrous, how helpful! She wondered if he had any idea of the
completeness of her triumph over a girlish illusion. She shook her head.
"No, he has not. It was here, at this very table, that an accident first
betrayed me to him. That past time still rises like a cloud between us.
Whenever I sit near Wohlfart of an evening, I am conscious of another's
shadow at my side; and when he speaks to me, his tone, his manner always
seem to say, 'You are not alone; he is with you.'" Sabine started, and
lovingly passed her hand over the beautiful flowers on the table before
her, as if to dispel a painful thought. She could not tell him that she
was free from that long-felt sorrow. Now, however, when he had lost a
friend whom he so much loved, she must show him that there were other
hearts that clung to him still. And again she walked up and down, trying
to devise a way of speaking to him alone.
Dinner was announced. Anton came with the rest, and took his place at
once. There was no opportunity of exchanging a word during the meal, but
he often met her sad and sympathizing eye. "He eats nothing at all
to-day," whispered her cousin; "not even any of the roast," she added,
reproachfully. Sabine was much perturbed. Mr. Jordan had already risen;
Anton would leave the room with the rest, and she should not see him
again the whole day through. So she called out, "The great Calla is
fully blown now. You were admiring the buds the other day; will you
remain a moment; I should like to show it you?" Anton bowed and staid
behind. A few more awkward moments, then her brother rose too; and,
hurrying to Anton, she took him to the room where the flowers were.
"You have had sorrowful tidings to-day," she began.
"The tidings themselves did not surprise me," replied Anton. "The doctor
gave no hope. But I lose much in him."
"I never saw him," said Sabine; "but I know from you that his life was
lonely--poor in affection and in enjoyment."
She moved an arm-chair toward Anton, and led him on to talk about his
friend. She listened to every word with warm sympathy, and well knew
what to ask and how to comfort. It was a relief to Anton to speak of the
departed one, to describe his quiet way of life, his erudition, his
poetical enthusiasm. After a pause, Sabine looked up frankly into his
face, and asked, "Have you any tidings of Herr von Fink?"
It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his departure that she had ever breathed his
name. Anton felt how touching her confidence was, given in this hour of
his sadness. In his emotion, he seized her hand, which she was slow in
withdrawing.
"He is not happy in his new life," he gravely replied. "There was a
savage humor in his last letter, from which I gather, even more than
from his actual words, that the business into which his uncle's death
has thrown him does not suit him."
"It is unworthy," cried Sabine.
"At all events, it is not what would be recognized as honorable in this
house," replied Anton. "Fink is upright, and has lived too long with
your brother to take pleasure in the wild speculations so common on the
other side the Atlantic. His partners and colleagues are for the most
part men without a conscience, and his feelings revolt against their
companionship."
"And can Herr von Fink tolerate such relations as these for a day?"
"It is a remarkable thing that he whose own will was ever so arbitrarily
exercised, should now be obliged against that will to obey a pressure
from without, and every where to work with his hands tied. The
organization of such speculations in America is so complicated that one
shareholder can do little to alter it; and, now that Fink has attained
what used to be the goal of his wishes--a large capital, and the
management of immense districts--his condition appears more uncertain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He was always in danger of thinking slightingly
of others, now I am distressed at the bitter contempt he expresses for
his own life. His last letter paints an intolerable state of things, and
seems to point to some decisive resolve."
"There is only one resolve for him," cried Sabine. "May I ask what you
said to him in reply?"
"I entreated him instantly, come what would, to free himself from the
business in which he was entangled. I said that his own strong will
might find a way of extrication, even if that which I pointed out proved
impracticable. Then I begged of him either to carry out his old plan of
becoming a landed proprietor in America, or to return to us."
"I knew that you would write thus," said Sabine, drawing a long breath.
"Yes, Wohlfart, he shall return," said she, gently, "but he shall not
return to us."
Anton was silent.
"And do you think that Herr von Fink will follow your advice?"
"I do not know. My advice was not very American."
"But it was worthy of you," cried Sabine, with proud delight.
"An officer wishes to speak to Mr. Wohlfart," said a servant at the
door.
Anton sprang up. Sabine went to her flowers and bent mournfully over
them. The shadows of others hovered still between her friend and her.
The few words spoken by the servant filled Anton with a vague terror. He
hurried into the ante-room: there stood Eugene von Rothsattel. Anton was
gladly rushing forward to greet him, but the young soldier's face of
agony made him start back. He whispered, "My mother wishes to speak to
you; something dreadful has occurred." Anton caught up his hat, ran into
the office, hurriedly asked Baumann to excuse him to the principal, and
then accompanied the lieutenant to the baron's house.
On the way, Eugene, who had lost all self-command, said unconnectedly to
Anton, "My father last night accidentally wounded himself by a
pistol-shot--a messenger was sent to summon me--when I came, I found my
mother in a swoon--my sister and I do not know what to do--Lenore
implored my mother on her knees to send for you--you are the only one in
whom w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our distress--I understand nothing about
business, but my father's affairs must be in a dreadful state--my mother
is beside herself--the whole house is in the greatest disorder."
From what Eugene said and what he did not say; from his broken sentences
and his look of agony, Anton guessed at the horrors of the previous
evening. In the boudoir of the baroness he found Lenore, weeping and
exhausted.
"Dear Wohlfart!" cried she, taking his hand and beginning again to sob,
while her head sank powerless on his shoulder.
Meanwhile Eugene walked up and down, wringing his hands, and at length
throwing himself on the sofa, he gave himself up to silent tears.
"It is horrible, Mr. Wohlfart," said Lenore, lifting up her head. "No
one may approach my father--Eugene may not, nor I--only my mother and
old John are with him; and early this morning the merchant Ehrenthal was
here, insisting that he must see my father. He screamed at my mother,
and called my father a deceiver, till she fainted away. When I rushed
into the room, the dreadful man went off threatening her with his
clenched fist."
Anton led Lenore to a chair and waited till she had told him all.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comforting in this case, and his own heart was
wrung to the utmost by the misery he witnessed.
"Call my mother, Eugene," said Lenore, at length.
Her brother left the room.
"Do not forsake us," implored Lenore, clasping her hands; "we are at the
last gasp; even your help can not save us."
"He is dead who might perhaps have done so," mournfully replied Anton.
"Whether I can be of any use I know not, but you can not doubt my
willingness to be so."
"No," cried Lenore. "And Eugene, too, thought of you at once."
The baroness now entered. She walked wearily; but, steadying herself by
a chair, she saluted Anton with dignity. "In our position," said she,
"we need a friend who knows more of business than we three do.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prevents the baron--possibly for a long time to
come--from managing his own affairs, and, little as I understand them, I
can see that our interests require prompt measures. My children have
mentioned you to me, but I fear I am unreasonable in asking you to
devote your time to our service."
She sat down, beckoned Anton to take a chair, and said to her children,
"Leave us; I shall be better able to tell Mr. Wohlfart the little that I
know when I do not see your grief."
When they were alone, she motioned him nearer and tried to speak, but
her lips quivered, and she hid her face in her handkerchief.
"Before I can consent, gracious lady," said he, "to your reposing in me
such confidence as this, I must first inquire whether the baron has no
relative or intimate friend to whom you could with less pain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I pray you to remember that my own knowledge of business
is but small, and my position not one to constitute me a proper
counselor to the baron."
"I know no one," said the baroness, hopelessly. "It is less painful to
me to tell you what I can not conceal, than to one of our own circle.
Consider yourself a physician sent for to visit a patient. The baron has
this morning told me some particulars of his present circumstances." And
then she proceeded to relate what she had gathered as to the nature of
his embarrassments, the danger in which the family property was placed,
and the capital needed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Polish estate.
"My husband," continued she, "has given me the key of his desk, and he
wishes Eugene, with the help of a man of business, to go over his
papers. I now request of you to make this examination together with my
son. When you need explanations, I will try to obtain them from the
baron. The question is now, whether you are inclined to undertake this
trouble for us, who are only strangers."
"I am most willing to do so," earnestly replied Anton; "and I hope that
the kindness of my principal will allow me the time needful for the
purpose, if you do not consider it more advisable to depute the baron's
experienced legal adviser to the task."
"There will be an opportunity of asking that gentleman's advice later,"
said the baroness.
Anton rose. "When do you wish to begin?"
"Immediately. I fear there is not a day to lose. I shall do all I can to
help you look the papers over." She led Anton into the next room, called
in Eugene, and unlocked the baron's desk. As she opened it she lost her
self-command for a moment, and moving to the window, the quivering of
the curtains betrayed the anguish that shook her fragile frame.
The mournful task began. Hour after hour passed. Eugene was in no
condition to peruse any thing, but his mother reached letters and
documents to Anton, and, though often obliged to desist a while, she
bravely returned to the task. Anton placed the papers in order, and
sought, by glancing over each, to arrive at least at a superficial view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It was evening, when the old servant opened the door in dismay, and
called out, "He is there again." The baroness could not repress a slight
scream, and made a gesture of aversion.
"I have told him that no one is at home, but he will not be dismissed;
he makes such a noise on the steps. I can not get rid of him."
"It will kill me if I hear his voice again," murmured the baroness.
"If the man be Ehrenthal," said Anton, rising, "I will try to get him
away. We have now done what was most necessary; have the goodness to
lock up these papers, and to allow me to return to-morrow." The baroness
silently assented, and sank back in her chair. Anton hurried off to the
ante-room, whence he could hear Ehrenthal's loudly-raised voi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usurer shocked him. His hat pushed half off his
head, his pale face swelled as if by drinking, his glazed eyes red with
tears, Ehrenthal stood before him, calling in broken sentences for the
baron, wailing and cursing alternately. "He must come! he must come at
once!" cried he; "the wicked man! A nobleman, indeed! he is a vagabond,
after whom I will send the police. Where is my money? Where is my
security? I want my mortgage from this man who is not at home."
Anton went straight up to him, and asked, "Do you know me, Mr.
Ehrenthal?" Ehrenthal turned his glazed eyes upon him, and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 friend of his dead son.
"He loved you!" he cried, in a lamentable voice. "He spoke to you more
than to his father. You were the only friend that he had on earth. Have
you heard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house of Ehrenthal?" continued he, in
a whisper. "Just as they stole the papers he died. He died with a hand
like this," and clenching his fist he struck his forehead. "Oh my son!
my son! why didst not thou forgive thy father!"
"We will go to your son," said Anton, taking the arm of the old man, who
unresistingly allowed himself to be led back to his own house.
From thence Anton hurried to Councilor Horn, with whom he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It was late before he returned home. In the midst of his anxiety about
those whose prosperity had filled his imagination years before,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in their adversity, reposed in him, dilated his
breast with a feeling of pride. He burned with desire to help them, and
hoped that his zealous devotion might yet find some way of rescue. As
yet he saw none. Looking up at the great building before him, so firm
and secure, in the moonlight, a thought flashed into his mind. If any
man could help them, it was his principal. His keen eye would be able to
unravel all the dark secrets in which the baron was entangled, and his
iron strength of will would crush the villains who held the unfortunate
nobleman in their power. And then he had a noble nature; he always
decided on the right, without an effort or a struggle. Anton looked at
the first floor. The whole house-front was dark, but in a corner room a
light still burned. It was the private office of his chief.
With sudden resolve, Anton begged the servant to take him to Mr.
Schröter, who looked with amazement at the unexpected visitor, and asked
what brought him, and whether any thing had happened.
"I implore your counsel--I implore your help," cried Anton.
"For yourself or for others?" inquired the merchant.
"For a family with whom I have accidentally become connected. They are
lost if a strong hand does not ward off the impending catastrophe."
Anton then rapidly related the occurrences of the afternoon, and,
seizing his principal's hand in his emotion, cried, "Have pity upon the
unhappy ladies, and help them."
"Help them!" replied the merchant; "how can I? Have you been
commissioned to apply to me, or are you only following the impulse of
your own feelings?"
"I am not commissioned; it is only the interest that I take in the
baron's fate which leads me to you."
"And what right have you to inform me of facts communicated in strict
confidence to yourself by the baron's lady?" asked the merchant, dryly.
"I am committing no indiscretion in telling you what will, in a few
days, be no secret, even to strangers."
"You are unusually excited, otherwise you would not forget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hatever, does a man of business venture to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without the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Of course, I shall make no wrong use of what you have said, but it was
by no means business-like, Wohlfart, to be so open toward me."
Anton was silent, feeling, indeed, that his principal was right, but yet
it seemed hard to be blamed for reposing confidence at such a time as
this. The merchant walked silently up and down; at length, stopping
before Anton, he said, "I do not now inquire how you come to take so
warm an interest in this family. I fear it is an acquaintance you owe to
Fink."
"You shall hear all," said Anton.
"Not at present. I will now content myself with repeating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interfere in these affairs without being specially
applied to by the parties themselves. I may add that I by no means wish
for such an application, and do not disguise from you that, were it
made, I should probably decline to do any thing for the Baron
Rothsattel."
Anton's feelings were roused to the utmost. "The question is the rescue
of an honorable man, and of lovely and amiable women from the toils of
rogues and impostors. To me, this seems the duty of every one; I, at
least, consider it a sacred obligation which I dare not shrink from. But
without your support I can do nothing."
"And how do you think this embarrassed man can be helped?" inquired the
merchant, seating himself.
With somewhat more composure, Anton repli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an experienced man of business making himself master of the case. There
must be some way of circumventing these villains. Your penetration would
discover it."
"Any attorney would be far more likely to do so, and the baron might
readily engage the services of experienced and upright legal advisers.
If his enemies have done any thing illegal, the quick eye of a lawyer is
the most likely to detect it."
"Alas! the baron's own lawyer gives but little hope," replied Anton.
"Then, my dear Wohlfart, no other is likely to do much good. Show me an
embarrassed man who has strength to grasp an offered hand, and bid me
help him, and for the sake of all I owe you, I will not refuse to do so.
I think you are convinced of this."
"I am," said Anton, dejectedly.
"From all I hear, however," the merchant went on,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the baron. From what I gather from general report, as well as from
you, his embarrassments arise from his having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usurers, which proves him deficient in what alone ennobles the life of
any man--good sense, and the power of steady exertion."
Anton could only sigh his assent.
"To help such a man," inexorably continued the merchant, "is a futile
attempt, against which reason may well protest. We are not to despair of
any, but want of strength is the most hopeless case of all. Our power of
laboring for others being limited, it becomes our duty to inquire,
before we devote our time to the weak, whether we are not thus
diminishing our chances of helping better men."
Anton interrupted him. "Does he not deserve every allowance to be made
for him? He was brought up to exact much; he has not learned, as we
have, to make his way by his own labor."
The merchant laid his hand on the young man's shoulder. "The very
reason. Believe me, a large number of these landed gentry, who pay the
penalty of their old family memories, are beyond help. I am the last to
deny that many worthy and admirable men belong to this class. Indeed,
wherever remarkable talent or nobility of character shoots up among
them, no doubt their position offers peculiar scope for its development,
but for average men it is not a favorable one. He who considers it his
hereditary privilege to enjoy life, and who assumes a distinguished
position in virtue of his family, will very often fail to put forth his
whole strength in order to deserve that position. Accordingly, numbers
of our oldest families are declining, and their fall will be no loss to
the state. Their family associations make them haughty without any
right to be so--limit their perceptions and confuse their judgment."
"Even if all this be true," cried Anton, "it does not absolve us from
helping individuals of the class who have excited our sympathy."
"No," said the principal, "if it be excited. But it does not glow so
rapidly in advancing years as in youth. The baron has endeavored to
isolate his property from the current of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leave it forever to his family. Forever! You, as a merchant, know how to
estimate the attempt. True, every rational man must allow it to be
desirable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same soil should be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We all prize what our forefathers have possessed before
us, and Sabine would unlock every room in this house with pride, because
her great-great-grandmother turned the same keys before her. It is
therefore natural that the landed proprietor should desire to preserve
those familiar scenes, which are the source of his own prosperity, to
those nearest and dearest to him. But there must be means to this end,
and these means are the making his own existence available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increase of his patrimony. Where energy dies in families
or individuals, then it is well that their means die too, that their
money should circulate through other hands, and their plowshare pass to
those who can guide it better. A family that has become effete through
luxury ought to sink down into common life, to make room for the
uprising of fresh energies and faculties. Every one who seeks, at the
cost of free activity for others, to preserve permanent possessions and
privileges for himself or his family, I must look upon as an enemy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social state. And if such a man ruin
himself in his endeavors, I should feel no malicious pleasure in his
downfall, but I should say that he is rightly served, because he has
sinned against a fundamental law of our social being; consequently, I
should consider it doubly wrong to support this man, because I could but
fear that I should thus be supporting an unsound condition of the body
politic."
Anton looked down mournfully. He had expected sympathy and warm
concurrence, and he met with disaffection and coldness that he despaired
of conquering. "I can not gainsay you," he at length replied; "but in
this case I can not feel as you do. I have been witness to the
unspeakable distress in the baron's family, and my whole soul is full
of sadness and sympathy, and of the wish to do something for those who
have opened their heart to me. After what you have said, I dare no
longer ask you to trouble yourself with their affairs, but I have
promised the baroness to assist her as far as my small powers permit,
and your kindness allows. I implore you to grant me permission to do
this. I shall endeavor to be regular in my attendance at the office, but
if during the next few weeks I am occasionally absent, I must ask you to
excuse me."
Once more the merchant walked up and down the room, and then, looking at
Anton's excited face, with deep seriousness and something of regret, he
replied, "Remember, Wohlfart, that every occupation which excites the
mind soon obtains a hold over a man, which may retard as well as advance
his success in life. It is thi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 to agree
to your wishes."
"I know it," said Anton, in a low voice; "but I have now no choice
left."
"Well, then, do what you must," said the merchant, gloomily; "I will lay
no hinderance in your way; and I hope that after a few weeks you will be
able to consider the whole circumstances more calmly." Anton left the
room, and the merchant stood looking long with frowning brow at the
place his clerk had occupied.
Nor was Anton in a more congenial mood. "So cold, so inexorable!"
exclaimed he, as he reached his own room. He began to suspect that his
principal was more selfish and less kindly than he had hitherto
supposed. Many an expression of Fink's recurred to his mind, as well as
that evening when young Rothsattel, in his boyish conceit, had spoken
impertinently to the merchant. "Is it possible," thought he, "that that
rude speech should be unforgotten?" And his chief's keen, deep-furrowed
face lost inexpressibly by contrast with the fair forms of the noble
ladies. "I am not wrong," he cried to himself; "let him say what he
will, my views are more just than his, and henceforth my destiny shall
be to choose for myself the way in which I shall walk." He sat long in
the darkness, and his thoughts were gloomy as it; then he went to the
window to look down into the dark court below. A great white blossom
rose before him like a phantom. Striking a light, he saw that it was the
beautiful Calla out of Sabine's room. It hung down mournfully on its
broken stem. Sabine had had it placed there. This little circumstance
struck him as a mournful omen.
Meanwhile Sabine, taper in hand, entered her brother's room.
"Good-night, Traugott," nodded she. "Wohlfart has been with you this
evening; how long he staid!"
"He will leave us," replied the merchant, gloomily.
Sabine started and dropped her taper on the table. "For God's sake, what
has happened? Has Wohlfart said that he was going away?"
"I do not yet know it, but I see it coming step by step; and I can not,
and still less can you, do any thing to retain him. When he stood before
me here with glowing cheeks and trembling voice, pleading for a ruined
man, I found out what it was that lured him away."
"I do not understand you," said Sabine, looking full at her brother.
"He chooses to become the confidential friend of a decayed noble. A pair
of bright eyes draws him away from us: it seems to him a worthy object
of ambition to become Rothsattel's man of business. This intimacy with
nobility is the legacy bequeathed to him by Fink."
"And you have refused to help him?" inquired Sabine, in a low voice.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said the merchant, harshly; and he
turned to his writing-table.
Sabine slowly withdrew. The taper trembled in her hand as she passed
through the long suite of rooms listening to her own footfall, and
shuddering as the feeling came over her that an invisible companion
glided by her side. This was the revenge of that other. The shadow that
once fell on her innocent life now drove her friend away from their
circle. Anton's affections clung to another. She had but been in his
eyes a mere stranger, who had once loved and languished for one now far
away, and who now, in widow's weeds, looked back regretfully to the
feelings of her youth.
The few next weeks were spent by Anton in over-hard work. He had great
difficulty in keeping up his counting-house duties, while he spent every
spare hour in conference with the baroness and the lawyer.
In the mean time, the misfortunes of the baron ran their course. He had
not been able to pay the interest of the sums with which his estate was
burdened. When last they were due, a whole series of claims was brought
against him, and the estate fell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district authorities. Complicated lawsuits arose. Ehrenthal complained
loudly, claiming the first mortgage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nay, he
was inclined to advance claims on the last mortgage offered by the baron
in the recent fatal hour. Löbel Pinkus also appeared as claimant of the
first mortgage, and asserted that he had paid the whole sum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Ehrenthal had no proof to bring forward, and had been
for some weeks past quite unable to manage his own affairs, while
Pinkus, on the contrary, fought with every weapon a hardened sinner can
devise or employ, and the deeds which the baron had executed at Veitel's
suggestion proved to be so capital a master-stroke of the cunning
advocate, that the baron's man of business had, from the first, little
hope of the case. We may here observe that Pinkus did eventually win it,
and that the mortgage was made over to him.
Anton was now gradually gaining some insight into the baron's
circumstances. But the double sale of the first mortgage was still kept
a secret by the latter, even from his wife. He declared Ehrenthal's
claim unfounded, and even expressed a suspicion that he had himself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robbery in his office. Indeed, he really
believed this. Then the name of Itzig was never broached, and the
suspicion against Ehrenthal, which the baron's lawyer shared, prevented
Anton seeking any explanation from him.
Meanwhile, an estrangement had sprung up between our hero and his
principal, which the whole counting-house remarked with surprise. The
merchant scowled at Anton's vacant seat when the latter chanced to be
absent during office-hours, or looked coldly at his clerk's face, made
pale as it was with excitement of mind and night-work. He took no notice
of his new occupation, and never seemed to remark him. Even to his
sister he maintained a stiff-necked silence; nor could all her attempts
lead him to speak of Anton, who, on his side, felt his heart revolt
against this coldness. After his return, to be treated like a child of
the house, praised, promoted, petted, and now to be treated like a mere
hireling, who is not worth the bread thrown to him; to be a toy of an
incomprehensible caprice--this, at least, he had not deserved; so he
became reserved toward the whole family, and sat silent at his desk; but
he fel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now and the then so keenly, that often,
when alone, he would spring up and stamp on the ground in the bitter
indignation of his heart.
One comfort remained. Sabine was not estranged. True, he saw little of
her, and at dinner she seemed to avoid speaking to him, but he knew that
she was on his side.
A few days after his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the merchant, she came down
stairs as he stood in the hall, and had to pass him by so closely that
her dress touched him. He had retreated, and made a formal bow, but she
looked at him imploringly, and whispered, "You must not be estranged
from me." It was an affair of a moment, but the faces of both were
radiant with a happy understanding.
The time had now arrived when Mr. Jordan was to quit the firm. The
principal again called Anton into his little office, and without any
severity, but also without a trace of his former cordiality, began: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o you my intention of appointing you Jordan's
successor; but,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your time has been more taken
up with other business than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such a post, I
therefore ask you whether you are now at liberty to undertake Jordan's
duties?"
"I am not," replied Anton.
"Can you name any--not very distant--time when you will be free from
your present occupation? In that case I will endeavor to find a
substitute until then."
Anton sorrowfully replied, "I can not at present say when I shall again
be master of my whole time; and, besides, I feel that, even as it is, I
tax your indulgence by many irregularities. Therefore, Mr. Schröter, I
beg that you will fill up this post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me."
The merchant's brow grew furrowed and dark, and he silently bowed
assent. Anton felt as he closed the door that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m was now complete, and, resuming his place, he leaned his throbbing
head on his hand. A moment later Baumann was summoned to the principal,
and Jordan's situation conferred upon him. On returning to the office,
he went up to Anton and whispered, "I refused at first, but Mr. Schröter
insisted. I am doing you an injustice." And that evening Mr. Baumann, in
his own room, read in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the chapters treating of
the unjust Saul (the principal), and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Jonathan
and the persecuted David, and strengthened his heart thereby.
The next day Anton was summoned to the baroness. Lenore and her mother
sat before a large table covered with jewel-boxes and toilette elegances
of every description, while a heavy iron chest stood at their feet. The
curtains were drawn, and the subdued light shone softly into the richly
furnished room. On the carpet glowed wreaths of unfading flowers, and
the clock ticked cheerfully in its alabaster case. Under the shade of
flowering plants sat the two love-birds in their silvered cage, hopping
from perch to perch, screaming ceaselessly, or sitting up quietly close
to each other. The whole room was beauty and perfume. "For how long?"
thought Anton. The baroness rose. "We are already obliged to trouble you
again," said she; "we are engaged in a very painful occupation." On the
table were all manner of ornaments, gold chains, brilliants, rings,
necklaces, gathered into a heap.
"We have been looking out all that we can dispense with," said the
baroness, "and now pray you to undertake to sell these things for us. I
have been told that some of them are of value, and as we are now in much
need of money, we turn here for help."
Anton looked in perplexity at the glittering heap.
"Tell us, Wohlfart," cried Lenore, anxiously, "is this necessary? can it
be of any use? Mamma has insisted upon setting apart for sale all our
ornaments, and whatever plate is not in daily use. What I can give is
not worth talking of, but my mother's jewels are costly; many of them
were presents made to her in youth, which she shall not part with unless
you say that it is necessary."
"I fear," said Anton, gravely, "that it will prove so."
"Take them," said the baroness to Anton; "I shall be calmer when I know
that we have at least done what we could."
"But do you wish to part with all?" inquired Anton, anxiously. "Much
that is dear to you may have but little value in a jeweler's eyes."
"I shall never wear an ornament again," quietly replied the baroness.
"Take them all;" and, holding her hands before her eyes, she turned
away.
"We are torturing my mother," cried Lenore, hastily; "will you lock up
all that is on the table, and get them out of the house as soon as you
can?"
"I can not undertake the charge of these valuables," said Anton,
"without taking some measures to decrease my own responsibility. First
of all, I will in your presence make a short note of all you intrust to
me."
"What useless cruelty!" exclaimed Lenore.
"It will not take long."
Anton took out a few sheets from his pocket-book, and began to note down
the different articles.
"You shall not see it done, mother," said Lenore, drawing her mother
away, and then returning to watch Anton at his task.
"These preparations for the market are horrible," said she. "My mother's
whole life will be sold; some memory of hers is linked with every single
thing. Look, Wohlfart, the princess gave her this diamond ornament when
she married my father."
"They are magnificent brilliants," cried Anton, admiringly.
"This ring was my grandfather's, and these are presents of poor papa's.
Alas! no man can know how we love all these things. It was always a
festival to me when mamma put on her diamonds. Now we come to my
possessions. They are not worth much. Do you think this bracelet good
gold?" She held out her hand as she spoke.
"I do not know."
"It shall go with the rest," said Lenore, taking it off. "Yes, you are a
kind, good man, Wohlfart," continued she, looking trustfully into his
tearful eyes; "do not forsake us. My brother has no experience, and is
more helpless than we are. It is a frightful position for me. Before
mamma I do all I can to be composed, else I could scream and weep the
whole day through." She sank in a chair, still holding his hand. "Dear
Wohlfart, do not forsake us."
Anton bent over her, and looked with passionate emotion at the lovely
face that turned so trustfully to him in the midst of its tears.
"I will be helpful to you when I can," said he, in the fullness of his
heart. "I will be at hand whenever you need me. You have too good an
opinion of my information and my faculties; I can be of less assistance
to you than you suppose, but what I can, that I will do in any and every
possible way."
Their hands parted with a warm pressure; the affair was settled.
The baroness now returned. "Our lawyer was with me this morning," said
she; "and now I must ask for your opinion on another subject. He tells
me that there is no prospect of preserving the baron's family estate."
"At this time, when interest is high, and money difficult to get, none,"
replied Anton.
"And you, too, think that we must turn all our efforts toward preserving
the Polish property?"
"I do," was the answer.
"For that, also, money will be necessary. Perhaps I may be able through
my relatives to intrust you with a small sum, which, with the help of
that"--she pointed to the iron chest--"may suffice to cover the first
necessary expenses. I do not, however, wish to sell the jewels here, and
a journey to the residence would be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cure the
sum to which I have just alluded. The baron's lawyer has spoken most
highly of your capacity for business. It is his wish which now decides
me to make a proposal to you. Will you for the next few years, or, at
all events, until our greatest difficulties are over, devote your whole
time to our affairs? I have consulted my children, and they agree with
me in believing that in your assistance lies our only hope of rescue.
The baron, too, has come in to the plan. The question now is whether
your circumstances allow you to give your support to our unfortunate
family. We shall be grateful to you, whatever conditions you affix; and
if you can find any way of making our great obligations to you apparent
in the position you hold, pray impart it to me."
Anton stood petrified. What the baroness required of him was separation
from the firm, separation from his principal, and from Sabine! Had this
thought occurred to him before, when standing in Lenore's presence or
bending over the baron's papers? At all events, now that the words were
spoken, they shocked him. He looked at Lenore, who stood behind her
mother with hands clasped in supplication. At length he replied, "I
stand in a position which I can not leav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others.
I was not prepared for this proposal, and beg to have time allowed me
for consideration. It is a step which will decide my whole future life."
"I do not press you," said the baroness; "I only request your
consideration. Whatever your decision be, our warmest gratitude will
still be yours; if you are unable to uphold our feeble strength, I fear
that we shall find no one to do so. You will think of that," she added,
beseechingly.
Anton hurried through the street with throbbing pulse. The noble lady's
glance of entreaty, Lenore's folded hands, beckoned him out of the
gloomy counting-house into a sphere of greater liberty, into a new
future, from whose depths bright images flashed out upon his fancy. A
request had been frankly made, and he was strongly inclined to justify
the confidence that prompted it. Those ladies required an unwearied,
self-sacrificing helper to save them from utter ruin, and if he
followed his impulse he should be doing a good work--fulfilling a duty.
In this mood he entered the merchant's dwelling. Alas! all that he saw
around him seemed to stretch out a hand to detain him. As he looked at
the warehouse, the good-humored faces of the porters, the chains of the
great scales, the hieroglyphics of the worthy Pix, again he felt that
this was the place that he belonged to. Sabine's dog kissed his hand,
and ran before him to his room--his and Fink's room. Here the childish
heart of the orphan boy had found a friend, kind companions, a home, a
definite and honorable life-purpose. Looking down through his window on
all the long-familiar objects, he saw a light in Sabine's store-chamber.
How often he had sought for that light, which brightened the whole great
building, and brought a sense of comfort and cheerfulness even into his
room. He now sprang up suddenly, and said to himself, "She shall
decide."
Sabine started in amazement when Anton appeared before her. "I am
irresistibly impelled to seek you," cried he. "I have to decide upon my
future life, and I feel undetermined, and unable to trust to my own
judgment. You have always been a kind friend to me since the day of my
arrival. I am accustomed to look up to you, and to think of you in
connection with all that interests me here. Let me hear your opinion
from your own lips. The Baroness Rothsattel has to-day proposed to me
permanently to undertake the situation of confidential adviser and
manager of the baron's affairs. Shall I accept; or shall I remain here?
I know not--tell me what is right both for myself and others."
"Not I," said Sabine, drawing back and growing very pale. "I can not
venture to decide in the matter. Nor do you wish me to do so, Wohlfart,
for you have already decided."
Anton looked straight before him and was silent.
"You have thought of leaving this house, and a wish to do so has sprung
out of the thought. And I am to justify you, and approve your resolve!
This is what you require of me," continued she, bitterly. "But this,
Wohlfart, I can not do, for I am sorry that you go away from us."
She turned away from him and leaned on the back of a chair.
"Oh, be not angry with me too!" said Anton; "that I can not bear. I have
suffered much of late. Mr. Schröter has suddenly withdrawn from me the
friendly regard that I long held my life's greatest treasure. I have not
deserved his coldness. What I have been doing has not been wrong, and
it was done with his knowledge. I had been spoiled by his kindness; I
have the more deeply felt his displeasure. My only comfort has been that
you did not condemn me. And now, do not you be cold toward me, else I
shall be wretched forever. There is not a soul on earth to whom I can
turn for affectionate comprehension of my difficulties. Had I a sister,
I should seek her heart to-day. You do not know what to me, lonely as I
am, your smile, your kindly shake of the hand has been till now. Do not
turn coldly from me, I beseech you."
Sabine was silent. At length she inquired, still with averted face,
"What draws you to those strangers; is it a joyful hope, is it sympathy
alone? Give this question close consideration before you answer it to
yourself at least."
"What it is that makes it possible for me to leave this house," said
Anton, "I do not myself know. If I can give a name to my motives, it is
gratitude felt toward one. She was the first to speak kindly to the
wandering boy on his way out into the world. I have admired her in the
peaceful brightness of her former life. I have often dreamed childish
dreams about her. There was a time when a tender feeling for her filled
my whole heart, and I then believed myself forever the slave of her
image. But years bring changes, and I learned to look on men and on life
with other eyes. Then I met her again, distressed, unhappy, despairing,
and my compassion became overmastering. When I am away from her, I know
that she is nothing to me; when I am with her, I feel only the spell of
her sorrow. Once, when I had to depart out of her circle like a culprit,
she came to me, and before the whole scornful assembly she gave me her
hand and acknowledged me her friend; and now she comes and asks for my
hand to help her father. Can I refuse it? Is it wrong to feel as I do? I
know not, and no one can tell me--no one but you alone."
Sabine's head had sunk down to the back of the chair on which she bent.
She now suddenly raised it, and with tearful eyes, and a voice full of
love and sorrow, cried, "Follow the voice that calls you. Go, Wohlfart,
go."
CHAPTER XXVII.
On a cold October day, two men were seen driving through the latticed
gate of the town of Rosmin on toward the plain, which stretched out
before them monotonous and boundless. Anton sat wrapped in his fur coat,
his hat low on his forehead, and at his side was young Sturm, in an old
cavalry cloak, with his soldier's cap cocked cheerily on one side. In
front of them a farm-servant, squatted on a heap of straw, flogged on
the small horses. The wind swept the sand and straw from the
stubble-fields, the road was a broad causeway without ditches or hedges,
the horses had to wade alternately through puddles and deep sand. Yellow
sand gleamed through the scanty herbage in all directions wherever a
field-mouse had made her way to her nest or an active mole had done what
he could to diversify the unbroken plain. Wherever the ground sank,
stagnant water lodged, and there hollow willow-trees stretched their
crippled arms in the air, their boughs flapping in the wind, and their
faded leaves fluttering down into the muddy pool below. Here and there
stood a small dwarf pine, a resting-place for the crows, who, scared by
the passing carriage, flew loudly croaking over the travelers' heads.
There was no house to be seen on the road, no pedestrian, and no
conveyance of any kind.
Karl looked every now and then at his silent companion, and said at
last, pointing to the horses, "How rough their coats are, and how pretty
their gray mouse skins! I wonder how many of these beasties would go to
make up my sergeant's horse! When I took leave of my father, the old man
said, 'Perhaps I shall pay you a visit, little one, when they light the
Christmas-tree.' 'You'll never be able,' said I. 'Why not?' asked he.
'You'll never trust yourself in any post-chaise.' Then the old boy
cried, 'Oho! post-chaises are always of a stout build; I shall be sure
to trust myself in one.' But now, Mr. Anton, I see that my father never
can pay us a visit."
"Why not?"
"It is possible that he may reach Rosmin; but, as soon as he sees these
horses and this road, he will instantly turn back. 'Shall I trust
myself,' he'll say, 'in a district where sand runs between one's legs
like water, and where mice are put into harness? The ground is not firm
enough for me.'"
"The horses are not the worst things here," said Anton, absently. "Look!
these go fast enough."
"Yes," replied Karl, "but they don't go like regular horses; they
entangle their legs like two cats playing in a parsley-bed. And what
things they have for shoes--regular webbed hoofs, I declare, which no
blacksmith can ever fit."
"If we could only get on!" returned Anton; "the wind blows cold, and I
am shivering in spite of my fur."
"You have slept but little the last few nights, sir," said Karl. "The
wind blows here as if over a threshing-floor. The earth is not round
hereabouts as elsewhere, but flat as a cake. This is a complete desert;
we have been driving for more than an hour, and there is not a village
to be seen."
"A desert indeed," sighed Anton; "let us hope it may improve." They
relapsed into profound silence. At length the driver stopped near a
pool, unharnessed the horses, and led them to the water's edge, without
noticing the travelers.
"What the deuce does this mean?" cried Karl, jumping down from the
carriage.
"I am going to feed," replied the servant, sulkily, in a foreign accent.
"I am anxious to know how that will be done," said Karl. "There is not
the shadow of a bag of provender."
The horses, however, soon proved that they could live without corn; they
stretched down their shaggy heads, and began to pull the grass and weeds
at the edge of the pool, sometimes taking a draught of the dirty water.
Meanwhile the servant drew a bundle from under his seat, settled himself
under the lee of an alder-bush, and, taking his knife, cut his bread and
cheese without even glancing at the travelers.
"I say, Ignatius or Jacob," cried Karl, sharply, "how long will this
breakfast of yours last?"
"An hour," replied the man, munching away.
"And how far is it from here to the estate?"
"Six miles, or maybe more."
"You can make nothing of him," said Anton; "we must put up with the
customs of the country;" and, leaving the carriage, they went to look on
at the horses feeding.
Anton is on his way to the Polish property. He is now the baron's agent.
Anxious months have the last proved to him. The parting from his
principal and the firm had been painful in the extreme. For some time
before it, indeed, Anton had found himself alone in the midst of his
colleagues. The quiet Baumann still remained his friend, but the others
considered him a castaway. The merchant received his resignation with
icy coldness; and even in the hour of parting, his hand lay impassive as
metal in Anton's grasp. Since then, our hero had undertaken several
journeys to the capital and to creditors in the family's behalf, and now
he was on his way to set the new estate in order, accompanied by Karl,
whom he had induced to become the baron's bailiff.
Ehrenthal had, by the authority conferred on him,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from the time of the sale by auction, and hired the Polish
bailiff for the baron. There had been unfair dealings between them at
the time, and it was well known in Rosmin that the bailiff had sold off
a good deal, and been guilty of all sorts of frauds since, so that Anton
had even now no prospect of a quiet life.
"The hour is come when I may execute my commission," cried Karl, groping
in the straw under the seat. He drew out a large japanned tin case, and
carried it to Anton. "Miss Sabine gave me this in charge for you." He
then joyously opened the lid, produced the materials for an excellent
breakfast, a bottle of wine, and a silver goblet. Anton took hold of the
case.
"It has a very knowing look," said Karl. "Miss Sabine planned it
herself."
Anton examined it on all sides, and placed it carefully on a tuft of
grass; then he took up the goblet, and saw his initials engraved on it,
and underneath the words, "To thy welfare." Whereupon he forgot the
breakfast and all around him, and stood gazing at the goblet, lost in
thought.
"Do not forget the breakfast, sir," suggested Karl, respectfully.
"Sit down by me, my faithful friend; eat and drink with me. Leave off
your absurd politeness. We shall have but little, either of us, but what
we have we will share like brothers. Take the bottle if you have no
glass."
"There's nothing like leather," said Karl, taking a small leathern
drinking-cup out of his pocket. "As for 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t was
kindly meant, and I thank you; but there must be subordination, if it
were but for the sake of the others; and so, sir, be kind enough to let
me shake hands with you now, and then let things be as they were before.
Only look at the horses, Mr. Anton. My faith! the creatures devour
thistles."
Again the horses were harnessed, again they threw out their short legs
in the sand, and again the carriage rolled through the barren
district--first through an empty plain, next through a wretched
fir-wood, then past a row of low sand-hills, then over a tumble-down
bridge crossing a small stream.
"This is the property," said the driver, turning round, and pointing
with his whip to a row of dirty thatched roofs that had just come into
sight.
Anton stood up to look for the group of trees in which the Hall might be
supposed to stand. Nothing of the sort to be seen. The village was
deficient in all that adorns the home of the poorest German peasant--no
orchard, no hedged-in gardens, no lime-trees in the market-place.
"This is wretched," said he, sitting down again; "much worse than they
told us in Rosmin."
"The village looks as if under a curse," cried Karl; "no teams working
in the fields--not a cow or a sheep to be seen."
The farm-servant flogged his horses into an irregular gallop, and so
they passed through the rows of mud huts which constituted the village,
and arrived at the public house. Karl sprang from the carriage, opened
the tavern door, and called for the landlord. A Jew slowly rose from his
seat by the stove and came to the threshold. "Is the gendarme from
Rosmin come?" He is gone into the village. "Which is the way to the
farm-yard?"
The landlord, an elderly man with an intelligent countenance, described
the way in German and Polish, and remained standing at the
door--bewildered, Karl declared, by the sight of two human beings. The
carriage turned into a cross-road, planted on both sides with thick
bushes, the remains of a fallen avenue. Over holes, stones, and puddles,
it rattled on to a group of mud huts, which still had a remnant of
whitewash upon them. "The barns and stables are empty," cried Karl, "for
I see gaps in the roofs large enough to drive our carriage through."
Anton said no more; he was prepared for every thing. They drove through
a break between the stables into the farm-yard, a large irregular space,
surrounded on three sides by tumble-down buildings, and open to the
fields on the fourth. A heap of _débris_ lay there--lime and rotten
timber, the remains of a ruined barn. The yard was empty; no trace of
farm implements or human labor to be seen. "Which is the inspector's
house," inquired Anton, in dismay. The driver looked round, and at last
made up his mind that it was a small one-storied building, with straw
thatch and dirty windows.
At the noise of the wheels a man appeared on the threshold, and waited
phlegmatically till the travelers had dismounted, and were standing
close before him. He was a broad-shouldered fellow, with a bloated,
brandy-drinking face, dressed in a jacket of shaggy cloth, while behind
him peered the muzzle of an equally shaggy dog, who snarled at the
strangers. "Are you the steward of this property?"
"I am," replied the man, in broken German, without stirring from where
he was.
"And I am the agent of the new proprietor," said Anton.
"That does not concern me," growled the shaggy man, turning sharp round,
entering the house, and bolting the door within.
Anton was thoroughly roused. "Break the window in, and help me to catch
the rascal," cried he to Karl, who coolly seized a piece of wood, struck
the panes so as to make the rotten framework give way, and cleared the
opening at one leap. Anton followed him. The room was empty, so was the
next, and in it an open window--the man was gone.
"After him!" cried Karl, and dashed on in pursuit, while Anton looked
about the house and out-buildings. He soon heard the barking of a dog,
and saw Karl capture the fugitive. Hurrying to his help, he held the man
fast, while, with a kick, Karl sent the dog flying. They then contrived
to force the steward back to the house, though he kept striking out
violently all the way.
"Go to the tavern, and bring the gendarme and the landlord," cried Anton
to the driver, who, undisturbed by all that had been going on, had
meanwhile unpacked the carriage. The man accordingly drove leisurely
off, and the fugitive being got into the room, Karl found an old cloth,
and with it bound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I beg your pardon, sir,"
said he; "it is only for an hour or so, till the arrival of the Rosmin
gendarme, whom we have appointed to meet us."
Anton then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house, bu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found but the merest necessaries; no books nor papers of any kind. It
had doubtless been emptied already. A bundle projected from the
coat-pocket of the prisoner, which turned out to be receipts and legal
documents in Polish. In time, the driver returned with the landlord and
the armed policeman. The landlord stood at the door in some perplexity,
and the policeman explained in a few moments what remained to be done.
"You must make a statement to the local judge, and give the man up to
me. He shall go back in your carriage to Rosmin. You will do well to get
rid of him, for this is a wild country, and it will be safer for you to
have him at Rosmin than here, where he has friends and accomplices."
After a long search, a sheet of paper was found in a cupboard, the
statement made and submitted to the policeman, who shook his head a
little over the Polish composition, and the prisoner lifted into the
carriage, the gendarme taking his seat beside him, and saying to Anton,
"I have long expected something of the kind. You may have often occasion
to want me again." The carriage then drove away, and thus the property
came under Anton's administration. He felt as if cast on a desert
island.
His portmanteau and traveling effects were leaning against a mud wall,
and the Polish landlord was the only man who could give him and Karl any
information or advice in their forlorn condition.
Now that the steward was fairly gone, the landlord grew more
communicative, and showed himself serviceable and obliging. A long
conversation ensued, and its purport was what Anton had apprehended from
the warning given by the Commissary Walter and other Rosmin officials.
The inspector had,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done all he could in the
way of spoliation, rendered daring by a report which had found its way
from the town to the village, that the present proprietor would never be
able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estate. At last Anton said, "What that
wretched man has done away with he will have to account for; our first
care must be to preserve what is still to be found on the property. You
must be our guide to-day."
They then examined the empty buildings. Four horses and two
servants--they were gone into the wood--a few old plows, a pair of
harrows, two wagons, a britzska, a cellar full of potatoes, a few
bundles of hay, a little straw--the inventory did not take much time in
drawing up. The buildings were all out of repair, not through age, but
neglect.
"Where is the dwelling-house?" inquired Anton. The landlord led the way
out of the yard to the meadow--a broad plain, gradually sloping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brook. It had been a great pasture. The cattle had
trodden it down into holes; the snouts of greedy swine had rooted it up;
gray molehills and rank tufts of grass rose on all sides.
The landlord stretched out his hand. "There is the castle. This castle
i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he added, reverentially; "no
nobleman in the district has a stone house like that. All the gentry
here live in wood and mud buildings. Herr von Tarow, the richest of
them, has but a poor dwelling."
About three hundred yards from the last out-building rose a great brick
edifice, with a black slate roof and a thick round tower. Its gloomy
walls on this treeless pasture-land, without one trace of life around,
rose beneath the cloudy sky like a phantom fortress which some evil
spirit had evoked from the abyss--a station from which to blight all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The strangers approached it. The castle had fallen into ruins before the
builders had finished their task. The tower had stood there for ages. It
was built of unhewn stone, and had small windows and loop-holes. The
former lords of the land had looked down from its summit on the tops of
the trees, which then stretched far into the plain. They had then ruled
with a rod of iron the serfs who cultivated their land, and toiled and
died for them. Many an arrow had sped through those loop-holes at the
enemy storming below, and many a Tartar horse had been overthrown before
those massive walls. Years ago, a despot of the district had, in
expiation of former sins, begun to add to the gray tower the walls of a
holy monastery; but the monastery never got finished, and the useless
walls had already stood there long, when the late count took it into his
head to convert them into a lordly dwelling for his race, and to raise a
house unparalleled for magnificence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 front of the house was added on to both sides of the tower, which
projected in the middle. The intention had been to have a high
terrace-road up to the castle, and the principal entrance had been made
in the tower, and arched over; but the terrace never having been formed,
the stone threshold of the main door was quite inacce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ladders, and the wide opening was left. The window-spaces of
the lower floor were merely closed up with boards, while on the second
story were some window-frames of beautifully carved wood, in which large
panes had once been placed, but they had got broken. In other windows
were temporary frames of rough deal, with small panes of muddy glass let
into them. A company of jackdaws sat on the top of the tower, looking
down in amazement on the strangers, and every now and then one flew off,
screaming loudly, to contemplate the intruders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A house for crows and bats, not for human beings," said Anton. "At
least, I see no way of getting into it."
The landlord now took them round the building. Behind, where the two
wings made a sort of horse-shoe, there were low entrances to the cellars
and offices; beneath which, again, were stables, great arched kitchens,
and small cells for the serfs. A wooden staircase led to the upper
story. The door turned creaking on its hinges, and a narrow passage took
them through a side wing to the front part of the house. There all was
at least magnificently planned. The circular entrance-hall--an arched
room of the old tower--was painted in mosaic, and through the great
doorway-opening was seen a wide expans
small disturbance made by the return of Anton had gradually settled
down. Those first-class treasures of Sabine's had made way for other
specimens of damask, still of a superior kind, it is true, but which
came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e elderly cousin's comprehension. She had
been quite right in prophesying that Anton would never remark those
signs of exuberant gratitude or their withdrawal. However, one change
had been permanently made--the greatest, the best of all changes--the
clerk retained a privileged place in the heart of the young mistress of
the firm, and his tall figure often appeared as one of the circle that
Sabine's fancy loved to gather round her when at her work-table or in
her treasure-chamber.
To-day she was walking restlessly up and down before dinner. The cousin,
who heard every thing, had just told her that a maid from Ehrenthal's
had run into the office to announce Bernhard's death to his friend. "How
will he bear it?" thought she. And the name of Ehrenthal forced her
thoughts back to the past, to one now far away, and to that painful hour
when the struggle going on in her own mind had been suddenly brought to
a close by a letter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parted. And Anton had known
of that conquered feeling of hers. How considerate he had always been,
how chivalrous, how helpful! She wondered if he had any idea of the
completeness of her triumph over a girlish illusion. She shook her head.
"No, he has not. It was here, at this very table, that an accident first
betrayed me to him. That past time still rises like a cloud between us.
Whenever I sit near Wohlfart of an evening, I am conscious of another's
shadow at my side; and when he speaks to me, his tone, his manner always
seem to say, 'You are not alone; he is with you.'" Sabine started, and
lovingly passed her hand over the beautiful flowers on the table before
her, as if to dispel a painful thought. She could not tell him that she
was free from that long-felt sorrow. Now, however, when he had lost a
friend whom he so much loved, she must show him that there were other
hearts that clung to him still. And again she walked up and down, trying
to devise a way of speaking to him alone.
Dinner was announced. Anton came with the rest, and took his place at
once. There was no opportunity of exchanging a word during the meal, but
he often met her sad and sympathizing eye. "He eats nothing at all
to-day," whispered her cousin; "not even any of the roast," she added,
reproachfully. Sabine was much perturbed. Mr. Jordan had already risen;
Anton would leave the room with the rest, and she should not see him
again the whole day through. So she called out, "The great Calla is
fully blown now. You were admiring the buds the other day; will you
remain a moment; I should like to show it you?" Anton bowed and staid
behind. A few more awkward moments, then her brother rose too; and,
hurrying to Anton, she took him to the room where the flowers were.
"You have had sorrowful tidings to-day," she began.
"The tidings themselves did not surprise me," replied Anton. "The doctor
gave no hope. But I lose much in him."
"I never saw him," said Sabine; "but I know from you that his life was
lonely--poor in affection and in enjoyment."
She moved an arm-chair toward Anton, and led him on to talk about his
friend. She listened to every word with warm sympathy, and well knew
what to ask and how to comfort. It was a relief to Anton to speak of the
departed one, to describe his quiet way of life, his erudition, his
poetical enthusiasm. After a pause, Sabine looked up frankly into his
face, and asked, "Have you any tidings of Herr von Fink?"
It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his departure that she had ever breathed his
name. Anton felt how touching her confidence was, given in this hour of
his sadness. In his emotion, he seized her hand, which she was slow in
withdrawing.
"He is not happy in his new life," he gravely replied. "There was a
savage humor in his last letter, from which I gather, even more than
from his actual words, that the business into which his uncle's death
has thrown him does not suit him."
"It is unworthy," cried Sabine.
"At all events, it is not what would be recognized as honorable in this
house," replied Anton. "Fink is upright, and has lived too long with
your brother to take pleasure in the wild speculations so common on the
other side the Atlantic. His partners and colleagues are for the most
part men without a conscience, and his feelings revolt against their
companionship."
"And can Herr von Fink tolerate such relations as these for a day?"
"It is a remarkable thing that he whose own will was ever so arbitrarily
exercised, should now be obliged against that will to obey a pressure
from without, and every where to work with his hands tied. The
organization of such speculations in America is so complicated that one
shareholder can do little to alter it; and, now that Fink has attained
what used to be the goal of his wishes--a large capital, and the
management of immense districts--his condition appears more uncertain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He was always in danger of thinking slightingly
of others, now I am distressed at the bitter contempt he expresses for
his own life. His last letter paints an intolerable state of things, and
seems to point to some decisive resolve."
"There is only one resolve for him," cried Sabine. "May I ask what you
said to him in reply?"
"I entreated him instantly, come what would, to free himself from the
business in which he was entangled. I said that his own strong will
might find a way of extrication, even if that which I pointed out proved
impracticable. Then I begged of him either to carry out his old plan of
becoming a landed proprietor in America, or to return to us."
"I knew that you would write thus," said Sabine, drawing a long breath.
"Yes, Wohlfart, he shall return," said she, gently, "but he shall not
return to us."
Anton was silent.
"And do you think that Herr von Fink will follow your advice?"
"I do not know. My advice was not very American."
"But it was worthy of you," cried Sabine, with proud delight.
"An officer wishes to speak to Mr. Wohlfart," said a servant at the
door.
Anton sprang up. Sabine went to her flowers and bent mournfully over
them. The shadows of others hovered still between her friend and her.
The few words spoken by the servant filled Anton with a vague terror. He
hurried into the ante-room: there stood Eugene von Rothsattel. Anton was
gladly rushing forward to greet him, but the young soldier's face of
agony made him start back. He whispered, "My mother wishes to speak to
you; something dreadful has occurred." Anton caught up his hat, ran into
the office, hurriedly asked Baumann to excuse him to the principal, and
then accompanied the lieutenant to the baron's house.
On the way, Eugene, who had lost all self-command, said unconnectedly to
Anton, "My father last night accidentally wounded himself by a
pistol-shot--a messenger was sent to summon me--when I came, I found my
mother in a swoon--my sister and I do not know what to do--Lenore
implored my mother on her knees to send for you--you are the only one in
whom w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our distress--I understand nothing about
business, but my father's affairs must be in a dreadful state--my mother
is beside herself--the whole house is in the greatest disorder."
From what Eugene said and what he did not say; from his broken sentences
and his look of agony, Anton guessed at the horrors of the previous
evening. In the boudoir of the baroness he found Lenore, weeping and
exhausted.
"Dear Wohlfart!" cried she, taking his hand and beginning again to sob,
while her head sank powerless on his shoulder.
Meanwhile Eugene walked up and down, wringing his hands, and at length
throwing himself on the sofa, he gave himself up to silent tears.
"It is horrible, Mr. Wohlfart," said Lenore, lifting up her head. "No
one may approach my father--Eugene may not, nor I--only my mother and
old John are with him; and early this morning the merchant Ehrenthal was
here, insisting that he must see my father. He screamed at my mother,
and called my father a deceiver, till she fainted away. When I rushed
into the room, the dreadful man went off threatening her with his
clenched fist."
Anton led Lenore to a chair and waited till she had told him all.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comforting in this case, and his own heart was
wrung to the utmost by the misery he witnessed.
"Call my mother, Eugene," said Lenore, at length.
Her brother left the room.
"Do not forsake us," implored Lenore, clasping her hands; "we are at the
last gasp; even your help can not save us."
"He is dead who might perhaps have done so," mournfully replied Anton.
"Whether I can be of any use I know not, but you can not doubt my
willingness to be so."
"No," cried Lenore. "And Eugene, too, thought of you at once."
The baroness now entered. She walked wearily; but, steadying herself by
a chair, she saluted Anton with dignity. "In our position," said she,
"we need a friend who knows more of business than we three do.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prevents the baron--possibly for a long time to
come--from managing his own affairs, and, little as I understand them, I
can see that our interests require prompt measures. My children have
mentioned you to me, but I fear I am unreasonable in asking you to
devote your time to our service."
She sat down, beckoned Anton to take a chair, and said to her children,
"Leave us; I shall be better able to tell Mr. Wohlfart the little that I
know when I do not see your grief."
When they were alone, she motioned him nearer and tried to speak, but
her lips quivered, and she hid her face in her handkerchief.
"Before I can consent, gracious lady," said he, "to your reposing in me
such confidence as this, I must first inquire whether the baron has no
relative or intimate friend to whom you could with less pain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I pray you to remember that my own knowledge of business
is but small, and my position not one to constitute me a proper
counselor to the baron."
"I know no one," said the baroness, hopelessly. "It is less painful to
me to tell you what I can not conceal, than to one of our own circle.
Consider yourself a physician sent for to visit a patient. The baron has
this morning told me some particulars of his present circumstances." And
then she proceeded to relate what she had gathered as to the nature of
his embarrassments, the danger in which the family property was placed,
and the capital needed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Polish estate.
"My husband," continued she, "has given me the key of his desk, and he
wishes Eugene, with the help of a man of business, to go over his
papers. I now request of you to make this examination together with my
son. When you need explanations, I will try to obtain them from the
baron. The question is now, whether you are inclined to undertake this
trouble for us, who are only strangers."
"I am most willing to do so," earnestly replied Anton; "and I hope that
the kindness of my principal will allow me the time needful for the
purpose, if you do not consider it more advisable to depute the baron's
experienced legal adviser to the task."
"There will be an opportunity of asking that gentleman's advice later,"
said the baroness.
Anton rose. "When do you wish to begin?"
"Immediately. I fear there is not a day to lose. I shall do all I can to
help you look the papers over." She led Anton into the next room, called
in Eugene, and unlocked the baron's desk. As she opened it she lost her
self-command for a moment, and moving to the window, the quivering of
the curtains betrayed the anguish that shook her fragile frame.
The mournful task began. Hour after hour passed. Eugene was in no
condition to peruse any thing, but his mother reached letters and
documents to Anton, and, though often obliged to desist a while, she
bravely returned to the task. Anton placed the papers in order, and
sought, by glancing over each, to arrive at least at a superficial view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It was evening, when the old servant opened the door in dismay, and
called out, "He is there again." The baroness could not repress a slight
scream, and made a gesture of aversion.
"I have told him that no one is at home, but he will not be dismissed;
he makes such a noise on the steps. I can not get rid of him."
"It will kill me if I hear his voice again," murmured the baroness.
"If the man be Ehrenthal," said Anton, rising, "I will try to get him
away. We have now done what was most necessary; have the goodness to
lock up these papers, and to allow me to return to-morrow." The baroness
silently assented, and sank back in her chair. Anton hurried off to the
ante-room, whence he could hear Ehrenthal's loudly-raised voi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usurer shocked him. His hat pushed half off his
head, his pale face swelled as if by drinking, his glazed eyes red with
tears, Ehrenthal stood before him, calling in broken sentences for the
baron, wailing and cursing alternately. "He must come! he must come at
once!" cried he; "the wicked man! A nobleman, indeed! he is a vagabond,
after whom I will send the police. Where is my money? Where is my
security? I want my mortgage from this man who is not at home."
Anton went straight up to him, and asked, "Do you know me, Mr.
Ehrenthal?" Ehrenthal turned his glazed eyes upon him, and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 friend of his dead son.
"He loved you!" he cried, in a lamentable voice. "He spoke to you more
than to his father. You were the only friend that he had on earth. Have
you heard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house of Ehrenthal?" continued he, in
a whisper. "Just as they stole the papers he died. He died with a hand
like this," and clenching his fist he struck his forehead. "Oh my son!
my son! why didst not thou forgive thy father!"
"We will go to your son," said Anton, taking the arm of the old man, who
unresistingly allowed himself to be led back to his own house.
From thence Anton hurried to Councilor Horn, with whom he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It was late before he returned home. In the midst of his anxiety about
those whose prosperity had filled his imagination years before,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in their adversity, reposed in him, dilated his
breast with a feeling of pride. He burned with desire to help them, and
hoped that his zealous devotion might yet find some way of rescue. As
yet he saw none. Looking up at the great building before him, so firm
and secure, in the moonlight, a thought flashed into his mind. If any
man could help them, it was his principal. His keen eye would be able to
unravel all the dark secrets in which the baron was entangled, and his
iron strength of will would crush the villains who held the unfortunate
nobleman in their power. And then he had a noble nature; he always
decided on the right, without an effort or a struggle. Anton looked at
the first floor. The whole house-front was dark, but in a corner room a
light still burned. It was the private office of his chief.
With sudden resolve, Anton begged the servant to take him to Mr.
Schröter, who looked with amazement at the unexpected visitor, and asked
what brought him, and whether any thing had happened.
"I implore your counsel--I implore your help," cried Anton.
"For yourself or for others?" inquired the merchant.
"For a family with whom I have accidentally become connected. They are
lost if a strong hand does not ward off the impending catastrophe."
Anton then rapidly related the occurrences of the afternoon, and,
seizing his principal's hand in his emotion, cried, "Have pity upon the
unhappy ladies, and help them."
"Help them!" replied the merchant; "how can I? Have you been
commissioned to apply to me, or are you only following the impulse of
your own feelings?"
"I am not commissioned; it is only the interest that I take in the
baron's fate which leads me to you."
"And what right have you to inform me of facts communicated in strict
confidence to yourself by the baron's lady?" asked the merchant, dryly.
"I am committing no indiscretion in telling you what will, in a few
days, be no secret, even to strangers."
"You are unusually excited, otherwise you would not forget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hatever, does a man of business venture to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without the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Of course, I shall make no wrong use of what you have said, but it was
by no means business-like, Wohlfart, to be so open toward me."
Anton was silent, feeling, indeed, that his principal was right, but yet
it seemed hard to be blamed for reposing confidence at such a time as
this. The merchant walked silently up and down; at length, stopping
before Anton, he said, "I do not now inquire how you come to take so
warm an interest in this family. I fear it is an acquaintance you owe to
Fink."
"You shall hear all," said Anton.
"Not at present. I will now content myself with repeating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interfere in these affairs without being specially
applied to by the parties themselves. I may add that I by no means wish
for such an application, and do not disguise from you that, were it
made, I should probably decline to do any thing for the Baron
Rothsattel."
Anton's feelings were roused to the utmost. "The question is the rescue
of an honorable man, and of lovely and amiable women from the toils of
rogues and impostors. To me, this seems the duty of every one; I, at
least, consider it a sacred obligation which I dare not shrink from. But
without your support I can do nothing."
"And how do you think this embarrassed man can be helped?" inquired the
merchant, seating himself.
With somewhat more composure, Anton repli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an experienced man of business making himself master of the case. There
must be some way of circumventing these villains. Your penetration would
discover it."
"Any attorney would be far more likely to do so, and the baron might
readily engage the services of experienced and upright legal advisers.
If his enemies have done any thing illegal, the quick eye of a lawyer is
the most likely to detect it."
"Alas! the baron's own lawyer gives but little hope," replied Anton.
"Then, my dear Wohlfart, no other is likely to do much good. Show me an
embarrassed man who has strength to grasp an offered hand, and bid me
help him, and for the sake of all I owe you, I will not refuse to do so.
I think you are convinced of this."
"I am," said Anton, dejectedly.
"From all I hear, however," the merchant went on,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the baron. From what I gather from general report, as well as from
you, his embarrassments arise from his having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usurers, which proves him deficient in what alone ennobles the life of
any man--good sense, and the power of steady exertion."
Anton could only sigh his assent.
"To help such a man," inexorably continued the merchant, "is a futile
attempt, against which reason may well protest. We are not to despair of
any, but want of strength is the most hopeless case of all. Our power of
laboring for others being limited, it becomes our duty to inquire,
before we devote our time to the weak, whether we are not thus
diminishing our chances of helping better men."
Anton interrupted him. "Does he not deserve every allowance to be made
for him? He was brought up to exact much; he has not learned, as we
have, to make his way by his own labor."
The merchant laid his hand on the young man's shoulder. "The very
reason. Believe me, a large number of these landed gentry, who pay the
penalty of their old family memories, are beyond help. I am the last to
deny that many worthy and admirable men belong to this class. Indeed,
wherever remarkable talent or nobility of character shoots up among
them, no doubt their position offers peculiar scope for its development,
but for average men it is not a favorable one. He who considers it his
hereditary privilege to enjoy life, and who assumes a distinguished
position in virtue of his family, will very often fail to put forth his
whole strength in order to deserve that position. Accordingly, numbers
of our oldest families are declining, and their fall will be no loss to
the state. Their family associations make them haughty without any
right to be so--limit their perceptions and confuse their judgment."
"Even if all this be true," cried Anton, "it does not absolve us from
helping individuals of the class who have excited our sympathy."
"No," said the principal, "if it be excited. But it does not glow so
rapidly in advancing years as in youth. The baron has endeavored to
isolate his property from the current of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leave it forever to his family. Forever! You, as a merchant, know how to
estimate the attempt. True, every rational man must allow it to be
desirable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same soil should be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We all prize what our forefathers have possessed before
us, and Sabine would unlock every room in this house with pride, because
her great-great-grandmother turned the same keys before her. It is
therefore natural that the landed proprietor should desire to preserve
those familiar scenes, which are the source of his own prosperity, to
those nearest and dearest to him. But there must be means to this end,
and these means are the making his own existence available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increase of his patrimony. Where energy dies in families
or individuals, then it is well that their means die too, that their
money should circulate through other hands, and their plowshare pass to
those who can guide it better. A family that has become effete through
luxury ought to sink down into common life, to make room for the
uprising of fresh energies and faculties. Every one who seeks, at the
cost of free activity for others, to preserve permanent possessions and
privileges for himself or his family, I must look upon as an enemy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social state. And if such a man ruin
himself in his endeavors, I should feel no malicious pleasure in his
downfall, but I should say that he is rightly served, because he has
sinned against a fundamental law of our social being; consequently, I
should consider it doubly wrong to support this man, because I could but
fear that I should thus be supporting an unsound condition of the body
politic."
Anton looked down mournfully. He had expected sympathy and warm
concurrence, and he met with disaffection and coldness that he despaired
of conquering. "I can not gainsay you," he at length replied; "but in
this case I can not feel as you do. I have been witness to the
unspeakable distress in the baron's family, and my whole soul is full
of sadness and sympathy, and of the wish to do something for those who
have opened their heart to me. After what you have said, I dare no
longer ask you to trouble yourself with their affairs, but I have
promised the baroness to assist her as far as my small powers permit,
and your kindness allows. I implore you to grant me permission to do
this. I shall endeavor to be regular in my attendance at the office, but
if during the next few weeks I am occasionally absent, I must ask you to
excuse me."
Once more the merchant walked up and down the room, and then, looking at
Anton's excited face, with deep seriousness and something of regret, he
replied, "Remember, Wohlfart, that every occupation which excites the
mind soon obtains a hold over a man, which may retard as well as advance
his success in life. It is thi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 to agree
to your wishes."
"I know it," said Anton, in a low voice; "but I have now no choice
left."
"Well, then, do what you must," said the merchant, gloomily; "I will lay
no hinderance in your way; and I hope that after a few weeks you will be
able to consider the whole circumstances more calmly." Anton left the
room, and the merchant stood looking long with frowning brow at the
place his clerk had occupied.
Nor was Anton in a more congenial mood. "So cold, so inexorable!"
exclaimed he, as he reached his own room. He began to suspect that his
principal was more selfish and less kindly than he had hitherto
supposed. Many an expression of Fink's recurred to his mind, as well as
that evening when young Rothsattel, in his boyish conceit, had spoken
impertinently to the merchant. "Is it possible," thought he, "that that
rude speech should be unforgotten?" And his chief's keen, deep-furrowed
face lost inexpressibly by contrast with the fair forms of the noble
ladies. "I am not wrong," he cried to himself; "let him say what he
will, my views are more just than his, and henceforth my destiny shall
be to choose for myself the way in which I shall walk." He sat long in
the darkness, and his thoughts were gloomy as it; then he went to the
window to look down into the dark court below. A great white blossom
rose before him like a phantom. Striking a light, he saw that it was the
beautiful Calla out of Sabine's room. It hung down mournfully on its
broken stem. Sabine had had it placed there. This little circumstance
struck him as a mournful omen.
Meanwhile Sabine, taper in hand, entered her brother's room.
"Good-night, Traugott," nodded she. "Wohlfart has been with you this
evening; how long he staid!"
"He will leave us," replied the merchant, gloomily.
Sabine started and dropped her taper on the table. "For God's sake, what
has happened? Has Wohlfart said that he was going away?"
"I do not yet know it, but I see it coming step by step; and I can not,
and still less can you, do any thing to retain him. When he stood before
me here with glowing cheeks and trembling voice, pleading for a ruined
man, I found out what it was that lured him away."
"I do not understand you," said Sabine, looking full at her brother.
"He chooses to become the confidential friend of a decayed noble. A pair
of bright eyes draws him away from us: it seems to him a worthy object
of ambition to become Rothsattel's man of business. This intimacy with
nobility is the legacy bequeathed to him by Fink."
"And you have refused to help him?" inquired Sabine, in a low voice.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said the merchant, harshly; and he
turned to his writing-table.
Sabine slowly withdrew. The taper trembled in her hand as she passed
through the long suite of rooms listening to her own footfall, and
shuddering as the feeling came over her that an invisible companion
glided by her side. This was the revenge of that other. The shadow that
once fell on her innocent life now drove her friend away from their
circle. Anton's affections clung to another. She had but been in his
eyes a mere stranger, who had once loved and languished for one now far
away, and who now, in widow's weeds, looked back regretfully to the
feelings of her youth.
The few next weeks were spent by Anton in over-hard work. He had great
difficulty in keeping up his counting-house duties, while he spent every
spare hour in conference with the baroness and the lawyer.
In the mean time, the misfortunes of the baron ran their course. He had
not been able to pay the interest of the sums with which his estate was
burdened. When last they were due, a whole series of claims was brought
against him, and the estate fell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district authorities. Complicated lawsuits arose. Ehrenthal complained
loudly, claiming the first mortgage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nay, he
was inclined to advance claims on the last mortgage offered by the baron
in the recent fatal hour. Löbel Pinkus also appeared as claimant of the
first mortgage, and asserted that he had paid the whole sum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Ehrenthal had no proof to bring forward, and had been
for some weeks past quite unable to manage his own affairs, while
Pinkus, on the contrary, fought with every weapon a hardened sinner can
devise or employ, and the deeds which the baron had executed at Veitel's
suggestion proved to be so capital a master-stroke of the cunning
advocate, that the baron's man of business had, from the first, little
hope of the case. We may here observe that Pinkus did eventually win it,
and that the mortgage was made over to him.
Anton was now gradually gaining some insight into the baron's
circumstances. But the double sale of the first mortgage was still kept
a secret by the latter, even from his wife. He declared Ehrenthal's
claim unfounded, and even expressed a suspicion that he had himself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robbery in his office. Indeed, he really
believed this. Then the name of Itzig was never broached, and the
suspicion against Ehrenthal, which the baron's lawyer shared, prevented
Anton seeking any explanation from him.
Meanwhile, an estrangement had sprung up between our hero and his
principal, which the whole counting-house remarked with surprise. The
merchant scowled at Anton's vacant seat when the latter chanced to be
absent during office-hours, or looked coldly at his clerk's face, made
pale as it was with excitement of mind and night-work. He took no notice
of his new occupation, and never seemed to remark him. Even to his
sister he maintained a stiff-necked silence; nor could all her attempts
lead him to speak of Anton, who, on his side, felt his heart revolt
against this coldness. After his return, to be treated like a child of
the house, praised, promoted, petted, and now to be treated like a mere
hireling, who is not worth the bread thrown to him; to be a toy of an
incomprehensible caprice--this, at least, he had not deserved; so he
became reserved toward the whole family, and sat silent at his desk; but
he fel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now and the then so keenly, that often,
when alone, he would spring up and stamp on the ground in the bitter
indignation of his heart.
One comfort remained. Sabine was not estranged. True, he saw little of
her, and at dinner she seemed to avoid speaking to him, but he knew that
she was on his side.
A few days after his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the merchant, she came down
stairs as he stood in the hall, and had to pass him by so closely that
her dress touched him. He had retreated, and made a formal bow, but she
looked at him imploringly, and whispered, "You must not be estranged
from me." It was an affair of a moment, but the faces of both were
radiant with a happy understanding.
The time had now arrived when Mr. Jordan was to quit the firm. The
principal again called Anton into his little office, and without any
severity, but also without a trace of his former cordiality, began: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o you my intention of appointing you Jordan's
successor; but,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your time has been more taken
up with other business than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such a post, I
therefore ask you whether you are now at liberty to undertake Jordan's
duties?"
"I am not," replied Anton.
"Can you name any--not very distant--time when you will be free from
your present occupation? In that case I will endeavor to find a
substitute until then."
Anton sorrowfully replied, "I can not at present say when I shall again
be master of my whole time; and, besides, I feel that, even as it is, I
tax your indulgence by many irregularities. Therefore, Mr. Schröter, I
beg that you will fill up this post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me."
The merchant's brow grew furrowed and dark, and he silently bowed
assent. Anton felt as he closed the door that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m was now complete, and, resuming his place, he leaned his throbbing
head on his hand. A moment later Baumann was summoned to the principal,
and Jordan's situation conferred upon him. On returning to the office,
he went up to Anton and whispered, "I refused at first, but Mr. Schröter
insisted. I am doing you an injustice." And that evening Mr. Baumann, in
his own room, read in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the chapters treating of
the unjust Saul (the principal), and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Jonathan
and the persecuted David, and strengthened his heart thereby.
The next day Anton was summoned to the baroness. Lenore and her mother
sat before a large table covered with jewel-boxes and toilette elegances
of every description, while a heavy iron chest stood at their feet. The
curtains were drawn, and the subdued light shone softly into the richly
furnished room. On the carpet glowed wreaths of unfading flowers, and
the clock ticked cheerfully in its alabaster case. Under the shade of
flowering plants sat the two love-birds in their silvered cage, hopping
from perch to perch, screaming ceaselessly, or sitting up quietly close
to each other. The whole room was beauty and perfume. "For how long?"
thought Anton. The baroness rose. "We are already obliged to trouble you
again," said she; "we are engaged in a very painful occupation." On the
table were all manner of ornaments, gold chains, brilliants, rings,
necklaces, gathered into a heap.
"We have been looking out all that we can dispense with," said the
baroness, "and now pray you to undertake to sell these things for us. I
have been told that some of them are of value, and as we are now in much
need of money, we turn here for help."
Anton looked in perplexity at the glittering heap.
"Tell us, Wohlfart," cried Lenore, anxiously, "is this necessary? can it
be of any use? Mamma has insisted upon setting apart for sale all our
ornaments, and whatever plate is not in daily use. What I can give is
not worth talking of, but my mother's jewels are costly; many of them
were presents made to her in youth, which she shall not part with unless
you say that it is necessary."
"I fear," said Anton, gravely, "that it will prove so."
"Take them," said the baroness to Anton; "I shall be calmer when I know
that we have at least done what we could."
"But do you wish to part with all?" inquired Anton, anxiously. "Much
that is dear to you may have but little value in a jeweler's eyes."
"I shall never wear an ornament again," quietly replied the baroness.
"Take them all;" and, holding her hands before her eyes, she turned
away.
"We are torturing my mother," cried Lenore, hastily; "will you lock up
all that is on the table, and get them out of the house as soon as you
can?"
"I can not undertake the charge of these valuables," said Anton,
"without taking some measures to decrease my own responsibility. First
of all, I will in your presence make a short note of all you intrust to
me."
"What useless cruelty!" exclaimed Lenore.
"It will not take long."
Anton took out a few sheets from his pocket-book, and began to note down
the different articles.
"You shall not see it done, mother," said Lenore, drawing her mother
away, and then returning to watch Anton at his task.
"These preparations for the market are horrible," said she. "My mother's
whole life will be sold; some memory of hers is linked with every single
thing. Look, Wohlfart, the princess gave her this diamond ornament when
she married my father."
"They are magnificent brilliants," cried Anton, admiringly.
"This ring was my grandfather's, and these are presents of poor papa's.
Alas! no man can know how we love all these things. It was always a
festival to me when mamma put on her diamonds. Now we come to my
possessions. They are not worth much. Do you think this bracelet good
gold?" She held out her hand as she spoke.
"I do not know."
"It shall go with the rest," said Lenore, taking it off. "Yes, you are a
kind, good man, Wohlfart," continued she, looking trustfully into his
tearful eyes; "do not forsake us. My brother has no experience, and is
more helpless than we are. It is a frightful position for me. Before
mamma I do all I can to be composed, else I could scream and weep the
whole day through." She sank in a chair, still holding his hand. "Dear
Wohlfart, do not forsake us."
Anton bent over her, and looked with passionate emotion at the lovely
face that turned so trustfully to him in the midst of its tears.
"I will be helpful to you when I can," said he, in the fullness of his
heart. "I will be at hand whenever you need me. You have too good an
opinion of my information and my faculties; I can be of less assistance
to you than you suppose, but what I can, that I will do in any and every
possible way."
Their hands parted with a warm pressure; the affair was settled.
The baroness now returned. "Our lawyer was with me this morning," said
she; "and now I must ask for your opinion on another subject. He tells
me that there is no prospect of preserving the baron's family estate."
"At this time, when interest is high, and money difficult to get, none,"
replied Anton.
"And you, too, think that we must turn all our efforts toward preserving
the Polish property?"
"I do," was the answer.
"For that, also, money will be necessary. Perhaps I may be able through
my relatives to intrust you with a small sum, which, with the help of
that"--she pointed to the iron chest--"may suffice to cover the first
necessary expenses. I do not, however, wish to sell the jewels here, and
a journey to the residence would be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cure the
sum to which I have just alluded. The baron's lawyer has spoken most
highly of your capacity for business. It is his wish which now decides
me to make a proposal to you. Will you for the next few years, or, at
all events, until our greatest difficulties are over, devote your whole
time to our affairs? I have consulted my children, and they agree with
me in believing that in your assistance lies our only hope of rescue.
The baron, too, has come in to the plan. The question now is whether
your circumstances allow you to give your support to our unfortunate
family. We shall be grateful to you, whatever conditions you affix; and
if you can find any way of making our great obligations to you apparent
in the position you hold, pray impart it to me."
Anton stood petrified. What the baroness required of him was separation
from the firm, separation from his principal, and from Sabine! Had this
thought occurred to him before, when standing in Lenore's presence or
bending over the baron's papers? At all events, now that the words were
spoken, they shocked him. He looked at Lenore, who stood behind her
mother with hands clasped in supplication. At length he replied, "I
stand in a position which I can not leav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others.
I was not prepared for this proposal, and beg to have time allowed me
for consideration. It is a step which will decide my whole future life."
"I do not press you," said the baroness; "I only request your
consideration. Whatever your decision be, our warmest gratitude will
still be yours; if you are unable to uphold our feeble strength, I fear
that we shall find no one to do so. You will think of that," she added,
beseechingly.
Anton hurried through the street with throbbing pulse. The noble lady's
glance of entreaty, Lenore's folded hands, beckoned him out of the
gloomy counting-house into a sphere of greater liberty, into a new
future, from whose depths bright images flashed out upon his fancy. A
request had been frankly made, and he was strongly inclined to justify
the confidence that prompted it. Those ladies required an unwearied,
self-sacrificing helper to save them from utter ruin, and if he
followed his impulse he should be doing a good work--fulfilling a duty.
In this mood he entered the merchant's dwelling. Alas! all that he saw
around him seemed to stretch out a hand to detain him. As he looked at
the warehouse, the good-humored faces of the porters, the chains of the
great scales, the hieroglyphics of the worthy Pix, again he felt that
this was the place that he belonged to. Sabine's dog kissed his hand,
and ran before him to his room--his and Fink's room. Here the childish
heart of the orphan boy had found a friend, kind companions, a home, a
definite and honorable life-purpose. Looking down through his window on
all the long-familiar objects, he saw a light in Sabine's store-chamber.
How often he had sought for that light, which brightened the whole great
building, and brought a sense of comfort and cheerfulness even into his
room. He now sprang up suddenly, and said to himself, "She shall
decide."
Sabine started in amazement when Anton appeared before her. "I am
irresistibly impelled to seek you," cried he. "I have to decide upon my
future life, and I feel undetermined, and unable to trust to my own
judgment. You have always been a kind friend to me since the day of my
arrival. I am accustomed to look up to you, and to think of you in
connection with all that interests me here. Let me hear your opinion
from your own lips. The Baroness Rothsattel has to-day proposed to me
permanently to undertake the situation of confidential adviser and
manager of the baron's affairs. Shall I accept; or shall I remain here?
I know not--tell me what is right both for myself and others."
"Not I," said Sabine, drawing back and growing very pale. "I can not
venture to decide in the matter. Nor do you wish me to do so, Wohlfart,
for you have already decided."
Anton looked straight before him and was silent.
"You have thought of leaving this house, and a wish to do so has sprung
out of the thought. And I am to justify you, and approve your resolve!
This is what you require of me," continued she, bitterly. "But this,
Wohlfart, I can not do, for I am sorry that you go away from us."
She turned away from him and leaned on the back of a chair.
"Oh, be not angry with me too!" said Anton; "that I can not bear. I have
suffered much of late. Mr. Schröter has suddenly withdrawn from me the
friendly regard that I long held my life's greatest treasure. I have not
deserved his coldness. What I have been doing has not been wrong, and
it was done with his knowledge. I had been spoiled by his kindness; I
have the more deeply felt his displeasure. My only comfort has been that
you did not condemn me. And now, do not you be cold toward me, else I
shall be wretched forever. There is not a soul on earth to whom I can
turn for affectionate comprehension of my difficulties. Had I a sister,
I should seek her heart to-day. You do not know what to me, lonely as I
am, your smile, your kindly shake of the hand has been till now. Do not
turn coldly from me, I beseech you."
Sabine was silent. At length she inquired, still with averted face,
"What draws you to those strangers; is it a joyful hope, is it sympathy
alone? Give this question close consideration before you answer it to
yourself at least."
"What it is that makes it possible for me to leave this house," said
Anton, "I do not myself know. If I can give a name to my motives, it is
gratitude felt toward one. She was the first to speak kindly to the
wandering boy on his way out into the world. I have admired her in the
peaceful brightness of her former life. I have often dreamed childish
dreams about her. There was a time when a tender feeling for her filled
my whole heart, and I then believed myself forever the slave of her
image. But years bring changes, and I learned to look on men and on life
with other eyes. Then I met her again, distressed, unhappy, despairing,
and my compassion became overmastering. When I am away from her, I know
that she is nothing to me; when I am with her, I feel only the spell of
her sorrow. Once, when I had to depart out of her circle like a culprit,
she came to me, and before the whole scornful assembly she gave me her
hand and acknowledged me her friend; and now she comes and asks for my
hand to help her father. Can I refuse it? Is it wrong to feel as I do? I
know not, and no one can tell me--no one but you alone."
Sabine's head had sunk down to the back of the chair on which she bent.
She now suddenly raised it, and with tearful eyes, and a voice full of
love and sorrow, cried, "Follow the voice that calls you. Go, Wohlfart,
go."
CHAPTER XXVII.
On a cold October day, two men were seen driving through the latticed
gate of the town of Rosmin on toward the plain, which stretched out
before them monotonous and boundless. Anton sat wrapped in his fur coat,
his hat low on his forehead, and at his side was young Sturm, in an old
cavalry cloak, with his soldier's cap cocked cheerily on one side. In
front of them a farm-servant, squatted on a heap of straw, flogged on
the small horses. The wind swept the sand and straw from the
stubble-fields, the road was a broad causeway without ditches or hedges,
the horses had to wade alternately through puddles and deep sand. Yellow
sand gleamed through the scanty herbage in all directions wherever a
field-mouse had made her way to her nest or an active mole had done what
he could to diversify the unbroken plain. Wherever the ground sank,
stagnant water lodged, and there hollow willow-trees stretched their
crippled arms in the air, their boughs flapping in the wind, and their
faded leaves fluttering down into the muddy pool below. Here and there
stood a small dwarf pine, a resting-place for the crows, who, scared by
the passing carriage, flew loudly croaking over the travelers' heads.
There was no house to be seen on the road, no pedestrian, and no
conveyance of any kind.
Karl looked every now and then at his silent companion, and said at
last, pointing to the horses, "How rough their coats are, and how pretty
their gray mouse skins! I wonder how many of these beasties would go to
make up my sergeant's horse! When I took leave of my father, the old man
said, 'Perhaps I shall pay you a visit, little one, when they light the
Christmas-tree.' 'You'll never be able,' said I. 'Why not?' asked he.
'You'll never trust yourself in any post-chaise.' Then the old boy
cried, 'Oho! post-chaises are always of a stout build; I shall be sure
to trust myself in one.' But now, Mr. Anton, I see that my father never
can pay us a visit."
"Why not?"
"It is possible that he may reach Rosmin; but, as soon as he sees these
horses and this road, he will instantly turn back. 'Shall I trust
myself,' he'll say, 'in a district where sand runs between one's legs
like water, and where mice are put into harness? The ground is not firm
enough for me.'"
"The horses are not the worst things here," said Anton, absently. "Look!
these go fast enough."
"Yes," replied Karl, "but they don't go like regular horses; they
entangle their legs like two cats playing in a parsley-bed. And what
things they have for shoes--regular webbed hoofs, I declare, which no
blacksmith can ever fit."
"If we could only get on!" returned Anton; "the wind blows cold, and I
am shivering in spite of my fur."
"You have slept but little the last few nights, sir," said Karl. "The
wind blows here as if over a threshing-floor. The earth is not round
hereabouts as elsewhere, but flat as a cake. This is a complete desert;
we have been driving for more than an hour, and there is not a village
to be seen."
"A desert indeed," sighed Anton; "let us hope it may improve." They
relapsed into profound silence. At length the driver stopped near a
pool, unharnessed the horses, and led them to the water's edge, without
noticing the travelers.
"What the deuce does this mean?" cried Karl, jumping down from the
carriage.
"I am going to feed," replied the servant, sulkily, in a foreign accent.
"I am anxious to know how that will be done," said Karl. "There is not
the shadow of a bag of provender."
The horses, however, soon proved that they could live without corn; they
stretched down their shaggy heads, and began to pull the grass and weeds
at the edge of the pool, sometimes taking a draught of the dirty water.
Meanwhile the servant drew a bundle from under his seat, settled himself
under the lee of an alder-bush, and, taking his knife, cut his bread and
cheese without even glancing at the travelers.
"I say, Ignatius or Jacob," cried Karl, sharply, "how long will this
breakfast of yours last?"
"An hour," replied the man, munching away.
"And how far is it from here to the estate?"
"Six miles, or maybe more."
"You can make nothing of him," said Anton; "we must put up with the
customs of the country;" and, leaving the carriage, they went to look on
at the horses feeding.
Anton is on his way to the Polish property. He is now the baron's agent.
Anxious months have the last proved to him. The parting from his
principal and the firm had been painful in the extreme. For some time
before it, indeed, Anton had found himself alone in the midst of his
colleagues. The quiet Baumann still remained his friend, but the others
considered him a castaway. The merchant received his resignation with
icy coldness; and even in the hour of parting, his hand lay impassive as
metal in Anton's grasp. Since then, our hero had undertaken several
journeys to the capital and to creditors in the family's behalf, and now
he was on his way to set the new estate in order, accompanied by Karl,
whom he had induced to become the baron's bailiff.
Ehrenthal had, by the authority conferred on him,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from the time of the sale by auction, and hired the Polish
bailiff for the baron. There had been unfair dealings between them at
the time, and it was well known in Rosmin that the bailiff had sold off
a good deal, and been guilty of all sorts of frauds since, so that Anton
had even now no prospect of a quiet life.
"The hour is come when I may execute my commission," cried Karl, groping
in the straw under the seat. He drew out a large japanned tin case, and
carried it to Anton. "Miss Sabine gave me this in charge for you." He
then joyously opened the lid, produced the materials for an excellent
breakfast, a bottle of wine, and a silver goblet. Anton took hold of the
case.
"It has a very knowing look," said Karl. "Miss Sabine planned it
herself."
Anton examined it on all sides, and placed it carefully on a tuft of
grass; then he took up the goblet, and saw his initials engraved on it,
and underneath the words, "To thy welfare." Whereupon he forgot the
breakfast and all around him, and stood gazing at the goblet, lost in
thought.
"Do not forget the breakfast, sir," suggested Karl, respectfully.
"Sit down by me, my faithful friend; eat and drink with me. Leave off
your absurd politeness. We shall have but little, either of us, but what
we have we will share like brothers. Take the bottle if you have no
glass."
"There's nothing like leather," said Karl, taking a small leathern
drinking-cup out of his pocket. "As for 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t was
kindly meant, and I thank you; but there must be subordination, if it
were but for the sake of the others; and so, sir, be kind enough to let
me shake hands with you now, and then let things be as they were before.
Only look at the horses, Mr. Anton. My faith! the creatures devour
thistles."
Again the horses were harnessed, again they threw out their short legs
in the sand, and again the carriage rolled through the barren
district--first through an empty plain, next through a wretched
fir-wood, then past a row of low sand-hills, then over a tumble-down
bridge crossing a small stream.
"This is the property," said the driver, turning round, and pointing
with his whip to a row of dirty thatched roofs that had just come into
sight.
Anton stood up to look for the group of trees in which the Hall might be
supposed to stand. Nothing of the sort to be seen. The village was
deficient in all that adorns the home of the poorest German peasant--no
orchard, no hedged-in gardens, no lime-trees in the market-place.
"This is wretched," said he, sitting down again; "much worse than they
told us in Rosmin."
"The village looks as if under a curse," cried Karl; "no teams working
in the fields--not a cow or a sheep to be seen."
The farm-servant flogged his horses into an irregular gallop, and so
they passed through the rows of mud huts which constituted the village,
and arrived at the public house. Karl sprang from the carriage, opened
the tavern door, and called for the landlord. A Jew slowly rose from his
seat by the stove and came to the threshold. "Is the gendarme from
Rosmin come?" He is gone into the village. "Which is the way to the
farm-yard?"
The landlord, an elderly man with an intelligent countenance, described
the way in German and Polish, and remained standing at the
door--bewildered, Karl declared, by the sight of two human beings. The
carriage turned into a cross-road, planted on both sides with thick
bushes, the remains of a fallen avenue. Over holes, stones, and puddles,
it rattled on to a group of mud huts, which still had a remnant of
whitewash upon them. "The barns and stables are empty," cried Karl, "for
I see gaps in the roofs large enough to drive our carriage through."
Anton said no more; he was prepared for every thing. They drove through
a break between the stables into the farm-yard, a large irregular space,
surrounded on three sides by tumble-down buildings, and open to the
fields on the fourth. A heap of _débris_ lay there--lime and rotten
timber, the remains of a ruined barn. The yard was empty; no trace of
farm implements or human labor to be seen. "Which is the inspector's
house," inquired Anton, in dismay. The driver looked round, and at last
made up his mind that it was a small one-storied building, with straw
thatch and dirty windows.
At the noise of the wheels a man appeared on the threshold, and waited
phlegmatically till the travelers had dismounted, and were standing
close before him. He was a broad-shouldered fellow, with a bloated,
brandy-drinking face, dressed in a jacket of shaggy cloth, while behind
him peered the muzzle of an equally shaggy dog, who snarled at the
strangers. "Are you the steward of this property?"
"I am," replied the man, in broken German, without stirring from where
he was.
"And I am the agent of the new proprietor," said Anton.
"That does not concern me," growled the shaggy man, turning sharp round,
entering the house, and bolting the door within.
Anton was thoroughly roused. "Break the window in, and help me to catch
the rascal," cried he to Karl, who coolly seized a piece of wood, struck
the panes so as to make the rotten framework give way, and cleared the
opening at one leap. Anton followed him. The room was empty, so was the
next, and in it an open window--the man was gone.
"After him!" cried Karl, and dashed on in pursuit, while Anton looked
about the house and out-buildings. He soon heard the barking of a dog,
and saw Karl capture the fugitive. Hurrying to his help, he held the man
fast, while, with a kick, Karl sent the dog flying. They then contrived
to force the steward back to the house, though he kept striking out
violently all the way.
"Go to the tavern, and bring the gendarme and the landlord," cried Anton
to the driver, who, undisturbed by all that had been going on, had
meanwhile unpacked the carriage. The man accordingly drove leisurely
off, and the fugitive being got into the room, Karl found an old cloth,
and with it bound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I beg your pardon, sir,"
said he; "it is only for an hour or so, till the arrival of the Rosmin
gendarme, whom we have appointed to meet us."
Anton then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house, bu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found but the merest necessaries; no books nor papers of any kind. It
had doubtless been emptied already. A bundle projected from the
coat-pocket of the prisoner, which turned out to be receipts and legal
documents in Polish. In time, the driver returned with the landlord and
the armed policeman. The landlord stood at the door in some perplexity,
and the policeman explained in a few moments what remained to be done.
"You must make a statement to the local judge, and give the man up to
me. He shall go back in your carriage to Rosmin. You will do well to get
rid of him, for this is a wild country, and it will be safer for you to
have him at Rosmin than here, where he has friends and accomplices."
After a long search, a sheet of paper was found in a cupboard, the
statement made and submitted to the policeman, who shook his head a
little over the Polish composition, and the prisoner lifted into the
carriage, the gendarme taking his seat beside him, and saying to Anton,
"I have long expected something of the kind. You may have often occasion
to want me again." The carriage then drove away, and thus the property
came under Anton's administration. He felt as if cast on a desert
island.
His portmanteau and traveling effects were leaning against a mud wall,
and the Polish landlord was the only man who could give him and Karl any
information or advice in their forlorn condition.
Now that the steward was fairly gone, the landlord grew more
communicative, and showed himself serviceable and obliging. A long
conversation ensued, and its purport was what Anton had apprehended from
the warning given by the Commissary Walter and other Rosmin officials.
The inspector had,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done all he could in the
way of spoliation, rendered daring by a report which had found its way
from the town to the village, that the present proprietor would never be
able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estate. At last Anton said, "What that
wretched man has done away with he will have to account for; our first
care must be to preserve what is still to be found on the property. You
must be our guide to-day."
They then examined the empty buildings. Four horses and two
servants--they were gone into the wood--a few old plows, a pair of
harrows, two wagons, a britzska, a cellar full of potatoes, a few
bundles of hay, a little straw--the inventory did not take much time in
drawing up. The buildings were all out of repair, not through age, but
neglect.
"Where is the dwelling-house?" inquired Anton. The landlord led the way
out of the yard to the meadow--a broad plain, gradually sloping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brook. It had been a great pasture. The cattle had
trodden it down into holes; the snouts of greedy swine had rooted it up;
gray molehills and rank tufts of grass rose on all sides.
The landlord stretched out his hand. "There is the castle. This castle
i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he added, reverentially; "no
nobleman in the district has a stone house like that. All the gentry
here live in wood and mud buildings. Herr von Tarow, the richest of
them, has but a poor dwelling."
About three hundred yards from the last out-building rose a great brick
edifice, with a black slate roof and a thick round tower. Its gloomy
walls on this treeless pasture-land, without one trace of life around,
rose beneath the cloudy sky like a phantom fortress which some evil
spirit had evoked from the abyss--a station from which to blight all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The strangers approached it. The castle had fallen into ruins before the
builders had finished their task. The tower had stood there for ages. It
was built of unhewn stone, and had small windows and loop-holes. The
former lords of the land had looked down from its summit on the tops of
the trees, which then stretched far into the plain. They had then ruled
with a rod of iron the serfs who cultivated their land, and toiled and
died for them. Many an arrow had sped through those loop-holes at the
enemy storming below, and many a Tartar horse had been overthrown before
those massive walls. Years ago, a despot of the district had, in
expiation of former sins, begun to add to the gray tower the walls of a
holy monastery; but the monastery never got finished, and the useless
walls had already stood there long, when the late count took it into his
head to convert them into a lordly dwelling for his race, and to raise a
house unparalleled for magnificence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 front of the house was added on to both sides of the tower, which
projected in the middle. The intention had been to have a high
terrace-road up to the castle, and the principal entrance had been made
in the tower, and arched over; but the terrace never having been formed,
the stone threshold of the main door was quite inacce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ladders, and the wide opening was left. The window-spaces of
the lower floor were merely closed up with boards, while on the second
story were some window-frames of beautifully carved wood, in which large
panes had once been placed, but they had got broken. In other windows
were temporary frames of rough deal, with small panes of muddy glass let
into them. A company of jackdaws sat on the top of the tower, looking
down in amazement on the strangers, and every now and then one flew off,
screaming loudly, to contemplate the intruders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A house for crows and bats, not for human beings," said Anton. "At
least, I see no way of getting into it."
The landlord now took them round the building. Behind, where the two
wings made a sort of horse-shoe, there were low entrances to the cellars
and offices; beneath which, again, were stables, great arched kitchens,
and small cells for the serfs. A wooden staircase led to the upper
story. The door turned creaking on its hinges, and a narrow passage took
them through a side wing to the front part of the house. There all was
at least magnificently planned. The circular entrance-hall--an arched
room of the old tower--was painted in mosaic, and through the great
doorway-opening was seen a wide expans
small disturbance made by the return of Anton had gradually settled
down. Those first-class treasures of Sabine's had made way for other
specimens of damask, still of a superior kind, it is true, but which
came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e elderly cousin's comprehension. She had
been quite right in prophesying that Anton would never remark those
signs of exuberant gratitude or their withdrawal. However, one change
had been permanently made--the greatest, the best of all changes--the
clerk retained a privileged place in the heart of the young mistress of
the firm, and his tall figure often appeared as one of the circle that
Sabine's fancy loved to gather round her when at her work-table or in
her treasure-chamber.
To-day she was walking restlessly up and down before dinner. The cousin,
who heard every thing, had just told her that a maid from Ehrenthal's
had run into the office to announce Bernhard's death to his friend. "How
will he bear it?" thought she. And the name of Ehrenthal forced her
thoughts back to the past, to one now far away, and to that painful hour
when the struggle going on in her own mind had been suddenly brought to
a close by a letter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parted. And Anton had known
of that conquered feeling of hers. How considerate he had always been,
how chivalrous, how helpful! She wondered if he had any idea of the
completeness of her triumph over a girlish illusion. She shook her head.
"No, he has not. It was here, at this very table, that an accident first
betrayed me to him. That past time still rises like a cloud between us.
Whenever I sit near Wohlfart of an evening, I am conscious of another's
shadow at my side; and when he speaks to me, his tone, his manner always
seem to say, 'You are not alone; he is with you.'" Sabine started, and
lovingly passed her hand over the beautiful flowers on the table before
her, as if to dispel a painful thought. She could not tell him that she
was free from that long-felt sorrow. Now, however, when he had lost a
friend whom he so much loved, she must show him that there were other
hearts that clung to him still. And again she walked up and down, trying
to devise a way of speaking to him alone.
Dinner was announced. Anton came with the rest, and took his place at
once. There was no opportunity of exchanging a word during the meal, but
he often met her sad and sympathizing eye. "He eats nothing at all
to-day," whispered her cousin; "not even any of the roast," she added,
reproachfully. Sabine was much perturbed. Mr. Jordan had already risen;
Anton would leave the room with the rest, and she should not see him
again the whole day through. So she called out, "The great Calla is
fully blown now. You were admiring the buds the other day; will you
remain a moment; I should like to show it you?" Anton bowed and staid
behind. A few more awkward moments, then her brother rose too; and,
hurrying to Anton, she took him to the room where the flowers were.
"You have had sorrowful tidings to-day," she began.
"The tidings themselves did not surprise me," replied Anton. "The doctor
gave no hope. But I lose much in him."
"I never saw him," said Sabine; "but I know from you that his life was
lonely--poor in affection and in enjoyment."
She moved an arm-chair toward Anton, and led him on to talk about his
friend. She listened to every word with warm sympathy, and well knew
what to ask and how to comfort. It was a relief to Anton to speak of the
departed one, to describe his quiet way of life, his erudition, his
poetical enthusiasm. After a pause, Sabine looked up frankly into his
face, and asked, "Have you any tidings of Herr von Fink?"
It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his departure that she had ever breathed his
name. Anton felt how touching her confidence was, given in this hour of
his sadness. In his emotion, he seized her hand, which she was slow in
withdrawing.
"He is not happy in his new life," he gravely replied. "There was a
savage humor in his last letter, from which I gather, even more than
from his actual words, that the business into which his uncle's death
has thrown him does not suit him."
"It is unworthy," cried Sabine.
"At all events, it is not what would be recognized as honorable in this
house," replied Anton. "Fink is upright, and has lived too long with
your brother to take pleasure in the wild speculations so common on the
other side the Atlantic. His partners and colleagues are for the most
part men without a conscience, and his feelings revolt against their
companionship."
"And can Herr von Fink tolerate such relations as these for a day?"
"It is a remarkable thing that he whose own will was ever so arbitrarily
exercised, should now be obliged against that will to obey a pressure
from without, and every where to work with his hands tied. The
organization of such speculations in America is so complicated that one
shareholder can do little to alter it; and, now that Fink has attained
what used to be the goal of his wishes--a large capital, and the
management of immense districts--his condition appears more uncertain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He was always in danger of thinking slightingly
of others, now I am distressed at the bitter contempt he expresses for
his own life. His last letter paints an intolerable state of things, and
seems to point to some decisive resolve."
"There is only one resolve for him," cried Sabine. "May I ask what you
said to him in reply?"
"I entreated him instantly, come what would, to free himself from the
business in which he was entangled. I said that his own strong will
might find a way of extrication, even if that which I pointed out proved
impracticable. Then I begged of him either to carry out his old plan of
becoming a landed proprietor in America, or to return to us."
"I knew that you would write thus," said Sabine, drawing a long breath.
"Yes, Wohlfart, he shall return," said she, gently, "but he shall not
return to us."
Anton was silent.
"And do you think that Herr von Fink will follow your advice?"
"I do not know. My advice was not very American."
"But it was worthy of you," cried Sabine, with proud delight.
"An officer wishes to speak to Mr. Wohlfart," said a servant at the
door.
Anton sprang up. Sabine went to her flowers and bent mournfully over
them. The shadows of others hovered still between her friend and her.
The few words spoken by the servant filled Anton with a vague terror. He
hurried into the ante-room: there stood Eugene von Rothsattel. Anton was
gladly rushing forward to greet him, but the young soldier's face of
agony made him start back. He whispered, "My mother wishes to speak to
you; something dreadful has occurred." Anton caught up his hat, ran into
the office, hurriedly asked Baumann to excuse him to the principal, and
then accompanied the lieutenant to the baron's house.
On the way, Eugene, who had lost all self-command, said unconnectedly to
Anton, "My father last night accidentally wounded himself by a
pistol-shot--a messenger was sent to summon me--when I came, I found my
mother in a swoon--my sister and I do not know what to do--Lenore
implored my mother on her knees to send for you--you are the only one in
whom w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our distress--I understand nothing about
business, but my father's affairs must be in a dreadful state--my mother
is beside herself--the whole house is in the greatest disorder."
From what Eugene said and what he did not say; from his broken sentences
and his look of agony, Anton guessed at the horrors of the previous
evening. In the boudoir of the baroness he found Lenore, weeping and
exhausted.
"Dear Wohlfart!" cried she, taking his hand and beginning again to sob,
while her head sank powerless on his shoulder.
Meanwhile Eugene walked up and down, wringing his hands, and at length
throwing himself on the sofa, he gave himself up to silent tears.
"It is horrible, Mr. Wohlfart," said Lenore, lifting up her head. "No
one may approach my father--Eugene may not, nor I--only my mother and
old John are with him; and early this morning the merchant Ehrenthal was
here, insisting that he must see my father. He screamed at my mother,
and called my father a deceiver, till she fainted away. When I rushed
into the room, the dreadful man went off threatening her with his
clenched fist."
Anton led Lenore to a chair and waited till she had told him all.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comforting in this case, and his own heart was
wrung to the utmost by the misery he witnessed.
"Call my mother, Eugene," said Lenore, at length.
Her brother left the room.
"Do not forsake us," implored Lenore, clasping her hands; "we are at the
last gasp; even your help can not save us."
"He is dead who might perhaps have done so," mournfully replied Anton.
"Whether I can be of any use I know not, but you can not doubt my
willingness to be so."
"No," cried Lenore. "And Eugene, too, thought of you at once."
The baroness now entered. She walked wearily; but, steadying herself by
a chair, she saluted Anton with dignity. "In our position," said she,
"we need a friend who knows more of business than we three do.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prevents the baron--possibly for a long time to
come--from managing his own affairs, and, little as I understand them, I
can see that our interests require prompt measures. My children have
mentioned you to me, but I fear I am unreasonable in asking you to
devote your time to our service."
She sat down, beckoned Anton to take a chair, and said to her children,
"Leave us; I shall be better able to tell Mr. Wohlfart the little that I
know when I do not see your grief."
When they were alone, she motioned him nearer and tried to speak, but
her lips quivered, and she hid her face in her handkerchief.
"Before I can consent, gracious lady," said he, "to your reposing in me
such confidence as this, I must first inquire whether the baron has no
relative or intimate friend to whom you could with less pain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I pray you to remember that my own knowledge of business
is but small, and my position not one to constitute me a proper
counselor to the baron."
"I know no one," said the baroness, hopelessly. "It is less painful to
me to tell you what I can not conceal, than to one of our own circle.
Consider yourself a physician sent for to visit a patient. The baron has
this morning told me some particulars of his present circumstances." And
then she proceeded to relate what she had gathered as to the nature of
his embarrassments, the danger in which the family property was placed,
and the capital needed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Polish estate.
"My husband," continued she, "has given me the key of his desk, and he
wishes Eugene, with the help of a man of business, to go over his
papers. I now request of you to make this examination together with my
son. When you need explanations, I will try to obtain them from the
baron. The question is now, whether you are inclined to undertake this
trouble for us, who are only strangers."
"I am most willing to do so," earnestly replied Anton; "and I hope that
the kindness of my principal will allow me the time needful for the
purpose, if you do not consider it more advisable to depute the baron's
experienced legal adviser to the task."
"There will be an opportunity of asking that gentleman's advice later,"
said the baroness.
Anton rose. "When do you wish to begin?"
"Immediately. I fear there is not a day to lose. I shall do all I can to
help you look the papers over." She led Anton into the next room, called
in Eugene, and unlocked the baron's desk. As she opened it she lost her
self-command for a moment, and moving to the window, the quivering of
the curtains betrayed the anguish that shook her fragile frame.
The mournful task began. Hour after hour passed. Eugene was in no
condition to peruse any thing, but his mother reached letters and
documents to Anton, and, though often obliged to desist a while, she
bravely returned to the task. Anton placed the papers in order, and
sought, by glancing over each, to arrive at least at a superficial view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It was evening, when the old servant opened the door in dismay, and
called out, "He is there again." The baroness could not repress a slight
scream, and made a gesture of aversion.
"I have told him that no one is at home, but he will not be dismissed;
he makes such a noise on the steps. I can not get rid of him."
"It will kill me if I hear his voice again," murmured the baroness.
"If the man be Ehrenthal," said Anton, rising, "I will try to get him
away. We have now done what was most necessary; have the goodness to
lock up these papers, and to allow me to return to-morrow." The baroness
silently assented, and sank back in her chair. Anton hurried off to the
ante-room, whence he could hear Ehrenthal's loudly-raised voi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usurer shocked him. His hat pushed half off his
head, his pale face swelled as if by drinking, his glazed eyes red with
tears, Ehrenthal stood before him, calling in broken sentences for the
baron, wailing and cursing alternately. "He must come! he must come at
once!" cried he; "the wicked man! A nobleman, indeed! he is a vagabond,
after whom I will send the police. Where is my money? Where is my
security? I want my mortgage from this man who is not at home."
Anton went straight up to him, and asked, "Do you know me, Mr.
Ehrenthal?" Ehrenthal turned his glazed eyes upon him, and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 friend of his dead son.
"He loved you!" he cried, in a lamentable voice. "He spoke to you more
than to his father. You were the only friend that he had on earth. Have
you heard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house of Ehrenthal?" continued he, in
a whisper. "Just as they stole the papers he died. He died with a hand
like this," and clenching his fist he struck his forehead. "Oh my son!
my son! why didst not thou forgive thy father!"
"We will go to your son," said Anton, taking the arm of the old man, who
unresistingly allowed himself to be led back to his own house.
From thence Anton hurried to Councilor Horn, with whom he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It was late before he returned home. In the midst of his anxiety about
those whose prosperity had filled his imagination years before,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in their adversity, reposed in him, dilated his
breast with a feeling of pride. He burned with desire to help them, and
hoped that his zealous devotion might yet find some way of rescue. As
yet he saw none. Looking up at the great building before him, so firm
and secure, in the moonlight, a thought flashed into his mind. If any
man could help them, it was his principal. His keen eye would be able to
unravel all the dark secrets in which the baron was entangled, and his
iron strength of will would crush the villains who held the unfortunate
nobleman in their power. And then he had a noble nature; he always
decided on the right, without an effort or a struggle. Anton looked at
the first floor. The whole house-front was dark, but in a corner room a
light still burned. It was the private office of his chief.
With sudden resolve, Anton begged the servant to take him to Mr.
Schröter, who looked with amazement at the unexpected visitor, and asked
what brought him, and whether any thing had happened.
"I implore your counsel--I implore your help," cried Anton.
"For yourself or for others?" inquired the merchant.
"For a family with whom I have accidentally become connected. They are
lost if a strong hand does not ward off the impending catastrophe."
Anton then rapidly related the occurrences of the afternoon, and,
seizing his principal's hand in his emotion, cried, "Have pity upon the
unhappy ladies, and help them."
"Help them!" replied the merchant; "how can I? Have you been
commissioned to apply to me, or are you only following the impulse of
your own feelings?"
"I am not commissioned; it is only the interest that I take in the
baron's fate which leads me to you."
"And what right have you to inform me of facts communicated in strict
confidence to yourself by the baron's lady?" asked the merchant, dryly.
"I am committing no indiscretion in telling you what will, in a few
days, be no secret, even to strangers."
"You are unusually excited, otherwise you would not forget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hatever, does a man of business venture to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without the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Of course, I shall make no wrong use of what you have said, but it was
by no means business-like, Wohlfart, to be so open toward me."
Anton was silent, feeling, indeed, that his principal was right, but yet
it seemed hard to be blamed for reposing confidence at such a time as
this. The merchant walked silently up and down; at length, stopping
before Anton, he said, "I do not now inquire how you come to take so
warm an interest in this family. I fear it is an acquaintance you owe to
Fink."
"You shall hear all," said Anton.
"Not at present. I will now content myself with repeating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interfere in these affairs without being specially
applied to by the parties themselves. I may add that I by no means wish
for such an application, and do not disguise from you that, were it
made, I should probably decline to do any thing for the Baron
Rothsattel."
Anton's feelings were roused to the utmost. "The question is the rescue
of an honorable man, and of lovely and amiable women from the toils of
rogues and impostors. To me, this seems the duty of every one; I, at
least, consider it a sacred obligation which I dare not shrink from. But
without your support I can do nothing."
"And how do you think this embarrassed man can be helped?" inquired the
merchant, seating himself.
With somewhat more composure, Anton repli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an experienced man of business making himself master of the case. There
must be some way of circumventing these villains. Your penetration would
discover it."
"Any attorney would be far more likely to do so, and the baron might
readily engage the services of experienced and upright legal advisers.
If his enemies have done any thing illegal, the quick eye of a lawyer is
the most likely to detect it."
"Alas! the baron's own lawyer gives but little hope," replied Anton.
"Then, my dear Wohlfart, no other is likely to do much good. Show me an
embarrassed man who has strength to grasp an offered hand, and bid me
help him, and for the sake of all I owe you, I will not refuse to do so.
I think you are convinced of this."
"I am," said Anton, dejectedly.
"From all I hear, however," the merchant went on,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the baron. From what I gather from general report, as well as from
you, his embarrassments arise from his having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usurers, which proves him deficient in what alone ennobles the life of
any man--good sense, and the power of steady exertion."
Anton could only sigh his assent.
"To help such a man," inexorably continued the merchant, "is a futile
attempt, against which reason may well protest. We are not to despair of
any, but want of strength is the most hopeless case of all. Our power of
laboring for others being limited, it becomes our duty to inquire,
before we devote our time to the weak, whether we are not thus
diminishing our chances of helping better men."
Anton interrupted him. "Does he not deserve every allowance to be made
for him? He was brought up to exact much; he has not learned, as we
have, to make his way by his own labor."
The merchant laid his hand on the young man's shoulder. "The very
reason. Believe me, a large number of these landed gentry, who pay the
penalty of their old family memories, are beyond help. I am the last to
deny that many worthy and admirable men belong to this class. Indeed,
wherever remarkable talent or nobility of character shoots up among
them, no doubt their position offers peculiar scope for its development,
but for average men it is not a favorable one. He who considers it his
hereditary privilege to enjoy life, and who assumes a distinguished
position in virtue of his family, will very often fail to put forth his
whole strength in order to deserve that position. Accordingly, numbers
of our oldest families are declining, and their fall will be no loss to
the state. Their family associations make them haughty without any
right to be so--limit their perceptions and confuse their judgment."
"Even if all this be true," cried Anton, "it does not absolve us from
helping individuals of the class who have excited our sympathy."
"No," said the principal, "if it be excited. But it does not glow so
rapidly in advancing years as in youth. The baron has endeavored to
isolate his property from the current of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leave it forever to his family. Forever! You, as a merchant, know how to
estimate the attempt. True, every rational man must allow it to be
desirable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same soil should be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We all prize what our forefathers have possessed before
us, and Sabine would unlock every room in this house with pride, because
her great-great-grandmother turned the same keys before her. It is
therefore natural that the landed proprietor should desire to preserve
those familiar scenes, which are the source of his own prosperity, to
those nearest and dearest to him. But there must be means to this end,
and these means are the making his own existence available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increase of his patrimony. Where energy dies in families
or individuals, then it is well that their means die too, that their
money should circulate through other hands, and their plowshare pass to
those who can guide it better. A family that has become effete through
luxury ought to sink down into common life, to make room for the
uprising of fresh energies and faculties. Every one who seeks, at the
cost of free activity for others, to preserve permanent possessions and
privileges for himself or his family, I must look upon as an enemy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social state. And if such a man ruin
himself in his endeavors, I should feel no malicious pleasure in his
downfall, but I should say that he is rightly served, because he has
sinned against a fundamental law of our social being; consequently, I
should consider it doubly wrong to support this man, because I could but
fear that I should thus be supporting an unsound condition of the body
politic."
Anton looked down mournfully. He had expected sympathy and warm
concurrence, and he met with disaffection and coldness that he despaired
of conquering. "I can not gainsay you," he at length replied; "but in
this case I can not feel as you do. I have been witness to the
unspeakable distress in the baron's family, and my whole soul is full
of sadness and sympathy, and of the wish to do something for those who
have opened their heart to me. After what you have said, I dare no
longer ask you to trouble yourself with their affairs, but I have
promised the baroness to assist her as far as my small powers permit,
and your kindness allows. I implore you to grant me permission to do
this. I shall endeavor to be regular in my attendance at the office, but
if during the next few weeks I am occasionally absent, I must ask you to
excuse me."
Once more the merchant walked up and down the room, and then, looking at
Anton's excited face, with deep seriousness and something of regret, he
replied, "Remember, Wohlfart, that every occupation which excites the
mind soon obtains a hold over a man, which may retard as well as advance
his success in life. It is thi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 to agree
to your wishes."
"I know it," said Anton, in a low voice; "but I have now no choice
left."
"Well, then, do what you must," said the merchant, gloomily; "I will lay
no hinderance in your way; and I hope that after a few weeks you will be
able to consider the whole circumstances more calmly." Anton left the
room, and the merchant stood looking long with frowning brow at the
place his clerk had occupied.
Nor was Anton in a more congenial mood. "So cold, so inexorable!"
exclaimed he, as he reached his own room. He began to suspect that his
principal was more selfish and less kindly than he had hitherto
supposed. Many an expression of Fink's recurred to his mind, as well as
that evening when young Rothsattel, in his boyish conceit, had spoken
impertinently to the merchant. "Is it possible," thought he, "that that
rude speech should be unforgotten?" And his chief's keen, deep-furrowed
face lost inexpressibly by contrast with the fair forms of the noble
ladies. "I am not wrong," he cried to himself; "let him say what he
will, my views are more just than his, and henceforth my destiny shall
be to choose for myself the way in which I shall walk." He sat long in
the darkness, and his thoughts were gloomy as it; then he went to the
window to look down into the dark court below. A great white blossom
rose before him like a phantom. Striking a light, he saw that it was the
beautiful Calla out of Sabine's room. It hung down mournfully on its
broken stem. Sabine had had it placed there. This little circumstance
struck him as a mournful omen.
Meanwhile Sabine, taper in hand, entered her brother's room.
"Good-night, Traugott," nodded she. "Wohlfart has been with you this
evening; how long he staid!"
"He will leave us," replied the merchant, gloomily.
Sabine started and dropped her taper on the table. "For God's sake, what
has happened? Has Wohlfart said that he was going away?"
"I do not yet know it, but I see it coming step by step; and I can not,
and still less can you, do any thing to retain him. When he stood before
me here with glowing cheeks and trembling voice, pleading for a ruined
man, I found out what it was that lured him away."
"I do not understand you," said Sabine, looking full at her brother.
"He chooses to become the confidential friend of a decayed noble. A pair
of bright eyes draws him away from us: it seems to him a worthy object
of ambition to become Rothsattel's man of business. This intimacy with
nobility is the legacy bequeathed to him by Fink."
"And you have refused to help him?" inquired Sabine, in a low voice.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said the merchant, harshly; and he
turned to his writing-table.
Sabine slowly withdrew. The taper trembled in her hand as she passed
through the long suite of rooms listening to her own footfall, and
shuddering as the feeling came over her that an invisible companion
glided by her side. This was the revenge of that other. The shadow that
once fell on her innocent life now drove her friend away from their
circle. Anton's affections clung to another. She had but been in his
eyes a mere stranger, who had once loved and languished for one now far
away, and who now, in widow's weeds, looked back regretfully to the
feelings of her youth.
The few next weeks were spent by Anton in over-hard work. He had great
difficulty in keeping up his counting-house duties, while he spent every
spare hour in conference with the baroness and the lawyer.
In the mean time, the misfortunes of the baron ran their course. He had
not been able to pay the interest of the sums with which his estate was
burdened. When last they were due, a whole series of claims was brought
against him, and the estate fell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district authorities. Complicated lawsuits arose. Ehrenthal complained
loudly, claiming the first mortgage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nay, he
was inclined to advance claims on the last mortgage offered by the baron
in the recent fatal hour. Löbel Pinkus also appeared as claimant of the
first mortgage, and asserted that he had paid the whole sum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Ehrenthal had no proof to bring forward, and had been
for some weeks past quite unable to manage his own affairs, while
Pinkus, on the contrary, fought with every weapon a hardened sinner can
devise or employ, and the deeds which the baron had executed at Veitel's
suggestion proved to be so capital a master-stroke of the cunning
advocate, that the baron's man of business had, from the first, little
hope of the case. We may here observe that Pinkus did eventually win it,
and that the mortgage was made over to him.
Anton was now gradually gaining some insight into the baron's
circumstances. But the double sale of the first mortgage was still kept
a secret by the latter, even from his wife. He declared Ehrenthal's
claim unfounded, and even expressed a suspicion that he had himself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robbery in his office. Indeed, he really
believed this. Then the name of Itzig was never broached, and the
suspicion against Ehrenthal, which the baron's lawyer shared, prevented
Anton seeking any explanation from him.
Meanwhile, an estrangement had sprung up between our hero and his
principal, which the whole counting-house remarked with surprise. The
merchant scowled at Anton's vacant seat when the latter chanced to be
absent during office-hours, or looked coldly at his clerk's face, made
pale as it was with excitement of mind and night-work. He took no notice
of his new occupation, and never seemed to remark him. Even to his
sister he maintained a stiff-necked silence; nor could all her attempts
lead him to speak of Anton, who, on his side, felt his heart revolt
against this coldness. After his return, to be treated like a child of
the house, praised, promoted, petted, and now to be treated like a mere
hireling, who is not worth the bread thrown to him; to be a toy of an
incomprehensible caprice--this, at least, he had not deserved; so he
became reserved toward the whole family, and sat silent at his desk; but
he fel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now and the then so keenly, that often,
when alone, he would spring up and stamp on the ground in the bitter
indignation of his heart.
One comfort remained. Sabine was not estranged. True, he saw little of
her, and at dinner she seemed to avoid speaking to him, but he knew that
she was on his side.
A few days after his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the merchant, she came down
stairs as he stood in the hall, and had to pass him by so closely that
her dress touched him. He had retreated, and made a formal bow, but she
looked at him imploringly, and whispered, "You must not be estranged
from me." It was an affair of a moment, but the faces of both were
radiant with a happy understanding.
The time had now arrived when Mr. Jordan was to quit the firm. The
principal again called Anton into his little office, and without any
severity, but also without a trace of his former cordiality, began: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o you my intention of appointing you Jordan's
successor; but,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your time has been more taken
up with other business than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such a post, I
therefore ask you whether you are now at liberty to undertake Jordan's
duties?"
"I am not," replied Anton.
"Can you name any--not very distant--time when you will be free from
your present occupation? In that case I will endeavor to find a
substitute until then."
Anton sorrowfully replied, "I can not at present say when I shall again
be master of my whole time; and, besides, I feel that, even as it is, I
tax your indulgence by many irregularities. Therefore, Mr. Schröter, I
beg that you will fill up this post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me."
The merchant's brow grew furrowed and dark, and he silently bowed
assent. Anton felt as he closed the door that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m was now complete, and, resuming his place, he leaned his throbbing
head on his hand. A moment later Baumann was summoned to the principal,
and Jordan's situation conferred upon him. On returning to the office,
he went up to Anton and whispered, "I refused at first, but Mr. Schröter
insisted. I am doing you an injustice." And that evening Mr. Baumann, in
his own room, read in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the chapters treating of
the unjust Saul (the principal), and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Jonathan
and the persecuted David, and strengthened his heart thereby.
The next day Anton was summoned to the baroness. Lenore and her mother
sat before a large table covered with jewel-boxes and toilette elegances
of every description, while a heavy iron chest stood at their feet. The
curtains were drawn, and the subdued light shone softly into the richly
furnished room. On the carpet glowed wreaths of unfading flowers, and
the clock ticked cheerfully in its alabaster case. Under the shade of
flowering plants sat the two love-birds in their silvered cage, hopping
from perch to perch, screaming ceaselessly, or sitting up quietly close
to each other. The whole room was beauty and perfume. "For how long?"
thought Anton. The baroness rose. "We are already obliged to trouble you
again," said she; "we are engaged in a very painful occupation." On the
table were all manner of ornaments, gold chains, brilliants, rings,
necklaces, gathered into a heap.
"We have been looking out all that we can dispense with," said the
baroness, "and now pray you to undertake to sell these things for us. I
have been told that some of them are of value, and as we are now in much
need of money, we turn here for help."
Anton looked in perplexity at the glittering heap.
"Tell us, Wohlfart," cried Lenore, anxiously, "is this necessary? can it
be of any use? Mamma has insisted upon setting apart for sale all our
ornaments, and whatever plate is not in daily use. What I can give is
not worth talking of, but my mother's jewels are costly; many of them
were presents made to her in youth, which she shall not part with unless
you say that it is necessary."
"I fear," said Anton, gravely, "that it will prove so."
"Take them," said the baroness to Anton; "I shall be calmer when I know
that we have at least done what we could."
"But do you wish to part with all?" inquired Anton, anxiously. "Much
that is dear to you may have but little value in a jeweler's eyes."
"I shall never wear an ornament again," quietly replied the baroness.
"Take them all;" and, holding her hands before her eyes, she turned
away.
"We are torturing my mother," cried Lenore, hastily; "will you lock up
all that is on the table, and get them out of the house as soon as you
can?"
"I can not undertake the charge of these valuables," said Anton,
"without taking some measures to decrease my own responsibility. First
of all, I will in your presence make a short note of all you intrust to
me."
"What useless cruelty!" exclaimed Lenore.
"It will not take long."
Anton took out a few sheets from his pocket-book, and began to note down
the different articles.
"You shall not see it done, mother," said Lenore, drawing her mother
away, and then returning to watch Anton at his task.
"These preparations for the market are horrible," said she. "My mother's
whole life will be sold; some memory of hers is linked with every single
thing. Look, Wohlfart, the princess gave her this diamond ornament when
she married my father."
"They are magnificent brilliants," cried Anton, admiringly.
"This ring was my grandfather's, and these are presents of poor papa's.
Alas! no man can know how we love all these things. It was always a
festival to me when mamma put on her diamonds. Now we come to my
possessions. They are not worth much. Do you think this bracelet good
gold?" She held out her hand as she spoke.
"I do not know."
"It shall go with the rest," said Lenore, taking it off. "Yes, you are a
kind, good man, Wohlfart," continued she, looking trustfully into his
tearful eyes; "do not forsake us. My brother has no experience, and is
more helpless than we are. It is a frightful position for me. Before
mamma I do all I can to be composed, else I could scream and weep the
whole day through." She sank in a chair, still holding his hand. "Dear
Wohlfart, do not forsake us."
Anton bent over her, and looked with passionate emotion at the lovely
face that turned so trustfully to him in the midst of its tears.
"I will be helpful to you when I can," said he, in the fullness of his
heart. "I will be at hand whenever you need me. You have too good an
opinion of my information and my faculties; I can be of less assistance
to you than you suppose, but what I can, that I will do in any and every
possible way."
Their hands parted with a warm pressure; the affair was settled.
The baroness now returned. "Our lawyer was with me this morning," said
she; "and now I must ask for your opinion on another subject. He tells
me that there is no prospect of preserving the baron's family estate."
"At this time, when interest is high, and money difficult to get, none,"
replied Anton.
"And you, too, think that we must turn all our efforts toward preserving
the Polish property?"
"I do," was the answer.
"For that, also, money will be necessary. Perhaps I may be able through
my relatives to intrust you with a small sum, which, with the help of
that"--she pointed to the iron chest--"may suffice to cover the first
necessary expenses. I do not, however, wish to sell the jewels here, and
a journey to the residence would be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cure the
sum to which I have just alluded. The baron's lawyer has spoken most
highly of your capacity for business. It is his wish which now decides
me to make a proposal to you. Will you for the next few years, or, at
all events, until our greatest difficulties are over, devote your whole
time to our affairs? I have consulted my children, and they agree with
me in believing that in your assistance lies our only hope of rescue.
The baron, too, has come in to the plan. The question now is whether
your circumstances allow you to give your support to our unfortunate
family. We shall be grateful to you, whatever conditions you affix; and
if you can find any way of making our great obligations to you apparent
in the position you hold, pray impart it to me."
Anton stood petrified. What the baroness required of him was separation
from the firm, separation from his principal, and from Sabine! Had this
thought occurred to him before, when standing in Lenore's presence or
bending over the baron's papers? At all events, now that the words were
spoken, they shocked him. He looked at Lenore, who stood behind her
mother with hands clasped in supplication. At length he replied, "I
stand in a position which I can not leav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others.
I was not prepared for this proposal, and beg to have time allowed me
for consideration. It is a step which will decide my whole future life."
"I do not press you," said the baroness; "I only request your
consideration. Whatever your decision be, our warmest gratitude will
still be yours; if you are unable to uphold our feeble strength, I fear
that we shall find no one to do so. You will think of that," she added,
beseechingly.
Anton hurried through the street with throbbing pulse. The noble lady's
glance of entreaty, Lenore's folded hands, beckoned him out of the
gloomy counting-house into a sphere of greater liberty, into a new
future, from whose depths bright images flashed out upon his fancy. A
request had been frankly made, and he was strongly inclined to justify
the confidence that prompted it. Those ladies required an unwearied,
self-sacrificing helper to save them from utter ruin, and if he
followed his impulse he should be doing a good work--fulfilling a duty.
In this mood he entered the merchant's dwelling. Alas! all that he saw
around him seemed to stretch out a hand to detain him. As he looked at
the warehouse, the good-humored faces of the porters, the chains of the
great scales, the hieroglyphics of the worthy Pix, again he felt that
this was the place that he belonged to. Sabine's dog kissed his hand,
and ran before him to his room--his and Fink's room. Here the childish
heart of the orphan boy had found a friend, kind companions, a home, a
definite and honorable life-purpose. Looking down through his window on
all the long-familiar objects, he saw a light in Sabine's store-chamber.
How often he had sought for that light, which brightened the whole great
building, and brought a sense of comfort and cheerfulness even into his
room. He now sprang up suddenly, and said to himself, "She shall
decide."
Sabine started in amazement when Anton appeared before her. "I am
irresistibly impelled to seek you," cried he. "I have to decide upon my
future life, and I feel undetermined, and unable to trust to my own
judgment. You have always been a kind friend to me since the day of my
arrival. I am accustomed to look up to you, and to think of you in
connection with all that interests me here. Let me hear your opinion
from your own lips. The Baroness Rothsattel has to-day proposed to me
permanently to undertake the situation of confidential adviser and
manager of the baron's affairs. Shall I accept; or shall I remain here?
I know not--tell me what is right both for myself and others."
"Not I," said Sabine, drawing back and growing very pale. "I can not
venture to decide in the matter. Nor do you wish me to do so, Wohlfart,
for you have already decided."
Anton looked straight before him and was silent.
"You have thought of leaving this house, and a wish to do so has sprung
out of the thought. And I am to justify you, and approve your resolve!
This is what you require of me," continued she, bitterly. "But this,
Wohlfart, I can not do, for I am sorry that you go away from us."
She turned away from him and leaned on the back of a chair.
"Oh, be not angry with me too!" said Anton; "that I can not bear. I have
suffered much of late. Mr. Schröter has suddenly withdrawn from me the
friendly regard that I long held my life's greatest treasure. I have not
deserved his coldness. What I have been doing has not been wrong, and
it was done with his knowledge. I had been spoiled by his kindness; I
have the more deeply felt his displeasure. My only comfort has been that
you did not condemn me. And now, do not you be cold toward me, else I
shall be wretched forever. There is not a soul on earth to whom I can
turn for affectionate comprehension of my difficulties. Had I a sister,
I should seek her heart to-day. You do not know what to me, lonely as I
am, your smile, your kindly shake of the hand has been till now. Do not
turn coldly from me, I beseech you."
Sabine was silent. At length she inquired, still with averted face,
"What draws you to those strangers; is it a joyful hope, is it sympathy
alone? Give this question close consideration before you answer it to
yourself at least."
"What it is that makes it possible for me to leave this house," said
Anton, "I do not myself know. If I can give a name to my motives, it is
gratitude felt toward one. She was the first to speak kindly to the
wandering boy on his way out into the world. I have admired her in the
peaceful brightness of her former life. I have often dreamed childish
dreams about her. There was a time when a tender feeling for her filled
my whole heart, and I then believed myself forever the slave of her
image. But years bring changes, and I learned to look on men and on life
with other eyes. Then I met her again, distressed, unhappy, despairing,
and my compassion became overmastering. When I am away from her, I know
that she is nothing to me; when I am with her, I feel only the spell of
her sorrow. Once, when I had to depart out of her circle like a culprit,
she came to me, and before the whole scornful assembly she gave me her
hand and acknowledged me her friend; and now she comes and asks for my
hand to help her father. Can I refuse it? Is it wrong to feel as I do? I
know not, and no one can tell me--no one but you alone."
Sabine's head had sunk down to the back of the chair on which she bent.
She now suddenly raised it, and with tearful eyes, and a voice full of
love and sorrow, cried, "Follow the voice that calls you. Go, Wohlfart,
go."
CHAPTER XXVII.
On a cold October day, two men were seen driving through the latticed
gate of the town of Rosmin on toward the plain, which stretched out
before them monotonous and boundless. Anton sat wrapped in his fur coat,
his hat low on his forehead, and at his side was young Sturm, in an old
cavalry cloak, with his soldier's cap cocked cheerily on one side. In
front of them a farm-servant, squatted on a heap of straw, flogged on
the small horses. The wind swept the sand and straw from the
stubble-fields, the road was a broad causeway without ditches or hedges,
the horses had to wade alternately through puddles and deep sand. Yellow
sand gleamed through the scanty herbage in all directions wherever a
field-mouse had made her way to her nest or an active mole had done what
he could to diversify the unbroken plain. Wherever the ground sank,
stagnant water lodged, and there hollow willow-trees stretched their
crippled arms in the air, their boughs flapping in the wind, and their
faded leaves fluttering down into the muddy pool below. Here and there
stood a small dwarf pine, a resting-place for the crows, who, scared by
the passing carriage, flew loudly croaking over the travelers' heads.
There was no house to be seen on the road, no pedestrian, and no
conveyance of any kind.
Karl looked every now and then at his silent companion, and said at
last, pointing to the horses, "How rough their coats are, and how pretty
their gray mouse skins! I wonder how many of these beasties would go to
make up my sergeant's horse! When I took leave of my father, the old man
said, 'Perhaps I shall pay you a visit, little one, when they light the
Christmas-tree.' 'You'll never be able,' said I. 'Why not?' asked he.
'You'll never trust yourself in any post-chaise.' Then the old boy
cried, 'Oho! post-chaises are always of a stout build; I shall be sure
to trust myself in one.' But now, Mr. Anton, I see that my father never
can pay us a visit."
"Why not?"
"It is possible that he may reach Rosmin; but, as soon as he sees these
horses and this road, he will instantly turn back. 'Shall I trust
myself,' he'll say, 'in a district where sand runs between one's legs
like water, and where mice are put into harness? The ground is not firm
enough for me.'"
"The horses are not the worst things here," said Anton, absently. "Look!
these go fast enough."
"Yes," replied Karl, "but they don't go like regular horses; they
entangle their legs like two cats playing in a parsley-bed. And what
things they have for shoes--regular webbed hoofs, I declare, which no
blacksmith can ever fit."
"If we could only get on!" returned Anton; "the wind blows cold, and I
am shivering in spite of my fur."
"You have slept but little the last few nights, sir," said Karl. "The
wind blows here as if over a threshing-floor. The earth is not round
hereabouts as elsewhere, but flat as a cake. This is a complete desert;
we have been driving for more than an hour, and there is not a village
to be seen."
"A desert indeed," sighed Anton; "let us hope it may improve." They
relapsed into profound silence. At length the driver stopped near a
pool, unharnessed the horses, and led them to the water's edge, without
noticing the travelers.
"What the deuce does this mean?" cried Karl, jumping down from the
carriage.
"I am going to feed," replied the servant, sulkily, in a foreign accent.
"I am anxious to know how that will be done," said Karl. "There is not
the shadow of a bag of provender."
The horses, however, soon proved that they could live without corn; they
stretched down their shaggy heads, and began to pull the grass and weeds
at the edge of the pool, sometimes taking a draught of the dirty water.
Meanwhile the servant drew a bundle from under his seat, settled himself
under the lee of an alder-bush, and, taking his knife, cut his bread and
cheese without even glancing at the travelers.
"I say, Ignatius or Jacob," cried Karl, sharply, "how long will this
breakfast of yours last?"
"An hour," replied the man, munching away.
"And how far is it from here to the estate?"
"Six miles, or maybe more."
"You can make nothing of him," said Anton; "we must put up with the
customs of the country;" and, leaving the carriage, they went to look on
at the horses feeding.
Anton is on his way to the Polish property. He is now the baron's agent.
Anxious months have the last proved to him. The parting from his
principal and the firm had been painful in the extreme. For some time
before it, indeed, Anton had found himself alone in the midst of his
colleagues. The quiet Baumann still remained his friend, but the others
considered him a castaway. The merchant received his resignation with
icy coldness; and even in the hour of parting, his hand lay impassive as
metal in Anton's grasp. Since then, our hero had undertaken several
journeys to the capital and to creditors in the family's behalf, and now
he was on his way to set the new estate in order, accompanied by Karl,
whom he had induced to become the baron's bailiff.
Ehrenthal had, by the authority conferred on him,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from the time of the sale by auction, and hired the Polish
bailiff for the baron. There had been unfair dealings between them at
the time, and it was well known in Rosmin that the bailiff had sold off
a good deal, and been guilty of all sorts of frauds since, so that Anton
had even now no prospect of a quiet life.
"The hour is come when I may execute my commission," cried Karl, groping
in the straw under the seat. He drew out a large japanned tin case, and
carried it to Anton. "Miss Sabine gave me this in charge for you." He
then joyously opened the lid, produced the materials for an excellent
breakfast, a bottle of wine, and a silver goblet. Anton took hold of the
case.
"It has a very knowing look," said Karl. "Miss Sabine planned it
herself."
Anton examined it on all sides, and placed it carefully on a tuft of
grass; then he took up the goblet, and saw his initials engraved on it,
and underneath the words, "To thy welfare." Whereupon he forgot the
breakfast and all around him, and stood gazing at the goblet, lost in
thought.
"Do not forget the breakfast, sir," suggested Karl, respectfully.
"Sit down by me, my faithful friend; eat and drink with me. Leave off
your absurd politeness. We shall have but little, either of us, but what
we have we will share like brothers. Take the bottle if you have no
glass."
"There's nothing like leather," said Karl, taking a small leathern
drinking-cup out of his pocket. "As for 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t was
kindly meant, and I thank you; but there must be subordination, if it
were but for the sake of the others; and so, sir, be kind enough to let
me shake hands with you now, and then let things be as they were before.
Only look at the horses, Mr. Anton. My faith! the creatures devour
thistles."
Again the horses were harnessed, again they threw out their short legs
in the sand, and again the carriage rolled through the barren
district--first through an empty plain, next through a wretched
fir-wood, then past a row of low sand-hills, then over a tumble-down
bridge crossing a small stream.
"This is the property," said the driver, turning round, and pointing
with his whip to a row of dirty thatched roofs that had just come into
sight.
Anton stood up to look for the group of trees in which the Hall might be
supposed to stand. Nothing of the sort to be seen. The village was
deficient in all that adorns the home of the poorest German peasant--no
orchard, no hedged-in gardens, no lime-trees in the market-place.
"This is wretched," said he, sitting down again; "much worse than they
told us in Rosmin."
"The village looks as if under a curse," cried Karl; "no teams working
in the fields--not a cow or a sheep to be seen."
The farm-servant flogged his horses into an irregular gallop, and so
they passed through the rows of mud huts which constituted the village,
and arrived at the public house. Karl sprang from the carriage, opened
the tavern door, and called for the landlord. A Jew slowly rose from his
seat by the stove and came to the threshold. "Is the gendarme from
Rosmin come?" He is gone into the village. "Which is the way to the
farm-yard?"
The landlord, an elderly man with an intelligent countenance, described
the way in German and Polish, and remained standing at the
door--bewildered, Karl declared, by the sight of two human beings. The
carriage turned into a cross-road, planted on both sides with thick
bushes, the remains of a fallen avenue. Over holes, stones, and puddles,
it rattled on to a group of mud huts, which still had a remnant of
whitewash upon them. "The barns and stables are empty," cried Karl, "for
I see gaps in the roofs large enough to drive our carriage through."
Anton said no more; he was prepared for every thing. They drove through
a break between the stables into the farm-yard, a large irregular space,
surrounded on three sides by tumble-down buildings, and open to the
fields on the fourth. A heap of _débris_ lay there--lime and rotten
timber, the remains of a ruined barn. The yard was empty; no trace of
farm implements or human labor to be seen. "Which is the inspector's
house," inquired Anton, in dismay. The driver looked round, and at last
made up his mind that it was a small one-storied building, with straw
thatch and dirty windows.
At the noise of the wheels a man appeared on the threshold, and waited
phlegmatically till the travelers had dismounted, and were standing
close before him. He was a broad-shouldered fellow, with a bloated,
brandy-drinking face, dressed in a jacket of shaggy cloth, while behind
him peered the muzzle of an equally shaggy dog, who snarled at the
strangers. "Are you the steward of this property?"
"I am," replied the man, in broken German, without stirring from where
he was.
"And I am the agent of the new proprietor," said Anton.
"That does not concern me," growled the shaggy man, turning sharp round,
entering the house, and bolting the door within.
Anton was thoroughly roused. "Break the window in, and help me to catch
the rascal," cried he to Karl, who coolly seized a piece of wood, struck
the panes so as to make the rotten framework give way, and cleared the
opening at one leap. Anton followed him. The room was empty, so was the
next, and in it an open window--the man was gone.
"After him!" cried Karl, and dashed on in pursuit, while Anton looked
about the house and out-buildings. He soon heard the barking of a dog,
and saw Karl capture the fugitive. Hurrying to his help, he held the man
fast, while, with a kick, Karl sent the dog flying. They then contrived
to force the steward back to the house, though he kept striking out
violently all the way.
"Go to the tavern, and bring the gendarme and the landlord," cried Anton
to the driver, who, undisturbed by all that had been going on, had
meanwhile unpacked the carriage. The man accordingly drove leisurely
off, and the fugitive being got into the room, Karl found an old cloth,
and with it bound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I beg your pardon, sir,"
said he; "it is only for an hour or so, till the arrival of the Rosmin
gendarme, whom we have appointed to meet us."
Anton then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house, bu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found but the merest necessaries; no books nor papers of any kind. It
had doubtless been emptied already. A bundle projected from the
coat-pocket of the prisoner, which turned out to be receipts and legal
documents in Polish. In time, the driver returned with the landlord and
the armed policeman. The landlord stood at the door in some perplexity,
and the policeman explained in a few moments what remained to be done.
"You must make a statement to the local judge, and give the man up to
me. He shall go back in your carriage to Rosmin. You will do well to get
rid of him, for this is a wild country, and it will be safer for you to
have him at Rosmin than here, where he has friends and accomplices."
After a long search, a sheet of paper was found in a cupboard, the
statement made and submitted to the policeman, who shook his head a
little over the Polish composition, and the prisoner lifted into the
carriage, the gendarme taking his seat beside him, and saying to Anton,
"I have long expected something of the kind. You may have often occasion
to want me again." The carriage then drove away, and thus the property
came under Anton's administration. He felt as if cast on a desert
island.
His portmanteau and traveling effects were leaning against a mud wall,
and the Polish landlord was the only man who could give him and Karl any
information or advice in their forlorn condition.
Now that the steward was fairly gone, the landlord grew more
communicative, and showed himself serviceable and obliging. A long
conversation ensued, and its purport was what Anton had apprehended from
the warning given by the Commissary Walter and other Rosmin officials.
The inspector had,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done all he could in the
way of spoliation, rendered daring by a report which had found its way
from the town to the village, that the present proprietor would never be
able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estate. At last Anton said, "What that
wretched man has done away with he will have to account for; our first
care must be to preserve what is still to be found on the property. You
must be our guide to-day."
They then examined the empty buildings. Four horses and two
servants--they were gone into the wood--a few old plows, a pair of
harrows, two wagons, a britzska, a cellar full of potatoes, a few
bundles of hay, a little straw--the inventory did not take much time in
drawing up. The buildings were all out of repair, not through age, but
neglect.
"Where is the dwelling-house?" inquired Anton. The landlord led the way
out of the yard to the meadow--a broad plain, gradually sloping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brook. It had been a great pasture. The cattle had
trodden it down into holes; the snouts of greedy swine had rooted it up;
gray molehills and rank tufts of grass rose on all sides.
The landlord stretched out his hand. "There is the castle. This castle
i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he added, reverentially; "no
nobleman in the district has a stone house like that. All the gentry
here live in wood and mud buildings. Herr von Tarow, the richest of
them, has but a poor dwelling."
About three hundred yards from the last out-building rose a great brick
edifice, with a black slate roof and a thick round tower. Its gloomy
walls on this treeless pasture-land, without one trace of life around,
rose beneath the cloudy sky like a phantom fortress which some evil
spirit had evoked from the abyss--a station from which to blight all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The strangers approached it. The castle had fallen into ruins before the
builders had finished their task. The tower had stood there for ages. It
was built of unhewn stone, and had small windows and loop-holes. The
former lords of the land had looked down from its summit on the tops of
the trees, which then stretched far into the plain. They had then ruled
with a rod of iron the serfs who cultivated their land, and toiled and
died for them. Many an arrow had sped through those loop-holes at the
enemy storming below, and many a Tartar horse had been overthrown before
those massive walls. Years ago, a despot of the district had, in
expiation of former sins, begun to add to the gray tower the walls of a
holy monastery; but the monastery never got finished, and the useless
walls had already stood there long, when the late count took it into his
head to convert them into a lordly dwelling for his race, and to raise a
house unparalleled for magnificence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 front of the house was added on to both sides of the tower, which
projected in the middle. The intention had been to have a high
terrace-road up to the castle, and the principal entrance had been made
in the tower, and arched over; but the terrace never having been formed,
the stone threshold of the main door was quite inacce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ladders, and the wide opening was left. The window-spaces of
the lower floor were merely closed up with boards, while on the second
story were some window-frames of beautifully carved wood, in which large
panes had once been placed, but they had got broken. In other windows
were temporary frames of rough deal, with small panes of muddy glass let
into them. A company of jackdaws sat on the top of the tower, looking
down in amazement on the strangers, and every now and then one flew off,
screaming loudly, to contemplate the intruders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A house for crows and bats, not for human beings," said Anton. "At
least, I see no way of getting into it."
The landlord now took them round the building. Behind, where the two
wings made a sort of horse-shoe, there were low entrances to the cellars
and offices; beneath which, again, were stables, great arched kitchens,
and small cells for the serfs. A wooden staircase led to the upper
story. The door turned creaking on its hinges, and a narrow passage took
them through a side wing to the front part of the house. There all was
at least magnificently planned. The circular entrance-hall--an arched
room of the old tower--was painted in mosaic, and through the great
doorway-opening was seen a wide expans
small disturbance made by the return of Anton had gradually settled
down. Those first-class treasures of Sabine's had made way for other
specimens of damask, still of a superior kind, it is true, but which
came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e elderly cousin's comprehension. She had
been quite right in prophesying that Anton would never remark those
signs of exuberant gratitude or their withdrawal. However, one change
had been permanently made--the greatest, the best of all changes--the
clerk retained a privileged place in the heart of the young mistress of
the firm, and his tall figure often appeared as one of the circle that
Sabine's fancy loved to gather round her when at her work-table or in
her treasure-chamber.
To-day she was walking restlessly up and down before dinner. The cousin,
who heard every thing, had just told her that a maid from Ehrenthal's
had run into the office to announce Bernhard's death to his friend. "How
will he bear it?" thought she. And the name of Ehrenthal forced her
thoughts back to the past, to one now far away, and to that painful hour
when the struggle going on in her own mind had been suddenly brought to
a close by a letter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parted. And Anton had known
of that conquered feeling of hers. How considerate he had always been,
how chivalrous, how helpful! She wondered if he had any idea of the
completeness of her triumph over a girlish illusion. She shook her head.
"No, he has not. It was here, at this very table, that an accident first
betrayed me to him. That past time still rises like a cloud between us.
Whenever I sit near Wohlfart of an evening, I am conscious of another's
shadow at my side; and when he speaks to me, his tone, his manner always
seem to say, 'You are not alone; he is with you.'" Sabine started, and
lovingly passed her hand over the beautiful flowers on the table before
her, as if to dispel a painful thought. She could not tell him that she
was free from that long-felt sorrow. Now, however, when he had lost a
friend whom he so much loved, she must show him that there were other
hearts that clung to him still. And again she walked up and down, trying
to devise a way of speaking to him alone.
Dinner was announced. Anton came with the rest, and took his place at
once. There was no opportunity of exchanging a word during the meal, but
he often met her sad and sympathizing eye. "He eats nothing at all
to-day," whispered her cousin; "not even any of the roast," she added,
reproachfully. Sabine was much perturbed. Mr. Jordan had already risen;
Anton would leave the room with the rest, and she should not see him
again the whole day through. So she called out, "The great Calla is
fully blown now. You were admiring the buds the other day; will you
remain a moment; I should like to show it you?" Anton bowed and staid
behind. A few more awkward moments, then her brother rose too; and,
hurrying to Anton, she took him to the room where the flowers were.
"You have had sorrowful tidings to-day," she began.
"The tidings themselves did not surprise me," replied Anton. "The doctor
gave no hope. But I lose much in him."
"I never saw him," said Sabine; "but I know from you that his life was
lonely--poor in affection and in enjoyment."
She moved an arm-chair toward Anton, and led him on to talk about his
friend. She listened to every word with warm sympathy, and well knew
what to ask and how to comfort. It was a relief to Anton to speak of the
departed one, to describe his quiet way of life, his erudition, his
poetical enthusiasm. After a pause, Sabine looked up frankly into his
face, and asked, "Have you any tidings of Herr von Fink?"
It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his departure that she had ever breathed his
name. Anton felt how touching her confidence was, given in this hour of
his sadness. In his emotion, he seized her hand, which she was slow in
withdrawing.
"He is not happy in his new life," he gravely replied. "There was a
savage humor in his last letter, from which I gather, even more than
from his actual words, that the business into which his uncle's death
has thrown him does not suit him."
"It is unworthy," cried Sabine.
"At all events, it is not what would be recognized as honorable in this
house," replied Anton. "Fink is upright, and has lived too long with
your brother to take pleasure in the wild speculations so common on the
other side the Atlantic. His partners and colleagues are for the most
part men without a conscience, and his feelings revolt against their
companionship."
"And can Herr von Fink tolerate such relations as these for a day?"
"It is a remarkable thing that he whose own will was ever so arbitrarily
exercised, should now be obliged against that will to obey a pressure
from without, and every where to work with his hands tied. The
organization of such speculations in America is so complicated that one
shareholder can do little to alter it; and, now that Fink has attained
what used to be the goal of his wishes--a large capital, and the
management of immense districts--his condition appears more uncertain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He was always in danger of thinking slightingly
of others, now I am distressed at the bitter contempt he expresses for
his own life. His last letter paints an intolerable state of things, and
seems to point to some decisive resolve."
"There is only one resolve for him," cried Sabine. "May I ask what you
said to him in reply?"
"I entreated him instantly, come what would, to free himself from the
business in which he was entangled. I said that his own strong will
might find a way of extrication, even if that which I pointed out proved
impracticable. Then I begged of him either to carry out his old plan of
becoming a landed proprietor in America, or to return to us."
"I knew that you would write thus," said Sabine, drawing a long breath.
"Yes, Wohlfart, he shall return," said she, gently, "but he shall not
return to us."
Anton was silent.
"And do you think that Herr von Fink will follow your advice?"
"I do not know. My advice was not very American."
"But it was worthy of you," cried Sabine, with proud delight.
"An officer wishes to speak to Mr. Wohlfart," said a servant at the
door.
Anton sprang up. Sabine went to her flowers and bent mournfully over
them. The shadows of others hovered still between her friend and her.
The few words spoken by the servant filled Anton with a vague terror. He
hurried into the ante-room: there stood Eugene von Rothsattel. Anton was
gladly rushing forward to greet him, but the young soldier's face of
agony made him start back. He whispered, "My mother wishes to speak to
you; something dreadful has occurred." Anton caught up his hat, ran into
the office, hurriedly asked Baumann to excuse him to the principal, and
then accompanied the lieutenant to the baron's house.
On the way, Eugene, who had lost all self-command, said unconnectedly to
Anton, "My father last night accidentally wounded himself by a
pistol-shot--a messenger was sent to summon me--when I came, I found my
mother in a swoon--my sister and I do not know what to do--Lenore
implored my mother on her knees to send for you--you are the only one in
whom w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our distress--I understand nothing about
business, but my father's affairs must be in a dreadful state--my mother
is beside herself--the whole house is in the greatest disorder."
From what Eugene said and what he did not say; from his broken sentences
and his look of agony, Anton guessed at the horrors of the previous
evening. In the boudoir of the baroness he found Lenore, weeping and
exhausted.
"Dear Wohlfart!" cried she, taking his hand and beginning again to sob,
while her head sank powerless on his shoulder.
Meanwhile Eugene walked up and down, wringing his hands, and at length
throwing himself on the sofa, he gave himself up to silent tears.
"It is horrible, Mr. Wohlfart," said Lenore, lifting up her head. "No
one may approach my father--Eugene may not, nor I--only my mother and
old John are with him; and early this morning the merchant Ehrenthal was
here, insisting that he must see my father. He screamed at my mother,
and called my father a deceiver, till she fainted away. When I rushed
into the room, the dreadful man went off threatening her with his
clenched fist."
Anton led Lenore to a chair and waited till she had told him all.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comforting in this case, and his own heart was
wrung to the utmost by the misery he witnessed.
"Call my mother, Eugene," said Lenore, at length.
Her brother left the room.
"Do not forsake us," implored Lenore, clasping her hands; "we are at the
last gasp; even your help can not save us."
"He is dead who might perhaps have done so," mournfully replied Anton.
"Whether I can be of any use I know not, but you can not doubt my
willingness to be so."
"No," cried Lenore. "And Eugene, too, thought of you at once."
The baroness now entered. She walked wearily; but, steadying herself by
a chair, she saluted Anton with dignity. "In our position," said she,
"we need a friend who knows more of business than we three do.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prevents the baron--possibly for a long time to
come--from managing his own affairs, and, little as I understand them, I
can see that our interests require prompt measures. My children have
mentioned you to me, but I fear I am unreasonable in asking you to
devote your time to our service."
She sat down, beckoned Anton to take a chair, and said to her children,
"Leave us; I shall be better able to tell Mr. Wohlfart the little that I
know when I do not see your grief."
When they were alone, she motioned him nearer and tried to speak, but
her lips quivered, and she hid her face in her handkerchief.
"Before I can consent, gracious lady," said he, "to your reposing in me
such confidence as this, I must first inquire whether the baron has no
relative or intimate friend to whom you could with less pain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I pray you to remember that my own knowledge of business
is but small, and my position not one to constitute me a proper
counselor to the baron."
"I know no one," said the baroness, hopelessly. "It is less painful to
me to tell you what I can not conceal, than to one of our own circle.
Consider yourself a physician sent for to visit a patient. The baron has
this morning told me some particulars of his present circumstances." And
then she proceeded to relate what she had gathered as to the nature of
his embarrassments, the danger in which the family property was placed,
and the capital needed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Polish estate.
"My husband," continued she, "has given me the key of his desk, and he
wishes Eugene, with the help of a man of business, to go over his
papers. I now request of you to make this examination together with my
son. When you need explanations, I will try to obtain them from the
baron. The question is now, whether you are inclined to undertake this
trouble for us, who are only strangers."
"I am most willing to do so," earnestly replied Anton; "and I hope that
the kindness of my principal will allow me the time needful for the
purpose, if you do not consider it more advisable to depute the baron's
experienced legal adviser to the task."
"There will be an opportunity of asking that gentleman's advice later,"
said the baroness.
Anton rose. "When do you wish to begin?"
"Immediately. I fear there is not a day to lose. I shall do all I can to
help you look the papers over." She led Anton into the next room, called
in Eugene, and unlocked the baron's desk. As she opened it she lost her
self-command for a moment, and moving to the window, the quivering of
the curtains betrayed the anguish that shook her fragile frame.
The mournful task began. Hour after hour passed. Eugene was in no
condition to peruse any thing, but his mother reached letters and
documents to Anton, and, though often obliged to desist a while, she
bravely returned to the task. Anton placed the papers in order, and
sought, by glancing over each, to arrive at least at a superficial view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It was evening, when the old servant opened the door in dismay, and
called out, "He is there again." The baroness could not repress a slight
scream, and made a gesture of aversion.
"I have told him that no one is at home, but he will not be dismissed;
he makes such a noise on the steps. I can not get rid of him."
"It will kill me if I hear his voice again," murmured the baroness.
"If the man be Ehrenthal," said Anton, rising, "I will try to get him
away. We have now done what was most necessary; have the goodness to
lock up these papers, and to allow me to return to-morrow." The baroness
silently assented, and sank back in her chair. Anton hurried off to the
ante-room, whence he could hear Ehrenthal's loudly-raised voi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usurer shocked him. His hat pushed half off his
head, his pale face swelled as if by drinking, his glazed eyes red with
tears, Ehrenthal stood before him, calling in broken sentences for the
baron, wailing and cursing alternately. "He must come! he must come at
once!" cried he; "the wicked man! A nobleman, indeed! he is a vagabond,
after whom I will send the police. Where is my money? Where is my
security? I want my mortgage from this man who is not at home."
Anton went straight up to him, and asked, "Do you know me, Mr.
Ehrenthal?" Ehrenthal turned his glazed eyes upon him, and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 friend of his dead son.
"He loved you!" he cried, in a lamentable voice. "He spoke to you more
than to his father. You were the only friend that he had on earth. Have
you heard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house of Ehrenthal?" continued he, in
a whisper. "Just as they stole the papers he died. He died with a hand
like this," and clenching his fist he struck his forehead. "Oh my son!
my son! why didst not thou forgive thy father!"
"We will go to your son," said Anton, taking the arm of the old man, who
unresistingly allowed himself to be led back to his own house.
From thence Anton hurried to Councilor Horn, with whom he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It was late before he returned home. In the midst of his anxiety about
those whose prosperity had filled his imagination years before,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in their adversity, reposed in him, dilated his
breast with a feeling of pride. He burned with desire to help them, and
hoped that his zealous devotion might yet find some way of rescue. As
yet he saw none. Looking up at the great building before him, so firm
and secure, in the moonlight, a thought flashed into his mind. If any
man could help them, it was his principal. His keen eye would be able to
unravel all the dark secrets in which the baron was entangled, and his
iron strength of will would crush the villains who held the unfortunate
nobleman in their power. And then he had a noble nature; he always
decided on the right, without an effort or a struggle. Anton looked at
the first floor. The whole house-front was dark, but in a corner room a
light still burned. It was the private office of his chief.
With sudden resolve, Anton begged the servant to take him to Mr.
Schröter, who looked with amazement at the unexpected visitor, and asked
what brought him, and whether any thing had happened.
"I implore your counsel--I implore your help," cried Anton.
"For yourself or for others?" inquired the merchant.
"For a family with whom I have accidentally become connected. They are
lost if a strong hand does not ward off the impending catastrophe."
Anton then rapidly related the occurrences of the afternoon, and,
seizing his principal's hand in his emotion, cried, "Have pity upon the
unhappy ladies, and help them."
"Help them!" replied the merchant; "how can I? Have you been
commissioned to apply to me, or are you only following the impulse of
your own feelings?"
"I am not commissioned; it is only the interest that I take in the
baron's fate which leads me to you."
"And what right have you to inform me of facts communicated in strict
confidence to yourself by the baron's lady?" asked the merchant, dryly.
"I am committing no indiscretion in telling you what will, in a few
days, be no secret, even to strangers."
"You are unusually excited, otherwise you would not forget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hatever, does a man of business venture to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without the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Of course, I shall make no wrong use of what you have said, but it was
by no means business-like, Wohlfart, to be so open toward me."
Anton was silent, feeling, indeed, that his principal was right, but yet
it seemed hard to be blamed for reposing confidence at such a time as
this. The merchant walked silently up and down; at length, stopping
before Anton, he said, "I do not now inquire how you come to take so
warm an interest in this family. I fear it is an acquaintance you owe to
Fink."
"You shall hear all," said Anton.
"Not at present. I will now content myself with repeating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interfere in these affairs without being specially
applied to by the parties themselves. I may add that I by no means wish
for such an application, and do not disguise from you that, were it
made, I should probably decline to do any thing for the Baron
Rothsattel."
Anton's feelings were roused to the utmost. "The question is the rescue
of an honorable man, and of lovely and amiable women from the toils of
rogues and impostors. To me, this seems the duty of every one; I, at
least, consider it a sacred obligation which I dare not shrink from. But
without your support I can do nothing."
"And how do you think this embarrassed man can be helped?" inquired the
merchant, seating himself.
With somewhat more composure, Anton repli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an experienced man of business making himself master of the case. There
must be some way of circumventing these villains. Your penetration would
discover it."
"Any attorney would be far more likely to do so, and the baron might
readily engage the services of experienced and upright legal advisers.
If his enemies have done any thing illegal, the quick eye of a lawyer is
the most likely to detect it."
"Alas! the baron's own lawyer gives but little hope," replied Anton.
"Then, my dear Wohlfart, no other is likely to do much good. Show me an
embarrassed man who has strength to grasp an offered hand, and bid me
help him, and for the sake of all I owe you, I will not refuse to do so.
I think you are convinced of this."
"I am," said Anton, dejectedly.
"From all I hear, however," the merchant went on,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the baron. From what I gather from general report, as well as from
you, his embarrassments arise from his having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usurers, which proves him deficient in what alone ennobles the life of
any man--good sense, and the power of steady exertion."
Anton could only sigh his assent.
"To help such a man," inexorably continued the merchant, "is a futile
attempt, against which reason may well protest. We are not to despair of
any, but want of strength is the most hopeless case of all. Our power of
laboring for others being limited, it becomes our duty to inquire,
before we devote our time to the weak, whether we are not thus
diminishing our chances of helping better men."
Anton interrupted him. "Does he not deserve every allowance to be made
for him? He was brought up to exact much; he has not learned, as we
have, to make his way by his own labor."
The merchant laid his hand on the young man's shoulder. "The very
reason. Believe me, a large number of these landed gentry, who pay the
penalty of their old family memories, are beyond help. I am the last to
deny that many worthy and admirable men belong to this class. Indeed,
wherever remarkable talent or nobility of character shoots up among
them, no doubt their position offers peculiar scope for its development,
but for average men it is not a favorable one. He who considers it his
hereditary privilege to enjoy life, and who assumes a distinguished
position in virtue of his family, will very often fail to put forth his
whole strength in order to deserve that position. Accordingly, numbers
of our oldest families are declining, and their fall will be no loss to
the state. Their family associations make them haughty without any
right to be so--limit their perceptions and confuse their judgment."
"Even if all this be true," cried Anton, "it does not absolve us from
helping individuals of the class who have excited our sympathy."
"No," said the principal, "if it be excited. But it does not glow so
rapidly in advancing years as in youth. The baron has endeavored to
isolate his property from the current of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leave it forever to his family. Forever! You, as a merchant, know how to
estimate the attempt. True, every rational man must allow it to be
desirable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same soil should be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We all prize what our forefathers have possessed before
us, and Sabine would unlock every room in this house with pride, because
her great-great-grandmother turned the same keys before her. It is
therefore natural that the landed proprietor should desire to preserve
those familiar scenes, which are the source of his own prosperity, to
those nearest and dearest to him. But there must be means to this end,
and these means are the making his own existence available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increase of his patrimony. Where energy dies in families
or individuals, then it is well that their means die too, that their
money should circulate through other hands, and their plowshare pass to
those who can guide it better. A family that has become effete through
luxury ought to sink down into common life, to make room for the
uprising of fresh energies and faculties. Every one who seeks, at the
cost of free activity for others, to preserve permanent possessions and
privileges for himself or his family, I must look upon as an enemy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social state. And if such a man ruin
himself in his endeavors, I should feel no malicious pleasure in his
downfall, but I should say that he is rightly served, because he has
sinned against a fundamental law of our social being; consequently, I
should consider it doubly wrong to support this man, because I could but
fear that I should thus be supporting an unsound condition of the body
politic."
Anton looked down mournfully. He had expected sympathy and warm
concurrence, and he met with disaffection and coldness that he despaired
of conquering. "I can not gainsay you," he at length replied; "but in
this case I can not feel as you do. I have been witness to the
unspeakable distress in the baron's family, and my whole soul is full
of sadness and sympathy, and of the wish to do something for those who
have opened their heart to me. After what you have said, I dare no
longer ask you to trouble yourself with their affairs, but I have
promised the baroness to assist her as far as my small powers permit,
and your kindness allows. I implore you to grant me permission to do
this. I shall endeavor to be regular in my attendance at the office, but
if during the next few weeks I am occasionally absent, I must ask you to
excuse me."
Once more the merchant walked up and down the room, and then, looking at
Anton's excited face, with deep seriousness and something of regret, he
replied, "Remember, Wohlfart, that every occupation which excites the
mind soon obtains a hold over a man, which may retard as well as advance
his success in life. It is thi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 to agree
to your wishes."
"I know it," said Anton, in a low voice; "but I have now no choice
left."
"Well, then, do what you must," said the merchant, gloomily; "I will lay
no hinderance in your way; and I hope that after a few weeks you will be
able to consider the whole circumstances more calmly." Anton left the
room, and the merchant stood looking long with frowning brow at the
place his clerk had occupied.
Nor was Anton in a more congenial mood. "So cold, so inexorable!"
exclaimed he, as he reached his own room. He began to suspect that his
principal was more selfish and less kindly than he had hitherto
supposed. Many an expression of Fink's recurred to his mind, as well as
that evening when young Rothsattel, in his boyish conceit, had spoken
impertinently to the merchant. "Is it possible," thought he, "that that
rude speech should be unforgotten?" And his chief's keen, deep-furrowed
face lost inexpressibly by contrast with the fair forms of the noble
ladies. "I am not wrong," he cried to himself; "let him say what he
will, my views are more just than his, and henceforth my destiny shall
be to choose for myself the way in which I shall walk." He sat long in
the darkness, and his thoughts were gloomy as it; then he went to the
window to look down into the dark court below. A great white blossom
rose before him like a phantom. Striking a light, he saw that it was the
beautiful Calla out of Sabine's room. It hung down mournfully on its
broken stem. Sabine had had it placed there. This little circumstance
struck him as a mournful omen.
Meanwhile Sabine, taper in hand, entered her brother's room.
"Good-night, Traugott," nodded she. "Wohlfart has been with you this
evening; how long he staid!"
"He will leave us," replied the merchant, gloomily.
Sabine started and dropped her taper on the table. "For God's sake, what
has happened? Has Wohlfart said that he was going away?"
"I do not yet know it, but I see it coming step by step; and I can not,
and still less can you, do any thing to retain him. When he stood before
me here with glowing cheeks and trembling voice, pleading for a ruined
man, I found out what it was that lured him away."
"I do not understand you," said Sabine, looking full at her brother.
"He chooses to become the confidential friend of a decayed noble. A pair
of bright eyes draws him away from us: it seems to him a worthy object
of ambition to become Rothsattel's man of business. This intimacy with
nobility is the legacy bequeathed to him by Fink."
"And you have refused to help him?" inquired Sabine, in a low voice.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said the merchant, harshly; and he
turned to his writing-table.
Sabine slowly withdrew. The taper trembled in her hand as she passed
through the long suite of rooms listening to her own footfall, and
shuddering as the feeling came over her that an invisible companion
glided by her side. This was the revenge of that other. The shadow that
once fell on her innocent life now drove her friend away from their
circle. Anton's affections clung to another. She had but been in his
eyes a mere stranger, who had once loved and languished for one now far
away, and who now, in widow's weeds, looked back regretfully to the
feelings of her youth.
The few next weeks were spent by Anton in over-hard work. He had great
difficulty in keeping up his counting-house duties, while he spent every
spare hour in conference with the baroness and the lawyer.
In the mean time, the misfortunes of the baron ran their course. He had
not been able to pay the interest of the sums with which his estate was
burdened. When last they were due, a whole series of claims was brought
against him, and the estate fell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district authorities. Complicated lawsuits arose. Ehrenthal complained
loudly, claiming the first mortgage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nay, he
was inclined to advance claims on the last mortgage offered by the baron
in the recent fatal hour. Löbel Pinkus also appeared as claimant of the
first mortgage, and asserted that he had paid the whole sum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Ehrenthal had no proof to bring forward, and had been
for some weeks past quite unable to manage his own affairs, while
Pinkus, on the contrary, fought with every weapon a hardened sinner can
devise or employ, and the deeds which the baron had executed at Veitel's
suggestion proved to be so capital a master-stroke of the cunning
advocate, that the baron's man of business had, from the first, little
hope of the case. We may here observe that Pinkus did eventually win it,
and that the mortgage was made over to him.
Anton was now gradually gaining some insight into the baron's
circumstances. But the double sale of the first mortgage was still kept
a secret by the latter, even from his wife. He declared Ehrenthal's
claim unfounded, and even expressed a suspicion that he had himself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robbery in his office. Indeed, he really
believed this. Then the name of Itzig was never broached, and the
suspicion against Ehrenthal, which the baron's lawyer shared, prevented
Anton seeking any explanation from him.
Meanwhile, an estrangement had sprung up between our hero and his
principal, which the whole counting-house remarked with surprise. The
merchant scowled at Anton's vacant seat when the latter chanced to be
absent during office-hours, or looked coldly at his clerk's face, made
pale as it was with excitement of mind and night-work. He took no notice
of his new occupation, and never seemed to remark him. Even to his
sister he maintained a stiff-necked silence; nor could all her attempts
lead him to speak of Anton, who, on his side, felt his heart revolt
against this coldness. After his return, to be treated like a child of
the house, praised, promoted, petted, and now to be treated like a mere
hireling, who is not worth the bread thrown to him; to be a toy of an
incomprehensible caprice--this, at least, he had not deserved; so he
became reserved toward the whole family, and sat silent at his desk; but
he fel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now and the then so keenly, that often,
when alone, he would spring up and stamp on the ground in the bitter
indignation of his heart.
One comfort remained. Sabine was not estranged. True, he saw little of
her, and at dinner she seemed to avoid speaking to him, but he knew that
she was on his side.
A few days after his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the merchant, she came down
stairs as he stood in the hall, and had to pass him by so closely that
her dress touched him. He had retreated, and made a formal bow, but she
looked at him imploringly, and whispered, "You must not be estranged
from me." It was an affair of a moment, but the faces of both were
radiant with a happy understanding.
The time had now arrived when Mr. Jordan was to quit the firm. The
principal again called Anton into his little office, and without any
severity, but also without a trace of his former cordiality, began: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o you my intention of appointing you Jordan's
successor; but,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your time has been more taken
up with other business than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such a post, I
therefore ask you whether you are now at liberty to undertake Jordan's
duties?"
"I am not," replied Anton.
"Can you name any--not very distant--time when you will be free from
your present occupation? In that case I will endeavor to find a
substitute until then."
Anton sorrowfully replied, "I can not at present say when I shall again
be master of my whole time; and, besides, I feel that, even as it is, I
tax your indulgence by many irregularities. Therefore, Mr. Schröter, I
beg that you will fill up this post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me."
The merchant's brow grew furrowed and dark, and he silently bowed
assent. Anton felt as he closed the door that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m was now complete, and, resuming his place, he leaned his throbbing
head on his hand. A moment later Baumann was summoned to the principal,
and Jordan's situation conferred upon him. On returning to the office,
he went up to Anton and whispered, "I refused at first, but Mr. Schröter
insisted. I am doing you an injustice." And that evening Mr. Baumann, in
his own room, read in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the chapters treating of
the unjust Saul (the principal), and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Jonathan
and the persecuted David, and strengthened his heart thereby.
The next day Anton was summoned to the baroness. Lenore and her mother
sat before a large table covered with jewel-boxes and toilette elegances
of every description, while a heavy iron chest stood at their feet. The
curtains were drawn, and the subdued light shone softly into the richly
furnished room. On the carpet glowed wreaths of unfading flowers, and
the clock ticked cheerfully in its alabaster case. Under the shade of
flowering plants sat the two love-birds in their silvered cage, hopping
from perch to perch, screaming ceaselessly, or sitting up quietly close
to each other. The whole room was beauty and perfume. "For how long?"
thought Anton. The baroness rose. "We are already obliged to trouble you
again," said she; "we are engaged in a very painful occupation." On the
table were all manner of ornaments, gold chains, brilliants, rings,
necklaces, gathered into a heap.
"We have been looking out all that we can dispense with," said the
baroness, "and now pray you to undertake to sell these things for us. I
have been told that some of them are of value, and as we are now in much
need of money, we turn here for help."
Anton looked in perplexity at the glittering heap.
"Tell us, Wohlfart," cried Lenore, anxiously, "is this necessary? can it
be of any use? Mamma has insisted upon setting apart for sale all our
ornaments, and whatever plate is not in daily use. What I can give is
not worth talking of, but my mother's jewels are costly; many of them
were presents made to her in youth, which she shall not part with unless
you say that it is necessary."
"I fear," said Anton, gravely, "that it will prove so."
"Take them," said the baroness to Anton; "I shall be calmer when I know
that we have at least done what we could."
"But do you wish to part with all?" inquired Anton, anxiously. "Much
that is dear to you may have but little value in a jeweler's eyes."
"I shall never wear an ornament again," quietly replied the baroness.
"Take them all;" and, holding her hands before her eyes, she turned
away.
"We are torturing my mother," cried Lenore, hastily; "will you lock up
all that is on the table, and get them out of the house as soon as you
can?"
"I can not undertake the charge of these valuables," said Anton,
"without taking some measures to decrease my own responsibility. First
of all, I will in your presence make a short note of all you intrust to
me."
"What useless cruelty!" exclaimed Lenore.
"It will not take long."
Anton took out a few sheets from his pocket-book, and began to note down
the different articles.
"You shall not see it done, mother," said Lenore, drawing her mother
away, and then returning to watch Anton at his task.
"These preparations for the market are horrible," said she. "My mother's
whole life will be sold; some memory of hers is linked with every single
thing. Look, Wohlfart, the princess gave her this diamond ornament when
she married my father."
"They are magnificent brilliants," cried Anton, admiringly.
"This ring was my grandfather's, and these are presents of poor papa's.
Alas! no man can know how we love all these things. It was always a
festival to me when mamma put on her diamonds. Now we come to my
possessions. They are not worth much. Do you think this bracelet good
gold?" She held out her hand as she spoke.
"I do not know."
"It shall go with the rest," said Lenore, taking it off. "Yes, you are a
kind, good man, Wohlfart," continued she, looking trustfully into his
tearful eyes; "do not forsake us. My brother has no experience, and is
more helpless than we are. It is a frightful position for me. Before
mamma I do all I can to be composed, else I could scream and weep the
whole day through." She sank in a chair, still holding his hand. "Dear
Wohlfart, do not forsake us."
Anton bent over her, and looked with passionate emotion at the lovely
face that turned so trustfully to him in the midst of its tears.
"I will be helpful to you when I can," said he, in the fullness of his
heart. "I will be at hand whenever you need me. You have too good an
opinion of my information and my faculties; I can be of less assistance
to you than you suppose, but what I can, that I will do in any and every
possible way."
Their hands parted with a warm pressure; the affair was settled.
The baroness now returned. "Our lawyer was with me this morning," said
she; "and now I must ask for your opinion on another subject. He tells
me that there is no prospect of preserving the baron's family estate."
"At this time, when interest is high, and money difficult to get, none,"
replied Anton.
"And you, too, think that we must turn all our efforts toward preserving
the Polish property?"
"I do," was the answer.
"For that, also, money will be necessary. Perhaps I may be able through
my relatives to intrust you with a small sum, which, with the help of
that"--she pointed to the iron chest--"may suffice to cover the first
necessary expenses. I do not, however, wish to sell the jewels here, and
a journey to the residence would be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cure the
sum to which I have just alluded. The baron's lawyer has spoken most
highly of your capacity for business. It is his wish which now decides
me to make a proposal to you. Will you for the next few years, or, at
all events, until our greatest difficulties are over, devote your whole
time to our affairs? I have consulted my children, and they agree with
me in believing that in your assistance lies our only hope of rescue.
The baron, too, has come in to the plan. The question now is whether
your circumstances allow you to give your support to our unfortunate
family. We shall be grateful to you, whatever conditions you affix; and
if you can find any way of making our great obligations to you apparent
in the position you hold, pray impart it to me."
Anton stood petrified. What the baroness required of him was separation
from the firm, separation from his principal, and from Sabine! Had this
thought occurred to him before, when standing in Lenore's presence or
bending over the baron's papers? At all events, now that the words were
spoken, they shocked him. He looked at Lenore, who stood behind her
mother with hands clasped in supplication. At length he replied, "I
stand in a position which I can not leav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others.
I was not prepared for this proposal, and beg to have time allowed me
for consideration. It is a step which will decide my whole future life."
"I do not press you," said the baroness; "I only request your
consideration. Whatever your decision be, our warmest gratitude will
still be yours; if you are unable to uphold our feeble strength, I fear
that we shall find no one to do so. You will think of that," she added,
beseechingly.
Anton hurried through the street with throbbing pulse. The noble lady's
glance of entreaty, Lenore's folded hands, beckoned him out of the
gloomy counting-house into a sphere of greater liberty, into a new
future, from whose depths bright images flashed out upon his fancy. A
request had been frankly made, and he was strongly inclined to justify
the confidence that prompted it. Those ladies required an unwearied,
self-sacrificing helper to save them from utter ruin, and if he
followed his impulse he should be doing a good work--fulfilling a duty.
In this mood he entered the merchant's dwelling. Alas! all that he saw
around him seemed to stretch out a hand to detain him. As he looked at
the warehouse, the good-humored faces of the porters, the chains of the
great scales, the hieroglyphics of the worthy Pix, again he felt that
this was the place that he belonged to. Sabine's dog kissed his hand,
and ran before him to his room--his and Fink's room. Here the childish
heart of the orphan boy had found a friend, kind companions, a home, a
definite and honorable life-purpose. Looking down through his window on
all the long-familiar objects, he saw a light in Sabine's store-chamber.
How often he had sought for that light, which brightened the whole great
building, and brought a sense of comfort and cheerfulness even into his
room. He now sprang up suddenly, and said to himself, "She shall
decide."
Sabine started in amazement when Anton appeared before her. "I am
irresistibly impelled to seek you," cried he. "I have to decide upon my
future life, and I feel undetermined, and unable to trust to my own
judgment. You have always been a kind friend to me since the day of my
arrival. I am accustomed to look up to you, and to think of you in
connection with all that interests me here. Let me hear your opinion
from your own lips. The Baroness Rothsattel has to-day proposed to me
permanently to undertake the situation of confidential adviser and
manager of the baron's affairs. Shall I accept; or shall I remain here?
I know not--tell me what is right both for myself and others."
"Not I," said Sabine, drawing back and growing very pale. "I can not
venture to decide in the matter. Nor do you wish me to do so, Wohlfart,
for you have already decided."
Anton looked straight before him and was silent.
"You have thought of leaving this house, and a wish to do so has sprung
out of the thought. And I am to justify you, and approve your resolve!
This is what you require of me," continued she, bitterly. "But this,
Wohlfart, I can not do, for I am sorry that you go away from us."
She turned away from him and leaned on the back of a chair.
"Oh, be not angry with me too!" said Anton; "that I can not bear. I have
suffered much of late. Mr. Schröter has suddenly withdrawn from me the
friendly regard that I long held my life's greatest treasure. I have not
deserved his coldness. What I have been doing has not been wrong, and
it was done with his knowledge. I had been spoiled by his kindness; I
have the more deeply felt his displeasure. My only comfort has been that
you did not condemn me. And now, do not you be cold toward me, else I
shall be wretched forever. There is not a soul on earth to whom I can
turn for affectionate comprehension of my difficulties. Had I a sister,
I should seek her heart to-day. You do not know what to me, lonely as I
am, your smile, your kindly shake of the hand has been till now. Do not
turn coldly from me, I beseech you."
Sabine was silent. At length she inquired, still with averted face,
"What draws you to those strangers; is it a joyful hope, is it sympathy
alone? Give this question close consideration before you answer it to
yourself at least."
"What it is that makes it possible for me to leave this house," said
Anton, "I do not myself know. If I can give a name to my motives, it is
gratitude felt toward one. She was the first to speak kindly to the
wandering boy on his way out into the world. I have admired her in the
peaceful brightness of her former life. I have often dreamed childish
dreams about her. There was a time when a tender feeling for her filled
my whole heart, and I then believed myself forever the slave of her
image. But years bring changes, and I learned to look on men and on life
with other eyes. Then I met her again, distressed, unhappy, despairing,
and my compassion became overmastering. When I am away from her, I know
that she is nothing to me; when I am with her, I feel only the spell of
her sorrow. Once, when I had to depart out of her circle like a culprit,
she came to me, and before the whole scornful assembly she gave me her
hand and acknowledged me her friend; and now she comes and asks for my
hand to help her father. Can I refuse it? Is it wrong to feel as I do? I
know not, and no one can tell me--no one but you alone."
Sabine's head had sunk down to the back of the chair on which she bent.
She now suddenly raised it, and with tearful eyes, and a voice full of
love and sorrow, cried, "Follow the voice that calls you. Go, Wohlfart,
go."
CHAPTER XXVII.
On a cold October day, two men were seen driving through the latticed
gate of the town of Rosmin on toward the plain, which stretched out
before them monotonous and boundless. Anton sat wrapped in his fur coat,
his hat low on his forehead, and at his side was young Sturm, in an old
cavalry cloak, with his soldier's cap cocked cheerily on one side. In
front of them a farm-servant, squatted on a heap of straw, flogged on
the small horses. The wind swept the sand and straw from the
stubble-fields, the road was a broad causeway without ditches or hedges,
the horses had to wade alternately through puddles and deep sand. Yellow
sand gleamed through the scanty herbage in all directions wherever a
field-mouse had made her way to her nest or an active mole had done what
he could to diversify the unbroken plain. Wherever the ground sank,
stagnant water lodged, and there hollow willow-trees stretched their
crippled arms in the air, their boughs flapping in the wind, and their
faded leaves fluttering down into the muddy pool below. Here and there
stood a small dwarf pine, a resting-place for the crows, who, scared by
the passing carriage, flew loudly croaking over the travelers' heads.
There was no house to be seen on the road, no pedestrian, and no
conveyance of any kind.
Karl looked every now and then at his silent companion, and said at
last, pointing to the horses, "How rough their coats are, and how pretty
their gray mouse skins! I wonder how many of these beasties would go to
make up my sergeant's horse! When I took leave of my father, the old man
said, 'Perhaps I shall pay you a visit, little one, when they light the
Christmas-tree.' 'You'll never be able,' said I. 'Why not?' asked he.
'You'll never trust yourself in any post-chaise.' Then the old boy
cried, 'Oho! post-chaises are always of a stout build; I shall be sure
to trust myself in one.' But now, Mr. Anton, I see that my father never
can pay us a visit."
"Why not?"
"It is possible that he may reach Rosmin; but, as soon as he sees these
horses and this road, he will instantly turn back. 'Shall I trust
myself,' he'll say, 'in a district where sand runs between one's legs
like water, and where mice are put into harness? The ground is not firm
enough for me.'"
"The horses are not the worst things here," said Anton, absently. "Look!
these go fast enough."
"Yes," replied Karl, "but they don't go like regular horses; they
entangle their legs like two cats playing in a parsley-bed. And what
things they have for shoes--regular webbed hoofs, I declare, which no
blacksmith can ever fit."
"If we could only get on!" returned Anton; "the wind blows cold, and I
am shivering in spite of my fur."
"You have slept but little the last few nights, sir," said Karl. "The
wind blows here as if over a threshing-floor. The earth is not round
hereabouts as elsewhere, but flat as a cake. This is a complete desert;
we have been driving for more than an hour, and there is not a village
to be seen."
"A desert indeed," sighed Anton; "let us hope it may improve." They
relapsed into profound silence. At length the driver stopped near a
pool, unharnessed the horses, and led them to the water's edge, without
noticing the travelers.
"What the deuce does this mean?" cried Karl, jumping down from the
carriage.
"I am going to feed," replied the servant, sulkily, in a foreign accent.
"I am anxious to know how that will be done," said Karl. "There is not
the shadow of a bag of provender."
The horses, however, soon proved that they could live without corn; they
stretched down their shaggy heads, and began to pull the grass and weeds
at the edge of the pool, sometimes taking a draught of the dirty water.
Meanwhile the servant drew a bundle from under his seat, settled himself
under the lee of an alder-bush, and, taking his knife, cut his bread and
cheese without even glancing at the travelers.
"I say, Ignatius or Jacob," cried Karl, sharply, "how long will this
breakfast of yours last?"
"An hour," replied the man, munching away.
"And how far is it from here to the estate?"
"Six miles, or maybe more."
"You can make nothing of him," said Anton; "we must put up with the
customs of the country;" and, leaving the carriage, they went to look on
at the horses feeding.
Anton is on his way to the Polish property. He is now the baron's agent.
Anxious months have the last proved to him. The parting from his
principal and the firm had been painful in the extreme. For some time
before it, indeed, Anton had found himself alone in the midst of his
colleagues. The quiet Baumann still remained his friend, but the others
considered him a castaway. The merchant received his resignation with
icy coldness; and even in the hour of parting, his hand lay impassive as
metal in Anton's grasp. Since then, our hero had undertaken several
journeys to the capital and to creditors in the family's behalf, and now
he was on his way to set the new estate in order, accompanied by Karl,
whom he had induced to become the baron's bailiff.
Ehrenthal had, by the authority conferred on him,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from the time of the sale by auction, and hired the Polish
bailiff for the baron. There had been unfair dealings between them at
the time, and it was well known in Rosmin that the bailiff had sold off
a good deal, and been guilty of all sorts of frauds since, so that Anton
had even now no prospect of a quiet life.
"The hour is come when I may execute my commission," cried Karl, groping
in the straw under the seat. He drew out a large japanned tin case, and
carried it to Anton. "Miss Sabine gave me this in charge for you." He
then joyously opened the lid, produced the materials for an excellent
breakfast, a bottle of wine, and a silver goblet. Anton took hold of the
case.
"It has a very knowing look," said Karl. "Miss Sabine planned it
herself."
Anton examined it on all sides, and placed it carefully on a tuft of
grass; then he took up the goblet, and saw his initials engraved on it,
and underneath the words, "To thy welfare." Whereupon he forgot the
breakfast and all around him, and stood gazing at the goblet, lost in
thought.
"Do not forget the breakfast, sir," suggested Karl, respectfully.
"Sit down by me, my faithful friend; eat and drink with me. Leave off
your absurd politeness. We shall have but little, either of us, but what
we have we will share like brothers. Take the bottle if you have no
glass."
"There's nothing like leather," said Karl, taking a small leathern
drinking-cup out of his pocket. "As for 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t was
kindly meant, and I thank you; but there must be subordination, if it
were but for the sake of the others; and so, sir, be kind enough to let
me shake hands with you now, and then let things be as they were before.
Only look at the horses, Mr. Anton. My faith! the creatures devour
thistles."
Again the horses were harnessed, again they threw out their short legs
in the sand, and again the carriage rolled through the barren
district--first through an empty plain, next through a wretched
fir-wood, then past a row of low sand-hills, then over a tumble-down
bridge crossing a small stream.
"This is the property," said the driver, turning round, and pointing
with his whip to a row of dirty thatched roofs that had just come into
sight.
Anton stood up to look for the group of trees in which the Hall might be
supposed to stand. Nothing of the sort to be seen. The village was
deficient in all that adorns the home of the poorest German peasant--no
orchard, no hedged-in gardens, no lime-trees in the market-place.
"This is wretched," said he, sitting down again; "much worse than they
told us in Rosmin."
"The village looks as if under a curse," cried Karl; "no teams working
in the fields--not a cow or a sheep to be seen."
The farm-servant flogged his horses into an irregular gallop, and so
they passed through the rows of mud huts which constituted the village,
and arrived at the public house. Karl sprang from the carriage, opened
the tavern door, and called for the landlord. A Jew slowly rose from his
seat by the stove and came to the threshold. "Is the gendarme from
Rosmin come?" He is gone into the village. "Which is the way to the
farm-yard?"
The landlord, an elderly man with an intelligent countenance, described
the way in German and Polish, and remained standing at the
door--bewildered, Karl declared, by the sight of two human beings. The
carriage turned into a cross-road, planted on both sides with thick
bushes, the remains of a fallen avenue. Over holes, stones, and puddles,
it rattled on to a group of mud huts, which still had a remnant of
whitewash upon them. "The barns and stables are empty," cried Karl, "for
I see gaps in the roofs large enough to drive our carriage through."
Anton said no more; he was prepared for every thing. They drove through
a break between the stables into the farm-yard, a large irregular space,
surrounded on three sides by tumble-down buildings, and open to the
fields on the fourth. A heap of _débris_ lay there--lime and rotten
timber, the remains of a ruined barn. The yard was empty; no trace of
farm implements or human labor to be seen. "Which is the inspector's
house," inquired Anton, in dismay. The driver looked round, and at last
made up his mind that it was a small one-storied building, with straw
thatch and dirty windows.
At the noise of the wheels a man appeared on the threshold, and waited
phlegmatically till the travelers had dismounted, and were standing
close before him. He was a broad-shouldered fellow, with a bloated,
brandy-drinking face, dressed in a jacket of shaggy cloth, while behind
him peered the muzzle of an equally shaggy dog, who snarled at the
strangers. "Are you the steward of this property?"
"I am," replied the man, in broken German, without stirring from where
he was.
"And I am the agent of the new proprietor," said Anton.
"That does not concern me," growled the shaggy man, turning sharp round,
entering the house, and bolting the door within.
Anton was thoroughly roused. "Break the window in, and help me to catch
the rascal," cried he to Karl, who coolly seized a piece of wood, struck
the panes so as to make the rotten framework give way, and cleared the
opening at one leap. Anton followed him. The room was empty, so was the
next, and in it an open window--the man was gone.
"After him!" cried Karl, and dashed on in pursuit, while Anton looked
about the house and out-buildings. He soon heard the barking of a dog,
and saw Karl capture the fugitive. Hurrying to his help, he held the man
fast, while, with a kick, Karl sent the dog flying. They then contrived
to force the steward back to the house, though he kept striking out
violently all the way.
"Go to the tavern, and bring the gendarme and the landlord," cried Anton
to the driver, who, undisturbed by all that had been going on, had
meanwhile unpacked the carriage. The man accordingly drove leisurely
off, and the fugitive being got into the room, Karl found an old cloth,
and with it bound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I beg your pardon, sir,"
said he; "it is only for an hour or so, till the arrival of the Rosmin
gendarme, whom we have appointed to meet us."
Anton then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house, bu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found but the merest necessaries; no books nor papers of any kind. It
had doubtless been emptied already. A bundle projected from the
coat-pocket of the prisoner, which turned out to be receipts and legal
documents in Polish. In time, the driver returned with the landlord and
the armed policeman. The landlord stood at the door in some perplexity,
and the policeman explained in a few moments what remained to be done.
"You must make a statement to the local judge, and give the man up to
me. He shall go back in your carriage to Rosmin. You will do well to get
rid of him, for this is a wild country, and it will be safer for you to
have him at Rosmin than here, where he has friends and accomplices."
After a long search, a sheet of paper was found in a cupboard, the
statement made and submitted to the policeman, who shook his head a
little over the Polish composition, and the prisoner lifted into the
carriage, the gendarme taking his seat beside him, and saying to Anton,
"I have long expected something of the kind. You may have often occasion
to want me again." The carriage then drove away, and thus the property
came under Anton's administration. He felt as if cast on a desert
island.
His portmanteau and traveling effects were leaning against a mud wall,
and the Polish landlord was the only man who could give him and Karl any
information or advice in their forlorn condition.
Now that the steward was fairly gone, the landlord grew more
communicative, and showed himself serviceable and obliging. A long
conversation ensued, and its purport was what Anton had apprehended from
the warning given by the Commissary Walter and other Rosmin officials.
The inspector had,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done all he could in the
way of spoliation, rendered daring by a report which had found its way
from the town to the village, that the present proprietor would never be
able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estate. At last Anton said, "What that
wretched man has done away with he will have to account for; our first
care must be to preserve what is still to be found on the property. You
must be our guide to-day."
They then examined the empty buildings. Four horses and two
servants--they were gone into the wood--a few old plows, a pair of
harrows, two wagons, a britzska, a cellar full of potatoes, a few
bundles of hay, a little straw--the inventory did not take much time in
drawing up. The buildings were all out of repair, not through age, but
neglect.
"Where is the dwelling-house?" inquired Anton. The landlord led the way
out of the yard to the meadow--a broad plain, gradually sloping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brook. It had been a great pasture. The cattle had
trodden it down into holes; the snouts of greedy swine had rooted it up;
gray molehills and rank tufts of grass rose on all sides.
The landlord stretched out his hand. "There is the castle. This castle
i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he added, reverentially; "no
nobleman in the district has a stone house like that. All the gentry
here live in wood and mud buildings. Herr von Tarow, the richest of
them, has but a poor dwelling."
About three hundred yards from the last out-building rose a great brick
edifice, with a black slate roof and a thick round tower. Its gloomy
walls on this treeless pasture-land, without one trace of life around,
rose beneath the cloudy sky like a phantom fortress which some evil
spirit had evoked from the abyss--a station from which to blight all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The strangers approached it. The castle had fallen into ruins before the
builders had finished their task. The tower had stood there for ages. It
was built of unhewn stone, and had small windows and loop-holes. The
former lords of the land had looked down from its summit on the tops of
the trees, which then stretched far into the plain. They had then ruled
with a rod of iron the serfs who cultivated their land, and toiled and
died for them. Many an arrow had sped through those loop-holes at the
enemy storming below, and many a Tartar horse had been overthrown before
those massive walls. Years ago, a despot of the district had, in
expiation of former sins, begun to add to the gray tower the walls of a
holy monastery; but the monastery never got finished, and the useless
walls had already stood there long, when the late count took it into his
head to convert them into a lordly dwelling for his race, and to raise a
house unparalleled for magnificence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 front of the house was added on to both sides of the tower, which
projected in the middle. The intention had been to have a high
terrace-road up to the castle, and the principal entrance had been made
in the tower, and arched over; but the terrace never having been formed,
the stone threshold of the main door was quite inacce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ladders, and the wide opening was left. The window-spaces of
the lower floor were merely closed up with boards, while on the second
story were some window-frames of beautifully carved wood, in which large
panes had once been placed, but they had got broken. In other windows
were temporary frames of rough deal, with small panes of muddy glass let
into them. A company of jackdaws sat on the top of the tower, looking
down in amazement on the strangers, and every now and then one flew off,
screaming loudly, to contemplate the intruders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A house for crows and bats, not for human beings," said Anton. "At
least, I see no way of getting into it."
The landlord now took them round the building. Behind, where the two
wings made a sort of horse-shoe, there were low entrances to the cellars
and offices; beneath which, again, were stables, great arched kitchens,
and small cells for the serfs. A wooden staircase led to the upper
story. The door turned creaking on its hinges, and a narrow passage took
them through a side wing to the front part of the house. There all was
at least magnificently planned. The circular entrance-hall--an arched
room of the old tower--was painted in mosaic, and through the great
doorway-opening was seen a wide expans
small disturbance made by the return of Anton had gradually settled
down. Those first-class treasures of Sabine's had made way for other
specimens of damask, still of a superior kind, it is true, but which
came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e elderly cousin's comprehension. She had
been quite right in prophesying that Anton would never remark those
signs of exuberant gratitude or their withdrawal. However, one change
had been permanently made--the greatest, the best of all changes--the
clerk retained a privileged place in the heart of the young mistress of
the firm, and his tall figure often appeared as one of the circle that
Sabine's fancy loved to gather round her when at her work-table or in
her treasure-chamber.
To-day she was walking restlessly up and down before dinner. The cousin,
who heard every thing, had just told her that a maid from Ehrenthal's
had run into the office to announce Bernhard's death to his friend. "How
will he bear it?" thought she. And the name of Ehrenthal forced her
thoughts back to the past, to one now far away, and to that painful hour
when the struggle going on in her own mind had been suddenly brought to
a close by a letter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parted. And Anton had known
of that conquered feeling of hers. How considerate he had always been,
how chivalrous, how helpful! She wondered if he had any idea of the
completeness of her triumph over a girlish illusion. She shook her head.
"No, he has not. It was here, at this very table, that an accident first
betrayed me to him. That past time still rises like a cloud between us.
Whenever I sit near Wohlfart of an evening, I am conscious of another's
shadow at my side; and when he speaks to me, his tone, his manner always
seem to say, 'You are not alone; he is with you.'" Sabine started, and
lovingly passed her hand over the beautiful flowers on the table before
her, as if to dispel a painful thought. She could not tell him that she
was free from that long-felt sorrow. Now, however, when he had lost a
friend whom he so much loved, she must show him that there were other
hearts that clung to him still. And again she walked up and down, trying
to devise a way of speaking to him alone.
Dinner was announced. Anton came with the rest, and took his place at
once. There was no opportunity of exchanging a word during the meal, but
he often met her sad and sympathizing eye. "He eats nothing at all
to-day," whispered her cousin; "not even any of the roast," she added,
reproachfully. Sabine was much perturbed. Mr. Jordan had already risen;
Anton would leave the room with the rest, and she should not see him
again the whole day through. So she called out, "The great Calla is
fully blown now. You were admiring the buds the other day; will you
remain a moment; I should like to show it you?" Anton bowed and staid
behind. A few more awkward moments, then her brother rose too; and,
hurrying to Anton, she took him to the room where the flowers were.
"You have had sorrowful tidings to-day," she began.
"The tidings themselves did not surprise me," replied Anton. "The doctor
gave no hope. But I lose much in him."
"I never saw him," said Sabine; "but I know from you that his life was
lonely--poor in affection and in enjoyment."
She moved an arm-chair toward Anton, and led him on to talk about his
friend. She listened to every word with warm sympathy, and well knew
what to ask and how to comfort. It was a relief to Anton to speak of the
departed one, to describe his quiet way of life, his erudition, his
poetical enthusiasm. After a pause, Sabine looked up frankly into his
face, and asked, "Have you any tidings of Herr von Fink?"
It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his departure that she had ever breathed his
name. Anton felt how touching her confidence was, given in this hour of
his sadness. In his emotion, he seized her hand, which she was slow in
withdrawing.
"He is not happy in his new life," he gravely replied. "There was a
savage humor in his last letter, from which I gather, even more than
from his actual words, that the business into which his uncle's death
has thrown him does not suit him."
"It is unworthy," cried Sabine.
"At all events, it is not what would be recognized as honorable in this
house," replied Anton. "Fink is upright, and has lived too long with
your brother to take pleasure in the wild speculations so common on the
other side the Atlantic. His partners and colleagues are for the most
part men without a conscience, and his feelings revolt against their
companionship."
"And can Herr von Fink tolerate such relations as these for a day?"
"It is a remarkable thing that he whose own will was ever so arbitrarily
exercised, should now be obliged against that will to obey a pressure
from without, and every where to work with his hands tied. The
organization of such speculations in America is so complicated that one
shareholder can do little to alter it; and, now that Fink has attained
what used to be the goal of his wishes--a large capital, and the
management of immense districts--his condition appears more uncertain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He was always in danger of thinking slightingly
of others, now I am distressed at the bitter contempt he expresses for
his own life. His last letter paints an intolerable state of things, and
seems to point to some decisive resolve."
"There is only one resolve for him," cried Sabine. "May I ask what you
said to him in reply?"
"I entreated him instantly, come what would, to free himself from the
business in which he was entangled. I said that his own strong will
might find a way of extrication, even if that which I pointed out proved
impracticable. Then I begged of him either to carry out his old plan of
becoming a landed proprietor in America, or to return to us."
"I knew that you would write thus," said Sabine, drawing a long breath.
"Yes, Wohlfart, he shall return," said she, gently, "but he shall not
return to us."
Anton was silent.
"And do you think that Herr von Fink will follow your advice?"
"I do not know. My advice was not very American."
"But it was worthy of you," cried Sabine, with proud delight.
"An officer wishes to speak to Mr. Wohlfart," said a servant at the
door.
Anton sprang up. Sabine went to her flowers and bent mournfully over
them. The shadows of others hovered still between her friend and her.
The few words spoken by the servant filled Anton with a vague terror. He
hurried into the ante-room: there stood Eugene von Rothsattel. Anton was
gladly rushing forward to greet him, but the young soldier's face of
agony made him start back. He whispered, "My mother wishes to speak to
you; something dreadful has occurred." Anton caught up his hat, ran into
the office, hurriedly asked Baumann to excuse him to the principal, and
then accompanied the lieutenant to the baron's house.
On the way, Eugene, who had lost all self-command, said unconnectedly to
Anton, "My father last night accidentally wounded himself by a
pistol-shot--a messenger was sent to summon me--when I came, I found my
mother in a swoon--my sister and I do not know what to do--Lenore
implored my mother on her knees to send for you--you are the only one in
whom w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our distress--I understand nothing about
business, but my father's affairs must be in a dreadful state--my mother
is beside herself--the whole house is in the greatest disorder."
From what Eugene said and what he did not say; from his broken sentences
and his look of agony, Anton guessed at the horrors of the previous
evening. In the boudoir of the baroness he found Lenore, weeping and
exhausted.
"Dear Wohlfart!" cried she, taking his hand and beginning again to sob,
while her head sank powerless on his shoulder.
Meanwhile Eugene walked up and down, wringing his hands, and at length
throwing himself on the sofa, he gave himself up to silent tears.
"It is horrible, Mr. Wohlfart," said Lenore, lifting up her head. "No
one may approach my father--Eugene may not, nor I--only my mother and
old John are with him; and early this morning the merchant Ehrenthal was
here, insisting that he must see my father. He screamed at my mother,
and called my father a deceiver, till she fainted away. When I rushed
into the room, the dreadful man went off threatening her with his
clenched fist."
Anton led Lenore to a chair and waited till she had told him all.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comforting in this case, and his own heart was
wrung to the utmost by the misery he witnessed.
"Call my mother, Eugene," said Lenore, at length.
Her brother left the room.
"Do not forsake us," implored Lenore, clasping her hands; "we are at the
last gasp; even your help can not save us."
"He is dead who might perhaps have done so," mournfully replied Anton.
"Whether I can be of any use I know not, but you can not doubt my
willingness to be so."
"No," cried Lenore. "And Eugene, too, thought of you at once."
The baroness now entered. She walked wearily; but, steadying herself by
a chair, she saluted Anton with dignity. "In our position," said she,
"we need a friend who knows more of business than we three do.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prevents the baron--possibly for a long time to
come--from managing his own affairs, and, little as I understand them, I
can see that our interests require prompt measures. My children have
mentioned you to me, but I fear I am unreasonable in asking you to
devote your time to our service."
She sat down, beckoned Anton to take a chair, and said to her children,
"Leave us; I shall be better able to tell Mr. Wohlfart the little that I
know when I do not see your grief."
When they were alone, she motioned him nearer and tried to speak, but
her lips quivered, and she hid her face in her handkerchief.
"Before I can consent, gracious lady," said he, "to your reposing in me
such confidence as this, I must first inquire whether the baron has no
relative or intimate friend to whom you could with less pain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I pray you to remember that my own knowledge of business
is but small, and my position not one to constitute me a proper
counselor to the baron."
"I know no one," said the baroness, hopelessly. "It is less painful to
me to tell you what I can not conceal, than to one of our own circle.
Consider yourself a physician sent for to visit a patient. The baron has
this morning told me some particulars of his present circumstances." And
then she proceeded to relate what she had gathered as to the nature of
his embarrassments, the danger in which the family property was placed,
and the capital needed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Polish estate.
"My husband," continued she, "has given me the key of his desk, and he
wishes Eugene, with the help of a man of business, to go over his
papers. I now request of you to make this examination together with my
son. When you need explanations, I will try to obtain them from the
baron. The question is now, whether you are inclined to undertake this
trouble for us, who are only strangers."
"I am most willing to do so," earnestly replied Anton; "and I hope that
the kindness of my principal will allow me the time needful for the
purpose, if you do not consider it more advisable to depute the baron's
experienced legal adviser to the task."
"There will be an opportunity of asking that gentleman's advice later,"
said the baroness.
Anton rose. "When do you wish to begin?"
"Immediately. I fear there is not a day to lose. I shall do all I can to
help you look the papers over." She led Anton into the next room, called
in Eugene, and unlocked the baron's desk. As she opened it she lost her
self-command for a moment, and moving to the window, the quivering of
the curtains betrayed the anguish that shook her fragile frame.
The mournful task began. Hour after hour passed. Eugene was in no
condition to peruse any thing, but his mother reached letters and
documents to Anton, and, though often obliged to desist a while, she
bravely returned to the task. Anton placed the papers in order, and
sought, by glancing over each, to arrive at least at a superficial view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It was evening, when the old servant opened the door in dismay, and
called out, "He is there again." The baroness could not repress a slight
scream, and made a gesture of aversion.
"I have told him that no one is at home, but he will not be dismissed;
he makes such a noise on the steps. I can not get rid of him."
"It will kill me if I hear his voice again," murmured the baroness.
"If the man be Ehrenthal," said Anton, rising, "I will try to get him
away. We have now done what was most necessary; have the goodness to
lock up these papers, and to allow me to return to-morrow." The baroness
silently assented, and sank back in her chair. Anton hurried off to the
ante-room, whence he could hear Ehrenthal's loudly-raised voi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usurer shocked him. His hat pushed half off his
head, his pale face swelled as if by drinking, his glazed eyes red with
tears, Ehrenthal stood before him, calling in broken sentences for the
baron, wailing and cursing alternately. "He must come! he must come at
once!" cried he; "the wicked man! A nobleman, indeed! he is a vagabond,
after whom I will send the police. Where is my money? Where is my
security? I want my mortgage from this man who is not at home."
Anton went straight up to him, and asked, "Do you know me, Mr.
Ehrenthal?" Ehrenthal turned his glazed eyes upon him, and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 friend of his dead son.
"He loved you!" he cried, in a lamentable voice. "He spoke to you more
than to his father. You were the only friend that he had on earth. Have
you heard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house of Ehrenthal?" continued he, in
a whisper. "Just as they stole the papers he died. He died with a hand
like this," and clenching his fist he struck his forehead. "Oh my son!
my son! why didst not thou forgive thy father!"
"We will go to your son," said Anton, taking the arm of the old man, who
unresistingly allowed himself to be led back to his own house.
From thence Anton hurried to Councilor Horn, with whom he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It was late before he returned home. In the midst of his anxiety about
those whose prosperity had filled his imagination years before,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in their adversity, reposed in him, dilated his
breast with a feeling of pride. He burned with desire to help them, and
hoped that his zealous devotion might yet find some way of rescue. As
yet he saw none. Looking up at the great building before him, so firm
and secure, in the moonlight, a thought flashed into his mind. If any
man could help them, it was his principal. His keen eye would be able to
unravel all the dark secrets in which the baron was entangled, and his
iron strength of will would crush the villains who held the unfortunate
nobleman in their power. And then he had a noble nature; he always
decided on the right, without an effort or a struggle. Anton looked at
the first floor. The whole house-front was dark, but in a corner room a
light still burned. It was the private office of his chief.
With sudden resolve, Anton begged the servant to take him to Mr.
Schröter, who looked with amazement at the unexpected visitor, and asked
what brought him, and whether any thing had happened.
"I implore your counsel--I implore your help," cried Anton.
"For yourself or for others?" inquired the merchant.
"For a family with whom I have accidentally become connected. They are
lost if a strong hand does not ward off the impending catastrophe."
Anton then rapidly related the occurrences of the afternoon, and,
seizing his principal's hand in his emotion, cried, "Have pity upon the
unhappy ladies, and help them."
"Help them!" replied the merchant; "how can I? Have you been
commissioned to apply to me, or are you only following the impulse of
your own feelings?"
"I am not commissioned; it is only the interest that I take in the
baron's fate which leads me to you."
"And what right have you to inform me of facts communicated in strict
confidence to yourself by the baron's lady?" asked the merchant, dryly.
"I am committing no indiscretion in telling you what will, in a few
days, be no secret, even to strangers."
"You are unusually excited, otherwise you would not forget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hatever, does a man of business venture to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without the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Of course, I shall make no wrong use of what you have said, but it was
by no means business-like, Wohlfart, to be so open toward me."
Anton was silent, feeling, indeed, that his principal was right, but yet
it seemed hard to be blamed for reposing confidence at such a time as
this. The merchant walked silently up and down; at length, stopping
before Anton, he said, "I do not now inquire how you come to take so
warm an interest in this family. I fear it is an acquaintance you owe to
Fink."
"You shall hear all," said Anton.
"Not at present. I will now content myself with repeating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interfere in these affairs without being specially
applied to by the parties themselves. I may add that I by no means wish
for such an application, and do not disguise from you that, were it
made, I should probably decline to do any thing for the Baron
Rothsattel."
Anton's feelings were roused to the utmost. "The question is the rescue
of an honorable man, and of lovely and amiable women from the toils of
rogues and impostors. To me, this seems the duty of every one; I, at
least, consider it a sacred obligation which I dare not shrink from. But
without your support I can do nothing."
"And how do you think this embarrassed man can be helped?" inquired the
merchant, seating himself.
With somewhat more composure, Anton repli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an experienced man of business making himself master of the case. There
must be some way of circumventing these villains. Your penetration would
discover it."
"Any attorney would be far more likely to do so, and the baron might
readily engage the services of experienced and upright legal advisers.
If his enemies have done any thing illegal, the quick eye of a lawyer is
the most likely to detect it."
"Alas! the baron's own lawyer gives but little hope," replied Anton.
"Then, my dear Wohlfart, no other is likely to do much good. Show me an
embarrassed man who has strength to grasp an offered hand, and bid me
help him, and for the sake of all I owe you, I will not refuse to do so.
I think you are convinced of this."
"I am," said Anton, dejectedly.
"From all I hear, however," the merchant went on,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the baron. From what I gather from general report, as well as from
you, his embarrassments arise from his having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usurers, which proves him deficient in what alone ennobles the life of
any man--good sense, and the power of steady exertion."
Anton could only sigh his assent.
"To help such a man," inexorably continued the merchant, "is a futile
attempt, against which reason may well protest. We are not to despair of
any, but want of strength is the most hopeless case of all. Our power of
laboring for others being limited, it becomes our duty to inquire,
before we devote our time to the weak, whether we are not thus
diminishing our chances of helping better men."
Anton interrupted him. "Does he not deserve every allowance to be made
for him? He was brought up to exact much; he has not learned, as we
have, to make his way by his own labor."
The merchant laid his hand on the young man's shoulder. "The very
reason. Believe me, a large number of these landed gentry, who pay the
penalty of their old family memories, are beyond help. I am the last to
deny that many worthy and admirable men belong to this class. Indeed,
wherever remarkable talent or nobility of character shoots up among
them, no doubt their position offers peculiar scope for its development,
but for average men it is not a favorable one. He who considers it his
hereditary privilege to enjoy life, and who assumes a distinguished
position in virtue of his family, will very often fail to put forth his
whole strength in order to deserve that position. Accordingly, numbers
of our oldest families are declining, and their fall will be no loss to
the state. Their family associations make them haughty without any
right to be so--limit their perceptions and confuse their judgment."
"Even if all this be true," cried Anton, "it does not absolve us from
helping individuals of the class who have excited our sympathy."
"No," said the principal, "if it be excited. But it does not glow so
rapidly in advancing years as in youth. The baron has endeavored to
isolate his property from the current of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leave it forever to his family. Forever! You, as a merchant, know how to
estimate the attempt. True, every rational man must allow it to be
desirable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same soil should be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We all prize what our forefathers have possessed before
us, and Sabine would unlock every room in this house with pride, because
her great-great-grandmother turned the same keys before her. It is
therefore natural that the landed proprietor should desire to preserve
those familiar scenes, which are the source of his own prosperity, to
those nearest and dearest to him. But there must be means to this end,
and these means are the making his own existence available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increase of his patrimony. Where energy dies in families
or individuals, then it is well that their means die too, that their
money should circulate through other hands, and their plowshare pass to
those who can guide it better. A family that has become effete through
luxury ought to sink down into common life, to make room for the
uprising of fresh energies and faculties. Every one who seeks, at the
cost of free activity for others, to preserve permanent possessions and
privileges for himself or his family, I must look upon as an enemy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social state. And if such a man ruin
himself in his endeavors, I should feel no malicious pleasure in his
downfall, but I should say that he is rightly served, because he has
sinned against a fundamental law of our social being; consequently, I
should consider it doubly wrong to support this man, because I could but
fear that I should thus be supporting an unsound condition of the body
politic."
Anton looked down mournfully. He had expected sympathy and warm
concurrence, and he met with disaffection and coldness that he despaired
of conquering. "I can not gainsay you," he at length replied; "but in
this case I can not feel as you do. I have been witness to the
unspeakable distress in the baron's family, and my whole soul is full
of sadness and sympathy, and of the wish to do something for those who
have opened their heart to me. After what you have said, I dare no
longer ask you to trouble yourself with their affairs, but I have
promised the baroness to assist her as far as my small powers permit,
and your kindness allows. I implore you to grant me permission to do
this. I shall endeavor to be regular in my attendance at the office, but
if during the next few weeks I am occasionally absent, I must ask you to
excuse me."
Once more the merchant walked up and down the room, and then, looking at
Anton's excited face, with deep seriousness and something of regret, he
replied, "Remember, Wohlfart, that every occupation which excites the
mind soon obtains a hold over a man, which may retard as well as advance
his success in life. It is thi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 to agree
to your wishes."
"I know it," said Anton, in a low voice; "but I have now no choice
left."
"Well, then, do what you must," said the merchant, gloomily; "I will lay
no hinderance in your way; and I hope that after a few weeks you will be
able to consider the whole circumstances more calmly." Anton left the
room, and the merchant stood looking long with frowning brow at the
place his clerk had occupied.
Nor was Anton in a more congenial mood. "So cold, so inexorable!"
exclaimed he, as he reached his own room. He began to suspect that his
principal was more selfish and less kindly than he had hitherto
supposed. Many an expression of Fink's recurred to his mind, as well as
that evening when young Rothsattel, in his boyish conceit, had spoken
impertinently to the merchant. "Is it possible," thought he, "that that
rude speech should be unforgotten?" And his chief's keen, deep-furrowed
face lost inexpressibly by contrast with the fair forms of the noble
ladies. "I am not wrong," he cried to himself; "let him say what he
will, my views are more just than his, and henceforth my destiny shall
be to choose for myself the way in which I shall walk." He sat long in
the darkness, and his thoughts were gloomy as it; then he went to the
window to look down into the dark court below. A great white blossom
rose before him like a phantom. Striking a light, he saw that it was the
beautiful Calla out of Sabine's room. It hung down mournfully on its
broken stem. Sabine had had it placed there. This little circumstance
struck him as a mournful omen.
Meanwhile Sabine, taper in hand, entered her brother's room.
"Good-night, Traugott," nodded she. "Wohlfart has been with you this
evening; how long he staid!"
"He will leave us," replied the merchant, gloomily.
Sabine started and dropped her taper on the table. "For God's sake, what
has happened? Has Wohlfart said that he was going away?"
"I do not yet know it, but I see it coming step by step; and I can not,
and still less can you, do any thing to retain him. When he stood before
me here with glowing cheeks and trembling voice, pleading for a ruined
man, I found out what it was that lured him away."
"I do not understand you," said Sabine, looking full at her brother.
"He chooses to become the confidential friend of a decayed noble. A pair
of bright eyes draws him away from us: it seems to him a worthy object
of ambition to become Rothsattel's man of business. This intimacy with
nobility is the legacy bequeathed to him by Fink."
"And you have refused to help him?" inquired Sabine, in a low voice.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said the merchant, harshly; and he
turned to his writing-table.
Sabine slowly withdrew. The taper trembled in her hand as she passed
through the long suite of rooms listening to her own footfall, and
shuddering as the feeling came over her that an invisible companion
glided by her side. This was the revenge of that other. The shadow that
once fell on her innocent life now drove her friend away from their
circle. Anton's affections clung to another. She had but been in his
eyes a mere stranger, who had once loved and languished for one now far
away, and who now, in widow's weeds, looked back regretfully to the
feelings of her youth.
The few next weeks were spent by Anton in over-hard work. He had great
difficulty in keeping up his counting-house duties, while he spent every
spare hour in conference with the baroness and the lawyer.
In the mean time, the misfortunes of the baron ran their course. He had
not been able to pay the interest of the sums with which his estate was
burdened. When last they were due, a whole series of claims was brought
against him, and the estate fell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district authorities. Complicated lawsuits arose. Ehrenthal complained
loudly, claiming the first mortgage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nay, he
was inclined to advance claims on the last mortgage offered by the baron
in the recent fatal hour. Löbel Pinkus also appeared as claimant of the
first mortgage, and asserted that he had paid the whole sum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Ehrenthal had no proof to bring forward, and had been
for some weeks past quite unable to manage his own affairs, while
Pinkus, on the contrary, fought with every weapon a hardened sinner can
devise or employ, and the deeds which the baron had executed at Veitel's
suggestion proved to be so capital a master-stroke of the cunning
advocate, that the baron's man of business had, from the first, little
hope of the case. We may here observe that Pinkus did eventually win it,
and that the mortgage was made over to him.
Anton was now gradually gaining some insight into the baron's
circumstances. But the double sale of the first mortgage was still kept
a secret by the latter, even from his wife. He declared Ehrenthal's
claim unfounded, and even expressed a suspicion that he had himself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robbery in his office. Indeed, he really
believed this. Then the name of Itzig was never broached, and the
suspicion against Ehrenthal, which the baron's lawyer shared, prevented
Anton seeking any explanation from him.
Meanwhile, an estrangement had sprung up between our hero and his
principal, which the whole counting-house remarked with surprise. The
merchant scowled at Anton's vacant seat when the latter chanced to be
absent during office-hours, or looked coldly at his clerk's face, made
pale as it was with excitement of mind and night-work. He took no notice
of his new occupation, and never seemed to remark him. Even to his
sister he maintained a stiff-necked silence; nor could all her attempts
lead him to speak of Anton, who, on his side, felt his heart revolt
against this coldness. After his return, to be treated like a child of
the house, praised, promoted, petted, and now to be treated like a mere
hireling, who is not worth the bread thrown to him; to be a toy of an
incomprehensible caprice--this, at least, he had not deserved; so he
became reserved toward the whole family, and sat silent at his desk; but
he fel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now and the then so keenly, that often,
when alone, he would spring up and stamp on the ground in the bitter
indignation of his heart.
One comfort remained. Sabine was not estranged. True, he saw little of
her, and at dinner she seemed to avoid speaking to him, but he knew that
she was on his side.
A few days after his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the merchant, she came down
stairs as he stood in the hall, and had to pass him by so closely that
her dress touched him. He had retreated, and made a formal bow, but she
looked at him imploringly, and whispered, "You must not be estranged
from me." It was an affair of a moment, but the faces of both were
radiant with a happy understanding.
The time had now arrived when Mr. Jordan was to quit the firm. The
principal again called Anton into his little office, and without any
severity, but also without a trace of his former cordiality, began: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o you my intention of appointing you Jordan's
successor; but,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your time has been more taken
up with other business than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such a post, I
therefore ask you whether you are now at liberty to undertake Jordan's
duties?"
"I am not," replied Anton.
"Can you name any--not very distant--time when you will be free from
your present occupation? In that case I will endeavor to find a
substitute until then."
Anton sorrowfully replied, "I can not at present say when I shall again
be master of my whole time; and, besides, I feel that, even as it is, I
tax your indulgence by many irregularities. Therefore, Mr. Schröter, I
beg that you will fill up this post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me."
The merchant's brow grew furrowed and dark, and he silently bowed
assent. Anton felt as he closed the door that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m was now complete, and, resuming his place, he leaned his throbbing
head on his hand. A moment later Baumann was summoned to the principal,
and Jordan's situation conferred upon him. On returning to the office,
he went up to Anton and whispered, "I refused at first, but Mr. Schröter
insisted. I am doing you an injustice." And that evening Mr. Baumann, in
his own room, read in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the chapters treating of
the unjust Saul (the principal), and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Jonathan
and the persecuted David, and strengthened his heart thereby.
The next day Anton was summoned to the baroness. Lenore and her mother
sat before a large table covered with jewel-boxes and toilette elegances
of every description, while a heavy iron chest stood at their feet. The
curtains were drawn, and the subdued light shone softly into the richly
furnished room. On the carpet glowed wreaths of unfading flowers, and
the clock ticked cheerfully in its alabaster case. Under the shade of
flowering plants sat the two love-birds in their silvered cage, hopping
from perch to perch, screaming ceaselessly, or sitting up quietly close
to each other. The whole room was beauty and perfume. "For how long?"
thought Anton. The baroness rose. "We are already obliged to trouble you
again," said she; "we are engaged in a very painful occupation." On the
table were all manner of ornaments, gold chains, brilliants, rings,
necklaces, gathered into a heap.
"We have been looking out all that we can dispense with," said the
baroness, "and now pray you to undertake to sell these things for us. I
have been told that some of them are of value, and as we are now in much
need of money, we turn here for help."
Anton looked in perplexity at the glittering heap.
"Tell us, Wohlfart," cried Lenore, anxiously, "is this necessary? can it
be of any use? Mamma has insisted upon setting apart for sale all our
ornaments, and whatever plate is not in daily use. What I can give is
not worth talking of, but my mother's jewels are costly; many of them
were presents made to her in youth, which she shall not part with unless
you say that it is necessary."
"I fear," said Anton, gravely, "that it will prove so."
"Take them," said the baroness to Anton; "I shall be calmer when I know
that we have at least done what we could."
"But do you wish to part with all?" inquired Anton, anxiously. "Much
that is dear to you may have but little value in a jeweler's eyes."
"I shall never wear an ornament again," quietly replied the baroness.
"Take them all;" and, holding her hands before her eyes, she turned
away.
"We are torturing my mother," cried Lenore, hastily; "will you lock up
all that is on the table, and get them out of the house as soon as you
can?"
"I can not undertake the charge of these valuables," said Anton,
"without taking some measures to decrease my own responsibility. First
of all, I will in your presence make a short note of all you intrust to
me."
"What useless cruelty!" exclaimed Lenore.
"It will not take long."
Anton took out a few sheets from his pocket-book, and began to note down
the different articles.
"You shall not see it done, mother," said Lenore, drawing her mother
away, and then returning to watch Anton at his task.
"These preparations for the market are horrible," said she. "My mother's
whole life will be sold; some memory of hers is linked with every single
thing. Look, Wohlfart, the princess gave her this diamond ornament when
she married my father."
"They are magnificent brilliants," cried Anton, admiringly.
"This ring was my grandfather's, and these are presents of poor papa's.
Alas! no man can know how we love all these things. It was always a
festival to me when mamma put on her diamonds. Now we come to my
possessions. They are not worth much. Do you think this bracelet good
gold?" She held out her hand as she spoke.
"I do not know."
"It shall go with the rest," said Lenore, taking it off. "Yes, you are a
kind, good man, Wohlfart," continued she, looking trustfully into his
tearful eyes; "do not forsake us. My brother has no experience, and is
more helpless than we are. It is a frightful position for me. Before
mamma I do all I can to be composed, else I could scream and weep the
whole day through." She sank in a chair, still holding his hand. "Dear
Wohlfart, do not forsake us."
Anton bent over her, and looked with passionate emotion at the lovely
face that turned so trustfully to him in the midst of its tears.
"I will be helpful to you when I can," said he, in the fullness of his
heart. "I will be at hand whenever you need me. You have too good an
opinion of my information and my faculties; I can be of less assistance
to you than you suppose, but what I can, that I will do in any and every
possible way."
Their hands parted with a warm pressure; the affair was settled.
The baroness now returned. "Our lawyer was with me this morning," said
she; "and now I must ask for your opinion on another subject. He tells
me that there is no prospect of preserving the baron's family estate."
"At this time, when interest is high, and money difficult to get, none,"
replied Anton.
"And you, too, think that we must turn all our efforts toward preserving
the Polish property?"
"I do," was the answer.
"For that, also, money will be necessary. Perhaps I may be able through
my relatives to intrust you with a small sum, which, with the help of
that"--she pointed to the iron chest--"may suffice to cover the first
necessary expenses. I do not, however, wish to sell the jewels here, and
a journey to the residence would be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cure the
sum to which I have just alluded. The baron's lawyer has spoken most
highly of your capacity for business. It is his wish which now decides
me to make a proposal to you. Will you for the next few years, or, at
all events, until our greatest difficulties are over, devote your whole
time to our affairs? I have consulted my children, and they agree with
me in believing that in your assistance lies our only hope of rescue.
The baron, too, has come in to the plan. The question now is whether
your circumstances allow you to give your support to our unfortunate
family. We shall be grateful to you, whatever conditions you affix; and
if you can find any way of making our great obligations to you apparent
in the position you hold, pray impart it to me."
Anton stood petrified. What the baroness required of him was separation
from the firm, separation from his principal, and from Sabine! Had this
thought occurred to him before, when standing in Lenore's presence or
bending over the baron's papers? At all events, now that the words were
spoken, they shocked him. He looked at Lenore, who stood behind her
mother with hands clasped in supplication. At length he replied, "I
stand in a position which I can not leav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others.
I was not prepared for this proposal, and beg to have time allowed me
for consideration. It is a step which will decide my whole future life."
"I do not press you," said the baroness; "I only request your
consideration. Whatever your decision be, our warmest gratitude will
still be yours; if you are unable to uphold our feeble strength, I fear
that we shall find no one to do so. You will think of that," she added,
beseechingly.
Anton hurried through the street with throbbing pulse. The noble lady's
glance of entreaty, Lenore's folded hands, beckoned him out of the
gloomy counting-house into a sphere of greater liberty, into a new
future, from whose depths bright images flashed out upon his fancy. A
request had been frankly made, and he was strongly inclined to justify
the confidence that prompted it. Those ladies required an unwearied,
self-sacrificing helper to save them from utter ruin, and if he
followed his impulse he should be doing a good work--fulfilling a duty.
In this mood he entered the merchant's dwelling. Alas! all that he saw
around him seemed to stretch out a hand to detain him. As he looked at
the warehouse, the good-humored faces of the porters, the chains of the
great scales, the hieroglyphics of the worthy Pix, again he felt that
this was the place that he belonged to. Sabine's dog kissed his hand,
and ran before him to his room--his and Fink's room. Here the childish
heart of the orphan boy had found a friend, kind companions, a home, a
definite and honorable life-purpose. Looking down through his window on
all the long-familiar objects, he saw a light in Sabine's store-chamber.
How often he had sought for that light, which brightened the whole great
building, and brought a sense of comfort and cheerfulness even into his
room. He now sprang up suddenly, and said to himself, "She shall
decide."
Sabine started in amazement when Anton appeared before her. "I am
irresistibly impelled to seek you," cried he. "I have to decide upon my
future life, and I feel undetermined, and unable to trust to my own
judgment. You have always been a kind friend to me since the day of my
arrival. I am accustomed to look up to you, and to think of you in
connection with all that interests me here. Let me hear your opinion
from your own lips. The Baroness Rothsattel has to-day proposed to me
permanently to undertake the situation of confidential adviser and
manager of the baron's affairs. Shall I accept; or shall I remain here?
I know not--tell me what is right both for myself and others."
"Not I," said Sabine, drawing back and growing very pale. "I can not
venture to decide in the matter. Nor do you wish me to do so, Wohlfart,
for you have already decided."
Anton looked straight before him and was silent.
"You have thought of leaving this house, and a wish to do so has sprung
out of the thought. And I am to justify you, and approve your resolve!
This is what you require of me," continued she, bitterly. "But this,
Wohlfart, I can not do, for I am sorry that you go away from us."
She turned away from him and leaned on the back of a chair.
"Oh, be not angry with me too!" said Anton; "that I can not bear. I have
suffered much of late. Mr. Schröter has suddenly withdrawn from me the
friendly regard that I long held my life's greatest treasure. I have not
deserved his coldness. What I have been doing has not been wrong, and
it was done with his knowledge. I had been spoiled by his kindness; I
have the more deeply felt his displeasure. My only comfort has been that
you did not condemn me. And now, do not you be cold toward me, else I
shall be wretched forever. There is not a soul on earth to whom I can
turn for affectionate comprehension of my difficulties. Had I a sister,
I should seek her heart to-day. You do not know what to me, lonely as I
am, your smile, your kindly shake of the hand has been till now. Do not
turn coldly from me, I beseech you."
Sabine was silent. At length she inquired, still with averted face,
"What draws you to those strangers; is it a joyful hope, is it sympathy
alone? Give this question close consideration before you answer it to
yourself at least."
"What it is that makes it possible for me to leave this house," said
Anton, "I do not myself know. If I can give a name to my motives, it is
gratitude felt toward one. She was the first to speak kindly to the
wandering boy on his way out into the world. I have admired her in the
peaceful brightness of her former life. I have often dreamed childish
dreams about her. There was a time when a tender feeling for her filled
my whole heart, and I then believed myself forever the slave of her
image. But years bring changes, and I learned to look on men and on life
with other eyes. Then I met her again, distressed, unhappy, despairing,
and my compassion became overmastering. When I am away from her, I know
that she is nothing to me; when I am with her, I feel only the spell of
her sorrow. Once, when I had to depart out of her circle like a culprit,
she came to me, and before the whole scornful assembly she gave me her
hand and acknowledged me her friend; and now she comes and asks for my
hand to help her father. Can I refuse it? Is it wrong to feel as I do? I
know not, and no one can tell me--no one but you alone."
Sabine's head had sunk down to the back of the chair on which she bent.
She now suddenly raised it, and with tearful eyes, and a voice full of
love and sorrow, cried, "Follow the voice that calls you. Go, Wohlfart,
go."
CHAPTER XXVII.
On a cold October day, two men were seen driving through the latticed
gate of the town of Rosmin on toward the plain, which stretched out
before them monotonous and boundless. Anton sat wrapped in his fur coat,
his hat low on his forehead, and at his side was young Sturm, in an old
cavalry cloak, with his soldier's cap cocked cheerily on one side. In
front of them a farm-servant, squatted on a heap of straw, flogged on
the small horses. The wind swept the sand and straw from the
stubble-fields, the road was a broad causeway without ditches or hedges,
the horses had to wade alternately through puddles and deep sand. Yellow
sand gleamed through the scanty herbage in all directions wherever a
field-mouse had made her way to her nest or an active mole had done what
he could to diversify the unbroken plain. Wherever the ground sank,
stagnant water lodged, and there hollow willow-trees stretched their
crippled arms in the air, their boughs flapping in the wind, and their
faded leaves fluttering down into the muddy pool below. Here and there
stood a small dwarf pine, a resting-place for the crows, who, scared by
the passing carriage, flew loudly croaking over the travelers' heads.
There was no house to be seen on the road, no pedestrian, and no
conveyance of any kind.
Karl looked every now and then at his silent companion, and said at
last, pointing to the horses, "How rough their coats are, and how pretty
their gray mouse skins! I wonder how many of these beasties would go to
make up my sergeant's horse! When I took leave of my father, the old man
said, 'Perhaps I shall pay you a visit, little one, when they light the
Christmas-tree.' 'You'll never be able,' said I. 'Why not?' asked he.
'You'll never trust yourself in any post-chaise.' Then the old boy
cried, 'Oho! post-chaises are always of a stout build; I shall be sure
to trust myself in one.' But now, Mr. Anton, I see that my father never
can pay us a visit."
"Why not?"
"It is possible that he may reach Rosmin; but, as soon as he sees these
horses and this road, he will instantly turn back. 'Shall I trust
myself,' he'll say, 'in a district where sand runs between one's legs
like water, and where mice are put into harness? The ground is not firm
enough for me.'"
"The horses are not the worst things here," said Anton, absently. "Look!
these go fast enough."
"Yes," replied Karl, "but they don't go like regular horses; they
entangle their legs like two cats playing in a parsley-bed. And what
things they have for shoes--regular webbed hoofs, I declare, which no
blacksmith can ever fit."
"If we could only get on!" returned Anton; "the wind blows cold, and I
am shivering in spite of my fur."
"You have slept but little the last few nights, sir," said Karl. "The
wind blows here as if over a threshing-floor. The earth is not round
hereabouts as elsewhere, but flat as a cake. This is a complete desert;
we have been driving for more than an hour, and there is not a village
to be seen."
"A desert indeed," sighed Anton; "let us hope it may improve." They
relapsed into profound silence. At length the driver stopped near a
pool, unharnessed the horses, and led them to the water's edge, without
noticing the travelers.
"What the deuce does this mean?" cried Karl, jumping down from the
carriage.
"I am going to feed," replied the servant, sulkily, in a foreign accent.
"I am anxious to know how that will be done," said Karl. "There is not
the shadow of a bag of provender."
The horses, however, soon proved that they could live without corn; they
stretched down their shaggy heads, and began to pull the grass and weeds
at the edge of the pool, sometimes taking a draught of the dirty water.
Meanwhile the servant drew a bundle from under his seat, settled himself
under the lee of an alder-bush, and, taking his knife, cut his bread and
cheese without even glancing at the travelers.
"I say, Ignatius or Jacob," cried Karl, sharply, "how long will this
breakfast of yours last?"
"An hour," replied the man, munching away.
"And how far is it from here to the estate?"
"Six miles, or maybe more."
"You can make nothing of him," said Anton; "we must put up with the
customs of the country;" and, leaving the carriage, they went to look on
at the horses feeding.
Anton is on his way to the Polish property. He is now the baron's agent.
Anxious months have the last proved to him. The parting from his
principal and the firm had been painful in the extreme. For some time
before it, indeed, Anton had found himself alone in the midst of his
colleagues. The quiet Baumann still remained his friend, but the others
considered him a castaway. The merchant received his resignation with
icy coldness; and even in the hour of parting, his hand lay impassive as
metal in Anton's grasp. Since then, our hero had undertaken several
journeys to the capital and to creditors in the family's behalf, and now
he was on his way to set the new estate in order, accompanied by Karl,
whom he had induced to become the baron's bailiff.
Ehrenthal had, by the authority conferred on him,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from the time of the sale by auction, and hired the Polish
bailiff for the baron. There had been unfair dealings between them at
the time, and it was well known in Rosmin that the bailiff had sold off
a good deal, and been guilty of all sorts of frauds since, so that Anton
had even now no prospect of a quiet life.
"The hour is come when I may execute my commission," cried Karl, groping
in the straw under the seat. He drew out a large japanned tin case, and
carried it to Anton. "Miss Sabine gave me this in charge for you." He
then joyously opened the lid, produced the materials for an excellent
breakfast, a bottle of wine, and a silver goblet. Anton took hold of the
case.
"It has a very knowing look," said Karl. "Miss Sabine planned it
herself."
Anton examined it on all sides, and placed it carefully on a tuft of
grass; then he took up the goblet, and saw his initials engraved on it,
and underneath the words, "To thy welfare." Whereupon he forgot the
breakfast and all around him, and stood gazing at the goblet, lost in
thought.
"Do not forget the breakfast, sir," suggested Karl, respectfully.
"Sit down by me, my faithful friend; eat and drink with me. Leave off
your absurd politeness. We shall have but little, either of us, but what
we have we will share like brothers. Take the bottle if you have no
glass."
"There's nothing like leather," said Karl, taking a small leathern
drinking-cup out of his pocket. "As for 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t was
kindly meant, and I thank you; but there must be subordination, if it
were but for the sake of the others; and so, sir, be kind enough to let
me shake hands with you now, and then let things be as they were before.
Only look at the horses, Mr. Anton. My faith! the creatures devour
thistles."
Again the horses were harnessed, again they threw out their short legs
in the sand, and again the carriage rolled through the barren
district--first through an empty plain, next through a wretched
fir-wood, then past a row of low sand-hills, then over a tumble-down
bridge crossing a small stream.
"This is the property," said the driver, turning round, and pointing
with his whip to a row of dirty thatched roofs that had just come into
sight.
Anton stood up to look for the group of trees in which the Hall might be
supposed to stand. Nothing of the sort to be seen. The village was
deficient in all that adorns the home of the poorest German peasant--no
orchard, no hedged-in gardens, no lime-trees in the market-place.
"This is wretched," said he, sitting down again; "much worse than they
told us in Rosmin."
"The village looks as if under a curse," cried Karl; "no teams working
in the fields--not a cow or a sheep to be seen."
The farm-servant flogged his horses into an irregular gallop, and so
they passed through the rows of mud huts which constituted the village,
and arrived at the public house. Karl sprang from the carriage, opened
the tavern door, and called for the landlord. A Jew slowly rose from his
seat by the stove and came to the threshold. "Is the gendarme from
Rosmin come?" He is gone into the village. "Which is the way to the
farm-yard?"
The landlord, an elderly man with an intelligent countenance, described
the way in German and Polish, and remained standing at the
door--bewildered, Karl declared, by the sight of two human beings. The
carriage turned into a cross-road, planted on both sides with thick
bushes, the remains of a fallen avenue. Over holes, stones, and puddles,
it rattled on to a group of mud huts, which still had a remnant of
whitewash upon them. "The barns and stables are empty," cried Karl, "for
I see gaps in the roofs large enough to drive our carriage through."
Anton said no more; he was prepared for every thing. They drove through
a break between the stables into the farm-yard, a large irregular space,
surrounded on three sides by tumble-down buildings, and open to the
fields on the fourth. A heap of _débris_ lay there--lime and rotten
timber, the remains of a ruined barn. The yard was empty; no trace of
farm implements or human labor to be seen. "Which is the inspector's
house," inquired Anton, in dismay. The driver looked round, and at last
made up his mind that it was a small one-storied building, with straw
thatch and dirty windows.
At the noise of the wheels a man appeared on the threshold, and waited
phlegmatically till the travelers had dismounted, and were standing
close before him. He was a broad-shouldered fellow, with a bloated,
brandy-drinking face, dressed in a jacket of shaggy cloth, while behind
him peered the muzzle of an equally shaggy dog, who snarled at the
strangers. "Are you the steward of this property?"
"I am," replied the man, in broken German, without stirring from where
he was.
"And I am the agent of the new proprietor," said Anton.
"That does not concern me," growled the shaggy man, turning sharp round,
entering the house, and bolting the door within.
Anton was thoroughly roused. "Break the window in, and help me to catch
the rascal," cried he to Karl, who coolly seized a piece of wood, struck
the panes so as to make the rotten framework give way, and cleared the
opening at one leap. Anton followed him. The room was empty, so was the
next, and in it an open window--the man was gone.
"After him!" cried Karl, and dashed on in pursuit, while Anton looked
about the house and out-buildings. He soon heard the barking of a dog,
and saw Karl capture the fugitive. Hurrying to his help, he held the man
fast, while, with a kick, Karl sent the dog flying. They then contrived
to force the steward back to the house, though he kept striking out
violently all the way.
"Go to the tavern, and bring the gendarme and the landlord," cried Anton
to the driver, who, undisturbed by all that had been going on, had
meanwhile unpacked the carriage. The man accordingly drove leisurely
off, and the fugitive being got into the room, Karl found an old cloth,
and with it bound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I beg your pardon, sir,"
said he; "it is only for an hour or so, till the arrival of the Rosmin
gendarme, whom we have appointed to meet us."
Anton then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house, bu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found but the merest necessaries; no books nor papers of any kind. It
had doubtless been emptied already. A bundle projected from the
coat-pocket of the prisoner, which turned out to be receipts and legal
documents in Polish. In time, the driver returned with the landlord and
the armed policeman. The landlord stood at the door in some perplexity,
and the policeman explained in a few moments what remained to be done.
"You must make a statement to the local judge, and give the man up to
me. He shall go back in your carriage to Rosmin. You will do well to get
rid of him, for this is a wild country, and it will be safer for you to
have him at Rosmin than here, where he has friends and accomplices."
After a long search, a sheet of paper was found in a cupboard, the
statement made and submitted to the policeman, who shook his head a
little over the Polish composition, and the prisoner lifted into the
carriage, the gendarme taking his seat beside him, and saying to Anton,
"I have long expected something of the kind. You may have often occasion
to want me again." The carriage then drove away, and thus the property
came under Anton's administration. He felt as if cast on a desert
island.
His portmanteau and traveling effects were leaning against a mud wall,
and the Polish landlord was the only man who could give him and Karl any
information or advice in their forlorn condition.
Now that the steward was fairly gone, the landlord grew more
communicative, and showed himself serviceable and obliging. A long
conversation ensued, and its purport was what Anton had apprehended from
the warning given by the Commissary Walter and other Rosmin officials.
The inspector had,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done all he could in the
way of spoliation, rendered daring by a report which had found its way
from the town to the village, that the present proprietor would never be
able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estate. At last Anton said, "What that
wretched man has done away with he will have to account for; our first
care must be to preserve what is still to be found on the property. You
must be our guide to-day."
They then examined the empty buildings. Four horses and two
servants--they were gone into the wood--a few old plows, a pair of
harrows, two wagons, a britzska, a cellar full of potatoes, a few
bundles of hay, a little straw--the inventory did not take much time in
drawing up. The buildings were all out of repair, not through age, but
neglect.
"Where is the dwelling-house?" inquired Anton. The landlord led the way
out of the yard to the meadow--a broad plain, gradually sloping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brook. It had been a great pasture. The cattle had
trodden it down into holes; the snouts of greedy swine had rooted it up;
gray molehills and rank tufts of grass rose on all sides.
The landlord stretched out his hand. "There is the castle. This castle
i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he added, reverentially; "no
nobleman in the district has a stone house like that. All the gentry
here live in wood and mud buildings. Herr von Tarow, the richest of
them, has but a poor dwelling."
About three hundred yards from the last out-building rose a great brick
edifice, with a black slate roof and a thick round tower. Its gloomy
walls on this treeless pasture-land, without one trace of life around,
rose beneath the cloudy sky like a phantom fortress which some evil
spirit had evoked from the abyss--a station from which to blight all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The strangers approached it. The castle had fallen into ruins before the
builders had finished their task. The tower had stood there for ages. It
was built of unhewn stone, and had small windows and loop-holes. The
former lords of the land had looked down from its summit on the tops of
the trees, which then stretched far into the plain. They had then ruled
with a rod of iron the serfs who cultivated their land, and toiled and
died for them. Many an arrow had sped through those loop-holes at the
enemy storming below, and many a Tartar horse had been overthrown before
those massive walls. Years ago, a despot of the district had, in
expiation of former sins, begun to add to the gray tower the walls of a
holy monastery; but the monastery never got finished, and the useless
walls had already stood there long, when the late count took it into his
head to convert them into a lordly dwelling for his race, and to raise a
house unparalleled for magnificence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 front of the house was added on to both sides of the tower, which
projected in the middle. The intention had been to have a high
terrace-road up to the castle, and the principal entrance had been made
in the tower, and arched over; but the terrace never having been formed,
the stone threshold of the main door was quite inacce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ladders, and the wide opening was left. The window-spaces of
the lower floor were merely closed up with boards, while on the second
story were some window-frames of beautifully carved wood, in which large
panes had once been placed, but they had got broken. In other windows
were temporary frames of rough deal, with small panes of muddy glass let
into them. A company of jackdaws sat on the top of the tower, looking
down in amazement on the strangers, and every now and then one flew off,
screaming loudly, to contemplate the intruders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A house for crows and bats, not for human beings," said Anton. "At
least, I see no way of getting into it."
The landlord now took them round the building. Behind, where the two
wings made a sort of horse-shoe, there were low entrances to the cellars
and offices; beneath which, again, were stables, great arched kitchens,
and small cells for the serfs. A wooden staircase led to the upper
story. The door turned creaking on its hinges, and a narrow passage took
them through a side wing to the front part of the house. There all was
at least magnificently planned. The circular entrance-hall--an arched
room of the old tower--was painted in mosaic, and through the great
doorway-opening was seen a wide expans
small disturbance made by the return of Anton had gradually settled
down. Those first-class treasures of Sabine's had made way for other
specimens of damask, still of a superior kind, it is true, but which
came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e elderly cousin's comprehension. She had
been quite right in prophesying that Anton would never remark those
signs of exuberant gratitude or their withdrawal. However, one change
had been permanently made--the greatest, the best of all changes--the
clerk retained a privileged place in the heart of the young mistress of
the firm, and his tall figure often appeared as one of the circle that
Sabine's fancy loved to gather round her when at her work-table or in
her treasure-chamber.
To-day she was walking restlessly up and down before dinner. The cousin,
who heard every thing, had just told her that a maid from Ehrenthal's
had run into the office to announce Bernhard's death to his friend. "How
will he bear it?" thought she. And the name of Ehrenthal forced her
thoughts back to the past, to one now far away, and to that painful hour
when the struggle going on in her own mind had been suddenly brought to
a close by a letter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parted. And Anton had known
of that conquered feeling of hers. How considerate he had always been,
how chivalrous, how helpful! She wondered if he had any idea of the
completeness of her triumph over a girlish illusion. She shook her head.
"No, he has not. It was here, at this very table, that an accident first
betrayed me to him. That past time still rises like a cloud between us.
Whenever I sit near Wohlfart of an evening, I am conscious of another's
shadow at my side; and when he speaks to me, his tone, his manner always
seem to say, 'You are not alone; he is with you.'" Sabine started, and
lovingly passed her hand over the beautiful flowers on the table before
her, as if to dispel a painful thought. She could not tell him that she
was free from that long-felt sorrow. Now, however, when he had lost a
friend whom he so much loved, she must show him that there were other
hearts that clung to him still. And again she walked up and down, trying
to devise a way of speaking to him alone.
Dinner was announced. Anton came with the rest, and took his place at
once. There was no opportunity of exchanging a word during the meal, but
he often met her sad and sympathizing eye. "He eats nothing at all
to-day," whispered her cousin; "not even any of the roast," she added,
reproachfully. Sabine was much perturbed. Mr. Jordan had already risen;
Anton would leave the room with the rest, and she should not see him
again the whole day through. So she called out, "The great Calla is
fully blown now. You were admiring the buds the other day; will you
remain a moment; I should like to show it you?" Anton bowed and staid
behind. A few more awkward moments, then her brother rose too; and,
hurrying to Anton, she took him to the room where the flowers were.
"You have had sorrowful tidings to-day," she began.
"The tidings themselves did not surprise me," replied Anton. "The doctor
gave no hope. But I lose much in him."
"I never saw him," said Sabine; "but I know from you that his life was
lonely--poor in affection and in enjoyment."
She moved an arm-chair toward Anton, and led him on to talk about his
friend. She listened to every word with warm sympathy, and well knew
what to ask and how to comfort. It was a relief to Anton to speak of the
departed one, to describe his quiet way of life, his erudition, his
poetical enthusiasm. After a pause, Sabine looked up frankly into his
face, and asked, "Have you any tidings of Herr von Fink?"
It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his departure that she had ever breathed his
name. Anton felt how touching her confidence was, given in this hour of
his sadness. In his emotion, he seized her hand, which she was slow in
withdrawing.
"He is not happy in his new life," he gravely replied. "There was a
savage humor in his last letter, from which I gather, even more than
from his actual words, that the business into which his uncle's death
has thrown him does not suit him."
"It is unworthy," cried Sabine.
"At all events, it is not what would be recognized as honorable in this
house," replied Anton. "Fink is upright, and has lived too long with
your brother to take pleasure in the wild speculations so common on the
other side the Atlantic. His partners and colleagues are for the most
part men without a conscience, and his feelings revolt against their
companionship."
"And can Herr von Fink tolerate such relations as these for a day?"
"It is a remarkable thing that he whose own will was ever so arbitrarily
exercised, should now be obliged against that will to obey a pressure
from without, and every where to work with his hands tied. The
organization of such speculations in America is so complicated that one
shareholder can do little to alter it; and, now that Fink has attained
what used to be the goal of his wishes--a large capital, and the
management of immense districts--his condition appears more uncertain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He was always in danger of thinking slightingly
of others, now I am distressed at the bitter contempt he expresses for
his own life. His last letter paints an intolerable state of things, and
seems to point to some decisive resolve."
"There is only one resolve for him," cried Sabine. "May I ask what you
said to him in reply?"
"I entreated him instantly, come what would, to free himself from the
business in which he was entangled. I said that his own strong will
might find a way of extrication, even if that which I pointed out proved
impracticable. Then I begged of him either to carry out his old plan of
becoming a landed proprietor in America, or to return to us."
"I knew that you would write thus," said Sabine, drawing a long breath.
"Yes, Wohlfart, he shall return," said she, gently, "but he shall not
return to us."
Anton was silent.
"And do you think that Herr von Fink will follow your advice?"
"I do not know. My advice was not very American."
"But it was worthy of you," cried Sabine, with proud delight.
"An officer wishes to speak to Mr. Wohlfart," said a servant at the
door.
Anton sprang up. Sabine went to her flowers and bent mournfully over
them. The shadows of others hovered still between her friend and her.
The few words spoken by the servant filled Anton with a vague terror. He
hurried into the ante-room: there stood Eugene von Rothsattel. Anton was
gladly rushing forward to greet him, but the young soldier's face of
agony made him start back. He whispered, "My mother wishes to speak to
you; something dreadful has occurred." Anton caught up his hat, ran into
the office, hurriedly asked Baumann to excuse him to the principal, and
then accompanied the lieutenant to the baron's house.
On the way, Eugene, who had lost all self-command, said unconnectedly to
Anton, "My father last night accidentally wounded himself by a
pistol-shot--a messenger was sent to summon me--when I came, I found my
mother in a swoon--my sister and I do not know what to do--Lenore
implored my mother on her knees to send for you--you are the only one in
whom w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our distress--I understand nothing about
business, but my father's affairs must be in a dreadful state--my mother
is beside herself--the whole house is in the greatest disorder."
From what Eugene said and what he did not say; from his broken sentences
and his look of agony, Anton guessed at the horrors of the previous
evening. In the boudoir of the baroness he found Lenore, weeping and
exhausted.
"Dear Wohlfart!" cried she, taking his hand and beginning again to sob,
while her head sank powerless on his shoulder.
Meanwhile Eugene walked up and down, wringing his hands, and at length
throwing himself on the sofa, he gave himself up to silent tears.
"It is horrible, Mr. Wohlfart," said Lenore, lifting up her head. "No
one may approach my father--Eugene may not, nor I--only my mother and
old John are with him; and early this morning the merchant Ehrenthal was
here, insisting that he must see my father. He screamed at my mother,
and called my father a deceiver, till she fainted away. When I rushed
into the room, the dreadful man went off threatening her with his
clenched fist."
Anton led Lenore to a chair and waited till she had told him all.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comforting in this case, and his own heart was
wrung to the utmost by the misery he witnessed.
"Call my mother, Eugene," said Lenore, at length.
Her brother left the room.
"Do not forsake us," implored Lenore, clasping her hands; "we are at the
last gasp; even your help can not save us."
"He is dead who might perhaps have done so," mournfully replied Anton.
"Whether I can be of any use I know not, but you can not doubt my
willingness to be so."
"No," cried Lenore. "And Eugene, too, thought of you at once."
The baroness now entered. She walked wearily; but, steadying herself by
a chair, she saluted Anton with dignity. "In our position," said she,
"we need a friend who knows more of business than we three do.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prevents the baron--possibly for a long time to
come--from managing his own affairs, and, little as I understand them, I
can see that our interests require prompt measures. My children have
mentioned you to me, but I fear I am unreasonable in asking you to
devote your time to our service."
She sat down, beckoned Anton to take a chair, and said to her children,
"Leave us; I shall be better able to tell Mr. Wohlfart the little that I
know when I do not see your grief."
When they were alone, she motioned him nearer and tried to speak, but
her lips quivered, and she hid her face in her handkerchief.
"Before I can consent, gracious lady," said he, "to your reposing in me
such confidence as this, I must first inquire whether the baron has no
relative or intimate friend to whom you could with less pain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I pray you to remember that my own knowledge of business
is but small, and my position not one to constitute me a proper
counselor to the baron."
"I know no one," said the baroness, hopelessly. "It is less painful to
me to tell you what I can not conceal, than to one of our own circle.
Consider yourself a physician sent for to visit a patient. The baron has
this morning told me some particulars of his present circumstances." And
then she proceeded to relate what she had gathered as to the nature of
his embarrassments, the danger in which the family property was placed,
and the capital needed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Polish estate.
"My husband," continued she, "has given me the key of his desk, and he
wishes Eugene, with the help of a man of business, to go over his
papers. I now request of you to make this examination together with my
son. When you need explanations, I will try to obtain them from the
baron. The question is now, whether you are inclined to undertake this
trouble for us, who are only strangers."
"I am most willing to do so," earnestly replied Anton; "and I hope that
the kindness of my principal will allow me the time needful for the
purpose, if you do not consider it more advisable to depute the baron's
experienced legal adviser to the task."
"There will be an opportunity of asking that gentleman's advice later,"
said the baroness.
Anton rose. "When do you wish to begin?"
"Immediately. I fear there is not a day to lose. I shall do all I can to
help you look the papers over." She led Anton into the next room, called
in Eugene, and unlocked the baron's desk. As she opened it she lost her
self-command for a moment, and moving to the window, the quivering of
the curtains betrayed the anguish that shook her fragile frame.
The mournful task began. Hour after hour passed. Eugene was in no
condition to peruse any thing, but his mother reached letters and
documents to Anton, and, though often obliged to desist a while, she
bravely returned to the task. Anton placed the papers in order, and
sought, by glancing over each, to arrive at least at a superficial view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It was evening, when the old servant opened the door in dismay, and
called out, "He is there again." The baroness could not repress a slight
scream, and made a gesture of aversion.
"I have told him that no one is at home, but he will not be dismissed;
he makes such a noise on the steps. I can not get rid of him."
"It will kill me if I hear his voice again," murmured the baroness.
"If the man be Ehrenthal," said Anton, rising, "I will try to get him
away. We have now done what was most necessary; have the goodness to
lock up these papers, and to allow me to return to-morrow." The baroness
silently assented, and sank back in her chair. Anton hurried off to the
ante-room, whence he could hear Ehrenthal's loudly-raised voi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usurer shocked him. His hat pushed half off his
head, his pale face swelled as if by drinking, his glazed eyes red with
tears, Ehrenthal stood before him, calling in broken sentences for the
baron, wailing and cursing alternately. "He must come! he must come at
once!" cried he; "the wicked man! A nobleman, indeed! he is a vagabond,
after whom I will send the police. Where is my money? Where is my
security? I want my mortgage from this man who is not at home."
Anton went straight up to him, and asked, "Do you know me, Mr.
Ehrenthal?" Ehrenthal turned his glazed eyes upon him, and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 friend of his dead son.
"He loved you!" he cried, in a lamentable voice. "He spoke to you more
than to his father. You were the only friend that he had on earth. Have
you heard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house of Ehrenthal?" continued he, in
a whisper. "Just as they stole the papers he died. He died with a hand
like this," and clenching his fist he struck his forehead. "Oh my son!
my son! why didst not thou forgive thy father!"
"We will go to your son," said Anton, taking the arm of the old man, who
unresistingly allowed himself to be led back to his own house.
From thence Anton hurried to Councilor Horn, with whom he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It was late before he returned home. In the midst of his anxiety about
those whose prosperity had filled his imagination years before,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in their adversity, reposed in him, dilated his
breast with a feeling of pride. He burned with desire to help them, and
hoped that his zealous devotion might yet find some way of rescue. As
yet he saw none. Looking up at the great building before him, so firm
and secure, in the moonlight, a thought flashed into his mind. If any
man could help them, it was his principal. His keen eye would be able to
unravel all the dark secrets in which the baron was entangled, and his
iron strength of will would crush the villains who held the unfortunate
nobleman in their power. And then he had a noble nature; he always
decided on the right, without an effort or a struggle. Anton looked at
the first floor. The whole house-front was dark, but in a corner room a
light still burned. It was the private office of his chief.
With sudden resolve, Anton begged the servant to take him to Mr.
Schröter, who looked with amazement at the unexpected visitor, and asked
what brought him, and whether any thing had happened.
"I implore your counsel--I implore your help," cried Anton.
"For yourself or for others?" inquired the merchant.
"For a family with whom I have accidentally become connected. They are
lost if a strong hand does not ward off the impending catastrophe."
Anton then rapidly related the occurrences of the afternoon, and,
seizing his principal's hand in his emotion, cried, "Have pity upon the
unhappy ladies, and help them."
"Help them!" replied the merchant; "how can I? Have you been
commissioned to apply to me, or are you only following the impulse of
your own feelings?"
"I am not commissioned; it is only the interest that I take in the
baron's fate which leads me to you."
"And what right have you to inform me of facts communicated in strict
confidence to yourself by the baron's lady?" asked the merchant, dryly.
"I am committing no indiscretion in telling you what will, in a few
days, be no secret, even to strangers."
"You are unusually excited, otherwise you would not forget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hatever, does a man of business venture to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without the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Of course, I shall make no wrong use of what you have said, but it was
by no means business-like, Wohlfart, to be so open toward me."
Anton was silent, feeling, indeed, that his principal was right, but yet
it seemed hard to be blamed for reposing confidence at such a time as
this. The merchant walked silently up and down; at length, stopping
before Anton, he said, "I do not now inquire how you come to take so
warm an interest in this family. I fear it is an acquaintance you owe to
Fink."
"You shall hear all," said Anton.
"Not at present. I will now content myself with repeating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interfere in these affairs without being specially
applied to by the parties themselves. I may add that I by no means wish
for such an application, and do not disguise from you that, were it
made, I should probably decline to do any thing for the Baron
Rothsattel."
Anton's feelings were roused to the utmost. "The question is the rescue
of an honorable man, and of lovely and amiable women from the toils of
rogues and impostors. To me, this seems the duty of every one; I, at
least, consider it a sacred obligation which I dare not shrink from. But
without your support I can do nothing."
"And how do you think this embarrassed man can be helped?" inquired the
merchant, seating himself.
With somewhat more composure, Anton repli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an experienced man of business making himself master of the case. There
must be some way of circumventing these villains. Your penetration would
discover it."
"Any attorney would be far more likely to do so, and the baron might
readily engage the services of experienced and upright legal advisers.
If his enemies have done any thing illegal, the quick eye of a lawyer is
the most likely to detect it."
"Alas! the baron's own lawyer gives but little hope," replied Anton.
"Then, my dear Wohlfart, no other is likely to do much good. Show me an
embarrassed man who has strength to grasp an offered hand, and bid me
help him, and for the sake of all I owe you, I will not refuse to do so.
I think you are convinced of this."
"I am," said Anton, dejectedly.
"From all I hear, however," the merchant went on,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the baron. From what I gather from general report, as well as from
you, his embarrassments arise from his having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usurers, which proves him deficient in what alone ennobles the life of
any man--good sense, and the power of steady exertion."
Anton could only sigh his assent.
"To help such a man," inexorably continued the merchant, "is a futile
attempt, against which reason may well protest. We are not to despair of
any, but want of strength is the most hopeless case of all. Our power of
laboring for others being limited, it becomes our duty to inquire,
before we devote our time to the weak, whether we are not thus
diminishing our chances of helping better men."
Anton interrupted him. "Does he not deserve every allowance to be made
for him? He was brought up to exact much; he has not learned, as we
have, to make his way by his own labor."
The merchant laid his hand on the young man's shoulder. "The very
reason. Believe me, a large number of these landed gentry, who pay the
penalty of their old family memories, are beyond help. I am the last to
deny that many worthy and admirable men belong to this class. Indeed,
wherever remarkable talent or nobility of character shoots up among
them, no doubt their position offers peculiar scope for its development,
but for average men it is not a favorable one. He who considers it his
hereditary privilege to enjoy life, and who assumes a distinguished
position in virtue of his family, will very often fail to put forth his
whole strength in order to deserve that position. Accordingly, numbers
of our oldest families are declining, and their fall will be no loss to
the state. Their family associations make them haughty without any
right to be so--limit their perceptions and confuse their judgment."
"Even if all this be true," cried Anton, "it does not absolve us from
helping individuals of the class who have excited our sympathy."
"No," said the principal, "if it be excited. But it does not glow so
rapidly in advancing years as in youth. The baron has endeavored to
isolate his property from the current of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leave it forever to his family. Forever! You, as a merchant, know how to
estimate the attempt. True, every rational man must allow it to be
desirable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same soil should be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We all prize what our forefathers have possessed before
us, and Sabine would unlock every room in this house with pride, because
her great-great-grandmother turned the same keys before her. It is
therefore natural that the landed proprietor should desire to preserve
those familiar scenes, which are the source of his own prosperity, to
those nearest and dearest to him. But there must be means to this end,
and these means are the making his own existence available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increase of his patrimony. Where energy dies in families
or individuals, then it is well that their means die too, that their
money should circulate through other hands, and their plowshare pass to
those who can guide it better. A family that has become effete through
luxury ought to sink down into common life, to make room for the
uprising of fresh energies and faculties. Every one who seeks, at the
cost of free activity for others, to preserve permanent possessions and
privileges for himself or his family, I must look upon as an enemy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social state. And if such a man ruin
himself in his endeavors, I should feel no malicious pleasure in his
downfall, but I should say that he is rightly served, because he has
sinned against a fundamental law of our social being; consequently, I
should consider it doubly wrong to support this man, because I could but
fear that I should thus be supporting an unsound condition of the body
politic."
Anton looked down mournfully. He had expected sympathy and warm
concurrence, and he met with disaffection and coldness that he despaired
of conquering. "I can not gainsay you," he at length replied; "but in
this case I can not feel as you do. I have been witness to the
unspeakable distress in the baron's family, and my whole soul is full
of sadness and sympathy, and of the wish to do something for those who
have opened their heart to me. After what you have said, I dare no
longer ask you to trouble yourself with their affairs, but I have
promised the baroness to assist her as far as my small powers permit,
and your kindness allows. I implore you to grant me permission to do
this. I shall endeavor to be regular in my attendance at the office, but
if during the next few weeks I am occasionally absent, I must ask you to
excuse me."
Once more the merchant walked up and down the room, and then, looking at
Anton's excited face, with deep seriousness and something of regret, he
replied, "Remember, Wohlfart, that every occupation which excites the
mind soon obtains a hold over a man, which may retard as well as advance
his success in life. It is thi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 to agree
to your wishes."
"I know it," said Anton, in a low voice; "but I have now no choice
left."
"Well, then, do what you must," said the merchant, gloomily; "I will lay
no hinderance in your way; and I hope that after a few weeks you will be
able to consider the whole circumstances more calmly." Anton left the
room, and the merchant stood looking long with frowning brow at the
place his clerk had occupied.
Nor was Anton in a more congenial mood. "So cold, so inexorable!"
exclaimed he, as he reached his own room. He began to suspect that his
principal was more selfish and less kindly than he had hitherto
supposed. Many an expression of Fink's recurred to his mind, as well as
that evening when young Rothsattel, in his boyish conceit, had spoken
impertinently to the merchant. "Is it possible," thought he, "that that
rude speech should be unforgotten?" And his chief's keen, deep-furrowed
face lost inexpressibly by contrast with the fair forms of the noble
ladies. "I am not wrong," he cried to himself; "let him say what he
will, my views are more just than his, and henceforth my destiny shall
be to choose for myself the way in which I shall walk." He sat long in
the darkness, and his thoughts were gloomy as it; then he went to the
window to look down into the dark court below. A great white blossom
rose before him like a phantom. Striking a light, he saw that it was the
beautiful Calla out of Sabine's room. It hung down mournfully on its
broken stem. Sabine had had it placed there. This little circumstance
struck him as a mournful omen.
Meanwhile Sabine, taper in hand, entered her brother's room.
"Good-night, Traugott," nodded she. "Wohlfart has been with you this
evening; how long he staid!"
"He will leave us," replied the merchant, gloomily.
Sabine started and dropped her taper on the table. "For God's sake, what
has happened? Has Wohlfart said that he was going away?"
"I do not yet know it, but I see it coming step by step; and I can not,
and still less can you, do any thing to retain him. When he stood before
me here with glowing cheeks and trembling voice, pleading for a ruined
man, I found out what it was that lured him away."
"I do not understand you," said Sabine, looking full at her brother.
"He chooses to become the confidential friend of a decayed noble. A pair
of bright eyes draws him away from us: it seems to him a worthy object
of ambition to become Rothsattel's man of business. This intimacy with
nobility is the legacy bequeathed to him by Fink."
"And you have refused to help him?" inquired Sabine, in a low voice.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said the merchant, harshly; and he
turned to his writing-table.
Sabine slowly withdrew. The taper trembled in her hand as she passed
through the long suite of rooms listening to her own footfall, and
shuddering as the feeling came over her that an invisible companion
glided by her side. This was the revenge of that other. The shadow that
once fell on her innocent life now drove her friend away from their
circle. Anton's affections clung to another. She had but been in his
eyes a mere stranger, who had once loved and languished for one now far
away, and who now, in widow's weeds, looked back regretfully to the
feelings of her youth.
The few next weeks were spent by Anton in over-hard work. He had great
difficulty in keeping up his counting-house duties, while he spent every
spare hour in conference with the baroness and the lawyer.
In the mean time, the misfortunes of the baron ran their course. He had
not been able to pay the interest of the sums with which his estate was
burdened. When last they were due, a whole series of claims was brought
against him, and the estate fell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district authorities. Complicated lawsuits arose. Ehrenthal complained
loudly, claiming the first mortgage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nay, he
was inclined to advance claims on the last mortgage offered by the baron
in the recent fatal hour. Löbel Pinkus also appeared as claimant of the
first mortgage, and asserted that he had paid the whole sum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Ehrenthal had no proof to bring forward, and had been
for some weeks past quite unable to manage his own affairs, while
Pinkus, on the contrary, fought with every weapon a hardened sinner can
devise or employ, and the deeds which the baron had executed at Veitel's
suggestion proved to be so capital a master-stroke of the cunning
advocate, that the baron's man of business had, from the first, little
hope of the case. We may here observe that Pinkus did eventually win it,
and that the mortgage was made over to him.
Anton was now gradually gaining some insight into the baron's
circumstances. But the double sale of the first mortgage was still kept
a secret by the latter, even from his wife. He declared Ehrenthal's
claim unfounded, and even expressed a suspicion that he had himself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robbery in his office. Indeed, he really
believed this. Then the name of Itzig was never broached, and the
suspicion against Ehrenthal, which the baron's lawyer shared, prevented
Anton seeking any explanation from him.
Meanwhile, an estrangement had sprung up between our hero and his
principal, which the whole counting-house remarked with surprise. The
merchant scowled at Anton's vacant seat when the latter chanced to be
absent during office-hours, or looked coldly at his clerk's face, made
pale as it was with excitement of mind and night-work. He took no notice
of his new occupation, and never seemed to remark him. Even to his
sister he maintained a stiff-necked silence; nor could all her attempts
lead him to speak of Anton, who, on his side, felt his heart revolt
against this coldness. After his return, to be treated like a child of
the house, praised, promoted, petted, and now to be treated like a mere
hireling, who is not worth the bread thrown to him; to be a toy of an
incomprehensible caprice--this, at least, he had not deserved; so he
became reserved toward the whole family, and sat silent at his desk; but
he fel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now and the then so keenly, that often,
when alone, he would spring up and stamp on the ground in the bitter
indignation of his heart.
One comfort remained. Sabine was not estranged. True, he saw little of
her, and at dinner she seemed to avoid speaking to him, but he knew that
she was on his side.
A few days after his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the merchant, she came down
stairs as he stood in the hall, and had to pass him by so closely that
her dress touched him. He had retreated, and made a formal bow, but she
looked at him imploringly, and whispered, "You must not be estranged
from me." It was an affair of a moment, but the faces of both were
radiant with a happy understanding.
The time had now arrived when Mr. Jordan was to quit the firm. The
principal again called Anton into his little office, and without any
severity, but also without a trace of his former cordiality, began: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o you my intention of appointing you Jordan's
successor; but,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your time has been more taken
up with other business than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such a post, I
therefore ask you whether you are now at liberty to undertake Jordan's
duties?"
"I am not," replied Anton.
"Can you name any--not very distant--time when you will be free from
your present occupation? In that case I will endeavor to find a
substitute until then."
Anton sorrowfully replied, "I can not at present say when I shall again
be master of my whole time; and, besides, I feel that, even as it is, I
tax your indulgence by many irregularities. Therefore, Mr. Schröter, I
beg that you will fill up this post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me."
The merchant's brow grew furrowed and dark, and he silently bowed
assent. Anton felt as he closed the door that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m was now complete, and, resuming his place, he leaned his throbbing
head on his hand. A moment later Baumann was summoned to the principal,
and Jordan's situation conferred upon him. On returning to the office,
he went up to Anton and whispered, "I refused at first, but Mr. Schröter
insisted. I am doing you an injustice." And that evening Mr. Baumann, in
his own room, read in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the chapters treating of
the unjust Saul (the principal), and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Jonathan
and the persecuted David, and strengthened his heart thereby.
The next day Anton was summoned to the baroness. Lenore and her mother
sat before a large table covered with jewel-boxes and toilette elegances
of every description, while a heavy iron chest stood at their feet. The
curtains were drawn, and the subdued light shone softly into the richly
furnished room. On the carpet glowed wreaths of unfading flowers, and
the clock ticked cheerfully in its alabaster case. Under the shade of
flowering plants sat the two love-birds in their silvered cage, hopping
from perch to perch, screaming ceaselessly, or sitting up quietly close
to each other. The whole room was beauty and perfume. "For how long?"
thought Anton. The baroness rose. "We are already obliged to trouble you
again," said she; "we are engaged in a very painful occupation." On the
table were all manner of ornaments, gold chains, brilliants, rings,
necklaces, gathered into a heap.
"We have been looking out all that we can dispense with," said the
baroness, "and now pray you to undertake to sell these things for us. I
have been told that some of them are of value, and as we are now in much
need of money, we turn here for help."
Anton looked in perplexity at the glittering heap.
"Tell us, Wohlfart," cried Lenore, anxiously, "is this necessary? can it
be of any use? Mamma has insisted upon setting apart for sale all our
ornaments, and whatever plate is not in daily use. What I can give is
not worth talking of, but my mother's jewels are costly; many of them
were presents made to her in youth, which she shall not part with unless
you say that it is necessary."
"I fear," said Anton, gravely, "that it will prove so."
"Take them," said the baroness to Anton; "I shall be calmer when I know
that we have at least done what we could."
"But do you wish to part with all?" inquired Anton, anxiously. "Much
that is dear to you may have but little value in a jeweler's eyes."
"I shall never wear an ornament again," quietly replied the baroness.
"Take them all;" and, holding her hands before her eyes, she turned
away.
"We are torturing my mother," cried Lenore, hastily; "will you lock up
all that is on the table, and get them out of the house as soon as you
can?"
"I can not undertake the charge of these valuables," said Anton,
"without taking some measures to decrease my own responsibility. First
of all, I will in your presence make a short note of all you intrust to
me."
"What useless cruelty!" exclaimed Lenore.
"It will not take long."
Anton took out a few sheets from his pocket-book, and began to note down
the different articles.
"You shall not see it done, mother," said Lenore, drawing her mother
away, and then returning to watch Anton at his task.
"These preparations for the market are horrible," said she. "My mother's
whole life will be sold; some memory of hers is linked with every single
thing. Look, Wohlfart, the princess gave her this diamond ornament when
she married my father."
"They are magnificent brilliants," cried Anton, admiringly.
"This ring was my grandfather's, and these are presents of poor papa's.
Alas! no man can know how we love all these things. It was always a
festival to me when mamma put on her diamonds. Now we come to my
possessions. They are not worth much. Do you think this bracelet good
gold?" She held out her hand as she spoke.
"I do not know."
"It shall go with the rest," said Lenore, taking it off. "Yes, you are a
kind, good man, Wohlfart," continued she, looking trustfully into his
tearful eyes; "do not forsake us. My brother has no experience, and is
more helpless than we are. It is a frightful position for me. Before
mamma I do all I can to be composed, else I could scream and weep the
whole day through." She sank in a chair, still holding his hand. "Dear
Wohlfart, do not forsake us."
Anton bent over her, and looked with passionate emotion at the lovely
face that turned so trustfully to him in the midst of its tears.
"I will be helpful to you when I can," said he, in the fullness of his
heart. "I will be at hand whenever you need me. You have too good an
opinion of my information and my faculties; I can be of less assistance
to you than you suppose, but what I can, that I will do in any and every
possible way."
Their hands parted with a warm pressure; the affair was settled.
The baroness now returned. "Our lawyer was with me this morning," said
she; "and now I must ask for your opinion on another subject. He tells
me that there is no prospect of preserving the baron's family estate."
"At this time, when interest is high, and money difficult to get, none,"
replied Anton.
"And you, too, think that we must turn all our efforts toward preserving
the Polish property?"
"I do," was the answer.
"For that, also, money will be necessary. Perhaps I may be able through
my relatives to intrust you with a small sum, which, with the help of
that"--she pointed to the iron chest--"may suffice to cover the first
necessary expenses. I do not, however, wish to sell the jewels here, and
a journey to the residence would be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cure the
sum to which I have just alluded. The baron's lawyer has spoken most
highly of your capacity for business. It is his wish which now decides
me to make a proposal to you. Will you for the next few years, or, at
all events, until our greatest difficulties are over, devote your whole
time to our affairs? I have consulted my children, and they agree with
me in believing that in your assistance lies our only hope of rescue.
The baron, too, has come in to the plan. The question now is whether
your circumstances allow you to give your support to our unfortunate
family. We shall be grateful to you, whatever conditions you affix; and
if you can find any way of making our great obligations to you apparent
in the position you hold, pray impart it to me."
Anton stood petrified. What the baroness required of him was separation
from the firm, separation from his principal, and from Sabine! Had this
thought occurred to him before, when standing in Lenore's presence or
bending over the baron's papers? At all events, now that the words were
spoken, they shocked him. He looked at Lenore, who stood behind her
mother with hands clasped in supplication. At length he replied, "I
stand in a position which I can not leav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others.
I was not prepared for this proposal, and beg to have time allowed me
for consideration. It is a step which will decide my whole future life."
"I do not press you," said the baroness; "I only request your
consideration. Whatever your decision be, our warmest gratitude will
still be yours; if you are unable to uphold our feeble strength, I fear
that we shall find no one to do so. You will think of that," she added,
beseechingly.
Anton hurried through the street with throbbing pulse. The noble lady's
glance of entreaty, Lenore's folded hands, beckoned him out of the
gloomy counting-house into a sphere of greater liberty, into a new
future, from whose depths bright images flashed out upon his fancy. A
request had been frankly made, and he was strongly inclined to justify
the confidence that prompted it. Those ladies required an unwearied,
self-sacrificing helper to save them from utter ruin, and if he
followed his impulse he should be doing a good work--fulfilling a duty.
In this mood he entered the merchant's dwelling. Alas! all that he saw
around him seemed to stretch out a hand to detain him. As he looked at
the warehouse, the good-humored faces of the porters, the chains of the
great scales, the hieroglyphics of the worthy Pix, again he felt that
this was the place that he belonged to. Sabine's dog kissed his hand,
and ran before him to his room--his and Fink's room. Here the childish
heart of the orphan boy had found a friend, kind companions, a home, a
definite and honorable life-purpose. Looking down through his window on
all the long-familiar objects, he saw a light in Sabine's store-chamber.
How often he had sought for that light, which brightened the whole great
building, and brought a sense of comfort and cheerfulness even into his
room. He now sprang up suddenly, and said to himself, "She shall
decide."
Sabine started in amazement when Anton appeared before her. "I am
irresistibly impelled to seek you," cried he. "I have to decide upon my
future life, and I feel undetermined, and unable to trust to my own
judgment. You have always been a kind friend to me since the day of my
arrival. I am accustomed to look up to you, and to think of you in
connection with all that interests me here. Let me hear your opinion
from your own lips. The Baroness Rothsattel has to-day proposed to me
permanently to undertake the situation of confidential adviser and
manager of the baron's affairs. Shall I accept; or shall I remain here?
I know not--tell me what is right both for myself and others."
"Not I," said Sabine, drawing back and growing very pale. "I can not
venture to decide in the matter. Nor do you wish me to do so, Wohlfart,
for you have already decided."
Anton looked straight before him and was silent.
"You have thought of leaving this house, and a wish to do so has sprung
out of the thought. And I am to justify you, and approve your resolve!
This is what you require of me," continued she, bitterly. "But this,
Wohlfart, I can not do, for I am sorry that you go away from us."
She turned away from him and leaned on the back of a chair.
"Oh, be not angry with me too!" said Anton; "that I can not bear. I have
suffered much of late. Mr. Schröter has suddenly withdrawn from me the
friendly regard that I long held my life's greatest treasure. I have not
deserved his coldness. What I have been doing has not been wrong, and
it was done with his knowledge. I had been spoiled by his kindness; I
have the more deeply felt his displeasure. My only comfort has been that
you did not condemn me. And now, do not you be cold toward me, else I
shall be wretched forever. There is not a soul on earth to whom I can
turn for affectionate comprehension of my difficulties. Had I a sister,
I should seek her heart to-day. You do not know what to me, lonely as I
am, your smile, your kindly shake of the hand has been till now. Do not
turn coldly from me, I beseech you."
Sabine was silent. At length she inquired, still with averted face,
"What draws you to those strangers; is it a joyful hope, is it sympathy
alone? Give this question close consideration before you answer it to
yourself at least."
"What it is that makes it possible for me to leave this house," said
Anton, "I do not myself know. If I can give a name to my motives, it is
gratitude felt toward one. She was the first to speak kindly to the
wandering boy on his way out into the world. I have admired her in the
peaceful brightness of her former life. I have often dreamed childish
dreams about her. There was a time when a tender feeling for her filled
my whole heart, and I then believed myself forever the slave of her
image. But years bring changes, and I learned to look on men and on life
with other eyes. Then I met her again, distressed, unhappy, despairing,
and my compassion became overmastering. When I am away from her, I know
that she is nothing to me; when I am with her, I feel only the spell of
her sorrow. Once, when I had to depart out of her circle like a culprit,
she came to me, and before the whole scornful assembly she gave me her
hand and acknowledged me her friend; and now she comes and asks for my
hand to help her father. Can I refuse it? Is it wrong to feel as I do? I
know not, and no one can tell me--no one but you alone."
Sabine's head had sunk down to the back of the chair on which she bent.
She now suddenly raised it, and with tearful eyes, and a voice full of
love and sorrow, cried, "Follow the voice that calls you. Go, Wohlfart,
go."
CHAPTER XXVII.
On a cold October day, two men were seen driving through the latticed
gate of the town of Rosmin on toward the plain, which stretched out
before them monotonous and boundless. Anton sat wrapped in his fur coat,
his hat low on his forehead, and at his side was young Sturm, in an old
cavalry cloak, with his soldier's cap cocked cheerily on one side. In
front of them a farm-servant, squatted on a heap of straw, flogged on
the small horses. The wind swept the sand and straw from the
stubble-fields, the road was a broad causeway without ditches or hedges,
the horses had to wade alternately through puddles and deep sand. Yellow
sand gleamed through the scanty herbage in all directions wherever a
field-mouse had made her way to her nest or an active mole had done what
he could to diversify the unbroken plain. Wherever the ground sank,
stagnant water lodged, and there hollow willow-trees stretched their
crippled arms in the air, their boughs flapping in the wind, and their
faded leaves fluttering down into the muddy pool below. Here and there
stood a small dwarf pine, a resting-place for the crows, who, scared by
the passing carriage, flew loudly croaking over the travelers' heads.
There was no house to be seen on the road, no pedestrian, and no
conveyance of any kind.
Karl looked every now and then at his silent companion, and said at
last, pointing to the horses, "How rough their coats are, and how pretty
their gray mouse skins! I wonder how many of these beasties would go to
make up my sergeant's horse! When I took leave of my father, the old man
said, 'Perhaps I shall pay you a visit, little one, when they light the
Christmas-tree.' 'You'll never be able,' said I. 'Why not?' asked he.
'You'll never trust yourself in any post-chaise.' Then the old boy
cried, 'Oho! post-chaises are always of a stout build; I shall be sure
to trust myself in one.' But now, Mr. Anton, I see that my father never
can pay us a visit."
"Why not?"
"It is possible that he may reach Rosmin; but, as soon as he sees these
horses and this road, he will instantly turn back. 'Shall I trust
myself,' he'll say, 'in a district where sand runs between one's legs
like water, and where mice are put into harness? The ground is not firm
enough for me.'"
"The horses are not the worst things here," said Anton, absently. "Look!
these go fast enough."
"Yes," replied Karl, "but they don't go like regular horses; they
entangle their legs like two cats playing in a parsley-bed. And what
things they have for shoes--regular webbed hoofs, I declare, which no
blacksmith can ever fit."
"If we could only get on!" returned Anton; "the wind blows cold, and I
am shivering in spite of my fur."
"You have slept but little the last few nights, sir," said Karl. "The
wind blows here as if over a threshing-floor. The earth is not round
hereabouts as elsewhere, but flat as a cake. This is a complete desert;
we have been driving for more than an hour, and there is not a village
to be seen."
"A desert indeed," sighed Anton; "let us hope it may improve." They
relapsed into profound silence. At length the driver stopped near a
pool, unharnessed the horses, and led them to the water's edge, without
noticing the travelers.
"What the deuce does this mean?" cried Karl, jumping down from the
carriage.
"I am going to feed," replied the servant, sulkily, in a foreign accent.
"I am anxious to know how that will be done," said Karl. "There is not
the shadow of a bag of provender."
The horses, however, soon proved that they could live without corn; they
stretched down their shaggy heads, and began to pull the grass and weeds
at the edge of the pool, sometimes taking a draught of the dirty water.
Meanwhile the servant drew a bundle from under his seat, settled himself
under the lee of an alder-bush, and, taking his knife, cut his bread and
cheese without even glancing at the travelers.
"I say, Ignatius or Jacob," cried Karl, sharply, "how long will this
breakfast of yours last?"
"An hour," replied the man, munching away.
"And how far is it from here to the estate?"
"Six miles, or maybe more."
"You can make nothing of him," said Anton; "we must put up with the
customs of the country;" and, leaving the carriage, they went to look on
at the horses feeding.
Anton is on his way to the Polish property. He is now the baron's agent.
Anxious months have the last proved to him. The parting from his
principal and the firm had been painful in the extreme. For some time
before it, indeed, Anton had found himself alone in the midst of his
colleagues. The quiet Baumann still remained his friend, but the others
considered him a castaway. The merchant received his resignation with
icy coldness; and even in the hour of parting, his hand lay impassive as
metal in Anton's grasp. Since then, our hero had undertaken several
journeys to the capital and to creditors in the family's behalf, and now
he was on his way to set the new estate in order, accompanied by Karl,
whom he had induced to become the baron's bailiff.
Ehrenthal had, by the authority conferred on him,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from the time of the sale by auction, and hired the Polish
bailiff for the baron. There had been unfair dealings between them at
the time, and it was well known in Rosmin that the bailiff had sold off
a good deal, and been guilty of all sorts of frauds since, so that Anton
had even now no prospect of a quiet life.
"The hour is come when I may execute my commission," cried Karl, groping
in the straw under the seat. He drew out a large japanned tin case, and
carried it to Anton. "Miss Sabine gave me this in charge for you." He
then joyously opened the lid, produced the materials for an excellent
breakfast, a bottle of wine, and a silver goblet. Anton took hold of the
case.
"It has a very knowing look," said Karl. "Miss Sabine planned it
herself."
Anton examined it on all sides, and placed it carefully on a tuft of
grass; then he took up the goblet, and saw his initials engraved on it,
and underneath the words, "To thy welfare." Whereupon he forgot the
breakfast and all around him, and stood gazing at the goblet, lost in
thought.
"Do not forget the breakfast, sir," suggested Karl, respectfully.
"Sit down by me, my faithful friend; eat and drink with me. Leave off
your absurd politeness. We shall have but little, either of us, but what
we have we will share like brothers. Take the bottle if you have no
glass."
"There's nothing like leather," said Karl, taking a small leathern
drinking-cup out of his pocket. "As for 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t was
kindly meant, and I thank you; but there must be subordination, if it
were but for the sake of the others; and so, sir, be kind enough to let
me shake hands with you now, and then let things be as they were before.
Only look at the horses, Mr. Anton. My faith! the creatures devour
thistles."
Again the horses were harnessed, again they threw out their short legs
in the sand, and again the carriage rolled through the barren
district--first through an empty plain, next through a wretched
fir-wood, then past a row of low sand-hills, then over a tumble-down
bridge crossing a small stream.
"This is the property," said the driver, turning round, and pointing
with his whip to a row of dirty thatched roofs that had just come into
sight.
Anton stood up to look for the group of trees in which the Hall might be
supposed to stand. Nothing of the sort to be seen. The village was
deficient in all that adorns the home of the poorest German peasant--no
orchard, no hedged-in gardens, no lime-trees in the market-place.
"This is wretched," said he, sitting down again; "much worse than they
told us in Rosmin."
"The village looks as if under a curse," cried Karl; "no teams working
in the fields--not a cow or a sheep to be seen."
The farm-servant flogged his horses into an irregular gallop, and so
they passed through the rows of mud huts which constituted the village,
and arrived at the public house. Karl sprang from the carriage, opened
the tavern door, and called for the landlord. A Jew slowly rose from his
seat by the stove and came to the threshold. "Is the gendarme from
Rosmin come?" He is gone into the village. "Which is the way to the
farm-yard?"
The landlord, an elderly man with an intelligent countenance, described
the way in German and Polish, and remained standing at the
door--bewildered, Karl declared, by the sight of two human beings. The
carriage turned into a cross-road, planted on both sides with thick
bushes, the remains of a fallen avenue. Over holes, stones, and puddles,
it rattled on to a group of mud huts, which still had a remnant of
whitewash upon them. "The barns and stables are empty," cried Karl, "for
I see gaps in the roofs large enough to drive our carriage through."
Anton said no more; he was prepared for every thing. They drove through
a break between the stables into the farm-yard, a large irregular space,
surrounded on three sides by tumble-down buildings, and open to the
fields on the fourth. A heap of _débris_ lay there--lime and rotten
timber, the remains of a ruined barn. The yard was empty; no trace of
farm implements or human labor to be seen. "Which is the inspector's
house," inquired Anton, in dismay. The driver looked round, and at last
made up his mind that it was a small one-storied building, with straw
thatch and dirty windows.
At the noise of the wheels a man appeared on the threshold, and waited
phlegmatically till the travelers had dismounted, and were standing
close before him. He was a broad-shouldered fellow, with a bloated,
brandy-drinking face, dressed in a jacket of shaggy cloth, while behind
him peered the muzzle of an equally shaggy dog, who snarled at the
strangers. "Are you the steward of this property?"
"I am," replied the man, in broken German, without stirring from where
he was.
"And I am the agent of the new proprietor," said Anton.
"That does not concern me," growled the shaggy man, turning sharp round,
entering the house, and bolting the door within.
Anton was thoroughly roused. "Break the window in, and help me to catch
the rascal," cried he to Karl, who coolly seized a piece of wood, struck
the panes so as to make the rotten framework give way, and cleared the
opening at one leap. Anton followed him. The room was empty, so was the
next, and in it an open window--the man was gone.
"After him!" cried Karl, and dashed on in pursuit, while Anton looked
about the house and out-buildings. He soon heard the barking of a dog,
and saw Karl capture the fugitive. Hurrying to his help, he held the man
fast, while, with a kick, Karl sent the dog flying. They then contrived
to force the steward back to the house, though he kept striking out
violently all the way.
"Go to the tavern, and bring the gendarme and the landlord," cried Anton
to the driver, who, undisturbed by all that had been going on, had
meanwhile unpacked the carriage. The man accordingly drove leisurely
off, and the fugitive being got into the room, Karl found an old cloth,
and with it bound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I beg your pardon, sir,"
said he; "it is only for an hour or so, till the arrival of the Rosmin
gendarme, whom we have appointed to meet us."
Anton then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house, bu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found but the merest necessaries; no books nor papers of any kind. It
had doubtless been emptied already. A bundle projected from the
coat-pocket of the prisoner, which turned out to be receipts and legal
documents in Polish. In time, the driver returned with the landlord and
the armed policeman. The landlord stood at the door in some perplexity,
and the policeman explained in a few moments what remained to be done.
"You must make a statement to the local judge, and give the man up to
me. He shall go back in your carriage to Rosmin. You will do well to get
rid of him, for this is a wild country, and it will be safer for you to
have him at Rosmin than here, where he has friends and accomplices."
After a long search, a sheet of paper was found in a cupboard, the
statement made and submitted to the policeman, who shook his head a
little over the Polish composition, and the prisoner lifted into the
carriage, the gendarme taking his seat beside him, and saying to Anton,
"I have long expected something of the kind. You may have often occasion
to want me again." The carriage then drove away, and thus the property
came under Anton's administration. He felt as if cast on a desert
island.
His portmanteau and traveling effects were leaning against a mud wall,
and the Polish landlord was the only man who could give him and Karl any
information or advice in their forlorn condition.
Now that the steward was fairly gone, the landlord grew more
communicative, and showed himself serviceable and obliging. A long
conversation ensued, and its purport was what Anton had apprehended from
the warning given by the Commissary Walter and other Rosmin officials.
The inspector had,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done all he could in the
way of spoliation, rendered daring by a report which had found its way
from the town to the village, that the present proprietor would never be
able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estate. At last Anton said, "What that
wretched man has done away with he will have to account for; our first
care must be to preserve what is still to be found on the property. You
must be our guide to-day."
They then examined the empty buildings. Four horses and two
servants--they were gone into the wood--a few old plows, a pair of
harrows, two wagons, a britzska, a cellar full of potatoes, a few
bundles of hay, a little straw--the inventory did not take much time in
drawing up. The buildings were all out of repair, not through age, but
neglect.
"Where is the dwelling-house?" inquired Anton. The landlord led the way
out of the yard to the meadow--a broad plain, gradually sloping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brook. It had been a great pasture. The cattle had
trodden it down into holes; the snouts of greedy swine had rooted it up;
gray molehills and rank tufts of grass rose on all sides.
The landlord stretched out his hand. "There is the castle. This castle
i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he added, reverentially; "no
nobleman in the district has a stone house like that. All the gentry
here live in wood and mud buildings. Herr von Tarow, the richest of
them, has but a poor dwelling."
About three hundred yards from the last out-building rose a great brick
edifice, with a black slate roof and a thick round tower. Its gloomy
walls on this treeless pasture-land, without one trace of life around,
rose beneath the cloudy sky like a phantom fortress which some evil
spirit had evoked from the abyss--a station from which to blight all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The strangers approached it. The castle had fallen into ruins before the
builders had finished their task. The tower had stood there for ages. It
was built of unhewn stone, and had small windows and loop-holes. The
former lords of the land had looked down from its summit on the tops of
the trees, which then stretched far into the plain. They had then ruled
with a rod of iron the serfs who cultivated their land, and toiled and
died for them. Many an arrow had sped through those loop-holes at the
enemy storming below, and many a Tartar horse had been overthrown before
those massive walls. Years ago, a despot of the district had, in
expiation of former sins, begun to add to the gray tower the walls of a
holy monastery; but the monastery never got finished, and the useless
walls had already stood there long, when the late count took it into his
head to convert them into a lordly dwelling for his race, and to raise a
house unparalleled for magnificence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 front of the house was added on to both sides of the tower, which
projected in the middle. The intention had been to have a high
terrace-road up to the castle, and the principal entrance had been made
in the tower, and arched over; but the terrace never having been formed,
the stone threshold of the main door was quite inacce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ladders, and the wide opening was left. The window-spaces of
the lower floor were merely closed up with boards, while on the second
story were some window-frames of beautifully carved wood, in which large
panes had once been placed, but they had got broken. In other windows
were temporary frames of rough deal, with small panes of muddy glass let
into them. A company of jackdaws sat on the top of the tower, looking
down in amazement on the strangers, and every now and then one flew off,
screaming loudly, to contemplate the intruders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A house for crows and bats, not for human beings," said Anton. "At
least, I see no way of getting into it."
The landlord now took them round the building. Behind, where the two
wings made a sort of horse-shoe, there were low entrances to the cellars
and offices; beneath which, again, were stables, great arched kitchens,
and small cells for the serfs. A wooden staircase led to the upper
story. The door turned creaking on its hinges, and a narrow passage took
them through a side wing to the front part of the house. There all was
at least magnificently planned. The circular entrance-hall--an arched
room of the old tower--was painted in mosaic, and through the great
doorway-opening was seen a wide expans
small disturbance made by the return of Anton had gradually settled
down. Those first-class treasures of Sabine's had made way for other
specimens of damask, still of a superior kind, it is true, but which
came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e elderly cousin's comprehension. She had
been quite right in prophesying that Anton would never remark those
signs of exuberant gratitude or their withdrawal. However, one change
had been permanently made--the greatest, the best of all changes--the
clerk retained a privileged place in the heart of the young mistress of
the firm, and his tall figure often appeared as one of the circle that
Sabine's fancy loved to gather round her when at her work-table or in
her treasure-chamber.
To-day she was walking restlessly up and down before dinner. The cousin,
who heard every thing, had just told her that a maid from Ehrenthal's
had run into the office to announce Bernhard's death to his friend. "How
will he bear it?" thought she. And the name of Ehrenthal forced her
thoughts back to the past, to one now far away, and to that painful hour
when the struggle going on in her own mind had been suddenly brought to
a close by a letter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parted. And Anton had known
of that conquered feeling of hers. How considerate he had always been,
how chivalrous, how helpful! She wondered if he had any idea of the
completeness of her triumph over a girlish illusion. She shook her head.
"No, he has not. It was here, at this very table, that an accident first
betrayed me to him. That past time still rises like a cloud between us.
Whenever I sit near Wohlfart of an evening, I am conscious of another's
shadow at my side; and when he speaks to me, his tone, his manner always
seem to say, 'You are not alone; he is with you.'" Sabine started, and
lovingly passed her hand over the beautiful flowers on the table before
her, as if to dispel a painful thought. She could not tell him that she
was free from that long-felt sorrow. Now, however, when he had lost a
friend whom he so much loved, she must show him that there were other
hearts that clung to him still. And again she walked up and down, trying
to devise a way of speaking to him alone.
Dinner was announced. Anton came with the rest, and took his place at
once. There was no opportunity of exchanging a word during the meal, but
he often met her sad and sympathizing eye. "He eats nothing at all
to-day," whispered her cousin; "not even any of the roast," she added,
reproachfully. Sabine was much perturbed. Mr. Jordan had already risen;
Anton would leave the room with the rest, and she should not see him
again the whole day through. So she called out, "The great Calla is
fully blown now. You were admiring the buds the other day; will you
remain a moment; I should like to show it you?" Anton bowed and staid
behind. A few more awkward moments, then her brother rose too; and,
hurrying to Anton, she took him to the room where the flowers were.
"You have had sorrowful tidings to-day," she began.
"The tidings themselves did not surprise me," replied Anton. "The doctor
gave no hope. But I lose much in him."
"I never saw him," said Sabine; "but I know from you that his life was
lonely--poor in affection and in enjoyment."
She moved an arm-chair toward Anton, and led him on to talk about his
friend. She listened to every word with warm sympathy, and well knew
what to ask and how to comfort. It was a relief to Anton to speak of the
departed one, to describe his quiet way of life, his erudition, his
poetical enthusiasm. After a pause, Sabine looked up frankly into his
face, and asked, "Have you any tidings of Herr von Fink?"
It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his departure that she had ever breathed his
name. Anton felt how touching her confidence was, given in this hour of
his sadness. In his emotion, he seized her hand, which she was slow in
withdrawing.
"He is not happy in his new life," he gravely replied. "There was a
savage humor in his last letter, from which I gather, even more than
from his actual words, that the business into which his uncle's death
has thrown him does not suit him."
"It is unworthy," cried Sabine.
"At all events, it is not what would be recognized as honorable in this
house," replied Anton. "Fink is upright, and has lived too long with
your brother to take pleasure in the wild speculations so common on the
other side the Atlantic. His partners and colleagues are for the most
part men without a conscience, and his feelings revolt against their
companionship."
"And can Herr von Fink tolerate such relations as these for a day?"
"It is a remarkable thing that he whose own will was ever so arbitrarily
exercised, should now be obliged against that will to obey a pressure
from without, and every where to work with his hands tied. The
organization of such speculations in America is so complicated that one
shareholder can do little to alter it; and, now that Fink has attained
what used to be the goal of his wishes--a large capital, and the
management of immense districts--his condition appears more uncertain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He was always in danger of thinking slightingly
of others, now I am distressed at the bitter contempt he expresses for
his own life. His last letter paints an intolerable state of things, and
seems to point to some decisive resolve."
"There is only one resolve for him," cried Sabine. "May I ask what you
said to him in reply?"
"I entreated him instantly, come what would, to free himself from the
business in which he was entangled. I said that his own strong will
might find a way of extrication, even if that which I pointed out proved
impracticable. Then I begged of him either to carry out his old plan of
becoming a landed proprietor in America, or to return to us."
"I knew that you would write thus," said Sabine, drawing a long breath.
"Yes, Wohlfart, he shall return," said she, gently, "but he shall not
return to us."
Anton was silent.
"And do you think that Herr von Fink will follow your advice?"
"I do not know. My advice was not very American."
"But it was worthy of you," cried Sabine, with proud delight.
"An officer wishes to speak to Mr. Wohlfart," said a servant at the
door.
Anton sprang up. Sabine went to her flowers and bent mournfully over
them. The shadows of others hovered still between her friend and her.
The few words spoken by the servant filled Anton with a vague terror. He
hurried into the ante-room: there stood Eugene von Rothsattel. Anton was
gladly rushing forward to greet him, but the young soldier's face of
agony made him start back. He whispered, "My mother wishes to speak to
you; something dreadful has occurred." Anton caught up his hat, ran into
the office, hurriedly asked Baumann to excuse him to the principal, and
then accompanied the lieutenant to the baron's house.
On the way, Eugene, who had lost all self-command, said unconnectedly to
Anton, "My father last night accidentally wounded himself by a
pistol-shot--a messenger was sent to summon me--when I came, I found my
mother in a swoon--my sister and I do not know what to do--Lenore
implored my mother on her knees to send for you--you are the only one in
whom w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our distress--I understand nothing about
business, but my father's affairs must be in a dreadful state--my mother
is beside herself--the whole house is in the greatest disorder."
From what Eugene said and what he did not say; from his broken sentences
and his look of agony, Anton guessed at the horrors of the previous
evening. In the boudoir of the baroness he found Lenore, weeping and
exhausted.
"Dear Wohlfart!" cried she, taking his hand and beginning again to sob,
while her head sank powerless on his shoulder.
Meanwhile Eugene walked up and down, wringing his hands, and at length
throwing himself on the sofa, he gave himself up to silent tears.
"It is horrible, Mr. Wohlfart," said Lenore, lifting up her head. "No
one may approach my father--Eugene may not, nor I--only my mother and
old John are with him; and early this morning the merchant Ehrenthal was
here, insisting that he must see my father. He screamed at my mother,
and called my father a deceiver, till she fainted away. When I rushed
into the room, the dreadful man went off threatening her with his
clenched fist."
Anton led Lenore to a chair and waited till she had told him all.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comforting in this case, and his own heart was
wrung to the utmost by the misery he witnessed.
"Call my mother, Eugene," said Lenore, at length.
Her brother left the room.
"Do not forsake us," implored Lenore, clasping her hands; "we are at the
last gasp; even your help can not save us."
"He is dead who might perhaps have done so," mournfully replied Anton.
"Whether I can be of any use I know not, but you can not doubt my
willingness to be so."
"No," cried Lenore. "And Eugene, too, thought of you at once."
The baroness now entered. She walked wearily; but, steadying herself by
a chair, she saluted Anton with dignity. "In our position," said she,
"we need a friend who knows more of business than we three do.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prevents the baron--possibly for a long time to
come--from managing his own affairs, and, little as I understand them, I
can see that our interests require prompt measures. My children have
mentioned you to me, but I fear I am unreasonable in asking you to
devote your time to our service."
She sat down, beckoned Anton to take a chair, and said to her children,
"Leave us; I shall be better able to tell Mr. Wohlfart the little that I
know when I do not see your grief."
When they were alone, she motioned him nearer and tried to speak, but
her lips quivered, and she hid her face in her handkerchief.
"Before I can consent, gracious lady," said he, "to your reposing in me
such confidence as this, I must first inquire whether the baron has no
relative or intimate friend to whom you could with less pain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I pray you to remember that my own knowledge of business
is but small, and my position not one to constitute me a proper
counselor to the baron."
"I know no one," said the baroness, hopelessly. "It is less painful to
me to tell you what I can not conceal, than to one of our own circle.
Consider yourself a physician sent for to visit a patient. The baron has
this morning told me some particulars of his present circumstances." And
then she proceeded to relate what she had gathered as to the nature of
his embarrassments, the danger in which the family property was placed,
and the capital needed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Polish estate.
"My husband," continued she, "has given me the key of his desk, and he
wishes Eugene, with the help of a man of business, to go over his
papers. I now request of you to make this examination together with my
son. When you need explanations, I will try to obtain them from the
baron. The question is now, whether you are inclined to undertake this
trouble for us, who are only strangers."
"I am most willing to do so," earnestly replied Anton; "and I hope that
the kindness of my principal will allow me the time needful for the
purpose, if you do not consider it more advisable to depute the baron's
experienced legal adviser to the task."
"There will be an opportunity of asking that gentleman's advice later,"
said the baroness.
Anton rose. "When do you wish to begin?"
"Immediately. I fear there is not a day to lose. I shall do all I can to
help you look the papers over." She led Anton into the next room, called
in Eugene, and unlocked the baron's desk. As she opened it she lost her
self-command for a moment, and moving to the window, the quivering of
the curtains betrayed the anguish that shook her fragile frame.
The mournful task began. Hour after hour passed. Eugene was in no
condition to peruse any thing, but his mother reached letters and
documents to Anton, and, though often obliged to desist a while, she
bravely returned to the task. Anton placed the papers in order, and
sought, by glancing over each, to arrive at least at a superficial view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It was evening, when the old servant opened the door in dismay, and
called out, "He is there again." The baroness could not repress a slight
scream, and made a gesture of aversion.
"I have told him that no one is at home, but he will not be dismissed;
he makes such a noise on the steps. I can not get rid of him."
"It will kill me if I hear his voice again," murmured the baroness.
"If the man be Ehrenthal," said Anton, rising, "I will try to get him
away. We have now done what was most necessary; have the goodness to
lock up these papers, and to allow me to return to-morrow." The baroness
silently assented, and sank back in her chair. Anton hurried off to the
ante-room, whence he could hear Ehrenthal's loudly-raised voi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usurer shocked him. His hat pushed half off his
head, his pale face swelled as if by drinking, his glazed eyes red with
tears, Ehrenthal stood before him, calling in broken sentences for the
baron, wailing and cursing alternately. "He must come! he must come at
once!" cried he; "the wicked man! A nobleman, indeed! he is a vagabond,
after whom I will send the police. Where is my money? Where is my
security? I want my mortgage from this man who is not at home."
Anton went straight up to him, and asked, "Do you know me, Mr.
Ehrenthal?" Ehrenthal turned his glazed eyes upon him, and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 friend of his dead son.
"He loved you!" he cried, in a lamentable voice. "He spoke to you more
than to his father. You were the only friend that he had on earth. Have
you heard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house of Ehrenthal?" continued he, in
a whisper. "Just as they stole the papers he died. He died with a hand
like this," and clenching his fist he struck his forehead. "Oh my son!
my son! why didst not thou forgive thy father!"
"We will go to your son," said Anton, taking the arm of the old man, who
unresistingly allowed himself to be led back to his own house.
From thence Anton hurried to Councilor Horn, with whom he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It was late before he returned home. In the midst of his anxiety about
those whose prosperity had filled his imagination years before,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in their adversity, reposed in him, dilated his
breast with a feeling of pride. He burned with desire to help them, and
hoped that his zealous devotion might yet find some way of rescue. As
yet he saw none. Looking up at the great building before him, so firm
and secure, in the moonlight, a thought flashed into his mind. If any
man could help them, it was his principal. His keen eye would be able to
unravel all the dark secrets in which the baron was entangled, and his
iron strength of will would crush the villains who held the unfortunate
nobleman in their power. And then he had a noble nature; he always
decided on the right, without an effort or a struggle. Anton looked at
the first floor. The whole house-front was dark, but in a corner room a
light still burned. It was the private office of his chief.
With sudden resolve, Anton begged the servant to take him to Mr.
Schröter, who looked with amazement at the unexpected visitor, and asked
what brought him, and whether any thing had happened.
"I implore your counsel--I implore your help," cried Anton.
"For yourself or for others?" inquired the merchant.
"For a family with whom I have accidentally become connected. They are
lost if a strong hand does not ward off the impending catastrophe."
Anton then rapidly related the occurrences of the afternoon, and,
seizing his principal's hand in his emotion, cried, "Have pity upon the
unhappy ladies, and help them."
"Help them!" replied the merchant; "how can I? Have you been
commissioned to apply to me, or are you only following the impulse of
your own feelings?"
"I am not commissioned; it is only the interest that I take in the
baron's fate which leads me to you."
"And what right have you to inform me of facts communicated in strict
confidence to yourself by the baron's lady?" asked the merchant, dryly.
"I am committing no indiscretion in telling you what will, in a few
days, be no secret, even to strangers."
"You are unusually excited, otherwise you would not forget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hatever, does a man of business venture to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without the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Of course, I shall make no wrong use of what you have said, but it was
by no means business-like, Wohlfart, to be so open toward me."
Anton was silent, feeling, indeed, that his principal was right, but yet
it seemed hard to be blamed for reposing confidence at such a time as
this. The merchant walked silently up and down; at length, stopping
before Anton, he said, "I do not now inquire how you come to take so
warm an interest in this family. I fear it is an acquaintance you owe to
Fink."
"You shall hear all," said Anton.
"Not at present. I will now content myself with repeating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interfere in these affairs without being specially
applied to by the parties themselves. I may add that I by no means wish
for such an application, and do not disguise from you that, were it
made, I should probably decline to do any thing for the Baron
Rothsattel."
Anton's feelings were roused to the utmost. "The question is the rescue
of an honorable man, and of lovely and amiable women from the toils of
rogues and impostors. To me, this seems the duty of every one; I, at
least, consider it a sacred obligation which I dare not shrink from. But
without your support I can do nothing."
"And how do you think this embarrassed man can be helped?" inquired the
merchant, seating himself.
With somewhat more composure, Anton repli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an experienced man of business making himself master of the case. There
must be some way of circumventing these villains. Your penetration would
discover it."
"Any attorney would be far more likely to do so, and the baron might
readily engage the services of experienced and upright legal advisers.
If his enemies have done any thing illegal, the quick eye of a lawyer is
the most likely to detect it."
"Alas! the baron's own lawyer gives but little hope," replied Anton.
"Then, my dear Wohlfart, no other is likely to do much good. Show me an
embarrassed man who has strength to grasp an offered hand, and bid me
help him, and for the sake of all I owe you, I will not refuse to do so.
I think you are convinced of this."
"I am," said Anton, dejectedly.
"From all I hear, however," the merchant went on,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the baron. From what I gather from general report, as well as from
you, his embarrassments arise from his having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usurers, which proves him deficient in what alone ennobles the life of
any man--good sense, and the power of steady exertion."
Anton could only sigh his assent.
"To help such a man," inexorably continued the merchant, "is a futile
attempt, against which reason may well protest. We are not to despair of
any, but want of strength is the most hopeless case of all. Our power of
laboring for others being limited, it becomes our duty to inquire,
before we devote our time to the weak, whether we are not thus
diminishing our chances of helping better men."
Anton interrupted him. "Does he not deserve every allowance to be made
for him? He was brought up to exact much; he has not learned, as we
have, to make his way by his own labor."
The merchant laid his hand on the young man's shoulder. "The very
reason. Believe me, a large number of these landed gentry, who pay the
penalty of their old family memories, are beyond help. I am the last to
deny that many worthy and admirable men belong to this class. Indeed,
wherever remarkable talent or nobility of character shoots up among
them, no doubt their position offers peculiar scope for its development,
but for average men it is not a favorable one. He who considers it his
hereditary privilege to enjoy life, and who assumes a distinguished
position in virtue of his family, will very often fail to put forth his
whole strength in order to deserve that position. Accordingly, numbers
of our oldest families are declining, and their fall will be no loss to
the state. Their family associations make them haughty without any
right to be so--limit their perceptions and confuse their judgment."
"Even if all this be true," cried Anton, "it does not absolve us from
helping individuals of the class who have excited our sympathy."
"No," said the principal, "if it be excited. But it does not glow so
rapidly in advancing years as in youth. The baron has endeavored to
isolate his property from the current of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leave it forever to his family. Forever! You, as a merchant, know how to
estimate the attempt. True, every rational man must allow it to be
desirable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same soil should be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We all prize what our forefathers have possessed before
us, and Sabine would unlock every room in this house with pride, because
her great-great-grandmother turned the same keys before her. It is
therefore natural that the landed proprietor should desire to preserve
those familiar scenes, which are the source of his own prosperity, to
those nearest and dearest to him. But there must be means to this end,
and these means are the making his own existence available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increase of his patrimony. Where energy dies in families
or individuals, then it is well that their means die too, that their
money should circulate through other hands, and their plowshare pass to
those who can guide it better. A family that has become effete through
luxury ought to sink down into common life, to make room for the
uprising of fresh energies and faculties. Every one who seeks, at the
cost of free activity for others, to preserve permanent possessions and
privileges for himself or his family, I must look upon as an enemy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social state. And if such a man ruin
himself in his endeavors, I should feel no malicious pleasure in his
downfall, but I should say that he is rightly served, because he has
sinned against a fundamental law of our social being; consequently, I
should consider it doubly wrong to support this man, because I could but
fear that I should thus be supporting an unsound condition of the body
politic."
Anton looked down mournfully. He had expected sympathy and warm
concurrence, and he met with disaffection and coldness that he despaired
of conquering. "I can not gainsay you," he at length replied; "but in
this case I can not feel as you do. I have been witness to the
unspeakable distress in the baron's family, and my whole soul is full
of sadness and sympathy, and of the wish to do something for those who
have opened their heart to me. After what you have said, I dare no
longer ask you to trouble yourself with their affairs, but I have
promised the baroness to assist her as far as my small powers permit,
and your kindness allows. I implore you to grant me permission to do
this. I shall endeavor to be regular in my attendance at the office, but
if during the next few weeks I am occasionally absent, I must ask you to
excuse me."
Once more the merchant walked up and down the room, and then, looking at
Anton's excited face, with deep seriousness and something of regret, he
replied, "Remember, Wohlfart, that every occupation which excites the
mind soon obtains a hold over a man, which may retard as well as advance
his success in life. It is thi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 to agree
to your wishes."
"I know it," said Anton, in a low voice; "but I have now no choice
left."
"Well, then, do what you must," said the merchant, gloomily; "I will lay
no hinderance in your way; and I hope that after a few weeks you will be
able to consider the whole circumstances more calmly." Anton left the
room, and the merchant stood looking long with frowning brow at the
place his clerk had occupied.
Nor was Anton in a more congenial mood. "So cold, so inexorable!"
exclaimed he, as he reached his own room. He began to suspect that his
principal was more selfish and less kindly than he had hitherto
supposed. Many an expression of Fink's recurred to his mind, as well as
that evening when young Rothsattel, in his boyish conceit, had spoken
impertinently to the merchant. "Is it possible," thought he, "that that
rude speech should be unforgotten?" And his chief's keen, deep-furrowed
face lost inexpressibly by contrast with the fair forms of the noble
ladies. "I am not wrong," he cried to himself; "let him say what he
will, my views are more just than his, and henceforth my destiny shall
be to choose for myself the way in which I shall walk." He sat long in
the darkness, and his thoughts were gloomy as it; then he went to the
window to look down into the dark court below. A great white blossom
rose before him like a phantom. Striking a light, he saw that it was the
beautiful Calla out of Sabine's room. It hung down mournfully on its
broken stem. Sabine had had it placed there. This little circumstance
struck him as a mournful omen.
Meanwhile Sabine, taper in hand, entered her brother's room.
"Good-night, Traugott," nodded she. "Wohlfart has been with you this
evening; how long he staid!"
"He will leave us," replied the merchant, gloomily.
Sabine started and dropped her taper on the table. "For God's sake, what
has happened? Has Wohlfart said that he was going away?"
"I do not yet know it, but I see it coming step by step; and I can not,
and still less can you, do any thing to retain him. When he stood before
me here with glowing cheeks and trembling voice, pleading for a ruined
man, I found out what it was that lured him away."
"I do not understand you," said Sabine, looking full at her brother.
"He chooses to become the confidential friend of a decayed noble. A pair
of bright eyes draws him away from us: it seems to him a worthy object
of ambition to become Rothsattel's man of business. This intimacy with
nobility is the legacy bequeathed to him by Fink."
"And you have refused to help him?" inquired Sabine, in a low voice.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said the merchant, harshly; and he
turned to his writing-table.
Sabine slowly withdrew. The taper trembled in her hand as she passed
through the long suite of rooms listening to her own footfall, and
shuddering as the feeling came over her that an invisible companion
glided by her side. This was the revenge of that other. The shadow that
once fell on her innocent life now drove her friend away from their
circle. Anton's affections clung to another. She had but been in his
eyes a mere stranger, who had once loved and languished for one now far
away, and who now, in widow's weeds, looked back regretfully to the
feelings of her youth.
The few next weeks were spent by Anton in over-hard work. He had great
difficulty in keeping up his counting-house duties, while he spent every
spare hour in conference with the baroness and the lawyer.
In the mean time, the misfortunes of the baron ran their course. He had
not been able to pay the interest of the sums with which his estate was
burdened. When last they were due, a whole series of claims was brought
against him, and the estate fell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district authorities. Complicated lawsuits arose. Ehrenthal complained
loudly, claiming the first mortgage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nay, he
was inclined to advance claims on the last mortgage offered by the baron
in the recent fatal hour. Löbel Pinkus also appeared as claimant of the
first mortgage, and asserted that he had paid the whole sum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Ehrenthal had no proof to bring forward, and had been
for some weeks past quite unable to manage his own affairs, while
Pinkus, on the contrary, fought with every weapon a hardened sinner can
devise or employ, and the deeds which the baron had executed at Veitel's
suggestion proved to be so capital a master-stroke of the cunning
advocate, that the baron's man of business had, from the first, little
hope of the case. We may here observe that Pinkus did eventually win it,
and that the mortgage was made over to him.
Anton was now gradually gaining some insight into the baron's
circumstances. But the double sale of the first mortgage was still kept
a secret by the latter, even from his wife. He declared Ehrenthal's
claim unfounded, and even expressed a suspicion that he had himself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robbery in his office. Indeed, he really
believed this. Then the name of Itzig was never broached, and the
suspicion against Ehrenthal, which the baron's lawyer shared, prevented
Anton seeking any explanation from him.
Meanwhile, an estrangement had sprung up between our hero and his
principal, which the whole counting-house remarked with surprise. The
merchant scowled at Anton's vacant seat when the latter chanced to be
absent during office-hours, or looked coldly at his clerk's face, made
pale as it was with excitement of mind and night-work. He took no notice
of his new occupation, and never seemed to remark him. Even to his
sister he maintained a stiff-necked silence; nor could all her attempts
lead him to speak of Anton, who, on his side, felt his heart revolt
against this coldness. After his return, to be treated like a child of
the house, praised, promoted, petted, and now to be treated like a mere
hireling, who is not worth the bread thrown to him; to be a toy of an
incomprehensible caprice--this, at least, he had not deserved; so he
became reserved toward the whole family, and sat silent at his desk; but
he fel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now and the then so keenly, that often,
when alone, he would spring up and stamp on the ground in the bitter
indignation of his heart.
One comfort remained. Sabine was not estranged. True, he saw little of
her, and at dinner she seemed to avoid speaking to him, but he knew that
she was on his side.
A few days after his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the merchant, she came down
stairs as he stood in the hall, and had to pass him by so closely that
her dress touched him. He had retreated, and made a formal bow, but she
looked at him imploringly, and whispered, "You must not be estranged
from me." It was an affair of a moment, but the faces of both were
radiant with a happy understanding.
The time had now arrived when Mr. Jordan was to quit the firm. The
principal again called Anton into his little office, and without any
severity, but also without a trace of his former cordiality, began: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o you my intention of appointing you Jordan's
successor; but,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your time has been more taken
up with other business than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such a post, I
therefore ask you whether you are now at liberty to undertake Jordan's
duties?"
"I am not," replied Anton.
"Can you name any--not very distant--time when you will be free from
your present occupation? In that case I will endeavor to find a
substitute until then."
Anton sorrowfully replied, "I can not at present say when I shall again
be master of my whole time; and, besides, I feel that, even as it is, I
tax your indulgence by many irregularities. Therefore, Mr. Schröter, I
beg that you will fill up this post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me."
The merchant's brow grew furrowed and dark, and he silently bowed
assent. Anton felt as he closed the door that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m was now complete, and, resuming his place, he leaned his throbbing
head on his hand. A moment later Baumann was summoned to the principal,
and Jordan's situation conferred upon him. On returning to the office,
he went up to Anton and whispered, "I refused at first, but Mr. Schröter
insisted. I am doing you an injustice." And that evening Mr. Baumann, in
his own room, read in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the chapters treating of
the unjust Saul (the principal), and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Jonathan
and the persecuted David, and strengthened his heart thereby.
The next day Anton was summoned to the baroness. Lenore and her mother
sat before a large table covered with jewel-boxes and toilette elegances
of every description, while a heavy iron chest stood at their feet. The
curtains were drawn, and the subdued light shone softly into the richly
furnished room. On the carpet glowed wreaths of unfading flowers, and
the clock ticked cheerfully in its alabaster case. Under the shade of
flowering plants sat the two love-birds in their silvered cage, hopping
from perch to perch, screaming ceaselessly, or sitting up quietly close
to each other. The whole room was beauty and perfume. "For how long?"
thought Anton. The baroness rose. "We are already obliged to trouble you
again," said she; "we are engaged in a very painful occupation." On the
table were all manner of ornaments, gold chains, brilliants, rings,
necklaces, gathered into a heap.
"We have been looking out all that we can dispense with," said the
baroness, "and now pray you to undertake to sell these things for us. I
have been told that some of them are of value, and as we are now in much
need of money, we turn here for help."
Anton looked in perplexity at the glittering heap.
"Tell us, Wohlfart," cried Lenore, anxiously, "is this necessary? can it
be of any use? Mamma has insisted upon setting apart for sale all our
ornaments, and whatever plate is not in daily use. What I can give is
not worth talking of, but my mother's jewels are costly; many of them
were presents made to her in youth, which she shall not part with unless
you say that it is necessary."
"I fear," said Anton, gravely, "that it will prove so."
"Take them," said the baroness to Anton; "I shall be calmer when I know
that we have at least done what we could."
"But do you wish to part with all?" inquired Anton, anxiously. "Much
that is dear to you may have but little value in a jeweler's eyes."
"I shall never wear an ornament again," quietly replied the baroness.
"Take them all;" and, holding her hands before her eyes, she turned
away.
"We are torturing my mother," cried Lenore, hastily; "will you lock up
all that is on the table, and get them out of the house as soon as you
can?"
"I can not undertake the charge of these valuables," said Anton,
"without taking some measures to decrease my own responsibility. First
of all, I will in your presence make a short note of all you intrust to
me."
"What useless cruelty!" exclaimed Lenore.
"It will not take long."
Anton took out a few sheets from his pocket-book, and began to note down
the different articles.
"You shall not see it done, mother," said Lenore, drawing her mother
away, and then returning to watch Anton at his task.
"These preparations for the market are horrible," said she. "My mother's
whole life will be sold; some memory of hers is linked with every single
thing. Look, Wohlfart, the princess gave her this diamond ornament when
she married my father."
"They are magnificent brilliants," cried Anton, admiringly.
"This ring was my grandfather's, and these are presents of poor papa's.
Alas! no man can know how we love all these things. It was always a
festival to me when mamma put on her diamonds. Now we come to my
possessions. They are not worth much. Do you think this bracelet good
gold?" She held out her hand as she spoke.
"I do not know."
"It shall go with the rest," said Lenore, taking it off. "Yes, you are a
kind, good man, Wohlfart," continued she, looking trustfully into his
tearful eyes; "do not forsake us. My brother has no experience, and is
more helpless than we are. It is a frightful position for me. Before
mamma I do all I can to be composed, else I could scream and weep the
whole day through." She sank in a chair, still holding his hand. "Dear
Wohlfart, do not forsake us."
Anton bent over her, and looked with passionate emotion at the lovely
face that turned so trustfully to him in the midst of its tears.
"I will be helpful to you when I can," said he, in the fullness of his
heart. "I will be at hand whenever you need me. You have too good an
opinion of my information and my faculties; I can be of less assistance
to you than you suppose, but what I can, that I will do in any and every
possible way."
Their hands parted with a warm pressure; the affair was settled.
The baroness now returned. "Our lawyer was with me this morning," said
she; "and now I must ask for your opinion on another subject. He tells
me that there is no prospect of preserving the baron's family estate."
"At this time, when interest is high, and money difficult to get, none,"
replied Anton.
"And you, too, think that we must turn all our efforts toward preserving
the Polish property?"
"I do," was the answer.
"For that, also, money will be necessary. Perhaps I may be able through
my relatives to intrust you with a small sum, which, with the help of
that"--she pointed to the iron chest--"may suffice to cover the first
necessary expenses. I do not, however, wish to sell the jewels here, and
a journey to the residence would be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cure the
sum to which I have just alluded. The baron's lawyer has spoken most
highly of your capacity for business. It is his wish which now decides
me to make a proposal to you. Will you for the next few years, or, at
all events, until our greatest difficulties are over, devote your whole
time to our affairs? I have consulted my children, and they agree with
me in believing that in your assistance lies our only hope of rescue.
The baron, too, has come in to the plan. The question now is whether
your circumstances allow you to give your support to our unfortunate
family. We shall be grateful to you, whatever conditions you affix; and
if you can find any way of making our great obligations to you apparent
in the position you hold, pray impart it to me."
Anton stood petrified. What the baroness required of him was separation
from the firm, separation from his principal, and from Sabine! Had this
thought occurred to him before, when standing in Lenore's presence or
bending over the baron's papers? At all events, now that the words were
spoken, they shocked him. He looked at Lenore, who stood behind her
mother with hands clasped in supplication. At length he replied, "I
stand in a position which I can not leav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others.
I was not prepared for this proposal, and beg to have time allowed me
for consideration. It is a step which will decide my whole future life."
"I do not press you," said the baroness; "I only request your
consideration. Whatever your decision be, our warmest gratitude will
still be yours; if you are unable to uphold our feeble strength, I fear
that we shall find no one to do so. You will think of that," she added,
beseechingly.
Anton hurried through the street with throbbing pulse. The noble lady's
glance of entreaty, Lenore's folded hands, beckoned him out of the
gloomy counting-house into a sphere of greater liberty, into a new
future, from whose depths bright images flashed out upon his fancy. A
request had been frankly made, and he was strongly inclined to justify
the confidence that prompted it. Those ladies required an unwearied,
self-sacrificing helper to save them from utter ruin, and if he
followed his impulse he should be doing a good work--fulfilling a duty.
In this mood he entered the merchant's dwelling. Alas! all that he saw
around him seemed to stretch out a hand to detain him. As he looked at
the warehouse, the good-humored faces of the porters, the chains of the
great scales, the hieroglyphics of the worthy Pix, again he felt that
this was the place that he belonged to. Sabine's dog kissed his hand,
and ran before him to his room--his and Fink's room. Here the childish
heart of the orphan boy had found a friend, kind companions, a home, a
definite and honorable life-purpose. Looking down through his window on
all the long-familiar objects, he saw a light in Sabine's store-chamber.
How often he had sought for that light, which brightened the whole great
building, and brought a sense of comfort and cheerfulness even into his
room. He now sprang up suddenly, and said to himself, "She shall
decide."
Sabine started in amazement when Anton appeared before her. "I am
irresistibly impelled to seek you," cried he. "I have to decide upon my
future life, and I feel undetermined, and unable to trust to my own
judgment. You have always been a kind friend to me since the day of my
arrival. I am accustomed to look up to you, and to think of you in
connection with all that interests me here. Let me hear your opinion
from your own lips. The Baroness Rothsattel has to-day proposed to me
permanently to undertake the situation of confidential adviser and
manager of the baron's affairs. Shall I accept; or shall I remain here?
I know not--tell me what is right both for myself and others."
"Not I," said Sabine, drawing back and growing very pale. "I can not
venture to decide in the matter. Nor do you wish me to do so, Wohlfart,
for you have already decided."
Anton looked straight before him and was silent.
"You have thought of leaving this house, and a wish to do so has sprung
out of the thought. And I am to justify you, and approve your resolve!
This is what you require of me," continued she, bitterly. "But this,
Wohlfart, I can not do, for I am sorry that you go away from us."
She turned away from him and leaned on the back of a chair.
"Oh, be not angry with me too!" said Anton; "that I can not bear. I have
suffered much of late. Mr. Schröter has suddenly withdrawn from me the
friendly regard that I long held my life's greatest treasure. I have not
deserved his coldness. What I have been doing has not been wrong, and
it was done with his knowledge. I had been spoiled by his kindness; I
have the more deeply felt his displeasure. My only comfort has been that
you did not condemn me. And now, do not you be cold toward me, else I
shall be wretched forever. There is not a soul on earth to whom I can
turn for affectionate comprehension of my difficulties. Had I a sister,
I should seek her heart to-day. You do not know what to me, lonely as I
am, your smile, your kindly shake of the hand has been till now. Do not
turn coldly from me, I beseech you."
Sabine was silent. At length she inquired, still with averted face,
"What draws you to those strangers; is it a joyful hope, is it sympathy
alone? Give this question close consideration before you answer it to
yourself at least."
"What it is that makes it possible for me to leave this house," said
Anton, "I do not myself know. If I can give a name to my motives, it is
gratitude felt toward one. She was the first to speak kindly to the
wandering boy on his way out into the world. I have admired her in the
peaceful brightness of her former life. I have often dreamed childish
dreams about her. There was a time when a tender feeling for her filled
my whole heart, and I then believed myself forever the slave of her
image. But years bring changes, and I learned to look on men and on life
with other eyes. Then I met her again, distressed, unhappy, despairing,
and my compassion became overmastering. When I am away from her, I know
that she is nothing to me; when I am with her, I feel only the spell of
her sorrow. Once, when I had to depart out of her circle like a culprit,
she came to me, and before the whole scornful assembly she gave me her
hand and acknowledged me her friend; and now she comes and asks for my
hand to help her father. Can I refuse it? Is it wrong to feel as I do? I
know not, and no one can tell me--no one but you alone."
Sabine's head had sunk down to the back of the chair on which she bent.
She now suddenly raised it, and with tearful eyes, and a voice full of
love and sorrow, cried, "Follow the voice that calls you. Go, Wohlfart,
go."
CHAPTER XXVII.
On a cold October day, two men were seen driving through the latticed
gate of the town of Rosmin on toward the plain, which stretched out
before them monotonous and boundless. Anton sat wrapped in his fur coat,
his hat low on his forehead, and at his side was young Sturm, in an old
cavalry cloak, with his soldier's cap cocked cheerily on one side. In
front of them a farm-servant, squatted on a heap of straw, flogged on
the small horses. The wind swept the sand and straw from the
stubble-fields, the road was a broad causeway without ditches or hedges,
the horses had to wade alternately through puddles and deep sand. Yellow
sand gleamed through the scanty herbage in all directions wherever a
field-mouse had made her way to her nest or an active mole had done what
he could to diversify the unbroken plain. Wherever the ground sank,
stagnant water lodged, and there hollow willow-trees stretched their
crippled arms in the air, their boughs flapping in the wind, and their
faded leaves fluttering down into the muddy pool below. Here and there
stood a small dwarf pine, a resting-place for the crows, who, scared by
the passing carriage, flew loudly croaking over the travelers' heads.
There was no house to be seen on the road, no pedestrian, and no
conveyance of any kind.
Karl looked every now and then at his silent companion, and said at
last, pointing to the horses, "How rough their coats are, and how pretty
their gray mouse skins! I wonder how many of these beasties would go to
make up my sergeant's horse! When I took leave of my father, the old man
said, 'Perhaps I shall pay you a visit, little one, when they light the
Christmas-tree.' 'You'll never be able,' said I. 'Why not?' asked he.
'You'll never trust yourself in any post-chaise.' Then the old boy
cried, 'Oho! post-chaises are always of a stout build; I shall be sure
to trust myself in one.' But now, Mr. Anton, I see that my father never
can pay us a visit."
"Why not?"
"It is possible that he may reach Rosmin; but, as soon as he sees these
horses and this road, he will instantly turn back. 'Shall I trust
myself,' he'll say, 'in a district where sand runs between one's legs
like water, and where mice are put into harness? The ground is not firm
enough for me.'"
"The horses are not the worst things here," said Anton, absently. "Look!
these go fast enough."
"Yes," replied Karl, "but they don't go like regular horses; they
entangle their legs like two cats playing in a parsley-bed. And what
things they have for shoes--regular webbed hoofs, I declare, which no
blacksmith can ever fit."
"If we could only get on!" returned Anton; "the wind blows cold, and I
am shivering in spite of my fur."
"You have slept but little the last few nights, sir," said Karl. "The
wind blows here as if over a threshing-floor. The earth is not round
hereabouts as elsewhere, but flat as a cake. This is a complete desert;
we have been driving for more than an hour, and there is not a village
to be seen."
"A desert indeed," sighed Anton; "let us hope it may improve." They
relapsed into profound silence. At length the driver stopped near a
pool, unharnessed the horses, and led them to the water's edge, without
noticing the travelers.
"What the deuce does this mean?" cried Karl, jumping down from the
carriage.
"I am going to feed," replied the servant, sulkily, in a foreign accent.
"I am anxious to know how that will be done," said Karl. "There is not
the shadow of a bag of provender."
The horses, however, soon proved that they could live without corn; they
stretched down their shaggy heads, and began to pull the grass and weeds
at the edge of the pool, sometimes taking a draught of the dirty water.
Meanwhile the servant drew a bundle from under his seat, settled himself
under the lee of an alder-bush, and, taking his knife, cut his bread and
cheese without even glancing at the travelers.
"I say, Ignatius or Jacob," cried Karl, sharply, "how long will this
breakfast of yours last?"
"An hour," replied the man, munching away.
"And how far is it from here to the estate?"
"Six miles, or maybe more."
"You can make nothing of him," said Anton; "we must put up with the
customs of the country;" and, leaving the carriage, they went to look on
at the horses feeding.
Anton is on his way to the Polish property. He is now the baron's agent.
Anxious months have the last proved to him. The parting from his
principal and the firm had been painful in the extreme. For some time
before it, indeed, Anton had found himself alone in the midst of his
colleagues. The quiet Baumann still remained his friend, but the others
considered him a castaway. The merchant received his resignation with
icy coldness; and even in the hour of parting, his hand lay impassive as
metal in Anton's grasp. Since then, our hero had undertaken several
journeys to the capital and to creditors in the family's behalf, and now
he was on his way to set the new estate in order, accompanied by Karl,
whom he had induced to become the baron's bailiff.
Ehrenthal had, by the authority conferred on him,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from the time of the sale by auction, and hired the Polish
bailiff for the baron. There had been unfair dealings between them at
the time, and it was well known in Rosmin that the bailiff had sold off
a good deal, and been guilty of all sorts of frauds since, so that Anton
had even now no prospect of a quiet life.
"The hour is come when I may execute my commission," cried Karl, groping
in the straw under the seat. He drew out a large japanned tin case, and
carried it to Anton. "Miss Sabine gave me this in charge for you." He
then joyously opened the lid, produced the materials for an excellent
breakfast, a bottle of wine, and a silver goblet. Anton took hold of the
case.
"It has a very knowing look," said Karl. "Miss Sabine planned it
herself."
Anton examined it on all sides, and placed it carefully on a tuft of
grass; then he took up the goblet, and saw his initials engraved on it,
and underneath the words, "To thy welfare." Whereupon he forgot the
breakfast and all around him, and stood gazing at the goblet, lost in
thought.
"Do not forget the breakfast, sir," suggested Karl, respectfully.
"Sit down by me, my faithful friend; eat and drink with me. Leave off
your absurd politeness. We shall have but little, either of us, but what
we have we will share like brothers. Take the bottle if you have no
glass."
"There's nothing like leather," said Karl, taking a small leathern
drinking-cup out of his pocket. "As for 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t was
kindly meant, and I thank you; but there must be subordination, if it
were but for the sake of the others; and so, sir, be kind enough to let
me shake hands with you now, and then let things be as they were before.
Only look at the horses, Mr. Anton. My faith! the creatures devour
thistles."
Again the horses were harnessed, again they threw out their short legs
in the sand, and again the carriage rolled through the barren
district--first through an empty plain, next through a wretched
fir-wood, then past a row of low sand-hills, then over a tumble-down
bridge crossing a small stream.
"This is the property," said the driver, turning round, and pointing
with his whip to a row of dirty thatched roofs that had just come into
sight.
Anton stood up to look for the group of trees in which the Hall might be
supposed to stand. Nothing of the sort to be seen. The village was
deficient in all that adorns the home of the poorest German peasant--no
orchard, no hedged-in gardens, no lime-trees in the market-place.
"This is wretched," said he, sitting down again; "much worse than they
told us in Rosmin."
"The village looks as if under a curse," cried Karl; "no teams working
in the fields--not a cow or a sheep to be seen."
The farm-servant flogged his horses into an irregular gallop, and so
they passed through the rows of mud huts which constituted the village,
and arrived at the public house. Karl sprang from the carriage, opened
the tavern door, and called for the landlord. A Jew slowly rose from his
seat by the stove and came to the threshold. "Is the gendarme from
Rosmin come?" He is gone into the village. "Which is the way to the
farm-yard?"
The landlord, an elderly man with an intelligent countenance, described
the way in German and Polish, and remained standing at the
door--bewildered, Karl declared, by the sight of two human beings. The
carriage turned into a cross-road, planted on both sides with thick
bushes, the remains of a fallen avenue. Over holes, stones, and puddles,
it rattled on to a group of mud huts, which still had a remnant of
whitewash upon them. "The barns and stables are empty," cried Karl, "for
I see gaps in the roofs large enough to drive our carriage through."
Anton said no more; he was prepared for every thing. They drove through
a break between the stables into the farm-yard, a large irregular space,
surrounded on three sides by tumble-down buildings, and open to the
fields on the fourth. A heap of _débris_ lay there--lime and rotten
timber, the remains of a ruined barn. The yard was empty; no trace of
farm implements or human labor to be seen. "Which is the inspector's
house," inquired Anton, in dismay. The driver looked round, and at last
made up his mind that it was a small one-storied building, with straw
thatch and dirty windows.
At the noise of the wheels a man appeared on the threshold, and waited
phlegmatically till the travelers had dismounted, and were standing
close before him. He was a broad-shouldered fellow, with a bloated,
brandy-drinking face, dressed in a jacket of shaggy cloth, while behind
him peered the muzzle of an equally shaggy dog, who snarled at the
strangers. "Are you the steward of this property?"
"I am," replied the man, in broken German, without stirring from where
he was.
"And I am the agent of the new proprietor," said Anton.
"That does not concern me," growled the shaggy man, turning sharp round,
entering the house, and bolting the door within.
Anton was thoroughly roused. "Break the window in, and help me to catch
the rascal," cried he to Karl, who coolly seized a piece of wood, struck
the panes so as to make the rotten framework give way, and cleared the
opening at one leap. Anton followed him. The room was empty, so was the
next, and in it an open window--the man was gone.
"After him!" cried Karl, and dashed on in pursuit, while Anton looked
about the house and out-buildings. He soon heard the barking of a dog,
and saw Karl capture the fugitive. Hurrying to his help, he held the man
fast, while, with a kick, Karl sent the dog flying. They then contrived
to force the steward back to the house, though he kept striking out
violently all the way.
"Go to the tavern, and bring the gendarme and the landlord," cried Anton
to the driver, who, undisturbed by all that had been going on, had
meanwhile unpacked the carriage. The man accordingly drove leisurely
off, and the fugitive being got into the room, Karl found an old cloth,
and with it bound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I beg your pardon, sir,"
said he; "it is only for an hour or so, till the arrival of the Rosmin
gendarme, whom we have appointed to meet us."
Anton then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house, bu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found but the merest necessaries; no books nor papers of any kind. It
had doubtless been emptied already. A bundle projected from the
coat-pocket of the prisoner, which turned out to be receipts and legal
documents in Polish. In time, the driver returned with the landlord and
the armed policeman. The landlord stood at the door in some perplexity,
and the policeman explained in a few moments what remained to be done.
"You must make a statement to the local judge, and give the man up to
me. He shall go back in your carriage to Rosmin. You will do well to get
rid of him, for this is a wild country, and it will be safer for you to
have him at Rosmin than here, where he has friends and accomplices."
After a long search, a sheet of paper was found in a cupboard, the
statement made and submitted to the policeman, who shook his head a
little over the Polish composition, and the prisoner lifted into the
carriage, the gendarme taking his seat beside him, and saying to Anton,
"I have long expected something of the kind. You may have often occasion
to want me again." The carriage then drove away, and thus the property
came under Anton's administration. He felt as if cast on a desert
island.
His portmanteau and traveling effects were leaning against a mud wall,
and the Polish landlord was the only man who could give him and Karl any
information or advice in their forlorn condition.
Now that the steward was fairly gone, the landlord grew more
communicative, and showed himself serviceable and obliging. A long
conversation ensued, and its purport was what Anton had apprehended from
the warning given by the Commissary Walter and other Rosmin officials.
The inspector had,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done all he could in the
way of spoliation, rendered daring by a report which had found its way
from the town to the village, that the present proprietor would never be
able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estate. At last Anton said, "What that
wretched man has done away with he will have to account for; our first
care must be to preserve what is still to be found on the property. You
must be our guide to-day."
They then examined the empty buildings. Four horses and two
servants--they were gone into the wood--a few old plows, a pair of
harrows, two wagons, a britzska, a cellar full of potatoes, a few
bundles of hay, a little straw--the inventory did not take much time in
drawing up. The buildings were all out of repair, not through age, but
neglect.
"Where is the dwelling-house?" inquired Anton. The landlord led the way
out of the yard to the meadow--a broad plain, gradually sloping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brook. It had been a great pasture. The cattle had
trodden it down into holes; the snouts of greedy swine had rooted it up;
gray molehills and rank tufts of grass rose on all sides.
The landlord stretched out his hand. "There is the castle. This castle
i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he added, reverentially; "no
nobleman in the district has a stone house like that. All the gentry
here live in wood and mud buildings. Herr von Tarow, the richest of
them, has but a poor dwelling."
About three hundred yards from the last out-building rose a great brick
edifice, with a black slate roof and a thick round tower. Its gloomy
walls on this treeless pasture-land, without one trace of life around,
rose beneath the cloudy sky like a phantom fortress which some evil
spirit had evoked from the abyss--a station from which to blight all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The strangers approached it. The castle had fallen into ruins before the
builders had finished their task. The tower had stood there for ages. It
was built of unhewn stone, and had small windows and loop-holes. The
former lords of the land had looked down from its summit on the tops of
the trees, which then stretched far into the plain. They had then ruled
with a rod of iron the serfs who cultivated their land, and toiled and
died for them. Many an arrow had sped through those loop-holes at the
enemy storming below, and many a Tartar horse had been overthrown before
those massive walls. Years ago, a despot of the district had, in
expiation of former sins, begun to add to the gray tower the walls of a
holy monastery; but the monastery never got finished, and the useless
walls had already stood there long, when the late count took it into his
head to convert them into a lordly dwelling for his race, and to raise a
house unparalleled for magnificence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 front of the house was added on to both sides of the tower, which
projected in the middle. The intention had been to have a high
terrace-road up to the castle, and the principal entrance had been made
in the tower, and arched over; but the terrace never having been formed,
the stone threshold of the main door was quite inacce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ladders, and the wide opening was left. The window-spaces of
the lower floor were merely closed up with boards, while on the second
story were some window-frames of beautifully carved wood, in which large
panes had once been placed, but they had got broken. In other windows
were temporary frames of rough deal, with small panes of muddy glass let
into them. A company of jackdaws sat on the top of the tower, looking
down in amazement on the strangers, and every now and then one flew off,
screaming loudly, to contemplate the intruders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A house for crows and bats, not for human beings," said Anton. "At
least, I see no way of getting into it."
The landlord now took them round the building. Behind, where the two
wings made a sort of horse-shoe, there were low entrances to the cellars
and offices; beneath which, again, were stables, great arched kitchens,
and small cells for the serfs. A wooden staircase led to the upper
story. The door turned creaking on its hinges, and a narrow passage took
them through a side wing to the front part of the house. There all was
at least magnificently planned. The circular entrance-hall--an arched
room of the old tower--was painted in mosaic, and through the great
doorway-opening was seen a wide expans
small disturbance made by the return of Anton had gradually settled
down. Those first-class treasures of Sabine's had made way for other
specimens of damask, still of a superior kind, it is true, but which
came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e elderly cousin's comprehension. She had
been quite right in prophesying that Anton would never remark those
signs of exuberant gratitude or their withdrawal. However, one change
had been permanently made--the greatest, the best of all changes--the
clerk retained a privileged place in the heart of the young mistress of
the firm, and his tall figure often appeared as one of the circle that
Sabine's fancy loved to gather round her when at her work-table or in
her treasure-chamber.
To-day she was walking restlessly up and down before dinner. The cousin,
who heard every thing, had just told her that a maid from Ehrenthal's
had run into the office to announce Bernhard's death to his friend. "How
will he bear it?" thought she. And the name of Ehrenthal forced her
thoughts back to the past, to one now far away, and to that painful hour
when the struggle going on in her own mind had been suddenly brought to
a close by a letter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parted. And Anton had known
of that conquered feeling of hers. How considerate he had always been,
how chivalrous, how helpful! She wondered if he had any idea of the
completeness of her triumph over a girlish illusion. She shook her head.
"No, he has not. It was here, at this very table, that an accident first
betrayed me to him. That past time still rises like a cloud between us.
Whenever I sit near Wohlfart of an evening, I am conscious of another's
shadow at my side; and when he speaks to me, his tone, his manner always
seem to say, 'You are not alone; he is with you.'" Sabine started, and
lovingly passed her hand over the beautiful flowers on the table before
her, as if to dispel a painful thought. She could not tell him that she
was free from that long-felt sorrow. Now, however, when he had lost a
friend whom he so much loved, she must show him that there were other
hearts that clung to him still. And again she walked up and down, trying
to devise a way of speaking to him alone.
Dinner was announced. Anton came with the rest, and took his place at
once. There was no opportunity of exchanging a word during the meal, but
he often met her sad and sympathizing eye. "He eats nothing at all
to-day," whispered her cousin; "not even any of the roast," she added,
reproachfully. Sabine was much perturbed. Mr. Jordan had already risen;
Anton would leave the room with the rest, and she should not see him
again the whole day through. So she called out, "The great Calla is
fully blown now. You were admiring the buds the other day; will you
remain a moment; I should like to show it you?" Anton bowed and staid
behind. A few more awkward moments, then her brother rose too; and,
hurrying to Anton, she took him to the room where the flowers were.
"You have had sorrowful tidings to-day," she began.
"The tidings themselves did not surprise me," replied Anton. "The doctor
gave no hope. But I lose much in him."
"I never saw him," said Sabine; "but I know from you that his life was
lonely--poor in affection and in enjoyment."
She moved an arm-chair toward Anton, and led him on to talk about his
friend. She listened to every word with warm sympathy, and well knew
what to ask and how to comfort. It was a relief to Anton to speak of the
departed one, to describe his quiet way of life, his erudition, his
poetical enthusiasm. After a pause, Sabine looked up frankly into his
face, and asked, "Have you any tidings of Herr von Fink?"
It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his departure that she had ever breathed his
name. Anton felt how touching her confidence was, given in this hour of
his sadness. In his emotion, he seized her hand, which she was slow in
withdrawing.
"He is not happy in his new life," he gravely replied. "There was a
savage humor in his last letter, from which I gather, even more than
from his actual words, that the business into which his uncle's death
has thrown him does not suit him."
"It is unworthy," cried Sabine.
"At all events, it is not what would be recognized as honorable in this
house," replied Anton. "Fink is upright, and has lived too long with
your brother to take pleasure in the wild speculations so common on the
other side the Atlantic. His partners and colleagues are for the most
part men without a conscience, and his feelings revolt against their
companionship."
"And can Herr von Fink tolerate such relations as these for a day?"
"It is a remarkable thing that he whose own will was ever so arbitrarily
exercised, should now be obliged against that will to obey a pressure
from without, and every where to work with his hands tied. The
organization of such speculations in America is so complicated that one
shareholder can do little to alter it; and, now that Fink has attained
what used to be the goal of his wishes--a large capital, and the
management of immense districts--his condition appears more uncertain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He was always in danger of thinking slightingly
of others, now I am distressed at the bitter contempt he expresses for
his own life. His last letter paints an intolerable state of things, and
seems to point to some decisive resolve."
"There is only one resolve for him," cried Sabine. "May I ask what you
said to him in reply?"
"I entreated him instantly, come what would, to free himself from the
business in which he was entangled. I said that his own strong will
might find a way of extrication, even if that which I pointed out proved
impracticable. Then I begged of him either to carry out his old plan of
becoming a landed proprietor in America, or to return to us."
"I knew that you would write thus," said Sabine, drawing a long breath.
"Yes, Wohlfart, he shall return," said she, gently, "but he shall not
return to us."
Anton was silent.
"And do you think that Herr von Fink will follow your advice?"
"I do not know. My advice was not very American."
"But it was worthy of you," cried Sabine, with proud delight.
"An officer wishes to speak to Mr. Wohlfart," said a servant at the
door.
Anton sprang up. Sabine went to her flowers and bent mournfully over
them. The shadows of others hovered still between her friend and her.
The few words spoken by the servant filled Anton with a vague terror. He
hurried into the ante-room: there stood Eugene von Rothsattel. Anton was
gladly rushing forward to greet him, but the young soldier's face of
agony made him start back. He whispered, "My mother wishes to speak to
you; something dreadful has occurred." Anton caught up his hat, ran into
the office, hurriedly asked Baumann to excuse him to the principal, and
then accompanied the lieutenant to the baron's house.
On the way, Eugene, who had lost all self-command, said unconnectedly to
Anton, "My father last night accidentally wounded himself by a
pistol-shot--a messenger was sent to summon me--when I came, I found my
mother in a swoon--my sister and I do not know what to do--Lenore
implored my mother on her knees to send for you--you are the only one in
whom w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our distress--I understand nothing about
business, but my father's affairs must be in a dreadful state--my mother
is beside herself--the whole house is in the greatest disorder."
From what Eugene said and what he did not say; from his broken sentences
and his look of agony, Anton guessed at the horrors of the previous
evening. In the boudoir of the baroness he found Lenore, weeping and
exhausted.
"Dear Wohlfart!" cried she, taking his hand and beginning again to sob,
while her head sank powerless on his shoulder.
Meanwhile Eugene walked up and down, wringing his hands, and at length
throwing himself on the sofa, he gave himself up to silent tears.
"It is horrible, Mr. Wohlfart," said Lenore, lifting up her head. "No
one may approach my father--Eugene may not, nor I--only my mother and
old John are with him; and early this morning the merchant Ehrenthal was
here, insisting that he must see my father. He screamed at my mother,
and called my father a deceiver, till she fainted away. When I rushed
into the room, the dreadful man went off threatening her with his
clenched fist."
Anton led Lenore to a chair and waited till she had told him all.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comforting in this case, and his own heart was
wrung to the utmost by the misery he witnessed.
"Call my mother, Eugene," said Lenore, at length.
Her brother left the room.
"Do not forsake us," implored Lenore, clasping her hands; "we are at the
last gasp; even your help can not save us."
"He is dead who might perhaps have done so," mournfully replied Anton.
"Whether I can be of any use I know not, but you can not doubt my
willingness to be so."
"No," cried Lenore. "And Eugene, too, thought of you at once."
The baroness now entered. She walked wearily; but, steadying herself by
a chair, she saluted Anton with dignity. "In our position," said she,
"we need a friend who knows more of business than we three do.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prevents the baron--possibly for a long time to
come--from managing his own affairs, and, little as I understand them, I
can see that our interests require prompt measures. My children have
mentioned you to me, but I fear I am unreasonable in asking you to
devote your time to our service."
She sat down, beckoned Anton to take a chair, and said to her children,
"Leave us; I shall be better able to tell Mr. Wohlfart the little that I
know when I do not see your grief."
When they were alone, she motioned him nearer and tried to speak, but
her lips quivered, and she hid her face in her handkerchief.
"Before I can consent, gracious lady," said he, "to your reposing in me
such confidence as this, I must first inquire whether the baron has no
relative or intimate friend to whom you could with less pain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I pray you to remember that my own knowledge of business
is but small, and my position not one to constitute me a proper
counselor to the baron."
"I know no one," said the baroness, hopelessly. "It is less painful to
me to tell you what I can not conceal, than to one of our own circle.
Consider yourself a physician sent for to visit a patient. The baron has
this morning told me some particulars of his present circumstances." And
then she proceeded to relate what she had gathered as to the nature of
his embarrassments, the danger in which the family property was placed,
and the capital needed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Polish estate.
"My husband," continued she, "has given me the key of his desk, and he
wishes Eugene, with the help of a man of business, to go over his
papers. I now request of you to make this examination together with my
son. When you need explanations, I will try to obtain them from the
baron. The question is now, whether you are inclined to undertake this
trouble for us, who are only strangers."
"I am most willing to do so," earnestly replied Anton; "and I hope that
the kindness of my principal will allow me the time needful for the
purpose, if you do not consider it more advisable to depute the baron's
experienced legal adviser to the task."
"There will be an opportunity of asking that gentleman's advice later,"
said the baroness.
Anton rose. "When do you wish to begin?"
"Immediately. I fear there is not a day to lose. I shall do all I can to
help you look the papers over." She led Anton into the next room, called
in Eugene, and unlocked the baron's desk. As she opened it she lost her
self-command for a moment, and moving to the window, the quivering of
the curtains betrayed the anguish that shook her fragile frame.
The mournful task began. Hour after hour passed. Eugene was in no
condition to peruse any thing, but his mother reached letters and
documents to Anton, and, though often obliged to desist a while, she
bravely returned to the task. Anton placed the papers in order, and
sought, by glancing over each, to arrive at least at a superficial view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It was evening, when the old servant opened the door in dismay, and
called out, "He is there again." The baroness could not repress a slight
scream, and made a gesture of aversion.
"I have told him that no one is at home, but he will not be dismissed;
he makes such a noise on the steps. I can not get rid of him."
"It will kill me if I hear his voice again," murmured the baroness.
"If the man be Ehrenthal," said Anton, rising, "I will try to get him
away. We have now done what was most necessary; have the goodness to
lock up these papers, and to allow me to return to-morrow." The baroness
silently assented, and sank back in her chair. Anton hurried off to the
ante-room, whence he could hear Ehrenthal's loudly-raised voi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usurer shocked him. His hat pushed half off his
head, his pale face swelled as if by drinking, his glazed eyes red with
tears, Ehrenthal stood before him, calling in broken sentences for the
baron, wailing and cursing alternately. "He must come! he must come at
once!" cried he; "the wicked man! A nobleman, indeed! he is a vagabond,
after whom I will send the police. Where is my money? Where is my
security? I want my mortgage from this man who is not at home."
Anton went straight up to him, and asked, "Do you know me, Mr.
Ehrenthal?" Ehrenthal turned his glazed eyes upon him, and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 friend of his dead son.
"He loved you!" he cried, in a lamentable voice. "He spoke to you more
than to his father. You were the only friend that he had on earth. Have
you heard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house of Ehrenthal?" continued he, in
a whisper. "Just as they stole the papers he died. He died with a hand
like this," and clenching his fist he struck his forehead. "Oh my son!
my son! why didst not thou forgive thy father!"
"We will go to your son," said Anton, taking the arm of the old man, who
unresistingly allowed himself to be led back to his own house.
From thence Anton hurried to Councilor Horn, with whom he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It was late before he returned home. In the midst of his anxiety about
those whose prosperity had filled his imagination years before,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in their adversity, reposed in him, dilated his
breast with a feeling of pride. He burned with desire to help them, and
hoped that his zealous devotion might yet find some way of rescue. As
yet he saw none. Looking up at the great building before him, so firm
and secure, in the moonlight, a thought flashed into his mind. If any
man could help them, it was his principal. His keen eye would be able to
unravel all the dark secrets in which the baron was entangled, and his
iron strength of will would crush the villains who held the unfortunate
nobleman in their power. And then he had a noble nature; he always
decided on the right, without an effort or a struggle. Anton looked at
the first floor. The whole house-front was dark, but in a corner room a
light still burned. It was the private office of his chief.
With sudden resolve, Anton begged the servant to take him to Mr.
Schröter, who looked with amazement at the unexpected visitor, and asked
what brought him, and whether any thing had happened.
"I implore your counsel--I implore your help," cried Anton.
"For yourself or for others?" inquired the merchant.
"For a family with whom I have accidentally become connected. They are
lost if a strong hand does not ward off the impending catastrophe."
Anton then rapidly related the occurrences of the afternoon, and,
seizing his principal's hand in his emotion, cried, "Have pity upon the
unhappy ladies, and help them."
"Help them!" replied the merchant; "how can I? Have you been
commissioned to apply to me, or are you only following the impulse of
your own feelings?"
"I am not commissioned; it is only the interest that I take in the
baron's fate which leads me to you."
"And what right have you to inform me of facts communicated in strict
confidence to yourself by the baron's lady?" asked the merchant, dryly.
"I am committing no indiscretion in telling you what will, in a few
days, be no secret, even to strangers."
"You are unusually excited, otherwise you would not forget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hatever, does a man of business venture to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without the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Of course, I shall make no wrong use of what you have said, but it was
by no means business-like, Wohlfart, to be so open toward me."
Anton was silent, feeling, indeed, that his principal was right, but yet
it seemed hard to be blamed for reposing confidence at such a time as
this. The merchant walked silently up and down; at length, stopping
before Anton, he said, "I do not now inquire how you come to take so
warm an interest in this family. I fear it is an acquaintance you owe to
Fink."
"You shall hear all," said Anton.
"Not at present. I will now content myself with repeating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interfere in these affairs without being specially
applied to by the parties themselves. I may add that I by no means wish
for such an application, and do not disguise from you that, were it
made, I should probably decline to do any thing for the Baron
Rothsattel."
Anton's feelings were roused to the utmost. "The question is the rescue
of an honorable man, and of lovely and amiable women from the toils of
rogues and impostors. To me, this seems the duty of every one; I, at
least, consider it a sacred obligation which I dare not shrink from. But
without your support I can do nothing."
"And how do you think this embarrassed man can be helped?" inquired the
merchant, seating himself.
With somewhat more composure, Anton repli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an experienced man of business making himself master of the case. There
must be some way of circumventing these villains. Your penetration would
discover it."
"Any attorney would be far more likely to do so, and the baron might
readily engage the services of experienced and upright legal advisers.
If his enemies have done any thing illegal, the quick eye of a lawyer is
the most likely to detect it."
"Alas! the baron's own lawyer gives but little hope," replied Anton.
"Then, my dear Wohlfart, no other is likely to do much good. Show me an
embarrassed man who has strength to grasp an offered hand, and bid me
help him, and for the sake of all I owe you, I will not refuse to do so.
I think you are convinced of this."
"I am," said Anton, dejectedly.
"From all I hear, however," the merchant went on,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the baron. From what I gather from general report, as well as from
you, his embarrassments arise from his having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usurers, which proves him deficient in what alone ennobles the life of
any man--good sense, and the power of steady exertion."
Anton could only sigh his assent.
"To help such a man," inexorably continued the merchant, "is a futile
attempt, against which reason may well protest. We are not to despair of
any, but want of strength is the most hopeless case of all. Our power of
laboring for others being limited, it becomes our duty to inquire,
before we devote our time to the weak, whether we are not thus
diminishing our chances of helping better men."
Anton interrupted him. "Does he not deserve every allowance to be made
for him? He was brought up to exact much; he has not learned, as we
have, to make his way by his own labor."
The merchant laid his hand on the young man's shoulder. "The very
reason. Believe me, a large number of these landed gentry, who pay the
penalty of their old family memories, are beyond help. I am the last to
deny that many worthy and admirable men belong to this class. Indeed,
wherever remarkable talent or nobility of character shoots up among
them, no doubt their position offers peculiar scope for its development,
but for average men it is not a favorable one. He who considers it his
hereditary privilege to enjoy life, and who assumes a distinguished
position in virtue of his family, will very often fail to put forth his
whole strength in order to deserve that position. Accordingly, numbers
of our oldest families are declining, and their fall will be no loss to
the state. Their family associations make them haughty without any
right to be so--limit their perceptions and confuse their judgment."
"Even if all this be true," cried Anton, "it does not absolve us from
helping individuals of the class who have excited our sympathy."
"No," said the principal, "if it be excited. But it does not glow so
rapidly in advancing years as in youth. The baron has endeavored to
isolate his property from the current of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leave it forever to his family. Forever! You, as a merchant, know how to
estimate the attempt. True, every rational man must allow it to be
desirable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same soil should be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We all prize what our forefathers have possessed before
us, and Sabine would unlock every room in this house with pride, because
her great-great-grandmother turned the same keys before her. It is
therefore natural that the landed proprietor should desire to preserve
those familiar scenes, which are the source of his own prosperity, to
those nearest and dearest to him. But there must be means to this end,
and these means are the making his own existence available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increase of his patrimony. Where energy dies in families
or individuals, then it is well that their means die too, that their
money should circulate through other hands, and their plowshare pass to
those who can guide it better. A family that has become effete through
luxury ought to sink down into common life, to make room for the
uprising of fresh energies and faculties. Every one who seeks, at the
cost of free activity for others, to preserve permanent possessions and
privileges for himself or his family, I must look upon as an enemy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social state. And if such a man ruin
himself in his endeavors, I should feel no malicious pleasure in his
downfall, but I should say that he is rightly served, because he has
sinned against a fundamental law of our social being; consequently, I
should consider it doubly wrong to support this man, because I could but
fear that I should thus be supporting an unsound condition of the body
politic."
Anton looked down mournfully. He had expected sympathy and warm
concurrence, and he met with disaffection and coldness that he despaired
of conquering. "I can not gainsay you," he at length replied; "but in
this case I can not feel as you do. I have been witness to the
unspeakable distress in the baron's family, and my whole soul is full
of sadness and sympathy, and of the wish to do something for those who
have opened their heart to me. After what you have said, I dare no
longer ask you to trouble yourself with their affairs, but I have
promised the baroness to assist her as far as my small powers permit,
and your kindness allows. I implore you to grant me permission to do
this. I shall endeavor to be regular in my attendance at the office, but
if during the next few weeks I am occasionally absent, I must ask you to
excuse me."
Once more the merchant walked up and down the room, and then, looking at
Anton's excited face, with deep seriousness and something of regret, he
replied, "Remember, Wohlfart, that every occupation which excites the
mind soon obtains a hold over a man, which may retard as well as advance
his success in life. It is thi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 to agree
to your wishes."
"I know it," said Anton, in a low voice; "but I have now no choice
left."
"Well, then, do what you must," said the merchant, gloomily; "I will lay
no hinderance in your way; and I hope that after a few weeks you will be
able to consider the whole circumstances more calmly." Anton left the
room, and the merchant stood looking long with frowning brow at the
place his clerk had occupied.
Nor was Anton in a more congenial mood. "So cold, so inexorable!"
exclaimed he, as he reached his own room. He began to suspect that his
principal was more selfish and less kindly than he had hitherto
supposed. Many an expression of Fink's recurred to his mind, as well as
that evening when young Rothsattel, in his boyish conceit, had spoken
impertinently to the merchant. "Is it possible," thought he, "that that
rude speech should be unforgotten?" And his chief's keen, deep-furrowed
face lost inexpressibly by contrast with the fair forms of the noble
ladies. "I am not wrong," he cried to himself; "let him say what he
will, my views are more just than his, and henceforth my destiny shall
be to choose for myself the way in which I shall walk." He sat long in
the darkness, and his thoughts were gloomy as it; then he went to the
window to look down into the dark court below. A great white blossom
rose before him like a phantom. Striking a light, he saw that it was the
beautiful Calla out of Sabine's room. It hung down mournfully on its
broken stem. Sabine had had it placed there. This little circumstance
struck him as a mournful omen.
Meanwhile Sabine, taper in hand, entered her brother's room.
"Good-night, Traugott," nodded she. "Wohlfart has been with you this
evening; how long he staid!"
"He will leave us," replied the merchant, gloomily.
Sabine started and dropped her taper on the table. "For God's sake, what
has happened? Has Wohlfart said that he was going away?"
"I do not yet know it, but I see it coming step by step; and I can not,
and still less can you, do any thing to retain him. When he stood before
me here with glowing cheeks and trembling voice, pleading for a ruined
man, I found out what it was that lured him away."
"I do not understand you," said Sabine, looking full at her brother.
"He chooses to become the confidential friend of a decayed noble. A pair
of bright eyes draws him away from us: it seems to him a worthy object
of ambition to become Rothsattel's man of business. This intimacy with
nobility is the legacy bequeathed to him by Fink."
"And you have refused to help him?" inquired Sabine, in a low voice.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said the merchant, harshly; and he
turned to his writing-table.
Sabine slowly withdrew. The taper trembled in her hand as she passed
through the long suite of rooms listening to her own footfall, and
shuddering as the feeling came over her that an invisible companion
glided by her side. This was the revenge of that other. The shadow that
once fell on her innocent life now drove her friend away from their
circle. Anton's affections clung to another. She had but been in his
eyes a mere stranger, who had once loved and languished for one now far
away, and who now, in widow's weeds, looked back regretfully to the
feelings of her youth.
The few next weeks were spent by Anton in over-hard work. He had great
difficulty in keeping up his counting-house duties, while he spent every
spare hour in conference with the baroness and the lawyer.
In the mean time, the misfortunes of the baron ran their course. He had
not been able to pay the interest of the sums with which his estate was
burdened. When last they were due, a whole series of claims was brought
against him, and the estate fell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district authorities. Complicated lawsuits arose. Ehrenthal complained
loudly, claiming the first mortgage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nay, he
was inclined to advance claims on the last mortgage offered by the baron
in the recent fatal hour. Löbel Pinkus also appeared as claimant of the
first mortgage, and asserted that he had paid the whole sum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Ehrenthal had no proof to bring forward, and had been
for some weeks past quite unable to manage his own affairs, while
Pinkus, on the contrary, fought with every weapon a hardened sinner can
devise or employ, and the deeds which the baron had executed at Veitel's
suggestion proved to be so capital a master-stroke of the cunning
advocate, that the baron's man of business had, from the first, little
hope of the case. We may here observe that Pinkus did eventually win it,
and that the mortgage was made over to him.
Anton was now gradually gaining some insight into the baron's
circumstances. But the double sale of the first mortgage was still kept
a secret by the latter, even from his wife. He declared Ehrenthal's
claim unfounded, and even expressed a suspicion that he had himself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robbery in his office. Indeed, he really
believed this. Then the name of Itzig was never broached, and the
suspicion against Ehrenthal, which the baron's lawyer shared, prevented
Anton seeking any explanation from him.
Meanwhile, an estrangement had sprung up between our hero and his
principal, which the whole counting-house remarked with surprise. The
merchant scowled at Anton's vacant seat when the latter chanced to be
absent during office-hours, or looked coldly at his clerk's face, made
pale as it was with excitement of mind and night-work. He took no notice
of his new occupation, and never seemed to remark him. Even to his
sister he maintained a stiff-necked silence; nor could all her attempts
lead him to speak of Anton, who, on his side, felt his heart revolt
against this coldness. After his return, to be treated like a child of
the house, praised, promoted, petted, and now to be treated like a mere
hireling, who is not worth the bread thrown to him; to be a toy of an
incomprehensible caprice--this, at least, he had not deserved; so he
became reserved toward the whole family, and sat silent at his desk; but
he fel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now and the then so keenly, that often,
when alone, he would spring up and stamp on the ground in the bitter
indignation of his heart.
One comfort remained. Sabine was not estranged. True, he saw little of
her, and at dinner she seemed to avoid speaking to him, but he knew that
she was on his side.
A few days after his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the merchant, she came down
stairs as he stood in the hall, and had to pass him by so closely that
her dress touched him. He had retreated, and made a formal bow, but she
looked at him imploringly, and whispered, "You must not be estranged
from me." It was an affair of a moment, but the faces of both were
radiant with a happy understanding.
The time had now arrived when Mr. Jordan was to quit the firm. The
principal again called Anton into his little office, and without any
severity, but also without a trace of his former cordiality, began: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o you my intention of appointing you Jordan's
successor; but,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your time has been more taken
up with other business than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such a post, I
therefore ask you whether you are now at liberty to undertake Jordan's
duties?"
"I am not," replied Anton.
"Can you name any--not very distant--time when you will be free from
your present occupation? In that case I will endeavor to find a
substitute until then."
Anton sorrowfully replied, "I can not at present say when I shall again
be master of my whole time; and, besides, I feel that, even as it is, I
tax your indulgence by many irregularities. Therefore, Mr. Schröter, I
beg that you will fill up this post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me."
The merchant's brow grew furrowed and dark, and he silently bowed
assent. Anton felt as he closed the door that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m was now complete, and, resuming his place, he leaned his throbbing
head on his hand. A moment later Baumann was summoned to the principal,
and Jordan's situation conferred upon him. On returning to the office,
he went up to Anton and whispered, "I refused at first, but Mr. Schröter
insisted. I am doing you an injustice." And that evening Mr. Baumann, in
his own room, read in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the chapters treating of
the unjust Saul (the principal), and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Jonathan
and the persecuted David, and strengthened his heart thereby.
The next day Anton was summoned to the baroness. Lenore and her mother
sat before a large table covered with jewel-boxes and toilette elegances
of every description, while a heavy iron chest stood at their feet. The
curtains were drawn, and the subdued light shone softly into the richly
furnished room. On the carpet glowed wreaths of unfading flowers, and
the clock ticked cheerfully in its alabaster case. Under the shade of
flowering plants sat the two love-birds in their silvered cage, hopping
from perch to perch, screaming ceaselessly, or sitting up quietly close
to each other. The whole room was beauty and perfume. "For how long?"
thought Anton. The baroness rose. "We are already obliged to trouble you
again," said she; "we are engaged in a very painful occupation." On the
table were all manner of ornaments, gold chains, brilliants, rings,
necklaces, gathered into a heap.
"We have been looking out all that we can dispense with," said the
baroness, "and now pray you to undertake to sell these things for us. I
have been told that some of them are of value, and as we are now in much
need of money, we turn here for help."
Anton looked in perplexity at the glittering heap.
"Tell us, Wohlfart," cried Lenore, anxiously, "is this necessary? can it
be of any use? Mamma has insisted upon setting apart for sale all our
ornaments, and whatever plate is not in daily use. What I can give is
not worth talking of, but my mother's jewels are costly; many of them
were presents made to her in youth, which she shall not part with unless
you say that it is necessary."
"I fear," said Anton, gravely, "that it will prove so."
"Take them," said the baroness to Anton; "I shall be calmer when I know
that we have at least done what we could."
"But do you wish to part with all?" inquired Anton, anxiously. "Much
that is dear to you may have but little value in a jeweler's eyes."
"I shall never wear an ornament again," quietly replied the baroness.
"Take them all;" and, holding her hands before her eyes, she turned
away.
"We are torturing my mother," cried Lenore, hastily; "will you lock up
all that is on the table, and get them out of the house as soon as you
can?"
"I can not undertake the charge of these valuables," said Anton,
"without taking some measures to decrease my own responsibility. First
of all, I will in your presence make a short note of all you intrust to
me."
"What useless cruelty!" exclaimed Lenore.
"It will not take long."
Anton took out a few sheets from his pocket-book, and began to note down
the different articles.
"You shall not see it done, mother," said Lenore, drawing her mother
away, and then returning to watch Anton at his task.
"These preparations for the market are horrible," said she. "My mother's
whole life will be sold; some memory of hers is linked with every single
thing. Look, Wohlfart, the princess gave her this diamond ornament when
she married my father."
"They are magnificent brilliants," cried Anton, admiringly.
"This ring was my grandfather's, and these are presents of poor papa's.
Alas! no man can know how we love all these things. It was always a
festival to me when mamma put on her diamonds. Now we come to my
possessions. They are not worth much. Do you think this bracelet good
gold?" She held out her hand as she spoke.
"I do not know."
"It shall go with the rest," said Lenore, taking it off. "Yes, you are a
kind, good man, Wohlfart," continued she, looking trustfully into his
tearful eyes; "do not forsake us. My brother has no experience, and is
more helpless than we are. It is a frightful position for me. Before
mamma I do all I can to be composed, else I could scream and weep the
whole day through." She sank in a chair, still holding his hand. "Dear
Wohlfart, do not forsake us."
Anton bent over her, and looked with passionate emotion at the lovely
face that turned so trustfully to him in the midst of its tears.
"I will be helpful to you when I can," said he, in the fullness of his
heart. "I will be at hand whenever you need me. You have too good an
opinion of my information and my faculties; I can be of less assistance
to you than you suppose, but what I can, that I will do in any and every
possible way."
Their hands parted with a warm pressure; the affair was settled.
The baroness now returned. "Our lawyer was with me this morning," said
she; "and now I must ask for your opinion on another subject. He tells
me that there is no prospect of preserving the baron's family estate."
"At this time, when interest is high, and money difficult to get, none,"
replied Anton.
"And you, too, think that we must turn all our efforts toward preserving
the Polish property?"
"I do," was the answer.
"For that, also, money will be necessary. Perhaps I may be able through
my relatives to intrust you with a small sum, which, with the help of
that"--she pointed to the iron chest--"may suffice to cover the first
necessary expenses. I do not, however, wish to sell the jewels here, and
a journey to the residence would be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cure the
sum to which I have just alluded. The baron's lawyer has spoken most
highly of your capacity for business. It is his wish which now decides
me to make a proposal to you. Will you for the next few years, or, at
all events, until our greatest difficulties are over, devote your whole
time to our affairs? I have consulted my children, and they agree with
me in believing that in your assistance lies our only hope of rescue.
The baron, too, has come in to the plan. The question now is whether
your circumstances allow you to give your support to our unfortunate
family. We shall be grateful to you, whatever conditions you affix; and
if you can find any way of making our great obligations to you apparent
in the position you hold, pray impart it to me."
Anton stood petrified. What the baroness required of him was separation
from the firm, separation from his principal, and from Sabine! Had this
thought occurred to him before, when standing in Lenore's presence or
bending over the baron's papers? At all events, now that the words were
spoken, they shocked him. He looked at Lenore, who stood behind her
mother with hands clasped in supplication. At length he replied, "I
stand in a position which I can not leav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others.
I was not prepared for this proposal, and beg to have time allowed me
for consideration. It is a step which will decide my whole future life."
"I do not press you," said the baroness; "I only request your
consideration. Whatever your decision be, our warmest gratitude will
still be yours; if you are unable to uphold our feeble strength, I fear
that we shall find no one to do so. You will think of that," she added,
beseechingly.
Anton hurried through the street with throbbing pulse. The noble lady's
glance of entreaty, Lenore's folded hands, beckoned him out of the
gloomy counting-house into a sphere of greater liberty, into a new
future, from whose depths bright images flashed out upon his fancy. A
request had been frankly made, and he was strongly inclined to justify
the confidence that prompted it. Those ladies required an unwearied,
self-sacrificing helper to save them from utter ruin, and if he
followed his impulse he should be doing a good work--fulfilling a duty.
In this mood he entered the merchant's dwelling. Alas! all that he saw
around him seemed to stretch out a hand to detain him. As he looked at
the warehouse, the good-humored faces of the porters, the chains of the
great scales, the hieroglyphics of the worthy Pix, again he felt that
this was the place that he belonged to. Sabine's dog kissed his hand,
and ran before him to his room--his and Fink's room. Here the childish
heart of the orphan boy had found a friend, kind companions, a home, a
definite and honorable life-purpose. Looking down through his window on
all the long-familiar objects, he saw a light in Sabine's store-chamber.
How often he had sought for that light, which brightened the whole great
building, and brought a sense of comfort and cheerfulness even into his
room. He now sprang up suddenly, and said to himself, "She shall
decide."
Sabine started in amazement when Anton appeared before her. "I am
irresistibly impelled to seek you," cried he. "I have to decide upon my
future life, and I feel undetermined, and unable to trust to my own
judgment. You have always been a kind friend to me since the day of my
arrival. I am accustomed to look up to you, and to think of you in
connection with all that interests me here. Let me hear your opinion
from your own lips. The Baroness Rothsattel has to-day proposed to me
permanently to undertake the situation of confidential adviser and
manager of the baron's affairs. Shall I accept; or shall I remain here?
I know not--tell me what is right both for myself and others."
"Not I," said Sabine, drawing back and growing very pale. "I can not
venture to decide in the matter. Nor do you wish me to do so, Wohlfart,
for you have already decided."
Anton looked straight before him and was silent.
"You have thought of leaving this house, and a wish to do so has sprung
out of the thought. And I am to justify you, and approve your resolve!
This is what you require of me," continued she, bitterly. "But this,
Wohlfart, I can not do, for I am sorry that you go away from us."
She turned away from him and leaned on the back of a chair.
"Oh, be not angry with me too!" said Anton; "that I can not bear. I have
suffered much of late. Mr. Schröter has suddenly withdrawn from me the
friendly regard that I long held my life's greatest treasure. I have not
deserved his coldness. What I have been doing has not been wrong, and
it was done with his knowledge. I had been spoiled by his kindness; I
have the more deeply felt his displeasure. My only comfort has been that
you did not condemn me. And now, do not you be cold toward me, else I
shall be wretched forever. There is not a soul on earth to whom I can
turn for affectionate comprehension of my difficulties. Had I a sister,
I should seek her heart to-day. You do not know what to me, lonely as I
am, your smile, your kindly shake of the hand has been till now. Do not
turn coldly from me, I beseech you."
Sabine was silent. At length she inquired, still with averted face,
"What draws you to those strangers; is it a joyful hope, is it sympathy
alone? Give this question close consideration before you answer it to
yourself at least."
"What it is that makes it possible for me to leave this house," said
Anton, "I do not myself know. If I can give a name to my motives, it is
gratitude felt toward one. She was the first to speak kindly to the
wandering boy on his way out into the world. I have admired her in the
peaceful brightness of her former life. I have often dreamed childish
dreams about her. There was a time when a tender feeling for her filled
my whole heart, and I then believed myself forever the slave of her
image. But years bring changes, and I learned to look on men and on life
with other eyes. Then I met her again, distressed, unhappy, despairing,
and my compassion became overmastering. When I am away from her, I know
that she is nothing to me; when I am with her, I feel only the spell of
her sorrow. Once, when I had to depart out of her circle like a culprit,
she came to me, and before the whole scornful assembly she gave me her
hand and acknowledged me her friend; and now she comes and asks for my
hand to help her father. Can I refuse it? Is it wrong to feel as I do? I
know not, and no one can tell me--no one but you alone."
Sabine's head had sunk down to the back of the chair on which she bent.
She now suddenly raised it, and with tearful eyes, and a voice full of
love and sorrow, cried, "Follow the voice that calls you. Go, Wohlfart,
go."
CHAPTER XXVII.
On a cold October day, two men were seen driving through the latticed
gate of the town of Rosmin on toward the plain, which stretched out
before them monotonous and boundless. Anton sat wrapped in his fur coat,
his hat low on his forehead, and at his side was young Sturm, in an old
cavalry cloak, with his soldier's cap cocked cheerily on one side. In
front of them a farm-servant, squatted on a heap of straw, flogged on
the small horses. The wind swept the sand and straw from the
stubble-fields, the road was a broad causeway without ditches or hedges,
the horses had to wade alternately through puddles and deep sand. Yellow
sand gleamed through the scanty herbage in all directions wherever a
field-mouse had made her way to her nest or an active mole had done what
he could to diversify the unbroken plain. Wherever the ground sank,
stagnant water lodged, and there hollow willow-trees stretched their
crippled arms in the air, their boughs flapping in the wind, and their
faded leaves fluttering down into the muddy pool below. Here and there
stood a small dwarf pine, a resting-place for the crows, who, scared by
the passing carriage, flew loudly croaking over the travelers' heads.
There was no house to be seen on the road, no pedestrian, and no
conveyance of any kind.
Karl looked every now and then at his silent companion, and said at
last, pointing to the horses, "How rough their coats are, and how pretty
their gray mouse skins! I wonder how many of these beasties would go to
make up my sergeant's horse! When I took leave of my father, the old man
said, 'Perhaps I shall pay you a visit, little one, when they light the
Christmas-tree.' 'You'll never be able,' said I. 'Why not?' asked he.
'You'll never trust yourself in any post-chaise.' Then the old boy
cried, 'Oho! post-chaises are always of a stout build; I shall be sure
to trust myself in one.' But now, Mr. Anton, I see that my father never
can pay us a visit."
"Why not?"
"It is possible that he may reach Rosmin; but, as soon as he sees these
horses and this road, he will instantly turn back. 'Shall I trust
myself,' he'll say, 'in a district where sand runs between one's legs
like water, and where mice are put into harness? The ground is not firm
enough for me.'"
"The horses are not the worst things here," said Anton, absently. "Look!
these go fast enough."
"Yes," replied Karl, "but they don't go like regular horses; they
entangle their legs like two cats playing in a parsley-bed. And what
things they have for shoes--regular webbed hoofs, I declare, which no
blacksmith can ever fit."
"If we could only get on!" returned Anton; "the wind blows cold, and I
am shivering in spite of my fur."
"You have slept but little the last few nights, sir," said Karl. "The
wind blows here as if over a threshing-floor. The earth is not round
hereabouts as elsewhere, but flat as a cake. This is a complete desert;
we have been driving for more than an hour, and there is not a village
to be seen."
"A desert indeed," sighed Anton; "let us hope it may improve." They
relapsed into profound silence. At length the driver stopped near a
pool, unharnessed the horses, and led them to the water's edge, without
noticing the travelers.
"What the deuce does this mean?" cried Karl, jumping down from the
carriage.
"I am going to feed," replied the servant, sulkily, in a foreign accent.
"I am anxious to know how that will be done," said Karl. "There is not
the shadow of a bag of provender."
The horses, however, soon proved that they could live without corn; they
stretched down their shaggy heads, and began to pull the grass and weeds
at the edge of the pool, sometimes taking a draught of the dirty water.
Meanwhile the servant drew a bundle from under his seat, settled himself
under the lee of an alder-bush, and, taking his knife, cut his bread and
cheese without even glancing at the travelers.
"I say, Ignatius or Jacob," cried Karl, sharply, "how long will this
breakfast of yours last?"
"An hour," replied the man, munching away.
"And how far is it from here to the estate?"
"Six miles, or maybe more."
"You can make nothing of him," said Anton; "we must put up with the
customs of the country;" and, leaving the carriage, they went to look on
at the horses feeding.
Anton is on his way to the Polish property. He is now the baron's agent.
Anxious months have the last proved to him. The parting from his
principal and the firm had been painful in the extreme. For some time
before it, indeed, Anton had found himself alone in the midst of his
colleagues. The quiet Baumann still remained his friend, but the others
considered him a castaway. The merchant received his resignation with
icy coldness; and even in the hour of parting, his hand lay impassive as
metal in Anton's grasp. Since then, our hero had undertaken several
journeys to the capital and to creditors in the family's behalf, and now
he was on his way to set the new estate in order, accompanied by Karl,
whom he had induced to become the baron's bailiff.
Ehrenthal had, by the authority conferred on him,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from the time of the sale by auction, and hired the Polish
bailiff for the baron. There had been unfair dealings between them at
the time, and it was well known in Rosmin that the bailiff had sold off
a good deal, and been guilty of all sorts of frauds since, so that Anton
had even now no prospect of a quiet life.
"The hour is come when I may execute my commission," cried Karl, groping
in the straw under the seat. He drew out a large japanned tin case, and
carried it to Anton. "Miss Sabine gave me this in charge for you." He
then joyously opened the lid, produced the materials for an excellent
breakfast, a bottle of wine, and a silver goblet. Anton took hold of the
case.
"It has a very knowing look," said Karl. "Miss Sabine planned it
herself."
Anton examined it on all sides, and placed it carefully on a tuft of
grass; then he took up the goblet, and saw his initials engraved on it,
and underneath the words, "To thy welfare." Whereupon he forgot the
breakfast and all around him, and stood gazing at the goblet, lost in
thought.
"Do not forget the breakfast, sir," suggested Karl, respectfully.
"Sit down by me, my faithful friend; eat and drink with me. Leave off
your absurd politeness. We shall have but little, either of us, but what
we have we will share like brothers. Take the bottle if you have no
glass."
"There's nothing like leather," said Karl, taking a small leathern
drinking-cup out of his pocket. "As for 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t was
kindly meant, and I thank you; but there must be subordination, if it
were but for the sake of the others; and so, sir, be kind enough to let
me shake hands with you now, and then let things be as they were before.
Only look at the horses, Mr. Anton. My faith! the creatures devour
thistles."
Again the horses were harnessed, again they threw out their short legs
in the sand, and again the carriage rolled through the barren
district--first through an empty plain, next through a wretched
fir-wood, then past a row of low sand-hills, then over a tumble-down
bridge crossing a small stream.
"This is the property," said the driver, turning round, and pointing
with his whip to a row of dirty thatched roofs that had just come into
sight.
Anton stood up to look for the group of trees in which the Hall might be
supposed to stand. Nothing of the sort to be seen. The village was
deficient in all that adorns the home of the poorest German peasant--no
orchard, no hedged-in gardens, no lime-trees in the market-place.
"This is wretched," said he, sitting down again; "much worse than they
told us in Rosmin."
"The village looks as if under a curse," cried Karl; "no teams working
in the fields--not a cow or a sheep to be seen."
The farm-servant flogged his horses into an irregular gallop, and so
they passed through the rows of mud huts which constituted the village,
and arrived at the public house. Karl sprang from the carriage, opened
the tavern door, and called for the landlord. A Jew slowly rose from his
seat by the stove and came to the threshold. "Is the gendarme from
Rosmin come?" He is gone into the village. "Which is the way to the
farm-yard?"
The landlord, an elderly man with an intelligent countenance, described
the way in German and Polish, and remained standing at the
door--bewildered, Karl declared, by the sight of two human beings. The
carriage turned into a cross-road, planted on both sides with thick
bushes, the remains of a fallen avenue. Over holes, stones, and puddles,
it rattled on to a group of mud huts, which still had a remnant of
whitewash upon them. "The barns and stables are empty," cried Karl, "for
I see gaps in the roofs large enough to drive our carriage through."
Anton said no more; he was prepared for every thing. They drove through
a break between the stables into the farm-yard, a large irregular space,
surrounded on three sides by tumble-down buildings, and open to the
fields on the fourth. A heap of _débris_ lay there--lime and rotten
timber, the remains of a ruined barn. The yard was empty; no trace of
farm implements or human labor to be seen. "Which is the inspector's
house," inquired Anton, in dismay. The driver looked round, and at last
made up his mind that it was a small one-storied building, with straw
thatch and dirty windows.
At the noise of the wheels a man appeared on the threshold, and waited
phlegmatically till the travelers had dismounted, and were standing
close before him. He was a broad-shouldered fellow, with a bloated,
brandy-drinking face, dressed in a jacket of shaggy cloth, while behind
him peered the muzzle of an equally shaggy dog, who snarled at the
strangers. "Are you the steward of this property?"
"I am," replied the man, in broken German, without stirring from where
he was.
"And I am the agent of the new proprietor," said Anton.
"That does not concern me," growled the shaggy man, turning sharp round,
entering the house, and bolting the door within.
Anton was thoroughly roused. "Break the window in, and help me to catch
the rascal," cried he to Karl, who coolly seized a piece of wood, struck
the panes so as to make the rotten framework give way, and cleared the
opening at one leap. Anton followed him. The room was empty, so was the
next, and in it an open window--the man was gone.
"After him!" cried Karl, and dashed on in pursuit, while Anton looked
about the house and out-buildings. He soon heard the barking of a dog,
and saw Karl capture the fugitive. Hurrying to his help, he held the man
fast, while, with a kick, Karl sent the dog flying. They then contrived
to force the steward back to the house, though he kept striking out
violently all the way.
"Go to the tavern, and bring the gendarme and the landlord," cried Anton
to the driver, who, undisturbed by all that had been going on, had
meanwhile unpacked the carriage. The man accordingly drove leisurely
off, and the fugitive being got into the room, Karl found an old cloth,
and with it bound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I beg your pardon, sir,"
said he; "it is only for an hour or so, till the arrival of the Rosmin
gendarme, whom we have appointed to meet us."
Anton then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house, bu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found but the merest necessaries; no books nor papers of any kind. It
had doubtless been emptied already. A bundle projected from the
coat-pocket of the prisoner, which turned out to be receipts and legal
documents in Polish. In time, the driver returned with the landlord and
the armed policeman. The landlord stood at the door in some perplexity,
and the policeman explained in a few moments what remained to be done.
"You must make a statement to the local judge, and give the man up to
me. He shall go back in your carriage to Rosmin. You will do well to get
rid of him, for this is a wild country, and it will be safer for you to
have him at Rosmin than here, where he has friends and accomplices."
After a long search, a sheet of paper was found in a cupboard, the
statement made and submitted to the policeman, who shook his head a
little over the Polish composition, and the prisoner lifted into the
carriage, the gendarme taking his seat beside him, and saying to Anton,
"I have long expected something of the kind. You may have often occasion
to want me again." The carriage then drove away, and thus the property
came under Anton's administration. He felt as if cast on a desert
island.
His portmanteau and traveling effects were leaning against a mud wall,
and the Polish landlord was the only man who could give him and Karl any
information or advice in their forlorn condition.
Now that the steward was fairly gone, the landlord grew more
communicative, and showed himself serviceable and obliging. A long
conversation ensued, and its purport was what Anton had apprehended from
the warning given by the Commissary Walter and other Rosmin officials.
The inspector had,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done all he could in the
way of spoliation, rendered daring by a report which had found its way
from the town to the village, that the present proprietor would never be
able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estate. At last Anton said, "What that
wretched man has done away with he will have to account for; our first
care must be to preserve what is still to be found on the property. You
must be our guide to-day."
They then examined the empty buildings. Four horses and two
servants--they were gone into the wood--a few old plows, a pair of
harrows, two wagons, a britzska, a cellar full of potatoes, a few
bundles of hay, a little straw--the inventory did not take much time in
drawing up. The buildings were all out of repair, not through age, but
neglect.
"Where is the dwelling-house?" inquired Anton. The landlord led the way
out of the yard to the meadow--a broad plain, gradually sloping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brook. It had been a great pasture. The cattle had
trodden it down into holes; the snouts of greedy swine had rooted it up;
gray molehills and rank tufts of grass rose on all sides.
The landlord stretched out his hand. "There is the castle. This castle
i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he added, reverentially; "no
nobleman in the district has a stone house like that. All the gentry
here live in wood and mud buildings. Herr von Tarow, the richest of
them, has but a poor dwelling."
About three hundred yards from the last out-building rose a great brick
edifice, with a black slate roof and a thick round tower. Its gloomy
walls on this treeless pasture-land, without one trace of life around,
rose beneath the cloudy sky like a phantom fortress which some evil
spirit had evoked from the abyss--a station from which to blight all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The strangers approached it. The castle had fallen into ruins before the
builders had finished their task. The tower had stood there for ages. It
was built of unhewn stone, and had small windows and loop-holes. The
former lords of the land had looked down from its summit on the tops of
the trees, which then stretched far into the plain. They had then ruled
with a rod of iron the serfs who cultivated their land, and toiled and
died for them. Many an arrow had sped through those loop-holes at the
enemy storming below, and many a Tartar horse had been overthrown before
those massive walls. Years ago, a despot of the district had, in
expiation of former sins, begun to add to the gray tower the walls of a
holy monastery; but the monastery never got finished, and the useless
walls had already stood there long, when the late count took it into his
head to convert them into a lordly dwelling for his race, and to raise a
house unparalleled for magnificence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 front of the house was added on to both sides of the tower, which
projected in the middle. The intention had been to have a high
terrace-road up to the castle, and the principal entrance had been made
in the tower, and arched over; but the terrace never having been formed,
the stone threshold of the main door was quite inacce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ladders, and the wide opening was left. The window-spaces of
the lower floor were merely closed up with boards, while on the second
story were some window-frames of beautifully carved wood, in which large
panes had once been placed, but they had got broken. In other windows
were temporary frames of rough deal, with small panes of muddy glass let
into them. A company of jackdaws sat on the top of the tower, looking
down in amazement on the strangers, and every now and then one flew off,
screaming loudly, to contemplate the intruders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A house for crows and bats, not for human beings," said Anton. "At
least, I see no way of getting into it."
The landlord now took them round the building. Behind, where the two
wings made a sort of horse-shoe, there were low entrances to the cellars
and offices; beneath which, again, were stables, great arched kitchens,
and small cells for the serfs. A wooden staircase led to the upper
story. The door turned creaking on its hinges, and a narrow passage took
them through a side wing to the front part of the house. There all was
at least magnificently planned. The circular entrance-hall--an arched
room of the old tower--was painted in mosaic, and through the great
doorway-opening was seen a wide expans
small disturbance made by the return of Anton had gradually settled
down. Those first-class treasures of Sabine's had made way for other
specimens of damask, still of a superior kind, it is true, but which
came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e elderly cousin's comprehension. She had
been quite right in prophesying that Anton would never remark those
signs of exuberant gratitude or their withdrawal. However, one change
had been permanently made--the greatest, the best of all changes--the
clerk retained a privileged place in the heart of the young mistress of
the firm, and his tall figure often appeared as one of the circle that
Sabine's fancy loved to gather round her when at her work-table or in
her treasure-chamber.
To-day she was walking restlessly up and down before dinner. The cousin,
who heard every thing, had just told her that a maid from Ehrenthal's
had run into the office to announce Bernhard's death to his friend. "How
will he bear it?" thought she. And the name of Ehrenthal forced her
thoughts back to the past, to one now far away, and to that painful hour
when the struggle going on in her own mind had been suddenly brought to
a close by a letter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parted. And Anton had known
of that conquered feeling of hers. How considerate he had always been,
how chivalrous, how helpful! She wondered if he had any idea of the
completeness of her triumph over a girlish illusion. She shook her head.
"No, he has not. It was here, at this very table, that an accident first
betrayed me to him. That past time still rises like a cloud between us.
Whenever I sit near Wohlfart of an evening, I am conscious of another's
shadow at my side; and when he speaks to me, his tone, his manner always
seem to say, 'You are not alone; he is with you.'" Sabine started, and
lovingly passed her hand over the beautiful flowers on the table before
her, as if to dispel a painful thought. She could not tell him that she
was free from that long-felt sorrow. Now, however, when he had lost a
friend whom he so much loved, she must show him that there were other
hearts that clung to him still. And again she walked up and down, trying
to devise a way of speaking to him alone.
Dinner was announced. Anton came with the rest, and took his place at
once. There was no opportunity of exchanging a word during the meal, but
he often met her sad and sympathizing eye. "He eats nothing at all
to-day," whispered her cousin; "not even any of the roast," she added,
reproachfully. Sabine was much perturbed. Mr. Jordan had already risen;
Anton would leave the room with the rest, and she should not see him
again the whole day through. So she called out, "The great Calla is
fully blown now. You were admiring the buds the other day; will you
remain a moment; I should like to show it you?" Anton bowed and staid
behind. A few more awkward moments, then her brother rose too; and,
hurrying to Anton, she took him to the room where the flowers were.
"You have had sorrowful tidings to-day," she began.
"The tidings themselves did not surprise me," replied Anton. "The doctor
gave no hope. But I lose much in him."
"I never saw him," said Sabine; "but I know from you that his life was
lonely--poor in affection and in enjoyment."
She moved an arm-chair toward Anton, and led him on to talk about his
friend. She listened to every word with warm sympathy, and well knew
what to ask and how to comfort. It was a relief to Anton to speak of the
departed one, to describe his quiet way of life, his erudition, his
poetical enthusiasm. After a pause, Sabine looked up frankly into his
face, and asked, "Have you any tidings of Herr von Fink?"
It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his departure that she had ever breathed his
name. Anton felt how touching her confidence was, given in this hour of
his sadness. In his emotion, he seized her hand, which she was slow in
withdrawing.
"He is not happy in his new life," he gravely replied. "There was a
savage humor in his last letter, from which I gather, even more than
from his actual words, that the business into which his uncle's death
has thrown him does not suit him."
"It is unworthy," cried Sabine.
"At all events, it is not what would be recognized as honorable in this
house," replied Anton. "Fink is upright, and has lived too long with
your brother to take pleasure in the wild speculations so common on the
other side the Atlantic. His partners and colleagues are for the most
part men without a conscience, and his feelings revolt against their
companionship."
"And can Herr von Fink tolerate such relations as these for a day?"
"It is a remarkable thing that he whose own will was ever so arbitrarily
exercised, should now be obliged against that will to obey a pressure
from without, and every where to work with his hands tied. The
organization of such speculations in America is so complicated that one
shareholder can do little to alter it; and, now that Fink has attained
what used to be the goal of his wishes--a large capital, and the
management of immense districts--his condition appears more uncertain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He was always in danger of thinking slightingly
of others, now I am distressed at the bitter contempt he expresses for
his own life. His last letter paints an intolerable state of things, and
seems to point to some decisive resolve."
"There is only one resolve for him," cried Sabine. "May I ask what you
said to him in reply?"
"I entreated him instantly, come what would, to free himself from the
business in which he was entangled. I said that his own strong will
might find a way of extrication, even if that which I pointed out proved
impracticable. Then I begged of him either to carry out his old plan of
becoming a landed proprietor in America, or to return to us."
"I knew that you would write thus," said Sabine, drawing a long breath.
"Yes, Wohlfart, he shall return," said she, gently, "but he shall not
return to us."
Anton was silent.
"And do you think that Herr von Fink will follow your advice?"
"I do not know. My advice was not very American."
"But it was worthy of you," cried Sabine, with proud delight.
"An officer wishes to speak to Mr. Wohlfart," said a servant at the
door.
Anton sprang up. Sabine went to her flowers and bent mournfully over
them. The shadows of others hovered still between her friend and her.
The few words spoken by the servant filled Anton with a vague terror. He
hurried into the ante-room: there stood Eugene von Rothsattel. Anton was
gladly rushing forward to greet him, but the young soldier's face of
agony made him start back. He whispered, "My mother wishes to speak to
you; something dreadful has occurred." Anton caught up his hat, ran into
the office, hurriedly asked Baumann to excuse him to the principal, and
then accompanied the lieutenant to the baron's house.
On the way, Eugene, who had lost all self-command, said unconnectedly to
Anton, "My father last night accidentally wounded himself by a
pistol-shot--a messenger was sent to summon me--when I came, I found my
mother in a swoon--my sister and I do not know what to do--Lenore
implored my mother on her knees to send for you--you are the only one in
whom w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our distress--I understand nothing about
business, but my father's affairs must be in a dreadful state--my mother
is beside herself--the whole house is in the greatest disorder."
From what Eugene said and what he did not say; from his broken sentences
and his look of agony, Anton guessed at the horrors of the previous
evening. In the boudoir of the baroness he found Lenore, weeping and
exhausted.
"Dear Wohlfart!" cried she, taking his hand and beginning again to sob,
while her head sank powerless on his shoulder.
Meanwhile Eugene walked up and down, wringing his hands, and at length
throwing himself on the sofa, he gave himself up to silent tears.
"It is horrible, Mr. Wohlfart," said Lenore, lifting up her head. "No
one may approach my father--Eugene may not, nor I--only my mother and
old John are with him; and early this morning the merchant Ehrenthal was
here, insisting that he must see my father. He screamed at my mother,
and called my father a deceiver, till she fainted away. When I rushed
into the room, the dreadful man went off threatening her with his
clenched fist."
Anton led Lenore to a chair and waited till she had told him all.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comforting in this case, and his own heart was
wrung to the utmost by the misery he witnessed.
"Call my mother, Eugene," said Lenore, at length.
Her brother left the room.
"Do not forsake us," implored Lenore, clasping her hands; "we are at the
last gasp; even your help can not save us."
"He is dead who might perhaps have done so," mournfully replied Anton.
"Whether I can be of any use I know not, but you can not doubt my
willingness to be so."
"No," cried Lenore. "And Eugene, too, thought of you at once."
The baroness now entered. She walked wearily; but, steadying herself by
a chair, she saluted Anton with dignity. "In our position," said she,
"we need a friend who knows more of business than we three do.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prevents the baron--possibly for a long time to
come--from managing his own affairs, and, little as I understand them, I
can see that our interests require prompt measures. My children have
mentioned you to me, but I fear I am unreasonable in asking you to
devote your time to our service."
She sat down, beckoned Anton to take a chair, and said to her children,
"Leave us; I shall be better able to tell Mr. Wohlfart the little that I
know when I do not see your grief."
When they were alone, she motioned him nearer and tried to speak, but
her lips quivered, and she hid her face in her handkerchief.
"Before I can consent, gracious lady," said he, "to your reposing in me
such confidence as this, I must first inquire whether the baron has no
relative or intimate friend to whom you could with less pain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I pray you to remember that my own knowledge of business
is but small, and my position not one to constitute me a proper
counselor to the baron."
"I know no one," said the baroness, hopelessly. "It is less painful to
me to tell you what I can not conceal, than to one of our own circle.
Consider yourself a physician sent for to visit a patient. The baron has
this morning told me some particulars of his present circumstances." And
then she proceeded to relate what she had gathered as to the nature of
his embarrassments, the danger in which the family property was placed,
and the capital needed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Polish estate.
"My husband," continued she, "has given me the key of his desk, and he
wishes Eugene, with the help of a man of business, to go over his
papers. I now request of you to make this examination together with my
son. When you need explanations, I will try to obtain them from the
baron. The question is now, whether you are inclined to undertake this
trouble for us, who are only strangers."
"I am most willing to do so," earnestly replied Anton; "and I hope that
the kindness of my principal will allow me the time needful for the
purpose, if you do not consider it more advisable to depute the baron's
experienced legal adviser to the task."
"There will be an opportunity of asking that gentleman's advice later,"
said the baroness.
Anton rose. "When do you wish to begin?"
"Immediately. I fear there is not a day to lose. I shall do all I can to
help you look the papers over." She led Anton into the next room, called
in Eugene, and unlocked the baron's desk. As she opened it she lost her
self-command for a moment, and moving to the window, the quivering of
the curtains betrayed the anguish that shook her fragile frame.
The mournful task began. Hour after hour passed. Eugene was in no
condition to peruse any thing, but his mother reached letters and
documents to Anton, and, though often obliged to desist a while, she
bravely returned to the task. Anton placed the papers in order, and
sought, by glancing over each, to arrive at least at a superficial view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It was evening, when the old servant opened the door in dismay, and
called out, "He is there again." The baroness could not repress a slight
scream, and made a gesture of aversion.
"I have told him that no one is at home, but he will not be dismissed;
he makes such a noise on the steps. I can not get rid of him."
"It will kill me if I hear his voice again," murmured the baroness.
"If the man be Ehrenthal," said Anton, rising, "I will try to get him
away. We have now done what was most necessary; have the goodness to
lock up these papers, and to allow me to return to-morrow." The baroness
silently assented, and sank back in her chair. Anton hurried off to the
ante-room, whence he could hear Ehrenthal's loudly-raised voi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usurer shocked him. His hat pushed half off his
head, his pale face swelled as if by drinking, his glazed eyes red with
tears, Ehrenthal stood before him, calling in broken sentences for the
baron, wailing and cursing alternately. "He must come! he must come at
once!" cried he; "the wicked man! A nobleman, indeed! he is a vagabond,
after whom I will send the police. Where is my money? Where is my
security? I want my mortgage from this man who is not at home."
Anton went straight up to him, and asked, "Do you know me, Mr.
Ehrenthal?" Ehrenthal turned his glazed eyes upon him, and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 friend of his dead son.
"He loved you!" he cried, in a lamentable voice. "He spoke to you more
than to his father. You were the only friend that he had on earth. Have
you heard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house of Ehrenthal?" continued he, in
a whisper. "Just as they stole the papers he died. He died with a hand
like this," and clenching his fist he struck his forehead. "Oh my son!
my son! why didst not thou forgive thy father!"
"We will go to your son," said Anton, taking the arm of the old man, who
unresistingly allowed himself to be led back to his own house.
From thence Anton hurried to Councilor Horn, with whom he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It was late before he returned home. In the midst of his anxiety about
those whose prosperity had filled his imagination years before,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in their adversity, reposed in him, dilated his
breast with a feeling of pride. He burned with desire to help them, and
hoped that his zealous devotion might yet find some way of rescue. As
yet he saw none. Looking up at the great building before him, so firm
and secure, in the moonlight, a thought flashed into his mind. If any
man could help them, it was his principal. His keen eye would be able to
unravel all the dark secrets in which the baron was entangled, and his
iron strength of will would crush the villains who held the unfortunate
nobleman in their power. And then he had a noble nature; he always
decided on the right, without an effort or a struggle. Anton looked at
the first floor. The whole house-front was dark, but in a corner room a
light still burned. It was the private office of his chief.
With sudden resolve, Anton begged the servant to take him to Mr.
Schröter, who looked with amazement at the unexpected visitor, and asked
what brought him, and whether any thing had happened.
"I implore your counsel--I implore your help," cried Anton.
"For yourself or for others?" inquired the merchant.
"For a family with whom I have accidentally become connected. They are
lost if a strong hand does not ward off the impending catastrophe."
Anton then rapidly related the occurrences of the afternoon, and,
seizing his principal's hand in his emotion, cried, "Have pity upon the
unhappy ladies, and help them."
"Help them!" replied the merchant; "how can I? Have you been
commissioned to apply to me, or are you only following the impulse of
your own feelings?"
"I am not commissioned; it is only the interest that I take in the
baron's fate which leads me to you."
"And what right have you to inform me of facts communicated in strict
confidence to yourself by the baron's lady?" asked the merchant, dryly.
"I am committing no indiscretion in telling you what will, in a few
days, be no secret, even to strangers."
"You are unusually excited, otherwise you would not forget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hatever, does a man of business venture to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without the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Of course, I shall make no wrong use of what you have said, but it was
by no means business-like, Wohlfart, to be so open toward me."
Anton was silent, feeling, indeed, that his principal was right, but yet
it seemed hard to be blamed for reposing confidence at such a time as
this. The merchant walked silently up and down; at length, stopping
before Anton, he said, "I do not now inquire how you come to take so
warm an interest in this family. I fear it is an acquaintance you owe to
Fink."
"You shall hear all," said Anton.
"Not at present. I will now content myself with repeating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interfere in these affairs without being specially
applied to by the parties themselves. I may add that I by no means wish
for such an application, and do not disguise from you that, were it
made, I should probably decline to do any thing for the Baron
Rothsattel."
Anton's feelings were roused to the utmost. "The question is the rescue
of an honorable man, and of lovely and amiable women from the toils of
rogues and impostors. To me, this seems the duty of every one; I, at
least, consider it a sacred obligation which I dare not shrink from. But
without your support I can do nothing."
"And how do you think this embarrassed man can be helped?" inquired the
merchant, seating himself.
With somewhat more composure, Anton repli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an experienced man of business making himself master of the case. There
must be some way of circumventing these villains. Your penetration would
discover it."
"Any attorney would be far more likely to do so, and the baron might
readily engage the services of experienced and upright legal advisers.
If his enemies have done any thing illegal, the quick eye of a lawyer is
the most likely to detect it."
"Alas! the baron's own lawyer gives but little hope," replied Anton.
"Then, my dear Wohlfart, no other is likely to do much good. Show me an
embarrassed man who has strength to grasp an offered hand, and bid me
help him, and for the sake of all I owe you, I will not refuse to do so.
I think you are convinced of this."
"I am," said Anton, dejectedly.
"From all I hear, however," the merchant went on,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the baron. From what I gather from general report, as well as from
you, his embarrassments arise from his having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usurers, which proves him deficient in what alone ennobles the life of
any man--good sense, and the power of steady exertion."
Anton could only sigh his assent.
"To help such a man," inexorably continued the merchant, "is a futile
attempt, against which reason may well protest. We are not to despair of
any, but want of strength is the most hopeless case of all. Our power of
laboring for others being limited, it becomes our duty to inquire,
before we devote our time to the weak, whether we are not thus
diminishing our chances of helping better men."
Anton interrupted him. "Does he not deserve every allowance to be made
for him? He was brought up to exact much; he has not learned, as we
have, to make his way by his own labor."
The merchant laid his hand on the young man's shoulder. "The very
reason. Believe me, a large number of these landed gentry, who pay the
penalty of their old family memories, are beyond help. I am the last to
deny that many worthy and admirable men belong to this class. Indeed,
wherever remarkable talent or nobility of character shoots up among
them, no doubt their position offers peculiar scope for its development,
but for average men it is not a favorable one. He who considers it his
hereditary privilege to enjoy life, and who assumes a distinguished
position in virtue of his family, will very often fail to put forth his
whole strength in order to deserve that position. Accordingly, numbers
of our oldest families are declining, and their fall will be no loss to
the state. Their family associations make them haughty without any
right to be so--limit their perceptions and confuse their judgment."
"Even if all this be true," cried Anton, "it does not absolve us from
helping individuals of the class who have excited our sympathy."
"No," said the principal, "if it be excited. But it does not glow so
rapidly in advancing years as in youth. The baron has endeavored to
isolate his property from the current of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leave it forever to his family. Forever! You, as a merchant, know how to
estimate the attempt. True, every rational man must allow it to be
desirable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same soil should be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We all prize what our forefathers have possessed before
us, and Sabine would unlock every room in this house with pride, because
her great-great-grandmother turned the same keys before her. It is
therefore natural that the landed proprietor should desire to preserve
those familiar scenes, which are the source of his own prosperity, to
those nearest and dearest to him. But there must be means to this end,
and these means are the making his own existence available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increase of his patrimony. Where energy dies in families
or individuals, then it is well that their means die too, that their
money should circulate through other hands, and their plowshare pass to
those who can guide it better. A family that has become effete through
luxury ought to sink down into common life, to make room for the
uprising of fresh energies and faculties. Every one who seeks, at the
cost of free activity for others, to preserve permanent possessions and
privileges for himself or his family, I must look upon as an enemy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social state. And if such a man ruin
himself in his endeavors, I should feel no malicious pleasure in his
downfall, but I should say that he is rightly served, because he has
sinned against a fundamental law of our social being; consequently, I
should consider it doubly wrong to support this man, because I could but
fear that I should thus be supporting an unsound condition of the body
politic."
Anton looked down mournfully. He had expected sympathy and warm
concurrence, and he met with disaffection and coldness that he despaired
of conquering. "I can not gainsay you," he at length replied; "but in
this case I can not feel as you do. I have been witness to the
unspeakable distress in the baron's family, and my whole soul is full
of sadness and sympathy, and of the wish to do something for those who
have opened their heart to me. After what you have said, I dare no
longer ask you to trouble yourself with their affairs, but I have
promised the baroness to assist her as far as my small powers permit,
and your kindness allows. I implore you to grant me permission to do
this. I shall endeavor to be regular in my attendance at the office, but
if during the next few weeks I am occasionally absent, I must ask you to
excuse me."
Once more the merchant walked up and down the room, and then, looking at
Anton's excited face, with deep seriousness and something of regret, he
replied, "Remember, Wohlfart, that every occupation which excites the
mind soon obtains a hold over a man, which may retard as well as advance
his success in life. It is thi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 to agree
to your wishes."
"I know it," said Anton, in a low voice; "but I have now no choice
left."
"Well, then, do what you must," said the merchant, gloomily; "I will lay
no hinderance in your way; and I hope that after a few weeks you will be
able to consider the whole circumstances more calmly." Anton left the
room, and the merchant stood looking long with frowning brow at the
place his clerk had occupied.
Nor was Anton in a more congenial mood. "So cold, so inexorable!"
exclaimed he, as he reached his own room. He began to suspect that his
principal was more selfish and less kindly than he had hitherto
supposed. Many an expression of Fink's recurred to his mind, as well as
that evening when young Rothsattel, in his boyish conceit, had spoken
impertinently to the merchant. "Is it possible," thought he, "that that
rude speech should be unforgotten?" And his chief's keen, deep-furrowed
face lost inexpressibly by contrast with the fair forms of the noble
ladies. "I am not wrong," he cried to himself; "let him say what he
will, my views are more just than his, and henceforth my destiny shall
be to choose for myself the way in which I shall walk." He sat long in
the darkness, and his thoughts were gloomy as it; then he went to the
window to look down into the dark court below. A great white blossom
rose before him like a phantom. Striking a light, he saw that it was the
beautiful Calla out of Sabine's room. It hung down mournfully on its
broken stem. Sabine had had it placed there. This little circumstance
struck him as a mournful omen.
Meanwhile Sabine, taper in hand, entered her brother's room.
"Good-night, Traugott," nodded she. "Wohlfart has been with you this
evening; how long he staid!"
"He will leave us," replied the merchant, gloomily.
Sabine started and dropped her taper on the table. "For God's sake, what
has happened? Has Wohlfart said that he was going away?"
"I do not yet know it, but I see it coming step by step; and I can not,
and still less can you, do any thing to retain him. When he stood before
me here with glowing cheeks and trembling voice, pleading for a ruined
man, I found out what it was that lured him away."
"I do not understand you," said Sabine, looking full at her brother.
"He chooses to become the confidential friend of a decayed noble. A pair
of bright eyes draws him away from us: it seems to him a worthy object
of ambition to become Rothsattel's man of business. This intimacy with
nobility is the legacy bequeathed to him by Fink."
"And you have refused to help him?" inquired Sabine, in a low voice.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said the merchant, harshly; and he
turned to his writing-table.
Sabine slowly withdrew. The taper trembled in her hand as she passed
through the long suite of rooms listening to her own footfall, and
shuddering as the feeling came over her that an invisible companion
glided by her side. This was the revenge of that other. The shadow that
once fell on her innocent life now drove her friend away from their
circle. Anton's affections clung to another. She had but been in his
eyes a mere stranger, who had once loved and languished for one now far
away, and who now, in widow's weeds, looked back regretfully to the
feelings of her youth.
The few next weeks were spent by Anton in over-hard work. He had great
difficulty in keeping up his counting-house duties, while he spent every
spare hour in conference with the baroness and the lawyer.
In the mean time, the misfortunes of the baron ran their course. He had
not been able to pay the interest of the sums with which his estate was
burdened. When last they were due, a whole series of claims was brought
against him, and the estate fell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district authorities. Complicated lawsuits arose. Ehrenthal complained
loudly, claiming the first mortgage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nay, he
was inclined to advance claims on the last mortgage offered by the baron
in the recent fatal hour. Löbel Pinkus also appeared as claimant of the
first mortgage, and asserted that he had paid the whole sum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Ehrenthal had no proof to bring forward, and had been
for some weeks past quite unable to manage his own affairs, while
Pinkus, on the contrary, fought with every weapon a hardened sinner can
devise or employ, and the deeds which the baron had executed at Veitel's
suggestion proved to be so capital a master-stroke of the cunning
advocate, that the baron's man of business had, from the first, little
hope of the case. We may here observe that Pinkus did eventually win it,
and that the mortgage was made over to him.
Anton was now gradually gaining some insight into the baron's
circumstances. But the double sale of the first mortgage was still kept
a secret by the latter, even from his wife. He declared Ehrenthal's
claim unfounded, and even expressed a suspicion that he had himself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robbery in his office. Indeed, he really
believed this. Then the name of Itzig was never broached, and the
suspicion against Ehrenthal, which the baron's lawyer shared, prevented
Anton seeking any explanation from him.
Meanwhile, an estrangement had sprung up between our hero and his
principal, which the whole counting-house remarked with surprise. The
merchant scowled at Anton's vacant seat when the latter chanced to be
absent during office-hours, or looked coldly at his clerk's face, made
pale as it was with excitement of mind and night-work. He took no notice
of his new occupation, and never seemed to remark him. Even to his
sister he maintained a stiff-necked silence; nor could all her attempts
lead him to speak of Anton, who, on his side, felt his heart revolt
against this coldness. After his return, to be treated like a child of
the house, praised, promoted, petted, and now to be treated like a mere
hireling, who is not worth the bread thrown to him; to be a toy of an
incomprehensible caprice--this, at least, he had not deserved; so he
became reserved toward the whole family, and sat silent at his desk; but
he fel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now and the then so keenly, that often,
when alone, he would spring up and stamp on the ground in the bitter
indignation of his heart.
One comfort remained. Sabine was not estranged. True, he saw little of
her, and at dinner she seemed to avoid speaking to him, but he knew that
she was on his side.
A few days after his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the merchant, she came down
stairs as he stood in the hall, and had to pass him by so closely that
her dress touched him. He had retreated, and made a formal bow, but she
looked at him imploringly, and whispered, "You must not be estranged
from me." It was an affair of a moment, but the faces of both were
radiant with a happy understanding.
The time had now arrived when Mr. Jordan was to quit the firm. The
principal again called Anton into his little office, and without any
severity, but also without a trace of his former cordiality, began: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o you my intention of appointing you Jordan's
successor; but,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your time has been more taken
up with other business than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such a post, I
therefore ask you whether you are now at liberty to undertake Jordan's
duties?"
"I am not," replied Anton.
"Can you name any--not very distant--time when you will be free from
your present occupation? In that case I will endeavor to find a
substitute until then."
Anton sorrowfully replied, "I can not at present say when I shall again
be master of my whole time; and, besides, I feel that, even as it is, I
tax your indulgence by many irregularities. Therefore, Mr. Schröter, I
beg that you will fill up this post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me."
The merchant's brow grew furrowed and dark, and he silently bowed
assent. Anton felt as he closed the door that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m was now complete, and, resuming his place, he leaned his throbbing
head on his hand. A moment later Baumann was summoned to the principal,
and Jordan's situation conferred upon him. On returning to the office,
he went up to Anton and whispered, "I refused at first, but Mr. Schröter
insisted. I am doing you an injustice." And that evening Mr. Baumann, in
his own room, read in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the chapters treating of
the unjust Saul (the principal), and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Jonathan
and the persecuted David, and strengthened his heart thereby.
The next day Anton was summoned to the baroness. Lenore and her mother
sat before a large table covered with jewel-boxes and toilette elegances
of every description, while a heavy iron chest stood at their feet. The
curtains were drawn, and the subdued light shone softly into the richly
furnished room. On the carpet glowed wreaths of unfading flowers, and
the clock ticked cheerfully in its alabaster case. Under the shade of
flowering plants sat the two love-birds in their silvered cage, hopping
from perch to perch, screaming ceaselessly, or sitting up quietly close
to each other. The whole room was beauty and perfume. "For how long?"
thought Anton. The baroness rose. "We are already obliged to trouble you
again," said she; "we are engaged in a very painful occupation." On the
table were all manner of ornaments, gold chains, brilliants, rings,
necklaces, gathered into a heap.
"We have been looking out all that we can dispense with," said the
baroness, "and now pray you to undertake to sell these things for us. I
have been told that some of them are of value, and as we are now in much
need of money, we turn here for help."
Anton looked in perplexity at the glittering heap.
"Tell us, Wohlfart," cried Lenore, anxiously, "is this necessary? can it
be of any use? Mamma has insisted upon setting apart for sale all our
ornaments, and whatever plate is not in daily use. What I can give is
not worth talking of, but my mother's jewels are costly; many of them
were presents made to her in youth, which she shall not part with unless
you say that it is necessary."
"I fear," said Anton, gravely, "that it will prove so."
"Take them," said the baroness to Anton; "I shall be calmer when I know
that we have at least done what we could."
"But do you wish to part with all?" inquired Anton, anxiously. "Much
that is dear to you may have but little value in a jeweler's eyes."
"I shall never wear an ornament again," quietly replied the baroness.
"Take them all;" and, holding her hands before her eyes, she turned
away.
"We are torturing my mother," cried Lenore, hastily; "will you lock up
all that is on the table, and get them out of the house as soon as you
can?"
"I can not undertake the charge of these valuables," said Anton,
"without taking some measures to decrease my own responsibility. First
of all, I will in your presence make a short note of all you intrust to
me."
"What useless cruelty!" exclaimed Lenore.
"It will not take long."
Anton took out a few sheets from his pocket-book, and began to note down
the different articles.
"You shall not see it done, mother," said Lenore, drawing her mother
away, and then returning to watch Anton at his task.
"These preparations for the market are horrible," said she. "My mother's
whole life will be sold; some memory of hers is linked with every single
thing. Look, Wohlfart, the princess gave her this diamond ornament when
she married my father."
"They are magnificent brilliants," cried Anton, admiringly.
"This ring was my grandfather's, and these are presents of poor papa's.
Alas! no man can know how we love all these things. It was always a
festival to me when mamma put on her diamonds. Now we come to my
possessions. They are not worth much. Do you think this bracelet good
gold?" She held out her hand as she spoke.
"I do not know."
"It shall go with the rest," said Lenore, taking it off. "Yes, you are a
kind, good man, Wohlfart," continued she, looking trustfully into his
tearful eyes; "do not forsake us. My brother has no experience, and is
more helpless than we are. It is a frightful position for me. Before
mamma I do all I can to be composed, else I could scream and weep the
whole day through." She sank in a chair, still holding his hand. "Dear
Wohlfart, do not forsake us."
Anton bent over her, and looked with passionate emotion at the lovely
face that turned so trustfully to him in the midst of its tears.
"I will be helpful to you when I can," said he, in the fullness of his
heart. "I will be at hand whenever you need me. You have too good an
opinion of my information and my faculties; I can be of less assistance
to you than you suppose, but what I can, that I will do in any and every
possible way."
Their hands parted with a warm pressure; the affair was settled.
The baroness now returned. "Our lawyer was with me this morning," said
she; "and now I must ask for your opinion on another subject. He tells
me that there is no prospect of preserving the baron's family estate."
"At this time, when interest is high, and money difficult to get, none,"
replied Anton.
"And you, too, think that we must turn all our efforts toward preserving
the Polish property?"
"I do," was the answer.
"For that, also, money will be necessary. Perhaps I may be able through
my relatives to intrust you with a small sum, which, with the help of
that"--she pointed to the iron chest--"may suffice to cover the first
necessary expenses. I do not, however, wish to sell the jewels here, and
a journey to the residence would be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cure the
sum to which I have just alluded. The baron's lawyer has spoken most
highly of your capacity for business. It is his wish which now decides
me to make a proposal to you. Will you for the next few years, or, at
all events, until our greatest difficulties are over, devote your whole
time to our affairs? I have consulted my children, and they agree with
me in believing that in your assistance lies our only hope of rescue.
The baron, too, has come in to the plan. The question now is whether
your circumstances allow you to give your support to our unfortunate
family. We shall be grateful to you, whatever conditions you affix; and
if you can find any way of making our great obligations to you apparent
in the position you hold, pray impart it to me."
Anton stood petrified. What the baroness required of him was separation
from the firm, separation from his principal, and from Sabine! Had this
thought occurred to him before, when standing in Lenore's presence or
bending over the baron's papers? At all events, now that the words were
spoken, they shocked him. He looked at Lenore, who stood behind her
mother with hands clasped in supplication. At length he replied, "I
stand in a position which I can not leav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others.
I was not prepared for this proposal, and beg to have time allowed me
for consideration. It is a step which will decide my whole future life."
"I do not press you," said the baroness; "I only request your
consideration. Whatever your decision be, our warmest gratitude will
still be yours; if you are unable to uphold our feeble strength, I fear
that we shall find no one to do so. You will think of that," she added,
beseechingly.
Anton hurried through the street with throbbing pulse. The noble lady's
glance of entreaty, Lenore's folded hands, beckoned him out of the
gloomy counting-house into a sphere of greater liberty, into a new
future, from whose depths bright images flashed out upon his fancy. A
request had been frankly made, and he was strongly inclined to justify
the confidence that prompted it. Those ladies required an unwearied,
self-sacrificing helper to save them from utter ruin, and if he
followed his impulse he should be doing a good work--fulfilling a duty.
In this mood he entered the merchant's dwelling. Alas! all that he saw
around him seemed to stretch out a hand to detain him. As he looked at
the warehouse, the good-humored faces of the porters, the chains of the
great scales, the hieroglyphics of the worthy Pix, again he felt that
this was the place that he belonged to. Sabine's dog kissed his hand,
and ran before him to his room--his and Fink's room. Here the childish
heart of the orphan boy had found a friend, kind companions, a home, a
definite and honorable life-purpose. Looking down through his window on
all the long-familiar objects, he saw a light in Sabine's store-chamber.
How often he had sought for that light, which brightened the whole great
building, and brought a sense of comfort and cheerfulness even into his
room. He now sprang up suddenly, and said to himself, "She shall
decide."
Sabine started in amazement when Anton appeared before her. "I am
irresistibly impelled to seek you," cried he. "I have to decide upon my
future life, and I feel undetermined, and unable to trust to my own
judgment. You have always been a kind friend to me since the day of my
arrival. I am accustomed to look up to you, and to think of you in
connection with all that interests me here. Let me hear your opinion
from your own lips. The Baroness Rothsattel has to-day proposed to me
permanently to undertake the situation of confidential adviser and
manager of the baron's affairs. Shall I accept; or shall I remain here?
I know not--tell me what is right both for myself and others."
"Not I," said Sabine, drawing back and growing very pale. "I can not
venture to decide in the matter. Nor do you wish me to do so, Wohlfart,
for you have already decided."
Anton looked straight before him and was silent.
"You have thought of leaving this house, and a wish to do so has sprung
out of the thought. And I am to justify you, and approve your resolve!
This is what you require of me," continued she, bitterly. "But this,
Wohlfart, I can not do, for I am sorry that you go away from us."
She turned away from him and leaned on the back of a chair.
"Oh, be not angry with me too!" said Anton; "that I can not bear. I have
suffered much of late. Mr. Schröter has suddenly withdrawn from me the
friendly regard that I long held my life's greatest treasure. I have not
deserved his coldness. What I have been doing has not been wrong, and
it was done with his knowledge. I had been spoiled by his kindness; I
have the more deeply felt his displeasure. My only comfort has been that
you did not condemn me. And now, do not you be cold toward me, else I
shall be wretched forever. There is not a soul on earth to whom I can
turn for affectionate comprehension of my difficulties. Had I a sister,
I should seek her heart to-day. You do not know what to me, lonely as I
am, your smile, your kindly shake of the hand has been till now. Do not
turn coldly from me, I beseech you."
Sabine was silent. At length she inquired, still with averted face,
"What draws you to those strangers; is it a joyful hope, is it sympathy
alone? Give this question close consideration before you answer it to
yourself at least."
"What it is that makes it possible for me to leave this house," said
Anton, "I do not myself know. If I can give a name to my motives, it is
gratitude felt toward one. She was the first to speak kindly to the
wandering boy on his way out into the world. I have admired her in the
peaceful brightness of her former life. I have often dreamed childish
dreams about her. There was a time when a tender feeling for her filled
my whole heart, and I then believed myself forever the slave of her
image. But years bring changes, and I learned to look on men and on life
with other eyes. Then I met her again, distressed, unhappy, despairing,
and my compassion became overmastering. When I am away from her, I know
that she is nothing to me; when I am with her, I feel only the spell of
her sorrow. Once, when I had to depart out of her circle like a culprit,
she came to me, and before the whole scornful assembly she gave me her
hand and acknowledged me her friend; and now she comes and asks for my
hand to help her father. Can I refuse it? Is it wrong to feel as I do? I
know not, and no one can tell me--no one but you alone."
Sabine's head had sunk down to the back of the chair on which she bent.
She now suddenly raised it, and with tearful eyes, and a voice full of
love and sorrow, cried, "Follow the voice that calls you. Go, Wohlfart,
go."
CHAPTER XXVII.
On a cold October day, two men were seen driving through the latticed
gate of the town of Rosmin on toward the plain, which stretched out
before them monotonous and boundless. Anton sat wrapped in his fur coat,
his hat low on his forehead, and at his side was young Sturm, in an old
cavalry cloak, with his soldier's cap cocked cheerily on one side. In
front of them a farm-servant, squatted on a heap of straw, flogged on
the small horses. The wind swept the sand and straw from the
stubble-fields, the road was a broad causeway without ditches or hedges,
the horses had to wade alternately through puddles and deep sand. Yellow
sand gleamed through the scanty herbage in all directions wherever a
field-mouse had made her way to her nest or an active mole had done what
he could to diversify the unbroken plain. Wherever the ground sank,
stagnant water lodged, and there hollow willow-trees stretched their
crippled arms in the air, their boughs flapping in the wind, and their
faded leaves fluttering down into the muddy pool below. Here and there
stood a small dwarf pine, a resting-place for the crows, who, scared by
the passing carriage, flew loudly croaking over the travelers' heads.
There was no house to be seen on the road, no pedestrian, and no
conveyance of any kind.
Karl looked every now and then at his silent companion, and said at
last, pointing to the horses, "How rough their coats are, and how pretty
their gray mouse skins! I wonder how many of these beasties would go to
make up my sergeant's horse! When I took leave of my father, the old man
said, 'Perhaps I shall pay you a visit, little one, when they light the
Christmas-tree.' 'You'll never be able,' said I. 'Why not?' asked he.
'You'll never trust yourself in any post-chaise.' Then the old boy
cried, 'Oho! post-chaises are always of a stout build; I shall be sure
to trust myself in one.' But now, Mr. Anton, I see that my father never
can pay us a visit."
"Why not?"
"It is possible that he may reach Rosmin; but, as soon as he sees these
horses and this road, he will instantly turn back. 'Shall I trust
myself,' he'll say, 'in a district where sand runs between one's legs
like water, and where mice are put into harness? The ground is not firm
enough for me.'"
"The horses are not the worst things here," said Anton, absently. "Look!
these go fast enough."
"Yes," replied Karl, "but they don't go like regular horses; they
entangle their legs like two cats playing in a parsley-bed. And what
things they have for shoes--regular webbed hoofs, I declare, which no
blacksmith can ever fit."
"If we could only get on!" returned Anton; "the wind blows cold, and I
am shivering in spite of my fur."
"You have slept but little the last few nights, sir," said Karl. "The
wind blows here as if over a threshing-floor. The earth is not round
hereabouts as elsewhere, but flat as a cake. This is a complete desert;
we have been driving for more than an hour, and there is not a village
to be seen."
"A desert indeed," sighed Anton; "let us hope it may improve." They
relapsed into profound silence. At length the driver stopped near a
pool, unharnessed the horses, and led them to the water's edge, without
noticing the travelers.
"What the deuce does this mean?" cried Karl, jumping down from the
carriage.
"I am going to feed," replied the servant, sulkily, in a foreign accent.
"I am anxious to know how that will be done," said Karl. "There is not
the shadow of a bag of provender."
The horses, however, soon proved that they could live without corn; they
stretched down their shaggy heads, and began to pull the grass and weeds
at the edge of the pool, sometimes taking a draught of the dirty water.
Meanwhile the servant drew a bundle from under his seat, settled himself
under the lee of an alder-bush, and, taking his knife, cut his bread and
cheese without even glancing at the travelers.
"I say, Ignatius or Jacob," cried Karl, sharply, "how long will this
breakfast of yours last?"
"An hour," replied the man, munching away.
"And how far is it from here to the estate?"
"Six miles, or maybe more."
"You can make nothing of him," said Anton; "we must put up with the
customs of the country;" and, leaving the carriage, they went to look on
at the horses feeding.
Anton is on his way to the Polish property. He is now the baron's agent.
Anxious months have the last proved to him. The parting from his
principal and the firm had been painful in the extreme. For some time
before it, indeed, Anton had found himself alone in the midst of his
colleagues. The quiet Baumann still remained his friend, but the others
considered him a castaway. The merchant received his resignation with
icy coldness; and even in the hour of parting, his hand lay impassive as
metal in Anton's grasp. Since then, our hero had undertaken several
journeys to the capital and to creditors in the family's behalf, and now
he was on his way to set the new estate in order, accompanied by Karl,
whom he had induced to become the baron's bailiff.
Ehrenthal had, by the authority conferred on him,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from the time of the sale by auction, and hired the Polish
bailiff for the baron. There had been unfair dealings between them at
the time, and it was well known in Rosmin that the bailiff had sold off
a good deal, and been guilty of all sorts of frauds since, so that Anton
had even now no prospect of a quiet life.
"The hour is come when I may execute my commission," cried Karl, groping
in the straw under the seat. He drew out a large japanned tin case, and
carried it to Anton. "Miss Sabine gave me this in charge for you." He
then joyously opened the lid, produced the materials for an excellent
breakfast, a bottle of wine, and a silver goblet. Anton took hold of the
case.
"It has a very knowing look," said Karl. "Miss Sabine planned it
herself."
Anton examined it on all sides, and placed it carefully on a tuft of
grass; then he took up the goblet, and saw his initials engraved on it,
and underneath the words, "To thy welfare." Whereupon he forgot the
breakfast and all around him, and stood gazing at the goblet, lost in
thought.
"Do not forget the breakfast, sir," suggested Karl, respectfully.
"Sit down by me, my faithful friend; eat and drink with me. Leave off
your absurd politeness. We shall have but little, either of us, but what
we have we will share like brothers. Take the bottle if you have no
glass."
"There's nothing like leather," said Karl, taking a small leathern
drinking-cup out of his pocket. "As for 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t was
kindly meant, and I thank you; but there must be subordination, if it
were but for the sake of the others; and so, sir, be kind enough to let
me shake hands with you now, and then let things be as they were before.
Only look at the horses, Mr. Anton. My faith! the creatures devour
thistles."
Again the horses were harnessed, again they threw out their short legs
in the sand, and again the carriage rolled through the barren
district--first through an empty plain, next through a wretched
fir-wood, then past a row of low sand-hills, then over a tumble-down
bridge crossing a small stream.
"This is the property," said the driver, turning round, and pointing
with his whip to a row of dirty thatched roofs that had just come into
sight.
Anton stood up to look for the group of trees in which the Hall might be
supposed to stand. Nothing of the sort to be seen. The village was
deficient in all that adorns the home of the poorest German peasant--no
orchard, no hedged-in gardens, no lime-trees in the market-place.
"This is wretched," said he, sitting down again; "much worse than they
told us in Rosmin."
"The village looks as if under a curse," cried Karl; "no teams working
in the fields--not a cow or a sheep to be seen."
The farm-servant flogged his horses into an irregular gallop, and so
they passed through the rows of mud huts which constituted the village,
and arrived at the public house. Karl sprang from the carriage, opened
the tavern door, and called for the landlord. A Jew slowly rose from his
seat by the stove and came to the threshold. "Is the gendarme from
Rosmin come?" He is gone into the village. "Which is the way to the
farm-yard?"
The landlord, an elderly man with an intelligent countenance, described
the way in German and Polish, and remained standing at the
door--bewildered, Karl declared, by the sight of two human beings. The
carriage turned into a cross-road, planted on both sides with thick
bushes, the remains of a fallen avenue. Over holes, stones, and puddles,
it rattled on to a group of mud huts, which still had a remnant of
whitewash upon them. "The barns and stables are empty," cried Karl, "for
I see gaps in the roofs large enough to drive our carriage through."
Anton said no more; he was prepared for every thing. They drove through
a break between the stables into the farm-yard, a large irregular space,
surrounded on three sides by tumble-down buildings, and open to the
fields on the fourth. A heap of _débris_ lay there--lime and rotten
timber, the remains of a ruined barn. The yard was empty; no trace of
farm implements or human labor to be seen. "Which is the inspector's
house," inquired Anton, in dismay. The driver looked round, and at last
made up his mind that it was a small one-storied building, with straw
thatch and dirty windows.
At the noise of the wheels a man appeared on the threshold, and waited
phlegmatically till the travelers had dismounted, and were standing
close before him. He was a broad-shouldered fellow, with a bloated,
brandy-drinking face, dressed in a jacket of shaggy cloth, while behind
him peered the muzzle of an equally shaggy dog, who snarled at the
strangers. "Are you the steward of this property?"
"I am," replied the man, in broken German, without stirring from where
he was.
"And I am the agent of the new proprietor," said Anton.
"That does not concern me," growled the shaggy man, turning sharp round,
entering the house, and bolting the door within.
Anton was thoroughly roused. "Break the window in, and help me to catch
the rascal," cried he to Karl, who coolly seized a piece of wood, struck
the panes so as to make the rotten framework give way, and cleared the
opening at one leap. Anton followed him. The room was empty, so was the
next, and in it an open window--the man was gone.
"After him!" cried Karl, and dashed on in pursuit, while Anton looked
about the house and out-buildings. He soon heard the barking of a dog,
and saw Karl capture the fugitive. Hurrying to his help, he held the man
fast, while, with a kick, Karl sent the dog flying. They then contrived
to force the steward back to the house, though he kept striking out
violently all the way.
"Go to the tavern, and bring the gendarme and the landlord," cried Anton
to the driver, who, undisturbed by all that had been going on, had
meanwhile unpacked the carriage. The man accordingly drove leisurely
off, and the fugitive being got into the room, Karl found an old cloth,
and with it bound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I beg your pardon, sir,"
said he; "it is only for an hour or so, till the arrival of the Rosmin
gendarme, whom we have appointed to meet us."
Anton then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house, bu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found but the merest necessaries; no books nor papers of any kind. It
had doubtless been emptied already. A bundle projected from the
coat-pocket of the prisoner, which turned out to be receipts and legal
documents in Polish. In time, the driver returned with the landlord and
the armed policeman. The landlord stood at the door in some perplexity,
and the policeman explained in a few moments what remained to be done.
"You must make a statement to the local judge, and give the man up to
me. He shall go back in your carriage to Rosmin. You will do well to get
rid of him, for this is a wild country, and it will be safer for you to
have him at Rosmin than here, where he has friends and accomplices."
After a long search, a sheet of paper was found in a cupboard, the
statement made and submitted to the policeman, who shook his head a
little over the Polish composition, and the prisoner lifted into the
carriage, the gendarme taking his seat beside him, and saying to Anton,
"I have long expected something of the kind. You may have often occasion
to want me again." The carriage then drove away, and thus the property
came under Anton's administration. He felt as if cast on a desert
island.
His portmanteau and traveling effects were leaning against a mud wall,
and the Polish landlord was the only man who could give him and Karl any
information or advice in their forlorn condition.
Now that the steward was fairly gone, the landlord grew more
communicative, and showed himself serviceable and obliging. A long
conversation ensued, and its purport was what Anton had apprehended from
the warning given by the Commissary Walter and other Rosmin officials.
The inspector had,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done all he could in the
way of spoliation, rendered daring by a report which had found its way
from the town to the village, that the present proprietor would never be
able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estate. At last Anton said, "What that
wretched man has done away with he will have to account for; our first
care must be to preserve what is still to be found on the property. You
must be our guide to-day."
They then examined the empty buildings. Four horses and two
servants--they were gone into the wood--a few old plows, a pair of
harrows, two wagons, a britzska, a cellar full of potatoes, a few
bundles of hay, a little straw--the inventory did not take much time in
drawing up. The buildings were all out of repair, not through age, but
neglect.
"Where is the dwelling-house?" inquired Anton. The landlord led the way
out of the yard to the meadow--a broad plain, gradually sloping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brook. It had been a great pasture. The cattle had
trodden it down into holes; the snouts of greedy swine had rooted it up;
gray molehills and rank tufts of grass rose on all sides.
The landlord stretched out his hand. "There is the castle. This castle
i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he added, reverentially; "no
nobleman in the district has a stone house like that. All the gentry
here live in wood and mud buildings. Herr von Tarow, the richest of
them, has but a poor dwelling."
About three hundred yards from the last out-building rose a great brick
edifice, with a black slate roof and a thick round tower. Its gloomy
walls on this treeless pasture-land, without one trace of life around,
rose beneath the cloudy sky like a phantom fortress which some evil
spirit had evoked from the abyss--a station from which to blight all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The strangers approached it. The castle had fallen into ruins before the
builders had finished their task. The tower had stood there for ages. It
was built of unhewn stone, and had small windows and loop-holes. The
former lords of the land had looked down from its summit on the tops of
the trees, which then stretched far into the plain. They had then ruled
with a rod of iron the serfs who cultivated their land, and toiled and
died for them. Many an arrow had sped through those loop-holes at the
enemy storming below, and many a Tartar horse had been overthrown before
those massive walls. Years ago, a despot of the district had, in
expiation of former sins, begun to add to the gray tower the walls of a
holy monastery; but the monastery never got finished, and the useless
walls had already stood there long, when the late count took it into his
head to convert them into a lordly dwelling for his race, and to raise a
house unparalleled for magnificence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 front of the house was added on to both sides of the tower, which
projected in the middle. The intention had been to have a high
terrace-road up to the castle, and the principal entrance had been made
in the tower, and arched over; but the terrace never having been formed,
the stone threshold of the main door was quite inacce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ladders, and the wide opening was left. The window-spaces of
the lower floor were merely closed up with boards, while on the second
story were some window-frames of beautifully carved wood, in which large
panes had once been placed, but they had got broken. In other windows
were temporary frames of rough deal, with small panes of muddy glass let
into them. A company of jackdaws sat on the top of the tower, looking
down in amazement on the strangers, and every now and then one flew off,
screaming loudly, to contemplate the intruders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A house for crows and bats, not for human beings," said Anton. "At
least, I see no way of getting into it."
The landlord now took them round the building. Behind, where the two
wings made a sort of horse-shoe, there were low entrances to the cellars
and offices; beneath which, again, were stables, great arched kitchens,
and small cells for the serfs. A wooden staircase led to the upper
story. The door turned creaking on its hinges, and a narrow passage took
them through a side wing to the front part of the house. There all was
at least magnificently planned. The circular entrance-hall--an arched
room of the old tower--was painted in mosaic, and through the great
doorway-opening was seen a wide expans
small disturbance made by the return of Anton had gradually settled
down. Those first-class treasures of Sabine's had made way for other
specimens of damask, still of a superior kind, it is true, but which
came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e elderly cousin's comprehension. She had
been quite right in prophesying that Anton would never remark those
signs of exuberant gratitude or their withdrawal. However, one change
had been permanently made--the greatest, the best of all changes--the
clerk retained a privileged place in the heart of the young mistress of
the firm, and his tall figure often appeared as one of the circle that
Sabine's fancy loved to gather round her when at her work-table or in
her treasure-chamber.
To-day she was walking restlessly up and down before dinner. The cousin,
who heard every thing, had just told her that a maid from Ehrenthal's
had run into the office to announce Bernhard's death to his friend. "How
will he bear it?" thought she. And the name of Ehrenthal forced her
thoughts back to the past, to one now far away, and to that painful hour
when the struggle going on in her own mind had been suddenly brought to
a close by a letter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parted. And Anton had known
of that conquered feeling of hers. How considerate he had always been,
how chivalrous, how helpful! She wondered if he had any idea of the
completeness of her triumph over a girlish illusion. She shook her head.
"No, he has not. It was here, at this very table, that an accident first
betrayed me to him. That past time still rises like a cloud between us.
Whenever I sit near Wohlfart of an evening, I am conscious of another's
shadow at my side; and when he speaks to me, his tone, his manner always
seem to say, 'You are not alone; he is with you.'" Sabine started, and
lovingly passed her hand over the beautiful flowers on the table before
her, as if to dispel a painful thought. She could not tell him that she
was free from that long-felt sorrow. Now, however, when he had lost a
friend whom he so much loved, she must show him that there were other
hearts that clung to him still. And again she walked up and down, trying
to devise a way of speaking to him alone.
Dinner was announced. Anton came with the rest, and took his place at
once. There was no opportunity of exchanging a word during the meal, but
he often met her sad and sympathizing eye. "He eats nothing at all
to-day," whispered her cousin; "not even any of the roast," she added,
reproachfully. Sabine was much perturbed. Mr. Jordan had already risen;
Anton would leave the room with the rest, and she should not see him
again the whole day through. So she called out, "The great Calla is
fully blown now. You were admiring the buds the other day; will you
remain a moment; I should like to show it you?" Anton bowed and staid
behind. A few more awkward moments, then her brother rose too; and,
hurrying to Anton, she took him to the room where the flowers were.
"You have had sorrowful tidings to-day," she began.
"The tidings themselves did not surprise me," replied Anton. "The doctor
gave no hope. But I lose much in him."
"I never saw him," said Sabine; "but I know from you that his life was
lonely--poor in affection and in enjoyment."
She moved an arm-chair toward Anton, and led him on to talk about his
friend. She listened to every word with warm sympathy, and well knew
what to ask and how to comfort. It was a relief to Anton to speak of the
departed one, to describe his quiet way of life, his erudition, his
poetical enthusiasm. After a pause, Sabine looked up frankly into his
face, and asked, "Have you any tidings of Herr von Fink?"
It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his departure that she had ever breathed his
name. Anton felt how touching her confidence was, given in this hour of
his sadness. In his emotion, he seized her hand, which she was slow in
withdrawing.
"He is not happy in his new life," he gravely replied. "There was a
savage humor in his last letter, from which I gather, even more than
from his actual words, that the business into which his uncle's death
has thrown him does not suit him."
"It is unworthy," cried Sabine.
"At all events, it is not what would be recognized as honorable in this
house," replied Anton. "Fink is upright, and has lived too long with
your brother to take pleasure in the wild speculations so common on the
other side the Atlantic. His partners and colleagues are for the most
part men without a conscience, and his feelings revolt against their
companionship."
"And can Herr von Fink tolerate such relations as these for a day?"
"It is a remarkable thing that he whose own will was ever so arbitrarily
exercised, should now be obliged against that will to obey a pressure
from without, and every where to work with his hands tied. The
organization of such speculations in America is so complicated that one
shareholder can do little to alter it; and, now that Fink has attained
what used to be the goal of his wishes--a large capital, and the
management of immense districts--his condition appears more uncertain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He was always in danger of thinking slightingly
of others, now I am distressed at the bitter contempt he expresses for
his own life. His last letter paints an intolerable state of things, and
seems to point to some decisive resolve."
"There is only one resolve for him," cried Sabine. "May I ask what you
said to him in reply?"
"I entreated him instantly, come what would, to free himself from the
business in which he was entangled. I said that his own strong will
might find a way of extrication, even if that which I pointed out proved
impracticable. Then I begged of him either to carry out his old plan of
becoming a landed proprietor in America, or to return to us."
"I knew that you would write thus," said Sabine, drawing a long breath.
"Yes, Wohlfart, he shall return," said she, gently, "but he shall not
return to us."
Anton was silent.
"And do you think that Herr von Fink will follow your advice?"
"I do not know. My advice was not very American."
"But it was worthy of you," cried Sabine, with proud delight.
"An officer wishes to speak to Mr. Wohlfart," said a servant at the
door.
Anton sprang up. Sabine went to her flowers and bent mournfully over
them. The shadows of others hovered still between her friend and her.
The few words spoken by the servant filled Anton with a vague terror. He
hurried into the ante-room: there stood Eugene von Rothsattel. Anton was
gladly rushing forward to greet him, but the young soldier's face of
agony made him start back. He whispered, "My mother wishes to speak to
you; something dreadful has occurred." Anton caught up his hat, ran into
the office, hurriedly asked Baumann to excuse him to the principal, and
then accompanied the lieutenant to the baron's house.
On the way, Eugene, who had lost all self-command, said unconnectedly to
Anton, "My father last night accidentally wounded himself by a
pistol-shot--a messenger was sent to summon me--when I came, I found my
mother in a swoon--my sister and I do not know what to do--Lenore
implored my mother on her knees to send for you--you are the only one in
whom w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our distress--I understand nothing about
business, but my father's affairs must be in a dreadful state--my mother
is beside herself--the whole house is in the greatest disorder."
From what Eugene said and what he did not say; from his broken sentences
and his look of agony, Anton guessed at the horrors of the previous
evening. In the boudoir of the baroness he found Lenore, weeping and
exhausted.
"Dear Wohlfart!" cried she, taking his hand and beginning again to sob,
while her head sank powerless on his shoulder.
Meanwhile Eugene walked up and down, wringing his hands, and at length
throwing himself on the sofa, he gave himself up to silent tears.
"It is horrible, Mr. Wohlfart," said Lenore, lifting up her head. "No
one may approach my father--Eugene may not, nor I--only my mother and
old John are with him; and early this morning the merchant Ehrenthal was
here, insisting that he must see my father. He screamed at my mother,
and called my father a deceiver, till she fainted away. When I rushed
into the room, the dreadful man went off threatening her with his
clenched fist."
Anton led Lenore to a chair and waited till she had told him all.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comforting in this case, and his own heart was
wrung to the utmost by the misery he witnessed.
"Call my mother, Eugene," said Lenore, at length.
Her brother left the room.
"Do not forsake us," implored Lenore, clasping her hands; "we are at the
last gasp; even your help can not save us."
"He is dead who might perhaps have done so," mournfully replied Anton.
"Whether I can be of any use I know not, but you can not doubt my
willingness to be so."
"No," cried Lenore. "And Eugene, too, thought of you at once."
The baroness now entered. She walked wearily; but, steadying herself by
a chair, she saluted Anton with dignity. "In our position," said she,
"we need a friend who knows more of business than we three do.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prevents the baron--possibly for a long time to
come--from managing his own affairs, and, little as I understand them, I
can see that our interests require prompt measures. My children have
mentioned you to me, but I fear I am unreasonable in asking you to
devote your time to our service."
She sat down, beckoned Anton to take a chair, and said to her children,
"Leave us; I shall be better able to tell Mr. Wohlfart the little that I
know when I do not see your grief."
When they were alone, she motioned him nearer and tried to speak, but
her lips quivered, and she hid her face in her handkerchief.
"Before I can consent, gracious lady," said he, "to your reposing in me
such confidence as this, I must first inquire whether the baron has no
relative or intimate friend to whom you could with less pain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I pray you to remember that my own knowledge of business
is but small, and my position not one to constitute me a proper
counselor to the baron."
"I know no one," said the baroness, hopelessly. "It is less painful to
me to tell you what I can not conceal, than to one of our own circle.
Consider yourself a physician sent for to visit a patient. The baron has
this morning told me some particulars of his present circumstances." And
then she proceeded to relate what she had gathered as to the nature of
his embarrassments, the danger in which the family property was placed,
and the capital needed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Polish estate.
"My husband," continued she, "has given me the key of his desk, and he
wishes Eugene, with the help of a man of business, to go over his
papers. I now request of you to make this examination together with my
son. When you need explanations, I will try to obtain them from the
baron. The question is now, whether you are inclined to undertake this
trouble for us, who are only strangers."
"I am most willing to do so," earnestly replied Anton; "and I hope that
the kindness of my principal will allow me the time needful for the
purpose, if you do not consider it more advisable to depute the baron's
experienced legal adviser to the task."
"There will be an opportunity of asking that gentleman's advice later,"
said the baroness.
Anton rose. "When do you wish to begin?"
"Immediately. I fear there is not a day to lose. I shall do all I can to
help you look the papers over." She led Anton into the next room, called
in Eugene, and unlocked the baron's desk. As she opened it she lost her
self-command for a moment, and moving to the window, the quivering of
the curtains betrayed the anguish that shook her fragile frame.
The mournful task began. Hour after hour passed. Eugene was in no
condition to peruse any thing, but his mother reached letters and
documents to Anton, and, though often obliged to desist a while, she
bravely returned to the task. Anton placed the papers in order, and
sought, by glancing over each, to arrive at least at a superficial view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It was evening, when the old servant opened the door in dismay, and
called out, "He is there again." The baroness could not repress a slight
scream, and made a gesture of aversion.
"I have told him that no one is at home, but he will not be dismissed;
he makes such a noise on the steps. I can not get rid of him."
"It will kill me if I hear his voice again," murmured the baroness.
"If the man be Ehrenthal," said Anton, rising, "I will try to get him
away. We have now done what was most necessary; have the goodness to
lock up these papers, and to allow me to return to-morrow." The baroness
silently assented, and sank back in her chair. Anton hurried off to the
ante-room, whence he could hear Ehrenthal's loudly-raised voi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usurer shocked him. His hat pushed half off his
head, his pale face swelled as if by drinking, his glazed eyes red with
tears, Ehrenthal stood before him, calling in broken sentences for the
baron, wailing and cursing alternately. "He must come! he must come at
once!" cried he; "the wicked man! A nobleman, indeed! he is a vagabond,
after whom I will send the police. Where is my money? Where is my
security? I want my mortgage from this man who is not at home."
Anton went straight up to him, and asked, "Do you know me, Mr.
Ehrenthal?" Ehrenthal turned his glazed eyes upon him, and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 friend of his dead son.
"He loved you!" he cried, in a lamentable voice. "He spoke to you more
than to his father. You were the only friend that he had on earth. Have
you heard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house of Ehrenthal?" continued he, in
a whisper. "Just as they stole the papers he died. He died with a hand
like this," and clenching his fist he struck his forehead. "Oh my son!
my son! why didst not thou forgive thy father!"
"We will go to your son," said Anton, taking the arm of the old man, who
unresistingly allowed himself to be led back to his own house.
From thence Anton hurried to Councilor Horn, with whom he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It was late before he returned home. In the midst of his anxiety about
those whose prosperity had filled his imagination years before,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in their adversity, reposed in him, dilated his
breast with a feeling of pride. He burned with desire to help them, and
hoped that his zealous devotion might yet find some way of rescue. As
yet he saw none. Looking up at the great building before him, so firm
and secure, in the moonlight, a thought flashed into his mind. If any
man could help them, it was his principal. His keen eye would be able to
unravel all the dark secrets in which the baron was entangled, and his
iron strength of will would crush the villains who held the unfortunate
nobleman in their power. And then he had a noble nature; he always
decided on the right, without an effort or a struggle. Anton looked at
the first floor. The whole house-front was dark, but in a corner room a
light still burned. It was the private office of his chief.
With sudden resolve, Anton begged the servant to take him to Mr.
Schröter, who looked with amazement at the unexpected visitor, and asked
what brought him, and whether any thing had happened.
"I implore your counsel--I implore your help," cried Anton.
"For yourself or for others?" inquired the merchant.
"For a family with whom I have accidentally become connected. They are
lost if a strong hand does not ward off the impending catastrophe."
Anton then rapidly related the occurrences of the afternoon, and,
seizing his principal's hand in his emotion, cried, "Have pity upon the
unhappy ladies, and help them."
"Help them!" replied the merchant; "how can I? Have you been
commissioned to apply to me, or are you only following the impulse of
your own feelings?"
"I am not commissioned; it is only the interest that I take in the
baron's fate which leads me to you."
"And what right have you to inform me of facts communicated in strict
confidence to yourself by the baron's lady?" asked the merchant, dryly.
"I am committing no indiscretion in telling you what will, in a few
days, be no secret, even to strangers."
"You are unusually excited, otherwise you would not forget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hatever, does a man of business venture to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without the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Of course, I shall make no wrong use of what you have said, but it was
by no means business-like, Wohlfart, to be so open toward me."
Anton was silent, feeling, indeed, that his principal was right, but yet
it seemed hard to be blamed for reposing confidence at such a time as
this. The merchant walked silently up and down; at length, stopping
before Anton, he said, "I do not now inquire how you come to take so
warm an interest in this family. I fear it is an acquaintance you owe to
Fink."
"You shall hear all," said Anton.
"Not at present. I will now content myself with repeating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interfere in these affairs without being specially
applied to by the parties themselves. I may add that I by no means wish
for such an application, and do not disguise from you that, were it
made, I should probably decline to do any thing for the Baron
Rothsattel."
Anton's feelings were roused to the utmost. "The question is the rescue
of an honorable man, and of lovely and amiable women from the toils of
rogues and impostors. To me, this seems the duty of every one; I, at
least, consider it a sacred obligation which I dare not shrink from. But
without your support I can do nothing."
"And how do you think this embarrassed man can be helped?" inquired the
merchant, seating himself.
With somewhat more composure, Anton repli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an experienced man of business making himself master of the case. There
must be some way of circumventing these villains. Your penetration would
discover it."
"Any attorney would be far more likely to do so, and the baron might
readily engage the services of experienced and upright legal advisers.
If his enemies have done any thing illegal, the quick eye of a lawyer is
the most likely to detect it."
"Alas! the baron's own lawyer gives but little hope," replied Anton.
"Then, my dear Wohlfart, no other is likely to do much good. Show me an
embarrassed man who has strength to grasp an offered hand, and bid me
help him, and for the sake of all I owe you, I will not refuse to do so.
I think you are convinced of this."
"I am," said Anton, dejectedly.
"From all I hear, however," the merchant went on,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the baron. From what I gather from general report, as well as from
you, his embarrassments arise from his having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usurers, which proves him deficient in what alone ennobles the life of
any man--good sense, and the power of steady exertion."
Anton could only sigh his assent.
"To help such a man," inexorably continued the merchant, "is a futile
attempt, against which reason may well protest. We are not to despair of
any, but want of strength is the most hopeless case of all. Our power of
laboring for others being limited, it becomes our duty to inquire,
before we devote our time to the weak, whether we are not thus
diminishing our chances of helping better men."
Anton interrupted him. "Does he not deserve every allowance to be made
for him? He was brought up to exact much; he has not learned, as we
have, to make his way by his own labor."
The merchant laid his hand on the young man's shoulder. "The very
reason. Believe me, a large number of these landed gentry, who pay the
penalty of their old family memories, are beyond help. I am the last to
deny that many worthy and admirable men belong to this class. Indeed,
wherever remarkable talent or nobility of character shoots up among
them, no doubt their position offers peculiar scope for its development,
but for average men it is not a favorable one. He who considers it his
hereditary privilege to enjoy life, and who assumes a distinguished
position in virtue of his family, will very often fail to put forth his
whole strength in order to deserve that position. Accordingly, numbers
of our oldest families are declining, and their fall will be no loss to
the state. Their family associations make them haughty without any
right to be so--limit their perceptions and confuse their judgment."
"Even if all this be true," cried Anton, "it does not absolve us from
helping individuals of the class who have excited our sympathy."
"No," said the principal, "if it be excited. But it does not glow so
rapidly in advancing years as in youth. The baron has endeavored to
isolate his property from the current of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leave it forever to his family. Forever! You, as a merchant, know how to
estimate the attempt. True, every rational man must allow it to be
desirable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same soil should be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We all prize what our forefathers have possessed before
us, and Sabine would unlock every room in this house with pride, because
her great-great-grandmother turned the same keys before her. It is
therefore natural that the landed proprietor should desire to preserve
those familiar scenes, which are the source of his own prosperity, to
those nearest and dearest to him. But there must be means to this end,
and these means are the making his own existence available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increase of his patrimony. Where energy dies in families
or individuals, then it is well that their means die too, that their
money should circulate through other hands, and their plowshare pass to
those who can guide it better. A family that has become effete through
luxury ought to sink down into common life, to make room for the
uprising of fresh energies and faculties. Every one who seeks, at the
cost of free activity for others, to preserve permanent possessions and
privileges for himself or his family, I must look upon as an enemy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social state. And if such a man ruin
himself in his endeavors, I should feel no malicious pleasure in his
downfall, but I should say that he is rightly served, because he has
sinned against a fundamental law of our social being; consequently, I
should consider it doubly wrong to support this man, because I could but
fear that I should thus be supporting an unsound condition of the body
politic."
Anton looked down mournfully. He had expected sympathy and warm
concurrence, and he met with disaffection and coldness that he despaired
of conquering. "I can not gainsay you," he at length replied; "but in
this case I can not feel as you do. I have been witness to the
unspeakable distress in the baron's family, and my whole soul is full
of sadness and sympathy, and of the wish to do something for those who
have opened their heart to me. After what you have said, I dare no
longer ask you to trouble yourself with their affairs, but I have
promised the baroness to assist her as far as my small powers permit,
and your kindness allows. I implore you to grant me permission to do
this. I shall endeavor to be regular in my attendance at the office, but
if during the next few weeks I am occasionally absent, I must ask you to
excuse me."
Once more the merchant walked up and down the room, and then, looking at
Anton's excited face, with deep seriousness and something of regret, he
replied, "Remember, Wohlfart, that every occupation which excites the
mind soon obtains a hold over a man, which may retard as well as advance
his success in life. It is thi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 to agree
to your wishes."
"I know it," said Anton, in a low voice; "but I have now no choice
left."
"Well, then, do what you must," said the merchant, gloomily; "I will lay
no hinderance in your way; and I hope that after a few weeks you will be
able to consider the whole circumstances more calmly." Anton left the
room, and the merchant stood looking long with frowning brow at the
place his clerk had occupied.
Nor was Anton in a more congenial mood. "So cold, so inexorable!"
exclaimed he, as he reached his own room. He began to suspect that his
principal was more selfish and less kindly than he had hitherto
supposed. Many an expression of Fink's recurred to his mind, as well as
that evening when young Rothsattel, in his boyish conceit, had spoken
impertinently to the merchant. "Is it possible," thought he, "that that
rude speech should be unforgotten?" And his chief's keen, deep-furrowed
face lost inexpressibly by contrast with the fair forms of the noble
ladies. "I am not wrong," he cried to himself; "let him say what he
will, my views are more just than his, and henceforth my destiny shall
be to choose for myself the way in which I shall walk." He sat long in
the darkness, and his thoughts were gloomy as it; then he went to the
window to look down into the dark court below. A great white blossom
rose before him like a phantom. Striking a light, he saw that it was the
beautiful Calla out of Sabine's room. It hung down mournfully on its
broken stem. Sabine had had it placed there. This little circumstance
struck him as a mournful omen.
Meanwhile Sabine, taper in hand, entered her brother's room.
"Good-night, Traugott," nodded she. "Wohlfart has been with you this
evening; how long he staid!"
"He will leave us," replied the merchant, gloomily.
Sabine started and dropped her taper on the table. "For God's sake, what
has happened? Has Wohlfart said that he was going away?"
"I do not yet know it, but I see it coming step by step; and I can not,
and still less can you, do any thing to retain him. When he stood before
me here with glowing cheeks and trembling voice, pleading for a ruined
man, I found out what it was that lured him away."
"I do not understand you," said Sabine, looking full at her brother.
"He chooses to become the confidential friend of a decayed noble. A pair
of bright eyes draws him away from us: it seems to him a worthy object
of ambition to become Rothsattel's man of business. This intimacy with
nobility is the legacy bequeathed to him by Fink."
"And you have refused to help him?" inquired Sabine, in a low voice.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said the merchant, harshly; and he
turned to his writing-table.
Sabine slowly withdrew. The taper trembled in her hand as she passed
through the long suite of rooms listening to her own footfall, and
shuddering as the feeling came over her that an invisible companion
glided by her side. This was the revenge of that other. The shadow that
once fell on her innocent life now drove her friend away from their
circle. Anton's affections clung to another. She had but been in his
eyes a mere stranger, who had once loved and languished for one now far
away, and who now, in widow's weeds, looked back regretfully to the
feelings of her youth.
The few next weeks were spent by Anton in over-hard work. He had great
difficulty in keeping up his counting-house duties, while he spent every
spare hour in conference with the baroness and the lawyer.
In the mean time, the misfortunes of the baron ran their course. He had
not been able to pay the interest of the sums with which his estate was
burdened. When last they were due, a whole series of claims was brought
against him, and the estate fell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district authorities. Complicated lawsuits arose. Ehrenthal complained
loudly, claiming the first mortgage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nay, he
was inclined to advance claims on the last mortgage offered by the baron
in the recent fatal hour. Löbel Pinkus also appeared as claimant of the
first mortgage, and asserted that he had paid the whole sum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Ehrenthal had no proof to bring forward, and had been
for some weeks past quite unable to manage his own affairs, while
Pinkus, on the contrary, fought with every weapon a hardened sinner can
devise or employ, and the deeds which the baron had executed at Veitel's
suggestion proved to be so capital a master-stroke of the cunning
advocate, that the baron's man of business had, from the first, little
hope of the case. We may here observe that Pinkus did eventually win it,
and that the mortgage was made over to him.
Anton was now gradually gaining some insight into the baron's
circumstances. But the double sale of the first mortgage was still kept
a secret by the latter, even from his wife. He declared Ehrenthal's
claim unfounded, and even expressed a suspicion that he had himself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robbery in his office. Indeed, he really
believed this. Then the name of Itzig was never broached, and the
suspicion against Ehrenthal, which the baron's lawyer shared, prevented
Anton seeking any explanation from him.
Meanwhile, an estrangement had sprung up between our hero and his
principal, which the whole counting-house remarked with surprise. The
merchant scowled at Anton's vacant seat when the latter chanced to be
absent during office-hours, or looked coldly at his clerk's face, made
pale as it was with excitement of mind and night-work. He took no notice
of his new occupation, and never seemed to remark him. Even to his
sister he maintained a stiff-necked silence; nor could all her attempts
lead him to speak of Anton, who, on his side, felt his heart revolt
against this coldness. After his return, to be treated like a child of
the house, praised, promoted, petted, and now to be treated like a mere
hireling, who is not worth the bread thrown to him; to be a toy of an
incomprehensible caprice--this, at least, he had not deserved; so he
became reserved toward the whole family, and sat silent at his desk; but
he fel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now and the then so keenly, that often,
when alone, he would spring up and stamp on the ground in the bitter
indignation of his heart.
One comfort remained. Sabine was not estranged. True, he saw little of
her, and at dinner she seemed to avoid speaking to him, but he knew that
she was on his side.
A few days after his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the merchant, she came down
stairs as he stood in the hall, and had to pass him by so closely that
her dress touched him. He had retreated, and made a formal bow, but she
looked at him imploringly, and whispered, "You must not be estranged
from me." It was an affair of a moment, but the faces of both were
radiant with a happy understanding.
The time had now arrived when Mr. Jordan was to quit the firm. The
principal again called Anton into his little office, and without any
severity, but also without a trace of his former cordiality, began: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o you my intention of appointing you Jordan's
successor; but,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your time has been more taken
up with other business than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such a post, I
therefore ask you whether you are now at liberty to undertake Jordan's
duties?"
"I am not," replied Anton.
"Can you name any--not very distant--time when you will be free from
your present occupation? In that case I will endeavor to find a
substitute until then."
Anton sorrowfully replied, "I can not at present say when I shall again
be master of my whole time; and, besides, I feel that, even as it is, I
tax your indulgence by many irregularities. Therefore, Mr. Schröter, I
beg that you will fill up this post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me."
The merchant's brow grew furrowed and dark, and he silently bowed
assent. Anton felt as he closed the door that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m was now complete, and, resuming his place, he leaned his throbbing
head on his hand. A moment later Baumann was summoned to the principal,
and Jordan's situation conferred upon him. On returning to the office,
he went up to Anton and whispered, "I refused at first, but Mr. Schröter
insisted. I am doing you an injustice." And that evening Mr. Baumann, in
his own room, read in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the chapters treating of
the unjust Saul (the principal), and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Jonathan
and the persecuted David, and strengthened his heart thereby.
The next day Anton was summoned to the baroness. Lenore and her mother
sat before a large table covered with jewel-boxes and toilette elegances
of every description, while a heavy iron chest stood at their feet. The
curtains were drawn, and the subdued light shone softly into the richly
furnished room. On the carpet glowed wreaths of unfading flowers, and
the clock ticked cheerfully in its alabaster case. Under the shade of
flowering plants sat the two love-birds in their silvered cage, hopping
from perch to perch, screaming ceaselessly, or sitting up quietly close
to each other. The whole room was beauty and perfume. "For how long?"
thought Anton. The baroness rose. "We are already obliged to trouble you
again," said she; "we are engaged in a very painful occupation." On the
table were all manner of ornaments, gold chains, brilliants, rings,
necklaces, gathered into a heap.
"We have been looking out all that we can dispense with," said the
baroness, "and now pray you to undertake to sell these things for us. I
have been told that some of them are of value, and as we are now in much
need of money, we turn here for help."
Anton looked in perplexity at the glittering heap.
"Tell us, Wohlfart," cried Lenore, anxiously, "is this necessary? can it
be of any use? Mamma has insisted upon setting apart for sale all our
ornaments, and whatever plate is not in daily use. What I can give is
not worth talking of, but my mother's jewels are costly; many of them
were presents made to her in youth, which she shall not part with unless
you say that it is necessary."
"I fear," said Anton, gravely, "that it will prove so."
"Take them," said the baroness to Anton; "I shall be calmer when I know
that we have at least done what we could."
"But do you wish to part with all?" inquired Anton, anxiously. "Much
that is dear to you may have but little value in a jeweler's eyes."
"I shall never wear an ornament again," quietly replied the baroness.
"Take them all;" and, holding her hands before her eyes, she turned
away.
"We are torturing my mother," cried Lenore, hastily; "will you lock up
all that is on the table, and get them out of the house as soon as you
can?"
"I can not undertake the charge of these valuables," said Anton,
"without taking some measures to decrease my own responsibility. First
of all, I will in your presence make a short note of all you intrust to
me."
"What useless cruelty!" exclaimed Lenore.
"It will not take long."
Anton took out a few sheets from his pocket-book, and began to note down
the different articles.
"You shall not see it done, mother," said Lenore, drawing her mother
away, and then returning to watch Anton at his task.
"These preparations for the market are horrible," said she. "My mother's
whole life will be sold; some memory of hers is linked with every single
thing. Look, Wohlfart, the princess gave her this diamond ornament when
she married my father."
"They are magnificent brilliants," cried Anton, admiringly.
"This ring was my grandfather's, and these are presents of poor papa's.
Alas! no man can know how we love all these things. It was always a
festival to me when mamma put on her diamonds. Now we come to my
possessions. They are not worth much. Do you think this bracelet good
gold?" She held out her hand as she spoke.
"I do not know."
"It shall go with the rest," said Lenore, taking it off. "Yes, you are a
kind, good man, Wohlfart," continued she, looking trustfully into his
tearful eyes; "do not forsake us. My brother has no experience, and is
more helpless than we are. It is a frightful position for me. Before
mamma I do all I can to be composed, else I could scream and weep the
whole day through." She sank in a chair, still holding his hand. "Dear
Wohlfart, do not forsake us."
Anton bent over her, and looked with passionate emotion at the lovely
face that turned so trustfully to him in the midst of its tears.
"I will be helpful to you when I can," said he, in the fullness of his
heart. "I will be at hand whenever you need me. You have too good an
opinion of my information and my faculties; I can be of less assistance
to you than you suppose, but what I can, that I will do in any and every
possible way."
Their hands parted with a warm pressure; the affair was settled.
The baroness now returned. "Our lawyer was with me this morning," said
she; "and now I must ask for your opinion on another subject. He tells
me that there is no prospect of preserving the baron's family estate."
"At this time, when interest is high, and money difficult to get, none,"
replied Anton.
"And you, too, think that we must turn all our efforts toward preserving
the Polish property?"
"I do," was the answer.
"For that, also, money will be necessary. Perhaps I may be able through
my relatives to intrust you with a small sum, which, with the help of
that"--she pointed to the iron chest--"may suffice to cover the first
necessary expenses. I do not, however, wish to sell the jewels here, and
a journey to the residence would be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cure the
sum to which I have just alluded. The baron's lawyer has spoken most
highly of your capacity for business. It is his wish which now decides
me to make a proposal to you. Will you for the next few years, or, at
all events, until our greatest difficulties are over, devote your whole
time to our affairs? I have consulted my children, and they agree with
me in believing that in your assistance lies our only hope of rescue.
The baron, too, has come in to the plan. The question now is whether
your circumstances allow you to give your support to our unfortunate
family. We shall be grateful to you, whatever conditions you affix; and
if you can find any way of making our great obligations to you apparent
in the position you hold, pray impart it to me."
Anton stood petrified. What the baroness required of him was separation
from the firm, separation from his principal, and from Sabine! Had this
thought occurred to him before, when standing in Lenore's presence or
bending over the baron's papers? At all events, now that the words were
spoken, they shocked him. He looked at Lenore, who stood behind her
mother with hands clasped in supplication. At length he replied, "I
stand in a position which I can not leav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others.
I was not prepared for this proposal, and beg to have time allowed me
for consideration. It is a step which will decide my whole future life."
"I do not press you," said the baroness; "I only request your
consideration. Whatever your decision be, our warmest gratitude will
still be yours; if you are unable to uphold our feeble strength, I fear
that we shall find no one to do so. You will think of that," she added,
beseechingly.
Anton hurried through the street with throbbing pulse. The noble lady's
glance of entreaty, Lenore's folded hands, beckoned him out of the
gloomy counting-house into a sphere of greater liberty, into a new
future, from whose depths bright images flashed out upon his fancy. A
request had been frankly made, and he was strongly inclined to justify
the confidence that prompted it. Those ladies required an unwearied,
self-sacrificing helper to save them from utter ruin, and if he
followed his impulse he should be doing a good work--fulfilling a duty.
In this mood he entered the merchant's dwelling. Alas! all that he saw
around him seemed to stretch out a hand to detain him. As he looked at
the warehouse, the good-humored faces of the porters, the chains of the
great scales, the hieroglyphics of the worthy Pix, again he felt that
this was the place that he belonged to. Sabine's dog kissed his hand,
and ran before him to his room--his and Fink's room. Here the childish
heart of the orphan boy had found a friend, kind companions, a home, a
definite and honorable life-purpose. Looking down through his window on
all the long-familiar objects, he saw a light in Sabine's store-chamber.
How often he had sought for that light, which brightened the whole great
building, and brought a sense of comfort and cheerfulness even into his
room. He now sprang up suddenly, and said to himself, "She shall
decide."
Sabine started in amazement when Anton appeared before her. "I am
irresistibly impelled to seek you," cried he. "I have to decide upon my
future life, and I feel undetermined, and unable to trust to my own
judgment. You have always been a kind friend to me since the day of my
arrival. I am accustomed to look up to you, and to think of you in
connection with all that interests me here. Let me hear your opinion
from your own lips. The Baroness Rothsattel has to-day proposed to me
permanently to undertake the situation of confidential adviser and
manager of the baron's affairs. Shall I accept; or shall I remain here?
I know not--tell me what is right both for myself and others."
"Not I," said Sabine, drawing back and growing very pale. "I can not
venture to decide in the matter. Nor do you wish me to do so, Wohlfart,
for you have already decided."
Anton looked straight before him and was silent.
"You have thought of leaving this house, and a wish to do so has sprung
out of the thought. And I am to justify you, and approve your resolve!
This is what you require of me," continued she, bitterly. "But this,
Wohlfart, I can not do, for I am sorry that you go away from us."
She turned away from him and leaned on the back of a chair.
"Oh, be not angry with me too!" said Anton; "that I can not bear. I have
suffered much of late. Mr. Schröter has suddenly withdrawn from me the
friendly regard that I long held my life's greatest treasure. I have not
deserved his coldness. What I have been doing has not been wrong, and
it was done with his knowledge. I had been spoiled by his kindness; I
have the more deeply felt his displeasure. My only comfort has been that
you did not condemn me. And now, do not you be cold toward me, else I
shall be wretched forever. There is not a soul on earth to whom I can
turn for affectionate comprehension of my difficulties. Had I a sister,
I should seek her heart to-day. You do not know what to me, lonely as I
am, your smile, your kindly shake of the hand has been till now. Do not
turn coldly from me, I beseech you."
Sabine was silent. At length she inquired, still with averted face,
"What draws you to those strangers; is it a joyful hope, is it sympathy
alone? Give this question close consideration before you answer it to
yourself at least."
"What it is that makes it possible for me to leave this house," said
Anton, "I do not myself know. If I can give a name to my motives, it is
gratitude felt toward one. She was the first to speak kindly to the
wandering boy on his way out into the world. I have admired her in the
peaceful brightness of her former life. I have often dreamed childish
dreams about her. There was a time when a tender feeling for her filled
my whole heart, and I then believed myself forever the slave of her
image. But years bring changes, and I learned to look on men and on life
with other eyes. Then I met her again, distressed, unhappy, despairing,
and my compassion became overmastering. When I am away from her, I know
that she is nothing to me; when I am with her, I feel only the spell of
her sorrow. Once, when I had to depart out of her circle like a culprit,
she came to me, and before the whole scornful assembly she gave me her
hand and acknowledged me her friend; and now she comes and asks for my
hand to help her father. Can I refuse it? Is it wrong to feel as I do? I
know not, and no one can tell me--no one but you alone."
Sabine's head had sunk down to the back of the chair on which she bent.
She now suddenly raised it, and with tearful eyes, and a voice full of
love and sorrow, cried, "Follow the voice that calls you. Go, Wohlfart,
go."
CHAPTER XXVII.
On a cold October day, two men were seen driving through the latticed
gate of the town of Rosmin on toward the plain, which stretched out
before them monotonous and boundless. Anton sat wrapped in his fur coat,
his hat low on his forehead, and at his side was young Sturm, in an old
cavalry cloak, with his soldier's cap cocked cheerily on one side. In
front of them a farm-servant, squatted on a heap of straw, flogged on
the small horses. The wind swept the sand and straw from the
stubble-fields, the road was a broad causeway without ditches or hedges,
the horses had to wade alternately through puddles and deep sand. Yellow
sand gleamed through the scanty herbage in all directions wherever a
field-mouse had made her way to her nest or an active mole had done what
he could to diversify the unbroken plain. Wherever the ground sank,
stagnant water lodged, and there hollow willow-trees stretched their
crippled arms in the air, their boughs flapping in the wind, and their
faded leaves fluttering down into the muddy pool below. Here and there
stood a small dwarf pine, a resting-place for the crows, who, scared by
the passing carriage, flew loudly croaking over the travelers' heads.
There was no house to be seen on the road, no pedestrian, and no
conveyance of any kind.
Karl looked every now and then at his silent companion, and said at
last, pointing to the horses, "How rough their coats are, and how pretty
their gray mouse skins! I wonder how many of these beasties would go to
make up my sergeant's horse! When I took leave of my father, the old man
said, 'Perhaps I shall pay you a visit, little one, when they light the
Christmas-tree.' 'You'll never be able,' said I. 'Why not?' asked he.
'You'll never trust yourself in any post-chaise.' Then the old boy
cried, 'Oho! post-chaises are always of a stout build; I shall be sure
to trust myself in one.' But now, Mr. Anton, I see that my father never
can pay us a visit."
"Why not?"
"It is possible that he may reach Rosmin; but, as soon as he sees these
horses and this road, he will instantly turn back. 'Shall I trust
myself,' he'll say, 'in a district where sand runs between one's legs
like water, and where mice are put into harness? The ground is not firm
enough for me.'"
"The horses are not the worst things here," said Anton, absently. "Look!
these go fast enough."
"Yes," replied Karl, "but they don't go like regular horses; they
entangle their legs like two cats playing in a parsley-bed. And what
things they have for shoes--regular webbed hoofs, I declare, which no
blacksmith can ever fit."
"If we could only get on!" returned Anton; "the wind blows cold, and I
am shivering in spite of my fur."
"You have slept but little the last few nights, sir," said Karl. "The
wind blows here as if over a threshing-floor. The earth is not round
hereabouts as elsewhere, but flat as a cake. This is a complete desert;
we have been driving for more than an hour, and there is not a village
to be seen."
"A desert indeed," sighed Anton; "let us hope it may improve." They
relapsed into profound silence. At length the driver stopped near a
pool, unharnessed the horses, and led them to the water's edge, without
noticing the travelers.
"What the deuce does this mean?" cried Karl, jumping down from the
carriage.
"I am going to feed," replied the servant, sulkily, in a foreign accent.
"I am anxious to know how that will be done," said Karl. "There is not
the shadow of a bag of provender."
The horses, however, soon proved that they could live without corn; they
stretched down their shaggy heads, and began to pull the grass and weeds
at the edge of the pool, sometimes taking a draught of the dirty water.
Meanwhile the servant drew a bundle from under his seat, settled himself
under the lee of an alder-bush, and, taking his knife, cut his bread and
cheese without even glancing at the travelers.
"I say, Ignatius or Jacob," cried Karl, sharply, "how long will this
breakfast of yours last?"
"An hour," replied the man, munching away.
"And how far is it from here to the estate?"
"Six miles, or maybe more."
"You can make nothing of him," said Anton; "we must put up with the
customs of the country;" and, leaving the carriage, they went to look on
at the horses feeding.
Anton is on his way to the Polish property. He is now the baron's agent.
Anxious months have the last proved to him. The parting from his
principal and the firm had been painful in the extreme. For some time
before it, indeed, Anton had found himself alone in the midst of his
colleagues. The quiet Baumann still remained his friend, but the others
considered him a castaway. The merchant received his resignation with
icy coldness; and even in the hour of parting, his hand lay impassive as
metal in Anton's grasp. Since then, our hero had undertaken several
journeys to the capital and to creditors in the family's behalf, and now
he was on his way to set the new estate in order, accompanied by Karl,
whom he had induced to become the baron's bailiff.
Ehrenthal had, by the authority conferred on him,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from the time of the sale by auction, and hired the Polish
bailiff for the baron. There had been unfair dealings between them at
the time, and it was well known in Rosmin that the bailiff had sold off
a good deal, and been guilty of all sorts of frauds since, so that Anton
had even now no prospect of a quiet life.
"The hour is come when I may execute my commission," cried Karl, groping
in the straw under the seat. He drew out a large japanned tin case, and
carried it to Anton. "Miss Sabine gave me this in charge for you." He
then joyously opened the lid, produced the materials for an excellent
breakfast, a bottle of wine, and a silver goblet. Anton took hold of the
case.
"It has a very knowing look," said Karl. "Miss Sabine planned it
herself."
Anton examined it on all sides, and placed it carefully on a tuft of
grass; then he took up the goblet, and saw his initials engraved on it,
and underneath the words, "To thy welfare." Whereupon he forgot the
breakfast and all around him, and stood gazing at the goblet, lost in
thought.
"Do not forget the breakfast, sir," suggested Karl, respectfully.
"Sit down by me, my faithful friend; eat and drink with me. Leave off
your absurd politeness. We shall have but little, either of us, but what
we have we will share like brothers. Take the bottle if you have no
glass."
"There's nothing like leather," said Karl, taking a small leathern
drinking-cup out of his pocket. "As for 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t was
kindly meant, and I thank you; but there must be subordination, if it
were but for the sake of the others; and so, sir, be kind enough to let
me shake hands with you now, and then let things be as they were before.
Only look at the horses, Mr. Anton. My faith! the creatures devour
thistles."
Again the horses were harnessed, again they threw out their short legs
in the sand, and again the carriage rolled through the barren
district--first through an empty plain, next through a wretched
fir-wood, then past a row of low sand-hills, then over a tumble-down
bridge crossing a small stream.
"This is the property," said the driver, turning round, and pointing
with his whip to a row of dirty thatched roofs that had just come into
sight.
Anton stood up to look for the group of trees in which the Hall might be
supposed to stand. Nothing of the sort to be seen. The village was
deficient in all that adorns the home of the poorest German peasant--no
orchard, no hedged-in gardens, no lime-trees in the market-place.
"This is wretched," said he, sitting down again; "much worse than they
told us in Rosmin."
"The village looks as if under a curse," cried Karl; "no teams working
in the fields--not a cow or a sheep to be seen."
The farm-servant flogged his horses into an irregular gallop, and so
they passed through the rows of mud huts which constituted the village,
and arrived at the public house. Karl sprang from the carriage, opened
the tavern door, and called for the landlord. A Jew slowly rose from his
seat by the stove and came to the threshold. "Is the gendarme from
Rosmin come?" He is gone into the village. "Which is the way to the
farm-yard?"
The landlord, an elderly man with an intelligent countenance, described
the way in German and Polish, and remained standing at the
door--bewildered, Karl declared, by the sight of two human beings. The
carriage turned into a cross-road, planted on both sides with thick
bushes, the remains of a fallen avenue. Over holes, stones, and puddles,
it rattled on to a group of mud huts, which still had a remnant of
whitewash upon them. "The barns and stables are empty," cried Karl, "for
I see gaps in the roofs large enough to drive our carriage through."
Anton said no more; he was prepared for every thing. They drove through
a break between the stables into the farm-yard, a large irregular space,
surrounded on three sides by tumble-down buildings, and open to the
fields on the fourth. A heap of _débris_ lay there--lime and rotten
timber, the remains of a ruined barn. The yard was empty; no trace of
farm implements or human labor to be seen. "Which is the inspector's
house," inquired Anton, in dismay. The driver looked round, and at last
made up his mind that it was a small one-storied building, with straw
thatch and dirty windows.
At the noise of the wheels a man appeared on the threshold, and waited
phlegmatically till the travelers had dismounted, and were standing
close before him. He was a broad-shouldered fellow, with a bloated,
brandy-drinking face, dressed in a jacket of shaggy cloth, while behind
him peered the muzzle of an equally shaggy dog, who snarled at the
strangers. "Are you the steward of this property?"
"I am," replied the man, in broken German, without stirring from where
he was.
"And I am the agent of the new proprietor," said Anton.
"That does not concern me," growled the shaggy man, turning sharp round,
entering the house, and bolting the door within.
Anton was thoroughly roused. "Break the window in, and help me to catch
the rascal," cried he to Karl, who coolly seized a piece of wood, struck
the panes so as to make the rotten framework give way, and cleared the
opening at one leap. Anton followed him. The room was empty, so was the
next, and in it an open window--the man was gone.
"After him!" cried Karl, and dashed on in pursuit, while Anton looked
about the house and out-buildings. He soon heard the barking of a dog,
and saw Karl capture the fugitive. Hurrying to his help, he held the man
fast, while, with a kick, Karl sent the dog flying. They then contrived
to force the steward back to the house, though he kept striking out
violently all the way.
"Go to the tavern, and bring the gendarme and the landlord," cried Anton
to the driver, who, undisturbed by all that had been going on, had
meanwhile unpacked the carriage. The man accordingly drove leisurely
off, and the fugitive being got into the room, Karl found an old cloth,
and with it bound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I beg your pardon, sir,"
said he; "it is only for an hour or so, till the arrival of the Rosmin
gendarme, whom we have appointed to meet us."
Anton then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house, bu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found but the merest necessaries; no books nor papers of any kind. It
had doubtless been emptied already. A bundle projected from the
coat-pocket of the prisoner, which turned out to be receipts and legal
documents in Polish. In time, the driver returned with the landlord and
the armed policeman. The landlord stood at the door in some perplexity,
and the policeman explained in a few moments what remained to be done.
"You must make a statement to the local judge, and give the man up to
me. He shall go back in your carriage to Rosmin. You will do well to get
rid of him, for this is a wild country, and it will be safer for you to
have him at Rosmin than here, where he has friends and accomplices."
After a long search, a sheet of paper was found in a cupboard, the
statement made and submitted to the policeman, who shook his head a
little over the Polish composition, and the prisoner lifted into the
carriage, the gendarme taking his seat beside him, and saying to Anton,
"I have long expected something of the kind. You may have often occasion
to want me again." The carriage then drove away, and thus the property
came under Anton's administration. He felt as if cast on a desert
island.
His portmanteau and traveling effects were leaning against a mud wall,
and the Polish landlord was the only man who could give him and Karl any
information or advice in their forlorn condition.
Now that the steward was fairly gone, the landlord grew more
communicative, and showed himself serviceable and obliging. A long
conversation ensued, and its purport was what Anton had apprehended from
the warning given by the Commissary Walter and other Rosmin officials.
The inspector had,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done all he could in the
way of spoliation, rendered daring by a report which had found its way
from the town to the village, that the present proprietor would never be
able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estate. At last Anton said, "What that
wretched man has done away with he will have to account for; our first
care must be to preserve what is still to be found on the property. You
must be our guide to-day."
They then examined the empty buildings. Four horses and two
servants--they were gone into the wood--a few old plows, a pair of
harrows, two wagons, a britzska, a cellar full of potatoes, a few
bundles of hay, a little straw--the inventory did not take much time in
drawing up. The buildings were all out of repair, not through age, but
neglect.
"Where is the dwelling-house?" inquired Anton. The landlord led the way
out of the yard to the meadow--a broad plain, gradually sloping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brook. It had been a great pasture. The cattle had
trodden it down into holes; the snouts of greedy swine had rooted it up;
gray molehills and rank tufts of grass rose on all sides.
The landlord stretched out his hand. "There is the castle. This castle
i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he added, reverentially; "no
nobleman in the district has a stone house like that. All the gentry
here live in wood and mud buildings. Herr von Tarow, the richest of
them, has but a poor dwelling."
About three hundred yards from the last out-building rose a great brick
edifice, with a black slate roof and a thick round tower. Its gloomy
walls on this treeless pasture-land, without one trace of life around,
rose beneath the cloudy sky like a phantom fortress which some evil
spirit had evoked from the abyss--a station from which to blight all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The strangers approached it. The castle had fallen into ruins before the
builders had finished their task. The tower had stood there for ages. It
was built of unhewn stone, and had small windows and loop-holes. The
former lords of the land had looked down from its summit on the tops of
the trees, which then stretched far into the plain. They had then ruled
with a rod of iron the serfs who cultivated their land, and toiled and
died for them. Many an arrow had sped through those loop-holes at the
enemy storming below, and many a Tartar horse had been overthrown before
those massive walls. Years ago, a despot of the district had, in
expiation of former sins, begun to add to the gray tower the walls of a
holy monastery; but the monastery never got finished, and the useless
walls had already stood there long, when the late count took it into his
head to convert them into a lordly dwelling for his race, and to raise a
house unparalleled for magnificence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 front of the house was added on to both sides of the tower, which
projected in the middle. The intention had been to have a high
terrace-road up to the castle, and the principal entrance had been made
in the tower, and arched over; but the terrace never having been formed,
the stone threshold of the main door was quite inacce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ladders, and the wide opening was left. The window-spaces of
the lower floor were merely closed up with boards, while on the second
story were some window-frames of beautifully carved wood, in which large
panes had once been placed, but they had got broken. In other windows
were temporary frames of rough deal, with small panes of muddy glass let
into them. A company of jackdaws sat on the top of the tower, looking
down in amazement on the strangers, and every now and then one flew off,
screaming loudly, to contemplate the intruders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A house for crows and bats, not for human beings," said Anton. "At
least, I see no way of getting into it."
The landlord now took them round the building. Behind, where the two
wings made a sort of horse-shoe, there were low entrances to the cellars
and offices; beneath which, again, were stables, great arched kitchens,
and small cells for the serfs. A wooden staircase led to the upper
story. The door turned creaking on its hinges, and a narrow passage took
them through a side wing to the front part of the house. There all was
at least magnificently planned. The circular entrance-hall--an arched
room of the old tower--was painted in mosaic, and through the great
doorway-opening was seen a wide expans
small disturbance made by the return of Anton had gradually settled
down. Those first-class treasures of Sabine's had made way for other
specimens of damask, still of a superior kind, it is true, but which
came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e elderly cousin's comprehension. She had
been quite right in prophesying that Anton would never remark those
signs of exuberant gratitude or their withdrawal. However, one change
had been permanently made--the greatest, the best of all changes--the
clerk retained a privileged place in the heart of the young mistress of
the firm, and his tall figure often appeared as one of the circle that
Sabine's fancy loved to gather round her when at her work-table or in
her treasure-chamber.
To-day she was walking restlessly up and down before dinner. The cousin,
who heard every thing, had just told her that a maid from Ehrenthal's
had run into the office to announce Bernhard's death to his friend. "How
will he bear it?" thought she. And the name of Ehrenthal forced her
thoughts back to the past, to one now far away, and to that painful hour
when the struggle going on in her own mind had been suddenly brought to
a close by a letter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parted. And Anton had known
of that conquered feeling of hers. How considerate he had always been,
how chivalrous, how helpful! She wondered if he had any idea of the
completeness of her triumph over a girlish illusion. She shook her head.
"No, he has not. It was here, at this very table, that an accident first
betrayed me to him. That past time still rises like a cloud between us.
Whenever I sit near Wohlfart of an evening, I am conscious of another's
shadow at my side; and when he speaks to me, his tone, his manner always
seem to say, 'You are not alone; he is with you.'" Sabine started, and
lovingly passed her hand over the beautiful flowers on the table before
her, as if to dispel a painful thought. She could not tell him that she
was free from that long-felt sorrow. Now, however, when he had lost a
friend whom he so much loved, she must show him that there were other
hearts that clung to him still. And again she walked up and down, trying
to devise a way of speaking to him alone.
Dinner was announced. Anton came with the rest, and took his place at
once. There was no opportunity of exchanging a word during the meal, but
he often met her sad and sympathizing eye. "He eats nothing at all
to-day," whispered her cousin; "not even any of the roast," she added,
reproachfully. Sabine was much perturbed. Mr. Jordan had already risen;
Anton would leave the room with the rest, and she should not see him
again the whole day through. So she called out, "The great Calla is
fully blown now. You were admiring the buds the other day; will you
remain a moment; I should like to show it you?" Anton bowed and staid
behind. A few more awkward moments, then her brother rose too; and,
hurrying to Anton, she took him to the room where the flowers were.
"You have had sorrowful tidings to-day," she began.
"The tidings themselves did not surprise me," replied Anton. "The doctor
gave no hope. But I lose much in him."
"I never saw him," said Sabine; "but I know from you that his life was
lonely--poor in affection and in enjoyment."
She moved an arm-chair toward Anton, and led him on to talk about his
friend. She listened to every word with warm sympathy, and well knew
what to ask and how to comfort. It was a relief to Anton to speak of the
departed one, to describe his quiet way of life, his erudition, his
poetical enthusiasm. After a pause, Sabine looked up frankly into his
face, and asked, "Have you any tidings of Herr von Fink?"
It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his departure that she had ever breathed his
name. Anton felt how touching her confidence was, given in this hour of
his sadness. In his emotion, he seized her hand, which she was slow in
withdrawing.
"He is not happy in his new life," he gravely replied. "There was a
savage humor in his last letter, from which I gather, even more than
from his actual words, that the business into which his uncle's death
has thrown him does not suit him."
"It is unworthy," cried Sabine.
"At all events, it is not what would be recognized as honorable in this
house," replied Anton. "Fink is upright, and has lived too long with
your brother to take pleasure in the wild speculations so common on the
other side the Atlantic. His partners and colleagues are for the most
part men without a conscience, and his feelings revolt against their
companionship."
"And can Herr von Fink tolerate such relations as these for a day?"
"It is a remarkable thing that he whose own will was ever so arbitrarily
exercised, should now be obliged against that will to obey a pressure
from without, and every where to work with his hands tied. The
organization of such speculations in America is so complicated that one
shareholder can do little to alter it; and, now that Fink has attained
what used to be the goal of his wishes--a large capital, and the
management of immense districts--his condition appears more uncertain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He was always in danger of thinking slightingly
of others, now I am distressed at the bitter contempt he expresses for
his own life. His last letter paints an intolerable state of things, and
seems to point to some decisive resolve."
"There is only one resolve for him," cried Sabine. "May I ask what you
said to him in reply?"
"I entreated him instantly, come what would, to free himself from the
business in which he was entangled. I said that his own strong will
might find a way of extrication, even if that which I pointed out proved
impracticable. Then I begged of him either to carry out his old plan of
becoming a landed proprietor in America, or to return to us."
"I knew that you would write thus," said Sabine, drawing a long breath.
"Yes, Wohlfart, he shall return," said she, gently, "but he shall not
return to us."
Anton was silent.
"And do you think that Herr von Fink will follow your advice?"
"I do not know. My advice was not very American."
"But it was worthy of you," cried Sabine, with proud delight.
"An officer wishes to speak to Mr. Wohlfart," said a servant at the
door.
Anton sprang up. Sabine went to her flowers and bent mournfully over
them. The shadows of others hovered still between her friend and her.
The few words spoken by the servant filled Anton with a vague terror. He
hurried into the ante-room: there stood Eugene von Rothsattel. Anton was
gladly rushing forward to greet him, but the young soldier's face of
agony made him start back. He whispered, "My mother wishes to speak to
you; something dreadful has occurred." Anton caught up his hat, ran into
the office, hurriedly asked Baumann to excuse him to the principal, and
then accompanied the lieutenant to the baron's house.
On the way, Eugene, who had lost all self-command, said unconnectedly to
Anton, "My father last night accidentally wounded himself by a
pistol-shot--a messenger was sent to summon me--when I came, I found my
mother in a swoon--my sister and I do not know what to do--Lenore
implored my mother on her knees to send for you--you are the only one in
whom w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our distress--I understand nothing about
business, but my father's affairs must be in a dreadful state--my mother
is beside herself--the whole house is in the greatest disorder."
From what Eugene said and what he did not say; from his broken sentences
and his look of agony, Anton guessed at the horrors of the previous
evening. In the boudoir of the baroness he found Lenore, weeping and
exhausted.
"Dear Wohlfart!" cried she, taking his hand and beginning again to sob,
while her head sank powerless on his shoulder.
Meanwhile Eugene walked up and down, wringing his hands, and at length
throwing himself on the sofa, he gave himself up to silent tears.
"It is horrible, Mr. Wohlfart," said Lenore, lifting up her head. "No
one may approach my father--Eugene may not, nor I--only my mother and
old John are with him; and early this morning the merchant Ehrenthal was
here, insisting that he must see my father. He screamed at my mother,
and called my father a deceiver, till she fainted away. When I rushed
into the room, the dreadful man went off threatening her with his
clenched fist."
Anton led Lenore to a chair and waited till she had told him all.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comforting in this case, and his own heart was
wrung to the utmost by the misery he witnessed.
"Call my mother, Eugene," said Lenore, at length.
Her brother left the room.
"Do not forsake us," implored Lenore, clasping her hands; "we are at the
last gasp; even your help can not save us."
"He is dead who might perhaps have done so," mournfully replied Anton.
"Whether I can be of any use I know not, but you can not doubt my
willingness to be so."
"No," cried Lenore. "And Eugene, too, thought of you at once."
The baroness now entered. She walked wearily; but, steadying herself by
a chair, she saluted Anton with dignity. "In our position," said she,
"we need a friend who knows more of business than we three do.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prevents the baron--possibly for a long time to
come--from managing his own affairs, and, little as I understand them, I
can see that our interests require prompt measures. My children have
mentioned you to me, but I fear I am unreasonable in asking you to
devote your time to our service."
She sat down, beckoned Anton to take a chair, and said to her children,
"Leave us; I shall be better able to tell Mr. Wohlfart the little that I
know when I do not see your grief."
When they were alone, she motioned him nearer and tried to speak, but
her lips quivered, and she hid her face in her handkerchief.
"Before I can consent, gracious lady," said he, "to your reposing in me
such confidence as this, I must first inquire whether the baron has no
relative or intimate friend to whom you could with less pain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I pray you to remember that my own knowledge of business
is but small, and my position not one to constitute me a proper
counselor to the baron."
"I know no one," said the baroness, hopelessly. "It is less painful to
me to tell you what I can not conceal, than to one of our own circle.
Consider yourself a physician sent for to visit a patient. The baron has
this morning told me some particulars of his present circumstances." And
then she proceeded to relate what she had gathered as to the nature of
his embarrassments, the danger in which the family property was placed,
and the capital needed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Polish estate.
"My husband," continued she, "has given me the key of his desk, and he
wishes Eugene, with the help of a man of business, to go over his
papers. I now request of you to make this examination together with my
son. When you need explanations, I will try to obtain them from the
baron. The question is now, whether you are inclined to undertake this
trouble for us, who are only strangers."
"I am most willing to do so," earnestly replied Anton; "and I hope that
the kindness of my principal will allow me the time needful for the
purpose, if you do not consider it more advisable to depute the baron's
experienced legal adviser to the task."
"There will be an opportunity of asking that gentleman's advice later,"
said the baroness.
Anton rose. "When do you wish to begin?"
"Immediately. I fear there is not a day to lose. I shall do all I can to
help you look the papers over." She led Anton into the next room, called
in Eugene, and unlocked the baron's desk. As she opened it she lost her
self-command for a moment, and moving to the window, the quivering of
the curtains betrayed the anguish that shook her fragile frame.
The mournful task began. Hour after hour passed. Eugene was in no
condition to peruse any thing, but his mother reached letters and
documents to Anton, and, though often obliged to desist a while, she
bravely returned to the task. Anton placed the papers in order, and
sought, by glancing over each, to arrive at least at a superficial view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It was evening, when the old servant opened the door in dismay, and
called out, "He is there again." The baroness could not repress a slight
scream, and made a gesture of aversion.
"I have told him that no one is at home, but he will not be dismissed;
he makes such a noise on the steps. I can not get rid of him."
"It will kill me if I hear his voice again," murmured the baroness.
"If the man be Ehrenthal," said Anton, rising, "I will try to get him
away. We have now done what was most necessary; have the goodness to
lock up these papers, and to allow me to return to-morrow." The baroness
silently assented, and sank back in her chair. Anton hurried off to the
ante-room, whence he could hear Ehrenthal's loudly-raised voi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usurer shocked him. His hat pushed half off his
head, his pale face swelled as if by drinking, his glazed eyes red with
tears, Ehrenthal stood before him, calling in broken sentences for the
baron, wailing and cursing alternately. "He must come! he must come at
once!" cried he; "the wicked man! A nobleman, indeed! he is a vagabond,
after whom I will send the police. Where is my money? Where is my
security? I want my mortgage from this man who is not at home."
Anton went straight up to him, and asked, "Do you know me, Mr.
Ehrenthal?" Ehrenthal turned his glazed eyes upon him, and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 friend of his dead son.
"He loved you!" he cried, in a lamentable voice. "He spoke to you more
than to his father. You were the only friend that he had on earth. Have
you heard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house of Ehrenthal?" continued he, in
a whisper. "Just as they stole the papers he died. He died with a hand
like this," and clenching his fist he struck his forehead. "Oh my son!
my son! why didst not thou forgive thy father!"
"We will go to your son," said Anton, taking the arm of the old man, who
unresistingly allowed himself to be led back to his own house.
From thence Anton hurried to Councilor Horn, with whom he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It was late before he returned home. In the midst of his anxiety about
those whose prosperity had filled his imagination years before,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in their adversity, reposed in him, dilated his
breast with a feeling of pride. He burned with desire to help them, and
hoped that his zealous devotion might yet find some way of rescue. As
yet he saw none. Looking up at the great building before him, so firm
and secure, in the moonlight, a thought flashed into his mind. If any
man could help them, it was his principal. His keen eye would be able to
unravel all the dark secrets in which the baron was entangled, and his
iron strength of will would crush the villains who held the unfortunate
nobleman in their power. And then he had a noble nature; he always
decided on the right, without an effort or a struggle. Anton looked at
the first floor. The whole house-front was dark, but in a corner room a
light still burned. It was the private office of his chief.
With sudden resolve, Anton begged the servant to take him to Mr.
Schröter, who looked with amazement at the unexpected visitor, and asked
what brought him, and whether any thing had happened.
"I implore your counsel--I implore your help," cried Anton.
"For yourself or for others?" inquired the merchant.
"For a family with whom I have accidentally become connected. They are
lost if a strong hand does not ward off the impending catastrophe."
Anton then rapidly related the occurrences of the afternoon, and,
seizing his principal's hand in his emotion, cried, "Have pity upon the
unhappy ladies, and help them."
"Help them!" replied the merchant; "how can I? Have you been
commissioned to apply to me, or are you only following the impulse of
your own feelings?"
"I am not commissioned; it is only the interest that I take in the
baron's fate which leads me to you."
"And what right have you to inform me of facts communicated in strict
confidence to yourself by the baron's lady?" asked the merchant, dryly.
"I am committing no indiscretion in telling you what will, in a few
days, be no secret, even to strangers."
"You are unusually excited, otherwise you would not forget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hatever, does a man of business venture to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without the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Of course, I shall make no wrong use of what you have said, but it was
by no means business-like, Wohlfart, to be so open toward me."
Anton was silent, feeling, indeed, that his principal was right, but yet
it seemed hard to be blamed for reposing confidence at such a time as
this. The merchant walked silently up and down; at length, stopping
before Anton, he said, "I do not now inquire how you come to take so
warm an interest in this family. I fear it is an acquaintance you owe to
Fink."
"You shall hear all," said Anton.
"Not at present. I will now content myself with repeating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interfere in these affairs without being specially
applied to by the parties themselves. I may add that I by no means wish
for such an application, and do not disguise from you that, were it
made, I should probably decline to do any thing for the Baron
Rothsattel."
Anton's feelings were roused to the utmost. "The question is the rescue
of an honorable man, and of lovely and amiable women from the toils of
rogues and impostors. To me, this seems the duty of every one; I, at
least, consider it a sacred obligation which I dare not shrink from. But
without your support I can do nothing."
"And how do you think this embarrassed man can be helped?" inquired the
merchant, seating himself.
With somewhat more composure, Anton repli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an experienced man of business making himself master of the case. There
must be some way of circumventing these villains. Your penetration would
discover it."
"Any attorney would be far more likely to do so, and the baron might
readily engage the services of experienced and upright legal advisers.
If his enemies have done any thing illegal, the quick eye of a lawyer is
the most likely to detect it."
"Alas! the baron's own lawyer gives but little hope," replied Anton.
"Then, my dear Wohlfart, no other is likely to do much good. Show me an
embarrassed man who has strength to grasp an offered hand, and bid me
help him, and for the sake of all I owe you, I will not refuse to do so.
I think you are convinced of this."
"I am," said Anton, dejectedly.
"From all I hear, however," the merchant went on,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the baron. From what I gather from general report, as well as from
you, his embarrassments arise from his having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usurers, which proves him deficient in what alone ennobles the life of
any man--good sense, and the power of steady exertion."
Anton could only sigh his assent.
"To help such a man," inexorably continued the merchant, "is a futile
attempt, against which reason may well protest. We are not to despair of
any, but want of strength is the most hopeless case of all. Our power of
laboring for others being limited, it becomes our duty to inquire,
before we devote our time to the weak, whether we are not thus
diminishing our chances of helping better men."
Anton interrupted him. "Does he not deserve every allowance to be made
for him? He was brought up to exact much; he has not learned, as we
have, to make his way by his own labor."
The merchant laid his hand on the young man's shoulder. "The very
reason. Believe me, a large number of these landed gentry, who pay the
penalty of their old family memories, are beyond help. I am the last to
deny that many worthy and admirable men belong to this class. Indeed,
wherever remarkable talent or nobility of character shoots up among
them, no doubt their position offers peculiar scope for its development,
but for average men it is not a favorable one. He who considers it his
hereditary privilege to enjoy life, and who assumes a distinguished
position in virtue of his family, will very often fail to put forth his
whole strength in order to deserve that position. Accordingly, numbers
of our oldest families are declining, and their fall will be no loss to
the state. Their family associations make them haughty without any
right to be so--limit their perceptions and confuse their judgment."
"Even if all this be true," cried Anton, "it does not absolve us from
helping individuals of the class who have excited our sympathy."
"No," said the principal, "if it be excited. But it does not glow so
rapidly in advancing years as in youth. The baron has endeavored to
isolate his property from the current of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leave it forever to his family. Forever! You, as a merchant, know how to
estimate the attempt. True, every rational man must allow it to be
desirable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same soil should be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We all prize what our forefathers have possessed before
us, and Sabine would unlock every room in this house with pride, because
her great-great-grandmother turned the same keys before her. It is
therefore natural that the landed proprietor should desire to preserve
those familiar scenes, which are the source of his own prosperity, to
those nearest and dearest to him. But there must be means to this end,
and these means are the making his own existence available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increase of his patrimony. Where energy dies in families
or individuals, then it is well that their means die too, that their
money should circulate through other hands, and their plowshare pass to
those who can guide it better. A family that has become effete through
luxury ought to sink down into common life, to make room for the
uprising of fresh energies and faculties. Every one who seeks, at the
cost of free activity for others, to preserve permanent possessions and
privileges for himself or his family, I must look upon as an enemy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social state. And if such a man ruin
himself in his endeavors, I should feel no malicious pleasure in his
downfall, but I should say that he is rightly served, because he has
sinned against a fundamental law of our social being; consequently, I
should consider it doubly wrong to support this man, because I could but
fear that I should thus be supporting an unsound condition of the body
politic."
Anton looked down mournfully. He had expected sympathy and warm
concurrence, and he met with disaffection and coldness that he despaired
of conquering. "I can not gainsay you," he at length replied; "but in
this case I can not feel as you do. I have been witness to the
unspeakable distress in the baron's family, and my whole soul is full
of sadness and sympathy, and of the wish to do something for those who
have opened their heart to me. After what you have said, I dare no
longer ask you to trouble yourself with their affairs, but I have
promised the baroness to assist her as far as my small powers permit,
and your kindness allows. I implore you to grant me permission to do
this. I shall endeavor to be regular in my attendance at the office, but
if during the next few weeks I am occasionally absent, I must ask you to
excuse me."
Once more the merchant walked up and down the room, and then, looking at
Anton's excited face, with deep seriousness and something of regret, he
replied, "Remember, Wohlfart, that every occupation which excites the
mind soon obtains a hold over a man, which may retard as well as advance
his success in life. It is thi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 to agree
to your wishes."
"I know it," said Anton, in a low voice; "but I have now no choice
left."
"Well, then, do what you must," said the merchant, gloomily; "I will lay
no hinderance in your way; and I hope that after a few weeks you will be
able to consider the whole circumstances more calmly." Anton left the
room, and the merchant stood looking long with frowning brow at the
place his clerk had occupied.
Nor was Anton in a more congenial mood. "So cold, so inexorable!"
exclaimed he, as he reached his own room. He began to suspect that his
principal was more selfish and less kindly than he had hitherto
supposed. Many an expression of Fink's recurred to his mind, as well as
that evening when young Rothsattel, in his boyish conceit, had spoken
impertinently to the merchant. "Is it possible," thought he, "that that
rude speech should be unforgotten?" And his chief's keen, deep-furrowed
face lost inexpressibly by contrast with the fair forms of the noble
ladies. "I am not wrong," he cried to himself; "let him say what he
will, my views are more just than his, and henceforth my destiny shall
be to choose for myself the way in which I shall walk." He sat long in
the darkness, and his thoughts were gloomy as it; then he went to the
window to look down into the dark court below. A great white blossom
rose before him like a phantom. Striking a light, he saw that it was the
beautiful Calla out of Sabine's room. It hung down mournfully on its
broken stem. Sabine had had it placed there. This little circumstance
struck him as a mournful omen.
Meanwhile Sabine, taper in hand, entered her brother's room.
"Good-night, Traugott," nodded she. "Wohlfart has been with you this
evening; how long he staid!"
"He will leave us," replied the merchant, gloomily.
Sabine started and dropped her taper on the table. "For God's sake, what
has happened? Has Wohlfart said that he was going away?"
"I do not yet know it, but I see it coming step by step; and I can not,
and still less can you, do any thing to retain him. When he stood before
me here with glowing cheeks and trembling voice, pleading for a ruined
man, I found out what it was that lured him away."
"I do not understand you," said Sabine, looking full at her brother.
"He chooses to become the confidential friend of a decayed noble. A pair
of bright eyes draws him away from us: it seems to him a worthy object
of ambition to become Rothsattel's man of business. This intimacy with
nobility is the legacy bequeathed to him by Fink."
"And you have refused to help him?" inquired Sabine, in a low voice.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said the merchant, harshly; and he
turned to his writing-table.
Sabine slowly withdrew. The taper trembled in her hand as she passed
through the long suite of rooms listening to her own footfall, and
shuddering as the feeling came over her that an invisible companion
glided by her side. This was the revenge of that other. The shadow that
once fell on her innocent life now drove her friend away from their
circle. Anton's affections clung to another. She had but been in his
eyes a mere stranger, who had once loved and languished for one now far
away, and who now, in widow's weeds, looked back regretfully to the
feelings of her youth.
The few next weeks were spent by Anton in over-hard work. He had great
difficulty in keeping up his counting-house duties, while he spent every
spare hour in conference with the baroness and the lawyer.
In the mean time, the misfortunes of the baron ran their course. He had
not been able to pay the interest of the sums with which his estate was
burdened. When last they were due, a whole series of claims was brought
against him, and the estate fell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district authorities. Complicated lawsuits arose. Ehrenthal complained
loudly, claiming the first mortgage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nay, he
was inclined to advance claims on the last mortgage offered by the baron
in the recent fatal hour. Löbel Pinkus also appeared as claimant of the
first mortgage, and asserted that he had paid the whole sum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Ehrenthal had no proof to bring forward, and had been
for some weeks past quite unable to manage his own affairs, while
Pinkus, on the contrary, fought with every weapon a hardened sinner can
devise or employ, and the deeds which the baron had executed at Veitel's
suggestion proved to be so capital a master-stroke of the cunning
advocate, that the baron's man of business had, from the first, little
hope of the case. We may here observe that Pinkus did eventually win it,
and that the mortgage was made over to him.
Anton was now gradually gaining some insight into the baron's
circumstances. But the double sale of the first mortgage was still kept
a secret by the latter, even from his wife. He declared Ehrenthal's
claim unfounded, and even expressed a suspicion that he had himself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robbery in his office. Indeed, he really
believed this. Then the name of Itzig was never broached, and the
suspicion against Ehrenthal, which the baron's lawyer shared, prevented
Anton seeking any explanation from him.
Meanwhile, an estrangement had sprung up between our hero and his
principal, which the whole counting-house remarked with surprise. The
merchant scowled at Anton's vacant seat when the latter chanced to be
absent during office-hours, or looked coldly at his clerk's face, made
pale as it was with excitement of mind and night-work. He took no notice
of his new occupation, and never seemed to remark him. Even to his
sister he maintained a stiff-necked silence; nor could all her attempts
lead him to speak of Anton, who, on his side, felt his heart revolt
against this coldness. After his return, to be treated like a child of
the house, praised, promoted, petted, and now to be treated like a mere
hireling, who is not worth the bread thrown to him; to be a toy of an
incomprehensible caprice--this, at least, he had not deserved; so he
became reserved toward the whole family, and sat silent at his desk; but
he fel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now and the then so keenly, that often,
when alone, he would spring up and stamp on the ground in the bitter
indignation of his heart.
One comfort remained. Sabine was not estranged. True, he saw little of
her, and at dinner she seemed to avoid speaking to him, but he knew that
she was on his side.
A few days after his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the merchant, she came down
stairs as he stood in the hall, and had to pass him by so closely that
her dress touched him. He had retreated, and made a formal bow, but she
looked at him imploringly, and whispered, "You must not be estranged
from me." It was an affair of a moment, but the faces of both were
radiant with a happy understanding.
The time had now arrived when Mr. Jordan was to quit the firm. The
principal again called Anton into his little office, and without any
severity, but also without a trace of his former cordiality, began: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o you my intention of appointing you Jordan's
successor; but,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your time has been more taken
up with other business than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such a post, I
therefore ask you whether you are now at liberty to undertake Jordan's
duties?"
"I am not," replied Anton.
"Can you name any--not very distant--time when you will be free from
your present occupation? In that case I will endeavor to find a
substitute until then."
Anton sorrowfully replied, "I can not at present say when I shall again
be master of my whole time; and, besides, I feel that, even as it is, I
tax your indulgence by many irregularities. Therefore, Mr. Schröter, I
beg that you will fill up this post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me."
The merchant's brow grew furrowed and dark, and he silently bowed
assent. Anton felt as he closed the door that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m was now complete, and, resuming his place, he leaned his throbbing
head on his hand. A moment later Baumann was summoned to the principal,
and Jordan's situation conferred upon him. On returning to the office,
he went up to Anton and whispered, "I refused at first, but Mr. Schröter
insisted. I am doing you an injustice." And that evening Mr. Baumann, in
his own room, read in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the chapters treating of
the unjust Saul (the principal), and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Jonathan
and the persecuted David, and strengthened his heart thereby.
The next day Anton was summoned to the baroness. Lenore and her mother
sat before a large table covered with jewel-boxes and toilette elegances
of every description, while a heavy iron chest stood at their feet. The
curtains were drawn, and the subdued light shone softly into the richly
furnished room. On the carpet glowed wreaths of unfading flowers, and
the clock ticked cheerfully in its alabaster case. Under the shade of
flowering plants sat the two love-birds in their silvered cage, hopping
from perch to perch, screaming ceaselessly, or sitting up quietly close
to each other. The whole room was beauty and perfume. "For how long?"
thought Anton. The baroness rose. "We are already obliged to trouble you
again," said she; "we are engaged in a very painful occupation." On the
table were all manner of ornaments, gold chains, brilliants, rings,
necklaces, gathered into a heap.
"We have been looking out all that we can dispense with," said the
baroness, "and now pray you to undertake to sell these things for us. I
have been told that some of them are of value, and as we are now in much
need of money, we turn here for help."
Anton looked in perplexity at the glittering heap.
"Tell us, Wohlfart," cried Lenore, anxiously, "is this necessary? can it
be of any use? Mamma has insisted upon setting apart for sale all our
ornaments, and whatever plate is not in daily use. What I can give is
not worth talking of, but my mother's jewels are costly; many of them
were presents made to her in youth, which she shall not part with unless
you say that it is necessary."
"I fear," said Anton, gravely, "that it will prove so."
"Take them," said the baroness to Anton; "I shall be calmer when I know
that we have at least done what we could."
"But do you wish to part with all?" inquired Anton, anxiously. "Much
that is dear to you may have but little value in a jeweler's eyes."
"I shall never wear an ornament again," quietly replied the baroness.
"Take them all;" and, holding her hands before her eyes, she turned
away.
"We are torturing my mother," cried Lenore, hastily; "will you lock up
all that is on the table, and get them out of the house as soon as you
can?"
"I can not undertake the charge of these valuables," said Anton,
"without taking some measures to decrease my own responsibility. First
of all, I will in your presence make a short note of all you intrust to
me."
"What useless cruelty!" exclaimed Lenore.
"It will not take long."
Anton took out a few sheets from his pocket-book, and began to note down
the different articles.
"You shall not see it done, mother," said Lenore, drawing her mother
away, and then returning to watch Anton at his task.
"These preparations for the market are horrible," said she. "My mother's
whole life will be sold; some memory of hers is linked with every single
thing. Look, Wohlfart, the princess gave her this diamond ornament when
she married my father."
"They are magnificent brilliants," cried Anton, admiringly.
"This ring was my grandfather's, and these are presents of poor papa's.
Alas! no man can know how we love all these things. It was always a
festival to me when mamma put on her diamonds. Now we come to my
possessions. They are not worth much. Do you think this bracelet good
gold?" She held out her hand as she spoke.
"I do not know."
"It shall go with the rest," said Lenore, taking it off. "Yes, you are a
kind, good man, Wohlfart," continued she, looking trustfully into his
tearful eyes; "do not forsake us. My brother has no experience, and is
more helpless than we are. It is a frightful position for me. Before
mamma I do all I can to be composed, else I could scream and weep the
whole day through." She sank in a chair, still holding his hand. "Dear
Wohlfart, do not forsake us."
Anton bent over her, and looked with passionate emotion at the lovely
face that turned so trustfully to him in the midst of its tears.
"I will be helpful to you when I can," said he, in the fullness of his
heart. "I will be at hand whenever you need me. You have too good an
opinion of my information and my faculties; I can be of less assistance
to you than you suppose, but what I can, that I will do in any and every
possible way."
Their hands parted with a warm pressure; the affair was settled.
The baroness now returned. "Our lawyer was with me this morning," said
she; "and now I must ask for your opinion on another subject. He tells
me that there is no prospect of preserving the baron's family estate."
"At this time, when interest is high, and money difficult to get, none,"
replied Anton.
"And you, too, think that we must turn all our efforts toward preserving
the Polish property?"
"I do," was the answer.
"For that, also, money will be necessary. Perhaps I may be able through
my relatives to intrust you with a small sum, which, with the help of
that"--she pointed to the iron chest--"may suffice to cover the first
necessary expenses. I do not, however, wish to sell the jewels here, and
a journey to the residence would be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cure the
sum to which I have just alluded. The baron's lawyer has spoken most
highly of your capacity for business. It is his wish which now decides
me to make a proposal to you. Will you for the next few years, or, at
all events, until our greatest difficulties are over, devote your whole
time to our affairs? I have consulted my children, and they agree with
me in believing that in your assistance lies our only hope of rescue.
The baron, too, has come in to the plan. The question now is whether
your circumstances allow you to give your support to our unfortunate
family. We shall be grateful to you, whatever conditions you affix; and
if you can find any way of making our great obligations to you apparent
in the position you hold, pray impart it to me."
Anton stood petrified. What the baroness required of him was separation
from the firm, separation from his principal, and from Sabine! Had this
thought occurred to him before, when standing in Lenore's presence or
bending over the baron's papers? At all events, now that the words were
spoken, they shocked him. He looked at Lenore, who stood behind her
mother with hands clasped in supplication. At length he replied, "I
stand in a position which I can not leav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others.
I was not prepared for this proposal, and beg to have time allowed me
for consideration. It is a step which will decide my whole future life."
"I do not press you," said the baroness; "I only request your
consideration. Whatever your decision be, our warmest gratitude will
still be yours; if you are unable to uphold our feeble strength, I fear
that we shall find no one to do so. You will think of that," she added,
beseechingly.
Anton hurried through the street with throbbing pulse. The noble lady's
glance of entreaty, Lenore's folded hands, beckoned him out of the
gloomy counting-house into a sphere of greater liberty, into a new
future, from whose depths bright images flashed out upon his fancy. A
request had been frankly made, and he was strongly inclined to justify
the confidence that prompted it. Those ladies required an unwearied,
self-sacrificing helper to save them from utter ruin, and if he
followed his impulse he should be doing a good work--fulfilling a duty.
In this mood he entered the merchant's dwelling. Alas! all that he saw
around him seemed to stretch out a hand to detain him. As he looked at
the warehouse, the good-humored faces of the porters, the chains of the
great scales, the hieroglyphics of the worthy Pix, again he felt that
this was the place that he belonged to. Sabine's dog kissed his hand,
and ran before him to his room--his and Fink's room. Here the childish
heart of the orphan boy had found a friend, kind companions, a home, a
definite and honorable life-purpose. Looking down through his window on
all the long-familiar objects, he saw a light in Sabine's store-chamber.
How often he had sought for that light, which brightened the whole great
building, and brought a sense of comfort and cheerfulness even into his
room. He now sprang up suddenly, and said to himself, "She shall
decide."
Sabine started in amazement when Anton appeared before her. "I am
irresistibly impelled to seek you," cried he. "I have to decide upon my
future life, and I feel undetermined, and unable to trust to my own
judgment. You have always been a kind friend to me since the day of my
arrival. I am accustomed to look up to you, and to think of you in
connection with all that interests me here. Let me hear your opinion
from your own lips. The Baroness Rothsattel has to-day proposed to me
permanently to undertake the situation of confidential adviser and
manager of the baron's affairs. Shall I accept; or shall I remain here?
I know not--tell me what is right both for myself and others."
"Not I," said Sabine, drawing back and growing very pale. "I can not
venture to decide in the matter. Nor do you wish me to do so, Wohlfart,
for you have already decided."
Anton looked straight before him and was silent.
"You have thought of leaving this house, and a wish to do so has sprung
out of the thought. And I am to justify you, and approve your resolve!
This is what you require of me," continued she, bitterly. "But this,
Wohlfart, I can not do, for I am sorry that you go away from us."
She turned away from him and leaned on the back of a chair.
"Oh, be not angry with me too!" said Anton; "that I can not bear. I have
suffered much of late. Mr. Schröter has suddenly withdrawn from me the
friendly regard that I long held my life's greatest treasure. I have not
deserved his coldness. What I have been doing has not been wrong, and
it was done with his knowledge. I had been spoiled by his kindness; I
have the more deeply felt his displeasure. My only comfort has been that
you did not condemn me. And now, do not you be cold toward me, else I
shall be wretched forever. There is not a soul on earth to whom I can
turn for affectionate comprehension of my difficulties. Had I a sister,
I should seek her heart to-day. You do not know what to me, lonely as I
am, your smile, your kindly shake of the hand has been till now. Do not
turn coldly from me, I beseech you."
Sabine was silent. At length she inquired, still with averted face,
"What draws you to those strangers; is it a joyful hope, is it sympathy
alone? Give this question close consideration before you answer it to
yourself at least."
"What it is that makes it possible for me to leave this house," said
Anton, "I do not myself know. If I can give a name to my motives, it is
gratitude felt toward one. She was the first to speak kindly to the
wandering boy on his way out into the world. I have admired her in the
peaceful brightness of her former life. I have often dreamed childish
dreams about her. There was a time when a tender feeling for her filled
my whole heart, and I then believed myself forever the slave of her
image. But years bring changes, and I learned to look on men and on life
with other eyes. Then I met her again, distressed, unhappy, despairing,
and my compassion became overmastering. When I am away from her, I know
that she is nothing to me; when I am with her, I feel only the spell of
her sorrow. Once, when I had to depart out of her circle like a culprit,
she came to me, and before the whole scornful assembly she gave me her
hand and acknowledged me her friend; and now she comes and asks for my
hand to help her father. Can I refuse it? Is it wrong to feel as I do? I
know not, and no one can tell me--no one but you alone."
Sabine's head had sunk down to the back of the chair on which she bent.
She now suddenly raised it, and with tearful eyes, and a voice full of
love and sorrow, cried, "Follow the voice that calls you. Go, Wohlfart,
go."
CHAPTER XXVII.
On a cold October day, two men were seen driving through the latticed
gate of the town of Rosmin on toward the plain, which stretched out
before them monotonous and boundless. Anton sat wrapped in his fur coat,
his hat low on his forehead, and at his side was young Sturm, in an old
cavalry cloak, with his soldier's cap cocked cheerily on one side. In
front of them a farm-servant, squatted on a heap of straw, flogged on
the small horses. The wind swept the sand and straw from the
stubble-fields, the road was a broad causeway without ditches or hedges,
the horses had to wade alternately through puddles and deep sand. Yellow
sand gleamed through the scanty herbage in all directions wherever a
field-mouse had made her way to her nest or an active mole had done what
he could to diversify the unbroken plain. Wherever the ground sank,
stagnant water lodged, and there hollow willow-trees stretched their
crippled arms in the air, their boughs flapping in the wind, and their
faded leaves fluttering down into the muddy pool below. Here and there
stood a small dwarf pine, a resting-place for the crows, who, scared by
the passing carriage, flew loudly croaking over the travelers' heads.
There was no house to be seen on the road, no pedestrian, and no
conveyance of any kind.
Karl looked every now and then at his silent companion, and said at
last, pointing to the horses, "How rough their coats are, and how pretty
their gray mouse skins! I wonder how many of these beasties would go to
make up my sergeant's horse! When I took leave of my father, the old man
said, 'Perhaps I shall pay you a visit, little one, when they light the
Christmas-tree.' 'You'll never be able,' said I. 'Why not?' asked he.
'You'll never trust yourself in any post-chaise.' Then the old boy
cried, 'Oho! post-chaises are always of a stout build; I shall be sure
to trust myself in one.' But now, Mr. Anton, I see that my father never
can pay us a visit."
"Why not?"
"It is possible that he may reach Rosmin; but, as soon as he sees these
horses and this road, he will instantly turn back. 'Shall I trust
myself,' he'll say, 'in a district where sand runs between one's legs
like water, and where mice are put into harness? The ground is not firm
enough for me.'"
"The horses are not the worst things here," said Anton, absently. "Look!
these go fast enough."
"Yes," replied Karl, "but they don't go like regular horses; they
entangle their legs like two cats playing in a parsley-bed. And what
things they have for shoes--regular webbed hoofs, I declare, which no
blacksmith can ever fit."
"If we could only get on!" returned Anton; "the wind blows cold, and I
am shivering in spite of my fur."
"You have slept but little the last few nights, sir," said Karl. "The
wind blows here as if over a threshing-floor. The earth is not round
hereabouts as elsewhere, but flat as a cake. This is a complete desert;
we have been driving for more than an hour, and there is not a village
to be seen."
"A desert indeed," sighed Anton; "let us hope it may improve." They
relapsed into profound silence. At length the driver stopped near a
pool, unharnessed the horses, and led them to the water's edge, without
noticing the travelers.
"What the deuce does this mean?" cried Karl, jumping down from the
carriage.
"I am going to feed," replied the servant, sulkily, in a foreign accent.
"I am anxious to know how that will be done," said Karl. "There is not
the shadow of a bag of provender."
The horses, however, soon proved that they could live without corn; they
stretched down their shaggy heads, and began to pull the grass and weeds
at the edge of the pool, sometimes taking a draught of the dirty water.
Meanwhile the servant drew a bundle from under his seat, settled himself
under the lee of an alder-bush, and, taking his knife, cut his bread and
cheese without even glancing at the travelers.
"I say, Ignatius or Jacob," cried Karl, sharply, "how long will this
breakfast of yours last?"
"An hour," replied the man, munching away.
"And how far is it from here to the estate?"
"Six miles, or maybe more."
"You can make nothing of him," said Anton; "we must put up with the
customs of the country;" and, leaving the carriage, they went to look on
at the horses feeding.
Anton is on his way to the Polish property. He is now the baron's agent.
Anxious months have the last proved to him. The parting from his
principal and the firm had been painful in the extreme. For some time
before it, indeed, Anton had found himself alone in the midst of his
colleagues. The quiet Baumann still remained his friend, but the others
considered him a castaway. The merchant received his resignation with
icy coldness; and even in the hour of parting, his hand lay impassive as
metal in Anton's grasp. Since then, our hero had undertaken several
journeys to the capital and to creditors in the family's behalf, and now
he was on his way to set the new estate in order, accompanied by Karl,
whom he had induced to become the baron's bailiff.
Ehrenthal had, by the authority conferred on him,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from the time of the sale by auction, and hired the Polish
bailiff for the baron. There had been unfair dealings between them at
the time, and it was well known in Rosmin that the bailiff had sold off
a good deal, and been guilty of all sorts of frauds since, so that Anton
had even now no prospect of a quiet life.
"The hour is come when I may execute my commission," cried Karl, groping
in the straw under the seat. He drew out a large japanned tin case, and
carried it to Anton. "Miss Sabine gave me this in charge for you." He
then joyously opened the lid, produced the materials for an excellent
breakfast, a bottle of wine, and a silver goblet. Anton took hold of the
case.
"It has a very knowing look," said Karl. "Miss Sabine planned it
herself."
Anton examined it on all sides, and placed it carefully on a tuft of
grass; then he took up the goblet, and saw his initials engraved on it,
and underneath the words, "To thy welfare." Whereupon he forgot the
breakfast and all around him, and stood gazing at the goblet, lost in
thought.
"Do not forget the breakfast, sir," suggested Karl, respectfully.
"Sit down by me, my faithful friend; eat and drink with me. Leave off
your absurd politeness. We shall have but little, either of us, but what
we have we will share like brothers. Take the bottle if you have no
glass."
"There's nothing like leather," said Karl, taking a small leathern
drinking-cup out of his pocket. "As for 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t was
kindly meant, and I thank you; but there must be subordination, if it
were but for the sake of the others; and so, sir, be kind enough to let
me shake hands with you now, and then let things be as they were before.
Only look at the horses, Mr. Anton. My faith! the creatures devour
thistles."
Again the horses were harnessed, again they threw out their short legs
in the sand, and again the carriage rolled through the barren
district--first through an empty plain, next through a wretched
fir-wood, then past a row of low sand-hills, then over a tumble-down
bridge crossing a small stream.
"This is the property," said the driver, turning round, and pointing
with his whip to a row of dirty thatched roofs that had just come into
sight.
Anton stood up to look for the group of trees in which the Hall might be
supposed to stand. Nothing of the sort to be seen. The village was
deficient in all that adorns the home of the poorest German peasant--no
orchard, no hedged-in gardens, no lime-trees in the market-place.
"This is wretched," said he, sitting down again; "much worse than they
told us in Rosmin."
"The village looks as if under a curse," cried Karl; "no teams working
in the fields--not a cow or a sheep to be seen."
The farm-servant flogged his horses into an irregular gallop, and so
they passed through the rows of mud huts which constituted the village,
and arrived at the public house. Karl sprang from the carriage, opened
the tavern door, and called for the landlord. A Jew slowly rose from his
seat by the stove and came to the threshold. "Is the gendarme from
Rosmin come?" He is gone into the village. "Which is the way to the
farm-yard?"
The landlord, an elderly man with an intelligent countenance, described
the way in German and Polish, and remained standing at the
door--bewildered, Karl declared, by the sight of two human beings. The
carriage turned into a cross-road, planted on both sides with thick
bushes, the remains of a fallen avenue. Over holes, stones, and puddles,
it rattled on to a group of mud huts, which still had a remnant of
whitewash upon them. "The barns and stables are empty," cried Karl, "for
I see gaps in the roofs large enough to drive our carriage through."
Anton said no more; he was prepared for every thing. They drove through
a break between the stables into the farm-yard, a large irregular space,
surrounded on three sides by tumble-down buildings, and open to the
fields on the fourth. A heap of _débris_ lay there--lime and rotten
timber, the remains of a ruined barn. The yard was empty; no trace of
farm implements or human labor to be seen. "Which is the inspector's
house," inquired Anton, in dismay. The driver looked round, and at last
made up his mind that it was a small one-storied building, with straw
thatch and dirty windows.
At the noise of the wheels a man appeared on the threshold, and waited
phlegmatically till the travelers had dismounted, and were standing
close before him. He was a broad-shouldered fellow, with a bloated,
brandy-drinking face, dressed in a jacket of shaggy cloth, while behind
him peered the muzzle of an equally shaggy dog, who snarled at the
strangers. "Are you the steward of this property?"
"I am," replied the man, in broken German, without stirring from where
he was.
"And I am the agent of the new proprietor," said Anton.
"That does not concern me," growled the shaggy man, turning sharp round,
entering the house, and bolting the door within.
Anton was thoroughly roused. "Break the window in, and help me to catch
the rascal," cried he to Karl, who coolly seized a piece of wood, struck
the panes so as to make the rotten framework give way, and cleared the
opening at one leap. Anton followed him. The room was empty, so was the
next, and in it an open window--the man was gone.
"After him!" cried Karl, and dashed on in pursuit, while Anton looked
about the house and out-buildings. He soon heard the barking of a dog,
and saw Karl capture the fugitive. Hurrying to his help, he held the man
fast, while, with a kick, Karl sent the dog flying. They then contrived
to force the steward back to the house, though he kept striking out
violently all the way.
"Go to the tavern, and bring the gendarme and the landlord," cried Anton
to the driver, who, undisturbed by all that had been going on, had
meanwhile unpacked the carriage. The man accordingly drove leisurely
off, and the fugitive being got into the room, Karl found an old cloth,
and with it bound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I beg your pardon, sir,"
said he; "it is only for an hour or so, till the arrival of the Rosmin
gendarme, whom we have appointed to meet us."
Anton then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house, bu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found but the merest necessaries; no books nor papers of any kind. It
had doubtless been emptied already. A bundle projected from the
coat-pocket of the prisoner, which turned out to be receipts and legal
documents in Polish. In time, the driver returned with the landlord and
the armed policeman. The landlord stood at the door in some perplexity,
and the policeman explained in a few moments what remained to be done.
"You must make a statement to the local judge, and give the man up to
me. He shall go back in your carriage to Rosmin. You will do well to get
rid of him, for this is a wild country, and it will be safer for you to
have him at Rosmin than here, where he has friends and accomplices."
After a long search, a sheet of paper was found in a cupboard, the
statement made and submitted to the policeman, who shook his head a
little over the Polish composition, and the prisoner lifted into the
carriage, the gendarme taking his seat beside him, and saying to Anton,
"I have long expected something of the kind. You may have often occasion
to want me again." The carriage then drove away, and thus the property
came under Anton's administration. He felt as if cast on a desert
island.
His portmanteau and traveling effects were leaning against a mud wall,
and the Polish landlord was the only man who could give him and Karl any
information or advice in their forlorn condition.
Now that the steward was fairly gone, the landlord grew more
communicative, and showed himself serviceable and obliging. A long
conversation ensued, and its purport was what Anton had apprehended from
the warning given by the Commissary Walter and other Rosmin officials.
The inspector had,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done all he could in the
way of spoliation, rendered daring by a report which had found its way
from the town to the village, that the present proprietor would never be
able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estate. At last Anton said, "What that
wretched man has done away with he will have to account for; our first
care must be to preserve what is still to be found on the property. You
must be our guide to-day."
They then examined the empty buildings. Four horses and two
servants--they were gone into the wood--a few old plows, a pair of
harrows, two wagons, a britzska, a cellar full of potatoes, a few
bundles of hay, a little straw--the inventory did not take much time in
drawing up. The buildings were all out of repair, not through age, but
neglect.
"Where is the dwelling-house?" inquired Anton. The landlord led the way
out of the yard to the meadow--a broad plain, gradually sloping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brook. It had been a great pasture. The cattle had
trodden it down into holes; the snouts of greedy swine had rooted it up;
gray molehills and rank tufts of grass rose on all sides.
The landlord stretched out his hand. "There is the castle. This castle
i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he added, reverentially; "no
nobleman in the district has a stone house like that. All the gentry
here live in wood and mud buildings. Herr von Tarow, the richest of
them, has but a poor dwelling."
About three hundred yards from the last out-building rose a great brick
edifice, with a black slate roof and a thick round tower. Its gloomy
walls on this treeless pasture-land, without one trace of life around,
rose beneath the cloudy sky like a phantom fortress which some evil
spirit had evoked from the abyss--a station from which to blight all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The strangers approached it. The castle had fallen into ruins before the
builders had finished their task. The tower had stood there for ages. It
was built of unhewn stone, and had small windows and loop-holes. The
former lords of the land had looked down from its summit on the tops of
the trees, which then stretched far into the plain. They had then ruled
with a rod of iron the serfs who cultivated their land, and toiled and
died for them. Many an arrow had sped through those loop-holes at the
enemy storming below, and many a Tartar horse had been overthrown before
those massive walls. Years ago, a despot of the district had, in
expiation of former sins, begun to add to the gray tower the walls of a
holy monastery; but the monastery never got finished, and the useless
walls had already stood there long, when the late count took it into his
head to convert them into a lordly dwelling for his race, and to raise a
house unparalleled for magnificence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 front of the house was added on to both sides of the tower, which
projected in the middle. The intention had been to have a high
terrace-road up to the castle, and the principal entrance had been made
in the tower, and arched over; but the terrace never having been formed,
the stone threshold of the main door was quite inacce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ladders, and the wide opening was left. The window-spaces of
the lower floor were merely closed up with boards, while on the second
story were some window-frames of beautifully carved wood, in which large
panes had once been placed, but they had got broken. In other windows
were temporary frames of rough deal, with small panes of muddy glass let
into them. A company of jackdaws sat on the top of the tower, looking
down in amazement on the strangers, and every now and then one flew off,
screaming loudly, to contemplate the intruders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A house for crows and bats, not for human beings," said Anton. "At
least, I see no way of getting into it."
The landlord now took them round the building. Behind, where the two
wings made a sort of horse-shoe, there were low entrances to the cellars
and offices; beneath which, again, were stables, great arched kitchens,
and small cells for the serfs. A wooden staircase led to the upper
story. The door turned creaking on its hinges, and a narrow passage took
them through a side wing to the front part of the house. There all was
at least magnificently planned. The circular entrance-hall--an arched
room of the old tower--was painted in mosaic, and through the great
doorway-opening was seen a wide expans
small disturbance made by the return of Anton had gradually settled
down. Those first-class treasures of Sabine's had made way for other
specimens of damask, still of a superior kind, it is true, but which
came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e elderly cousin's comprehension. She had
been quite right in prophesying that Anton would never remark those
signs of exuberant gratitude or their withdrawal. However, one change
had been permanently made--the greatest, the best of all changes--the
clerk retained a privileged place in the heart of the young mistress of
the firm, and his tall figure often appeared as one of the circle that
Sabine's fancy loved to gather round her when at her work-table or in
her treasure-chamber.
To-day she was walking restlessly up and down before dinner. The cousin,
who heard every thing, had just told her that a maid from Ehrenthal's
had run into the office to announce Bernhard's death to his friend. "How
will he bear it?" thought she. And the name of Ehrenthal forced her
thoughts back to the past, to one now far away, and to that painful hour
when the struggle going on in her own mind had been suddenly brought to
a close by a letter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parted. And Anton had known
of that conquered feeling of hers. How considerate he had always been,
how chivalrous, how helpful! She wondered if he had any idea of the
completeness of her triumph over a girlish illusion. She shook her head.
"No, he has not. It was here, at this very table, that an accident first
betrayed me to him. That past time still rises like a cloud between us.
Whenever I sit near Wohlfart of an evening, I am conscious of another's
shadow at my side; and when he speaks to me, his tone, his manner always
seem to say, 'You are not alone; he is with you.'" Sabine started, and
lovingly passed her hand over the beautiful flowers on the table before
her, as if to dispel a painful thought. She could not tell him that she
was free from that long-felt sorrow. Now, however, when he had lost a
friend whom he so much loved, she must show him that there were other
hearts that clung to him still. And again she walked up and down, trying
to devise a way of speaking to him alone.
Dinner was announced. Anton came with the rest, and took his place at
once. There was no opportunity of exchanging a word during the meal, but
he often met her sad and sympathizing eye. "He eats nothing at all
to-day," whispered her cousin; "not even any of the roast," she added,
reproachfully. Sabine was much perturbed. Mr. Jordan had already risen;
Anton would leave the room with the rest, and she should not see him
again the whole day through. So she called out, "The great Calla is
fully blown now. You were admiring the buds the other day; will you
remain a moment; I should like to show it you?" Anton bowed and staid
behind. A few more awkward moments, then her brother rose too; and,
hurrying to Anton, she took him to the room where the flowers were.
"You have had sorrowful tidings to-day," she began.
"The tidings themselves did not surprise me," replied Anton. "The doctor
gave no hope. But I lose much in him."
"I never saw him," said Sabine; "but I know from you that his life was
lonely--poor in affection and in enjoyment."
She moved an arm-chair toward Anton, and led him on to talk about his
friend. She listened to every word with warm sympathy, and well knew
what to ask and how to comfort. It was a relief to Anton to speak of the
departed one, to describe his quiet way of life, his erudition, his
poetical enthusiasm. After a pause, Sabine looked up frankly into his
face, and asked, "Have you any tidings of Herr von Fink?"
It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his departure that she had ever breathed his
name. Anton felt how touching her confidence was, given in this hour of
his sadness. In his emotion, he seized her hand, which she was slow in
withdrawing.
"He is not happy in his new life," he gravely replied. "There was a
savage humor in his last letter, from which I gather, even more than
from his actual words, that the business into which his uncle's death
has thrown him does not suit him."
"It is unworthy," cried Sabine.
"At all events, it is not what would be recognized as honorable in this
house," replied Anton. "Fink is upright, and has lived too long with
your brother to take pleasure in the wild speculations so common on the
other side the Atlantic. His partners and colleagues are for the most
part men without a conscience, and his feelings revolt against their
companionship."
"And can Herr von Fink tolerate such relations as these for a day?"
"It is a remarkable thing that he whose own will was ever so arbitrarily
exercised, should now be obliged against that will to obey a pressure
from without, and every where to work with his hands tied. The
organization of such speculations in America is so complicated that one
shareholder can do little to alter it; and, now that Fink has attained
what used to be the goal of his wishes--a large capital, and the
management of immense districts--his condition appears more uncertain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He was always in danger of thinking slightingly
of others, now I am distressed at the bitter contempt he expresses for
his own life. His last letter paints an intolerable state of things, and
seems to point to some decisive resolve."
"There is only one resolve for him," cried Sabine. "May I ask what you
said to him in reply?"
"I entreated him instantly, come what would, to free himself from the
business in which he was entangled. I said that his own strong will
might find a way of extrication, even if that which I pointed out proved
impracticable. Then I begged of him either to carry out his old plan of
becoming a landed proprietor in America, or to return to us."
"I knew that you would write thus," said Sabine, drawing a long breath.
"Yes, Wohlfart, he shall return," said she, gently, "but he shall not
return to us."
Anton was silent.
"And do you think that Herr von Fink will follow your advice?"
"I do not know. My advice was not very American."
"But it was worthy of you," cried Sabine, with proud delight.
"An officer wishes to speak to Mr. Wohlfart," said a servant at the
door.
Anton sprang up. Sabine went to her flowers and bent mournfully over
them. The shadows of others hovered still between her friend and her.
The few words spoken by the servant filled Anton with a vague terror. He
hurried into the ante-room: there stood Eugene von Rothsattel. Anton was
gladly rushing forward to greet him, but the young soldier's face of
agony made him start back. He whispered, "My mother wishes to speak to
you; something dreadful has occurred." Anton caught up his hat, ran into
the office, hurriedly asked Baumann to excuse him to the principal, and
then accompanied the lieutenant to the baron's house.
On the way, Eugene, who had lost all self-command, said unconnectedly to
Anton, "My father last night accidentally wounded himself by a
pistol-shot--a messenger was sent to summon me--when I came, I found my
mother in a swoon--my sister and I do not know what to do--Lenore
implored my mother on her knees to send for you--you are the only one in
whom w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our distress--I understand nothing about
business, but my father's affairs must be in a dreadful state--my mother
is beside herself--the whole house is in the greatest disorder."
From what Eugene said and what he did not say; from his broken sentences
and his look of agony, Anton guessed at the horrors of the previous
evening. In the boudoir of the baroness he found Lenore, weeping and
exhausted.
"Dear Wohlfart!" cried she, taking his hand and beginning again to sob,
while her head sank powerless on his shoulder.
Meanwhile Eugene walked up and down, wringing his hands, and at length
throwing himself on the sofa, he gave himself up to silent tears.
"It is horrible, Mr. Wohlfart," said Lenore, lifting up her head. "No
one may approach my father--Eugene may not, nor I--only my mother and
old John are with him; and early this morning the merchant Ehrenthal was
here, insisting that he must see my father. He screamed at my mother,
and called my father a deceiver, till she fainted away. When I rushed
into the room, the dreadful man went off threatening her with his
clenched fist."
Anton led Lenore to a chair and waited till she had told him all.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comforting in this case, and his own heart was
wrung to the utmost by the misery he witnessed.
"Call my mother, Eugene," said Lenore, at length.
Her brother left the room.
"Do not forsake us," implored Lenore, clasping her hands; "we are at the
last gasp; even your help can not save us."
"He is dead who might perhaps have done so," mournfully replied Anton.
"Whether I can be of any use I know not, but you can not doubt my
willingness to be so."
"No," cried Lenore. "And Eugene, too, thought of you at once."
The baroness now entered. She walked wearily; but, steadying herself by
a chair, she saluted Anton with dignity. "In our position," said she,
"we need a friend who knows more of business than we three do.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prevents the baron--possibly for a long time to
come--from managing his own affairs, and, little as I understand them, I
can see that our interests require prompt measures. My children have
mentioned you to me, but I fear I am unreasonable in asking you to
devote your time to our service."
She sat down, beckoned Anton to take a chair, and said to her children,
"Leave us; I shall be better able to tell Mr. Wohlfart the little that I
know when I do not see your grief."
When they were alone, she motioned him nearer and tried to speak, but
her lips quivered, and she hid her face in her handkerchief.
"Before I can consent, gracious lady," said he, "to your reposing in me
such confidence as this, I must first inquire whether the baron has no
relative or intimate friend to whom you could with less pain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I pray you to remember that my own knowledge of business
is but small, and my position not one to constitute me a proper
counselor to the baron."
"I know no one," said the baroness, hopelessly. "It is less painful to
me to tell you what I can not conceal, than to one of our own circle.
Consider yourself a physician sent for to visit a patient. The baron has
this morning told me some particulars of his present circumstances." And
then she proceeded to relate what she had gathered as to the nature of
his embarrassments, the danger in which the family property was placed,
and the capital needed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Polish estate.
"My husband," continued she, "has given me the key of his desk, and he
wishes Eugene, with the help of a man of business, to go over his
papers. I now request of you to make this examination together with my
son. When you need explanations, I will try to obtain them from the
baron. The question is now, whether you are inclined to undertake this
trouble for us, who are only strangers."
"I am most willing to do so," earnestly replied Anton; "and I hope that
the kindness of my principal will allow me the time needful for the
purpose, if you do not consider it more advisable to depute the baron's
experienced legal adviser to the task."
"There will be an opportunity of asking that gentleman's advice later,"
said the baroness.
Anton rose. "When do you wish to begin?"
"Immediately. I fear there is not a day to lose. I shall do all I can to
help you look the papers over." She led Anton into the next room, called
in Eugene, and unlocked the baron's desk. As she opened it she lost her
self-command for a moment, and moving to the window, the quivering of
the curtains betrayed the anguish that shook her fragile frame.
The mournful task began. Hour after hour passed. Eugene was in no
condition to peruse any thing, but his mother reached letters and
documents to Anton, and, though often obliged to desist a while, she
bravely returned to the task. Anton placed the papers in order, and
sought, by glancing over each, to arrive at least at a superficial view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It was evening, when the old servant opened the door in dismay, and
called out, "He is there again." The baroness could not repress a slight
scream, and made a gesture of aversion.
"I have told him that no one is at home, but he will not be dismissed;
he makes such a noise on the steps. I can not get rid of him."
"It will kill me if I hear his voice again," murmured the baroness.
"If the man be Ehrenthal," said Anton, rising, "I will try to get him
away. We have now done what was most necessary; have the goodness to
lock up these papers, and to allow me to return to-morrow." The baroness
silently assented, and sank back in her chair. Anton hurried off to the
ante-room, whence he could hear Ehrenthal's loudly-raised voi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usurer shocked him. His hat pushed half off his
head, his pale face swelled as if by drinking, his glazed eyes red with
tears, Ehrenthal stood before him, calling in broken sentences for the
baron, wailing and cursing alternately. "He must come! he must come at
once!" cried he; "the wicked man! A nobleman, indeed! he is a vagabond,
after whom I will send the police. Where is my money? Where is my
security? I want my mortgage from this man who is not at home."
Anton went straight up to him, and asked, "Do you know me, Mr.
Ehrenthal?" Ehrenthal turned his glazed eyes upon him, and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 friend of his dead son.
"He loved you!" he cried, in a lamentable voice. "He spoke to you more
than to his father. You were the only friend that he had on earth. Have
you heard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house of Ehrenthal?" continued he, in
a whisper. "Just as they stole the papers he died. He died with a hand
like this," and clenching his fist he struck his forehead. "Oh my son!
my son! why didst not thou forgive thy father!"
"We will go to your son," said Anton, taking the arm of the old man, who
unresistingly allowed himself to be led back to his own house.
From thence Anton hurried to Councilor Horn, with whom he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It was late before he returned home. In the midst of his anxiety about
those whose prosperity had filled his imagination years before,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in their adversity, reposed in him, dilated his
breast with a feeling of pride. He burned with desire to help them, and
hoped that his zealous devotion might yet find some way of rescue. As
yet he saw none. Looking up at the great building before him, so firm
and secure, in the moonlight, a thought flashed into his mind. If any
man could help them, it was his principal. His keen eye would be able to
unravel all the dark secrets in which the baron was entangled, and his
iron strength of will would crush the villains who held the unfortunate
nobleman in their power. And then he had a noble nature; he always
decided on the right, without an effort or a struggle. Anton looked at
the first floor. The whole house-front was dark, but in a corner room a
light still burned. It was the private office of his chief.
With sudden resolve, Anton begged the servant to take him to Mr.
Schröter, who looked with amazement at the unexpected visitor, and asked
what brought him, and whether any thing had happened.
"I implore your counsel--I implore your help," cried Anton.
"For yourself or for others?" inquired the merchant.
"For a family with whom I have accidentally become connected. They are
lost if a strong hand does not ward off the impending catastrophe."
Anton then rapidly related the occurrences of the afternoon, and,
seizing his principal's hand in his emotion, cried, "Have pity upon the
unhappy ladies, and help them."
"Help them!" replied the merchant; "how can I? Have you been
commissioned to apply to me, or are you only following the impulse of
your own feelings?"
"I am not commissioned; it is only the interest that I take in the
baron's fate which leads me to you."
"And what right have you to inform me of facts communicated in strict
confidence to yourself by the baron's lady?" asked the merchant, dryly.
"I am committing no indiscretion in telling you what will, in a few
days, be no secret, even to strangers."
"You are unusually excited, otherwise you would not forget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hatever, does a man of business venture to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without the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Of course, I shall make no wrong use of what you have said, but it was
by no means business-like, Wohlfart, to be so open toward me."
Anton was silent, feeling, indeed, that his principal was right, but yet
it seemed hard to be blamed for reposing confidence at such a time as
this. The merchant walked silently up and down; at length, stopping
before Anton, he said, "I do not now inquire how you come to take so
warm an interest in this family. I fear it is an acquaintance you owe to
Fink."
"You shall hear all," said Anton.
"Not at present. I will now content myself with repeating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interfere in these affairs without being specially
applied to by the parties themselves. I may add that I by no means wish
for such an application, and do not disguise from you that, were it
made, I should probably decline to do any thing for the Baron
Rothsattel."
Anton's feelings were roused to the utmost. "The question is the rescue
of an honorable man, and of lovely and amiable women from the toils of
rogues and impostors. To me, this seems the duty of every one; I, at
least, consider it a sacred obligation which I dare not shrink from. But
without your support I can do nothing."
"And how do you think this embarrassed man can be helped?" inquired the
merchant, seating himself.
With somewhat more composure, Anton repli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an experienced man of business making himself master of the case. There
must be some way of circumventing these villains. Your penetration would
discover it."
"Any attorney would be far more likely to do so, and the baron might
readily engage the services of experienced and upright legal advisers.
If his enemies have done any thing illegal, the quick eye of a lawyer is
the most likely to detect it."
"Alas! the baron's own lawyer gives but little hope," replied Anton.
"Then, my dear Wohlfart, no other is likely to do much good. Show me an
embarrassed man who has strength to grasp an offered hand, and bid me
help him, and for the sake of all I owe you, I will not refuse to do so.
I think you are convinced of this."
"I am," said Anton, dejectedly.
"From all I hear, however," the merchant went on,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the baron. From what I gather from general report, as well as from
you, his embarrassments arise from his having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usurers, which proves him deficient in what alone ennobles the life of
any man--good sense, and the power of steady exertion."
Anton could only sigh his assent.
"To help such a man," inexorably continued the merchant, "is a futile
attempt, against which reason may well protest. We are not to despair of
any, but want of strength is the most hopeless case of all. Our power of
laboring for others being limited, it becomes our duty to inquire,
before we devote our time to the weak, whether we are not thus
diminishing our chances of helping better men."
Anton interrupted him. "Does he not deserve every allowance to be made
for him? He was brought up to exact much; he has not learned, as we
have, to make his way by his own labor."
The merchant laid his hand on the young man's shoulder. "The very
reason. Believe me, a large number of these landed gentry, who pay the
penalty of their old family memories, are beyond help. I am the last to
deny that many worthy and admirable men belong to this class. Indeed,
wherever remarkable talent or nobility of character shoots up among
them, no doubt their position offers peculiar scope for its development,
but for average men it is not a favorable one. He who considers it his
hereditary privilege to enjoy life, and who assumes a distinguished
position in virtue of his family, will very often fail to put forth his
whole strength in order to deserve that position. Accordingly, numbers
of our oldest families are declining, and their fall will be no loss to
the state. Their family associations make them haughty without any
right to be so--limit their perceptions and confuse their judgment."
"Even if all this be true," cried Anton, "it does not absolve us from
helping individuals of the class who have excited our sympathy."
"No," said the principal, "if it be excited. But it does not glow so
rapidly in advancing years as in youth. The baron has endeavored to
isolate his property from the current of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leave it forever to his family. Forever! You, as a merchant, know how to
estimate the attempt. True, every rational man must allow it to be
desirable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same soil should be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We all prize what our forefathers have possessed before
us, and Sabine would unlock every room in this house with pride, because
her great-great-grandmother turned the same keys before her. It is
therefore natural that the landed proprietor should desire to preserve
those familiar scenes, which are the source of his own prosperity, to
those nearest and dearest to him. But there must be means to this end,
and these means are the making his own existence available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increase of his patrimony. Where energy dies in families
or individuals, then it is well that their means die too, that their
money should circulate through other hands, and their plowshare pass to
those who can guide it better. A family that has become effete through
luxury ought to sink down into common life, to make room for the
uprising of fresh energies and faculties. Every one who seeks, at the
cost of free activity for others, to preserve permanent possessions and
privileges for himself or his family, I must look upon as an enemy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social state. And if such a man ruin
himself in his endeavors, I should feel no malicious pleasure in his
downfall, but I should say that he is rightly served, because he has
sinned against a fundamental law of our social being; consequently, I
should consider it doubly wrong to support this man, because I could but
fear that I should thus be supporting an unsound condition of the body
politic."
Anton looked down mournfully. He had expected sympathy and warm
concurrence, and he met with disaffection and coldness that he despaired
of conquering. "I can not gainsay you," he at length replied; "but in
this case I can not feel as you do. I have been witness to the
unspeakable distress in the baron's family, and my whole soul is full
of sadness and sympathy, and of the wish to do something for those who
have opened their heart to me. After what you have said, I dare no
longer ask you to trouble yourself with their affairs, but I have
promised the baroness to assist her as far as my small powers permit,
and your kindness allows. I implore you to grant me permission to do
this. I shall endeavor to be regular in my attendance at the office, but
if during the next few weeks I am occasionally absent, I must ask you to
excuse me."
Once more the merchant walked up and down the room, and then, looking at
Anton's excited face, with deep seriousness and something of regret, he
replied, "Remember, Wohlfart, that every occupation which excites the
mind soon obtains a hold over a man, which may retard as well as advance
his success in life. It is thi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 to agree
to your wishes."
"I know it," said Anton, in a low voice; "but I have now no choice
left."
"Well, then, do what you must," said the merchant, gloomily; "I will lay
no hinderance in your way; and I hope that after a few weeks you will be
able to consider the whole circumstances more calmly." Anton left the
room, and the merchant stood looking long with frowning brow at the
place his clerk had occupied.
Nor was Anton in a more congenial mood. "So cold, so inexorable!"
exclaimed he, as he reached his own room. He began to suspect that his
principal was more selfish and less kindly than he had hitherto
supposed. Many an expression of Fink's recurred to his mind, as well as
that evening when young Rothsattel, in his boyish conceit, had spoken
impertinently to the merchant. "Is it possible," thought he, "that that
rude speech should be unforgotten?" And his chief's keen, deep-furrowed
face lost inexpressibly by contrast with the fair forms of the noble
ladies. "I am not wrong," he cried to himself; "let him say what he
will, my views are more just than his, and henceforth my destiny shall
be to choose for myself the way in which I shall walk." He sat long in
the darkness, and his thoughts were gloomy as it; then he went to the
window to look down into the dark court below. A great white blossom
rose before him like a phantom. Striking a light, he saw that it was the
beautiful Calla out of Sabine's room. It hung down mournfully on its
broken stem. Sabine had had it placed there. This little circumstance
struck him as a mournful omen.
Meanwhile Sabine, taper in hand, entered her brother's room.
"Good-night, Traugott," nodded she. "Wohlfart has been with you this
evening; how long he staid!"
"He will leave us," replied the merchant, gloomily.
Sabine started and dropped her taper on the table. "For God's sake, what
has happened? Has Wohlfart said that he was going away?"
"I do not yet know it, but I see it coming step by step; and I can not,
and still less can you, do any thing to retain him. When he stood before
me here with glowing cheeks and trembling voice, pleading for a ruined
man, I found out what it was that lured him away."
"I do not understand you," said Sabine, looking full at her brother.
"He chooses to become the confidential friend of a decayed noble. A pair
of bright eyes draws him away from us: it seems to him a worthy object
of ambition to become Rothsattel's man of business. This intimacy with
nobility is the legacy bequeathed to him by Fink."
"And you have refused to help him?" inquired Sabine, in a low voice.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said the merchant, harshly; and he
turned to his writing-table.
Sabine slowly withdrew. The taper trembled in her hand as she passed
through the long suite of rooms listening to her own footfall, and
shuddering as the feeling came over her that an invisible companion
glided by her side. This was the revenge of that other. The shadow that
once fell on her innocent life now drove her friend away from their
circle. Anton's affections clung to another. She had but been in his
eyes a mere stranger, who had once loved and languished for one now far
away, and who now, in widow's weeds, looked back regretfully to the
feelings of her youth.
The few next weeks were spent by Anton in over-hard work. He had great
difficulty in keeping up his counting-house duties, while he spent every
spare hour in conference with the baroness and the lawyer.
In the mean time, the misfortunes of the baron ran their course. He had
not been able to pay the interest of the sums with which his estate was
burdened. When last they were due, a whole series of claims was brought
against him, and the estate fell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district authorities. Complicated lawsuits arose. Ehrenthal complained
loudly, claiming the first mortgage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nay, he
was inclined to advance claims on the last mortgage offered by the baron
in the recent fatal hour. Löbel Pinkus also appeared as claimant of the
first mortgage, and asserted that he had paid the whole sum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Ehrenthal had no proof to bring forward, and had been
for some weeks past quite unable to manage his own affairs, while
Pinkus, on the contrary, fought with every weapon a hardened sinner can
devise or employ, and the deeds which the baron had executed at Veitel's
suggestion proved to be so capital a master-stroke of the cunning
advocate, that the baron's man of business had, from the first, little
hope of the case. We may here observe that Pinkus did eventually win it,
and that the mortgage was made over to him.
Anton was now gradually gaining some insight into the baron's
circumstances. But the double sale of the first mortgage was still kept
a secret by the latter, even from his wife. He declared Ehrenthal's
claim unfounded, and even expressed a suspicion that he had himself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robbery in his office. Indeed, he really
believed this. Then the name of Itzig was never broached, and the
suspicion against Ehrenthal, which the baron's lawyer shared, prevented
Anton seeking any explanation from him.
Meanwhile, an estrangement had sprung up between our hero and his
principal, which the whole counting-house remarked with surprise. The
merchant scowled at Anton's vacant seat when the latter chanced to be
absent during office-hours, or looked coldly at his clerk's face, made
pale as it was with excitement of mind and night-work. He took no notice
of his new occupation, and never seemed to remark him. Even to his
sister he maintained a stiff-necked silence; nor could all her attempts
lead him to speak of Anton, who, on his side, felt his heart revolt
against this coldness. After his return, to be treated like a child of
the house, praised, promoted, petted, and now to be treated like a mere
hireling, who is not worth the bread thrown to him; to be a toy of an
incomprehensible caprice--this, at least, he had not deserved; so he
became reserved toward the whole family, and sat silent at his desk; but
he fel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now and the then so keenly, that often,
when alone, he would spring up and stamp on the ground in the bitter
indignation of his heart.
One comfort remained. Sabine was not estranged. True, he saw little of
her, and at dinner she seemed to avoid speaking to him, but he knew that
she was on his side.
A few days after his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the merchant, she came down
stairs as he stood in the hall, and had to pass him by so closely that
her dress touched him. He had retreated, and made a formal bow, but she
looked at him imploringly, and whispered, "You must not be estranged
from me." It was an affair of a moment, but the faces of both were
radiant with a happy understanding.
The time had now arrived when Mr. Jordan was to quit the firm. The
principal again called Anton into his little office, and without any
severity, but also without a trace of his former cordiality, began: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o you my intention of appointing you Jordan's
successor; but,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your time has been more taken
up with other business than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such a post, I
therefore ask you whether you are now at liberty to undertake Jordan's
duties?"
"I am not," replied Anton.
"Can you name any--not very distant--time when you will be free from
your present occupation? In that case I will endeavor to find a
substitute until then."
Anton sorrowfully replied, "I can not at present say when I shall again
be master of my whole time; and, besides, I feel that, even as it is, I
tax your indulgence by many irregularities. Therefore, Mr. Schröter, I
beg that you will fill up this post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me."
The merchant's brow grew furrowed and dark, and he silently bowed
assent. Anton felt as he closed the door that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m was now complete, and, resuming his place, he leaned his throbbing
head on his hand. A moment later Baumann was summoned to the principal,
and Jordan's situation conferred upon him. On returning to the office,
he went up to Anton and whispered, "I refused at first, but Mr. Schröter
insisted. I am doing you an injustice." And that evening Mr. Baumann, in
his own room, read in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the chapters treating of
the unjust Saul (the principal), and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Jonathan
and the persecuted David, and strengthened his heart thereby.
The next day Anton was summoned to the baroness. Lenore and her mother
sat before a large table covered with jewel-boxes and toilette elegances
of every description, while a heavy iron chest stood at their feet. The
curtains were drawn, and the subdued light shone softly into the richly
furnished room. On the carpet glowed wreaths of unfading flowers, and
the clock ticked cheerfully in its alabaster case. Under the shade of
flowering plants sat the two love-birds in their silvered cage, hopping
from perch to perch, screaming ceaselessly, or sitting up quietly close
to each other. The whole room was beauty and perfume. "For how long?"
thought Anton. The baroness rose. "We are already obliged to trouble you
again," said she; "we are engaged in a very painful occupation." On the
table were all manner of ornaments, gold chains, brilliants, rings,
necklaces, gathered into a heap.
"We have been looking out all that we can dispense with," said the
baroness, "and now pray you to undertake to sell these things for us. I
have been told that some of them are of value, and as we are now in much
need of money, we turn here for help."
Anton looked in perplexity at the glittering heap.
"Tell us, Wohlfart," cried Lenore, anxiously, "is this necessary? can it
be of any use? Mamma has insisted upon setting apart for sale all our
ornaments, and whatever plate is not in daily use. What I can give is
not worth talking of, but my mother's jewels are costly; many of them
were presents made to her in youth, which she shall not part with unless
you say that it is necessary."
"I fear," said Anton, gravely, "that it will prove so."
"Take them," said the baroness to Anton; "I shall be calmer when I know
that we have at least done what we could."
"But do you wish to part with all?" inquired Anton, anxiously. "Much
that is dear to you may have but little value in a jeweler's eyes."
"I shall never wear an ornament again," quietly replied the baroness.
"Take them all;" and, holding her hands before her eyes, she turned
away.
"We are torturing my mother," cried Lenore, hastily; "will you lock up
all that is on the table, and get them out of the house as soon as you
can?"
"I can not undertake the charge of these valuables," said Anton,
"without taking some measures to decrease my own responsibility. First
of all, I will in your presence make a short note of all you intrust to
me."
"What useless cruelty!" exclaimed Lenore.
"It will not take long."
Anton took out a few sheets from his pocket-book, and began to note down
the different articles.
"You shall not see it done, mother," said Lenore, drawing her mother
away, and then returning to watch Anton at his task.
"These preparations for the market are horrible," said she. "My mother's
whole life will be sold; some memory of hers is linked with every single
thing. Look, Wohlfart, the princess gave her this diamond ornament when
she married my father."
"They are magnificent brilliants," cried Anton, admiringly.
"This ring was my grandfather's, and these are presents of poor papa's.
Alas! no man can know how we love all these things. It was always a
festival to me when mamma put on her diamonds. Now we come to my
possessions. They are not worth much. Do you think this bracelet good
gold?" She held out her hand as she spoke.
"I do not know."
"It shall go with the rest," said Lenore, taking it off. "Yes, you are a
kind, good man, Wohlfart," continued she, looking trustfully into his
tearful eyes; "do not forsake us. My brother has no experience, and is
more helpless than we are. It is a frightful position for me. Before
mamma I do all I can to be composed, else I could scream and weep the
whole day through." She sank in a chair, still holding his hand. "Dear
Wohlfart, do not forsake us."
Anton bent over her, and looked with passionate emotion at the lovely
face that turned so trustfully to him in the midst of its tears.
"I will be helpful to you when I can," said he, in the fullness of his
heart. "I will be at hand whenever you need me. You have too good an
opinion of my information and my faculties; I can be of less assistance
to you than you suppose, but what I can, that I will do in any and every
possible way."
Their hands parted with a warm pressure; the affair was settled.
The baroness now returned. "Our lawyer was with me this morning," said
she; "and now I must ask for your opinion on another subject. He tells
me that there is no prospect of preserving the baron's family estate."
"At this time, when interest is high, and money difficult to get, none,"
replied Anton.
"And you, too, think that we must turn all our efforts toward preserving
the Polish property?"
"I do," was the answer.
"For that, also, money will be necessary. Perhaps I may be able through
my relatives to intrust you with a small sum, which, with the help of
that"--she pointed to the iron chest--"may suffice to cover the first
necessary expenses. I do not, however, wish to sell the jewels here, and
a journey to the residence would be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cure the
sum to which I have just alluded. The baron's lawyer has spoken most
highly of your capacity for business. It is his wish which now decides
me to make a proposal to you. Will you for the next few years, or, at
all events, until our greatest difficulties are over, devote your whole
time to our affairs? I have consulted my children, and they agree with
me in believing that in your assistance lies our only hope of rescue.
The baron, too, has come in to the plan. The question now is whether
your circumstances allow you to give your support to our unfortunate
family. We shall be grateful to you, whatever conditions you affix; and
if you can find any way of making our great obligations to you apparent
in the position you hold, pray impart it to me."
Anton stood petrified. What the baroness required of him was separation
from the firm, separation from his principal, and from Sabine! Had this
thought occurred to him before, when standing in Lenore's presence or
bending over the baron's papers? At all events, now that the words were
spoken, they shocked him. He looked at Lenore, who stood behind her
mother with hands clasped in supplication. At length he replied, "I
stand in a position which I can not leav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others.
I was not prepared for this proposal, and beg to have time allowed me
for consideration. It is a step which will decide my whole future life."
"I do not press you," said the baroness; "I only request your
consideration. Whatever your decision be, our warmest gratitude will
still be yours; if you are unable to uphold our feeble strength, I fear
that we shall find no one to do so. You will think of that," she added,
beseechingly.
Anton hurried through the street with throbbing pulse. The noble lady's
glance of entreaty, Lenore's folded hands, beckoned him out of the
gloomy counting-house into a sphere of greater liberty, into a new
future, from whose depths bright images flashed out upon his fancy. A
request had been frankly made, and he was strongly inclined to justify
the confidence that prompted it. Those ladies required an unwearied,
self-sacrificing helper to save them from utter ruin, and if he
followed his impulse he should be doing a good work--fulfilling a duty.
In this mood he entered the merchant's dwelling. Alas! all that he saw
around him seemed to stretch out a hand to detain him. As he looked at
the warehouse, the good-humored faces of the porters, the chains of the
great scales, the hieroglyphics of the worthy Pix, again he felt that
this was the place that he belonged to. Sabine's dog kissed his hand,
and ran before him to his room--his and Fink's room. Here the childish
heart of the orphan boy had found a friend, kind companions, a home, a
definite and honorable life-purpose. Looking down through his window on
all the long-familiar objects, he saw a light in Sabine's store-chamber.
How often he had sought for that light, which brightened the whole great
building, and brought a sense of comfort and cheerfulness even into his
room. He now sprang up suddenly, and said to himself, "She shall
decide."
Sabine started in amazement when Anton appeared before her. "I am
irresistibly impelled to seek you," cried he. "I have to decide upon my
future life, and I feel undetermined, and unable to trust to my own
judgment. You have always been a kind friend to me since the day of my
arrival. I am accustomed to look up to you, and to think of you in
connection with all that interests me here. Let me hear your opinion
from your own lips. The Baroness Rothsattel has to-day proposed to me
permanently to undertake the situation of confidential adviser and
manager of the baron's affairs. Shall I accept; or shall I remain here?
I know not--tell me what is right both for myself and others."
"Not I," said Sabine, drawing back and growing very pale. "I can not
venture to decide in the matter. Nor do you wish me to do so, Wohlfart,
for you have already decided."
Anton looked straight before him and was silent.
"You have thought of leaving this house, and a wish to do so has sprung
out of the thought. And I am to justify you, and approve your resolve!
This is what you require of me," continued she, bitterly. "But this,
Wohlfart, I can not do, for I am sorry that you go away from us."
She turned away from him and leaned on the back of a chair.
"Oh, be not angry with me too!" said Anton; "that I can not bear. I have
suffered much of late. Mr. Schröter has suddenly withdrawn from me the
friendly regard that I long held my life's greatest treasure. I have not
deserved his coldness. What I have been doing has not been wrong, and
it was done with his knowledge. I had been spoiled by his kindness; I
have the more deeply felt his displeasure. My only comfort has been that
you did not condemn me. And now, do not you be cold toward me, else I
shall be wretched forever. There is not a soul on earth to whom I can
turn for affectionate comprehension of my difficulties. Had I a sister,
I should seek her heart to-day. You do not know what to me, lonely as I
am, your smile, your kindly shake of the hand has been till now. Do not
turn coldly from me, I beseech you."
Sabine was silent. At length she inquired, still with averted face,
"What draws you to those strangers; is it a joyful hope, is it sympathy
alone? Give this question close consideration before you answer it to
yourself at least."
"What it is that makes it possible for me to leave this house," said
Anton, "I do not myself know. If I can give a name to my motives, it is
gratitude felt toward one. She was the first to speak kindly to the
wandering boy on his way out into the world. I have admired her in the
peaceful brightness of her former life. I have often dreamed childish
dreams about her. There was a time when a tender feeling for her filled
my whole heart, and I then believed myself forever the slave of her
image. But years bring changes, and I learned to look on men and on life
with other eyes. Then I met her again, distressed, unhappy, despairing,
and my compassion became overmastering. When I am away from her, I know
that she is nothing to me; when I am with her, I feel only the spell of
her sorrow. Once, when I had to depart out of her circle like a culprit,
she came to me, and before the whole scornful assembly she gave me her
hand and acknowledged me her friend; and now she comes and asks for my
hand to help her father. Can I refuse it? Is it wrong to feel as I do? I
know not, and no one can tell me--no one but you alone."
Sabine's head had sunk down to the back of the chair on which she bent.
She now suddenly raised it, and with tearful eyes, and a voice full of
love and sorrow, cried, "Follow the voice that calls you. Go, Wohlfart,
go."
CHAPTER XXVII.
On a cold October day, two men were seen driving through the latticed
gate of the town of Rosmin on toward the plain, which stretched out
before them monotonous and boundless. Anton sat wrapped in his fur coat,
his hat low on his forehead, and at his side was young Sturm, in an old
cavalry cloak, with his soldier's cap cocked cheerily on one side. In
front of them a farm-servant, squatted on a heap of straw, flogged on
the small horses. The wind swept the sand and straw from the
stubble-fields, the road was a broad causeway without ditches or hedges,
the horses had to wade alternately through puddles and deep sand. Yellow
sand gleamed through the scanty herbage in all directions wherever a
field-mouse had made her way to her nest or an active mole had done what
he could to diversify the unbroken plain. Wherever the ground sank,
stagnant water lodged, and there hollow willow-trees stretched their
crippled arms in the air, their boughs flapping in the wind, and their
faded leaves fluttering down into the muddy pool below. Here and there
stood a small dwarf pine, a resting-place for the crows, who, scared by
the passing carriage, flew loudly croaking over the travelers' heads.
There was no house to be seen on the road, no pedestrian, and no
conveyance of any kind.
Karl looked every now and then at his silent companion, and said at
last, pointing to the horses, "How rough their coats are, and how pretty
their gray mouse skins! I wonder how many of these beasties would go to
make up my sergeant's horse! When I took leave of my father, the old man
said, 'Perhaps I shall pay you a visit, little one, when they light the
Christmas-tree.' 'You'll never be able,' said I. 'Why not?' asked he.
'You'll never trust yourself in any post-chaise.' Then the old boy
cried, 'Oho! post-chaises are always of a stout build; I shall be sure
to trust myself in one.' But now, Mr. Anton, I see that my father never
can pay us a visit."
"Why not?"
"It is possible that he may reach Rosmin; but, as soon as he sees these
horses and this road, he will instantly turn back. 'Shall I trust
myself,' he'll say, 'in a district where sand runs between one's legs
like water, and where mice are put into harness? The ground is not firm
enough for me.'"
"The horses are not the worst things here," said Anton, absently. "Look!
these go fast enough."
"Yes," replied Karl, "but they don't go like regular horses; they
entangle their legs like two cats playing in a parsley-bed. And what
things they have for shoes--regular webbed hoofs, I declare, which no
blacksmith can ever fit."
"If we could only get on!" returned Anton; "the wind blows cold, and I
am shivering in spite of my fur."
"You have slept but little the last few nights, sir," said Karl. "The
wind blows here as if over a threshing-floor. The earth is not round
hereabouts as elsewhere, but flat as a cake. This is a complete desert;
we have been driving for more than an hour, and there is not a village
to be seen."
"A desert indeed," sighed Anton; "let us hope it may improve." They
relapsed into profound silence. At length the driver stopped near a
pool, unharnessed the horses, and led them to the water's edge, without
noticing the travelers.
"What the deuce does this mean?" cried Karl, jumping down from the
carriage.
"I am going to feed," replied the servant, sulkily, in a foreign accent.
"I am anxious to know how that will be done," said Karl. "There is not
the shadow of a bag of provender."
The horses, however, soon proved that they could live without corn; they
stretched down their shaggy heads, and began to pull the grass and weeds
at the edge of the pool, sometimes taking a draught of the dirty water.
Meanwhile the servant drew a bundle from under his seat, settled himself
under the lee of an alder-bush, and, taking his knife, cut his bread and
cheese without even glancing at the travelers.
"I say, Ignatius or Jacob," cried Karl, sharply, "how long will this
breakfast of yours last?"
"An hour," replied the man, munching away.
"And how far is it from here to the estate?"
"Six miles, or maybe more."
"You can make nothing of him," said Anton; "we must put up with the
customs of the country;" and, leaving the carriage, they went to look on
at the horses feeding.
Anton is on his way to the Polish property. He is now the baron's agent.
Anxious months have the last proved to him. The parting from his
principal and the firm had been painful in the extreme. For some time
before it, indeed, Anton had found himself alone in the midst of his
colleagues. The quiet Baumann still remained his friend, but the others
considered him a castaway. The merchant received his resignation with
icy coldness; and even in the hour of parting, his hand lay impassive as
metal in Anton's grasp. Since then, our hero had undertaken several
journeys to the capital and to creditors in the family's behalf, and now
he was on his way to set the new estate in order, accompanied by Karl,
whom he had induced to become the baron's bailiff.
Ehrenthal had, by the authority conferred on him,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from the time of the sale by auction, and hired the Polish
bailiff for the baron. There had been unfair dealings between them at
the time, and it was well known in Rosmin that the bailiff had sold off
a good deal, and been guilty of all sorts of frauds since, so that Anton
had even now no prospect of a quiet life.
"The hour is come when I may execute my commission," cried Karl, groping
in the straw under the seat. He drew out a large japanned tin case, and
carried it to Anton. "Miss Sabine gave me this in charge for you." He
then joyously opened the lid, produced the materials for an excellent
breakfast, a bottle of wine, and a silver goblet. Anton took hold of the
case.
"It has a very knowing look," said Karl. "Miss Sabine planned it
herself."
Anton examined it on all sides, and placed it carefully on a tuft of
grass; then he took up the goblet, and saw his initials engraved on it,
and underneath the words, "To thy welfare." Whereupon he forgot the
breakfast and all around him, and stood gazing at the goblet, lost in
thought.
"Do not forget the breakfast, sir," suggested Karl, respectfully.
"Sit down by me, my faithful friend; eat and drink with me. Leave off
your absurd politeness. We shall have but little, either of us, but what
we have we will share like brothers. Take the bottle if you have no
glass."
"There's nothing like leather," said Karl, taking a small leathern
drinking-cup out of his pocket. "As for 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t was
kindly meant, and I thank you; but there must be subordination, if it
were but for the sake of the others; and so, sir, be kind enough to let
me shake hands with you now, and then let things be as they were before.
Only look at the horses, Mr. Anton. My faith! the creatures devour
thistles."
Again the horses were harnessed, again they threw out their short legs
in the sand, and again the carriage rolled through the barren
district--first through an empty plain, next through a wretched
fir-wood, then past a row of low sand-hills, then over a tumble-down
bridge crossing a small stream.
"This is the property," said the driver, turning round, and pointing
with his whip to a row of dirty thatched roofs that had just come into
sight.
Anton stood up to look for the group of trees in which the Hall might be
supposed to stand. Nothing of the sort to be seen. The village was
deficient in all that adorns the home of the poorest German peasant--no
orchard, no hedged-in gardens, no lime-trees in the market-place.
"This is wretched," said he, sitting down again; "much worse than they
told us in Rosmin."
"The village looks as if under a curse," cried Karl; "no teams working
in the fields--not a cow or a sheep to be seen."
The farm-servant flogged his horses into an irregular gallop, and so
they passed through the rows of mud huts which constituted the village,
and arrived at the public house. Karl sprang from the carriage, opened
the tavern door, and called for the landlord. A Jew slowly rose from his
seat by the stove and came to the threshold. "Is the gendarme from
Rosmin come?" He is gone into the village. "Which is the way to the
farm-yard?"
The landlord, an elderly man with an intelligent countenance, described
the way in German and Polish, and remained standing at the
door--bewildered, Karl declared, by the sight of two human beings. The
carriage turned into a cross-road, planted on both sides with thick
bushes, the remains of a fallen avenue. Over holes, stones, and puddles,
it rattled on to a group of mud huts, which still had a remnant of
whitewash upon them. "The barns and stables are empty," cried Karl, "for
I see gaps in the roofs large enough to drive our carriage through."
Anton said no more; he was prepared for every thing. They drove through
a break between the stables into the farm-yard, a large irregular space,
surrounded on three sides by tumble-down buildings, and open to the
fields on the fourth. A heap of _débris_ lay there--lime and rotten
timber, the remains of a ruined barn. The yard was empty; no trace of
farm implements or human labor to be seen. "Which is the inspector's
house," inquired Anton, in dismay. The driver looked round, and at last
made up his mind that it was a small one-storied building, with straw
thatch and dirty windows.
At the noise of the wheels a man appeared on the threshold, and waited
phlegmatically till the travelers had dismounted, and were standing
close before him. He was a broad-shouldered fellow, with a bloated,
brandy-drinking face, dressed in a jacket of shaggy cloth, while behind
him peered the muzzle of an equally shaggy dog, who snarled at the
strangers. "Are you the steward of this property?"
"I am," replied the man, in broken German, without stirring from where
he was.
"And I am the agent of the new proprietor," said Anton.
"That does not concern me," growled the shaggy man, turning sharp round,
entering the house, and bolting the door within.
Anton was thoroughly roused. "Break the window in, and help me to catch
the rascal," cried he to Karl, who coolly seized a piece of wood, struck
the panes so as to make the rotten framework give way, and cleared the
opening at one leap. Anton followed him. The room was empty, so was the
next, and in it an open window--the man was gone.
"After him!" cried Karl, and dashed on in pursuit, while Anton looked
about the house and out-buildings. He soon heard the barking of a dog,
and saw Karl capture the fugitive. Hurrying to his help, he held the man
fast, while, with a kick, Karl sent the dog flying. They then contrived
to force the steward back to the house, though he kept striking out
violently all the way.
"Go to the tavern, and bring the gendarme and the landlord," cried Anton
to the driver, who, undisturbed by all that had been going on, had
meanwhile unpacked the carriage. The man accordingly drove leisurely
off, and the fugitive being got into the room, Karl found an old cloth,
and with it bound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I beg your pardon, sir,"
said he; "it is only for an hour or so, till the arrival of the Rosmin
gendarme, whom we have appointed to meet us."
Anton then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house, bu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found but the merest necessaries; no books nor papers of any kind. It
had doubtless been emptied already. A bundle projected from the
coat-pocket of the prisoner, which turned out to be receipts and legal
documents in Polish. In time, the driver returned with the landlord and
the armed policeman. The landlord stood at the door in some perplexity,
and the policeman explained in a few moments what remained to be done.
"You must make a statement to the local judge, and give the man up to
me. He shall go back in your carriage to Rosmin. You will do well to get
rid of him, for this is a wild country, and it will be safer for you to
have him at Rosmin than here, where he has friends and accomplices."
After a long search, a sheet of paper was found in a cupboard, the
statement made and submitted to the policeman, who shook his head a
little over the Polish composition, and the prisoner lifted into the
carriage, the gendarme taking his seat beside him, and saying to Anton,
"I have long expected something of the kind. You may have often occasion
to want me again." The carriage then drove away, and thus the property
came under Anton's administration. He felt as if cast on a desert
island.
His portmanteau and traveling effects were leaning against a mud wall,
and the Polish landlord was the only man who could give him and Karl any
information or advice in their forlorn condition.
Now that the steward was fairly gone, the landlord grew more
communicative, and showed himself serviceable and obliging. A long
conversation ensued, and its purport was what Anton had apprehended from
the warning given by the Commissary Walter and other Rosmin officials.
The inspector had,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done all he could in the
way of spoliation, rendered daring by a report which had found its way
from the town to the village, that the present proprietor would never be
able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estate. At last Anton said, "What that
wretched man has done away with he will have to account for; our first
care must be to preserve what is still to be found on the property. You
must be our guide to-day."
They then examined the empty buildings. Four horses and two
servants--they were gone into the wood--a few old plows, a pair of
harrows, two wagons, a britzska, a cellar full of potatoes, a few
bundles of hay, a little straw--the inventory did not take much time in
drawing up. The buildings were all out of repair, not through age, but
neglect.
"Where is the dwelling-house?" inquired Anton. The landlord led the way
out of the yard to the meadow--a broad plain, gradually sloping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brook. It had been a great pasture. The cattle had
trodden it down into holes; the snouts of greedy swine had rooted it up;
gray molehills and rank tufts of grass rose on all sides.
The landlord stretched out his hand. "There is the castle. This castle
i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he added, reverentially; "no
nobleman in the district has a stone house like that. All the gentry
here live in wood and mud buildings. Herr von Tarow, the richest of
them, has but a poor dwelling."
About three hundred yards from the last out-building rose a great brick
edifice, with a black slate roof and a thick round tower. Its gloomy
walls on this treeless pasture-land, without one trace of life around,
rose beneath the cloudy sky like a phantom fortress which some evil
spirit had evoked from the abyss--a station from which to blight all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The strangers approached it. The castle had fallen into ruins before the
builders had finished their task. The tower had stood there for ages. It
was built of unhewn stone, and had small windows and loop-holes. The
former lords of the land had looked down from its summit on the tops of
the trees, which then stretched far into the plain. They had then ruled
with a rod of iron the serfs who cultivated their land, and toiled and
died for them. Many an arrow had sped through those loop-holes at the
enemy storming below, and many a Tartar horse had been overthrown before
those massive walls. Years ago, a despot of the district had, in
expiation of former sins, begun to add to the gray tower the walls of a
holy monastery; but the monastery never got finished, and the useless
walls had already stood there long, when the late count took it into his
head to convert them into a lordly dwelling for his race, and to raise a
house unparalleled for magnificence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 front of the house was added on to both sides of the tower, which
projected in the middle. The intention had been to have a high
terrace-road up to the castle, and the principal entrance had been made
in the tower, and arched over; but the terrace never having been formed,
the stone threshold of the main door was quite inacce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ladders, and the wide opening was left. The window-spaces of
the lower floor were merely closed up with boards, while on the second
story were some window-frames of beautifully carved wood, in which large
panes had once been placed, but they had got broken. In other windows
were temporary frames of rough deal, with small panes of muddy glass let
into them. A company of jackdaws sat on the top of the tower, looking
down in amazement on the strangers, and every now and then one flew off,
screaming loudly, to contemplate the intruders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A house for crows and bats, not for human beings," said Anton. "At
least, I see no way of getting into it."
The landlord now took them round the building. Behind, where the two
wings made a sort of horse-shoe, there were low entrances to the cellars
and offices; beneath which, again, were stables, great arched kitchens,
and small cells for the serfs. A wooden staircase led to the upper
story. The door turned creaking on its hinges, and a narrow passage took
them through a side wing to the front part of the house. There all was
at least magnificently planned. The circular entrance-hall--an arched
room of the old tower--was painted in mosaic, and through the great
doorway-opening was seen a wide expans
small disturbance made by the return of Anton had gradually settled
down. Those first-class treasures of Sabine's had made way for other
specimens of damask, still of a superior kind, it is true, but which
came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e elderly cousin's comprehension. She had
been quite right in prophesying that Anton would never remark those
signs of exuberant gratitude or their withdrawal. However, one change
had been permanently made--the greatest, the best of all changes--the
clerk retained a privileged place in the heart of the young mistress of
the firm, and his tall figure often appeared as one of the circle that
Sabine's fancy loved to gather round her when at her work-table or in
her treasure-chamber.
To-day she was walking restlessly up and down before dinner. The cousin,
who heard every thing, had just told her that a maid from Ehrenthal's
had run into the office to announce Bernhard's death to his friend. "How
will he bear it?" thought she. And the name of Ehrenthal forced her
thoughts back to the past, to one now far away, and to that painful hour
when the struggle going on in her own mind had been suddenly brought to
a close by a letter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parted. And Anton had known
of that conquered feeling of hers. How considerate he had always been,
how chivalrous, how helpful! She wondered if he had any idea of the
completeness of her triumph over a girlish illusion. She shook her head.
"No, he has not. It was here, at this very table, that an accident first
betrayed me to him. That past time still rises like a cloud between us.
Whenever I sit near Wohlfart of an evening, I am conscious of another's
shadow at my side; and when he speaks to me, his tone, his manner always
seem to say, 'You are not alone; he is with you.'" Sabine started, and
lovingly passed her hand over the beautiful flowers on the table before
her, as if to dispel a painful thought. She could not tell him that she
was free from that long-felt sorrow. Now, however, when he had lost a
friend whom he so much loved, she must show him that there were other
hearts that clung to him still. And again she walked up and down, trying
to devise a way of speaking to him alone.
Dinner was announced. Anton came with the rest, and took his place at
once. There was no opportunity of exchanging a word during the meal, but
he often met her sad and sympathizing eye. "He eats nothing at all
to-day," whispered her cousin; "not even any of the roast," she added,
reproachfully. Sabine was much perturbed. Mr. Jordan had already risen;
Anton would leave the room with the rest, and she should not see him
again the whole day through. So she called out, "The great Calla is
fully blown now. You were admiring the buds the other day; will you
remain a moment; I should like to show it you?" Anton bowed and staid
behind. A few more awkward moments, then her brother rose too; and,
hurrying to Anton, she took him to the room where the flowers were.
"You have had sorrowful tidings to-day," she began.
"The tidings themselves did not surprise me," replied Anton. "The doctor
gave no hope. But I lose much in him."
"I never saw him," said Sabine; "but I know from you that his life was
lonely--poor in affection and in enjoyment."
She moved an arm-chair toward Anton, and led him on to talk about his
friend. She listened to every word with warm sympathy, and well knew
what to ask and how to comfort. It was a relief to Anton to speak of the
departed one, to describe his quiet way of life, his erudition, his
poetical enthusiasm. After a pause, Sabine looked up frankly into his
face, and asked, "Have you any tidings of Herr von Fink?"
It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his departure that she had ever breathed his
name. Anton felt how touching her confidence was, given in this hour of
his sadness. In his emotion, he seized her hand, which she was slow in
withdrawing.
"He is not happy in his new life," he gravely replied. "There was a
savage humor in his last letter, from which I gather, even more than
from his actual words, that the business into which his uncle's death
has thrown him does not suit him."
"It is unworthy," cried Sabine.
"At all events, it is not what would be recognized as honorable in this
house," replied Anton. "Fink is upright, and has lived too long with
your brother to take pleasure in the wild speculations so common on the
other side the Atlantic. His partners and colleagues are for the most
part men without a conscience, and his feelings revolt against their
companionship."
"And can Herr von Fink tolerate such relations as these for a day?"
"It is a remarkable thing that he whose own will was ever so arbitrarily
exercised, should now be obliged against that will to obey a pressure
from without, and every where to work with his hands tied. The
organization of such speculations in America is so complicated that one
shareholder can do little to alter it; and, now that Fink has attained
what used to be the goal of his wishes--a large capital, and the
management of immense districts--his condition appears more uncertain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He was always in danger of thinking slightingly
of others, now I am distressed at the bitter contempt he expresses for
his own life. His last letter paints an intolerable state of things, and
seems to point to some decisive resolve."
"There is only one resolve for him," cried Sabine. "May I ask what you
said to him in reply?"
"I entreated him instantly, come what would, to free himself from the
business in which he was entangled. I said that his own strong will
might find a way of extrication, even if that which I pointed out proved
impracticable. Then I begged of him either to carry out his old plan of
becoming a landed proprietor in America, or to return to us."
"I knew that you would write thus," said Sabine, drawing a long breath.
"Yes, Wohlfart, he shall return," said she, gently, "but he shall not
return to us."
Anton was silent.
"And do you think that Herr von Fink will follow your advice?"
"I do not know. My advice was not very American."
"But it was worthy of you," cried Sabine, with proud delight.
"An officer wishes to speak to Mr. Wohlfart," said a servant at the
door.
Anton sprang up. Sabine went to her flowers and bent mournfully over
them. The shadows of others hovered still between her friend and her.
The few words spoken by the servant filled Anton with a vague terror. He
hurried into the ante-room: there stood Eugene von Rothsattel. Anton was
gladly rushing forward to greet him, but the young soldier's face of
agony made him start back. He whispered, "My mother wishes to speak to
you; something dreadful has occurred." Anton caught up his hat, ran into
the office, hurriedly asked Baumann to excuse him to the principal, and
then accompanied the lieutenant to the baron's house.
On the way, Eugene, who had lost all self-command, said unconnectedly to
Anton, "My father last night accidentally wounded himself by a
pistol-shot--a messenger was sent to summon me--when I came, I found my
mother in a swoon--my sister and I do not know what to do--Lenore
implored my mother on her knees to send for you--you are the only one in
whom w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our distress--I understand nothing about
business, but my father's affairs must be in a dreadful state--my mother
is beside herself--the whole house is in the greatest disorder."
From what Eugene said and what he did not say; from his broken sentences
and his look of agony, Anton guessed at the horrors of the previous
evening. In the boudoir of the baroness he found Lenore, weeping and
exhausted.
"Dear Wohlfart!" cried she, taking his hand and beginning again to sob,
while her head sank powerless on his shoulder.
Meanwhile Eugene walked up and down, wringing his hands, and at length
throwing himself on the sofa, he gave himself up to silent tears.
"It is horrible, Mr. Wohlfart," said Lenore, lifting up her head. "No
one may approach my father--Eugene may not, nor I--only my mother and
old John are with him; and early this morning the merchant Ehrenthal was
here, insisting that he must see my father. He screamed at my mother,
and called my father a deceiver, till she fainted away. When I rushed
into the room, the dreadful man went off threatening her with his
clenched fist."
Anton led Lenore to a chair and waited till she had told him all.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comforting in this case, and his own heart was
wrung to the utmost by the misery he witnessed.
"Call my mother, Eugene," said Lenore, at length.
Her brother left the room.
"Do not forsake us," implored Lenore, clasping her hands; "we are at the
last gasp; even your help can not save us."
"He is dead who might perhaps have done so," mournfully replied Anton.
"Whether I can be of any use I know not, but you can not doubt my
willingness to be so."
"No," cried Lenore. "And Eugene, too, thought of you at once."
The baroness now entered. She walked wearily; but, steadying herself by
a chair, she saluted Anton with dignity. "In our position," said she,
"we need a friend who knows more of business than we three do.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prevents the baron--possibly for a long time to
come--from managing his own affairs, and, little as I understand them, I
can see that our interests require prompt measures. My children have
mentioned you to me, but I fear I am unreasonable in asking you to
devote your time to our service."
She sat down, beckoned Anton to take a chair, and said to her children,
"Leave us; I shall be better able to tell Mr. Wohlfart the little that I
know when I do not see your grief."
When they were alone, she motioned him nearer and tried to speak, but
her lips quivered, and she hid her face in her handkerchief.
"Before I can consent, gracious lady," said he, "to your reposing in me
such confidence as this, I must first inquire whether the baron has no
relative or intimate friend to whom you could with less pain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I pray you to remember that my own knowledge of business
is but small, and my position not one to constitute me a proper
counselor to the baron."
"I know no one," said the baroness, hopelessly. "It is less painful to
me to tell you what I can not conceal, than to one of our own circle.
Consider yourself a physician sent for to visit a patient. The baron has
this morning told me some particulars of his present circumstances." And
then she proceeded to relate what she had gathered as to the nature of
his embarrassments, the danger in which the family property was placed,
and the capital needed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Polish estate.
"My husband," continued she, "has given me the key of his desk, and he
wishes Eugene, with the help of a man of business, to go over his
papers. I now request of you to make this examination together with my
son. When you need explanations, I will try to obtain them from the
baron. The question is now, whether you are inclined to undertake this
trouble for us, who are only strangers."
"I am most willing to do so," earnestly replied Anton; "and I hope that
the kindness of my principal will allow me the time needful for the
purpose, if you do not consider it more advisable to depute the baron's
experienced legal adviser to the task."
"There will be an opportunity of asking that gentleman's advice later,"
said the baroness.
Anton rose. "When do you wish to begin?"
"Immediately. I fear there is not a day to lose. I shall do all I can to
help you look the papers over." She led Anton into the next room, called
in Eugene, and unlocked the baron's desk. As she opened it she lost her
self-command for a moment, and moving to the window, the quivering of
the curtains betrayed the anguish that shook her fragile frame.
The mournful task began. Hour after hour passed. Eugene was in no
condition to peruse any thing, but his mother reached letters and
documents to Anton, and, though often obliged to desist a while, she
bravely returned to the task. Anton placed the papers in order, and
sought, by glancing over each, to arrive at least at a superficial view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It was evening, when the old servant opened the door in dismay, and
called out, "He is there again." The baroness could not repress a slight
scream, and made a gesture of aversion.
"I have told him that no one is at home, but he will not be dismissed;
he makes such a noise on the steps. I can not get rid of him."
"It will kill me if I hear his voice again," murmured the baroness.
"If the man be Ehrenthal," said Anton, rising, "I will try to get him
away. We have now done what was most necessary; have the goodness to
lock up these papers, and to allow me to return to-morrow." The baroness
silently assented, and sank back in her chair. Anton hurried off to the
ante-room, whence he could hear Ehrenthal's loudly-raised voi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usurer shocked him. His hat pushed half off his
head, his pale face swelled as if by drinking, his glazed eyes red with
tears, Ehrenthal stood before him, calling in broken sentences for the
baron, wailing and cursing alternately. "He must come! he must come at
once!" cried he; "the wicked man! A nobleman, indeed! he is a vagabond,
after whom I will send the police. Where is my money? Where is my
security? I want my mortgage from this man who is not at home."
Anton went straight up to him, and asked, "Do you know me, Mr.
Ehrenthal?" Ehrenthal turned his glazed eyes upon him, and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 friend of his dead son.
"He loved you!" he cried, in a lamentable voice. "He spoke to you more
than to his father. You were the only friend that he had on earth. Have
you heard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house of Ehrenthal?" continued he, in
a whisper. "Just as they stole the papers he died. He died with a hand
like this," and clenching his fist he struck his forehead. "Oh my son!
my son! why didst not thou forgive thy father!"
"We will go to your son," said Anton, taking the arm of the old man, who
unresistingly allowed himself to be led back to his own house.
From thence Anton hurried to Councilor Horn, with whom he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It was late before he returned home. In the midst of his anxiety about
those whose prosperity had filled his imagination years before,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in their adversity, reposed in him, dilated his
breast with a feeling of pride. He burned with desire to help them, and
hoped that his zealous devotion might yet find some way of rescue. As
yet he saw none. Looking up at the great building before him, so firm
and secure, in the moonlight, a thought flashed into his mind. If any
man could help them, it was his principal. His keen eye would be able to
unravel all the dark secrets in which the baron was entangled, and his
iron strength of will would crush the villains who held the unfortunate
nobleman in their power. And then he had a noble nature; he always
decided on the right, without an effort or a struggle. Anton looked at
the first floor. The whole house-front was dark, but in a corner room a
light still burned. It was the private office of his chief.
With sudden resolve, Anton begged the servant to take him to Mr.
Schröter, who looked with amazement at the unexpected visitor, and asked
what brought him, and whether any thing had happened.
"I implore your counsel--I implore your help," cried Anton.
"For yourself or for others?" inquired the merchant.
"For a family with whom I have accidentally become connected. They are
lost if a strong hand does not ward off the impending catastrophe."
Anton then rapidly related the occurrences of the afternoon, and,
seizing his principal's hand in his emotion, cried, "Have pity upon the
unhappy ladies, and help them."
"Help them!" replied the merchant; "how can I? Have you been
commissioned to apply to me, or are you only following the impulse of
your own feelings?"
"I am not commissioned; it is only the interest that I take in the
baron's fate which leads me to you."
"And what right have you to inform me of facts communicated in strict
confidence to yourself by the baron's lady?" asked the merchant, dryly.
"I am committing no indiscretion in telling you what will, in a few
days, be no secret, even to strangers."
"You are unusually excited, otherwise you would not forget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hatever, does a man of business venture to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without the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Of course, I shall make no wrong use of what you have said, but it was
by no means business-like, Wohlfart, to be so open toward me."
Anton was silent, feeling, indeed, that his principal was right, but yet
it seemed hard to be blamed for reposing confidence at such a time as
this. The merchant walked silently up and down; at length, stopping
before Anton, he said, "I do not now inquire how you come to take so
warm an interest in this family. I fear it is an acquaintance you owe to
Fink."
"You shall hear all," said Anton.
"Not at present. I will now content myself with repeating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interfere in these affairs without being specially
applied to by the parties themselves. I may add that I by no means wish
for such an application, and do not disguise from you that, were it
made, I should probably decline to do any thing for the Baron
Rothsattel."
Anton's feelings were roused to the utmost. "The question is the rescue
of an honorable man, and of lovely and amiable women from the toils of
rogues and impostors. To me, this seems the duty of every one; I, at
least, consider it a sacred obligation which I dare not shrink from. But
without your support I can do nothing."
"And how do you think this embarrassed man can be helped?" inquired the
merchant, seating himself.
With somewhat more composure, Anton repli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an experienced man of business making himself master of the case. There
must be some way of circumventing these villains. Your penetration would
discover it."
"Any attorney would be far more likely to do so, and the baron might
readily engage the services of experienced and upright legal advisers.
If his enemies have done any thing illegal, the quick eye of a lawyer is
the most likely to detect it."
"Alas! the baron's own lawyer gives but little hope," replied Anton.
"Then, my dear Wohlfart, no other is likely to do much good. Show me an
embarrassed man who has strength to grasp an offered hand, and bid me
help him, and for the sake of all I owe you, I will not refuse to do so.
I think you are convinced of this."
"I am," said Anton, dejectedly.
"From all I hear, however," the merchant went on,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the baron. From what I gather from general report, as well as from
you, his embarrassments arise from his having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usurers, which proves him deficient in what alone ennobles the life of
any man--good sense, and the power of steady exertion."
Anton could only sigh his assent.
"To help such a man," inexorably continued the merchant, "is a futile
attempt, against which reason may well protest. We are not to despair of
any, but want of strength is the most hopeless case of all. Our power of
laboring for others being limited, it becomes our duty to inquire,
before we devote our time to the weak, whether we are not thus
diminishing our chances of helping better men."
Anton interrupted him. "Does he not deserve every allowance to be made
for him? He was brought up to exact much; he has not learned, as we
have, to make his way by his own labor."
The merchant laid his hand on the young man's shoulder. "The very
reason. Believe me, a large number of these landed gentry, who pay the
penalty of their old family memories, are beyond help. I am the last to
deny that many worthy and admirable men belong to this class. Indeed,
wherever remarkable talent or nobility of character shoots up among
them, no doubt their position offers peculiar scope for its development,
but for average men it is not a favorable one. He who considers it his
hereditary privilege to enjoy life, and who assumes a distinguished
position in virtue of his family, will very often fail to put forth his
whole strength in order to deserve that position. Accordingly, numbers
of our oldest families are declining, and their fall will be no loss to
the state. Their family associations make them haughty without any
right to be so--limit their perceptions and confuse their judgment."
"Even if all this be true," cried Anton, "it does not absolve us from
helping individuals of the class who have excited our sympathy."
"No," said the principal, "if it be excited. But it does not glow so
rapidly in advancing years as in youth. The baron has endeavored to
isolate his property from the current of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leave it forever to his family. Forever! You, as a merchant, know how to
estimate the attempt. True, every rational man must allow it to be
desirable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same soil should be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We all prize what our forefathers have possessed before
us, and Sabine would unlock every room in this house with pride, because
her great-great-grandmother turned the same keys before her. It is
therefore natural that the landed proprietor should desire to preserve
those familiar scenes, which are the source of his own prosperity, to
those nearest and dearest to him. But there must be means to this end,
and these means are the making his own existence available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increase of his patrimony. Where energy dies in families
or individuals, then it is well that their means die too, that their
money should circulate through other hands, and their plowshare pass to
those who can guide it better. A family that has become effete through
luxury ought to sink down into common life, to make room for the
uprising of fresh energies and faculties. Every one who seeks, at the
cost of free activity for others, to preserve permanent possessions and
privileges for himself or his family, I must look upon as an enemy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social state. And if such a man ruin
himself in his endeavors, I should feel no malicious pleasure in his
downfall, but I should say that he is rightly served, because he has
sinned against a fundamental law of our social being; consequently, I
should consider it doubly wrong to support this man, because I could but
fear that I should thus be supporting an unsound condition of the body
politic."
Anton looked down mournfully. He had expected sympathy and warm
concurrence, and he met with disaffection and coldness that he despaired
of conquering. "I can not gainsay you," he at length replied; "but in
this case I can not feel as you do. I have been witness to the
unspeakable distress in the baron's family, and my whole soul is full
of sadness and sympathy, and of the wish to do something for those who
have opened their heart to me. After what you have said, I dare no
longer ask you to trouble yourself with their affairs, but I have
promised the baroness to assist her as far as my small powers permit,
and your kindness allows. I implore you to grant me permission to do
this. I shall endeavor to be regular in my attendance at the office, but
if during the next few weeks I am occasionally absent, I must ask you to
excuse me."
Once more the merchant walked up and down the room, and then, looking at
Anton's excited face, with deep seriousness and something of regret, he
replied, "Remember, Wohlfart, that every occupation which excites the
mind soon obtains a hold over a man, which may retard as well as advance
his success in life. It is thi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 to agree
to your wishes."
"I know it," said Anton, in a low voice; "but I have now no choice
left."
"Well, then, do what you must," said the merchant, gloomily; "I will lay
no hinderance in your way; and I hope that after a few weeks you will be
able to consider the whole circumstances more calmly." Anton left the
room, and the merchant stood looking long with frowning brow at the
place his clerk had occupied.
Nor was Anton in a more congenial mood. "So cold, so inexorable!"
exclaimed he, as he reached his own room. He began to suspect that his
principal was more selfish and less kindly than he had hitherto
supposed. Many an expression of Fink's recurred to his mind, as well as
that evening when young Rothsattel, in his boyish conceit, had spoken
impertinently to the merchant. "Is it possible," thought he, "that that
rude speech should be unforgotten?" And his chief's keen, deep-furrowed
face lost inexpressibly by contrast with the fair forms of the noble
ladies. "I am not wrong," he cried to himself; "let him say what he
will, my views are more just than his, and henceforth my destiny shall
be to choose for myself the way in which I shall walk." He sat long in
the darkness, and his thoughts were gloomy as it; then he went to the
window to look down into the dark court below. A great white blossom
rose before him like a phantom. Striking a light, he saw that it was the
beautiful Calla out of Sabine's room. It hung down mournfully on its
broken stem. Sabine had had it placed there. This little circumstance
struck him as a mournful omen.
Meanwhile Sabine, taper in hand, entered her brother's room.
"Good-night, Traugott," nodded she. "Wohlfart has been with you this
evening; how long he staid!"
"He will leave us," replied the merchant, gloomily.
Sabine started and dropped her taper on the table. "For God's sake, what
has happened? Has Wohlfart said that he was going away?"
"I do not yet know it, but I see it coming step by step; and I can not,
and still less can you, do any thing to retain him. When he stood before
me here with glowing cheeks and trembling voice, pleading for a ruined
man, I found out what it was that lured him away."
"I do not understand you," said Sabine, looking full at her brother.
"He chooses to become the confidential friend of a decayed noble. A pair
of bright eyes draws him away from us: it seems to him a worthy object
of ambition to become Rothsattel's man of business. This intimacy with
nobility is the legacy bequeathed to him by Fink."
"And you have refused to help him?" inquired Sabine, in a low voice.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said the merchant, harshly; and he
turned to his writing-table.
Sabine slowly withdrew. The taper trembled in her hand as she passed
through the long suite of rooms listening to her own footfall, and
shuddering as the feeling came over her that an invisible companion
glided by her side. This was the revenge of that other. The shadow that
once fell on her innocent life now drove her friend away from their
circle. Anton's affections clung to another. She had but been in his
eyes a mere stranger, who had once loved and languished for one now far
away, and who now, in widow's weeds, looked back regretfully to the
feelings of her youth.
The few next weeks were spent by Anton in over-hard work. He had great
difficulty in keeping up his counting-house duties, while he spent every
spare hour in conference with the baroness and the lawyer.
In the mean time, the misfortunes of the baron ran their course. He had
not been able to pay the interest of the sums with which his estate was
burdened. When last they were due, a whole series of claims was brought
against him, and the estate fell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district authorities. Complicated lawsuits arose. Ehrenthal complained
loudly, claiming the first mortgage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nay, he
was inclined to advance claims on the last mortgage offered by the baron
in the recent fatal hour. Löbel Pinkus also appeared as claimant of the
first mortgage, and asserted that he had paid the whole sum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Ehrenthal had no proof to bring forward, and had been
for some weeks past quite unable to manage his own affairs, while
Pinkus, on the contrary, fought with every weapon a hardened sinner can
devise or employ, and the deeds which the baron had executed at Veitel's
suggestion proved to be so capital a master-stroke of the cunning
advocate, that the baron's man of business had, from the first, little
hope of the case. We may here observe that Pinkus did eventually win it,
and that the mortgage was made over to him.
Anton was now gradually gaining some insight into the baron's
circumstances. But the double sale of the first mortgage was still kept
a secret by the latter, even from his wife. He declared Ehrenthal's
claim unfounded, and even expressed a suspicion that he had himself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robbery in his office. Indeed, he really
believed this. Then the name of Itzig was never broached, and the
suspicion against Ehrenthal, which the baron's lawyer shared, prevented
Anton seeking any explanation from him.
Meanwhile, an estrangement had sprung up between our hero and his
principal, which the whole counting-house remarked with surprise. The
merchant scowled at Anton's vacant seat when the latter chanced to be
absent during office-hours, or looked coldly at his clerk's face, made
pale as it was with excitement of mind and night-work. He took no notice
of his new occupation, and never seemed to remark him. Even to his
sister he maintained a stiff-necked silence; nor could all her attempts
lead him to speak of Anton, who, on his side, felt his heart revolt
against this coldness. After his return, to be treated like a child of
the house, praised, promoted, petted, and now to be treated like a mere
hireling, who is not worth the bread thrown to him; to be a toy of an
incomprehensible caprice--this, at least, he had not deserved; so he
became reserved toward the whole family, and sat silent at his desk; but
he fel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now and the then so keenly, that often,
when alone, he would spring up and stamp on the ground in the bitter
indignation of his heart.
One comfort remained. Sabine was not estranged. True, he saw little of
her, and at dinner she seemed to avoid speaking to him, but he knew that
she was on his side.
A few days after his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the merchant, she came down
stairs as he stood in the hall, and had to pass him by so closely that
her dress touched him. He had retreated, and made a formal bow, but she
looked at him imploringly, and whispered, "You must not be estranged
from me." It was an affair of a moment, but the faces of both were
radiant with a happy understanding.
The time had now arrived when Mr. Jordan was to quit the firm. The
principal again called Anton into his little office, and without any
severity, but also without a trace of his former cordiality, began: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o you my intention of appointing you Jordan's
successor; but,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your time has been more taken
up with other business than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such a post, I
therefore ask you whether you are now at liberty to undertake Jordan's
duties?"
"I am not," replied Anton.
"Can you name any--not very distant--time when you will be free from
your present occupation? In that case I will endeavor to find a
substitute until then."
Anton sorrowfully replied, "I can not at present say when I shall again
be master of my whole time; and, besides, I feel that, even as it is, I
tax your indulgence by many irregularities. Therefore, Mr. Schröter, I
beg that you will fill up this post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me."
The merchant's brow grew furrowed and dark, and he silently bowed
assent. Anton felt as he closed the door that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m was now complete, and, resuming his place, he leaned his throbbing
head on his hand. A moment later Baumann was summoned to the principal,
and Jordan's situation conferred upon him. On returning to the office,
he went up to Anton and whispered, "I refused at first, but Mr. Schröter
insisted. I am doing you an injustice." And that evening Mr. Baumann, in
his own room, read in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the chapters treating of
the unjust Saul (the principal), and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Jonathan
and the persecuted David, and strengthened his heart thereby.
The next day Anton was summoned to the baroness. Lenore and her mother
sat before a large table covered with jewel-boxes and toilette elegances
of every description, while a heavy iron chest stood at their feet. The
curtains were drawn, and the subdued light shone softly into the richly
furnished room. On the carpet glowed wreaths of unfading flowers, and
the clock ticked cheerfully in its alabaster case. Under the shade of
flowering plants sat the two love-birds in their silvered cage, hopping
from perch to perch, screaming ceaselessly, or sitting up quietly close
to each other. The whole room was beauty and perfume. "For how long?"
thought Anton. The baroness rose. "We are already obliged to trouble you
again," said she; "we are engaged in a very painful occupation." On the
table were all manner of ornaments, gold chains, brilliants, rings,
necklaces, gathered into a heap.
"We have been looking out all that we can dispense with," said the
baroness, "and now pray you to undertake to sell these things for us. I
have been told that some of them are of value, and as we are now in much
need of money, we turn here for help."
Anton looked in perplexity at the glittering heap.
"Tell us, Wohlfart," cried Lenore, anxiously, "is this necessary? can it
be of any use? Mamma has insisted upon setting apart for sale all our
ornaments, and whatever plate is not in daily use. What I can give is
not worth talking of, but my mother's jewels are costly; many of them
were presents made to her in youth, which she shall not part with unless
you say that it is necessary."
"I fear," said Anton, gravely, "that it will prove so."
"Take them," said the baroness to Anton; "I shall be calmer when I know
that we have at least done what we could."
"But do you wish to part with all?" inquired Anton, anxiously. "Much
that is dear to you may have but little value in a jeweler's eyes."
"I shall never wear an ornament again," quietly replied the baroness.
"Take them all;" and, holding her hands before her eyes, she turned
away.
"We are torturing my mother," cried Lenore, hastily; "will you lock up
all that is on the table, and get them out of the house as soon as you
can?"
"I can not undertake the charge of these valuables," said Anton,
"without taking some measures to decrease my own responsibility. First
of all, I will in your presence make a short note of all you intrust to
me."
"What useless cruelty!" exclaimed Lenore.
"It will not take long."
Anton took out a few sheets from his pocket-book, and began to note down
the different articles.
"You shall not see it done, mother," said Lenore, drawing her mother
away, and then returning to watch Anton at his task.
"These preparations for the market are horrible," said she. "My mother's
whole life will be sold; some memory of hers is linked with every single
thing. Look, Wohlfart, the princess gave her this diamond ornament when
she married my father."
"They are magnificent brilliants," cried Anton, admiringly.
"This ring was my grandfather's, and these are presents of poor papa's.
Alas! no man can know how we love all these things. It was always a
festival to me when mamma put on her diamonds. Now we come to my
possessions. They are not worth much. Do you think this bracelet good
gold?" She held out her hand as she spoke.
"I do not know."
"It shall go with the rest," said Lenore, taking it off. "Yes, you are a
kind, good man, Wohlfart," continued she, looking trustfully into his
tearful eyes; "do not forsake us. My brother has no experience, and is
more helpless than we are. It is a frightful position for me. Before
mamma I do all I can to be composed, else I could scream and weep the
whole day through." She sank in a chair, still holding his hand. "Dear
Wohlfart, do not forsake us."
Anton bent over her, and looked with passionate emotion at the lovely
face that turned so trustfully to him in the midst of its tears.
"I will be helpful to you when I can," said he, in the fullness of his
heart. "I will be at hand whenever you need me. You have too good an
opinion of my information and my faculties; I can be of less assistance
to you than you suppose, but what I can, that I will do in any and every
possible way."
Their hands parted with a warm pressure; the affair was settled.
The baroness now returned. "Our lawyer was with me this morning," said
she; "and now I must ask for your opinion on another subject. He tells
me that there is no prospect of preserving the baron's family estate."
"At this time, when interest is high, and money difficult to get, none,"
replied Anton.
"And you, too, think that we must turn all our efforts toward preserving
the Polish property?"
"I do," was the answer.
"For that, also, money will be necessary. Perhaps I may be able through
my relatives to intrust you with a small sum, which, with the help of
that"--she pointed to the iron chest--"may suffice to cover the first
necessary expenses. I do not, however, wish to sell the jewels here, and
a journey to the residence would be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cure the
sum to which I have just alluded. The baron's lawyer has spoken most
highly of your capacity for business. It is his wish which now decides
me to make a proposal to you. Will you for the next few years, or, at
all events, until our greatest difficulties are over, devote your whole
time to our affairs? I have consulted my children, and they agree with
me in believing that in your assistance lies our only hope of rescue.
The baron, too, has come in to the plan. The question now is whether
your circumstances allow you to give your support to our unfortunate
family. We shall be grateful to you, whatever conditions you affix; and
if you can find any way of making our great obligations to you apparent
in the position you hold, pray impart it to me."
Anton stood petrified. What the baroness required of him was separation
from the firm, separation from his principal, and from Sabine! Had this
thought occurred to him before, when standing in Lenore's presence or
bending over the baron's papers? At all events, now that the words were
spoken, they shocked him. He looked at Lenore, who stood behind her
mother with hands clasped in supplication. At length he replied, "I
stand in a position which I can not leav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others.
I was not prepared for this proposal, and beg to have time allowed me
for consideration. It is a step which will decide my whole future life."
"I do not press you," said the baroness; "I only request your
consideration. Whatever your decision be, our warmest gratitude will
still be yours; if you are unable to uphold our feeble strength, I fear
that we shall find no one to do so. You will think of that," she added,
beseechingly.
Anton hurried through the street with throbbing pulse. The noble lady's
glance of entreaty, Lenore's folded hands, beckoned him out of the
gloomy counting-house into a sphere of greater liberty, into a new
future, from whose depths bright images flashed out upon his fancy. A
request had been frankly made, and he was strongly inclined to justify
the confidence that prompted it. Those ladies required an unwearied,
self-sacrificing helper to save them from utter ruin, and if he
followed his impulse he should be doing a good work--fulfilling a duty.
In this mood he entered the merchant's dwelling. Alas! all that he saw
around him seemed to stretch out a hand to detain him. As he looked at
the warehouse, the good-humored faces of the porters, the chains of the
great scales, the hieroglyphics of the worthy Pix, again he felt that
this was the place that he belonged to. Sabine's dog kissed his hand,
and ran before him to his room--his and Fink's room. Here the childish
heart of the orphan boy had found a friend, kind companions, a home, a
definite and honorable life-purpose. Looking down through his window on
all the long-familiar objects, he saw a light in Sabine's store-chamber.
How often he had sought for that light, which brightened the whole great
building, and brought a sense of comfort and cheerfulness even into his
room. He now sprang up suddenly, and said to himself, "She shall
decide."
Sabine started in amazement when Anton appeared before her. "I am
irresistibly impelled to seek you," cried he. "I have to decide upon my
future life, and I feel undetermined, and unable to trust to my own
judgment. You have always been a kind friend to me since the day of my
arrival. I am accustomed to look up to you, and to think of you in
connection with all that interests me here. Let me hear your opinion
from your own lips. The Baroness Rothsattel has to-day proposed to me
permanently to undertake the situation of confidential adviser and
manager of the baron's affairs. Shall I accept; or shall I remain here?
I know not--tell me what is right both for myself and others."
"Not I," said Sabine, drawing back and growing very pale. "I can not
venture to decide in the matter. Nor do you wish me to do so, Wohlfart,
for you have already decided."
Anton looked straight before him and was silent.
"You have thought of leaving this house, and a wish to do so has sprung
out of the thought. And I am to justify you, and approve your resolve!
This is what you require of me," continued she, bitterly. "But this,
Wohlfart, I can not do, for I am sorry that you go away from us."
She turned away from him and leaned on the back of a chair.
"Oh, be not angry with me too!" said Anton; "that I can not bear. I have
suffered much of late. Mr. Schröter has suddenly withdrawn from me the
friendly regard that I long held my life's greatest treasure. I have not
deserved his coldness. What I have been doing has not been wrong, and
it was done with his knowledge. I had been spoiled by his kindness; I
have the more deeply felt his displeasure. My only comfort has been that
you did not condemn me. And now, do not you be cold toward me, else I
shall be wretched forever. There is not a soul on earth to whom I can
turn for affectionate comprehension of my difficulties. Had I a sister,
I should seek her heart to-day. You do not know what to me, lonely as I
am, your smile, your kindly shake of the hand has been till now. Do not
turn coldly from me, I beseech you."
Sabine was silent. At length she inquired, still with averted face,
"What draws you to those strangers; is it a joyful hope, is it sympathy
alone? Give this question close consideration before you answer it to
yourself at least."
"What it is that makes it possible for me to leave this house," said
Anton, "I do not myself know. If I can give a name to my motives, it is
gratitude felt toward one. She was the first to speak kindly to the
wandering boy on his way out into the world. I have admired her in the
peaceful brightness of her former life. I have often dreamed childish
dreams about her. There was a time when a tender feeling for her filled
my whole heart, and I then believed myself forever the slave of her
image. But years bring changes, and I learned to look on men and on life
with other eyes. Then I met her again, distressed, unhappy, despairing,
and my compassion became overmastering. When I am away from her, I know
that she is nothing to me; when I am with her, I feel only the spell of
her sorrow. Once, when I had to depart out of her circle like a culprit,
she came to me, and before the whole scornful assembly she gave me her
hand and acknowledged me her friend; and now she comes and asks for my
hand to help her father. Can I refuse it? Is it wrong to feel as I do? I
know not, and no one can tell me--no one but you alone."
Sabine's head had sunk down to the back of the chair on which she bent.
She now suddenly raised it, and with tearful eyes, and a voice full of
love and sorrow, cried, "Follow the voice that calls you. Go, Wohlfart,
go."
CHAPTER XXVII.
On a cold October day, two men were seen driving through the latticed
gate of the town of Rosmin on toward the plain, which stretched out
before them monotonous and boundless. Anton sat wrapped in his fur coat,
his hat low on his forehead, and at his side was young Sturm, in an old
cavalry cloak, with his soldier's cap cocked cheerily on one side. In
front of them a farm-servant, squatted on a heap of straw, flogged on
the small horses. The wind swept the sand and straw from the
stubble-fields, the road was a broad causeway without ditches or hedges,
the horses had to wade alternately through puddles and deep sand. Yellow
sand gleamed through the scanty herbage in all directions wherever a
field-mouse had made her way to her nest or an active mole had done what
he could to diversify the unbroken plain. Wherever the ground sank,
stagnant water lodged, and there hollow willow-trees stretched their
crippled arms in the air, their boughs flapping in the wind, and their
faded leaves fluttering down into the muddy pool below. Here and there
stood a small dwarf pine, a resting-place for the crows, who, scared by
the passing carriage, flew loudly croaking over the travelers' heads.
There was no house to be seen on the road, no pedestrian, and no
conveyance of any kind.
Karl looked every now and then at his silent companion, and said at
last, pointing to the horses, "How rough their coats are, and how pretty
their gray mouse skins! I wonder how many of these beasties would go to
make up my sergeant's horse! When I took leave of my father, the old man
said, 'Perhaps I shall pay you a visit, little one, when they light the
Christmas-tree.' 'You'll never be able,' said I. 'Why not?' asked he.
'You'll never trust yourself in any post-chaise.' Then the old boy
cried, 'Oho! post-chaises are always of a stout build; I shall be sure
to trust myself in one.' But now, Mr. Anton, I see that my father never
can pay us a visit."
"Why not?"
"It is possible that he may reach Rosmin; but, as soon as he sees these
horses and this road, he will instantly turn back. 'Shall I trust
myself,' he'll say, 'in a district where sand runs between one's legs
like water, and where mice are put into harness? The ground is not firm
enough for me.'"
"The horses are not the worst things here," said Anton, absently. "Look!
these go fast enough."
"Yes," replied Karl, "but they don't go like regular horses; they
entangle their legs like two cats playing in a parsley-bed. And what
things they have for shoes--regular webbed hoofs, I declare, which no
blacksmith can ever fit."
"If we could only get on!" returned Anton; "the wind blows cold, and I
am shivering in spite of my fur."
"You have slept but little the last few nights, sir," said Karl. "The
wind blows here as if over a threshing-floor. The earth is not round
hereabouts as elsewhere, but flat as a cake. This is a complete desert;
we have been driving for more than an hour, and there is not a village
to be seen."
"A desert indeed," sighed Anton; "let us hope it may improve." They
relapsed into profound silence. At length the driver stopped near a
pool, unharnessed the horses, and led them to the water's edge, without
noticing the travelers.
"What the deuce does this mean?" cried Karl, jumping down from the
carriage.
"I am going to feed," replied the servant, sulkily, in a foreign accent.
"I am anxious to know how that will be done," said Karl. "There is not
the shadow of a bag of provender."
The horses, however, soon proved that they could live without corn; they
stretched down their shaggy heads, and began to pull the grass and weeds
at the edge of the pool, sometimes taking a draught of the dirty water.
Meanwhile the servant drew a bundle from under his seat, settled himself
under the lee of an alder-bush, and, taking his knife, cut his bread and
cheese without even glancing at the travelers.
"I say, Ignatius or Jacob," cried Karl, sharply, "how long will this
breakfast of yours last?"
"An hour," replied the man, munching away.
"And how far is it from here to the estate?"
"Six miles, or maybe more."
"You can make nothing of him," said Anton; "we must put up with the
customs of the country;" and, leaving the carriage, they went to look on
at the horses feeding.
Anton is on his way to the Polish property. He is now the baron's agent.
Anxious months have the last proved to him. The parting from his
principal and the firm had been painful in the extreme. For some time
before it, indeed, Anton had found himself alone in the midst of his
colleagues. The quiet Baumann still remained his friend, but the others
considered him a castaway. The merchant received his resignation with
icy coldness; and even in the hour of parting, his hand lay impassive as
metal in Anton's grasp. Since then, our hero had undertaken several
journeys to the capital and to creditors in the family's behalf, and now
he was on his way to set the new estate in order, accompanied by Karl,
whom he had induced to become the baron's bailiff.
Ehrenthal had, by the authority conferred on him,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from the time of the sale by auction, and hired the Polish
bailiff for the baron. There had been unfair dealings between them at
the time, and it was well known in Rosmin that the bailiff had sold off
a good deal, and been guilty of all sorts of frauds since, so that Anton
had even now no prospect of a quiet life.
"The hour is come when I may execute my commission," cried Karl, groping
in the straw under the seat. He drew out a large japanned tin case, and
carried it to Anton. "Miss Sabine gave me this in charge for you." He
then joyously opened the lid, produced the materials for an excellent
breakfast, a bottle of wine, and a silver goblet. Anton took hold of the
case.
"It has a very knowing look," said Karl. "Miss Sabine planned it
herself."
Anton examined it on all sides, and placed it carefully on a tuft of
grass; then he took up the goblet, and saw his initials engraved on it,
and underneath the words, "To thy welfare." Whereupon he forgot the
breakfast and all around him, and stood gazing at the goblet, lost in
thought.
"Do not forget the breakfast, sir," suggested Karl, respectfully.
"Sit down by me, my faithful friend; eat and drink with me. Leave off
your absurd politeness. We shall have but little, either of us, but what
we have we will share like brothers. Take the bottle if you have no
glass."
"There's nothing like leather," said Karl, taking a small leathern
drinking-cup out of his pocket. "As for 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t was
kindly meant, and I thank you; but there must be subordination, if it
were but for the sake of the others; and so, sir, be kind enough to let
me shake hands with you now, and then let things be as they were before.
Only look at the horses, Mr. Anton. My faith! the creatures devour
thistles."
Again the horses were harnessed, again they threw out their short legs
in the sand, and again the carriage rolled through the barren
district--first through an empty plain, next through a wretched
fir-wood, then past a row of low sand-hills, then over a tumble-down
bridge crossing a small stream.
"This is the property," said the driver, turning round, and pointing
with his whip to a row of dirty thatched roofs that had just come into
sight.
Anton stood up to look for the group of trees in which the Hall might be
supposed to stand. Nothing of the sort to be seen. The village was
deficient in all that adorns the home of the poorest German peasant--no
orchard, no hedged-in gardens, no lime-trees in the market-place.
"This is wretched," said he, sitting down again; "much worse than they
told us in Rosmin."
"The village looks as if under a curse," cried Karl; "no teams working
in the fields--not a cow or a sheep to be seen."
The farm-servant flogged his horses into an irregular gallop, and so
they passed through the rows of mud huts which constituted the village,
and arrived at the public house. Karl sprang from the carriage, opened
the tavern door, and called for the landlord. A Jew slowly rose from his
seat by the stove and came to the threshold. "Is the gendarme from
Rosmin come?" He is gone into the village. "Which is the way to the
farm-yard?"
The landlord, an elderly man with an intelligent countenance, described
the way in German and Polish, and remained standing at the
door--bewildered, Karl declared, by the sight of two human beings. The
carriage turned into a cross-road, planted on both sides with thick
bushes, the remains of a fallen avenue. Over holes, stones, and puddles,
it rattled on to a group of mud huts, which still had a remnant of
whitewash upon them. "The barns and stables are empty," cried Karl, "for
I see gaps in the roofs large enough to drive our carriage through."
Anton said no more; he was prepared for every thing. They drove through
a break between the stables into the farm-yard, a large irregular space,
surrounded on three sides by tumble-down buildings, and open to the
fields on the fourth. A heap of _débris_ lay there--lime and rotten
timber, the remains of a ruined barn. The yard was empty; no trace of
farm implements or human labor to be seen. "Which is the inspector's
house," inquired Anton, in dismay. The driver looked round, and at last
made up his mind that it was a small one-storied building, with straw
thatch and dirty windows.
At the noise of the wheels a man appeared on the threshold, and waited
phlegmatically till the travelers had dismounted, and were standing
close before him. He was a broad-shouldered fellow, with a bloated,
brandy-drinking face, dressed in a jacket of shaggy cloth, while behind
him peered the muzzle of an equally shaggy dog, who snarled at the
strangers. "Are you the steward of this property?"
"I am," replied the man, in broken German, without stirring from where
he was.
"And I am the agent of the new proprietor," said Anton.
"That does not concern me," growled the shaggy man, turning sharp round,
entering the house, and bolting the door within.
Anton was thoroughly roused. "Break the window in, and help me to catch
the rascal," cried he to Karl, who coolly seized a piece of wood, struck
the panes so as to make the rotten framework give way, and cleared the
opening at one leap. Anton followed him. The room was empty, so was the
next, and in it an open window--the man was gone.
"After him!" cried Karl, and dashed on in pursuit, while Anton looked
about the house and out-buildings. He soon heard the barking of a dog,
and saw Karl capture the fugitive. Hurrying to his help, he held the man
fast, while, with a kick, Karl sent the dog flying. They then contrived
to force the steward back to the house, though he kept striking out
violently all the way.
"Go to the tavern, and bring the gendarme and the landlord," cried Anton
to the driver, who, undisturbed by all that had been going on, had
meanwhile unpacked the carriage. The man accordingly drove leisurely
off, and the fugitive being got into the room, Karl found an old cloth,
and with it bound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I beg your pardon, sir,"
said he; "it is only for an hour or so, till the arrival of the Rosmin
gendarme, whom we have appointed to meet us."
Anton then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house, bu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found but the merest necessaries; no books nor papers of any kind. It
had doubtless been emptied already. A bundle projected from the
coat-pocket of the prisoner, which turned out to be receipts and legal
documents in Polish. In time, the driver returned with the landlord and
the armed policeman. The landlord stood at the door in some perplexity,
and the policeman explained in a few moments what remained to be done.
"You must make a statement to the local judge, and give the man up to
me. He shall go back in your carriage to Rosmin. You will do well to get
rid of him, for this is a wild country, and it will be safer for you to
have him at Rosmin than here, where he has friends and accomplices."
After a long search, a sheet of paper was found in a cupboard, the
statement made and submitted to the policeman, who shook his head a
little over the Polish composition, and the prisoner lifted into the
carriage, the gendarme taking his seat beside him, and saying to Anton,
"I have long expected something of the kind. You may have often occasion
to want me again." The carriage then drove away, and thus the property
came under Anton's administration. He felt as if cast on a desert
island.
His portmanteau and traveling effects were leaning against a mud wall,
and the Polish landlord was the only man who could give him and Karl any
information or advice in their forlorn condition.
Now that the steward was fairly gone, the landlord grew more
communicative, and showed himself serviceable and obliging. A long
conversation ensued, and its purport was what Anton had apprehended from
the warning given by the Commissary Walter and other Rosmin officials.
The inspector had,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done all he could in the
way of spoliation, rendered daring by a report which had found its way
from the town to the village, that the present proprietor would never be
able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estate. At last Anton said, "What that
wretched man has done away with he will have to account for; our first
care must be to preserve what is still to be found on the property. You
must be our guide to-day."
They then examined the empty buildings. Four horses and two
servants--they were gone into the wood--a few old plows, a pair of
harrows, two wagons, a britzska, a cellar full of potatoes, a few
bundles of hay, a little straw--the inventory did not take much time in
drawing up. The buildings were all out of repair, not through age, but
neglect.
"Where is the dwelling-house?" inquired Anton. The landlord led the way
out of the yard to the meadow--a broad plain, gradually sloping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brook. It had been a great pasture. The cattle had
trodden it down into holes; the snouts of greedy swine had rooted it up;
gray molehills and rank tufts of grass rose on all sides.
The landlord stretched out his hand. "There is the castle. This castle
i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he added, reverentially; "no
nobleman in the district has a stone house like that. All the gentry
here live in wood and mud buildings. Herr von Tarow, the richest of
them, has but a poor dwelling."
About three hundred yards from the last out-building rose a great brick
edifice, with a black slate roof and a thick round tower. Its gloomy
walls on this treeless pasture-land, without one trace of life around,
rose beneath the cloudy sky like a phantom fortress which some evil
spirit had evoked from the abyss--a station from which to blight all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The strangers approached it. The castle had fallen into ruins before the
builders had finished their task. The tower had stood there for ages. It
was built of unhewn stone, and had small windows and loop-holes. The
former lords of the land had looked down from its summit on the tops of
the trees, which then stretched far into the plain. They had then ruled
with a rod of iron the serfs who cultivated their land, and toiled and
died for them. Many an arrow had sped through those loop-holes at the
enemy storming below, and many a Tartar horse had been overthrown before
those massive walls. Years ago, a despot of the district had, in
expiation of former sins, begun to add to the gray tower the walls of a
holy monastery; but the monastery never got finished, and the useless
walls had already stood there long, when the late count took it into his
head to convert them into a lordly dwelling for his race, and to raise a
house unparalleled for magnificence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 front of the house was added on to both sides of the tower, which
projected in the middle. The intention had been to have a high
terrace-road up to the castle, and the principal entrance had been made
in the tower, and arched over; but the terrace never having been formed,
the stone threshold of the main door was quite inacce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ladders, and the wide opening was left. The window-spaces of
the lower floor were merely closed up with boards, while on the second
story were some window-frames of beautifully carved wood, in which large
panes had once been placed, but they had got broken. In other windows
were temporary frames of rough deal, with small panes of muddy glass let
into them. A company of jackdaws sat on the top of the tower, looking
down in amazement on the strangers, and every now and then one flew off,
screaming loudly, to contemplate the intruders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A house for crows and bats, not for human beings," said Anton. "At
least, I see no way of getting into it."
The landlord now took them round the building. Behind, where the two
wings made a sort of horse-shoe, there were low entrances to the cellars
and offices; beneath which, again, were stables, great arched kitchens,
and small cells for the serfs. A wooden staircase led to the upper
story. The door turned creaking on its hinges, and a narrow passage took
them through a side wing to the front part of the house. There all was
at least magnificently planned. The circular entrance-hall--an arched
room of the old tower--was painted in mosaic, and through the great
doorway-opening was seen a wide expans
small disturbance made by the return of Anton had gradually settled
down. Those first-class treasures of Sabine's had made way for other
specimens of damask, still of a superior kind, it is true, but which
came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e elderly cousin's comprehension. She had
been quite right in prophesying that Anton would never remark those
signs of exuberant gratitude or their withdrawal. However, one change
had been permanently made--the greatest, the best of all changes--the
clerk retained a privileged place in the heart of the young mistress of
the firm, and his tall figure often appeared as one of the circle that
Sabine's fancy loved to gather round her when at her work-table or in
her treasure-chamber.
To-day she was walking restlessly up and down before dinner. The cousin,
who heard every thing, had just told her that a maid from Ehrenthal's
had run into the office to announce Bernhard's death to his friend. "How
will he bear it?" thought she. And the name of Ehrenthal forced her
thoughts back to the past, to one now far away, and to that painful hour
when the struggle going on in her own mind had been suddenly brought to
a close by a letter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parted. And Anton had known
of that conquered feeling of hers. How considerate he had always been,
how chivalrous, how helpful! She wondered if he had any idea of the
completeness of her triumph over a girlish illusion. She shook her head.
"No, he has not. It was here, at this very table, that an accident first
betrayed me to him. That past time still rises like a cloud between us.
Whenever I sit near Wohlfart of an evening, I am conscious of another's
shadow at my side; and when he speaks to me, his tone, his manner always
seem to say, 'You are not alone; he is with you.'" Sabine started, and
lovingly passed her hand over the beautiful flowers on the table before
her, as if to dispel a painful thought. She could not tell him that she
was free from that long-felt sorrow. Now, however, when he had lost a
friend whom he so much loved, she must show him that there were other
hearts that clung to him still. And again she walked up and down, trying
to devise a way of speaking to him alone.
Dinner was announced. Anton came with the rest, and took his place at
once. There was no opportunity of exchanging a word during the meal, but
he often met her sad and sympathizing eye. "He eats nothing at all
to-day," whispered her cousin; "not even any of the roast," she added,
reproachfully. Sabine was much perturbed. Mr. Jordan had already risen;
Anton would leave the room with the rest, and she should not see him
again the whole day through. So she called out, "The great Calla is
fully blown now. You were admiring the buds the other day; will you
remain a moment; I should like to show it you?" Anton bowed and staid
behind. A few more awkward moments, then her brother rose too; and,
hurrying to Anton, she took him to the room where the flowers were.
"You have had sorrowful tidings to-day," she began.
"The tidings themselves did not surprise me," replied Anton. "The doctor
gave no hope. But I lose much in him."
"I never saw him," said Sabine; "but I know from you that his life was
lonely--poor in affection and in enjoyment."
She moved an arm-chair toward Anton, and led him on to talk about his
friend. She listened to every word with warm sympathy, and well knew
what to ask and how to comfort. It was a relief to Anton to speak of the
departed one, to describe his quiet way of life, his erudition, his
poetical enthusiasm. After a pause, Sabine looked up frankly into his
face, and asked, "Have you any tidings of Herr von Fink?"
It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his departure that she had ever breathed his
name. Anton felt how touching her confidence was, given in this hour of
his sadness. In his emotion, he seized her hand, which she was slow in
withdrawing.
"He is not happy in his new life," he gravely replied. "There was a
savage humor in his last letter, from which I gather, even more than
from his actual words, that the business into which his uncle's death
has thrown him does not suit him."
"It is unworthy," cried Sabine.
"At all events, it is not what would be recognized as honorable in this
house," replied Anton. "Fink is upright, and has lived too long with
your brother to take pleasure in the wild speculations so common on the
other side the Atlantic. His partners and colleagues are for the most
part men without a conscience, and his feelings revolt against their
companionship."
"And can Herr von Fink tolerate such relations as these for a day?"
"It is a remarkable thing that he whose own will was ever so arbitrarily
exercised, should now be obliged against that will to obey a pressure
from without, and every where to work with his hands tied. The
organization of such speculations in America is so complicated that one
shareholder can do little to alter it; and, now that Fink has attained
what used to be the goal of his wishes--a large capital, and the
management of immense districts--his condition appears more uncertain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He was always in danger of thinking slightingly
of others, now I am distressed at the bitter contempt he expresses for
his own life. His last letter paints an intolerable state of things, and
seems to point to some decisive resolve."
"There is only one resolve for him," cried Sabine. "May I ask what you
said to him in reply?"
"I entreated him instantly, come what would, to free himself from the
business in which he was entangled. I said that his own strong will
might find a way of extrication, even if that which I pointed out proved
impracticable. Then I begged of him either to carry out his old plan of
becoming a landed proprietor in America, or to return to us."
"I knew that you would write thus," said Sabine, drawing a long breath.
"Yes, Wohlfart, he shall return," said she, gently, "but he shall not
return to us."
Anton was silent.
"And do you think that Herr von Fink will follow your advice?"
"I do not know. My advice was not very American."
"But it was worthy of you," cried Sabine, with proud delight.
"An officer wishes to speak to Mr. Wohlfart," said a servant at the
door.
Anton sprang up. Sabine went to her flowers and bent mournfully over
them. The shadows of others hovered still between her friend and her.
The few words spoken by the servant filled Anton with a vague terror. He
hurried into the ante-room: there stood Eugene von Rothsattel. Anton was
gladly rushing forward to greet him, but the young soldier's face of
agony made him start back. He whispered, "My mother wishes to speak to
you; something dreadful has occurred." Anton caught up his hat, ran into
the office, hurriedly asked Baumann to excuse him to the principal, and
then accompanied the lieutenant to the baron's house.
On the way, Eugene, who had lost all self-command, said unconnectedly to
Anton, "My father last night accidentally wounded himself by a
pistol-shot--a messenger was sent to summon me--when I came, I found my
mother in a swoon--my sister and I do not know what to do--Lenore
implored my mother on her knees to send for you--you are the only one in
whom w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our distress--I understand nothing about
business, but my father's affairs must be in a dreadful state--my mother
is beside herself--the whole house is in the greatest disorder."
From what Eugene said and what he did not say; from his broken sentences
and his look of agony, Anton guessed at the horrors of the previous
evening. In the boudoir of the baroness he found Lenore, weeping and
exhausted.
"Dear Wohlfart!" cried she, taking his hand and beginning again to sob,
while her head sank powerless on his shoulder.
Meanwhile Eugene walked up and down, wringing his hands, and at length
throwing himself on the sofa, he gave himself up to silent tears.
"It is horrible, Mr. Wohlfart," said Lenore, lifting up her head. "No
one may approach my father--Eugene may not, nor I--only my mother and
old John are with him; and early this morning the merchant Ehrenthal was
here, insisting that he must see my father. He screamed at my mother,
and called my father a deceiver, till she fainted away. When I rushed
into the room, the dreadful man went off threatening her with his
clenched fist."
Anton led Lenore to a chair and waited till she had told him all.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comforting in this case, and his own heart was
wrung to the utmost by the misery he witnessed.
"Call my mother, Eugene," said Lenore, at length.
Her brother left the room.
"Do not forsake us," implored Lenore, clasping her hands; "we are at the
last gasp; even your help can not save us."
"He is dead who might perhaps have done so," mournfully replied Anton.
"Whether I can be of any use I know not, but you can not doubt my
willingness to be so."
"No," cried Lenore. "And Eugene, too, thought of you at once."
The baroness now entered. She walked wearily; but, steadying herself by
a chair, she saluted Anton with dignity. "In our position," said she,
"we need a friend who knows more of business than we three do.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prevents the baron--possibly for a long time to
come--from managing his own affairs, and, little as I understand them, I
can see that our interests require prompt measures. My children have
mentioned you to me, but I fear I am unreasonable in asking you to
devote your time to our service."
She sat down, beckoned Anton to take a chair, and said to her children,
"Leave us; I shall be better able to tell Mr. Wohlfart the little that I
know when I do not see your grief."
When they were alone, she motioned him nearer and tried to speak, but
her lips quivered, and she hid her face in her handkerchief.
"Before I can consent, gracious lady," said he, "to your reposing in me
such confidence as this, I must first inquire whether the baron has no
relative or intimate friend to whom you could with less pain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I pray you to remember that my own knowledge of business
is but small, and my position not one to constitute me a proper
counselor to the baron."
"I know no one," said the baroness, hopelessly. "It is less painful to
me to tell you what I can not conceal, than to one of our own circle.
Consider yourself a physician sent for to visit a patient. The baron has
this morning told me some particulars of his present circumstances." And
then she proceeded to relate what she had gathered as to the nature of
his embarrassments, the danger in which the family property was placed,
and the capital needed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Polish estate.
"My husband," continued she, "has given me the key of his desk, and he
wishes Eugene, with the help of a man of business, to go over his
papers. I now request of you to make this examination together with my
son. When you need explanations, I will try to obtain them from the
baron. The question is now, whether you are inclined to undertake this
trouble for us, who are only strangers."
"I am most willing to do so," earnestly replied Anton; "and I hope that
the kindness of my principal will allow me the time needful for the
purpose, if you do not consider it more advisable to depute the baron's
experienced legal adviser to the task."
"There will be an opportunity of asking that gentleman's advice later,"
said the baroness.
Anton rose. "When do you wish to begin?"
"Immediately. I fear there is not a day to lose. I shall do all I can to
help you look the papers over." She led Anton into the next room, called
in Eugene, and unlocked the baron's desk. As she opened it she lost her
self-command for a moment, and moving to the window, the quivering of
the curtains betrayed the anguish that shook her fragile frame.
The mournful task began. Hour after hour passed. Eugene was in no
condition to peruse any thing, but his mother reached letters and
documents to Anton, and, though often obliged to desist a while, she
bravely returned to the task. Anton placed the papers in order, and
sought, by glancing over each, to arrive at least at a superficial view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It was evening, when the old servant opened the door in dismay, and
called out, "He is there again." The baroness could not repress a slight
scream, and made a gesture of aversion.
"I have told him that no one is at home, but he will not be dismissed;
he makes such a noise on the steps. I can not get rid of him."
"It will kill me if I hear his voice again," murmured the baroness.
"If the man be Ehrenthal," said Anton, rising, "I will try to get him
away. We have now done what was most necessary; have the goodness to
lock up these papers, and to allow me to return to-morrow." The baroness
silently assented, and sank back in her chair. Anton hurried off to the
ante-room, whence he could hear Ehrenthal's loudly-raised voi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usurer shocked him. His hat pushed half off his
head, his pale face swelled as if by drinking, his glazed eyes red with
tears, Ehrenthal stood before him, calling in broken sentences for the
baron, wailing and cursing alternately. "He must come! he must come at
once!" cried he; "the wicked man! A nobleman, indeed! he is a vagabond,
after whom I will send the police. Where is my money? Where is my
security? I want my mortgage from this man who is not at home."
Anton went straight up to him, and asked, "Do you know me, Mr.
Ehrenthal?" Ehrenthal turned his glazed eyes upon him, and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 friend of his dead son.
"He loved you!" he cried, in a lamentable voice. "He spoke to you more
than to his father. You were the only friend that he had on earth. Have
you heard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house of Ehrenthal?" continued he, in
a whisper. "Just as they stole the papers he died. He died with a hand
like this," and clenching his fist he struck his forehead. "Oh my son!
my son! why didst not thou forgive thy father!"
"We will go to your son," said Anton, taking the arm of the old man, who
unresistingly allowed himself to be led back to his own house.
From thence Anton hurried to Councilor Horn, with whom he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It was late before he returned home. In the midst of his anxiety about
those whose prosperity had filled his imagination years before,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in their adversity, reposed in him, dilated his
breast with a feeling of pride. He burned with desire to help them, and
hoped that his zealous devotion might yet find some way of rescue. As
yet he saw none. Looking up at the great building before him, so firm
and secure, in the moonlight, a thought flashed into his mind. If any
man could help them, it was his principal. His keen eye would be able to
unravel all the dark secrets in which the baron was entangled, and his
iron strength of will would crush the villains who held the unfortunate
nobleman in their power. And then he had a noble nature; he always
decided on the right, without an effort or a struggle. Anton looked at
the first floor. The whole house-front was dark, but in a corner room a
light still burned. It was the private office of his chief.
With sudden resolve, Anton begged the servant to take him to Mr.
Schröter, who looked with amazement at the unexpected visitor, and asked
what brought him, and whether any thing had happened.
"I implore your counsel--I implore your help," cried Anton.
"For yourself or for others?" inquired the merchant.
"For a family with whom I have accidentally become connected. They are
lost if a strong hand does not ward off the impending catastrophe."
Anton then rapidly related the occurrences of the afternoon, and,
seizing his principal's hand in his emotion, cried, "Have pity upon the
unhappy ladies, and help them."
"Help them!" replied the merchant; "how can I? Have you been
commissioned to apply to me, or are you only following the impulse of
your own feelings?"
"I am not commissioned; it is only the interest that I take in the
baron's fate which leads me to you."
"And what right have you to inform me of facts communicated in strict
confidence to yourself by the baron's lady?" asked the merchant, dryly.
"I am committing no indiscretion in telling you what will, in a few
days, be no secret, even to strangers."
"You are unusually excited, otherwise you would not forget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hatever, does a man of business venture to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without the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Of course, I shall make no wrong use of what you have said, but it was
by no means business-like, Wohlfart, to be so open toward me."
Anton was silent, feeling, indeed, that his principal was right, but yet
it seemed hard to be blamed for reposing confidence at such a time as
this. The merchant walked silently up and down; at length, stopping
before Anton, he said, "I do not now inquire how you come to take so
warm an interest in this family. I fear it is an acquaintance you owe to
Fink."
"You shall hear all," said Anton.
"Not at present. I will now content myself with repeating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interfere in these affairs without being specially
applied to by the parties themselves. I may add that I by no means wish
for such an application, and do not disguise from you that, were it
made, I should probably decline to do any thing for the Baron
Rothsattel."
Anton's feelings were roused to the utmost. "The question is the rescue
of an honorable man, and of lovely and amiable women from the toils of
rogues and impostors. To me, this seems the duty of every one; I, at
least, consider it a sacred obligation which I dare not shrink from. But
without your support I can do nothing."
"And how do you think this embarrassed man can be helped?" inquired the
merchant, seating himself.
With somewhat more composure, Anton repli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an experienced man of business making himself master of the case. There
must be some way of circumventing these villains. Your penetration would
discover it."
"Any attorney would be far more likely to do so, and the baron might
readily engage the services of experienced and upright legal advisers.
If his enemies have done any thing illegal, the quick eye of a lawyer is
the most likely to detect it."
"Alas! the baron's own lawyer gives but little hope," replied Anton.
"Then, my dear Wohlfart, no other is likely to do much good. Show me an
embarrassed man who has strength to grasp an offered hand, and bid me
help him, and for the sake of all I owe you, I will not refuse to do so.
I think you are convinced of this."
"I am," said Anton, dejectedly.
"From all I hear, however," the merchant went on,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the baron. From what I gather from general report, as well as from
you, his embarrassments arise from his having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usurers, which proves him deficient in what alone ennobles the life of
any man--good sense, and the power of steady exertion."
Anton could only sigh his assent.
"To help such a man," inexorably continued the merchant, "is a futile
attempt, against which reason may well protest. We are not to despair of
any, but want of strength is the most hopeless case of all. Our power of
laboring for others being limited, it becomes our duty to inquire,
before we devote our time to the weak, whether we are not thus
diminishing our chances of helping better men."
Anton interrupted him. "Does he not deserve every allowance to be made
for him? He was brought up to exact much; he has not learned, as we
have, to make his way by his own labor."
The merchant laid his hand on the young man's shoulder. "The very
reason. Believe me, a large number of these landed gentry, who pay the
penalty of their old family memories, are beyond help. I am the last to
deny that many worthy and admirable men belong to this class. Indeed,
wherever remarkable talent or nobility of character shoots up among
them, no doubt their position offers peculiar scope for its development,
but for average men it is not a favorable one. He who considers it his
hereditary privilege to enjoy life, and who assumes a distinguished
position in virtue of his family, will very often fail to put forth his
whole strength in order to deserve that position. Accordingly, numbers
of our oldest families are declining, and their fall will be no loss to
the state. Their family associations make them haughty without any
right to be so--limit their perceptions and confuse their judgment."
"Even if all this be true," cried Anton, "it does not absolve us from
helping individuals of the class who have excited our sympathy."
"No," said the principal, "if it be excited. But it does not glow so
rapidly in advancing years as in youth. The baron has endeavored to
isolate his property from the current of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leave it forever to his family. Forever! You, as a merchant, know how to
estimate the attempt. True, every rational man must allow it to be
desirable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same soil should be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We all prize what our forefathers have possessed before
us, and Sabine would unlock every room in this house with pride, because
her great-great-grandmother turned the same keys before her. It is
therefore natural that the landed proprietor should desire to preserve
those familiar scenes, which are the source of his own prosperity, to
those nearest and dearest to him. But there must be means to this end,
and these means are the making his own existence available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increase of his patrimony. Where energy dies in families
or individuals, then it is well that their means die too, that their
money should circulate through other hands, and their plowshare pass to
those who can guide it better. A family that has become effete through
luxury ought to sink down into common life, to make room for the
uprising of fresh energies and faculties. Every one who seeks, at the
cost of free activity for others, to preserve permanent possessions and
privileges for himself or his family, I must look upon as an enemy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social state. And if such a man ruin
himself in his endeavors, I should feel no malicious pleasure in his
downfall, but I should say that he is rightly served, because he has
sinned against a fundamental law of our social being; consequently, I
should consider it doubly wrong to support this man, because I could but
fear that I should thus be supporting an unsound condition of the body
politic."
Anton looked down mournfully. He had expected sympathy and warm
concurrence, and he met with disaffection and coldness that he despaired
of conquering. "I can not gainsay you," he at length replied; "but in
this case I can not feel as you do. I have been witness to the
unspeakable distress in the baron's family, and my whole soul is full
of sadness and sympathy, and of the wish to do something for those who
have opened their heart to me. After what you have said, I dare no
longer ask you to trouble yourself with their affairs, but I have
promised the baroness to assist her as far as my small powers permit,
and your kindness allows. I implore you to grant me permission to do
this. I shall endeavor to be regular in my attendance at the office, but
if during the next few weeks I am occasionally absent, I must ask you to
excuse me."
Once more the merchant walked up and down the room, and then, looking at
Anton's excited face, with deep seriousness and something of regret, he
replied, "Remember, Wohlfart, that every occupation which excites the
mind soon obtains a hold over a man, which may retard as well as advance
his success in life. It is thi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 to agree
to your wishes."
"I know it," said Anton, in a low voice; "but I have now no choice
left."
"Well, then, do what you must," said the merchant, gloomily; "I will lay
no hinderance in your way; and I hope that after a few weeks you will be
able to consider the whole circumstances more calmly." Anton left the
room, and the merchant stood looking long with frowning brow at the
place his clerk had occupied.
Nor was Anton in a more congenial mood. "So cold, so inexorable!"
exclaimed he, as he reached his own room. He began to suspect that his
principal was more selfish and less kindly than he had hitherto
supposed. Many an expression of Fink's recurred to his mind, as well as
that evening when young Rothsattel, in his boyish conceit, had spoken
impertinently to the merchant. "Is it possible," thought he, "that that
rude speech should be unforgotten?" And his chief's keen, deep-furrowed
face lost inexpressibly by contrast with the fair forms of the noble
ladies. "I am not wrong," he cried to himself; "let him say what he
will, my views are more just than his, and henceforth my destiny shall
be to choose for myself the way in which I shall walk." He sat long in
the darkness, and his thoughts were gloomy as it; then he went to the
window to look down into the dark court below. A great white blossom
rose before him like a phantom. Striking a light, he saw that it was the
beautiful Calla out of Sabine's room. It hung down mournfully on its
broken stem. Sabine had had it placed there. This little circumstance
struck him as a mournful omen.
Meanwhile Sabine, taper in hand, entered her brother's room.
"Good-night, Traugott," nodded she. "Wohlfart has been with you this
evening; how long he staid!"
"He will leave us," replied the merchant, gloomily.
Sabine started and dropped her taper on the table. "For God's sake, what
has happened? Has Wohlfart said that he was going away?"
"I do not yet know it, but I see it coming step by step; and I can not,
and still less can you, do any thing to retain him. When he stood before
me here with glowing cheeks and trembling voice, pleading for a ruined
man, I found out what it was that lured him away."
"I do not understand you," said Sabine, looking full at her brother.
"He chooses to become the confidential friend of a decayed noble. A pair
of bright eyes draws him away from us: it seems to him a worthy object
of ambition to become Rothsattel's man of business. This intimacy with
nobility is the legacy bequeathed to him by Fink."
"And you have refused to help him?" inquired Sabine, in a low voice.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said the merchant, harshly; and he
turned to his writing-table.
Sabine slowly withdrew. The taper trembled in her hand as she passed
through the long suite of rooms listening to her own footfall, and
shuddering as the feeling came over her that an invisible companion
glided by her side. This was the revenge of that other. The shadow that
once fell on her innocent life now drove her friend away from their
circle. Anton's affections clung to another. She had but been in his
eyes a mere stranger, who had once loved and languished for one now far
away, and who now, in widow's weeds, looked back regretfully to the
feelings of her youth.
The few next weeks were spent by Anton in over-hard work. He had great
difficulty in keeping up his counting-house duties, while he spent every
spare hour in conference with the baroness and the lawyer.
In the mean time, the misfortunes of the baron ran their course. He had
not been able to pay the interest of the sums with which his estate was
burdened. When last they were due, a whole series of claims was brought
against him, and the estate fell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district authorities. Complicated lawsuits arose. Ehrenthal complained
loudly, claiming the first mortgage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nay, he
was inclined to advance claims on the last mortgage offered by the baron
in the recent fatal hour. Löbel Pinkus also appeared as claimant of the
first mortgage, and asserted that he had paid the whole sum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Ehrenthal had no proof to bring forward, and had been
for some weeks past quite unable to manage his own affairs, while
Pinkus, on the contrary, fought with every weapon a hardened sinner can
devise or employ, and the deeds which the baron had executed at Veitel's
suggestion proved to be so capital a master-stroke of the cunning
advocate, that the baron's man of business had, from the first, little
hope of the case. We may here observe that Pinkus did eventually win it,
and that the mortgage was made over to him.
Anton was now gradually gaining some insight into the baron's
circumstances. But the double sale of the first mortgage was still kept
a secret by the latter, even from his wife. He declared Ehrenthal's
claim unfounded, and even expressed a suspicion that he had himself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robbery in his office. Indeed, he really
believed this. Then the name of Itzig was never broached, and the
suspicion against Ehrenthal, which the baron's lawyer shared, prevented
Anton seeking any explanation from him.
Meanwhile, an estrangement had sprung up between our hero and his
principal, which the whole counting-house remarked with surprise. The
merchant scowled at Anton's vacant seat when the latter chanced to be
absent during office-hours, or looked coldly at his clerk's face, made
pale as it was with excitement of mind and night-work. He took no notice
of his new occupation, and never seemed to remark him. Even to his
sister he maintained a stiff-necked silence; nor could all her attempts
lead him to speak of Anton, who, on his side, felt his heart revolt
against this coldness. After his return, to be treated like a child of
the house, praised, promoted, petted, and now to be treated like a mere
hireling, who is not worth the bread thrown to him; to be a toy of an
incomprehensible caprice--this, at least, he had not deserved; so he
became reserved toward the whole family, and sat silent at his desk; but
he fel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now and the then so keenly, that often,
when alone, he would spring up and stamp on the ground in the bitter
indignation of his heart.
One comfort remained. Sabine was not estranged. True, he saw little of
her, and at dinner she seemed to avoid speaking to him, but he knew that
she was on his side.
A few days after his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the merchant, she came down
stairs as he stood in the hall, and had to pass him by so closely that
her dress touched him. He had retreated, and made a formal bow, but she
looked at him imploringly, and whispered, "You must not be estranged
from me." It was an affair of a moment, but the faces of both were
radiant with a happy understanding.
The time had now arrived when Mr. Jordan was to quit the firm. The
principal again called Anton into his little office, and without any
severity, but also without a trace of his former cordiality, began: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o you my intention of appointing you Jordan's
successor; but,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your time has been more taken
up with other business than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such a post, I
therefore ask you whether you are now at liberty to undertake Jordan's
duties?"
"I am not," replied Anton.
"Can you name any--not very distant--time when you will be free from
your present occupation? In that case I will endeavor to find a
substitute until then."
Anton sorrowfully replied, "I can not at present say when I shall again
be master of my whole time; and, besides, I feel that, even as it is, I
tax your indulgence by many irregularities. Therefore, Mr. Schröter, I
beg that you will fill up this post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me."
The merchant's brow grew furrowed and dark, and he silently bowed
assent. Anton felt as he closed the door that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m was now complete, and, resuming his place, he leaned his throbbing
head on his hand. A moment later Baumann was summoned to the principal,
and Jordan's situation conferred upon him. On returning to the office,
he went up to Anton and whispered, "I refused at first, but Mr. Schröter
insisted. I am doing you an injustice." And that evening Mr. Baumann, in
his own room, read in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the chapters treating of
the unjust Saul (the principal), and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Jonathan
and the persecuted David, and strengthened his heart thereby.
The next day Anton was summoned to the baroness. Lenore and her mother
sat before a large table covered with jewel-boxes and toilette elegances
of every description, while a heavy iron chest stood at their feet. The
curtains were drawn, and the subdued light shone softly into the richly
furnished room. On the carpet glowed wreaths of unfading flowers, and
the clock ticked cheerfully in its alabaster case. Under the shade of
flowering plants sat the two love-birds in their silvered cage, hopping
from perch to perch, screaming ceaselessly, or sitting up quietly close
to each other. The whole room was beauty and perfume. "For how long?"
thought Anton. The baroness rose. "We are already obliged to trouble you
again," said she; "we are engaged in a very painful occupation." On the
table were all manner of ornaments, gold chains, brilliants, rings,
necklaces, gathered into a heap.
"We have been looking out all that we can dispense with," said the
baroness, "and now pray you to undertake to sell these things for us. I
have been told that some of them are of value, and as we are now in much
need of money, we turn here for help."
Anton looked in perplexity at the glittering heap.
"Tell us, Wohlfart," cried Lenore, anxiously, "is this necessary? can it
be of any use? Mamma has insisted upon setting apart for sale all our
ornaments, and whatever plate is not in daily use. What I can give is
not worth talking of, but my mother's jewels are costly; many of them
were presents made to her in youth, which she shall not part with unless
you say that it is necessary."
"I fear," said Anton, gravely, "that it will prove so."
"Take them," said the baroness to Anton; "I shall be calmer when I know
that we have at least done what we could."
"But do you wish to part with all?" inquired Anton, anxiously. "Much
that is dear to you may have but little value in a jeweler's eyes."
"I shall never wear an ornament again," quietly replied the baroness.
"Take them all;" and, holding her hands before her eyes, she turned
away.
"We are torturing my mother," cried Lenore, hastily; "will you lock up
all that is on the table, and get them out of the house as soon as you
can?"
"I can not undertake the charge of these valuables," said Anton,
"without taking some measures to decrease my own responsibility. First
of all, I will in your presence make a short note of all you intrust to
me."
"What useless cruelty!" exclaimed Lenore.
"It will not take long."
Anton took out a few sheets from his pocket-book, and began to note down
the different articles.
"You shall not see it done, mother," said Lenore, drawing her mother
away, and then returning to watch Anton at his task.
"These preparations for the market are horrible," said she. "My mother's
whole life will be sold; some memory of hers is linked with every single
thing. Look, Wohlfart, the princess gave her this diamond ornament when
she married my father."
"They are magnificent brilliants," cried Anton, admiringly.
"This ring was my grandfather's, and these are presents of poor papa's.
Alas! no man can know how we love all these things. It was always a
festival to me when mamma put on her diamonds. Now we come to my
possessions. They are not worth much. Do you think this bracelet good
gold?" She held out her hand as she spoke.
"I do not know."
"It shall go with the rest," said Lenore, taking it off. "Yes, you are a
kind, good man, Wohlfart," continued she, looking trustfully into his
tearful eyes; "do not forsake us. My brother has no experience, and is
more helpless than we are. It is a frightful position for me. Before
mamma I do all I can to be composed, else I could scream and weep the
whole day through." She sank in a chair, still holding his hand. "Dear
Wohlfart, do not forsake us."
Anton bent over her, and looked with passionate emotion at the lovely
face that turned so trustfully to him in the midst of its tears.
"I will be helpful to you when I can," said he, in the fullness of his
heart. "I will be at hand whenever you need me. You have too good an
opinion of my information and my faculties; I can be of less assistance
to you than you suppose, but what I can, that I will do in any and every
possible way."
Their hands parted with a warm pressure; the affair was settled.
The baroness now returned. "Our lawyer was with me this morning," said
she; "and now I must ask for your opinion on another subject. He tells
me that there is no prospect of preserving the baron's family estate."
"At this time, when interest is high, and money difficult to get, none,"
replied Anton.
"And you, too, think that we must turn all our efforts toward preserving
the Polish property?"
"I do," was the answer.
"For that, also, money will be necessary. Perhaps I may be able through
my relatives to intrust you with a small sum, which, with the help of
that"--she pointed to the iron chest--"may suffice to cover the first
necessary expenses. I do not, however, wish to sell the jewels here, and
a journey to the residence would be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cure the
sum to which I have just alluded. The baron's lawyer has spoken most
highly of your capacity for business. It is his wish which now decides
me to make a proposal to you. Will you for the next few years, or, at
all events, until our greatest difficulties are over, devote your whole
time to our affairs? I have consulted my children, and they agree with
me in believing that in your assistance lies our only hope of rescue.
The baron, too, has come in to the plan. The question now is whether
your circumstances allow you to give your support to our unfortunate
family. We shall be grateful to you, whatever conditions you affix; and
if you can find any way of making our great obligations to you apparent
in the position you hold, pray impart it to me."
Anton stood petrified. What the baroness required of him was separation
from the firm, separation from his principal, and from Sabine! Had this
thought occurred to him before, when standing in Lenore's presence or
bending over the baron's papers? At all events, now that the words were
spoken, they shocked him. He looked at Lenore, who stood behind her
mother with hands clasped in supplication. At length he replied, "I
stand in a position which I can not leav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others.
I was not prepared for this proposal, and beg to have time allowed me
for consideration. It is a step which will decide my whole future life."
"I do not press you," said the baroness; "I only request your
consideration. Whatever your decision be, our warmest gratitude will
still be yours; if you are unable to uphold our feeble strength, I fear
that we shall find no one to do so. You will think of that," she added,
beseechingly.
Anton hurried through the street with throbbing pulse. The noble lady's
glance of entreaty, Lenore's folded hands, beckoned him out of the
gloomy counting-house into a sphere of greater liberty, into a new
future, from whose depths bright images flashed out upon his fancy. A
request had been frankly made, and he was strongly inclined to justify
the confidence that prompted it. Those ladies required an unwearied,
self-sacrificing helper to save them from utter ruin, and if he
followed his impulse he should be doing a good work--fulfilling a duty.
In this mood he entered the merchant's dwelling. Alas! all that he saw
around him seemed to stretch out a hand to detain him. As he looked at
the warehouse, the good-humored faces of the porters, the chains of the
great scales, the hieroglyphics of the worthy Pix, again he felt that
this was the place that he belonged to. Sabine's dog kissed his hand,
and ran before him to his room--his and Fink's room. Here the childish
heart of the orphan boy had found a friend, kind companions, a home, a
definite and honorable life-purpose. Looking down through his window on
all the long-familiar objects, he saw a light in Sabine's store-chamber.
How often he had sought for that light, which brightened the whole great
building, and brought a sense of comfort and cheerfulness even into his
room. He now sprang up suddenly, and said to himself, "She shall
decide."
Sabine started in amazement when Anton appeared before her. "I am
irresistibly impelled to seek you," cried he. "I have to decide upon my
future life, and I feel undetermined, and unable to trust to my own
judgment. You have always been a kind friend to me since the day of my
arrival. I am accustomed to look up to you, and to think of you in
connection with all that interests me here. Let me hear your opinion
from your own lips. The Baroness Rothsattel has to-day proposed to me
permanently to undertake the situation of confidential adviser and
manager of the baron's affairs. Shall I accept; or shall I remain here?
I know not--tell me what is right both for myself and others."
"Not I," said Sabine, drawing back and growing very pale. "I can not
venture to decide in the matter. Nor do you wish me to do so, Wohlfart,
for you have already decided."
Anton looked straight before him and was silent.
"You have thought of leaving this house, and a wish to do so has sprung
out of the thought. And I am to justify you, and approve your resolve!
This is what you require of me," continued she, bitterly. "But this,
Wohlfart, I can not do, for I am sorry that you go away from us."
She turned away from him and leaned on the back of a chair.
"Oh, be not angry with me too!" said Anton; "that I can not bear. I have
suffered much of late. Mr. Schröter has suddenly withdrawn from me the
friendly regard that I long held my life's greatest treasure. I have not
deserved his coldness. What I have been doing has not been wrong, and
it was done with his knowledge. I had been spoiled by his kindness; I
have the more deeply felt his displeasure. My only comfort has been that
you did not condemn me. And now, do not you be cold toward me, else I
shall be wretched forever. There is not a soul on earth to whom I can
turn for affectionate comprehension of my difficulties. Had I a sister,
I should seek her heart to-day. You do not know what to me, lonely as I
am, your smile, your kindly shake of the hand has been till now. Do not
turn coldly from me, I beseech you."
Sabine was silent. At length she inquired, still with averted face,
"What draws you to those strangers; is it a joyful hope, is it sympathy
alone? Give this question close consideration before you answer it to
yourself at least."
"What it is that makes it possible for me to leave this house," said
Anton, "I do not myself know. If I can give a name to my motives, it is
gratitude felt toward one. She was the first to speak kindly to the
wandering boy on his way out into the world. I have admired her in the
peaceful brightness of her former life. I have often dreamed childish
dreams about her. There was a time when a tender feeling for her filled
my whole heart, and I then believed myself forever the slave of her
image. But years bring changes, and I learned to look on men and on life
with other eyes. Then I met her again, distressed, unhappy, despairing,
and my compassion became overmastering. When I am away from her, I know
that she is nothing to me; when I am with her, I feel only the spell of
her sorrow. Once, when I had to depart out of her circle like a culprit,
she came to me, and before the whole scornful assembly she gave me her
hand and acknowledged me her friend; and now she comes and asks for my
hand to help her father. Can I refuse it? Is it wrong to feel as I do? I
know not, and no one can tell me--no one but you alone."
Sabine's head had sunk down to the back of the chair on which she bent.
She now suddenly raised it, and with tearful eyes, and a voice full of
love and sorrow, cried, "Follow the voice that calls you. Go, Wohlfart,
go."
CHAPTER XXVII.
On a cold October day, two men were seen driving through the latticed
gate of the town of Rosmin on toward the plain, which stretched out
before them monotonous and boundless. Anton sat wrapped in his fur coat,
his hat low on his forehead, and at his side was young Sturm, in an old
cavalry cloak, with his soldier's cap cocked cheerily on one side. In
front of them a farm-servant, squatted on a heap of straw, flogged on
the small horses. The wind swept the sand and straw from the
stubble-fields, the road was a broad causeway without ditches or hedges,
the horses had to wade alternately through puddles and deep sand. Yellow
sand gleamed through the scanty herbage in all directions wherever a
field-mouse had made her way to her nest or an active mole had done what
he could to diversify the unbroken plain. Wherever the ground sank,
stagnant water lodged, and there hollow willow-trees stretched their
crippled arms in the air, their boughs flapping in the wind, and their
faded leaves fluttering down into the muddy pool below. Here and there
stood a small dwarf pine, a resting-place for the crows, who, scared by
the passing carriage, flew loudly croaking over the travelers' heads.
There was no house to be seen on the road, no pedestrian, and no
conveyance of any kind.
Karl looked every now and then at his silent companion, and said at
last, pointing to the horses, "How rough their coats are, and how pretty
their gray mouse skins! I wonder how many of these beasties would go to
make up my sergeant's horse! When I took leave of my father, the old man
said, 'Perhaps I shall pay you a visit, little one, when they light the
Christmas-tree.' 'You'll never be able,' said I. 'Why not?' asked he.
'You'll never trust yourself in any post-chaise.' Then the old boy
cried, 'Oho! post-chaises are always of a stout build; I shall be sure
to trust myself in one.' But now, Mr. Anton, I see that my father never
can pay us a visit."
"Why not?"
"It is possible that he may reach Rosmin; but, as soon as he sees these
horses and this road, he will instantly turn back. 'Shall I trust
myself,' he'll say, 'in a district where sand runs between one's legs
like water, and where mice are put into harness? The ground is not firm
enough for me.'"
"The horses are not the worst things here," said Anton, absently. "Look!
these go fast enough."
"Yes," replied Karl, "but they don't go like regular horses; they
entangle their legs like two cats playing in a parsley-bed. And what
things they have for shoes--regular webbed hoofs, I declare, which no
blacksmith can ever fit."
"If we could only get on!" returned Anton; "the wind blows cold, and I
am shivering in spite of my fur."
"You have slept but little the last few nights, sir," said Karl. "The
wind blows here as if over a threshing-floor. The earth is not round
hereabouts as elsewhere, but flat as a cake. This is a complete desert;
we have been driving for more than an hour, and there is not a village
to be seen."
"A desert indeed," sighed Anton; "let us hope it may improve." They
relapsed into profound silence. At length the driver stopped near a
pool, unharnessed the horses, and led them to the water's edge, without
noticing the travelers.
"What the deuce does this mean?" cried Karl, jumping down from the
carriage.
"I am going to feed," replied the servant, sulkily, in a foreign accent.
"I am anxious to know how that will be done," said Karl. "There is not
the shadow of a bag of provender."
The horses, however, soon proved that they could live without corn; they
stretched down their shaggy heads, and began to pull the grass and weeds
at the edge of the pool, sometimes taking a draught of the dirty water.
Meanwhile the servant drew a bundle from under his seat, settled himself
under the lee of an alder-bush, and, taking his knife, cut his bread and
cheese without even glancing at the travelers.
"I say, Ignatius or Jacob," cried Karl, sharply, "how long will this
breakfast of yours last?"
"An hour," replied the man, munching away.
"And how far is it from here to the estate?"
"Six miles, or maybe more."
"You can make nothing of him," said Anton; "we must put up with the
customs of the country;" and, leaving the carriage, they went to look on
at the horses feeding.
Anton is on his way to the Polish property. He is now the baron's agent.
Anxious months have the last proved to him. The parting from his
principal and the firm had been painful in the extreme. For some time
before it, indeed, Anton had found himself alone in the midst of his
colleagues. The quiet Baumann still remained his friend, but the others
considered him a castaway. The merchant received his resignation with
icy coldness; and even in the hour of parting, his hand lay impassive as
metal in Anton's grasp. Since then, our hero had undertaken several
journeys to the capital and to creditors in the family's behalf, and now
he was on his way to set the new estate in order, accompanied by Karl,
whom he had induced to become the baron's bailiff.
Ehrenthal had, by the authority conferred on him,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from the time of the sale by auction, and hired the Polish
bailiff for the baron. There had been unfair dealings between them at
the time, and it was well known in Rosmin that the bailiff had sold off
a good deal, and been guilty of all sorts of frauds since, so that Anton
had even now no prospect of a quiet life.
"The hour is come when I may execute my commission," cried Karl, groping
in the straw under the seat. He drew out a large japanned tin case, and
carried it to Anton. "Miss Sabine gave me this in charge for you." He
then joyously opened the lid, produced the materials for an excellent
breakfast, a bottle of wine, and a silver goblet. Anton took hold of the
case.
"It has a very knowing look," said Karl. "Miss Sabine planned it
herself."
Anton examined it on all sides, and placed it carefully on a tuft of
grass; then he took up the goblet, and saw his initials engraved on it,
and underneath the words, "To thy welfare." Whereupon he forgot the
breakfast and all around him, and stood gazing at the goblet, lost in
thought.
"Do not forget the breakfast, sir," suggested Karl, respectfully.
"Sit down by me, my faithful friend; eat and drink with me. Leave off
your absurd politeness. We shall have but little, either of us, but what
we have we will share like brothers. Take the bottle if you have no
glass."
"There's nothing like leather," said Karl, taking a small leathern
drinking-cup out of his pocket. "As for 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t was
kindly meant, and I thank you; but there must be subordination, if it
were but for the sake of the others; and so, sir, be kind enough to let
me shake hands with you now, and then let things be as they were before.
Only look at the horses, Mr. Anton. My faith! the creatures devour
thistles."
Again the horses were harnessed, again they threw out their short legs
in the sand, and again the carriage rolled through the barren
district--first through an empty plain, next through a wretched
fir-wood, then past a row of low sand-hills, then over a tumble-down
bridge crossing a small stream.
"This is the property," said the driver, turning round, and pointing
with his whip to a row of dirty thatched roofs that had just come into
sight.
Anton stood up to look for the group of trees in which the Hall might be
supposed to stand. Nothing of the sort to be seen. The village was
deficient in all that adorns the home of the poorest German peasant--no
orchard, no hedged-in gardens, no lime-trees in the market-place.
"This is wretched," said he, sitting down again; "much worse than they
told us in Rosmin."
"The village looks as if under a curse," cried Karl; "no teams working
in the fields--not a cow or a sheep to be seen."
The farm-servant flogged his horses into an irregular gallop, and so
they passed through the rows of mud huts which constituted the village,
and arrived at the public house. Karl sprang from the carriage, opened
the tavern door, and called for the landlord. A Jew slowly rose from his
seat by the stove and came to the threshold. "Is the gendarme from
Rosmin come?" He is gone into the village. "Which is the way to the
farm-yard?"
The landlord, an elderly man with an intelligent countenance, described
the way in German and Polish, and remained standing at the
door--bewildered, Karl declared, by the sight of two human beings. The
carriage turned into a cross-road, planted on both sides with thick
bushes, the remains of a fallen avenue. Over holes, stones, and puddles,
it rattled on to a group of mud huts, which still had a remnant of
whitewash upon them. "The barns and stables are empty," cried Karl, "for
I see gaps in the roofs large enough to drive our carriage through."
Anton said no more; he was prepared for every thing. They drove through
a break between the stables into the farm-yard, a large irregular space,
surrounded on three sides by tumble-down buildings, and open to the
fields on the fourth. A heap of _débris_ lay there--lime and rotten
timber, the remains of a ruined barn. The yard was empty; no trace of
farm implements or human labor to be seen. "Which is the inspector's
house," inquired Anton, in dismay. The driver looked round, and at last
made up his mind that it was a small one-storied building, with straw
thatch and dirty windows.
At the noise of the wheels a man appeared on the threshold, and waited
phlegmatically till the travelers had dismounted, and were standing
close before him. He was a broad-shouldered fellow, with a bloated,
brandy-drinking face, dressed in a jacket of shaggy cloth, while behind
him peered the muzzle of an equally shaggy dog, who snarled at the
strangers. "Are you the steward of this property?"
"I am," replied the man, in broken German, without stirring from where
he was.
"And I am the agent of the new proprietor," said Anton.
"That does not concern me," growled the shaggy man, turning sharp round,
entering the house, and bolting the door within.
Anton was thoroughly roused. "Break the window in, and help me to catch
the rascal," cried he to Karl, who coolly seized a piece of wood, struck
the panes so as to make the rotten framework give way, and cleared the
opening at one leap. Anton followed him. The room was empty, so was the
next, and in it an open window--the man was gone.
"After him!" cried Karl, and dashed on in pursuit, while Anton looked
about the house and out-buildings. He soon heard the barking of a dog,
and saw Karl capture the fugitive. Hurrying to his help, he held the man
fast, while, with a kick, Karl sent the dog flying. They then contrived
to force the steward back to the house, though he kept striking out
violently all the way.
"Go to the tavern, and bring the gendarme and the landlord," cried Anton
to the driver, who, undisturbed by all that had been going on, had
meanwhile unpacked the carriage. The man accordingly drove leisurely
off, and the fugitive being got into the room, Karl found an old cloth,
and with it bound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I beg your pardon, sir,"
said he; "it is only for an hour or so, till the arrival of the Rosmin
gendarme, whom we have appointed to meet us."
Anton then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house, bu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found but the merest necessaries; no books nor papers of any kind. It
had doubtless been emptied already. A bundle projected from the
coat-pocket of the prisoner, which turned out to be receipts and legal
documents in Polish. In time, the driver returned with the landlord and
the armed policeman. The landlord stood at the door in some perplexity,
and the policeman explained in a few moments what remained to be done.
"You must make a statement to the local judge, and give the man up to
me. He shall go back in your carriage to Rosmin. You will do well to get
rid of him, for this is a wild country, and it will be safer for you to
have him at Rosmin than here, where he has friends and accomplices."
After a long search, a sheet of paper was found in a cupboard, the
statement made and submitted to the policeman, who shook his head a
little over the Polish composition, and the prisoner lifted into the
carriage, the gendarme taking his seat beside him, and saying to Anton,
"I have long expected something of the kind. You may have often occasion
to want me again." The carriage then drove away, and thus the property
came under Anton's administration. He felt as if cast on a desert
island.
His portmanteau and traveling effects were leaning against a mud wall,
and the Polish landlord was the only man who could give him and Karl any
information or advice in their forlorn condition.
Now that the steward was fairly gone, the landlord grew more
communicative, and showed himself serviceable and obliging. A long
conversation ensued, and its purport was what Anton had apprehended from
the warning given by the Commissary Walter and other Rosmin officials.
The inspector had,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done all he could in the
way of spoliation, rendered daring by a report which had found its way
from the town to the village, that the present proprietor would never be
able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estate. At last Anton said, "What that
wretched man has done away with he will have to account for; our first
care must be to preserve what is still to be found on the property. You
must be our guide to-day."
They then examined the empty buildings. Four horses and two
servants--they were gone into the wood--a few old plows, a pair of
harrows, two wagons, a britzska, a cellar full of potatoes, a few
bundles of hay, a little straw--the inventory did not take much time in
drawing up. The buildings were all out of repair, not through age, but
neglect.
"Where is the dwelling-house?" inquired Anton. The landlord led the way
out of the yard to the meadow--a broad plain, gradually sloping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brook. It had been a great pasture. The cattle had
trodden it down into holes; the snouts of greedy swine had rooted it up;
gray molehills and rank tufts of grass rose on all sides.
The landlord stretched out his hand. "There is the castle. This castle
i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he added, reverentially; "no
nobleman in the district has a stone house like that. All the gentry
here live in wood and mud buildings. Herr von Tarow, the richest of
them, has but a poor dwelling."
About three hundred yards from the last out-building rose a great brick
edifice, with a black slate roof and a thick round tower. Its gloomy
walls on this treeless pasture-land, without one trace of life around,
rose beneath the cloudy sky like a phantom fortress which some evil
spirit had evoked from the abyss--a station from which to blight all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The strangers approached it. The castle had fallen into ruins before the
builders had finished their task. The tower had stood there for ages. It
was built of unhewn stone, and had small windows and loop-holes. The
former lords of the land had looked down from its summit on the tops of
the trees, which then stretched far into the plain. They had then ruled
with a rod of iron the serfs who cultivated their land, and toiled and
died for them. Many an arrow had sped through those loop-holes at the
enemy storming below, and many a Tartar horse had been overthrown before
those massive walls. Years ago, a despot of the district had, in
expiation of former sins, begun to add to the gray tower the walls of a
holy monastery; but the monastery never got finished, and the useless
walls had already stood there long, when the late count took it into his
head to convert them into a lordly dwelling for his race, and to raise a
house unparalleled for magnificence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 front of the house was added on to both sides of the tower, which
projected in the middle. The intention had been to have a high
terrace-road up to the castle, and the principal entrance had been made
in the tower, and arched over; but the terrace never having been formed,
the stone threshold of the main door was quite inacce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ladders, and the wide opening was left. The window-spaces of
the lower floor were merely closed up with boards, while on the second
story were some window-frames of beautifully carved wood, in which large
panes had once been placed, but they had got broken. In other windows
were temporary frames of rough deal, with small panes of muddy glass let
into them. A company of jackdaws sat on the top of the tower, looking
down in amazement on the strangers, and every now and then one flew off,
screaming loudly, to contemplate the intruders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A house for crows and bats, not for human beings," said Anton. "At
least, I see no way of getting into it."
The landlord now took them round the building. Behind, where the two
wings made a sort of horse-shoe, there were low entrances to the cellars
and offices; beneath which, again, were stables, great arched kitchens,
and small cells for the serfs. A wooden staircase led to the upper
story. The door turned creaking on its hinges, and a narrow passage took
them through a side wing to the front part of the house. There all was
at least magnificently planned. The circular entrance-hall--an arched
room of the old tower--was painted in mosaic, and through the great
doorway-opening was seen a wide expans
small disturbance made by the return of Anton had gradually settled
down. Those first-class treasures of Sabine's had made way for other
specimens of damask, still of a superior kind, it is true, but which
came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e elderly cousin's comprehension. She had
been quite right in prophesying that Anton would never remark those
signs of exuberant gratitude or their withdrawal. However, one change
had been permanently made--the greatest, the best of all changes--the
clerk retained a privileged place in the heart of the young mistress of
the firm, and his tall figure often appeared as one of the circle that
Sabine's fancy loved to gather round her when at her work-table or in
her treasure-chamber.
To-day she was walking restlessly up and down before dinner. The cousin,
who heard every thing, had just told her that a maid from Ehrenthal's
had run into the office to announce Bernhard's death to his friend. "How
will he bear it?" thought she. And the name of Ehrenthal forced her
thoughts back to the past, to one now far away, and to that painful hour
when the struggle going on in her own mind had been suddenly brought to
a close by a letter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parted. And Anton had known
of that conquered feeling of hers. How considerate he had always been,
how chivalrous, how helpful! She wondered if he had any idea of the
completeness of her triumph over a girlish illusion. She shook her head.
"No, he has not. It was here, at this very table, that an accident first
betrayed me to him. That past time still rises like a cloud between us.
Whenever I sit near Wohlfart of an evening, I am conscious of another's
shadow at my side; and when he speaks to me, his tone, his manner always
seem to say, 'You are not alone; he is with you.'" Sabine started, and
lovingly passed her hand over the beautiful flowers on the table before
her, as if to dispel a painful thought. She could not tell him that she
was free from that long-felt sorrow. Now, however, when he had lost a
friend whom he so much loved, she must show him that there were other
hearts that clung to him still. And again she walked up and down, trying
to devise a way of speaking to him alone.
Dinner was announced. Anton came with the rest, and took his place at
once. There was no opportunity of exchanging a word during the meal, but
he often met her sad and sympathizing eye. "He eats nothing at all
to-day," whispered her cousin; "not even any of the roast," she added,
reproachfully. Sabine was much perturbed. Mr. Jordan had already risen;
Anton would leave the room with the rest, and she should not see him
again the whole day through. So she called out, "The great Calla is
fully blown now. You were admiring the buds the other day; will you
remain a moment; I should like to show it you?" Anton bowed and staid
behind. A few more awkward moments, then her brother rose too; and,
hurrying to Anton, she took him to the room where the flowers were.
"You have had sorrowful tidings to-day," she began.
"The tidings themselves did not surprise me," replied Anton. "The doctor
gave no hope. But I lose much in him."
"I never saw him," said Sabine; "but I know from you that his life was
lonely--poor in affection and in enjoyment."
She moved an arm-chair toward Anton, and led him on to talk about his
friend. She listened to every word with warm sympathy, and well knew
what to ask and how to comfort. It was a relief to Anton to speak of the
departed one, to describe his quiet way of life, his erudition, his
poetical enthusiasm. After a pause, Sabine looked up frankly into his
face, and asked, "Have you any tidings of Herr von Fink?"
It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his departure that she had ever breathed his
name. Anton felt how touching her confidence was, given in this hour of
his sadness. In his emotion, he seized her hand, which she was slow in
withdrawing.
"He is not happy in his new life," he gravely replied. "There was a
savage humor in his last letter, from which I gather, even more than
from his actual words, that the business into which his uncle's death
has thrown him does not suit him."
"It is unworthy," cried Sabine.
"At all events, it is not what would be recognized as honorable in this
house," replied Anton. "Fink is upright, and has lived too long with
your brother to take pleasure in the wild speculations so common on the
other side the Atlantic. His partners and colleagues are for the most
part men without a conscience, and his feelings revolt against their
companionship."
"And can Herr von Fink tolerate such relations as these for a day?"
"It is a remarkable thing that he whose own will was ever so arbitrarily
exercised, should now be obliged against that will to obey a pressure
from without, and every where to work with his hands tied. The
organization of such speculations in America is so complicated that one
shareholder can do little to alter it; and, now that Fink has attained
what used to be the goal of his wishes--a large capital, and the
management of immense districts--his condition appears more uncertain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He was always in danger of thinking slightingly
of others, now I am distressed at the bitter contempt he expresses for
his own life. His last letter paints an intolerable state of things, and
seems to point to some decisive resolve."
"There is only one resolve for him," cried Sabine. "May I ask what you
said to him in reply?"
"I entreated him instantly, come what would, to free himself from the
business in which he was entangled. I said that his own strong will
might find a way of extrication, even if that which I pointed out proved
impracticable. Then I begged of him either to carry out his old plan of
becoming a landed proprietor in America, or to return to us."
"I knew that you would write thus," said Sabine, drawing a long breath.
"Yes, Wohlfart, he shall return," said she, gently, "but he shall not
return to us."
Anton was silent.
"And do you think that Herr von Fink will follow your advice?"
"I do not know. My advice was not very American."
"But it was worthy of you," cried Sabine, with proud delight.
"An officer wishes to speak to Mr. Wohlfart," said a servant at the
door.
Anton sprang up. Sabine went to her flowers and bent mournfully over
them. The shadows of others hovered still between her friend and her.
The few words spoken by the servant filled Anton with a vague terror. He
hurried into the ante-room: there stood Eugene von Rothsattel. Anton was
gladly rushing forward to greet him, but the young soldier's face of
agony made him start back. He whispered, "My mother wishes to speak to
you; something dreadful has occurred." Anton caught up his hat, ran into
the office, hurriedly asked Baumann to excuse him to the principal, and
then accompanied the lieutenant to the baron's house.
On the way, Eugene, who had lost all self-command, said unconnectedly to
Anton, "My father last night accidentally wounded himself by a
pistol-shot--a messenger was sent to summon me--when I came, I found my
mother in a swoon--my sister and I do not know what to do--Lenore
implored my mother on her knees to send for you--you are the only one in
whom w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our distress--I understand nothing about
business, but my father's affairs must be in a dreadful state--my mother
is beside herself--the whole house is in the greatest disorder."
From what Eugene said and what he did not say; from his broken sentences
and his look of agony, Anton guessed at the horrors of the previous
evening. In the boudoir of the baroness he found Lenore, weeping and
exhausted.
"Dear Wohlfart!" cried she, taking his hand and beginning again to sob,
while her head sank powerless on his shoulder.
Meanwhile Eugene walked up and down, wringing his hands, and at length
throwing himself on the sofa, he gave himself up to silent tears.
"It is horrible, Mr. Wohlfart," said Lenore, lifting up her head. "No
one may approach my father--Eugene may not, nor I--only my mother and
old John are with him; and early this morning the merchant Ehrenthal was
here, insisting that he must see my father. He screamed at my mother,
and called my father a deceiver, till she fainted away. When I rushed
into the room, the dreadful man went off threatening her with his
clenched fist."
Anton led Lenore to a chair and waited till she had told him all.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comforting in this case, and his own heart was
wrung to the utmost by the misery he witnessed.
"Call my mother, Eugene," said Lenore, at length.
Her brother left the room.
"Do not forsake us," implored Lenore, clasping her hands; "we are at the
last gasp; even your help can not save us."
"He is dead who might perhaps have done so," mournfully replied Anton.
"Whether I can be of any use I know not, but you can not doubt my
willingness to be so."
"No," cried Lenore. "And Eugene, too, thought of you at once."
The baroness now entered. She walked wearily; but, steadying herself by
a chair, she saluted Anton with dignity. "In our position," said she,
"we need a friend who knows more of business than we three do.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prevents the baron--possibly for a long time to
come--from managing his own affairs, and, little as I understand them, I
can see that our interests require prompt measures. My children have
mentioned you to me, but I fear I am unreasonable in asking you to
devote your time to our service."
She sat down, beckoned Anton to take a chair, and said to her children,
"Leave us; I shall be better able to tell Mr. Wohlfart the little that I
know when I do not see your grief."
When they were alone, she motioned him nearer and tried to speak, but
her lips quivered, and she hid her face in her handkerchief.
"Before I can consent, gracious lady," said he, "to your reposing in me
such confidence as this, I must first inquire whether the baron has no
relative or intimate friend to whom you could with less pain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I pray you to remember that my own knowledge of business
is but small, and my position not one to constitute me a proper
counselor to the baron."
"I know no one," said the baroness, hopelessly. "It is less painful to
me to tell you what I can not conceal, than to one of our own circle.
Consider yourself a physician sent for to visit a patient. The baron has
this morning told me some particulars of his present circumstances." And
then she proceeded to relate what she had gathered as to the nature of
his embarrassments, the danger in which the family property was placed,
and the capital needed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Polish estate.
"My husband," continued she, "has given me the key of his desk, and he
wishes Eugene, with the help of a man of business, to go over his
papers. I now request of you to make this examination together with my
son. When you need explanations, I will try to obtain them from the
baron. The question is now, whether you are inclined to undertake this
trouble for us, who are only strangers."
"I am most willing to do so," earnestly replied Anton; "and I hope that
the kindness of my principal will allow me the time needful for the
purpose, if you do not consider it more advisable to depute the baron's
experienced legal adviser to the task."
"There will be an opportunity of asking that gentleman's advice later,"
said the baroness.
Anton rose. "When do you wish to begin?"
"Immediately. I fear there is not a day to lose. I shall do all I can to
help you look the papers over." She led Anton into the next room, called
in Eugene, and unlocked the baron's desk. As she opened it she lost her
self-command for a moment, and moving to the window, the quivering of
the curtains betrayed the anguish that shook her fragile frame.
The mournful task began. Hour after hour passed. Eugene was in no
condition to peruse any thing, but his mother reached letters and
documents to Anton, and, though often obliged to desist a while, she
bravely returned to the task. Anton placed the papers in order, and
sought, by glancing over each, to arrive at least at a superficial view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It was evening, when the old servant opened the door in dismay, and
called out, "He is there again." The baroness could not repress a slight
scream, and made a gesture of aversion.
"I have told him that no one is at home, but he will not be dismissed;
he makes such a noise on the steps. I can not get rid of him."
"It will kill me if I hear his voice again," murmured the baroness.
"If the man be Ehrenthal," said Anton, rising, "I will try to get him
away. We have now done what was most necessary; have the goodness to
lock up these papers, and to allow me to return to-morrow." The baroness
silently assented, and sank back in her chair. Anton hurried off to the
ante-room, whence he could hear Ehrenthal's loudly-raised voi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usurer shocked him. His hat pushed half off his
head, his pale face swelled as if by drinking, his glazed eyes red with
tears, Ehrenthal stood before him, calling in broken sentences for the
baron, wailing and cursing alternately. "He must come! he must come at
once!" cried he; "the wicked man! A nobleman, indeed! he is a vagabond,
after whom I will send the police. Where is my money? Where is my
security? I want my mortgage from this man who is not at home."
Anton went straight up to him, and asked, "Do you know me, Mr.
Ehrenthal?" Ehrenthal turned his glazed eyes upon him, and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 friend of his dead son.
"He loved you!" he cried, in a lamentable voice. "He spoke to you more
than to his father. You were the only friend that he had on earth. Have
you heard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house of Ehrenthal?" continued he, in
a whisper. "Just as they stole the papers he died. He died with a hand
like this," and clenching his fist he struck his forehead. "Oh my son!
my son! why didst not thou forgive thy father!"
"We will go to your son," said Anton, taking the arm of the old man, who
unresistingly allowed himself to be led back to his own house.
From thence Anton hurried to Councilor Horn, with whom he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It was late before he returned home. In the midst of his anxiety about
those whose prosperity had filled his imagination years before,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in their adversity, reposed in him, dilated his
breast with a feeling of pride. He burned with desire to help them, and
hoped that his zealous devotion might yet find some way of rescue. As
yet he saw none. Looking up at the great building before him, so firm
and secure, in the moonlight, a thought flashed into his mind. If any
man could help them, it was his principal. His keen eye would be able to
unravel all the dark secrets in which the baron was entangled, and his
iron strength of will would crush the villains who held the unfortunate
nobleman in their power. And then he had a noble nature; he always
decided on the right, without an effort or a struggle. Anton looked at
the first floor. The whole house-front was dark, but in a corner room a
light still burned. It was the private office of his chief.
With sudden resolve, Anton begged the servant to take him to Mr.
Schröter, who looked with amazement at the unexpected visitor, and asked
what brought him, and whether any thing had happened.
"I implore your counsel--I implore your help," cried Anton.
"For yourself or for others?" inquired the merchant.
"For a family with whom I have accidentally become connected. They are
lost if a strong hand does not ward off the impending catastrophe."
Anton then rapidly related the occurrences of the afternoon, and,
seizing his principal's hand in his emotion, cried, "Have pity upon the
unhappy ladies, and help them."
"Help them!" replied the merchant; "how can I? Have you been
commissioned to apply to me, or are you only following the impulse of
your own feelings?"
"I am not commissioned; it is only the interest that I take in the
baron's fate which leads me to you."
"And what right have you to inform me of facts communicated in strict
confidence to yourself by the baron's lady?" asked the merchant, dryly.
"I am committing no indiscretion in telling you what will, in a few
days, be no secret, even to strangers."
"You are unusually excited, otherwise you would not forget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hatever, does a man of business venture to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without the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Of course, I shall make no wrong use of what you have said, but it was
by no means business-like, Wohlfart, to be so open toward me."
Anton was silent, feeling, indeed, that his principal was right, but yet
it seemed hard to be blamed for reposing confidence at such a time as
this. The merchant walked silently up and down; at length, stopping
before Anton, he said, "I do not now inquire how you come to take so
warm an interest in this family. I fear it is an acquaintance you owe to
Fink."
"You shall hear all," said Anton.
"Not at present. I will now content myself with repeating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interfere in these affairs without being specially
applied to by the parties themselves. I may add that I by no means wish
for such an application, and do not disguise from you that, were it
made, I should probably decline to do any thing for the Baron
Rothsattel."
Anton's feelings were roused to the utmost. "The question is the rescue
of an honorable man, and of lovely and amiable women from the toils of
rogues and impostors. To me, this seems the duty of every one; I, at
least, consider it a sacred obligation which I dare not shrink from. But
without your support I can do nothing."
"And how do you think this embarrassed man can be helped?" inquired the
merchant, seating himself.
With somewhat more composure, Anton repli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an experienced man of business making himself master of the case. There
must be some way of circumventing these villains. Your penetration would
discover it."
"Any attorney would be far more likely to do so, and the baron might
readily engage the services of experienced and upright legal advisers.
If his enemies have done any thing illegal, the quick eye of a lawyer is
the most likely to detect it."
"Alas! the baron's own lawyer gives but little hope," replied Anton.
"Then, my dear Wohlfart, no other is likely to do much good. Show me an
embarrassed man who has strength to grasp an offered hand, and bid me
help him, and for the sake of all I owe you, I will not refuse to do so.
I think you are convinced of this."
"I am," said Anton, dejectedly.
"From all I hear, however," the merchant went on,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the baron. From what I gather from general report, as well as from
you, his embarrassments arise from his having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usurers, which proves him deficient in what alone ennobles the life of
any man--good sense, and the power of steady exertion."
Anton could only sigh his assent.
"To help such a man," inexorably continued the merchant, "is a futile
attempt, against which reason may well protest. We are not to despair of
any, but want of strength is the most hopeless case of all. Our power of
laboring for others being limited, it becomes our duty to inquire,
before we devote our time to the weak, whether we are not thus
diminishing our chances of helping better men."
Anton interrupted him. "Does he not deserve every allowance to be made
for him? He was brought up to exact much; he has not learned, as we
have, to make his way by his own labor."
The merchant laid his hand on the young man's shoulder. "The very
reason. Believe me, a large number of these landed gentry, who pay the
penalty of their old family memories, are beyond help. I am the last to
deny that many worthy and admirable men belong to this class. Indeed,
wherever remarkable talent or nobility of character shoots up among
them, no doubt their position offers peculiar scope for its development,
but for average men it is not a favorable one. He who considers it his
hereditary privilege to enjoy life, and who assumes a distinguished
position in virtue of his family, will very often fail to put forth his
whole strength in order to deserve that position. Accordingly, numbers
of our oldest families are declining, and their fall will be no loss to
the state. Their family associations make them haughty without any
right to be so--limit their perceptions and confuse their judgment."
"Even if all this be true," cried Anton, "it does not absolve us from
helping individuals of the class who have excited our sympathy."
"No," said the principal, "if it be excited. But it does not glow so
rapidly in advancing years as in youth. The baron has endeavored to
isolate his property from the current of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leave it forever to his family. Forever! You, as a merchant, know how to
estimate the attempt. True, every rational man must allow it to be
desirable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same soil should be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We all prize what our forefathers have possessed before
us, and Sabine would unlock every room in this house with pride, because
her great-great-grandmother turned the same keys before her. It is
therefore natural that the landed proprietor should desire to preserve
those familiar scenes, which are the source of his own prosperity, to
those nearest and dearest to him. But there must be means to this end,
and these means are the making his own existence available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increase of his patrimony. Where energy dies in families
or individuals, then it is well that their means die too, that their
money should circulate through other hands, and their plowshare pass to
those who can guide it better. A family that has become effete through
luxury ought to sink down into common life, to make room for the
uprising of fresh energies and faculties. Every one who seeks, at the
cost of free activity for others, to preserve permanent possessions and
privileges for himself or his family, I must look upon as an enemy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social state. And if such a man ruin
himself in his endeavors, I should feel no malicious pleasure in his
downfall, but I should say that he is rightly served, because he has
sinned against a fundamental law of our social being; consequently, I
should consider it doubly wrong to support this man, because I could but
fear that I should thus be supporting an unsound condition of the body
politic."
Anton looked down mournfully. He had expected sympathy and warm
concurrence, and he met with disaffection and coldness that he despaired
of conquering. "I can not gainsay you," he at length replied; "but in
this case I can not feel as you do. I have been witness to the
unspeakable distress in the baron's family, and my whole soul is full
of sadness and sympathy, and of the wish to do something for those who
have opened their heart to me. After what you have said, I dare no
longer ask you to trouble yourself with their affairs, but I have
promised the baroness to assist her as far as my small powers permit,
and your kindness allows. I implore you to grant me permission to do
this. I shall endeavor to be regular in my attendance at the office, but
if during the next few weeks I am occasionally absent, I must ask you to
excuse me."
Once more the merchant walked up and down the room, and then, looking at
Anton's excited face, with deep seriousness and something of regret, he
replied, "Remember, Wohlfart, that every occupation which excites the
mind soon obtains a hold over a man, which may retard as well as advance
his success in life. It is thi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 to agree
to your wishes."
"I know it," said Anton, in a low voice; "but I have now no choice
left."
"Well, then, do what you must," said the merchant, gloomily; "I will lay
no hinderance in your way; and I hope that after a few weeks you will be
able to consider the whole circumstances more calmly." Anton left the
room, and the merchant stood looking long with frowning brow at the
place his clerk had occupied.
Nor was Anton in a more congenial mood. "So cold, so inexorable!"
exclaimed he, as he reached his own room. He began to suspect that his
principal was more selfish and less kindly than he had hitherto
supposed. Many an expression of Fink's recurred to his mind, as well as
that evening when young Rothsattel, in his boyish conceit, had spoken
impertinently to the merchant. "Is it possible," thought he, "that that
rude speech should be unforgotten?" And his chief's keen, deep-furrowed
face lost inexpressibly by contrast with the fair forms of the noble
ladies. "I am not wrong," he cried to himself; "let him say what he
will, my views are more just than his, and henceforth my destiny shall
be to choose for myself the way in which I shall walk." He sat long in
the darkness, and his thoughts were gloomy as it; then he went to the
window to look down into the dark court below. A great white blossom
rose before him like a phantom. Striking a light, he saw that it was the
beautiful Calla out of Sabine's room. It hung down mournfully on its
broken stem. Sabine had had it placed there. This little circumstance
struck him as a mournful omen.
Meanwhile Sabine, taper in hand, entered her brother's room.
"Good-night, Traugott," nodded she. "Wohlfart has been with you this
evening; how long he staid!"
"He will leave us," replied the merchant, gloomily.
Sabine started and dropped her taper on the table. "For God's sake, what
has happened? Has Wohlfart said that he was going away?"
"I do not yet know it, but I see it coming step by step; and I can not,
and still less can you, do any thing to retain him. When he stood before
me here with glowing cheeks and trembling voice, pleading for a ruined
man, I found out what it was that lured him away."
"I do not understand you," said Sabine, looking full at her brother.
"He chooses to become the confidential friend of a decayed noble. A pair
of bright eyes draws him away from us: it seems to him a worthy object
of ambition to become Rothsattel's man of business. This intimacy with
nobility is the legacy bequeathed to him by Fink."
"And you have refused to help him?" inquired Sabine, in a low voice.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said the merchant, harshly; and he
turned to his writing-table.
Sabine slowly withdrew. The taper trembled in her hand as she passed
through the long suite of rooms listening to her own footfall, and
shuddering as the feeling came over her that an invisible companion
glided by her side. This was the revenge of that other. The shadow that
once fell on her innocent life now drove her friend away from their
circle. Anton's affections clung to another. She had but been in his
eyes a mere stranger, who had once loved and languished for one now far
away, and who now, in widow's weeds, looked back regretfully to the
feelings of her youth.
The few next weeks were spent by Anton in over-hard work. He had great
difficulty in keeping up his counting-house duties, while he spent every
spare hour in conference with the baroness and the lawyer.
In the mean time, the misfortunes of the baron ran their course. He had
not been able to pay the interest of the sums with which his estate was
burdened. When last they were due, a whole series of claims was brought
against him, and the estate fell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district authorities. Complicated lawsuits arose. Ehrenthal complained
loudly, claiming the first mortgage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nay, he
was inclined to advance claims on the last mortgage offered by the baron
in the recent fatal hour. Löbel Pinkus also appeared as claimant of the
first mortgage, and asserted that he had paid the whole sum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Ehrenthal had no proof to bring forward, and had been
for some weeks past quite unable to manage his own affairs, while
Pinkus, on the contrary, fought with every weapon a hardened sinner can
devise or employ, and the deeds which the baron had executed at Veitel's
suggestion proved to be so capital a master-stroke of the cunning
advocate, that the baron's man of business had, from the first, little
hope of the case. We may here observe that Pinkus did eventually win it,
and that the mortgage was made over to him.
Anton was now gradually gaining some insight into the baron's
circumstances. But the double sale of the first mortgage was still kept
a secret by the latter, even from his wife. He declared Ehrenthal's
claim unfounded, and even expressed a suspicion that he had himself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robbery in his office. Indeed, he really
believed this. Then the name of Itzig was never broached, and the
suspicion against Ehrenthal, which the baron's lawyer shared, prevented
Anton seeking any explanation from him.
Meanwhile, an estrangement had sprung up between our hero and his
principal, which the whole counting-house remarked with surprise. The
merchant scowled at Anton's vacant seat when the latter chanced to be
absent during office-hours, or looked coldly at his clerk's face, made
pale as it was with excitement of mind and night-work. He took no notice
of his new occupation, and never seemed to remark him. Even to his
sister he maintained a stiff-necked silence; nor could all her attempts
lead him to speak of Anton, who, on his side, felt his heart revolt
against this coldness. After his return, to be treated like a child of
the house, praised, promoted, petted, and now to be treated like a mere
hireling, who is not worth the bread thrown to him; to be a toy of an
incomprehensible caprice--this, at least, he had not deserved; so he
became reserved toward the whole family, and sat silent at his desk; but
he fel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now and the then so keenly, that often,
when alone, he would spring up and stamp on the ground in the bitter
indignation of his heart.
One comfort remained. Sabine was not estranged. True, he saw little of
her, and at dinner she seemed to avoid speaking to him, but he knew that
she was on his side.
A few days after his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the merchant, she came down
stairs as he stood in the hall, and had to pass him by so closely that
her dress touched him. He had retreated, and made a formal bow, but she
looked at him imploringly, and whispered, "You must not be estranged
from me." It was an affair of a moment, but the faces of both were
radiant with a happy understanding.
The time had now arrived when Mr. Jordan was to quit the firm. The
principal again called Anton into his little office, and without any
severity, but also without a trace of his former cordiality, began: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o you my intention of appointing you Jordan's
successor; but,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your time has been more taken
up with other business than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such a post, I
therefore ask you whether you are now at liberty to undertake Jordan's
duties?"
"I am not," replied Anton.
"Can you name any--not very distant--time when you will be free from
your present occupation? In that case I will endeavor to find a
substitute until then."
Anton sorrowfully replied, "I can not at present say when I shall again
be master of my whole time; and, besides, I feel that, even as it is, I
tax your indulgence by many irregularities. Therefore, Mr. Schröter, I
beg that you will fill up this post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me."
The merchant's brow grew furrowed and dark, and he silently bowed
assent. Anton felt as he closed the door that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m was now complete, and, resuming his place, he leaned his throbbing
head on his hand. A moment later Baumann was summoned to the principal,
and Jordan's situation conferred upon him. On returning to the office,
he went up to Anton and whispered, "I refused at first, but Mr. Schröter
insisted. I am doing you an injustice." And that evening Mr. Baumann, in
his own room, read in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the chapters treating of
the unjust Saul (the principal), and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Jonathan
and the persecuted David, and strengthened his heart thereby.
The next day Anton was summoned to the baroness. Lenore and her mother
sat before a large table covered with jewel-boxes and toilette elegances
of every description, while a heavy iron chest stood at their feet. The
curtains were drawn, and the subdued light shone softly into the richly
furnished room. On the carpet glowed wreaths of unfading flowers, and
the clock ticked cheerfully in its alabaster case. Under the shade of
flowering plants sat the two love-birds in their silvered cage, hopping
from perch to perch, screaming ceaselessly, or sitting up quietly close
to each other. The whole room was beauty and perfume. "For how long?"
thought Anton. The baroness rose. "We are already obliged to trouble you
again," said she; "we are engaged in a very painful occupation." On the
table were all manner of ornaments, gold chains, brilliants, rings,
necklaces, gathered into a heap.
"We have been looking out all that we can dispense with," said the
baroness, "and now pray you to undertake to sell these things for us. I
have been told that some of them are of value, and as we are now in much
need of money, we turn here for help."
Anton looked in perplexity at the glittering heap.
"Tell us, Wohlfart," cried Lenore, anxiously, "is this necessary? can it
be of any use? Mamma has insisted upon setting apart for sale all our
ornaments, and whatever plate is not in daily use. What I can give is
not worth talking of, but my mother's jewels are costly; many of them
were presents made to her in youth, which she shall not part with unless
you say that it is necessary."
"I fear," said Anton, gravely, "that it will prove so."
"Take them," said the baroness to Anton; "I shall be calmer when I know
that we have at least done what we could."
"But do you wish to part with all?" inquired Anton, anxiously. "Much
that is dear to you may have but little value in a jeweler's eyes."
"I shall never wear an ornament again," quietly replied the baroness.
"Take them all;" and, holding her hands before her eyes, she turned
away.
"We are torturing my mother," cried Lenore, hastily; "will you lock up
all that is on the table, and get them out of the house as soon as you
can?"
"I can not undertake the charge of these valuables," said Anton,
"without taking some measures to decrease my own responsibility. First
of all, I will in your presence make a short note of all you intrust to
me."
"What useless cruelty!" exclaimed Lenore.
"It will not take long."
Anton took out a few sheets from his pocket-book, and began to note down
the different articles.
"You shall not see it done, mother," said Lenore, drawing her mother
away, and then returning to watch Anton at his task.
"These preparations for the market are horrible," said she. "My mother's
whole life will be sold; some memory of hers is linked with every single
thing. Look, Wohlfart, the princess gave her this diamond ornament when
she married my father."
"They are magnificent brilliants," cried Anton, admiringly.
"This ring was my grandfather's, and these are presents of poor papa's.
Alas! no man can know how we love all these things. It was always a
festival to me when mamma put on her diamonds. Now we come to my
possessions. They are not worth much. Do you think this bracelet good
gold?" She held out her hand as she spoke.
"I do not know."
"It shall go with the rest," said Lenore, taking it off. "Yes, you are a
kind, good man, Wohlfart," continued she, looking trustfully into his
tearful eyes; "do not forsake us. My brother has no experience, and is
more helpless than we are. It is a frightful position for me. Before
mamma I do all I can to be composed, else I could scream and weep the
whole day through." She sank in a chair, still holding his hand. "Dear
Wohlfart, do not forsake us."
Anton bent over her, and looked with passionate emotion at the lovely
face that turned so trustfully to him in the midst of its tears.
"I will be helpful to you when I can," said he, in the fullness of his
heart. "I will be at hand whenever you need me. You have too good an
opinion of my information and my faculties; I can be of less assistance
to you than you suppose, but what I can, that I will do in any and every
possible way."
Their hands parted with a warm pressure; the affair was settled.
The baroness now returned. "Our lawyer was with me this morning," said
she; "and now I must ask for your opinion on another subject. He tells
me that there is no prospect of preserving the baron's family estate."
"At this time, when interest is high, and money difficult to get, none,"
replied Anton.
"And you, too, think that we must turn all our efforts toward preserving
the Polish property?"
"I do," was the answer.
"For that, also, money will be necessary. Perhaps I may be able through
my relatives to intrust you with a small sum, which, with the help of
that"--she pointed to the iron chest--"may suffice to cover the first
necessary expenses. I do not, however, wish to sell the jewels here, and
a journey to the residence would be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cure the
sum to which I have just alluded. The baron's lawyer has spoken most
highly of your capacity for business. It is his wish which now decides
me to make a proposal to you. Will you for the next few years, or, at
all events, until our greatest difficulties are over, devote your whole
time to our affairs? I have consulted my children, and they agree with
me in believing that in your assistance lies our only hope of rescue.
The baron, too, has come in to the plan. The question now is whether
your circumstances allow you to give your support to our unfortunate
family. We shall be grateful to you, whatever conditions you affix; and
if you can find any way of making our great obligations to you apparent
in the position you hold, pray impart it to me."
Anton stood petrified. What the baroness required of him was separation
from the firm, separation from his principal, and from Sabine! Had this
thought occurred to him before, when standing in Lenore's presence or
bending over the baron's papers? At all events, now that the words were
spoken, they shocked him. He looked at Lenore, who stood behind her
mother with hands clasped in supplication. At length he replied, "I
stand in a position which I can not leav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others.
I was not prepared for this proposal, and beg to have time allowed me
for consideration. It is a step which will decide my whole future life."
"I do not press you," said the baroness; "I only request your
consideration. Whatever your decision be, our warmest gratitude will
still be yours; if you are unable to uphold our feeble strength, I fear
that we shall find no one to do so. You will think of that," she added,
beseechingly.
Anton hurried through the street with throbbing pulse. The noble lady's
glance of entreaty, Lenore's folded hands, beckoned him out of the
gloomy counting-house into a sphere of greater liberty, into a new
future, from whose depths bright images flashed out upon his fancy. A
request had been frankly made, and he was strongly inclined to justify
the confidence that prompted it. Those ladies required an unwearied,
self-sacrificing helper to save them from utter ruin, and if he
followed his impulse he should be doing a good work--fulfilling a duty.
In this mood he entered the merchant's dwelling. Alas! all that he saw
around him seemed to stretch out a hand to detain him. As he looked at
the warehouse, the good-humored faces of the porters, the chains of the
great scales, the hieroglyphics of the worthy Pix, again he felt that
this was the place that he belonged to. Sabine's dog kissed his hand,
and ran before him to his room--his and Fink's room. Here the childish
heart of the orphan boy had found a friend, kind companions, a home, a
definite and honorable life-purpose. Looking down through his window on
all the long-familiar objects, he saw a light in Sabine's store-chamber.
How often he had sought for that light, which brightened the whole great
building, and brought a sense of comfort and cheerfulness even into his
room. He now sprang up suddenly, and said to himself, "She shall
decide."
Sabine started in amazement when Anton appeared before her. "I am
irresistibly impelled to seek you," cried he. "I have to decide upon my
future life, and I feel undetermined, and unable to trust to my own
judgment. You have always been a kind friend to me since the day of my
arrival. I am accustomed to look up to you, and to think of you in
connection with all that interests me here. Let me hear your opinion
from your own lips. The Baroness Rothsattel has to-day proposed to me
permanently to undertake the situation of confidential adviser and
manager of the baron's affairs. Shall I accept; or shall I remain here?
I know not--tell me what is right both for myself and others."
"Not I," said Sabine, drawing back and growing very pale. "I can not
venture to decide in the matter. Nor do you wish me to do so, Wohlfart,
for you have already decided."
Anton looked straight before him and was silent.
"You have thought of leaving this house, and a wish to do so has sprung
out of the thought. And I am to justify you, and approve your resolve!
This is what you require of me," continued she, bitterly. "But this,
Wohlfart, I can not do, for I am sorry that you go away from us."
She turned away from him and leaned on the back of a chair.
"Oh, be not angry with me too!" said Anton; "that I can not bear. I have
suffered much of late. Mr. Schröter has suddenly withdrawn from me the
friendly regard that I long held my life's greatest treasure. I have not
deserved his coldness. What I have been doing has not been wrong, and
it was done with his knowledge. I had been spoiled by his kindness; I
have the more deeply felt his displeasure. My only comfort has been that
you did not condemn me. And now, do not you be cold toward me, else I
shall be wretched forever. There is not a soul on earth to whom I can
turn for affectionate comprehension of my difficulties. Had I a sister,
I should seek her heart to-day. You do not know what to me, lonely as I
am, your smile, your kindly shake of the hand has been till now. Do not
turn coldly from me, I beseech you."
Sabine was silent. At length she inquired, still with averted face,
"What draws you to those strangers; is it a joyful hope, is it sympathy
alone? Give this question close consideration before you answer it to
yourself at least."
"What it is that makes it possible for me to leave this house," said
Anton, "I do not myself know. If I can give a name to my motives, it is
gratitude felt toward one. She was the first to speak kindly to the
wandering boy on his way out into the world. I have admired her in the
peaceful brightness of her former life. I have often dreamed childish
dreams about her. There was a time when a tender feeling for her filled
my whole heart, and I then believed myself forever the slave of her
image. But years bring changes, and I learned to look on men and on life
with other eyes. Then I met her again, distressed, unhappy, despairing,
and my compassion became overmastering. When I am away from her, I know
that she is nothing to me; when I am with her, I feel only the spell of
her sorrow. Once, when I had to depart out of her circle like a culprit,
she came to me, and before the whole scornful assembly she gave me her
hand and acknowledged me her friend; and now she comes and asks for my
hand to help her father. Can I refuse it? Is it wrong to feel as I do? I
know not, and no one can tell me--no one but you alone."
Sabine's head had sunk down to the back of the chair on which she bent.
She now suddenly raised it, and with tearful eyes, and a voice full of
love and sorrow, cried, "Follow the voice that calls you. Go, Wohlfart,
go."
CHAPTER XXVII.
On a cold October day, two men were seen driving through the latticed
gate of the town of Rosmin on toward the plain, which stretched out
before them monotonous and boundless. Anton sat wrapped in his fur coat,
his hat low on his forehead, and at his side was young Sturm, in an old
cavalry cloak, with his soldier's cap cocked cheerily on one side. In
front of them a farm-servant, squatted on a heap of straw, flogged on
the small horses. The wind swept the sand and straw from the
stubble-fields, the road was a broad causeway without ditches or hedges,
the horses had to wade alternately through puddles and deep sand. Yellow
sand gleamed through the scanty herbage in all directions wherever a
field-mouse had made her way to her nest or an active mole had done what
he could to diversify the unbroken plain. Wherever the ground sank,
stagnant water lodged, and there hollow willow-trees stretched their
crippled arms in the air, their boughs flapping in the wind, and their
faded leaves fluttering down into the muddy pool below. Here and there
stood a small dwarf pine, a resting-place for the crows, who, scared by
the passing carriage, flew loudly croaking over the travelers' heads.
There was no house to be seen on the road, no pedestrian, and no
conveyance of any kind.
Karl looked every now and then at his silent companion, and said at
last, pointing to the horses, "How rough their coats are, and how pretty
their gray mouse skins! I wonder how many of these beasties would go to
make up my sergeant's horse! When I took leave of my father, the old man
said, 'Perhaps I shall pay you a visit, little one, when they light the
Christmas-tree.' 'You'll never be able,' said I. 'Why not?' asked he.
'You'll never trust yourself in any post-chaise.' Then the old boy
cried, 'Oho! post-chaises are always of a stout build; I shall be sure
to trust myself in one.' But now, Mr. Anton, I see that my father never
can pay us a visit."
"Why not?"
"It is possible that he may reach Rosmin; but, as soon as he sees these
horses and this road, he will instantly turn back. 'Shall I trust
myself,' he'll say, 'in a district where sand runs between one's legs
like water, and where mice are put into harness? The ground is not firm
enough for me.'"
"The horses are not the worst things here," said Anton, absently. "Look!
these go fast enough."
"Yes," replied Karl, "but they don't go like regular horses; they
entangle their legs like two cats playing in a parsley-bed. And what
things they have for shoes--regular webbed hoofs, I declare, which no
blacksmith can ever fit."
"If we could only get on!" returned Anton; "the wind blows cold, and I
am shivering in spite of my fur."
"You have slept but little the last few nights, sir," said Karl. "The
wind blows here as if over a threshing-floor. The earth is not round
hereabouts as elsewhere, but flat as a cake. This is a complete desert;
we have been driving for more than an hour, and there is not a village
to be seen."
"A desert indeed," sighed Anton; "let us hope it may improve." They
relapsed into profound silence. At length the driver stopped near a
pool, unharnessed the horses, and led them to the water's edge, without
noticing the travelers.
"What the deuce does this mean?" cried Karl, jumping down from the
carriage.
"I am going to feed," replied the servant, sulkily, in a foreign accent.
"I am anxious to know how that will be done," said Karl. "There is not
the shadow of a bag of provender."
The horses, however, soon proved that they could live without corn; they
stretched down their shaggy heads, and began to pull the grass and weeds
at the edge of the pool, sometimes taking a draught of the dirty water.
Meanwhile the servant drew a bundle from under his seat, settled himself
under the lee of an alder-bush, and, taking his knife, cut his bread and
cheese without even glancing at the travelers.
"I say, Ignatius or Jacob," cried Karl, sharply, "how long will this
breakfast of yours last?"
"An hour," replied the man, munching away.
"And how far is it from here to the estate?"
"Six miles, or maybe more."
"You can make nothing of him," said Anton; "we must put up with the
customs of the country;" and, leaving the carriage, they went to look on
at the horses feeding.
Anton is on his way to the Polish property. He is now the baron's agent.
Anxious months have the last proved to him. The parting from his
principal and the firm had been painful in the extreme. For some time
before it, indeed, Anton had found himself alone in the midst of his
colleagues. The quiet Baumann still remained his friend, but the others
considered him a castaway. The merchant received his resignation with
icy coldness; and even in the hour of parting, his hand lay impassive as
metal in Anton's grasp. Since then, our hero had undertaken several
journeys to the capital and to creditors in the family's behalf, and now
he was on his way to set the new estate in order, accompanied by Karl,
whom he had induced to become the baron's bailiff.
Ehrenthal had, by the authority conferred on him,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from the time of the sale by auction, and hired the Polish
bailiff for the baron. There had been unfair dealings between them at
the time, and it was well known in Rosmin that the bailiff had sold off
a good deal, and been guilty of all sorts of frauds since, so that Anton
had even now no prospect of a quiet life.
"The hour is come when I may execute my commission," cried Karl, groping
in the straw under the seat. He drew out a large japanned tin case, and
carried it to Anton. "Miss Sabine gave me this in charge for you." He
then joyously opened the lid, produced the materials for an excellent
breakfast, a bottle of wine, and a silver goblet. Anton took hold of the
case.
"It has a very knowing look," said Karl. "Miss Sabine planned it
herself."
Anton examined it on all sides, and placed it carefully on a tuft of
grass; then he took up the goblet, and saw his initials engraved on it,
and underneath the words, "To thy welfare." Whereupon he forgot the
breakfast and all around him, and stood gazing at the goblet, lost in
thought.
"Do not forget the breakfast, sir," suggested Karl, respectfully.
"Sit down by me, my faithful friend; eat and drink with me. Leave off
your absurd politeness. We shall have but little, either of us, but what
we have we will share like brothers. Take the bottle if you have no
glass."
"There's nothing like leather," said Karl, taking a small leathern
drinking-cup out of his pocket. "As for 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t was
kindly meant, and I thank you; but there must be subordination, if it
were but for the sake of the others; and so, sir, be kind enough to let
me shake hands with you now, and then let things be as they were before.
Only look at the horses, Mr. Anton. My faith! the creatures devour
thistles."
Again the horses were harnessed, again they threw out their short legs
in the sand, and again the carriage rolled through the barren
district--first through an empty plain, next through a wretched
fir-wood, then past a row of low sand-hills, then over a tumble-down
bridge crossing a small stream.
"This is the property," said the driver, turning round, and pointing
with his whip to a row of dirty thatched roofs that had just come into
sight.
Anton stood up to look for the group of trees in which the Hall might be
supposed to stand. Nothing of the sort to be seen. The village was
deficient in all that adorns the home of the poorest German peasant--no
orchard, no hedged-in gardens, no lime-trees in the market-place.
"This is wretched," said he, sitting down again; "much worse than they
told us in Rosmin."
"The village looks as if under a curse," cried Karl; "no teams working
in the fields--not a cow or a sheep to be seen."
The farm-servant flogged his horses into an irregular gallop, and so
they passed through the rows of mud huts which constituted the village,
and arrived at the public house. Karl sprang from the carriage, opened
the tavern door, and called for the landlord. A Jew slowly rose from his
seat by the stove and came to the threshold. "Is the gendarme from
Rosmin come?" He is gone into the village. "Which is the way to the
farm-yard?"
The landlord, an elderly man with an intelligent countenance, described
the way in German and Polish, and remained standing at the
door--bewildered, Karl declared, by the sight of two human beings. The
carriage turned into a cross-road, planted on both sides with thick
bushes, the remains of a fallen avenue. Over holes, stones, and puddles,
it rattled on to a group of mud huts, which still had a remnant of
whitewash upon them. "The barns and stables are empty," cried Karl, "for
I see gaps in the roofs large enough to drive our carriage through."
Anton said no more; he was prepared for every thing. They drove through
a break between the stables into the farm-yard, a large irregular space,
surrounded on three sides by tumble-down buildings, and open to the
fields on the fourth. A heap of _débris_ lay there--lime and rotten
timber, the remains of a ruined barn. The yard was empty; no trace of
farm implements or human labor to be seen. "Which is the inspector's
house," inquired Anton, in dismay. The driver looked round, and at last
made up his mind that it was a small one-storied building, with straw
thatch and dirty windows.
At the noise of the wheels a man appeared on the threshold, and waited
phlegmatically till the travelers had dismounted, and were standing
close before him. He was a broad-shouldered fellow, with a bloated,
brandy-drinking face, dressed in a jacket of shaggy cloth, while behind
him peered the muzzle of an equally shaggy dog, who snarled at the
strangers. "Are you the steward of this property?"
"I am," replied the man, in broken German, without stirring from where
he was.
"And I am the agent of the new proprietor," said Anton.
"That does not concern me," growled the shaggy man, turning sharp round,
entering the house, and bolting the door within.
Anton was thoroughly roused. "Break the window in, and help me to catch
the rascal," cried he to Karl, who coolly seized a piece of wood, struck
the panes so as to make the rotten framework give way, and cleared the
opening at one leap. Anton followed him. The room was empty, so was the
next, and in it an open window--the man was gone.
"After him!" cried Karl, and dashed on in pursuit, while Anton looked
about the house and out-buildings. He soon heard the barking of a dog,
and saw Karl capture the fugitive. Hurrying to his help, he held the man
fast, while, with a kick, Karl sent the dog flying. They then contrived
to force the steward back to the house, though he kept striking out
violently all the way.
"Go to the tavern, and bring the gendarme and the landlord," cried Anton
to the driver, who, undisturbed by all that had been going on, had
meanwhile unpacked the carriage. The man accordingly drove leisurely
off, and the fugitive being got into the room, Karl found an old cloth,
and with it bound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I beg your pardon, sir,"
said he; "it is only for an hour or so, till the arrival of the Rosmin
gendarme, whom we have appointed to meet us."
Anton then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house, bu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found but the merest necessaries; no books nor papers of any kind. It
had doubtless been emptied already. A bundle projected from the
coat-pocket of the prisoner, which turned out to be receipts and legal
documents in Polish. In time, the driver returned with the landlord and
the armed policeman. The landlord stood at the door in some perplexity,
and the policeman explained in a few moments what remained to be done.
"You must make a statement to the local judge, and give the man up to
me. He shall go back in your carriage to Rosmin. You will do well to get
rid of him, for this is a wild country, and it will be safer for you to
have him at Rosmin than here, where he has friends and accomplices."
After a long search, a sheet of paper was found in a cupboard, the
statement made and submitted to the policeman, who shook his head a
little over the Polish composition, and the prisoner lifted into the
carriage, the gendarme taking his seat beside him, and saying to Anton,
"I have long expected something of the kind. You may have often occasion
to want me again." The carriage then drove away, and thus the property
came under Anton's administration. He felt as if cast on a desert
island.
His portmanteau and traveling effects were leaning against a mud wall,
and the Polish landlord was the only man who could give him and Karl any
information or advice in their forlorn condition.
Now that the steward was fairly gone, the landlord grew more
communicative, and showed himself serviceable and obliging. A long
conversation ensued, and its purport was what Anton had apprehended from
the warning given by the Commissary Walter and other Rosmin officials.
The inspector had,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done all he could in the
way of spoliation, rendered daring by a report which had found its way
from the town to the village, that the present proprietor would never be
able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estate. At last Anton said, "What that
wretched man has done away with he will have to account for; our first
care must be to preserve what is still to be found on the property. You
must be our guide to-day."
They then examined the empty buildings. Four horses and two
servants--they were gone into the wood--a few old plows, a pair of
harrows, two wagons, a britzska, a cellar full of potatoes, a few
bundles of hay, a little straw--the inventory did not take much time in
drawing up. The buildings were all out of repair, not through age, but
neglect.
"Where is the dwelling-house?" inquired Anton. The landlord led the way
out of the yard to the meadow--a broad plain, gradually sloping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brook. It had been a great pasture. The cattle had
trodden it down into holes; the snouts of greedy swine had rooted it up;
gray molehills and rank tufts of grass rose on all sides.
The landlord stretched out his hand. "There is the castle. This castle
i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he added, reverentially; "no
nobleman in the district has a stone house like that. All the gentry
here live in wood and mud buildings. Herr von Tarow, the richest of
them, has but a poor dwelling."
About three hundred yards from the last out-building rose a great brick
edifice, with a black slate roof and a thick round tower. Its gloomy
walls on this treeless pasture-land, without one trace of life around,
rose beneath the cloudy sky like a phantom fortress which some evil
spirit had evoked from the abyss--a station from which to blight all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The strangers approached it. The castle had fallen into ruins before the
builders had finished their task. The tower had stood there for ages. It
was built of unhewn stone, and had small windows and loop-holes. The
former lords of the land had looked down from its summit on the tops of
the trees, which then stretched far into the plain. They had then ruled
with a rod of iron the serfs who cultivated their land, and toiled and
died for them. Many an arrow had sped through those loop-holes at the
enemy storming below, and many a Tartar horse had been overthrown before
those massive walls. Years ago, a despot of the district had, in
expiation of former sins, begun to add to the gray tower the walls of a
holy monastery; but the monastery never got finished, and the useless
walls had already stood there long, when the late count took it into his
head to convert them into a lordly dwelling for his race, and to raise a
house unparalleled for magnificence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 front of the house was added on to both sides of the tower, which
projected in the middle. The intention had been to have a high
terrace-road up to the castle, and the principal entrance had been made
in the tower, and arched over; but the terrace never having been formed,
the stone threshold of the main door was quite inacce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ladders, and the wide opening was left. The window-spaces of
the lower floor were merely closed up with boards, while on the second
story were some window-frames of beautifully carved wood, in which large
panes had once been placed, but they had got broken. In other windows
were temporary frames of rough deal, with small panes of muddy glass let
into them. A company of jackdaws sat on the top of the tower, looking
down in amazement on the strangers, and every now and then one flew off,
screaming loudly, to contemplate the intruders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A house for crows and bats, not for human beings," said Anton. "At
least, I see no way of getting into it."
The landlord now took them round the building. Behind, where the two
wings made a sort of horse-shoe, there were low entrances to the cellars
and offices; beneath which, again, were stables, great arched kitchens,
and small cells for the serfs. A wooden staircase led to the upper
story. The door turned creaking on its hinges, and a narrow passage took
them through a side wing to the front part of the house. There all was
at least magnificently planned. The circular entrance-hall--an arched
room of the old tower--was painted in mosaic, and through the great
doorway-opening was seen a wide expans
small disturbance made by the return of Anton had gradually settled
down. Those first-class treasures of Sabine's had made way for other
specimens of damask, still of a superior kind, it is true, but which
came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e elderly cousin's comprehension. She had
been quite right in prophesying that Anton would never remark those
signs of exuberant gratitude or their withdrawal. However, one change
had been permanently made--the greatest, the best of all changes--the
clerk retained a privileged place in the heart of the young mistress of
the firm, and his tall figure often appeared as one of the circle that
Sabine's fancy loved to gather round her when at her work-table or in
her treasure-chamber.
To-day she was walking restlessly up and down before dinner. The cousin,
who heard every thing, had just told her that a maid from Ehrenthal's
had run into the office to announce Bernhard's death to his friend. "How
will he bear it?" thought she. And the name of Ehrenthal forced her
thoughts back to the past, to one now far away, and to that painful hour
when the struggle going on in her own mind had been suddenly brought to
a close by a letter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parted. And Anton had known
of that conquered feeling of hers. How considerate he had always been,
how chivalrous, how helpful! She wondered if he had any idea of the
completeness of her triumph over a girlish illusion. She shook her head.
"No, he has not. It was here, at this very table, that an accident first
betrayed me to him. That past time still rises like a cloud between us.
Whenever I sit near Wohlfart of an evening, I am conscious of another's
shadow at my side; and when he speaks to me, his tone, his manner always
seem to say, 'You are not alone; he is with you.'" Sabine started, and
lovingly passed her hand over the beautiful flowers on the table before
her, as if to dispel a painful thought. She could not tell him that she
was free from that long-felt sorrow. Now, however, when he had lost a
friend whom he so much loved, she must show him that there were other
hearts that clung to him still. And again she walked up and down, trying
to devise a way of speaking to him alone.
Dinner was announced. Anton came with the rest, and took his place at
once. There was no opportunity of exchanging a word during the meal, but
he often met her sad and sympathizing eye. "He eats nothing at all
to-day," whispered her cousin; "not even any of the roast," she added,
reproachfully. Sabine was much perturbed. Mr. Jordan had already risen;
Anton would leave the room with the rest, and she should not see him
again the whole day through. So she called out, "The great Calla is
fully blown now. You were admiring the buds the other day; will you
remain a moment; I should like to show it you?" Anton bowed and staid
behind. A few more awkward moments, then her brother rose too; and,
hurrying to Anton, she took him to the room where the flowers were.
"You have had sorrowful tidings to-day," she began.
"The tidings themselves did not surprise me," replied Anton. "The doctor
gave no hope. But I lose much in him."
"I never saw him," said Sabine; "but I know from you that his life was
lonely--poor in affection and in enjoyment."
She moved an arm-chair toward Anton, and led him on to talk about his
friend. She listened to every word with warm sympathy, and well knew
what to ask and how to comfort. It was a relief to Anton to speak of the
departed one, to describe his quiet way of life, his erudition, his
poetical enthusiasm. After a pause, Sabine looked up frankly into his
face, and asked, "Have you any tidings of Herr von Fink?"
It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his departure that she had ever breathed his
name. Anton felt how touching her confidence was, given in this hour of
his sadness. In his emotion, he seized her hand, which she was slow in
withdrawing.
"He is not happy in his new life," he gravely replied. "There was a
savage humor in his last letter, from which I gather, even more than
from his actual words, that the business into which his uncle's death
has thrown him does not suit him."
"It is unworthy," cried Sabine.
"At all events, it is not what would be recognized as honorable in this
house," replied Anton. "Fink is upright, and has lived too long with
your brother to take pleasure in the wild speculations so common on the
other side the Atlantic. His partners and colleagues are for the most
part men without a conscience, and his feelings revolt against their
companionship."
"And can Herr von Fink tolerate such relations as these for a day?"
"It is a remarkable thing that he whose own will was ever so arbitrarily
exercised, should now be obliged against that will to obey a pressure
from without, and every where to work with his hands tied. The
organization of such speculations in America is so complicated that one
shareholder can do little to alter it; and, now that Fink has attained
what used to be the goal of his wishes--a large capital, and the
management of immense districts--his condition appears more uncertain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He was always in danger of thinking slightingly
of others, now I am distressed at the bitter contempt he expresses for
his own life. His last letter paints an intolerable state of things, and
seems to point to some decisive resolve."
"There is only one resolve for him," cried Sabine. "May I ask what you
said to him in reply?"
"I entreated him instantly, come what would, to free himself from the
business in which he was entangled. I said that his own strong will
might find a way of extrication, even if that which I pointed out proved
impracticable. Then I begged of him either to carry out his old plan of
becoming a landed proprietor in America, or to return to us."
"I knew that you would write thus," said Sabine, drawing a long breath.
"Yes, Wohlfart, he shall return," said she, gently, "but he shall not
return to us."
Anton was silent.
"And do you think that Herr von Fink will follow your advice?"
"I do not know. My advice was not very American."
"But it was worthy of you," cried Sabine, with proud delight.
"An officer wishes to speak to Mr. Wohlfart," said a servant at the
door.
Anton sprang up. Sabine went to her flowers and bent mournfully over
them. The shadows of others hovered still between her friend and her.
The few words spoken by the servant filled Anton with a vague terror. He
hurried into the ante-room: there stood Eugene von Rothsattel. Anton was
gladly rushing forward to greet him, but the young soldier's face of
agony made him start back. He whispered, "My mother wishes to speak to
you; something dreadful has occurred." Anton caught up his hat, ran into
the office, hurriedly asked Baumann to excuse him to the principal, and
then accompanied the lieutenant to the baron's house.
On the way, Eugene, who had lost all self-command, said unconnectedly to
Anton, "My father last night accidentally wounded himself by a
pistol-shot--a messenger was sent to summon me--when I came, I found my
mother in a swoon--my sister and I do not know what to do--Lenore
implored my mother on her knees to send for you--you are the only one in
whom w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our distress--I understand nothing about
business, but my father's affairs must be in a dreadful state--my mother
is beside herself--the whole house is in the greatest disorder."
From what Eugene said and what he did not say; from his broken sentences
and his look of agony, Anton guessed at the horrors of the previous
evening. In the boudoir of the baroness he found Lenore, weeping and
exhausted.
"Dear Wohlfart!" cried she, taking his hand and beginning again to sob,
while her head sank powerless on his shoulder.
Meanwhile Eugene walked up and down, wringing his hands, and at length
throwing himself on the sofa, he gave himself up to silent tears.
"It is horrible, Mr. Wohlfart," said Lenore, lifting up her head. "No
one may approach my father--Eugene may not, nor I--only my mother and
old John are with him; and early this morning the merchant Ehrenthal was
here, insisting that he must see my father. He screamed at my mother,
and called my father a deceiver, till she fainted away. When I rushed
into the room, the dreadful man went off threatening her with his
clenched fist."
Anton led Lenore to a chair and waited till she had told him all.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comforting in this case, and his own heart was
wrung to the utmost by the misery he witnessed.
"Call my mother, Eugene," said Lenore, at length.
Her brother left the room.
"Do not forsake us," implored Lenore, clasping her hands; "we are at the
last gasp; even your help can not save us."
"He is dead who might perhaps have done so," mournfully replied Anton.
"Whether I can be of any use I know not, but you can not doubt my
willingness to be so."
"No," cried Lenore. "And Eugene, too, thought of you at once."
The baroness now entered. She walked wearily; but, steadying herself by
a chair, she saluted Anton with dignity. "In our position," said she,
"we need a friend who knows more of business than we three do.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prevents the baron--possibly for a long time to
come--from managing his own affairs, and, little as I understand them, I
can see that our interests require prompt measures. My children have
mentioned you to me, but I fear I am unreasonable in asking you to
devote your time to our service."
She sat down, beckoned Anton to take a chair, and said to her children,
"Leave us; I shall be better able to tell Mr. Wohlfart the little that I
know when I do not see your grief."
When they were alone, she motioned him nearer and tried to speak, but
her lips quivered, and she hid her face in her handkerchief.
"Before I can consent, gracious lady," said he, "to your reposing in me
such confidence as this, I must first inquire whether the baron has no
relative or intimate friend to whom you could with less pain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I pray you to remember that my own knowledge of business
is but small, and my position not one to constitute me a proper
counselor to the baron."
"I know no one," said the baroness, hopelessly. "It is less painful to
me to tell you what I can not conceal, than to one of our own circle.
Consider yourself a physician sent for to visit a patient. The baron has
this morning told me some particulars of his present circumstances." And
then she proceeded to relate what she had gathered as to the nature of
his embarrassments, the danger in which the family property was placed,
and the capital needed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Polish estate.
"My husband," continued she, "has given me the key of his desk, and he
wishes Eugene, with the help of a man of business, to go over his
papers. I now request of you to make this examination together with my
son. When you need explanations, I will try to obtain them from the
baron. The question is now, whether you are inclined to undertake this
trouble for us, who are only strangers."
"I am most willing to do so," earnestly replied Anton; "and I hope that
the kindness of my principal will allow me the time needful for the
purpose, if you do not consider it more advisable to depute the baron's
experienced legal adviser to the task."
"There will be an opportunity of asking that gentleman's advice later,"
said the baroness.
Anton rose. "When do you wish to begin?"
"Immediately. I fear there is not a day to lose. I shall do all I can to
help you look the papers over." She led Anton into the next room, called
in Eugene, and unlocked the baron's desk. As she opened it she lost her
self-command for a moment, and moving to the window, the quivering of
the curtains betrayed the anguish that shook her fragile frame.
The mournful task began. Hour after hour passed. Eugene was in no
condition to peruse any thing, but his mother reached letters and
documents to Anton, and, though often obliged to desist a while, she
bravely returned to the task. Anton placed the papers in order, and
sought, by glancing over each, to arrive at least at a superficial view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It was evening, when the old servant opened the door in dismay, and
called out, "He is there again." The baroness could not repress a slight
scream, and made a gesture of aversion.
"I have told him that no one is at home, but he will not be dismissed;
he makes such a noise on the steps. I can not get rid of him."
"It will kill me if I hear his voice again," murmured the baroness.
"If the man be Ehrenthal," said Anton, rising, "I will try to get him
away. We have now done what was most necessary; have the goodness to
lock up these papers, and to allow me to return to-morrow." The baroness
silently assented, and sank back in her chair. Anton hurried off to the
ante-room, whence he could hear Ehrenthal's loudly-raised voi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usurer shocked him. His hat pushed half off his
head, his pale face swelled as if by drinking, his glazed eyes red with
tears, Ehrenthal stood before him, calling in broken sentences for the
baron, wailing and cursing alternately. "He must come! he must come at
once!" cried he; "the wicked man! A nobleman, indeed! he is a vagabond,
after whom I will send the police. Where is my money? Where is my
security? I want my mortgage from this man who is not at home."
Anton went straight up to him, and asked, "Do you know me, Mr.
Ehrenthal?" Ehrenthal turned his glazed eyes upon him, and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 friend of his dead son.
"He loved you!" he cried, in a lamentable voice. "He spoke to you more
than to his father. You were the only friend that he had on earth. Have
you heard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house of Ehrenthal?" continued he, in
a whisper. "Just as they stole the papers he died. He died with a hand
like this," and clenching his fist he struck his forehead. "Oh my son!
my son! why didst not thou forgive thy father!"
"We will go to your son," said Anton, taking the arm of the old man, who
unresistingly allowed himself to be led back to his own house.
From thence Anton hurried to Councilor Horn, with whom he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It was late before he returned home. In the midst of his anxiety about
those whose prosperity had filled his imagination years before,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in their adversity, reposed in him, dilated his
breast with a feeling of pride. He burned with desire to help them, and
hoped that his zealous devotion might yet find some way of rescue. As
yet he saw none. Looking up at the great building before him, so firm
and secure, in the moonlight, a thought flashed into his mind. If any
man could help them, it was his principal. His keen eye would be able to
unravel all the dark secrets in which the baron was entangled, and his
iron strength of will would crush the villains who held the unfortunate
nobleman in their power. And then he had a noble nature; he always
decided on the right, without an effort or a struggle. Anton looked at
the first floor. The whole house-front was dark, but in a corner room a
light still burned. It was the private office of his chief.
With sudden resolve, Anton begged the servant to take him to Mr.
Schröter, who looked with amazement at the unexpected visitor, and asked
what brought him, and whether any thing had happened.
"I implore your counsel--I implore your help," cried Anton.
"For yourself or for others?" inquired the merchant.
"For a family with whom I have accidentally become connected. They are
lost if a strong hand does not ward off the impending catastrophe."
Anton then rapidly related the occurrences of the afternoon, and,
seizing his principal's hand in his emotion, cried, "Have pity upon the
unhappy ladies, and help them."
"Help them!" replied the merchant; "how can I? Have you been
commissioned to apply to me, or are you only following the impulse of
your own feelings?"
"I am not commissioned; it is only the interest that I take in the
baron's fate which leads me to you."
"And what right have you to inform me of facts communicated in strict
confidence to yourself by the baron's lady?" asked the merchant, dryly.
"I am committing no indiscretion in telling you what will, in a few
days, be no secret, even to strangers."
"You are unusually excited, otherwise you would not forget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hatever, does a man of business venture to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without the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Of course, I shall make no wrong use of what you have said, but it was
by no means business-like, Wohlfart, to be so open toward me."
Anton was silent, feeling, indeed, that his principal was right, but yet
it seemed hard to be blamed for reposing confidence at such a time as
this. The merchant walked silently up and down; at length, stopping
before Anton, he said, "I do not now inquire how you come to take so
warm an interest in this family. I fear it is an acquaintance you owe to
Fink."
"You shall hear all," said Anton.
"Not at present. I will now content myself with repeating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interfere in these affairs without being specially
applied to by the parties themselves. I may add that I by no means wish
for such an application, and do not disguise from you that, were it
made, I should probably decline to do any thing for the Baron
Rothsattel."
Anton's feelings were roused to the utmost. "The question is the rescue
of an honorable man, and of lovely and amiable women from the toils of
rogues and impostors. To me, this seems the duty of every one; I, at
least, consider it a sacred obligation which I dare not shrink from. But
without your support I can do nothing."
"And how do you think this embarrassed man can be helped?" inquired the
merchant, seating himself.
With somewhat more composure, Anton repli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an experienced man of business making himself master of the case. There
must be some way of circumventing these villains. Your penetration would
discover it."
"Any attorney would be far more likely to do so, and the baron might
readily engage the services of experienced and upright legal advisers.
If his enemies have done any thing illegal, the quick eye of a lawyer is
the most likely to detect it."
"Alas! the baron's own lawyer gives but little hope," replied Anton.
"Then, my dear Wohlfart, no other is likely to do much good. Show me an
embarrassed man who has strength to grasp an offered hand, and bid me
help him, and for the sake of all I owe you, I will not refuse to do so.
I think you are convinced of this."
"I am," said Anton, dejectedly.
"From all I hear, however," the merchant went on,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the baron. From what I gather from general report, as well as from
you, his embarrassments arise from his having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usurers, which proves him deficient in what alone ennobles the life of
any man--good sense, and the power of steady exertion."
Anton could only sigh his assent.
"To help such a man," inexorably continued the merchant, "is a futile
attempt, against which reason may well protest. We are not to despair of
any, but want of strength is the most hopeless case of all. Our power of
laboring for others being limited, it becomes our duty to inquire,
before we devote our time to the weak, whether we are not thus
diminishing our chances of helping better men."
Anton interrupted him. "Does he not deserve every allowance to be made
for him? He was brought up to exact much; he has not learned, as we
have, to make his way by his own labor."
The merchant laid his hand on the young man's shoulder. "The very
reason. Believe me, a large number of these landed gentry, who pay the
penalty of their old family memories, are beyond help. I am the last to
deny that many worthy and admirable men belong to this class. Indeed,
wherever remarkable talent or nobility of character shoots up among
them, no doubt their position offers peculiar scope for its development,
but for average men it is not a favorable one. He who considers it his
hereditary privilege to enjoy life, and who assumes a distinguished
position in virtue of his family, will very often fail to put forth his
whole strength in order to deserve that position. Accordingly, numbers
of our oldest families are declining, and their fall will be no loss to
the state. Their family associations make them haughty without any
right to be so--limit their perceptions and confuse their judgment."
"Even if all this be true," cried Anton, "it does not absolve us from
helping individuals of the class who have excited our sympathy."
"No," said the principal, "if it be excited. But it does not glow so
rapidly in advancing years as in youth. The baron has endeavored to
isolate his property from the current of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leave it forever to his family. Forever! You, as a merchant, know how to
estimate the attempt. True, every rational man must allow it to be
desirable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same soil should be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We all prize what our forefathers have possessed before
us, and Sabine would unlock every room in this house with pride, because
her great-great-grandmother turned the same keys before her. It is
therefore natural that the landed proprietor should desire to preserve
those familiar scenes, which are the source of his own prosperity, to
those nearest and dearest to him. But there must be means to this end,
and these means are the making his own existence available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increase of his patrimony. Where energy dies in families
or individuals, then it is well that their means die too, that their
money should circulate through other hands, and their plowshare pass to
those who can guide it better. A family that has become effete through
luxury ought to sink down into common life, to make room for the
uprising of fresh energies and faculties. Every one who seeks, at the
cost of free activity for others, to preserve permanent possessions and
privileges for himself or his family, I must look upon as an enemy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social state. And if such a man ruin
himself in his endeavors, I should feel no malicious pleasure in his
downfall, but I should say that he is rightly served, because he has
sinned against a fundamental law of our social being; consequently, I
should consider it doubly wrong to support this man, because I could but
fear that I should thus be supporting an unsound condition of the body
politic."
Anton looked down mournfully. He had expected sympathy and warm
concurrence, and he met with disaffection and coldness that he despaired
of conquering. "I can not gainsay you," he at length replied; "but in
this case I can not feel as you do. I have been witness to the
unspeakable distress in the baron's family, and my whole soul is full
of sadness and sympathy, and of the wish to do something for those who
have opened their heart to me. After what you have said, I dare no
longer ask you to trouble yourself with their affairs, but I have
promised the baroness to assist her as far as my small powers permit,
and your kindness allows. I implore you to grant me permission to do
this. I shall endeavor to be regular in my attendance at the office, but
if during the next few weeks I am occasionally absent, I must ask you to
excuse me."
Once more the merchant walked up and down the room, and then, looking at
Anton's excited face, with deep seriousness and something of regret, he
replied, "Remember, Wohlfart, that every occupation which excites the
mind soon obtains a hold over a man, which may retard as well as advance
his success in life. It is thi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 to agree
to your wishes."
"I know it," said Anton, in a low voice; "but I have now no choice
left."
"Well, then, do what you must," said the merchant, gloomily; "I will lay
no hinderance in your way; and I hope that after a few weeks you will be
able to consider the whole circumstances more calmly." Anton left the
room, and the merchant stood looking long with frowning brow at the
place his clerk had occupied.
Nor was Anton in a more congenial mood. "So cold, so inexorable!"
exclaimed he, as he reached his own room. He began to suspect that his
principal was more selfish and less kindly than he had hitherto
supposed. Many an expression of Fink's recurred to his mind, as well as
that evening when young Rothsattel, in his boyish conceit, had spoken
impertinently to the merchant. "Is it possible," thought he, "that that
rude speech should be unforgotten?" And his chief's keen, deep-furrowed
face lost inexpressibly by contrast with the fair forms of the noble
ladies. "I am not wrong," he cried to himself; "let him say what he
will, my views are more just than his, and henceforth my destiny shall
be to choose for myself the way in which I shall walk." He sat long in
the darkness, and his thoughts were gloomy as it; then he went to the
window to look down into the dark court below. A great white blossom
rose before him like a phantom. Striking a light, he saw that it was the
beautiful Calla out of Sabine's room. It hung down mournfully on its
broken stem. Sabine had had it placed there. This little circumstance
struck him as a mournful omen.
Meanwhile Sabine, taper in hand, entered her brother's room.
"Good-night, Traugott," nodded she. "Wohlfart has been with you this
evening; how long he staid!"
"He will leave us," replied the merchant, gloomily.
Sabine started and dropped her taper on the table. "For God's sake, what
has happened? Has Wohlfart said that he was going away?"
"I do not yet know it, but I see it coming step by step; and I can not,
and still less can you, do any thing to retain him. When he stood before
me here with glowing cheeks and trembling voice, pleading for a ruined
man, I found out what it was that lured him away."
"I do not understand you," said Sabine, looking full at her brother.
"He chooses to become the confidential friend of a decayed noble. A pair
of bright eyes draws him away from us: it seems to him a worthy object
of ambition to become Rothsattel's man of business. This intimacy with
nobility is the legacy bequeathed to him by Fink."
"And you have refused to help him?" inquired Sabine, in a low voice.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said the merchant, harshly; and he
turned to his writing-table.
Sabine slowly withdrew. The taper trembled in her hand as she passed
through the long suite of rooms listening to her own footfall, and
shuddering as the feeling came over her that an invisible companion
glided by her side. This was the revenge of that other. The shadow that
once fell on her innocent life now drove her friend away from their
circle. Anton's affections clung to another. She had but been in his
eyes a mere stranger, who had once loved and languished for one now far
away, and who now, in widow's weeds, looked back regretfully to the
feelings of her youth.
The few next weeks were spent by Anton in over-hard work. He had great
difficulty in keeping up his counting-house duties, while he spent every
spare hour in conference with the baroness and the lawyer.
In the mean time, the misfortunes of the baron ran their course. He had
not been able to pay the interest of the sums with which his estate was
burdened. When last they were due, a whole series of claims was brought
against him, and the estate fell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district authorities. Complicated lawsuits arose. Ehrenthal complained
loudly, claiming the first mortgage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nay, he
was inclined to advance claims on the last mortgage offered by the baron
in the recent fatal hour. Löbel Pinkus also appeared as claimant of the
first mortgage, and asserted that he had paid the whole sum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Ehrenthal had no proof to bring forward, and had been
for some weeks past quite unable to manage his own affairs, while
Pinkus, on the contrary, fought with every weapon a hardened sinner can
devise or employ, and the deeds which the baron had executed at Veitel's
suggestion proved to be so capital a master-stroke of the cunning
advocate, that the baron's man of business had, from the first, little
hope of the case. We may here observe that Pinkus did eventually win it,
and that the mortgage was made over to him.
Anton was now gradually gaining some insight into the baron's
circumstances. But the double sale of the first mortgage was still kept
a secret by the latter, even from his wife. He declared Ehrenthal's
claim unfounded, and even expressed a suspicion that he had himself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robbery in his office. Indeed, he really
believed this. Then the name of Itzig was never broached, and the
suspicion against Ehrenthal, which the baron's lawyer shared, prevented
Anton seeking any explanation from him.
Meanwhile, an estrangement had sprung up between our hero and his
principal, which the whole counting-house remarked with surprise. The
merchant scowled at Anton's vacant seat when the latter chanced to be
absent during office-hours, or looked coldly at his clerk's face, made
pale as it was with excitement of mind and night-work. He took no notice
of his new occupation, and never seemed to remark him. Even to his
sister he maintained a stiff-necked silence; nor could all her attempts
lead him to speak of Anton, who, on his side, felt his heart revolt
against this coldness. After his return, to be treated like a child of
the house, praised, promoted, petted, and now to be treated like a mere
hireling, who is not worth the bread thrown to him; to be a toy of an
incomprehensible caprice--this, at least, he had not deserved; so he
became reserved toward the whole family, and sat silent at his desk; but
he fel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now and the then so keenly, that often,
when alone, he would spring up and stamp on the ground in the bitter
indignation of his heart.
One comfort remained. Sabine was not estranged. True, he saw little of
her, and at dinner she seemed to avoid speaking to him, but he knew that
she was on his side.
A few days after his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the merchant, she came down
stairs as he stood in the hall, and had to pass him by so closely that
her dress touched him. He had retreated, and made a formal bow, but she
looked at him imploringly, and whispered, "You must not be estranged
from me." It was an affair of a moment, but the faces of both were
radiant with a happy understanding.
The time had now arrived when Mr. Jordan was to quit the firm. The
principal again called Anton into his little office, and without any
severity, but also without a trace of his former cordiality, began: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o you my intention of appointing you Jordan's
successor; but,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your time has been more taken
up with other business than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such a post, I
therefore ask you whether you are now at liberty to undertake Jordan's
duties?"
"I am not," replied Anton.
"Can you name any--not very distant--time when you will be free from
your present occupation? In that case I will endeavor to find a
substitute until then."
Anton sorrowfully replied, "I can not at present say when I shall again
be master of my whole time; and, besides, I feel that, even as it is, I
tax your indulgence by many irregularities. Therefore, Mr. Schröter, I
beg that you will fill up this post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me."
The merchant's brow grew furrowed and dark, and he silently bowed
assent. Anton felt as he closed the door that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m was now complete, and, resuming his place, he leaned his throbbing
head on his hand. A moment later Baumann was summoned to the principal,
and Jordan's situation conferred upon him. On returning to the office,
he went up to Anton and whispered, "I refused at first, but Mr. Schröter
insisted. I am doing you an injustice." And that evening Mr. Baumann, in
his own room, read in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the chapters treating of
the unjust Saul (the principal), and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Jonathan
and the persecuted David, and strengthened his heart thereby.
The next day Anton was summoned to the baroness. Lenore and her mother
sat before a large table covered with jewel-boxes and toilette elegances
of every description, while a heavy iron chest stood at their feet. The
curtains were drawn, and the subdued light shone softly into the richly
furnished room. On the carpet glowed wreaths of unfading flowers, and
the clock ticked cheerfully in its alabaster case. Under the shade of
flowering plants sat the two love-birds in their silvered cage, hopping
from perch to perch, screaming ceaselessly, or sitting up quietly close
to each other. The whole room was beauty and perfume. "For how long?"
thought Anton. The baroness rose. "We are already obliged to trouble you
again," said she; "we are engaged in a very painful occupation." On the
table were all manner of ornaments, gold chains, brilliants, rings,
necklaces, gathered into a heap.
"We have been looking out all that we can dispense with," said the
baroness, "and now pray you to undertake to sell these things for us. I
have been told that some of them are of value, and as we are now in much
need of money, we turn here for help."
Anton looked in perplexity at the glittering heap.
"Tell us, Wohlfart," cried Lenore, anxiously, "is this necessary? can it
be of any use? Mamma has insisted upon setting apart for sale all our
ornaments, and whatever plate is not in daily use. What I can give is
not worth talking of, but my mother's jewels are costly; many of them
were presents made to her in youth, which she shall not part with unless
you say that it is necessary."
"I fear," said Anton, gravely, "that it will prove so."
"Take them," said the baroness to Anton; "I shall be calmer when I know
that we have at least done what we could."
"But do you wish to part with all?" inquired Anton, anxiously. "Much
that is dear to you may have but little value in a jeweler's eyes."
"I shall never wear an ornament again," quietly replied the baroness.
"Take them all;" and, holding her hands before her eyes, she turned
away.
"We are torturing my mother," cried Lenore, hastily; "will you lock up
all that is on the table, and get them out of the house as soon as you
can?"
"I can not undertake the charge of these valuables," said Anton,
"without taking some measures to decrease my own responsibility. First
of all, I will in your presence make a short note of all you intrust to
me."
"What useless cruelty!" exclaimed Lenore.
"It will not take long."
Anton took out a few sheets from his pocket-book, and began to note down
the different articles.
"You shall not see it done, mother," said Lenore, drawing her mother
away, and then returning to watch Anton at his task.
"These preparations for the market are horrible," said she. "My mother's
whole life will be sold; some memory of hers is linked with every single
thing. Look, Wohlfart, the princess gave her this diamond ornament when
she married my father."
"They are magnificent brilliants," cried Anton, admiringly.
"This ring was my grandfather's, and these are presents of poor papa's.
Alas! no man can know how we love all these things. It was always a
festival to me when mamma put on her diamonds. Now we come to my
possessions. They are not worth much. Do you think this bracelet good
gold?" She held out her hand as she spoke.
"I do not know."
"It shall go with the rest," said Lenore, taking it off. "Yes, you are a
kind, good man, Wohlfart," continued she, looking trustfully into his
tearful eyes; "do not forsake us. My brother has no experience, and is
more helpless than we are. It is a frightful position for me. Before
mamma I do all I can to be composed, else I could scream and weep the
whole day through." She sank in a chair, still holding his hand. "Dear
Wohlfart, do not forsake us."
Anton bent over her, and looked with passionate emotion at the lovely
face that turned so trustfully to him in the midst of its tears.
"I will be helpful to you when I can," said he, in the fullness of his
heart. "I will be at hand whenever you need me. You have too good an
opinion of my information and my faculties; I can be of less assistance
to you than you suppose, but what I can, that I will do in any and every
possible way."
Their hands parted with a warm pressure; the affair was settled.
The baroness now returned. "Our lawyer was with me this morning," said
she; "and now I must ask for your opinion on another subject. He tells
me that there is no prospect of preserving the baron's family estate."
"At this time, when interest is high, and money difficult to get, none,"
replied Anton.
"And you, too, think that we must turn all our efforts toward preserving
the Polish property?"
"I do," was the answer.
"For that, also, money will be necessary. Perhaps I may be able through
my relatives to intrust you with a small sum, which, with the help of
that"--she pointed to the iron chest--"may suffice to cover the first
necessary expenses. I do not, however, wish to sell the jewels here, and
a journey to the residence would be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cure the
sum to which I have just alluded. The baron's lawyer has spoken most
highly of your capacity for business. It is his wish which now decides
me to make a proposal to you. Will you for the next few years, or, at
all events, until our greatest difficulties are over, devote your whole
time to our affairs? I have consulted my children, and they agree with
me in believing that in your assistance lies our only hope of rescue.
The baron, too, has come in to the plan. The question now is whether
your circumstances allow you to give your support to our unfortunate
family. We shall be grateful to you, whatever conditions you affix; and
if you can find any way of making our great obligations to you apparent
in the position you hold, pray impart it to me."
Anton stood petrified. What the baroness required of him was separation
from the firm, separation from his principal, and from Sabine! Had this
thought occurred to him before, when standing in Lenore's presence or
bending over the baron's papers? At all events, now that the words were
spoken, they shocked him. He looked at Lenore, who stood behind her
mother with hands clasped in supplication. At length he replied, "I
stand in a position which I can not leav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others.
I was not prepared for this proposal, and beg to have time allowed me
for consideration. It is a step which will decide my whole future life."
"I do not press you," said the baroness; "I only request your
consideration. Whatever your decision be, our warmest gratitude will
still be yours; if you are unable to uphold our feeble strength, I fear
that we shall find no one to do so. You will think of that," she added,
beseechingly.
Anton hurried through the street with throbbing pulse. The noble lady's
glance of entreaty, Lenore's folded hands, beckoned him out of the
gloomy counting-house into a sphere of greater liberty, into a new
future, from whose depths bright images flashed out upon his fancy. A
request had been frankly made, and he was strongly inclined to justify
the confidence that prompted it. Those ladies required an unwearied,
self-sacrificing helper to save them from utter ruin, and if he
followed his impulse he should be doing a good work--fulfilling a duty.
In this mood he entered the merchant's dwelling. Alas! all that he saw
around him seemed to stretch out a hand to detain him. As he looked at
the warehouse, the good-humored faces of the porters, the chains of the
great scales, the hieroglyphics of the worthy Pix, again he felt that
this was the place that he belonged to. Sabine's dog kissed his hand,
and ran before him to his room--his and Fink's room. Here the childish
heart of the orphan boy had found a friend, kind companions, a home, a
definite and honorable life-purpose. Looking down through his window on
all the long-familiar objects, he saw a light in Sabine's store-chamber.
How often he had sought for that light, which brightened the whole great
building, and brought a sense of comfort and cheerfulness even into his
room. He now sprang up suddenly, and said to himself, "She shall
decide."
Sabine started in amazement when Anton appeared before her. "I am
irresistibly impelled to seek you," cried he. "I have to decide upon my
future life, and I feel undetermined, and unable to trust to my own
judgment. You have always been a kind friend to me since the day of my
arrival. I am accustomed to look up to you, and to think of you in
connection with all that interests me here. Let me hear your opinion
from your own lips. The Baroness Rothsattel has to-day proposed to me
permanently to undertake the situation of confidential adviser and
manager of the baron's affairs. Shall I accept; or shall I remain here?
I know not--tell me what is right both for myself and others."
"Not I," said Sabine, drawing back and growing very pale. "I can not
venture to decide in the matter. Nor do you wish me to do so, Wohlfart,
for you have already decided."
Anton looked straight before him and was silent.
"You have thought of leaving this house, and a wish to do so has sprung
out of the thought. And I am to justify you, and approve your resolve!
This is what you require of me," continued she, bitterly. "But this,
Wohlfart, I can not do, for I am sorry that you go away from us."
She turned away from him and leaned on the back of a chair.
"Oh, be not angry with me too!" said Anton; "that I can not bear. I have
suffered much of late. Mr. Schröter has suddenly withdrawn from me the
friendly regard that I long held my life's greatest treasure. I have not
deserved his coldness. What I have been doing has not been wrong, and
it was done with his knowledge. I had been spoiled by his kindness; I
have the more deeply felt his displeasure. My only comfort has been that
you did not condemn me. And now, do not you be cold toward me, else I
shall be wretched forever. There is not a soul on earth to whom I can
turn for affectionate comprehension of my difficulties. Had I a sister,
I should seek her heart to-day. You do not know what to me, lonely as I
am, your smile, your kindly shake of the hand has been till now. Do not
turn coldly from me, I beseech you."
Sabine was silent. At length she inquired, still with averted face,
"What draws you to those strangers; is it a joyful hope, is it sympathy
alone? Give this question close consideration before you answer it to
yourself at least."
"What it is that makes it possible for me to leave this house," said
Anton, "I do not myself know. If I can give a name to my motives, it is
gratitude felt toward one. She was the first to speak kindly to the
wandering boy on his way out into the world. I have admired her in the
peaceful brightness of her former life. I have often dreamed childish
dreams about her. There was a time when a tender feeling for her filled
my whole heart, and I then believed myself forever the slave of her
image. But years bring changes, and I learned to look on men and on life
with other eyes. Then I met her again, distressed, unhappy, despairing,
and my compassion became overmastering. When I am away from her, I know
that she is nothing to me; when I am with her, I feel only the spell of
her sorrow. Once, when I had to depart out of her circle like a culprit,
she came to me, and before the whole scornful assembly she gave me her
hand and acknowledged me her friend; and now she comes and asks for my
hand to help her father. Can I refuse it? Is it wrong to feel as I do? I
know not, and no one can tell me--no one but you alone."
Sabine's head had sunk down to the back of the chair on which she bent.
She now suddenly raised it, and with tearful eyes, and a voice full of
love and sorrow, cried, "Follow the voice that calls you. Go, Wohlfart,
go."
CHAPTER XXVII.
On a cold October day, two men were seen driving through the latticed
gate of the town of Rosmin on toward the plain, which stretched out
before them monotonous and boundless. Anton sat wrapped in his fur coat,
his hat low on his forehead, and at his side was young Sturm, in an old
cavalry cloak, with his soldier's cap cocked cheerily on one side. In
front of them a farm-servant, squatted on a heap of straw, flogged on
the small horses. The wind swept the sand and straw from the
stubble-fields, the road was a broad causeway without ditches or hedges,
the horses had to wade alternately through puddles and deep sand. Yellow
sand gleamed through the scanty herbage in all directions wherever a
field-mouse had made her way to her nest or an active mole had done what
he could to diversify the unbroken plain. Wherever the ground sank,
stagnant water lodged, and there hollow willow-trees stretched their
crippled arms in the air, their boughs flapping in the wind, and their
faded leaves fluttering down into the muddy pool below. Here and there
stood a small dwarf pine, a resting-place for the crows, who, scared by
the passing carriage, flew loudly croaking over the travelers' heads.
There was no house to be seen on the road, no pedestrian, and no
conveyance of any kind.
Karl looked every now and then at his silent companion, and said at
last, pointing to the horses, "How rough their coats are, and how pretty
their gray mouse skins! I wonder how many of these beasties would go to
make up my sergeant's horse! When I took leave of my father, the old man
said, 'Perhaps I shall pay you a visit, little one, when they light the
Christmas-tree.' 'You'll never be able,' said I. 'Why not?' asked he.
'You'll never trust yourself in any post-chaise.' Then the old boy
cried, 'Oho! post-chaises are always of a stout build; I shall be sure
to trust myself in one.' But now, Mr. Anton, I see that my father never
can pay us a visit."
"Why not?"
"It is possible that he may reach Rosmin; but, as soon as he sees these
horses and this road, he will instantly turn back. 'Shall I trust
myself,' he'll say, 'in a district where sand runs between one's legs
like water, and where mice are put into harness? The ground is not firm
enough for me.'"
"The horses are not the worst things here," said Anton, absently. "Look!
these go fast enough."
"Yes," replied Karl, "but they don't go like regular horses; they
entangle their legs like two cats playing in a parsley-bed. And what
things they have for shoes--regular webbed hoofs, I declare, which no
blacksmith can ever fit."
"If we could only get on!" returned Anton; "the wind blows cold, and I
am shivering in spite of my fur."
"You have slept but little the last few nights, sir," said Karl. "The
wind blows here as if over a threshing-floor. The earth is not round
hereabouts as elsewhere, but flat as a cake. This is a complete desert;
we have been driving for more than an hour, and there is not a village
to be seen."
"A desert indeed," sighed Anton; "let us hope it may improve." They
relapsed into profound silence. At length the driver stopped near a
pool, unharnessed the horses, and led them to the water's edge, without
noticing the travelers.
"What the deuce does this mean?" cried Karl, jumping down from the
carriage.
"I am going to feed," replied the servant, sulkily, in a foreign accent.
"I am anxious to know how that will be done," said Karl. "There is not
the shadow of a bag of provender."
The horses, however, soon proved that they could live without corn; they
stretched down their shaggy heads, and began to pull the grass and weeds
at the edge of the pool, sometimes taking a draught of the dirty water.
Meanwhile the servant drew a bundle from under his seat, settled himself
under the lee of an alder-bush, and, taking his knife, cut his bread and
cheese without even glancing at the travelers.
"I say, Ignatius or Jacob," cried Karl, sharply, "how long will this
breakfast of yours last?"
"An hour," replied the man, munching away.
"And how far is it from here to the estate?"
"Six miles, or maybe more."
"You can make nothing of him," said Anton; "we must put up with the
customs of the country;" and, leaving the carriage, they went to look on
at the horses feeding.
Anton is on his way to the Polish property. He is now the baron's agent.
Anxious months have the last proved to him. The parting from his
principal and the firm had been painful in the extreme. For some time
before it, indeed, Anton had found himself alone in the midst of his
colleagues. The quiet Baumann still remained his friend, but the others
considered him a castaway. The merchant received his resignation with
icy coldness; and even in the hour of parting, his hand lay impassive as
metal in Anton's grasp. Since then, our hero had undertaken several
journeys to the capital and to creditors in the family's behalf, and now
he was on his way to set the new estate in order, accompanied by Karl,
whom he had induced to become the baron's bailiff.
Ehrenthal had, by the authority conferred on him,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from the time of the sale by auction, and hired the Polish
bailiff for the baron. There had been unfair dealings between them at
the time, and it was well known in Rosmin that the bailiff had sold off
a good deal, and been guilty of all sorts of frauds since, so that Anton
had even now no prospect of a quiet life.
"The hour is come when I may execute my commission," cried Karl, groping
in the straw under the seat. He drew out a large japanned tin case, and
carried it to Anton. "Miss Sabine gave me this in charge for you." He
then joyously opened the lid, produced the materials for an excellent
breakfast, a bottle of wine, and a silver goblet. Anton took hold of the
case.
"It has a very knowing look," said Karl. "Miss Sabine planned it
herself."
Anton examined it on all sides, and placed it carefully on a tuft of
grass; then he took up the goblet, and saw his initials engraved on it,
and underneath the words, "To thy welfare." Whereupon he forgot the
breakfast and all around him, and stood gazing at the goblet, lost in
thought.
"Do not forget the breakfast, sir," suggested Karl, respectfully.
"Sit down by me, my faithful friend; eat and drink with me. Leave off
your absurd politeness. We shall have but little, either of us, but what
we have we will share like brothers. Take the bottle if you have no
glass."
"There's nothing like leather," said Karl, taking a small leathern
drinking-cup out of his pocket. "As for 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t was
kindly meant, and I thank you; but there must be subordination, if it
were but for the sake of the others; and so, sir, be kind enough to let
me shake hands with you now, and then let things be as they were before.
Only look at the horses, Mr. Anton. My faith! the creatures devour
thistles."
Again the horses were harnessed, again they threw out their short legs
in the sand, and again the carriage rolled through the barren
district--first through an empty plain, next through a wretched
fir-wood, then past a row of low sand-hills, then over a tumble-down
bridge crossing a small stream.
"This is the property," said the driver, turning round, and pointing
with his whip to a row of dirty thatched roofs that had just come into
sight.
Anton stood up to look for the group of trees in which the Hall might be
supposed to stand. Nothing of the sort to be seen. The village was
deficient in all that adorns the home of the poorest German peasant--no
orchard, no hedged-in gardens, no lime-trees in the market-place.
"This is wretched," said he, sitting down again; "much worse than they
told us in Rosmin."
"The village looks as if under a curse," cried Karl; "no teams working
in the fields--not a cow or a sheep to be seen."
The farm-servant flogged his horses into an irregular gallop, and so
they passed through the rows of mud huts which constituted the village,
and arrived at the public house. Karl sprang from the carriage, opened
the tavern door, and called for the landlord. A Jew slowly rose from his
seat by the stove and came to the threshold. "Is the gendarme from
Rosmin come?" He is gone into the village. "Which is the way to the
farm-yard?"
The landlord, an elderly man with an intelligent countenance, described
the way in German and Polish, and remained standing at the
door--bewildered, Karl declared, by the sight of two human beings. The
carriage turned into a cross-road, planted on both sides with thick
bushes, the remains of a fallen avenue. Over holes, stones, and puddles,
it rattled on to a group of mud huts, which still had a remnant of
whitewash upon them. "The barns and stables are empty," cried Karl, "for
I see gaps in the roofs large enough to drive our carriage through."
Anton said no more; he was prepared for every thing. They drove through
a break between the stables into the farm-yard, a large irregular space,
surrounded on three sides by tumble-down buildings, and open to the
fields on the fourth. A heap of _débris_ lay there--lime and rotten
timber, the remains of a ruined barn. The yard was empty; no trace of
farm implements or human labor to be seen. "Which is the inspector's
house," inquired Anton, in dismay. The driver looked round, and at last
made up his mind that it was a small one-storied building, with straw
thatch and dirty windows.
At the noise of the wheels a man appeared on the threshold, and waited
phlegmatically till the travelers had dismounted, and were standing
close before him. He was a broad-shouldered fellow, with a bloated,
brandy-drinking face, dressed in a jacket of shaggy cloth, while behind
him peered the muzzle of an equally shaggy dog, who snarled at the
strangers. "Are you the steward of this property?"
"I am," replied the man, in broken German, without stirring from where
he was.
"And I am the agent of the new proprietor," said Anton.
"That does not concern me," growled the shaggy man, turning sharp round,
entering the house, and bolting the door within.
Anton was thoroughly roused. "Break the window in, and help me to catch
the rascal," cried he to Karl, who coolly seized a piece of wood, struck
the panes so as to make the rotten framework give way, and cleared the
opening at one leap. Anton followed him. The room was empty, so was the
next, and in it an open window--the man was gone.
"After him!" cried Karl, and dashed on in pursuit, while Anton looked
about the house and out-buildings. He soon heard the barking of a dog,
and saw Karl capture the fugitive. Hurrying to his help, he held the man
fast, while, with a kick, Karl sent the dog flying. They then contrived
to force the steward back to the house, though he kept striking out
violently all the way.
"Go to the tavern, and bring the gendarme and the landlord," cried Anton
to the driver, who, undisturbed by all that had been going on, had
meanwhile unpacked the carriage. The man accordingly drove leisurely
off, and the fugitive being got into the room, Karl found an old cloth,
and with it bound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I beg your pardon, sir,"
said he; "it is only for an hour or so, till the arrival of the Rosmin
gendarme, whom we have appointed to meet us."
Anton then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house, bu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found but the merest necessaries; no books nor papers of any kind. It
had doubtless been emptied already. A bundle projected from the
coat-pocket of the prisoner, which turned out to be receipts and legal
documents in Polish. In time, the driver returned with the landlord and
the armed policeman. The landlord stood at the door in some perplexity,
and the policeman explained in a few moments what remained to be done.
"You must make a statement to the local judge, and give the man up to
me. He shall go back in your carriage to Rosmin. You will do well to get
rid of him, for this is a wild country, and it will be safer for you to
have him at Rosmin than here, where he has friends and accomplices."
After a long search, a sheet of paper was found in a cupboard, the
statement made and submitted to the policeman, who shook his head a
little over the Polish composition, and the prisoner lifted into the
carriage, the gendarme taking his seat beside him, and saying to Anton,
"I have long expected something of the kind. You may have often occasion
to want me again." The carriage then drove away, and thus the property
came under Anton's administration. He felt as if cast on a desert
island.
His portmanteau and traveling effects were leaning against a mud wall,
and the Polish landlord was the only man who could give him and Karl any
information or advice in their forlorn condition.
Now that the steward was fairly gone, the landlord grew more
communicative, and showed himself serviceable and obliging. A long
conversation ensued, and its purport was what Anton had apprehended from
the warning given by the Commissary Walter and other Rosmin officials.
The inspector had,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done all he could in the
way of spoliation, rendered daring by a report which had found its way
from the town to the village, that the present proprietor would never be
able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estate. At last Anton said, "What that
wretched man has done away with he will have to account for; our first
care must be to preserve what is still to be found on the property. You
must be our guide to-day."
They then examined the empty buildings. Four horses and two
servants--they were gone into the wood--a few old plows, a pair of
harrows, two wagons, a britzska, a cellar full of potatoes, a few
bundles of hay, a little straw--the inventory did not take much time in
drawing up. The buildings were all out of repair, not through age, but
neglect.
"Where is the dwelling-house?" inquired Anton. The landlord led the way
out of the yard to the meadow--a broad plain, gradually sloping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brook. It had been a great pasture. The cattle had
trodden it down into holes; the snouts of greedy swine had rooted it up;
gray molehills and rank tufts of grass rose on all sides.
The landlord stretched out his hand. "There is the castle. This castle
i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he added, reverentially; "no
nobleman in the district has a stone house like that. All the gentry
here live in wood and mud buildings. Herr von Tarow, the richest of
them, has but a poor dwelling."
About three hundred yards from the last out-building rose a great brick
edifice, with a black slate roof and a thick round tower. Its gloomy
walls on this treeless pasture-land, without one trace of life around,
rose beneath the cloudy sky like a phantom fortress which some evil
spirit had evoked from the abyss--a station from which to blight all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The strangers approached it. The castle had fallen into ruins before the
builders had finished their task. The tower had stood there for ages. It
was built of unhewn stone, and had small windows and loop-holes. The
former lords of the land had looked down from its summit on the tops of
the trees, which then stretched far into the plain. They had then ruled
with a rod of iron the serfs who cultivated their land, and toiled and
died for them. Many an arrow had sped through those loop-holes at the
enemy storming below, and many a Tartar horse had been overthrown before
those massive walls. Years ago, a despot of the district had, in
expiation of former sins, begun to add to the gray tower the walls of a
holy monastery; but the monastery never got finished, and the useless
walls had already stood there long, when the late count took it into his
head to convert them into a lordly dwelling for his race, and to raise a
house unparalleled for magnificence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 front of the house was added on to both sides of the tower, which
projected in the middle. The intention had been to have a high
terrace-road up to the castle, and the principal entrance had been made
in the tower, and arched over; but the terrace never having been formed,
the stone threshold of the main door was quite inacce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ladders, and the wide opening was left. The window-spaces of
the lower floor were merely closed up with boards, while on the second
story were some window-frames of beautifully carved wood, in which large
panes had once been placed, but they had got broken. In other windows
were temporary frames of rough deal, with small panes of muddy glass let
into them. A company of jackdaws sat on the top of the tower, looking
down in amazement on the strangers, and every now and then one flew off,
screaming loudly, to contemplate the intruders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A house for crows and bats, not for human beings," said Anton. "At
least, I see no way of getting into it."
The landlord now took them round the building. Behind, where the two
wings made a sort of horse-shoe, there were low entrances to the cellars
and offices; beneath which, again, were stables, great arched kitchens,
and small cells for the serfs. A wooden staircase led to the upper
story. The door turned creaking on its hinges, and a narrow passage took
them through a side wing to the front part of the house. There all was
at least magnificently planned. The circular entrance-hall--an arched
room of the old tower--was painted in mosaic, and through the great
doorway-opening was seen a wide expans
small disturbance made by the return of Anton had gradually settled
down. Those first-class treasures of Sabine's had made way for other
specimens of damask, still of a superior kind, it is true, but which
came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e elderly cousin's comprehension. She had
been quite right in prophesying that Anton would never remark those
signs of exuberant gratitude or their withdrawal. However, one change
had been permanently made--the greatest, the best of all changes--the
clerk retained a privileged place in the heart of the young mistress of
the firm, and his tall figure often appeared as one of the circle that
Sabine's fancy loved to gather round her when at her work-table or in
her treasure-chamber.
To-day she was walking restlessly up and down before dinner. The cousin,
who heard every thing, had just told her that a maid from Ehrenthal's
had run into the office to announce Bernhard's death to his friend. "How
will he bear it?" thought she. And the name of Ehrenthal forced her
thoughts back to the past, to one now far away, and to that painful hour
when the struggle going on in her own mind had been suddenly brought to
a close by a letter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parted. And Anton had known
of that conquered feeling of hers. How considerate he had always been,
how chivalrous, how helpful! She wondered if he had any idea of the
completeness of her triumph over a girlish illusion. She shook her head.
"No, he has not. It was here, at this very table, that an accident first
betrayed me to him. That past time still rises like a cloud between us.
Whenever I sit near Wohlfart of an evening, I am conscious of another's
shadow at my side; and when he speaks to me, his tone, his manner always
seem to say, 'You are not alone; he is with you.'" Sabine started, and
lovingly passed her hand over the beautiful flowers on the table before
her, as if to dispel a painful thought. She could not tell him that she
was free from that long-felt sorrow. Now, however, when he had lost a
friend whom he so much loved, she must show him that there were other
hearts that clung to him still. And again she walked up and down, trying
to devise a way of speaking to him alone.
Dinner was announced. Anton came with the rest, and took his place at
once. There was no opportunity of exchanging a word during the meal, but
he often met her sad and sympathizing eye. "He eats nothing at all
to-day," whispered her cousin; "not even any of the roast," she added,
reproachfully. Sabine was much perturbed. Mr. Jordan had already risen;
Anton would leave the room with the rest, and she should not see him
again the whole day through. So she called out, "The great Calla is
fully blown now. You were admiring the buds the other day; will you
remain a moment; I should like to show it you?" Anton bowed and staid
behind. A few more awkward moments, then her brother rose too; and,
hurrying to Anton, she took him to the room where the flowers were.
"You have had sorrowful tidings to-day," she began.
"The tidings themselves did not surprise me," replied Anton. "The doctor
gave no hope. But I lose much in him."
"I never saw him," said Sabine; "but I know from you that his life was
lonely--poor in affection and in enjoyment."
She moved an arm-chair toward Anton, and led him on to talk about his
friend. She listened to every word with warm sympathy, and well knew
what to ask and how to comfort. It was a relief to Anton to speak of the
departed one, to describe his quiet way of life, his erudition, his
poetical enthusiasm. After a pause, Sabine looked up frankly into his
face, and asked, "Have you any tidings of Herr von Fink?"
It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his departure that she had ever breathed his
name. Anton felt how touching her confidence was, given in this hour of
his sadness. In his emotion, he seized her hand, which she was slow in
withdrawing.
"He is not happy in his new life," he gravely replied. "There was a
savage humor in his last letter, from which I gather, even more than
from his actual words, that the business into which his uncle's death
has thrown him does not suit him."
"It is unworthy," cried Sabine.
"At all events, it is not what would be recognized as honorable in this
house," replied Anton. "Fink is upright, and has lived too long with
your brother to take pleasure in the wild speculations so common on the
other side the Atlantic. His partners and colleagues are for the most
part men without a conscience, and his feelings revolt against their
companionship."
"And can Herr von Fink tolerate such relations as these for a day?"
"It is a remarkable thing that he whose own will was ever so arbitrarily
exercised, should now be obliged against that will to obey a pressure
from without, and every where to work with his hands tied. The
organization of such speculations in America is so complicated that one
shareholder can do little to alter it; and, now that Fink has attained
what used to be the goal of his wishes--a large capital, and the
management of immense districts--his condition appears more uncertain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He was always in danger of thinking slightingly
of others, now I am distressed at the bitter contempt he expresses for
his own life. His last letter paints an intolerable state of things, and
seems to point to some decisive resolve."
"There is only one resolve for him," cried Sabine. "May I ask what you
said to him in reply?"
"I entreated him instantly, come what would, to free himself from the
business in which he was entangled. I said that his own strong will
might find a way of extrication, even if that which I pointed out proved
impracticable. Then I begged of him either to carry out his old plan of
becoming a landed proprietor in America, or to return to us."
"I knew that you would write thus," said Sabine, drawing a long breath.
"Yes, Wohlfart, he shall return," said she, gently, "but he shall not
return to us."
Anton was silent.
"And do you think that Herr von Fink will follow your advice?"
"I do not know. My advice was not very American."
"But it was worthy of you," cried Sabine, with proud delight.
"An officer wishes to speak to Mr. Wohlfart," said a servant at the
door.
Anton sprang up. Sabine went to her flowers and bent mournfully over
them. The shadows of others hovered still between her friend and her.
The few words spoken by the servant filled Anton with a vague terror. He
hurried into the ante-room: there stood Eugene von Rothsattel. Anton was
gladly rushing forward to greet him, but the young soldier's face of
agony made him start back. He whispered, "My mother wishes to speak to
you; something dreadful has occurred." Anton caught up his hat, ran into
the office, hurriedly asked Baumann to excuse him to the principal, and
then accompanied the lieutenant to the baron's house.
On the way, Eugene, who had lost all self-command, said unconnectedly to
Anton, "My father last night accidentally wounded himself by a
pistol-shot--a messenger was sent to summon me--when I came, I found my
mother in a swoon--my sister and I do not know what to do--Lenore
implored my mother on her knees to send for you--you are the only one in
whom w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our distress--I understand nothing about
business, but my father's affairs must be in a dreadful state--my mother
is beside herself--the whole house is in the greatest disorder."
From what Eugene said and what he did not say; from his broken sentences
and his look of agony, Anton guessed at the horrors of the previous
evening. In the boudoir of the baroness he found Lenore, weeping and
exhausted.
"Dear Wohlfart!" cried she, taking his hand and beginning again to sob,
while her head sank powerless on his shoulder.
Meanwhile Eugene walked up and down, wringing his hands, and at length
throwing himself on the sofa, he gave himself up to silent tears.
"It is horrible, Mr. Wohlfart," said Lenore, lifting up her head. "No
one may approach my father--Eugene may not, nor I--only my mother and
old John are with him; and early this morning the merchant Ehrenthal was
here, insisting that he must see my father. He screamed at my mother,
and called my father a deceiver, till she fainted away. When I rushed
into the room, the dreadful man went off threatening her with his
clenched fist."
Anton led Lenore to a chair and waited till she had told him all.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comforting in this case, and his own heart was
wrung to the utmost by the misery he witnessed.
"Call my mother, Eugene," said Lenore, at length.
Her brother left the room.
"Do not forsake us," implored Lenore, clasping her hands; "we are at the
last gasp; even your help can not save us."
"He is dead who might perhaps have done so," mournfully replied Anton.
"Whether I can be of any use I know not, but you can not doubt my
willingness to be so."
"No," cried Lenore. "And Eugene, too, thought of you at once."
The baroness now entered. She walked wearily; but, steadying herself by
a chair, she saluted Anton with dignity. "In our position," said she,
"we need a friend who knows more of business than we three do.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prevents the baron--possibly for a long time to
come--from managing his own affairs, and, little as I understand them, I
can see that our interests require prompt measures. My children have
mentioned you to me, but I fear I am unreasonable in asking you to
devote your time to our service."
She sat down, beckoned Anton to take a chair, and said to her children,
"Leave us; I shall be better able to tell Mr. Wohlfart the little that I
know when I do not see your grief."
When they were alone, she motioned him nearer and tried to speak, but
her lips quivered, and she hid her face in her handkerchief.
"Before I can consent, gracious lady," said he, "to your reposing in me
such confidence as this, I must first inquire whether the baron has no
relative or intimate friend to whom you could with less pain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I pray you to remember that my own knowledge of business
is but small, and my position not one to constitute me a proper
counselor to the baron."
"I know no one," said the baroness, hopelessly. "It is less painful to
me to tell you what I can not conceal, than to one of our own circle.
Consider yourself a physician sent for to visit a patient. The baron has
this morning told me some particulars of his present circumstances." And
then she proceeded to relate what she had gathered as to the nature of
his embarrassments, the danger in which the family property was placed,
and the capital needed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Polish estate.
"My husband," continued she, "has given me the key of his desk, and he
wishes Eugene, with the help of a man of business, to go over his
papers. I now request of you to make this examination together with my
son. When you need explanations, I will try to obtain them from the
baron. The question is now, whether you are inclined to undertake this
trouble for us, who are only strangers."
"I am most willing to do so," earnestly replied Anton; "and I hope that
the kindness of my principal will allow me the time needful for the
purpose, if you do not consider it more advisable to depute the baron's
experienced legal adviser to the task."
"There will be an opportunity of asking that gentleman's advice later,"
said the baroness.
Anton rose. "When do you wish to begin?"
"Immediately. I fear there is not a day to lose. I shall do all I can to
help you look the papers over." She led Anton into the next room, called
in Eugene, and unlocked the baron's desk. As she opened it she lost her
self-command for a moment, and moving to the window, the quivering of
the curtains betrayed the anguish that shook her fragile frame.
The mournful task began. Hour after hour passed. Eugene was in no
condition to peruse any thing, but his mother reached letters and
documents to Anton, and, though often obliged to desist a while, she
bravely returned to the task. Anton placed the papers in order, and
sought, by glancing over each, to arrive at least at a superficial view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It was evening, when the old servant opened the door in dismay, and
called out, "He is there again." The baroness could not repress a slight
scream, and made a gesture of aversion.
"I have told him that no one is at home, but he will not be dismissed;
he makes such a noise on the steps. I can not get rid of him."
"It will kill me if I hear his voice again," murmured the baroness.
"If the man be Ehrenthal," said Anton, rising, "I will try to get him
away. We have now done what was most necessary; have the goodness to
lock up these papers, and to allow me to return to-morrow." The baroness
silently assented, and sank back in her chair. Anton hurried off to the
ante-room, whence he could hear Ehrenthal's loudly-raised voi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usurer shocked him. His hat pushed half off his
head, his pale face swelled as if by drinking, his glazed eyes red with
tears, Ehrenthal stood before him, calling in broken sentences for the
baron, wailing and cursing alternately. "He must come! he must come at
once!" cried he; "the wicked man! A nobleman, indeed! he is a vagabond,
after whom I will send the police. Where is my money? Where is my
security? I want my mortgage from this man who is not at home."
Anton went straight up to him, and asked, "Do you know me, Mr.
Ehrenthal?" Ehrenthal turned his glazed eyes upon him, and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 friend of his dead son.
"He loved you!" he cried, in a lamentable voice. "He spoke to you more
than to his father. You were the only friend that he had on earth. Have
you heard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house of Ehrenthal?" continued he, in
a whisper. "Just as they stole the papers he died. He died with a hand
like this," and clenching his fist he struck his forehead. "Oh my son!
my son! why didst not thou forgive thy father!"
"We will go to your son," said Anton, taking the arm of the old man, who
unresistingly allowed himself to be led back to his own house.
From thence Anton hurried to Councilor Horn, with whom he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It was late before he returned home. In the midst of his anxiety about
those whose prosperity had filled his imagination years before,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in their adversity, reposed in him, dilated his
breast with a feeling of pride. He burned with desire to help them, and
hoped that his zealous devotion might yet find some way of rescue. As
yet he saw none. Looking up at the great building before him, so firm
and secure, in the moonlight, a thought flashed into his mind. If any
man could help them, it was his principal. His keen eye would be able to
unravel all the dark secrets in which the baron was entangled, and his
iron strength of will would crush the villains who held the unfortunate
nobleman in their power. And then he had a noble nature; he always
decided on the right, without an effort or a struggle. Anton looked at
the first floor. The whole house-front was dark, but in a corner room a
light still burned. It was the private office of his chief.
With sudden resolve, Anton begged the servant to take him to Mr.
Schröter, who looked with amazement at the unexpected visitor, and asked
what brought him, and whether any thing had happened.
"I implore your counsel--I implore your help," cried Anton.
"For yourself or for others?" inquired the merchant.
"For a family with whom I have accidentally become connected. They are
lost if a strong hand does not ward off the impending catastrophe."
Anton then rapidly related the occurrences of the afternoon, and,
seizing his principal's hand in his emotion, cried, "Have pity upon the
unhappy ladies, and help them."
"Help them!" replied the merchant; "how can I? Have you been
commissioned to apply to me, or are you only following the impulse of
your own feelings?"
"I am not commissioned; it is only the interest that I take in the
baron's fate which leads me to you."
"And what right have you to inform me of facts communicated in strict
confidence to yourself by the baron's lady?" asked the merchant, dryly.
"I am committing no indiscretion in telling you what will, in a few
days, be no secret, even to strangers."
"You are unusually excited, otherwise you would not forget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hatever, does a man of business venture to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without the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Of course, I shall make no wrong use of what you have said, but it was
by no means business-like, Wohlfart, to be so open toward me."
Anton was silent, feeling, indeed, that his principal was right, but yet
it seemed hard to be blamed for reposing confidence at such a time as
this. The merchant walked silently up and down; at length, stopping
before Anton, he said, "I do not now inquire how you come to take so
warm an interest in this family. I fear it is an acquaintance you owe to
Fink."
"You shall hear all," said Anton.
"Not at present. I will now content myself with repeating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interfere in these affairs without being specially
applied to by the parties themselves. I may add that I by no means wish
for such an application, and do not disguise from you that, were it
made, I should probably decline to do any thing for the Baron
Rothsattel."
Anton's feelings were roused to the utmost. "The question is the rescue
of an honorable man, and of lovely and amiable women from the toils of
rogues and impostors. To me, this seems the duty of every one; I, at
least, consider it a sacred obligation which I dare not shrink from. But
without your support I can do nothing."
"And how do you think this embarrassed man can be helped?" inquired the
merchant, seating himself.
With somewhat more composure, Anton repli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an experienced man of business making himself master of the case. There
must be some way of circumventing these villains. Your penetration would
discover it."
"Any attorney would be far more likely to do so, and the baron might
readily engage the services of experienced and upright legal advisers.
If his enemies have done any thing illegal, the quick eye of a lawyer is
the most likely to detect it."
"Alas! the baron's own lawyer gives but little hope," replied Anton.
"Then, my dear Wohlfart, no other is likely to do much good. Show me an
embarrassed man who has strength to grasp an offered hand, and bid me
help him, and for the sake of all I owe you, I will not refuse to do so.
I think you are convinced of this."
"I am," said Anton, dejectedly.
"From all I hear, however," the merchant went on,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the baron. From what I gather from general report, as well as from
you, his embarrassments arise from his having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usurers, which proves him deficient in what alone ennobles the life of
any man--good sense, and the power of steady exertion."
Anton could only sigh his assent.
"To help such a man," inexorably continued the merchant, "is a futile
attempt, against which reason may well protest. We are not to despair of
any, but want of strength is the most hopeless case of all. Our power of
laboring for others being limited, it becomes our duty to inquire,
before we devote our time to the weak, whether we are not thus
diminishing our chances of helping better men."
Anton interrupted him. "Does he not deserve every allowance to be made
for him? He was brought up to exact much; he has not learned, as we
have, to make his way by his own labor."
The merchant laid his hand on the young man's shoulder. "The very
reason. Believe me, a large number of these landed gentry, who pay the
penalty of their old family memories, are beyond help. I am the last to
deny that many worthy and admirable men belong to this class. Indeed,
wherever remarkable talent or nobility of character shoots up among
them, no doubt their position offers peculiar scope for its development,
but for average men it is not a favorable one. He who considers it his
hereditary privilege to enjoy life, and who assumes a distinguished
position in virtue of his family, will very often fail to put forth his
whole strength in order to deserve that position. Accordingly, numbers
of our oldest families are declining, and their fall will be no loss to
the state. Their family associations make them haughty without any
right to be so--limit their perceptions and confuse their judgment."
"Even if all this be true," cried Anton, "it does not absolve us from
helping individuals of the class who have excited our sympathy."
"No," said the principal, "if it be excited. But it does not glow so
rapidly in advancing years as in youth. The baron has endeavored to
isolate his property from the current of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leave it forever to his family. Forever! You, as a merchant, know how to
estimate the attempt. True, every rational man must allow it to be
desirable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same soil should be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We all prize what our forefathers have possessed before
us, and Sabine would unlock every room in this house with pride, because
her great-great-grandmother turned the same keys before her. It is
therefore natural that the landed proprietor should desire to preserve
those familiar scenes, which are the source of his own prosperity, to
those nearest and dearest to him. But there must be means to this end,
and these means are the making his own existence available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increase of his patrimony. Where energy dies in families
or individuals, then it is well that their means die too, that their
money should circulate through other hands, and their plowshare pass to
those who can guide it better. A family that has become effete through
luxury ought to sink down into common life, to make room for the
uprising of fresh energies and faculties. Every one who seeks, at the
cost of free activity for others, to preserve permanent possessions and
privileges for himself or his family, I must look upon as an enemy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social state. And if such a man ruin
himself in his endeavors, I should feel no malicious pleasure in his
downfall, but I should say that he is rightly served, because he has
sinned against a fundamental law of our social being; consequently, I
should consider it doubly wrong to support this man, because I could but
fear that I should thus be supporting an unsound condition of the body
politic."
Anton looked down mournfully. He had expected sympathy and warm
concurrence, and he met with disaffection and coldness that he despaired
of conquering. "I can not gainsay you," he at length replied; "but in
this case I can not feel as you do. I have been witness to the
unspeakable distress in the baron's family, and my whole soul is full
of sadness and sympathy, and of the wish to do something for those who
have opened their heart to me. After what you have said, I dare no
longer ask you to trouble yourself with their affairs, but I have
promised the baroness to assist her as far as my small powers permit,
and your kindness allows. I implore you to grant me permission to do
this. I shall endeavor to be regular in my attendance at the office, but
if during the next few weeks I am occasionally absent, I must ask you to
excuse me."
Once more the merchant walked up and down the room, and then, looking at
Anton's excited face, with deep seriousness and something of regret, he
replied, "Remember, Wohlfart, that every occupation which excites the
mind soon obtains a hold over a man, which may retard as well as advance
his success in life. It is thi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 to agree
to your wishes."
"I know it," said Anton, in a low voice; "but I have now no choice
left."
"Well, then, do what you must," said the merchant, gloomily; "I will lay
no hinderance in your way; and I hope that after a few weeks you will be
able to consider the whole circumstances more calmly." Anton left the
room, and the merchant stood looking long with frowning brow at the
place his clerk had occupied.
Nor was Anton in a more congenial mood. "So cold, so inexorable!"
exclaimed he, as he reached his own room. He began to suspect that his
principal was more selfish and less kindly than he had hitherto
supposed. Many an expression of Fink's recurred to his mind, as well as
that evening when young Rothsattel, in his boyish conceit, had spoken
impertinently to the merchant. "Is it possible," thought he, "that that
rude speech should be unforgotten?" And his chief's keen, deep-furrowed
face lost inexpressibly by contrast with the fair forms of the noble
ladies. "I am not wrong," he cried to himself; "let him say what he
will, my views are more just than his, and henceforth my destiny shall
be to choose for myself the way in which I shall walk." He sat long in
the darkness, and his thoughts were gloomy as it; then he went to the
window to look down into the dark court below. A great white blossom
rose before him like a phantom. Striking a light, he saw that it was the
beautiful Calla out of Sabine's room. It hung down mournfully on its
broken stem. Sabine had had it placed there. This little circumstance
struck him as a mournful omen.
Meanwhile Sabine, taper in hand, entered her brother's room.
"Good-night, Traugott," nodded she. "Wohlfart has been with you this
evening; how long he staid!"
"He will leave us," replied the merchant, gloomily.
Sabine started and dropped her taper on the table. "For God's sake, what
has happened? Has Wohlfart said that he was going away?"
"I do not yet know it, but I see it coming step by step; and I can not,
and still less can you, do any thing to retain him. When he stood before
me here with glowing cheeks and trembling voice, pleading for a ruined
man, I found out what it was that lured him away."
"I do not understand you," said Sabine, looking full at her brother.
"He chooses to become the confidential friend of a decayed noble. A pair
of bright eyes draws him away from us: it seems to him a worthy object
of ambition to become Rothsattel's man of business. This intimacy with
nobility is the legacy bequeathed to him by Fink."
"And you have refused to help him?" inquired Sabine, in a low voice.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said the merchant, harshly; and he
turned to his writing-table.
Sabine slowly withdrew. The taper trembled in her hand as she passed
through the long suite of rooms listening to her own footfall, and
shuddering as the feeling came over her that an invisible companion
glided by her side. This was the revenge of that other. The shadow that
once fell on her innocent life now drove her friend away from their
circle. Anton's affections clung to another. She had but been in his
eyes a mere stranger, who had once loved and languished for one now far
away, and who now, in widow's weeds, looked back regretfully to the
feelings of her youth.
The few next weeks were spent by Anton in over-hard work. He had great
difficulty in keeping up his counting-house duties, while he spent every
spare hour in conference with the baroness and the lawyer.
In the mean time, the misfortunes of the baron ran their course. He had
not been able to pay the interest of the sums with which his estate was
burdened. When last they were due, a whole series of claims was brought
against him, and the estate fell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district authorities. Complicated lawsuits arose. Ehrenthal complained
loudly, claiming the first mortgage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nay, he
was inclined to advance claims on the last mortgage offered by the baron
in the recent fatal hour. Löbel Pinkus also appeared as claimant of the
first mortgage, and asserted that he had paid the whole sum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Ehrenthal had no proof to bring forward, and had been
for some weeks past quite unable to manage his own affairs, while
Pinkus, on the contrary, fought with every weapon a hardened sinner can
devise or employ, and the deeds which the baron had executed at Veitel's
suggestion proved to be so capital a master-stroke of the cunning
advocate, that the baron's man of business had, from the first, little
hope of the case. We may here observe that Pinkus did eventually win it,
and that the mortgage was made over to him.
Anton was now gradually gaining some insight into the baron's
circumstances. But the double sale of the first mortgage was still kept
a secret by the latter, even from his wife. He declared Ehrenthal's
claim unfounded, and even expressed a suspicion that he had himself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robbery in his office. Indeed, he really
believed this. Then the name of Itzig was never broached, and the
suspicion against Ehrenthal, which the baron's lawyer shared, prevented
Anton seeking any explanation from him.
Meanwhile, an estrangement had sprung up between our hero and his
principal, which the whole counting-house remarked with surprise. The
merchant scowled at Anton's vacant seat when the latter chanced to be
absent during office-hours, or looked coldly at his clerk's face, made
pale as it was with excitement of mind and night-work. He took no notice
of his new occupation, and never seemed to remark him. Even to his
sister he maintained a stiff-necked silence; nor could all her attempts
lead him to speak of Anton, who, on his side, felt his heart revolt
against this coldness. After his return, to be treated like a child of
the house, praised, promoted, petted, and now to be treated like a mere
hireling, who is not worth the bread thrown to him; to be a toy of an
incomprehensible caprice--this, at least, he had not deserved; so he
became reserved toward the whole family, and sat silent at his desk; but
he fel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now and the then so keenly, that often,
when alone, he would spring up and stamp on the ground in the bitter
indignation of his heart.
One comfort remained. Sabine was not estranged. True, he saw little of
her, and at dinner she seemed to avoid speaking to him, but he knew that
she was on his side.
A few days after his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the merchant, she came down
stairs as he stood in the hall, and had to pass him by so closely that
her dress touched him. He had retreated, and made a formal bow, but she
looked at him imploringly, and whispered, "You must not be estranged
from me." It was an affair of a moment, but the faces of both were
radiant with a happy understanding.
The time had now arrived when Mr. Jordan was to quit the firm. The
principal again called Anton into his little office, and without any
severity, but also without a trace of his former cordiality, began: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o you my intention of appointing you Jordan's
successor; but,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your time has been more taken
up with other business than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such a post, I
therefore ask you whether you are now at liberty to undertake Jordan's
duties?"
"I am not," replied Anton.
"Can you name any--not very distant--time when you will be free from
your present occupation? In that case I will endeavor to find a
substitute until then."
Anton sorrowfully replied, "I can not at present say when I shall again
be master of my whole time; and, besides, I feel that, even as it is, I
tax your indulgence by many irregularities. Therefore, Mr. Schröter, I
beg that you will fill up this post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me."
The merchant's brow grew furrowed and dark, and he silently bowed
assent. Anton felt as he closed the door that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m was now complete, and, resuming his place, he leaned his throbbing
head on his hand. A moment later Baumann was summoned to the principal,
and Jordan's situation conferred upon him. On returning to the office,
he went up to Anton and whispered, "I refused at first, but Mr. Schröter
insisted. I am doing you an injustice." And that evening Mr. Baumann, in
his own room, read in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the chapters treating of
the unjust Saul (the principal), and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Jonathan
and the persecuted David, and strengthened his heart thereby.
The next day Anton was summoned to the baroness. Lenore and her mother
sat before a large table covered with jewel-boxes and toilette elegances
of every description, while a heavy iron chest stood at their feet. The
curtains were drawn, and the subdued light shone softly into the richly
furnished room. On the carpet glowed wreaths of unfading flowers, and
the clock ticked cheerfully in its alabaster case. Under the shade of
flowering plants sat the two love-birds in their silvered cage, hopping
from perch to perch, screaming ceaselessly, or sitting up quietly close
to each other. The whole room was beauty and perfume. "For how long?"
thought Anton. The baroness rose. "We are already obliged to trouble you
again," said she; "we are engaged in a very painful occupation." On the
table were all manner of ornaments, gold chains, brilliants, rings,
necklaces, gathered into a heap.
"We have been looking out all that we can dispense with," said the
baroness, "and now pray you to undertake to sell these things for us. I
have been told that some of them are of value, and as we are now in much
need of money, we turn here for help."
Anton looked in perplexity at the glittering heap.
"Tell us, Wohlfart," cried Lenore, anxiously, "is this necessary? can it
be of any use? Mamma has insisted upon setting apart for sale all our
ornaments, and whatever plate is not in daily use. What I can give is
not worth talking of, but my mother's jewels are costly; many of them
were presents made to her in youth, which she shall not part with unless
you say that it is necessary."
"I fear," said Anton, gravely, "that it will prove so."
"Take them," said the baroness to Anton; "I shall be calmer when I know
that we have at least done what we could."
"But do you wish to part with all?" inquired Anton, anxiously. "Much
that is dear to you may have but little value in a jeweler's eyes."
"I shall never wear an ornament again," quietly replied the baroness.
"Take them all;" and, holding her hands before her eyes, she turned
away.
"We are torturing my mother," cried Lenore, hastily; "will you lock up
all that is on the table, and get them out of the house as soon as you
can?"
"I can not undertake the charge of these valuables," said Anton,
"without taking some measures to decrease my own responsibility. First
of all, I will in your presence make a short note of all you intrust to
me."
"What useless cruelty!" exclaimed Lenore.
"It will not take long."
Anton took out a few sheets from his pocket-book, and began to note down
the different articles.
"You shall not see it done, mother," said Lenore, drawing her mother
away, and then returning to watch Anton at his task.
"These preparations for the market are horrible," said she. "My mother's
whole life will be sold; some memory of hers is linked with every single
thing. Look, Wohlfart, the princess gave her this diamond ornament when
she married my father."
"They are magnificent brilliants," cried Anton, admiringly.
"This ring was my grandfather's, and these are presents of poor papa's.
Alas! no man can know how we love all these things. It was always a
festival to me when mamma put on her diamonds. Now we come to my
possessions. They are not worth much. Do you think this bracelet good
gold?" She held out her hand as she spoke.
"I do not know."
"It shall go with the rest," said Lenore, taking it off. "Yes, you are a
kind, good man, Wohlfart," continued she, looking trustfully into his
tearful eyes; "do not forsake us. My brother has no experience, and is
more helpless than we are. It is a frightful position for me. Before
mamma I do all I can to be composed, else I could scream and weep the
whole day through." She sank in a chair, still holding his hand. "Dear
Wohlfart, do not forsake us."
Anton bent over her, and looked with passionate emotion at the lovely
face that turned so trustfully to him in the midst of its tears.
"I will be helpful to you when I can," said he, in the fullness of his
heart. "I will be at hand whenever you need me. You have too good an
opinion of my information and my faculties; I can be of less assistance
to you than you suppose, but what I can, that I will do in any and every
possible way."
Their hands parted with a warm pressure; the affair was settled.
The baroness now returned. "Our lawyer was with me this morning," said
she; "and now I must ask for your opinion on another subject. He tells
me that there is no prospect of preserving the baron's family estate."
"At this time, when interest is high, and money difficult to get, none,"
replied Anton.
"And you, too, think that we must turn all our efforts toward preserving
the Polish property?"
"I do," was the answer.
"For that, also, money will be necessary. Perhaps I may be able through
my relatives to intrust you with a small sum, which, with the help of
that"--she pointed to the iron chest--"may suffice to cover the first
necessary expenses. I do not, however, wish to sell the jewels here, and
a journey to the residence would be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cure the
sum to which I have just alluded. The baron's lawyer has spoken most
highly of your capacity for business. It is his wish which now decides
me to make a proposal to you. Will you for the next few years, or, at
all events, until our greatest difficulties are over, devote your whole
time to our affairs? I have consulted my children, and they agree with
me in believing that in your assistance lies our only hope of rescue.
The baron, too, has come in to the plan. The question now is whether
your circumstances allow you to give your support to our unfortunate
family. We shall be grateful to you, whatever conditions you affix; and
if you can find any way of making our great obligations to you apparent
in the position you hold, pray impart it to me."
Anton stood petrified. What the baroness required of him was separation
from the firm, separation from his principal, and from Sabine! Had this
thought occurred to him before, when standing in Lenore's presence or
bending over the baron's papers? At all events, now that the words were
spoken, they shocked him. He looked at Lenore, who stood behind her
mother with hands clasped in supplication. At length he replied, "I
stand in a position which I can not leav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others.
I was not prepared for this proposal, and beg to have time allowed me
for consideration. It is a step which will decide my whole future life."
"I do not press you," said the baroness; "I only request your
consideration. Whatever your decision be, our warmest gratitude will
still be yours; if you are unable to uphold our feeble strength, I fear
that we shall find no one to do so. You will think of that," she added,
beseechingly.
Anton hurried through the street with throbbing pulse. The noble lady's
glance of entreaty, Lenore's folded hands, beckoned him out of the
gloomy counting-house into a sphere of greater liberty, into a new
future, from whose depths bright images flashed out upon his fancy. A
request had been frankly made, and he was strongly inclined to justify
the confidence that prompted it. Those ladies required an unwearied,
self-sacrificing helper to save them from utter ruin, and if he
followed his impulse he should be doing a good work--fulfilling a duty.
In this mood he entered the merchant's dwelling. Alas! all that he saw
around him seemed to stretch out a hand to detain him. As he looked at
the warehouse, the good-humored faces of the porters, the chains of the
great scales, the hieroglyphics of the worthy Pix, again he felt that
this was the place that he belonged to. Sabine's dog kissed his hand,
and ran before him to his room--his and Fink's room. Here the childish
heart of the orphan boy had found a friend, kind companions, a home, a
definite and honorable life-purpose. Looking down through his window on
all the long-familiar objects, he saw a light in Sabine's store-chamber.
How often he had sought for that light, which brightened the whole great
building, and brought a sense of comfort and cheerfulness even into his
room. He now sprang up suddenly, and said to himself, "She shall
decide."
Sabine started in amazement when Anton appeared before her. "I am
irresistibly impelled to seek you," cried he. "I have to decide upon my
future life, and I feel undetermined, and unable to trust to my own
judgment. You have always been a kind friend to me since the day of my
arrival. I am accustomed to look up to you, and to think of you in
connection with all that interests me here. Let me hear your opinion
from your own lips. The Baroness Rothsattel has to-day proposed to me
permanently to undertake the situation of confidential adviser and
manager of the baron's affairs. Shall I accept; or shall I remain here?
I know not--tell me what is right both for myself and others."
"Not I," said Sabine, drawing back and growing very pale. "I can not
venture to decide in the matter. Nor do you wish me to do so, Wohlfart,
for you have already decided."
Anton looked straight before him and was silent.
"You have thought of leaving this house, and a wish to do so has sprung
out of the thought. And I am to justify you, and approve your resolve!
This is what you require of me," continued she, bitterly. "But this,
Wohlfart, I can not do, for I am sorry that you go away from us."
She turned away from him and leaned on the back of a chair.
"Oh, be not angry with me too!" said Anton; "that I can not bear. I have
suffered much of late. Mr. Schröter has suddenly withdrawn from me the
friendly regard that I long held my life's greatest treasure. I have not
deserved his coldness. What I have been doing has not been wrong, and
it was done with his knowledge. I had been spoiled by his kindness; I
have the more deeply felt his displeasure. My only comfort has been that
you did not condemn me. And now, do not you be cold toward me, else I
shall be wretched forever. There is not a soul on earth to whom I can
turn for affectionate comprehension of my difficulties. Had I a sister,
I should seek her heart to-day. You do not know what to me, lonely as I
am, your smile, your kindly shake of the hand has been till now. Do not
turn coldly from me, I beseech you."
Sabine was silent. At length she inquired, still with averted face,
"What draws you to those strangers; is it a joyful hope, is it sympathy
alone? Give this question close consideration before you answer it to
yourself at least."
"What it is that makes it possible for me to leave this house," said
Anton, "I do not myself know. If I can give a name to my motives, it is
gratitude felt toward one. She was the first to speak kindly to the
wandering boy on his way out into the world. I have admired her in the
peaceful brightness of her former life. I have often dreamed childish
dreams about her. There was a time when a tender feeling for her filled
my whole heart, and I then believed myself forever the slave of her
image. But years bring changes, and I learned to look on men and on life
with other eyes. Then I met her again, distressed, unhappy, despairing,
and my compassion became overmastering. When I am away from her, I know
that she is nothing to me; when I am with her, I feel only the spell of
her sorrow. Once, when I had to depart out of her circle like a culprit,
she came to me, and before the whole scornful assembly she gave me her
hand and acknowledged me her friend; and now she comes and asks for my
hand to help her father. Can I refuse it? Is it wrong to feel as I do? I
know not, and no one can tell me--no one but you alone."
Sabine's head had sunk down to the back of the chair on which she bent.
She now suddenly raised it, and with tearful eyes, and a voice full of
love and sorrow, cried, "Follow the voice that calls you. Go, Wohlfart,
go."
CHAPTER XXVII.
On a cold October day, two men were seen driving through the latticed
gate of the town of Rosmin on toward the plain, which stretched out
before them monotonous and boundless. Anton sat wrapped in his fur coat,
his hat low on his forehead, and at his side was young Sturm, in an old
cavalry cloak, with his soldier's cap cocked cheerily on one side. In
front of them a farm-servant, squatted on a heap of straw, flogged on
the small horses. The wind swept the sand and straw from the
stubble-fields, the road was a broad causeway without ditches or hedges,
the horses had to wade alternately through puddles and deep sand. Yellow
sand gleamed through the scanty herbage in all directions wherever a
field-mouse had made her way to her nest or an active mole had done what
he could to diversify the unbroken plain. Wherever the ground sank,
stagnant water lodged, and there hollow willow-trees stretched their
crippled arms in the air, their boughs flapping in the wind, and their
faded leaves fluttering down into the muddy pool below. Here and there
stood a small dwarf pine, a resting-place for the crows, who, scared by
the passing carriage, flew loudly croaking over the travelers' heads.
There was no house to be seen on the road, no pedestrian, and no
conveyance of any kind.
Karl looked every now and then at his silent companion, and said at
last, pointing to the horses, "How rough their coats are, and how pretty
their gray mouse skins! I wonder how many of these beasties would go to
make up my sergeant's horse! When I took leave of my father, the old man
said, 'Perhaps I shall pay you a visit, little one, when they light the
Christmas-tree.' 'You'll never be able,' said I. 'Why not?' asked he.
'You'll never trust yourself in any post-chaise.' Then the old boy
cried, 'Oho! post-chaises are always of a stout build; I shall be sure
to trust myself in one.' But now, Mr. Anton, I see that my father never
can pay us a visit."
"Why not?"
"It is possible that he may reach Rosmin; but, as soon as he sees these
horses and this road, he will instantly turn back. 'Shall I trust
myself,' he'll say, 'in a district where sand runs between one's legs
like water, and where mice are put into harness? The ground is not firm
enough for me.'"
"The horses are not the worst things here," said Anton, absently. "Look!
these go fast enough."
"Yes," replied Karl, "but they don't go like regular horses; they
entangle their legs like two cats playing in a parsley-bed. And what
things they have for shoes--regular webbed hoofs, I declare, which no
blacksmith can ever fit."
"If we could only get on!" returned Anton; "the wind blows cold, and I
am shivering in spite of my fur."
"You have slept but little the last few nights, sir," said Karl. "The
wind blows here as if over a threshing-floor. The earth is not round
hereabouts as elsewhere, but flat as a cake. This is a complete desert;
we have been driving for more than an hour, and there is not a village
to be seen."
"A desert indeed," sighed Anton; "let us hope it may improve." They
relapsed into profound silence. At length the driver stopped near a
pool, unharnessed the horses, and led them to the water's edge, without
noticing the travelers.
"What the deuce does this mean?" cried Karl, jumping down from the
carriage.
"I am going to feed," replied the servant, sulkily, in a foreign accent.
"I am anxious to know how that will be done," said Karl. "There is not
the shadow of a bag of provender."
The horses, however, soon proved that they could live without corn; they
stretched down their shaggy heads, and began to pull the grass and weeds
at the edge of the pool, sometimes taking a draught of the dirty water.
Meanwhile the servant drew a bundle from under his seat, settled himself
under the lee of an alder-bush, and, taking his knife, cut his bread and
cheese without even glancing at the travelers.
"I say, Ignatius or Jacob," cried Karl, sharply, "how long will this
breakfast of yours last?"
"An hour," replied the man, munching away.
"And how far is it from here to the estate?"
"Six miles, or maybe more."
"You can make nothing of him," said Anton; "we must put up with the
customs of the country;" and, leaving the carriage, they went to look on
at the horses feeding.
Anton is on his way to the Polish property. He is now the baron's agent.
Anxious months have the last proved to him. The parting from his
principal and the firm had been painful in the extreme. For some time
before it, indeed, Anton had found himself alone in the midst of his
colleagues. The quiet Baumann still remained his friend, but the others
considered him a castaway. The merchant received his resignation with
icy coldness; and even in the hour of parting, his hand lay impassive as
metal in Anton's grasp. Since then, our hero had undertaken several
journeys to the capital and to creditors in the family's behalf, and now
he was on his way to set the new estate in order, accompanied by Karl,
whom he had induced to become the baron's bailiff.
Ehrenthal had, by the authority conferred on him,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from the time of the sale by auction, and hired the Polish
bailiff for the baron. There had been unfair dealings between them at
the time, and it was well known in Rosmin that the bailiff had sold off
a good deal, and been guilty of all sorts of frauds since, so that Anton
had even now no prospect of a quiet life.
"The hour is come when I may execute my commission," cried Karl, groping
in the straw under the seat. He drew out a large japanned tin case, and
carried it to Anton. "Miss Sabine gave me this in charge for you." He
then joyously opened the lid, produced the materials for an excellent
breakfast, a bottle of wine, and a silver goblet. Anton took hold of the
case.
"It has a very knowing look," said Karl. "Miss Sabine planned it
herself."
Anton examined it on all sides, and placed it carefully on a tuft of
grass; then he took up the goblet, and saw his initials engraved on it,
and underneath the words, "To thy welfare." Whereupon he forgot the
breakfast and all around him, and stood gazing at the goblet, lost in
thought.
"Do not forget the breakfast, sir," suggested Karl, respectfully.
"Sit down by me, my faithful friend; eat and drink with me. Leave off
your absurd politeness. We shall have but little, either of us, but what
we have we will share like brothers. Take the bottle if you have no
glass."
"There's nothing like leather," said Karl, taking a small leathern
drinking-cup out of his pocket. "As for 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t was
kindly meant, and I thank you; but there must be subordination, if it
were but for the sake of the others; and so, sir, be kind enough to let
me shake hands with you now, and then let things be as they were before.
Only look at the horses, Mr. Anton. My faith! the creatures devour
thistles."
Again the horses were harnessed, again they threw out their short legs
in the sand, and again the carriage rolled through the barren
district--first through an empty plain, next through a wretched
fir-wood, then past a row of low sand-hills, then over a tumble-down
bridge crossing a small stream.
"This is the property," said the driver, turning round, and pointing
with his whip to a row of dirty thatched roofs that had just come into
sight.
Anton stood up to look for the group of trees in which the Hall might be
supposed to stand. Nothing of the sort to be seen. The village was
deficient in all that adorns the home of the poorest German peasant--no
orchard, no hedged-in gardens, no lime-trees in the market-place.
"This is wretched," said he, sitting down again; "much worse than they
told us in Rosmin."
"The village looks as if under a curse," cried Karl; "no teams working
in the fields--not a cow or a sheep to be seen."
The farm-servant flogged his horses into an irregular gallop, and so
they passed through the rows of mud huts which constituted the village,
and arrived at the public house. Karl sprang from the carriage, opened
the tavern door, and called for the landlord. A Jew slowly rose from his
seat by the stove and came to the threshold. "Is the gendarme from
Rosmin come?" He is gone into the village. "Which is the way to the
farm-yard?"
The landlord, an elderly man with an intelligent countenance, described
the way in German and Polish, and remained standing at the
door--bewildered, Karl declared, by the sight of two human beings. The
carriage turned into a cross-road, planted on both sides with thick
bushes, the remains of a fallen avenue. Over holes, stones, and puddles,
it rattled on to a group of mud huts, which still had a remnant of
whitewash upon them. "The barns and stables are empty," cried Karl, "for
I see gaps in the roofs large enough to drive our carriage through."
Anton said no more; he was prepared for every thing. They drove through
a break between the stables into the farm-yard, a large irregular space,
surrounded on three sides by tumble-down buildings, and open to the
fields on the fourth. A heap of _débris_ lay there--lime and rotten
timber, the remains of a ruined barn. The yard was empty; no trace of
farm implements or human labor to be seen. "Which is the inspector's
house," inquired Anton, in dismay. The driver looked round, and at last
made up his mind that it was a small one-storied building, with straw
thatch and dirty windows.
At the noise of the wheels a man appeared on the threshold, and waited
phlegmatically till the travelers had dismounted, and were standing
close before him. He was a broad-shouldered fellow, with a bloated,
brandy-drinking face, dressed in a jacket of shaggy cloth, while behind
him peered the muzzle of an equally shaggy dog, who snarled at the
strangers. "Are you the steward of this property?"
"I am," replied the man, in broken German, without stirring from where
he was.
"And I am the agent of the new proprietor," said Anton.
"That does not concern me," growled the shaggy man, turning sharp round,
entering the house, and bolting the door within.
Anton was thoroughly roused. "Break the window in, and help me to catch
the rascal," cried he to Karl, who coolly seized a piece of wood, struck
the panes so as to make the rotten framework give way, and cleared the
opening at one leap. Anton followed him. The room was empty, so was the
next, and in it an open window--the man was gone.
"After him!" cried Karl, and dashed on in pursuit, while Anton looked
about the house and out-buildings. He soon heard the barking of a dog,
and saw Karl capture the fugitive. Hurrying to his help, he held the man
fast, while, with a kick, Karl sent the dog flying. They then contrived
to force the steward back to the house, though he kept striking out
violently all the way.
"Go to the tavern, and bring the gendarme and the landlord," cried Anton
to the driver, who, undisturbed by all that had been going on, had
meanwhile unpacked the carriage. The man accordingly drove leisurely
off, and the fugitive being got into the room, Karl found an old cloth,
and with it bound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I beg your pardon, sir,"
said he; "it is only for an hour or so, till the arrival of the Rosmin
gendarme, whom we have appointed to meet us."
Anton then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house, bu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found but the merest necessaries; no books nor papers of any kind. It
had doubtless been emptied already. A bundle projected from the
coat-pocket of the prisoner, which turned out to be receipts and legal
documents in Polish. In time, the driver returned with the landlord and
the armed policeman. The landlord stood at the door in some perplexity,
and the policeman explained in a few moments what remained to be done.
"You must make a statement to the local judge, and give the man up to
me. He shall go back in your carriage to Rosmin. You will do well to get
rid of him, for this is a wild country, and it will be safer for you to
have him at Rosmin than here, where he has friends and accomplices."
After a long search, a sheet of paper was found in a cupboard, the
statement made and submitted to the policeman, who shook his head a
little over the Polish composition, and the prisoner lifted into the
carriage, the gendarme taking his seat beside him, and saying to Anton,
"I have long expected something of the kind. You may have often occasion
to want me again." The carriage then drove away, and thus the property
came under Anton's administration. He felt as if cast on a desert
island.
His portmanteau and traveling effects were leaning against a mud wall,
and the Polish landlord was the only man who could give him and Karl any
information or advice in their forlorn condition.
Now that the steward was fairly gone, the landlord grew more
communicative, and showed himself serviceable and obliging. A long
conversation ensued, and its purport was what Anton had apprehended from
the warning given by the Commissary Walter and other Rosmin officials.
The inspector had,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done all he could in the
way of spoliation, rendered daring by a report which had found its way
from the town to the village, that the present proprietor would never be
able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estate. At last Anton said, "What that
wretched man has done away with he will have to account for; our first
care must be to preserve what is still to be found on the property. You
must be our guide to-day."
They then examined the empty buildings. Four horses and two
servants--they were gone into the wood--a few old plows, a pair of
harrows, two wagons, a britzska, a cellar full of potatoes, a few
bundles of hay, a little straw--the inventory did not take much time in
drawing up. The buildings were all out of repair, not through age, but
neglect.
"Where is the dwelling-house?" inquired Anton. The landlord led the way
out of the yard to the meadow--a broad plain, gradually sloping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brook. It had been a great pasture. The cattle had
trodden it down into holes; the snouts of greedy swine had rooted it up;
gray molehills and rank tufts of grass rose on all sides.
The landlord stretched out his hand. "There is the castle. This castle
i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he added, reverentially; "no
nobleman in the district has a stone house like that. All the gentry
here live in wood and mud buildings. Herr von Tarow, the richest of
them, has but a poor dwelling."
About three hundred yards from the last out-building rose a great brick
edifice, with a black slate roof and a thick round tower. Its gloomy
walls on this treeless pasture-land, without one trace of life around,
rose beneath the cloudy sky like a phantom fortress which some evil
spirit had evoked from the abyss--a station from which to blight all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The strangers approached it. The castle had fallen into ruins before the
builders had finished their task. The tower had stood there for ages. It
was built of unhewn stone, and had small windows and loop-holes. The
former lords of the land had looked down from its summit on the tops of
the trees, which then stretched far into the plain. They had then ruled
with a rod of iron the serfs who cultivated their land, and toiled and
died for them. Many an arrow had sped through those loop-holes at the
enemy storming below, and many a Tartar horse had been overthrown before
those massive walls. Years ago, a despot of the district had, in
expiation of former sins, begun to add to the gray tower the walls of a
holy monastery; but the monastery never got finished, and the useless
walls had already stood there long, when the late count took it into his
head to convert them into a lordly dwelling for his race, and to raise a
house unparalleled for magnificence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 front of the house was added on to both sides of the tower, which
projected in the middle. The intention had been to have a high
terrace-road up to the castle, and the principal entrance had been made
in the tower, and arched over; but the terrace never having been formed,
the stone threshold of the main door was quite inacce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ladders, and the wide opening was left. The window-spaces of
the lower floor were merely closed up with boards, while on the second
story were some window-frames of beautifully carved wood, in which large
panes had once been placed, but they had got broken. In other windows
were temporary frames of rough deal, with small panes of muddy glass let
into them. A company of jackdaws sat on the top of the tower, looking
down in amazement on the strangers, and every now and then one flew off,
screaming loudly, to contemplate the intruders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A house for crows and bats, not for human beings," said Anton. "At
least, I see no way of getting into it."
The landlord now took them round the building. Behind, where the two
wings made a sort of horse-shoe, there were low entrances to the cellars
and offices; beneath which, again, were stables, great arched kitchens,
and small cells for the serfs. A wooden staircase led to the upper
story. The door turned creaking on its hinges, and a narrow passage took
them through a side wing to the front part of the house. There all was
at least magnificently planned. The circular entrance-hall--an arched
room of the old tower--was painted in mosaic, and through the great
doorway-opening was seen a wide expans
small disturbance made by the return of Anton had gradually settled
down. Those first-class treasures of Sabine's had made way for other
specimens of damask, still of a superior kind, it is true, but which
came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e elderly cousin's comprehension. She had
been quite right in prophesying that Anton would never remark those
signs of exuberant gratitude or their withdrawal. However, one change
had been permanently made--the greatest, the best of all changes--the
clerk retained a privileged place in the heart of the young mistress of
the firm, and his tall figure often appeared as one of the circle that
Sabine's fancy loved to gather round her when at her work-table or in
her treasure-chamber.
To-day she was walking restlessly up and down before dinner. The cousin,
who heard every thing, had just told her that a maid from Ehrenthal's
had run into the office to announce Bernhard's death to his friend. "How
will he bear it?" thought she. And the name of Ehrenthal forced her
thoughts back to the past, to one now far away, and to that painful hour
when the struggle going on in her own mind had been suddenly brought to
a close by a letter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parted. And Anton had known
of that conquered feeling of hers. How considerate he had always been,
how chivalrous, how helpful! She wondered if he had any idea of the
completeness of her triumph over a girlish illusion. She shook her head.
"No, he has not. It was here, at this very table, that an accident first
betrayed me to him. That past time still rises like a cloud between us.
Whenever I sit near Wohlfart of an evening, I am conscious of another's
shadow at my side; and when he speaks to me, his tone, his manner always
seem to say, 'You are not alone; he is with you.'" Sabine started, and
lovingly passed her hand over the beautiful flowers on the table before
her, as if to dispel a painful thought. She could not tell him that she
was free from that long-felt sorrow. Now, however, when he had lost a
friend whom he so much loved, she must show him that there were other
hearts that clung to him still. And again she walked up and down, trying
to devise a way of speaking to him alone.
Dinner was announced. Anton came with the rest, and took his place at
once. There was no opportunity of exchanging a word during the meal, but
he often met her sad and sympathizing eye. "He eats nothing at all
to-day," whispered her cousin; "not even any of the roast," she added,
reproachfully. Sabine was much perturbed. Mr. Jordan had already risen;
Anton would leave the room with the rest, and she should not see him
again the whole day through. So she called out, "The great Calla is
fully blown now. You were admiring the buds the other day; will you
remain a moment; I should like to show it you?" Anton bowed and staid
behind. A few more awkward moments, then her brother rose too; and,
hurrying to Anton, she took him to the room where the flowers were.
"You have had sorrowful tidings to-day," she began.
"The tidings themselves did not surprise me," replied Anton. "The doctor
gave no hope. But I lose much in him."
"I never saw him," said Sabine; "but I know from you that his life was
lonely--poor in affection and in enjoyment."
She moved an arm-chair toward Anton, and led him on to talk about his
friend. She listened to every word with warm sympathy, and well knew
what to ask and how to comfort. It was a relief to Anton to speak of the
departed one, to describe his quiet way of life, his erudition, his
poetical enthusiasm. After a pause, Sabine looked up frankly into his
face, and asked, "Have you any tidings of Herr von Fink?"
It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his departure that she had ever breathed his
name. Anton felt how touching her confidence was, given in this hour of
his sadness. In his emotion, he seized her hand, which she was slow in
withdrawing.
"He is not happy in his new life," he gravely replied. "There was a
savage humor in his last letter, from which I gather, even more than
from his actual words, that the business into which his uncle's death
has thrown him does not suit him."
"It is unworthy," cried Sabine.
"At all events, it is not what would be recognized as honorable in this
house," replied Anton. "Fink is upright, and has lived too long with
your brother to take pleasure in the wild speculations so common on the
other side the Atlantic. His partners and colleagues are for the most
part men without a conscience, and his feelings revolt against their
companionship."
"And can Herr von Fink tolerate such relations as these for a day?"
"It is a remarkable thing that he whose own will was ever so arbitrarily
exercised, should now be obliged against that will to obey a pressure
from without, and every where to work with his hands tied. The
organization of such speculations in America is so complicated that one
shareholder can do little to alter it; and, now that Fink has attained
what used to be the goal of his wishes--a large capital, and the
management of immense districts--his condition appears more uncertain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He was always in danger of thinking slightingly
of others, now I am distressed at the bitter contempt he expresses for
his own life. His last letter paints an intolerable state of things, and
seems to point to some decisive resolve."
"There is only one resolve for him," cried Sabine. "May I ask what you
said to him in reply?"
"I entreated him instantly, come what would, to free himself from the
business in which he was entangled. I said that his own strong will
might find a way of extrication, even if that which I pointed out proved
impracticable. Then I begged of him either to carry out his old plan of
becoming a landed proprietor in America, or to return to us."
"I knew that you would write thus," said Sabine, drawing a long breath.
"Yes, Wohlfart, he shall return," said she, gently, "but he shall not
return to us."
Anton was silent.
"And do you think that Herr von Fink will follow your advice?"
"I do not know. My advice was not very American."
"But it was worthy of you," cried Sabine, with proud delight.
"An officer wishes to speak to Mr. Wohlfart," said a servant at the
door.
Anton sprang up. Sabine went to her flowers and bent mournfully over
them. The shadows of others hovered still between her friend and her.
The few words spoken by the servant filled Anton with a vague terror. He
hurried into the ante-room: there stood Eugene von Rothsattel. Anton was
gladly rushing forward to greet him, but the young soldier's face of
agony made him start back. He whispered, "My mother wishes to speak to
you; something dreadful has occurred." Anton caught up his hat, ran into
the office, hurriedly asked Baumann to excuse him to the principal, and
then accompanied the lieutenant to the baron's house.
On the way, Eugene, who had lost all self-command, said unconnectedly to
Anton, "My father last night accidentally wounded himself by a
pistol-shot--a messenger was sent to summon me--when I came, I found my
mother in a swoon--my sister and I do not know what to do--Lenore
implored my mother on her knees to send for you--you are the only one in
whom w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our distress--I understand nothing about
business, but my father's affairs must be in a dreadful state--my mother
is beside herself--the whole house is in the greatest disorder."
From what Eugene said and what he did not say; from his broken sentences
and his look of agony, Anton guessed at the horrors of the previous
evening. In the boudoir of the baroness he found Lenore, weeping and
exhausted.
"Dear Wohlfart!" cried she, taking his hand and beginning again to sob,
while her head sank powerless on his shoulder.
Meanwhile Eugene walked up and down, wringing his hands, and at length
throwing himself on the sofa, he gave himself up to silent tears.
"It is horrible, Mr. Wohlfart," said Lenore, lifting up her head. "No
one may approach my father--Eugene may not, nor I--only my mother and
old John are with him; and early this morning the merchant Ehrenthal was
here, insisting that he must see my father. He screamed at my mother,
and called my father a deceiver, till she fainted away. When I rushed
into the room, the dreadful man went off threatening her with his
clenched fist."
Anton led Lenore to a chair and waited till she had told him all.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comforting in this case, and his own heart was
wrung to the utmost by the misery he witnessed.
"Call my mother, Eugene," said Lenore, at length.
Her brother left the room.
"Do not forsake us," implored Lenore, clasping her hands; "we are at the
last gasp; even your help can not save us."
"He is dead who might perhaps have done so," mournfully replied Anton.
"Whether I can be of any use I know not, but you can not doubt my
willingness to be so."
"No," cried Lenore. "And Eugene, too, thought of you at once."
The baroness now entered. She walked wearily; but, steadying herself by
a chair, she saluted Anton with dignity. "In our position," said she,
"we need a friend who knows more of business than we three do.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prevents the baron--possibly for a long time to
come--from managing his own affairs, and, little as I understand them, I
can see that our interests require prompt measures. My children have
mentioned you to me, but I fear I am unreasonable in asking you to
devote your time to our service."
She sat down, beckoned Anton to take a chair, and said to her children,
"Leave us; I shall be better able to tell Mr. Wohlfart the little that I
know when I do not see your grief."
When they were alone, she motioned him nearer and tried to speak, but
her lips quivered, and she hid her face in her handkerchief.
"Before I can consent, gracious lady," said he, "to your reposing in me
such confidence as this, I must first inquire whether the baron has no
relative or intimate friend to whom you could with less pain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I pray you to remember that my own knowledge of business
is but small, and my position not one to constitute me a proper
counselor to the baron."
"I know no one," said the baroness, hopelessly. "It is less painful to
me to tell you what I can not conceal, than to one of our own circle.
Consider yourself a physician sent for to visit a patient. The baron has
this morning told me some particulars of his present circumstances." And
then she proceeded to relate what she had gathered as to the nature of
his embarrassments, the danger in which the family property was placed,
and the capital needed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Polish estate.
"My husband," continued she, "has given me the key of his desk, and he
wishes Eugene, with the help of a man of business, to go over his
papers. I now request of you to make this examination together with my
son. When you need explanations, I will try to obtain them from the
baron. The question is now, whether you are inclined to undertake this
trouble for us, who are only strangers."
"I am most willing to do so," earnestly replied Anton; "and I hope that
the kindness of my principal will allow me the time needful for the
purpose, if you do not consider it more advisable to depute the baron's
experienced legal adviser to the task."
"There will be an opportunity of asking that gentleman's advice later,"
said the baroness.
Anton rose. "When do you wish to begin?"
"Immediately. I fear there is not a day to lose. I shall do all I can to
help you look the papers over." She led Anton into the next room, called
in Eugene, and unlocked the baron's desk. As she opened it she lost her
self-command for a moment, and moving to the window, the quivering of
the curtains betrayed the anguish that shook her fragile frame.
The mournful task began. Hour after hour passed. Eugene was in no
condition to peruse any thing, but his mother reached letters and
documents to Anton, and, though often obliged to desist a while, she
bravely returned to the task. Anton placed the papers in order, and
sought, by glancing over each, to arrive at least at a superficial view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It was evening, when the old servant opened the door in dismay, and
called out, "He is there again." The baroness could not repress a slight
scream, and made a gesture of aversion.
"I have told him that no one is at home, but he will not be dismissed;
he makes such a noise on the steps. I can not get rid of him."
"It will kill me if I hear his voice again," murmured the baroness.
"If the man be Ehrenthal," said Anton, rising, "I will try to get him
away. We have now done what was most necessary; have the goodness to
lock up these papers, and to allow me to return to-morrow." The baroness
silently assented, and sank back in her chair. Anton hurried off to the
ante-room, whence he could hear Ehrenthal's loudly-raised voi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usurer shocked him. His hat pushed half off his
head, his pale face swelled as if by drinking, his glazed eyes red with
tears, Ehrenthal stood before him, calling in broken sentences for the
baron, wailing and cursing alternately. "He must come! he must come at
once!" cried he; "the wicked man! A nobleman, indeed! he is a vagabond,
after whom I will send the police. Where is my money? Where is my
security? I want my mortgage from this man who is not at home."
Anton went straight up to him, and asked, "Do you know me, Mr.
Ehrenthal?" Ehrenthal turned his glazed eyes upon him, and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 friend of his dead son.
"He loved you!" he cried, in a lamentable voice. "He spoke to you more
than to his father. You were the only friend that he had on earth. Have
you heard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house of Ehrenthal?" continued he, in
a whisper. "Just as they stole the papers he died. He died with a hand
like this," and clenching his fist he struck his forehead. "Oh my son!
my son! why didst not thou forgive thy father!"
"We will go to your son," said Anton, taking the arm of the old man, who
unresistingly allowed himself to be led back to his own house.
From thence Anton hurried to Councilor Horn, with whom he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It was late before he returned home. In the midst of his anxiety about
those whose prosperity had filled his imagination years before,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in their adversity, reposed in him, dilated his
breast with a feeling of pride. He burned with desire to help them, and
hoped that his zealous devotion might yet find some way of rescue. As
yet he saw none. Looking up at the great building before him, so firm
and secure, in the moonlight, a thought flashed into his mind. If any
man could help them, it was his principal. His keen eye would be able to
unravel all the dark secrets in which the baron was entangled, and his
iron strength of will would crush the villains who held the unfortunate
nobleman in their power. And then he had a noble nature; he always
decided on the right, without an effort or a struggle. Anton looked at
the first floor. The whole house-front was dark, but in a corner room a
light still burned. It was the private office of his chief.
With sudden resolve, Anton begged the servant to take him to Mr.
Schröter, who looked with amazement at the unexpected visitor, and asked
what brought him, and whether any thing had happened.
"I implore your counsel--I implore your help," cried Anton.
"For yourself or for others?" inquired the merchant.
"For a family with whom I have accidentally become connected. They are
lost if a strong hand does not ward off the impending catastrophe."
Anton then rapidly related the occurrences of the afternoon, and,
seizing his principal's hand in his emotion, cried, "Have pity upon the
unhappy ladies, and help them."
"Help them!" replied the merchant; "how can I? Have you been
commissioned to apply to me, or are you only following the impulse of
your own feelings?"
"I am not commissioned; it is only the interest that I take in the
baron's fate which leads me to you."
"And what right have you to inform me of facts communicated in strict
confidence to yourself by the baron's lady?" asked the merchant, dryly.
"I am committing no indiscretion in telling you what will, in a few
days, be no secret, even to strangers."
"You are unusually excited, otherwise you would not forget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hatever, does a man of business venture to make such a
communication without the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Of course, I shall make no wrong use of what you have said, but it was
by no means business-like, Wohlfart, to be so open toward me."
Anton was silent, feeling, indeed, that his principal was right, but yet
it seemed hard to be blamed for reposing confidence at such a time as
this. The merchant walked silently up and down; at length, stopping
before Anton, he said, "I do not now inquire how you come to take so
warm an interest in this family. I fear it is an acquaintance you owe to
Fink."
"You shall hear all," said Anton.
"Not at present. I will now content myself with repeating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interfere in these affairs without being specially
applied to by the parties themselves. I may add that I by no means wish
for such an application, and do not disguise from you that, were it
made, I should probably decline to do any thing for the Baron
Rothsattel."
Anton's feelings were roused to the utmost. "The question is the rescue
of an honorable man, and of lovely and amiable women from the toils of
rogues and impostors. To me, this seems the duty of every one; I, at
least, consider it a sacred obligation which I dare not shrink from. But
without your support I can do nothing."
"And how do you think this embarrassed man can be helped?" inquired the
merchant, seating himself.
With somewhat more composure, Anton repli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an experienced man of business making himself master of the case. There
must be some way of circumventing these villains. Your penetration would
discover it."
"Any attorney would be far more likely to do so, and the baron might
readily engage the services of experienced and upright legal advisers.
If his enemies have done any thing illegal, the quick eye of a lawyer is
the most likely to detect it."
"Alas! the baron's own lawyer gives but little hope," replied Anton.
"Then, my dear Wohlfart, no other is likely to do much good. Show me an
embarrassed man who has strength to grasp an offered hand, and bid me
help him, and for the sake of all I owe you, I will not refuse to do so.
I think you are convinced of this."
"I am," said Anton, dejectedly.
"From all I hear, however," the merchant went on,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the baron. From what I gather from general report, as well as from
you, his embarrassments arise from his having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usurers, which proves him deficient in what alone ennobles the life of
any man--good sense, and the power of steady exertion."
Anton could only sigh his assent.
"To help such a man," inexorably continued the merchant, "is a futile
attempt, against which reason may well protest. We are not to despair of
any, but want of strength is the most hopeless case of all. Our power of
laboring for others being limited, it becomes our duty to inquire,
before we devote our time to the weak, whether we are not thus
diminishing our chances of helping better men."
Anton interrupted him. "Does he not deserve every allowance to be made
for him? He was brought up to exact much; he has not learned, as we
have, to make his way by his own labor."
The merchant laid his hand on the young man's shoulder. "The very
reason. Believe me, a large number of these landed gentry, who pay the
penalty of their old family memories, are beyond help. I am the last to
deny that many worthy and admirable men belong to this class. Indeed,
wherever remarkable talent or nobility of character shoots up among
them, no doubt their position offers peculiar scope for its development,
but for average men it is not a favorable one. He who considers it his
hereditary privilege to enjoy life, and who assumes a distinguished
position in virtue of his family, will very often fail to put forth his
whole strength in order to deserve that position. Accordingly, numbers
of our oldest families are declining, and their fall will be no loss to
the state. Their family associations make them haughty without any
right to be so--limit their perceptions and confuse their judgment."
"Even if all this be true," cried Anton, "it does not absolve us from
helping individuals of the class who have excited our sympathy."
"No," said the principal, "if it be excited. But it does not glow so
rapidly in advancing years as in youth. The baron has endeavored to
isolate his property from the current of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leave it forever to his family. Forever! You, as a merchant, know how to
estimate the attempt. True, every rational man must allow it to be
desirable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same soil should be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We all prize what our forefathers have possessed before
us, and Sabine would unlock every room in this house with pride, because
her great-great-grandmother turned the same keys before her. It is
therefore natural that the landed proprietor should desire to preserve
those familiar scenes, which are the source of his own prosperity, to
those nearest and dearest to him. But there must be means to this end,
and these means are the making his own existence available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increase of his patrimony. Where energy dies in families
or individuals, then it is well that their means die too, that their
money should circulate through other hands, and their plowshare pass to
those who can guide it better. A family that has become effete through
luxury ought to sink down into common life, to make room for the
uprising of fresh energies and faculties. Every one who seeks, at the
cost of free activity for others, to preserve permanent possessions and
privileges for himself or his family, I must look upon as an enemy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social state. And if such a man ruin
himself in his endeavors, I should feel no malicious pleasure in his
downfall, but I should say that he is rightly served, because he has
sinned against a fundamental law of our social being; consequently, I
should consider it doubly wrong to support this man, because I could but
fear that I should thus be supporting an unsound condition of the body
politic."
Anton looked down mournfully. He had expected sympathy and warm
concurrence, and he met with disaffection and coldness that he despaired
of conquering. "I can not gainsay you," he at length replied; "but in
this case I can not feel as you do. I have been witness to the
unspeakable distress in the baron's family, and my whole soul is full
of sadness and sympathy, and of the wish to do something for those who
have opened their heart to me. After what you have said, I dare no
longer ask you to trouble yourself with their affairs, but I have
promised the baroness to assist her as far as my small powers permit,
and your kindness allows. I implore you to grant me permission to do
this. I shall endeavor to be regular in my attendance at the office, but
if during the next few weeks I am occasionally absent, I must ask you to
excuse me."
Once more the merchant walked up and down the room, and then, looking at
Anton's excited face, with deep seriousness and something of regret, he
replied, "Remember, Wohlfart, that every occupation which excites the
mind soon obtains a hold over a man, which may retard as well as advance
his success in life. It is thi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 to agree
to your wishes."
"I know it," said Anton, in a low voice; "but I have now no choice
left."
"Well, then, do what you must," said the merchant, gloomily; "I will lay
no hinderance in your way; and I hope that after a few weeks you will be
able to consider the whole circumstances more calmly." Anton left the
room, and the merchant stood looking long with frowning brow at the
place his clerk had occupied.
Nor was Anton in a more congenial mood. "So cold, so inexorable!"
exclaimed he, as he reached his own room. He began to suspect that his
principal was more selfish and less kindly than he had hitherto
supposed. Many an expression of Fink's recurred to his mind, as well as
that evening when young Rothsattel, in his boyish conceit, had spoken
impertinently to the merchant. "Is it possible," thought he, "that that
rude speech should be unforgotten?" And his chief's keen, deep-furrowed
face lost inexpressibly by contrast with the fair forms of the noble
ladies. "I am not wrong," he cried to himself; "let him say what he
will, my views are more just than his, and henceforth my destiny shall
be to choose for myself the way in which I shall walk." He sat long in
the darkness, and his thoughts were gloomy as it; then he went to the
window to look down into the dark court below. A great white blossom
rose before him like a phantom. Striking a light, he saw that it was the
beautiful Calla out of Sabine's room. It hung down mournfully on its
broken stem. Sabine had had it placed there. This little circumstance
struck him as a mournful omen.
Meanwhile Sabine, taper in hand, entered her brother's room.
"Good-night, Traugott," nodded she. "Wohlfart has been with you this
evening; how long he staid!"
"He will leave us," replied the merchant, gloomily.
Sabine started and dropped her taper on the table. "For God's sake, what
has happened? Has Wohlfart said that he was going away?"
"I do not yet know it, but I see it coming step by step; and I can not,
and still less can you, do any thing to retain him. When he stood before
me here with glowing cheeks and trembling voice, pleading for a ruined
man, I found out what it was that lured him away."
"I do not understand you," said Sabine, looking full at her brother.
"He chooses to become the confidential friend of a decayed noble. A pair
of bright eyes draws him away from us: it seems to him a worthy object
of ambition to become Rothsattel's man of business. This intimacy with
nobility is the legacy bequeathed to him by Fink."
"And you have refused to help him?" inquired Sabine, in a low voice.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said the merchant, harshly; and he
turned to his writing-table.
Sabine slowly withdrew. The taper trembled in her hand as she passed
through the long suite of rooms listening to her own footfall, and
shuddering as the feeling came over her that an invisible companion
glided by her side. This was the revenge of that other. The shadow that
once fell on her innocent life now drove her friend away from their
circle. Anton's affections clung to another. She had but been in his
eyes a mere stranger, who had once loved and languished for one now far
away, and who now, in widow's weeds, looked back regretfully to the
feelings of her youth.
The few next weeks were spent by Anton in over-hard work. He had great
difficulty in keeping up his counting-house duties, while he spent every
spare hour in conference with the baroness and the lawyer.
In the mean time, the misfortunes of the baron ran their course. He had
not been able to pay the interest of the sums with which his estate was
burdened. When last they were due, a whole series of claims was brought
against him, and the estate fell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district authorities. Complicated lawsuits arose. Ehrenthal complained
loudly, claiming the first mortgage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nay, he
was inclined to advance claims on the last mortgage offered by the baron
in the recent fatal hour. Löbel Pinkus also appeared as claimant of the
first mortgage, and asserted that he had paid the whole sum of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Ehrenthal had no proof to bring forward, and had been
for some weeks past quite unable to manage his own affairs, while
Pinkus, on the contrary, fought with every weapon a hardened sinner can
devise or employ, and the deeds which the baron had executed at Veitel's
suggestion proved to be so capital a master-stroke of the cunning
advocate, that the baron's man of business had, from the first, little
hope of the case. We may here observe that Pinkus did eventually win it,
and that the mortgage was made over to him.
Anton was now gradually gaining some insight into the baron's
circumstances. But the double sale of the first mortgage was still kept
a secret by the latter, even from his wife. He declared Ehrenthal's
claim unfounded, and even expressed a suspicion that he had himself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robbery in his office. Indeed, he really
believed this. Then the name of Itzig was never broached, and the
suspicion against Ehrenthal, which the baron's lawyer shared, prevented
Anton seeking any explanation from him.
Meanwhile, an estrangement had sprung up between our hero and his
principal, which the whole counting-house remarked with surprise. The
merchant scowled at Anton's vacant seat when the latter chanced to be
absent during office-hours, or looked coldly at his clerk's face, made
pale as it was with excitement of mind and night-work. He took no notice
of his new occupation, and never seemed to remark him. Even to his
sister he maintained a stiff-necked silence; nor could all her attempts
lead him to speak of Anton, who, on his side, felt his heart revolt
against this coldness. After his return, to be treated like a child of
the house, praised, promoted, petted, and now to be treated like a mere
hireling, who is not worth the bread thrown to him; to be a toy of an
incomprehensible caprice--this, at least, he had not deserved; so he
became reserved toward the whole family, and sat silent at his desk; but
he fel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now and the then so keenly, that often,
when alone, he would spring up and stamp on the ground in the bitter
indignation of his heart.
One comfort remained. Sabine was not estranged. True, he saw little of
her, and at dinner she seemed to avoid speaking to him, but he knew that
she was on his side.
A few days after his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the merchant, she came down
stairs as he stood in the hall, and had to pass him by so closely that
her dress touched him. He had retreated, and made a formal bow, but she
looked at him imploringly, and whispered, "You must not be estranged
from me." It was an affair of a moment, but the faces of both were
radiant with a happy understanding.
The time had now arrived when Mr. Jordan was to quit the firm. The
principal again called Anton into his little office, and without any
severity, but also without a trace of his former cordiality, began: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o you my intention of appointing you Jordan's
successor; but,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your time has been more taken
up with other business than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such a post, I
therefore ask you whether you are now at liberty to undertake Jordan's
duties?"
"I am not," replied Anton.
"Can you name any--not very distant--time when you will be free from
your present occupation? In that case I will endeavor to find a
substitute until then."
Anton sorrowfully replied, "I can not at present say when I shall again
be master of my whole time; and, besides, I feel that, even as it is, I
tax your indulgence by many irregularities. Therefore, Mr. Schröter, I
beg that you will fill up this post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me."
The merchant's brow grew furrowed and dark, and he silently bowed
assent. Anton felt as he closed the door that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m was now complete, and, resuming his place, he leaned his throbbing
head on his hand. A moment later Baumann was summoned to the principal,
and Jordan's situation conferred upon him. On returning to the office,
he went up to Anton and whispered, "I refused at first, but Mr. Schröter
insisted. I am doing you an injustice." And that evening Mr. Baumann, in
his own room, read in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the chapters treating of
the unjust Saul (the principal), and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Jonathan
and the persecuted David, and strengthened his heart thereby.
The next day Anton was summoned to the baroness. Lenore and her mother
sat before a large table covered with jewel-boxes and toilette elegances
of every description, while a heavy iron chest stood at their feet. The
curtains were drawn, and the subdued light shone softly into the richly
furnished room. On the carpet glowed wreaths of unfading flowers, and
the clock ticked cheerfully in its alabaster case. Under the shade of
flowering plants sat the two love-birds in their silvered cage, hopping
from perch to perch, screaming ceaselessly, or sitting up quietly close
to each other. The whole room was beauty and perfume. "For how long?"
thought Anton. The baroness rose. "We are already obliged to trouble you
again," said she; "we are engaged in a very painful occupation." On the
table were all manner of ornaments, gold chains, brilliants, rings,
necklaces, gathered into a heap.
"We have been looking out all that we can dispense with," said the
baroness, "and now pray you to undertake to sell these things for us. I
have been told that some of them are of value, and as we are now in much
need of money, we turn here for help."
Anton looked in perplexity at the glittering heap.
"Tell us, Wohlfart," cried Lenore, anxiously, "is this necessary? can it
be of any use? Mamma has insisted upon setting apart for sale all our
ornaments, and whatever plate is not in daily use. What I can give is
not worth talking of, but my mother's jewels are costly; many of them
were presents made to her in youth, which she shall not part with unless
you say that it is necessary."
"I fear," said Anton, gravely, "that it will prove so."
"Take them," said the baroness to Anton; "I shall be calmer when I know
that we have at least done what we could."
"But do you wish to part with all?" inquired Anton, anxiously. "Much
that is dear to you may have but little value in a jeweler's eyes."
"I shall never wear an ornament again," quietly replied the baroness.
"Take them all;" and, holding her hands before her eyes, she turned
away.
"We are torturing my mother," cried Lenore, hastily; "will you lock up
all that is on the table, and get them out of the house as soon as you
can?"
"I can not undertake the charge of these valuables," said Anton,
"without taking some measures to decrease my own responsibility. First
of all, I will in your presence make a short note of all you intrust to
me."
"What useless cruelty!" exclaimed Lenore.
"It will not take long."
Anton took out a few sheets from his pocket-book, and began to note down
the different articles.
"You shall not see it done, mother," said Lenore, drawing her mother
away, and then returning to watch Anton at his task.
"These preparations for the market are horrible," said she. "My mother's
whole life will be sold; some memory of hers is linked with every single
thing. Look, Wohlfart, the princess gave her this diamond ornament when
she married my father."
"They are magnificent brilliants," cried Anton, admiringly.
"This ring was my grandfather's, and these are presents of poor papa's.
Alas! no man can know how we love all these things. It was always a
festival to me when mamma put on her diamonds. Now we come to my
possessions. They are not worth much. Do you think this bracelet good
gold?" She held out her hand as she spoke.
"I do not know."
"It shall go with the rest," said Lenore, taking it off. "Yes, you are a
kind, good man, Wohlfart," continued she, looking trustfully into his
tearful eyes; "do not forsake us. My brother has no experience, and is
more helpless than we are. It is a frightful position for me. Before
mamma I do all I can to be composed, else I could scream and weep the
whole day through." She sank in a chair, still holding his hand. "Dear
Wohlfart, do not forsake us."
Anton bent over her, and looked with passionate emotion at the lovely
face that turned so trustfully to him in the midst of its tears.
"I will be helpful to you when I can," said he, in the fullness of his
heart. "I will be at hand whenever you need me. You have too good an
opinion of my information and my faculties; I can be of less assistance
to you than you suppose, but what I can, that I will do in any and every
possible way."
Their hands parted with a warm pressure; the affair was settled.
The baroness now returned. "Our lawyer was with me this morning," said
she; "and now I must ask for your opinion on another subject. He tells
me that there is no prospect of preserving the baron's family estate."
"At this time, when interest is high, and money difficult to get, none,"
replied Anton.
"And you, too, think that we must turn all our efforts toward preserving
the Polish property?"
"I do," was the answer.
"For that, also, money will be necessary. Perhaps I may be able through
my relatives to intrust you with a small sum, which, with the help of
that"--she pointed to the iron chest--"may suffice to cover the first
necessary expenses. I do not, however, wish to sell the jewels here, and
a journey to the residence would be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cure the
sum to which I have just alluded. The baron's lawyer has spoken most
highly of your capacity for business. It is his wish which now decides
me to make a proposal to you. Will you for the next few years, or, at
all events, until our greatest difficulties are over, devote your whole
time to our affairs? I have consulted my children, and they agree with
me in believing that in your assistance lies our only hope of rescue.
The baron, too, has come in to the plan. The question now is whether
your circumstances allow you to give your support to our unfortunate
family. We shall be grateful to you, whatever conditions you affix; and
if you can find any way of making our great obligations to you apparent
in the position you hold, pray impart it to me."
Anton stood petrified. What the baroness required of him was separation
from the firm, separation from his principal, and from Sabine! Had this
thought occurred to him before, when standing in Lenore's presence or
bending over the baron's papers? At all events, now that the words were
spoken, they shocked him. He looked at Lenore, who stood behind her
mother with hands clasped in supplication. At length he replied, "I
stand in a position which I can not leav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others.
I was not prepared for this proposal, and beg to have time allowed me
for consideration. It is a step which will decide my whole future life."
"I do not press you," said the baroness; "I only request your
consideration. Whatever your decision be, our warmest gratitude will
still be yours; if you are unable to uphold our feeble strength, I fear
that we shall find no one to do so. You will think of that," she added,
beseechingly.
Anton hurried through the street with throbbing pulse. The noble lady's
glance of entreaty, Lenore's folded hands, beckoned him out of the
gloomy counting-house into a sphere of greater liberty, into a new
future, from whose depths bright images flashed out upon his fancy. A
request had been frankly made, and he was strongly inclined to justify
the confidence that prompted it. Those ladies required an unwearied,
self-sacrificing helper to save them from utter ruin, and if he
followed his impulse he should be doing a good work--fulfilling a duty.
In this mood he entered the merchant's dwelling. Alas! all that he saw
around him seemed to stretch out a hand to detain him. As he looked at
the warehouse, the good-humored faces of the porters, the chains of the
great scales, the hieroglyphics of the worthy Pix, again he felt that
this was the place that he belonged to. Sabine's dog kissed his hand,
and ran before him to his room--his and Fink's room. Here the childish
heart of the orphan boy had found a friend, kind companions, a home, a
definite and honorable life-purpose. Looking down through his window on
all the long-familiar objects, he saw a light in Sabine's store-chamber.
How often he had sought for that light, which brightened the whole great
building, and brought a sense of comfort and cheerfulness even into his
room. He now sprang up suddenly, and said to himself, "She shall
decide."
Sabine started in amazement when Anton appeared before her. "I am
irresistibly impelled to seek you," cried he. "I have to decide upon my
future life, and I feel undetermined, and unable to trust to my own
judgment. You have always been a kind friend to me since the day of my
arrival. I am accustomed to look up to you, and to think of you in
connection with all that interests me here. Let me hear your opinion
from your own lips. The Baroness Rothsattel has to-day proposed to me
permanently to undertake the situation of confidential adviser and
manager of the baron's affairs. Shall I accept; or shall I remain here?
I know not--tell me what is right both for myself and others."
"Not I," said Sabine, drawing back and growing very pale. "I can not
venture to decide in the matter. Nor do you wish me to do so, Wohlfart,
for you have already decided."
Anton looked straight before him and was silent.
"You have thought of leaving this house, and a wish to do so has sprung
out of the thought. And I am to justify you, and approve your resolve!
This is what you require of me," continued she, bitterly. "But this,
Wohlfart, I can not do, for I am sorry that you go away from us."
She turned away from him and leaned on the back of a chair.
"Oh, be not angry with me too!" said Anton; "that I can not bear. I have
suffered much of late. Mr. Schröter has suddenly withdrawn from me the
friendly regard that I long held my life's greatest treasure. I have not
deserved his coldness. What I have been doing has not been wrong, and
it was done with his knowledge. I had been spoiled by his kindness; I
have the more deeply felt his displeasure. My only comfort has been that
you did not condemn me. And now, do not you be cold toward me, else I
shall be wretched forever. There is not a soul on earth to whom I can
turn for affectionate comprehension of my difficulties. Had I a sister,
I should seek her heart to-day. You do not know what to me, lonely as I
am, your smile, your kindly shake of the hand has been till now. Do not
turn coldly from me, I beseech you."
Sabine was silent. At length she inquired, still with averted face,
"What draws you to those strangers; is it a joyful hope, is it sympathy
alone? Give this question close consideration before you answer it to
yourself at least."
"What it is that makes it possible for me to leave this house," said
Anton, "I do not myself know. If I can give a name to my motives, it is
gratitude felt toward one. She was the first to speak kindly to the
wandering boy on his way out into the world. I have admired her in the
peaceful brightness of her former life. I have often dreamed childish
dreams about her. There was a time when a tender feeling for her filled
my whole heart, and I then believed myself forever the slave of her
image. But years bring changes, and I learned to look on men and on life
with other eyes. Then I met her again, distressed, unhappy, despairing,
and my compassion became overmastering. When I am away from her, I know
that she is nothing to me; when I am with her, I feel only the spell of
her sorrow. Once, when I had to depart out of her circle like a culprit,
she came to me, and before the whole scornful assembly she gave me her
hand and acknowledged me her friend; and now she comes and asks for my
hand to help her father. Can I refuse it? Is it wrong to feel as I do? I
know not, and no one can tell me--no one but you alone."
Sabine's head had sunk down to the back of the chair on which she bent.
She now suddenly raised it, and with tearful eyes, and a voice full of
love and sorrow, cried, "Follow the voice that calls you. Go, Wohlfart,
go."
CHAPTER XXVII.
On a cold October day, two men were seen driving through the latticed
gate of the town of Rosmin on toward the plain, which stretched out
before them monotonous and boundless. Anton sat wrapped in his fur coat,
his hat low on his forehead, and at his side was young Sturm, in an old
cavalry cloak, with his soldier's cap cocked cheerily on one side. In
front of them a farm-servant, squatted on a heap of straw, flogged on
the small horses. The wind swept the sand and straw from the
stubble-fields, the road was a broad causeway without ditches or hedges,
the horses had to wade alternately through puddles and deep sand. Yellow
sand gleamed through the scanty herbage in all directions wherever a
field-mouse had made her way to her nest or an active mole had done what
he could to diversify the unbroken plain. Wherever the ground sank,
stagnant water lodged, and there hollow willow-trees stretched their
crippled arms in the air, their boughs flapping in the wind, and their
faded leaves fluttering down into the muddy pool below. Here and there
stood a small dwarf pine, a resting-place for the crows, who, scared by
the passing carriage, flew loudly croaking over the travelers' heads.
There was no house to be seen on the road, no pedestrian, and no
conveyance of any kind.
Karl looked every now and then at his silent companion, and said at
last, pointing to the horses, "How rough their coats are, and how pretty
their gray mouse skins! I wonder how many of these beasties would go to
make up my sergeant's horse! When I took leave of my father, the old man
said, 'Perhaps I shall pay you a visit, little one, when they light the
Christmas-tree.' 'You'll never be able,' said I. 'Why not?' asked he.
'You'll never trust yourself in any post-chaise.' Then the old boy
cried, 'Oho! post-chaises are always of a stout build; I shall be sure
to trust myself in one.' But now, Mr. Anton, I see that my father never
can pay us a visit."
"Why not?"
"It is possible that he may reach Rosmin; but, as soon as he sees these
horses and this road, he will instantly turn back. 'Shall I trust
myself,' he'll say, 'in a district where sand runs between one's legs
like water, and where mice are put into harness? The ground is not firm
enough for me.'"
"The horses are not the worst things here," said Anton, absently. "Look!
these go fast enough."
"Yes," replied Karl, "but they don't go like regular horses; they
entangle their legs like two cats playing in a parsley-bed. And what
things they have for shoes--regular webbed hoofs, I declare, which no
blacksmith can ever fit."
"If we could only get on!" returned Anton; "the wind blows cold, and I
am shivering in spite of my fur."
"You have slept but little the last few nights, sir," said Karl. "The
wind blows here as if over a threshing-floor. The earth is not round
hereabouts as elsewhere, but flat as a cake. This is a complete desert;
we have been driving for more than an hour, and there is not a village
to be seen."
"A desert indeed," sighed Anton; "let us hope it may improve." They
relapsed into profound silence. At length the driver stopped near a
pool, unharnessed the horses, and led them to the water's edge, without
noticing the travelers.
"What the deuce does this mean?" cried Karl, jumping down from the
carriage.
"I am going to feed," replied the servant, sulkily, in a foreign accent.
"I am anxious to know how that will be done," said Karl. "There is not
the shadow of a bag of provender."
The horses, however, soon proved that they could live without corn; they
stretched down their shaggy heads, and began to pull the grass and weeds
at the edge of the pool, sometimes taking a draught of the dirty water.
Meanwhile the servant drew a bundle from under his seat, settled himself
under the lee of an alder-bush, and, taking his knife, cut his bread and
cheese without even glancing at the travelers.
"I say, Ignatius or Jacob," cried Karl, sharply, "how long will this
breakfast of yours last?"
"An hour," replied the man, munching away.
"And how far is it from here to the estate?"
"Six miles, or maybe more."
"You can make nothing of him," said Anton; "we must put up with the
customs of the country;" and, leaving the carriage, they went to look on
at the horses feeding.
Anton is on his way to the Polish property. He is now the baron's agent.
Anxious months have the last proved to him. The parting from his
principal and the firm had been painful in the extreme. For some time
before it, indeed, Anton had found himself alone in the midst of his
colleagues. The quiet Baumann still remained his friend, but the others
considered him a castaway. The merchant received his resignation with
icy coldness; and even in the hour of parting, his hand lay impassive as
metal in Anton's grasp. Since then, our hero had undertaken several
journeys to the capital and to creditors in the family's behalf, and now
he was on his way to set the new estate in order, accompanied by Karl,
whom he had induced to become the baron's bailiff.
Ehrenthal had, by the authority conferred on him,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from the time of the sale by auction, and hired the Polish
bailiff for the baron. There had been unfair dealings between them at
the time, and it was well known in Rosmin that the bailiff had sold off
a good deal, and been guilty of all sorts of frauds since, so that Anton
had even now no prospect of a quiet life.
"The hour is come when I may execute my commission," cried Karl, groping
in the straw under the seat. He drew out a large japanned tin case, and
carried it to Anton. "Miss Sabine gave me this in charge for you." He
then joyously opened the lid, produced the materials for an excellent
breakfast, a bottle of wine, and a silver goblet. Anton took hold of the
case.
"It has a very knowing look," said Karl. "Miss Sabine planned it
herself."
Anton examined it on all sides, and placed it carefully on a tuft of
grass; then he took up the goblet, and saw his initials engraved on it,
and underneath the words, "To thy welfare." Whereupon he forgot the
breakfast and all around him, and stood gazing at the goblet, lost in
thought.
"Do not forget the breakfast, sir," suggested Karl, respectfully.
"Sit down by me, my faithful friend; eat and drink with me. Leave off
your absurd politeness. We shall have but little, either of us, but what
we have we will share like brothers. Take the bottle if you have no
glass."
"There's nothing like leather," said Karl, taking a small leathern
drinking-cup out of his pocket. "As for 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t was
kindly meant, and I thank you; but there must be subordination, if it
were but for the sake of the others; and so, sir, be kind enough to let
me shake hands with you now, and then let things be as they were before.
Only look at the horses, Mr. Anton. My faith! the creatures devour
thistles."
Again the horses were harnessed, again they threw out their short legs
in the sand, and again the carriage rolled through the barren
district--first through an empty plain, next through a wretched
fir-wood, then past a row of low sand-hills, then over a tumble-down
bridge crossing a small stream.
"This is the property," said the driver, turning round, and pointing
with his whip to a row of dirty thatched roofs that had just come into
sight.
Anton stood up to look for the group of trees in which the Hall might be
supposed to stand. Nothing of the sort to be seen. The village was
deficient in all that adorns the home of the poorest German peasant--no
orchard, no hedged-in gardens, no lime-trees in the market-place.
"This is wretched," said he, sitting down again; "much worse than they
told us in Rosmin."
"The village looks as if under a curse," cried Karl; "no teams working
in the fields--not a cow or a sheep to be seen."
The farm-servant flogged his horses into an irregular gallop, and so
they passed through the rows of mud huts which constituted the village,
and arrived at the public house. Karl sprang from the carriage, opened
the tavern door, and called for the landlord. A Jew slowly rose from his
seat by the stove and came to the threshold. "Is the gendarme from
Rosmin come?" He is gone into the village. "Which is the way to the
farm-yard?"
The landlord, an elderly man with an intelligent countenance, described
the way in German and Polish, and remained standing at the
door--bewildered, Karl declared, by the sight of two human beings. The
carriage turned into a cross-road, planted on both sides with thick
bushes, the remains of a fallen avenue. Over holes, stones, and puddles,
it rattled on to a group of mud huts, which still had a remnant of
whitewash upon them. "The barns and stables are empty," cried Karl, "for
I see gaps in the roofs large enough to drive our carriage through."
Anton said no more; he was prepared for every thing. They drove through
a break between the stables into the farm-yard, a large irregular space,
surrounded on three sides by tumble-down buildings, and open to the
fields on the fourth. A heap of _débris_ lay there--lime and rotten
timber, the remains of a ruined barn. The yard was empty; no trace of
farm implements or human labor to be seen. "Which is the inspector's
house," inquired Anton, in dismay. The driver looked round, and at last
made up his mind that it was a small one-storied building, with straw
thatch and dirty windows.
At the noise of the wheels a man appeared on the threshold, and waited
phlegmatically till the travelers had dismounted, and were standing
close before him. He was a broad-shouldered fellow, with a bloated,
brandy-drinking face, dressed in a jacket of shaggy cloth, while behind
him peered the muzzle of an equally shaggy dog, who snarled at the
strangers. "Are you the steward of this property?"
"I am," replied the man, in broken German, without stirring from where
he was.
"And I am the agent of the new proprietor," said Anton.
"That does not concern me," growled the shaggy man, turning sharp round,
entering the house, and bolting the door within.
Anton was thoroughly roused. "Break the window in, and help me to catch
the rascal," cried he to Karl, who coolly seized a piece of wood, struck
the panes so as to make the rotten framework give way, and cleared the
opening at one leap. Anton followed him. The room was empty, so was the
next, and in it an open window--the man was gone.
"After him!" cried Karl, and dashed on in pursuit, while Anton looked
about the house and out-buildings. He soon heard the barking of a dog,
and saw Karl capture the fugitive. Hurrying to his help, he held the man
fast, while, with a kick, Karl sent the dog flying. They then contrived
to force the steward back to the house, though he kept striking out
violently all the way.
"Go to the tavern, and bring the gendarme and the landlord," cried Anton
to the driver, who, undisturbed by all that had been going on, had
meanwhile unpacked the carriage. The man accordingly drove leisurely
off, and the fugitive being got into the room, Karl found an old cloth,
and with it bound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I beg your pardon, sir,"
said he; "it is only for an hour or so, till the arrival of the Rosmin
gendarme, whom we have appointed to meet us."
Anton then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house, bu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found but the merest necessaries; no books nor papers of any kind. It
had doubtless been emptied already. A bundle projected from the
coat-pocket of the prisoner, which turned out to be receipts and legal
documents in Polish. In time, the driver returned with the landlord and
the armed policeman. The landlord stood at the door in some perplexity,
and the policeman explained in a few moments what remained to be done.
"You must make a statement to the local judge, and give the man up to
me. He shall go back in your carriage to Rosmin. You will do well to get
rid of him, for this is a wild country, and it will be safer for you to
have him at Rosmin than here, where he has friends and accomplices."
After a long search, a sheet of paper was found in a cupboard, the
statement made and submitted to the policeman, who shook his head a
little over the Polish composition, and the prisoner lifted into the
carriage, the gendarme taking his seat beside him, and saying to Anton,
"I have long expected something of the kind. You may have often occasion
to want me again." The carriage then drove away, and thus the property
came under Anton's administration. He felt as if cast on a desert
island.
His portmanteau and traveling effects were leaning against a mud wall,
and the Polish landlord was the only man who could give him and Karl any
information or advice in their forlorn condition.
Now that the steward was fairly gone, the landlord grew more
communicative, and showed himself serviceable and obliging. A long
conversation ensued, and its purport was what Anton had apprehended from
the warning given by the Commissary Walter and other Rosmin officials.
The inspector had, during the last few weeks, done all he could in the
way of spoliation, rendered daring by a report which had found its way
from the town to the village, that the present proprietor would never be
able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estate. At last Anton said, "What that
wretched man has done away with he will have to account for; our first
care must be to preserve what is still to be found on the property. You
must be our guide to-day."
They then examined the empty buildings. Four horses and two
servants--they were gone into the wood--a few old plows, a pair of
harrows, two wagons, a britzska, a cellar full of potatoes, a few
bundles of hay, a little straw--the inventory did not take much time in
drawing up. The buildings were all out of repair, not through age, but
neglect.
"Where is the dwelling-house?" inquired Anton. The landlord led the way
out of the yard to the meadow--a broad plain, gradually sloping down to
the level of the brook. It had been a great pasture. The cattle had
trodden it down into holes; the snouts of greedy swine had rooted it up;
gray molehills and rank tufts of grass rose on all sides.
The landlord stretched out his hand. "There is the castle. This castle
i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he added, reverentially; "no
nobleman in the district has a stone house like that. All the gentry
here live in wood and mud buildings. Herr von Tarow, the richest of
them, has but a poor dwelling."
About three hundred yards from the last out-building rose a great brick
edifice, with a black slate roof and a thick round tower. Its gloomy
walls on this treeless pasture-land, without one trace of life around,
rose beneath the cloudy sky like a phantom fortress which some evil
spirit had evoked from the abyss--a station from which to blight all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The strangers approached it. The castle had fallen into ruins before the
builders had finished their task. The tower had stood there for ages. It
was built of unhewn stone, and had small windows and loop-holes. The
former lords of the land had looked down from its summit on the tops of
the trees, which then stretched far into the plain. They had then ruled
with a rod of iron the serfs who cultivated their land, and toiled and
died for them. Many an arrow had sped through those loop-holes at the
enemy storming below, and many a Tartar horse had been overthrown before
those massive walls. Years ago, a despot of the district had, in
expiation of former sins, begun to add to the gray tower the walls of a
holy monastery; but the monastery never got finished, and the useless
walls had already stood there long, when the late count took it into his
head to convert them into a lordly dwelling for his race, and to raise a
house unparalleled for magnificence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 front of the house was added on to both sides of the tower, which
projected in the middle. The intention had been to have a high
terrace-road up to the castle, and the principal entrance had been made
in the tower, and arched over; but the terrace never having been formed,
the stone threshold of the main door was quite inacce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ladders, and the wide opening was left. The window-spaces of
the lower floor were merely closed up with boards, while on the second
story were some window-frames of beautifully carved wood, in which large
panes had once been placed, but they had got broken. In other windows
were temporary frames of rough deal, with small panes of muddy glass let
into them. A company of jackdaws sat on the top of the tower, looking
down in amazement on the strangers, and every now and then one flew off,
screaming loudly, to contemplate the intruders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A house for crows and bats, not for human beings," said Anton. "At
least, I see no way of getting into it."
The landlord now took them round the building. Behind, where the two
wings made a sort of horse-shoe, there were low entrances to the cellars
and offices; beneath which, again, were stables, great arched kitchens,
and small cells for the serfs. A wooden staircase led to the upper
story. The door turned creaking on its hinges, and a narrow passage took
them through a side wing to the front part of the house. There all was
at least magnificently planned. The circular entrance-hall--an arched
room of the old tower--was painted in mosaic, and through the great
doorway-opening was seen a wide expans
ground. Thinking that the barn was the most likely place to get into
something and not get out again, they opened every old chest there and
pried into every corner, and moved every article. They went up-stairs
and looked through the lofts and corners. The roof being partly off, it
was as light as day, and if she had been there anywhere they would
surely have seen her. But there was no sign of her. They looked under
the roof of the barn that lay on the ground, thinking that she might
have crawled under that and become pinned down, but she was not there.
“Could she have fallen into the river?” asked Calvin.
“It wouldn’t have done her any harm if she had,” said Hinpoha. “Sahwah’s
more at home in the water than she is on land. It wouldn’t have been
unlike her to jump in and swim around and duck her head under every time
I came near, but then she would have heard us calling for her and come
out.”
They parted every bush and shrub, and looked closely at the branches of
every tree, half fearing to find her hanging by the hair somewhere.
“Do you suppose she went up the Balm of Gilead tree and into the attic
window?” asked Migwan. They searched through the attic, and a laborious
search it was, on account of the quantities of furniture and chests to
be moved. They pulled out every drawer and burst open every trunk and
chest, thinking she might have crawled into one and then the lid had
closed with a spring lock. It was fully noon before they were satisfied
that she was not up there.
“Could she be in the cellar?” asked Hinpoha. Down they went, carrying
lights to look into all the dark corners. But the search was vain. The
girls became extremely frightened. Something told them that Sahwah’s
disappearance was not voluntary. They looked at each other with growing
fear. What had the message on the door said?
“_If you folks know what’s good for you you’ll get out of that
house._”
Was that a warning of what had happened now? Was it a friendly or a
sinister warning? Migwan was almost beside herself to think that
anything had happened to Sahwah while she was staying with her. The day
dragged along like a nightmare. In the afternoon Calvin had an
inspiration. “Why didn’t I think of it before?” he almost shouted.
“Here’s Pointer; he’s a hunting dog and can follow a trail. We’ll set
him to find Sahwah’s trail.”
“That’s right,” said Migwan, in relief, “we’ll surely find her now.”
They gave Pointer a shoe of Sahwah’s and in a moment he had started off
with his nose to the ground. But if they had expected him to lead them
to her hiding-place they were disappointed, for all he did was follow
the trail around the garden between the house and the river. Once he
went down cellar, straining hard at the chain which held him, and they
were sure he would find something they had overlooked in their search,
but the trail ended in front of the fruit cellar.
“Sahwah came down here early this morning to bring up those melons,
don’t you remember?” said Migwan. “That’s all Pointer has found out.”
They kept Pointer at it for some time, but he never offered to leave the
garden.
“Are you sure he’s on the trail?” asked Hinpoha, doubtfully.
“Yes,” said Calvin, “he never whines that way unless he is. That long
howl is the hunting dog’s signal that he’s on the job. When he loses the
trail he runs back and forth uncertainly.”
“According to that, Sahwah must be very near,” said Gladys. “Are you
sure there isn’t any other place in the house, cellar or barn that she
could have gotten into, Migwan?”
“Quite sure,” said Migwan, disheartened. “You know yourself the way we
finecombed every foot of space.”
“There’s another thing that might have made Pointer lose the trail,”
said Nyoda. “Do you remember that he stopped short at the river once?
Well, it is my belief that Sahwah ran down to the river and either fell
or jumped in and swam away. That would destroy the trail, and Sahwah
might be miles away for all we know.” She carefully refrained from
suggesting that anything had happened to Sahwah and she might have gone
under the water and not come up again, but there was a fear tugging at
her heart that Sahwah had dived in and struck her head on something and
gone down.
But several of the others must have had much the same thought, for
Gladys remarked, without any apparent connection, “_You can see the
bottom almost all the way down the river._”
And Hinpoha said, “_Those tangled roots of trees in the river are nasty
things to get into._”
And Calvin set the dog free immediately and untied the rowboat. He and
Nyoda rowed down the river while the rest followed along the banks. The
stream was clear most of the distance and they could see to the bottom.
Here and there were sharp rocks jutting up and casting shadows on the
sunlit bottom, and in places the water had washed the dirt away from the
roots of trees so that they extended out into the river like
many-fingered creatures waiting to seize their prey. But nowhere did
they see what they feared.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river, toward the
mouth, the water was deeper and had been dredged free of all
obstructions, so while it was muddy and they could not see into its
depths they knew that nothing was to be found here.
Vaguely relieved and yet dreadfully anxious and mystified they returned
to Onoway House. “Do you suppose she was carried away by an automobile
or wagon?” asked Migwan. “Does anyone recall seeing anything of the kind
going by when we started to play?” Nobody did. While they were
discussing this new theory, Pointer, who had been left to run loose
while they were searching the river, came running up to them. With much
wagging of his tail he went to Calvin and laid something at his feet For
a moment they could not make out what it was. Migwan recognized it
first.
_It was Sahwah’s shoe, completely covered and dripping with black mud._
“Where did you find it, Pointer?” asked Calvin. Pointer wagged his tail
in evident satisfaction, but, of course, he could not answer his
master’s question.
“Is that the shoe Sahwah had on this morning?” asked Nyoda.
“Yes,” said Hinpoha. “I remember asking her why she wore those shoes
with the red buttons to run around in and she said they were getting
tight and she wanted to wear them out.”
“Where does that black mud come from around here?” asked Gladys.
It was Nyoda who guessed the dreadful fact first. All of a sudden she
remembered cleaning her shoes after she had come home from her visit to
Uncle Peter.
“_The marsh!_” she gasped. “_Sahwah’s caught in the marsh!_ It’s the
same mud. I went to the edge of the marsh the other day to see it and
got some on my shoe.”
Without stopping to hear more, Calvin dashed off in the direction of his
father’s farm, with Pointer at his heels and Gladys and Nyoda and
Hinpoha and Migwan and Tom and Betty trailing after him as fast as they
could go. Mrs. Gardiner followed a little distance behind. She could not
keep up with them. Calvin tore a flat board from one of the fences as he
ran along and called on the others to do the same thing. A little
farther on he found a rope and took that along. They reached the edge of
the marsh and looked eagerly for the figure of Sahwah imprisoned in the
treacherous ooze. But the green surface smiled up innocently at them.
Not a sign of a struggle, no indentation in the level, no break. To the
unknowing it looked like the smoothest lawn lying like a sheet of
emerald in the sun. But on second glance you saw the water bubbling up
through the grass and then you knew the secret of the greenness. Nowhere
could they see Sahwah.
Migwan had to force herself to ask the question that was in everybody’s
mind. “Has she gone under?”
“No,” said Calvin, positively. “It can’t be possible in so short a time.
They say that a horse went down here once long ago, and it took him more
than two days to be covered entirely.”
After being wrought up to such a pitch of expectancy it was a shock to
find that Sahwah was not in the marsh. _But how had her shoe come to be
covered with marsh mud, and what was it doing off her foot?_ Where had
Pointer found it?
“Oh, if only dogs could speak!” said Hinpoha. “Pointer, Pointer, where
did you find it?” But Pointer could only wag his tail and bark.
From where they stood at the edge of the marsh they could see the
cottage among the trees. A look of inquiry passed between Nyoda and
Migwan. Calvin saw the look and understood it.
“Would you like to look in Uncle Peter’s house?” he asked. His face was
very pale, and Nyoda, watching him keenly, thought she detected a sudden
suspicion and fear in his eyes. He looked apprehensively over his
shoulder at the Red House as they started to skirt the bog. Nyoda
understood that movement. Abner Smalley did not know that they knew
about Uncle Peter, and Calvin had said he would be very angry if he
found it out. Now he would be sure to see them going toward the house.
But this thought did not make Nyoda waver in her determination to search
the cottage. The urgency of the occasion released them from their
promise of secrecy. As Calvin had no key they were obliged to enter by
the window as on former occasions. But the front room was absolutely
blank and bare and they saw the impossibility of anyone’s being hidden
there. It was a tense moment when they opened the door of the inner room
and the girls who had never been there stepped behind the others and
held their breath. Uncle Peter sat at the table just as Nyoda and Migwan
had seen him a day or two before, playing with his rods and wheels. His
mild blue eyes rested in astonishment on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thronged the doorway.
“Come in, ladies,” he said, politely. The room was exactly as it had
been the other day and apparently he had not stirred from his position.
They all felt that Sahwah had not been there and that the old man knew
nothing about the matter. But Calvin spoke to him.
“Uncle Peter,” he said. The man turned at the name and stared at him but
gave no sign of recognizing him. “Do you know me, Uncle Peter?” said
Calvin. “It’s Calvin, Jim’s boy.”
The old man smiled vacantly and held out the bit of machinery he was
working on. “It’s a machine for saving time,” he said. “As the minutes
are ticked off——”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gotten out of him, and they
withdrew again. Calvin looked around him fearfully as they returned
through the fields, to see if his uncle had watched him take the girls
to the cottage, but there was no sign of him anywhere, at which he
breathed an unconscious sigh of relief. Tired out with their ceaseless
searching and sick with anxiety, they returned to Onoway House.
If we were writing an ingeniously intricate detective story the thing to
do would be to wait until Sahwah was discovered by some brilliant piece
of detective work and then have her tell her story, leaving the
explanation of the mystery until the last chapter, and keeping the
reader on the verge of nervous prostration to the end of the piece. But,
as this is only a faithful narrative of actual events, and as Sahwah is
our heroine as much as any of the girls, we know that the reader would
much prefer to follow her adventures with their own eyes, rather than
hear about them later when she tells the story to the wondering
household. And we also think it only fair to say that if Sahwah’s return
had depended on any brilliant detective work on the part of the others
we have very grave doubts as to its ever being accomplished. We will,
then, leave the dwellers at Onoway House to their searching and
theorizing and bewailing, and follow Sahwah from the time they started
to play hide-and-seek and Hinpoha blinded her eyes and began to count
“five, ten, fifteen, twenty.”
Sahwah ran across the garden toward the house, intending to swing
herself into one of the open cellar windows. Near this window was a
flower bed which Migwan had filled with especially rich black soil. That
morning she had watered the bed and had done it so thoroughly that the
ground was turned into a very soft mud. Sahwah, not looking where she
was going, stepped into this mud and sank in over her shoe top with one
foot. When she had entered the window she stood on the cellar floor and
regarded the muddy shoe disgustedly. Feeling that it was wet through,
she ripped it off and flung it out of the window. It landed back in the
muddy bed and was hidden by the growing plants. Sahwah then proceeded to
hide herself in the fruit cellar. This was a partitioned off place in a
dark corner. She sat among the cupboards and baskets and watched Hinpoha
pass the window several times as she hunted for the players. Once
Hinpoha peered searchingly into the window and Sahwah thought she was on
the verge of being discovered and pressed back in her corner. There was
a basket of potatoes in the way of her getting quite into the corner and
she moved this out. There was also a barrel of vinegar and she slipped
in behind this. As she moved the barrel it dropped back upon her
shoeless foot and it was all she could do to repress a cry of pain as
she stood and held the battered member in her hand. But the pain became
so bad she decided to give up the game and get something to relieve it.
She pushed hard against the barrel to move it out, but this time it
would not move. She pushed harder, bracing her back against the wooden
wall behind her, when, without warning, the wall caved in as if by
magic, and she fell backwards head over heels into inky darkness. The
wall through which she had fallen closed with a bang.
Sahwah sat up and reached mechanically for the hurt foot. The pain had
increased alarmingly and for a time shut out all other sensations. Then
it abated a little and Sahwah had time to wonder what she had fallen
into. She was sitting on a stone floor, she could make that out. It must
be a room of some kind, she decided, but the darkness was so intense
that she could make nothing out. “There must have been another part to
the cellar behind the fruit cellar, although we never knew it,” thought
Sahwah, “and the back of the fruit cellar was the door.” As soon as she
could stand upon her foot again she moved forward in the direction from
which she thought she had come and searched with her hands for a
doorknob. But her fingers encountered only a smooth wall surface and
after about five minutes of careful feeling she came to the startled
conclusion that there was no such thing. “I must have got turned around
when I tumbled,” she thought, “and am feeling of the wrong wall.” She
accordingly moved forward until her outstretched hands encountered
another hard surface and she repeated the process of looking for a
doorknob. No more success here. “Well, there are four walls to every
room,” thought Sahwah, “and I’ve still got two more trys.” Again she
moved out cautiously and with ever increasing nervousness admitted that
there was no door in that direction. “Now for the fourth side, the right
one at last,” she said to herself. “One, two, three, out goes me!” She
moved quickly in the fourth and last direction. Without warning she ran
hard into something which tripped her up. She felt her head striking
violently against something hard and then she knew no more.
She woke to a dream consciousness first. She dreamed she was lying in
the soft sand on the lake shore near one of the great stone piers, where
a number of men were at work. They were pounding the stones with great
hammers and the vibrations from the blows shook the beach and went
through her as she lay on the sand. Gradually the sparkling water faded
from her sight; the sky grew dark and night fell, but still the blows
continued to sound on the stone. Just where the dream ended and reality
began she never knew, but, with a rush of consciousness she knew that
she was awake and alive; that everything was dark and that she was lying
on her face in something soft that was like sand and yet not like it.
And the pounding she had heard in her dream was still going on. Thud,
thud, it shook the earth and jarred her so her teeth were on edge. For a
long time she lay and listened without wondering much what it was. Her
head ached with such intensity that it might have been the throbbing of
her temples that was shaking the earth so. After a while that dulled,
but the jarring blows still kept up. With a cessation of the pain came
the power to think and Sahwah remembered the strange noises they had
heard issuing from the ground. It must be the same noise; only it was a
hundred times louder now. It was a sort of clanging thump; like the
sound of steel on stone. Even with all that noise going on Sahwah
slipped off into half consciousness at times. Although there did not
seem to be any doors or windows, she was not suffering for lack of air,
but at the time she was too dazed to notice this and wonder at it.
She woke with a start from one of these dozes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re was a broad streak of light on the floor. Fully conscious now, she
raised her head and looked around. She was lying in a bin filled with
sawdust. When she held up her head her eyes came just to the top of it.
By the light she could see that she was indeed in a sort of sub-cellar.
It must have been older than the other cellar for the floor was made of
great slabs of mouldy stone. Her eyes followed the beam of light and she
saw that a door had been opened into still another cellar beyond. In
this chamber a lantern stood on the floor, whence came the light, and
its ray produced weird and fantastic moving shadows. These shadows came
from a man who was wielding a pickaxe against a spot in the stone wall.
It was this that was causing the jarring blows. Startled almost out of
her senses at seeing a man thus apparently caged up in the sub-cellar of
Onoway House, Sahwah could only lay back with a gasp. She could not
raise her voice to cry out had she been so inclined.
But fast on the heels of that shock came another. The worker paused in
his exertions to wipe the perspiration from his brow, and stood where
the light of the lantern shone full in his face. Sahwah’s heart gave a
great leap when she recognized Abner Smalley. Abner Smalley in the
hidden sub-cellar of Onoway House, digging a hole in the wall! Sahwah
forgot her own plight in curiosity as to what he was doing. She lay and
watched him fascinated while he resumed his pounding. So he was the
mysterious intruder who had wrought such terror among them! This, then,
was the well digger’s ghost! What could he be searching for in the
cellar of his neighbor’s house? Sahwah dug her feet into the soft
sawdust as she watched the pick rise and fall. She had no idea of the
flight of time. She thought it was only a few minutes since she had
fallen into the sub-cellar. She lay thinking of the expressions on the
faces of the girls when she would tell them her discovery. To think that
she had been the one to solve the mystery! She felt a little
disappointed that the mysterious intruder should have turned out to be
someone they knew. It would have been more in keeping with her idea of
romance to have found a prince shut up in the cellar.
While she was thinking these thoughts the light suddenly vanished and
she heard the bang of a door shutting. She was in darkness once more. In
a moment she heard footsteps retreating and dying away in the distance.
All was silent again. It took her some moments to collect her thoughts
sufficiently to realize a new and significant fact. _Abner Smalley had
not gone out by the door into the fruit cellar. There must be, then,
another way of egress from the sub-cellar._ Instantly Sahwah made up her
mind to follow him and see how he had gotten out at the other end. Her
feet were imbedded deeply in the sawdust and she became aware of the
fact that her shoeless foot was resting against something with a sharp
edge. She drew it away and then carefully felt with her hands for the
object. She could not see it when she had it but it felt like a metal
box of some kind, possibly tin. She carried it with her and moved toward
the place where she now knew there was a door. She found the handle
easily and opened it. This was the side of the wall toward which she had
moved when she had run into the bin before, and so she did not discover
it. A strong breath of air struck her as she advanced into this chamber.
It was scarcely more than a passage, for by reaching out her arms she
could touch the wall on both sides. She moved cautiously, fearing to
fall again in the dark. She felt the place in the wall where Abner
Smalley had made an indentation with his pick. She was wondering where
this passage led and wishing it would come to an end soon, when she
struck the already sore foot against what must have been the pickaxe set
against the wall and fell on her nose once more. The tin box she carried
was rammed into the pit of her stomach and knocked the breath out of
her, but this time she had not hit her head.
She lay still for a moment trying to get her breath back. Her eyes were
becoming accustomed to the inky darkness by this time. She looked down
and saw a stone floor beneath her. She turned her head to one side and
saw a stone wall beside her. She turned over altogether and looked
up—and saw the constellation Cassiopea flashing down at her from the
sky. For a moment she could not believe her senses. Of all the strange
sights she had seen nothing had affected her so powerfully as the sight
of that familiar group of stars. What she had expected to see she could
not tell, stone perhaps, but anything except the open sky. She sat up in
a hurry and began to investigate where she was. The wall around her
seemed to be circular and all of a sudden Sahwah had the answer. She was
in the cistern—the old unused cistern which was not a great distance
from the house. This, then, was the opening of the sub-cellar, the way
in which Mr. Smalley had made his escape. There was usually a covering
over the cistern, but he had evidently been in a hurry and left it off.
The fact that there were stars out took Sahwah’s breath away. It was
night then; had she been in that cellar all day? It was inconceivable,
yet it was undoubtedly true. By the faint glimmer of the stars she could
make out that there were hollows in the stone side of the cistern by
which a person could easily climb out. She lost no time in climbing when
she made this discovery. What a joy it was to be coming up into God’s
outdoors again! As she emerged from the cistern she saw Migwan standing
in the garden beside the back porch. The moon shone full on her as she
stepped out of the hole in the ground and just then Migwan caught sight
of her. The apparition was too much for Migwan and she screamed one
terrified scream after another until the girls came running from all
over to see what fresh calamity had happened. Only seeing Sahwah
standing in their midst and not having seen her appear magically out of
the depths of the ground, they could not understand Migwan’s terror.
“Stop screaming, Migwan,” said Sahwah, and when Migwan heard her voice
and saw that it was really she, she quieted down and listened while
Sahwah told her tale of adventure since going down into the cellar to
hide. The day had passed so quickly for Sahwah, she having lain
unconscious until late in the afternoon, that she, of course, knew
nothing of their frantic search for her and so could not comprehend why
they made such a fuss over her return. They laughed and cried all at
once and hugged her until she finally protested.
“What have you brought along as a souvenir of your trip?” asked Nyoda,
who had regained her light-hearted manner now that Sahwah was safely
back.
Sahwah looked down at the box she held in her hand. “I found it in the
bin of sawdust,” she said. “It was just like playing ‘Fish-pond’ at the
children’s parties. You put your hand in a box of sawdust and draw out a
handsome prize.” And Sahwah laughed, her familiar long drawn-out giggle,
that they had despaired of ever hearing again. She laid the box on the
table. It was of tin, about nine inches long by three inches wide by
three high, with a closely fitting cover. “Shall I open it, Nyoda?” she
asked.
“I don’t see any harm in doing so,” said Nyoda. Sahwah took off the
cover. There was nothing in the box but a folded piece of paper. She
took it and spread it before them on the table.
“What is it?” they all cried, crowding around. The first thing that
caught their eye was a slanting line drawn across the paper in heavy
ink. There was some writing beside it, but this was so faded that it
took some studying to make it out. Finally they got it. It read:
“_Supposed extension of gas vein._” The upper end of the line was marked
“_36 feet west of cistern._” There was a cross at that point also, and
this was marked, “_Place where gas was struck at 300 feet._”
“The Deacon’s gas well!” they all exclaimed in chorus. It was true,
then.
“And there was a well digger’s ghost, even if it didn’t turn out to be
the one we expected!” said Migwan.
That day was never to be forgotten, although the next cleared up the
mystery and brought still another surprise. Dave Beeman, the constable,
was once more brought out and this time furnished with information that
nearly caused his eyes to start from his head. Abner Smalley, the (as
everyone supposed) respectable citizen of Centerville Road, breaking
into his neighbor’s house and deliberately trying to dig a hole in the
stone wall. It was the sensation of his career. “Well, I’ll be
jiggered!” he gasped.
But his surprise was nothing compared to Abner Smalley’s when he was
confronted with the accusation without warning. He turned so pale and
trembled so much that it was useless to deny his guilt.
“You are guilty, Abney Smalley,” said the constable, in such a solemn
tone that the girls could hardly keep straight faces. “You’d better make
a clean breast of it and tell what you were doing in that house or it
might go hard with you.”
Abner Smalley, although he was a bully by nature, was a coward when the
odds were against him, and he had always had a wholesome fear of the
law, so at Dave Beeman’s suggestion he decided to “make a clean breast
of it.” We will not weary the reader with all the conversation that took
place, but will simply tell the facts of the story.
Some time ago, while the old caretaker lived on the place yet, the story
of the Deacon’s gas well had come to Abner Smalley’s ears. He heard a
fact connected with it, however, that was not generally known, namely,
that the Deacon had made a record of the place where the gas was found.
Believing that the Deacon had left it hidden somewhere in the house, he
had devised a means of breaking in and searching for it. His first plan
had been to frighten the dwellers in the house and make them believe
there was a ghost in the attic so they would give the place a wide berth
at night and leave him free to ransack the Deacon’s old furniture. He
frightened the Mitchells so that they moved. But no sooner had the
Mitchells departed than the new caretakers had come; and they were a
much bigger houseful than the others.
He had tried the same plan with them as he had with the others, namely,
mysterious noises around the place at night. But what had frightened
Mrs. Mitchell into moving had no effect on these new farmers. They shot
off a gun when he was doing his best ghost stunt, namely, blowing into a
bottle, which had produced that weird moaning sound. He it was who had
dressed up as a ghost and appeared to Nyoda in the tepee; throwing the
red pepper into her face when she made as if to attack him with a pole.
It was he whom they had seen coming out of the barn that night, and
later it was he again whom Migwan had seen during the hail storm. He had
disappeared so utterly by jumping down the cistern.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he had been down, and on this occasion he had discovered the
passage leading to the sub-cellar. It was he the girls had heard in the
attic on numerous occasions. He had entered and gone out after dark by
means of the Balm of Gilead tree. One time he broke the window. He had
been down cellar that night when Sahwah nearly caught him. He was
looking for the other entrance to the sub-cellar, which he never found.
He knocked over the basket of potatoes which had mystified them so. He
had been on the point of entering the house that day when Sahwah
suddenly returned from town after he thought the whole family was gone
for the day. When he saw her go off along the river he went in anyway
and was nearly caught in the attic by the girls. He had escaped
detection by hiding in a large chest.
The day they had gone for the picnic he saw them go and spent all day
looking through the desks in the house. Finally the dog barked so he
gave him the poisoned meat he had brought along to use if necessary.
Then the family had returned and he had had a narrow escape into the
cistern. He had stayed there until night, when he had set fire to the
tepee, not knowing that anyone was sleeping in it. After starting the
blaze he had again sought refuge in the cistern and when the crowd had
gathered, came out in their midst so that his absence from such an
exciting event in the neighborhood would cause no comment among the
farmers. The cistern was in the shadow and everyone was watching the
fire so intently that he was able to emerge unseen.
He had sprayed the tomatoes with lime and written the note which they
found on the door. He had left the chisel in the automobile on one
occasion when he had been hunting through the things in the barn;
forgetting to take it with him when he went out.
He wanted to get hold of that record secretly and be sure whether the
great vein of gas which the Deacon knew existed was on the property now
owned by the Bartletts or that of the Landsdownes, and then he was going
to buy that property before the owners knew about the gas, as the land
would be worth a fortune if that fact ever became known. He was pretty
sure, after discovering that sub-cellar, that the Deacon had left his
papers down there when he went to California. By pounding on the walls
he had discovered one place which he was sure was hollow. If the stone
that covered the place could be removed by any trick he failed to
discover it and had to resort to digging it out with a pick. This, as we
already know, produced the dull thudding sound underground which had
frightened the household almost out of their wits. The reason he could
prowl around in the yard at night after they had set the dog to watch
was that Pointer knew him and made no disturbance upon seeing him.
Abner Smalley was marched off triumphantly by Dave Beeman, and was held
on such a complicated charge of house-breaking, arson, assault and
battery, and intimidating peaceful citizens, that it took the combined
efforts of the village to draw it up. Thus ended the great mystery which
had kept Onoway House in more or less of an uproar all summer.
“I never saw anything like the way we Winnebagos have of falling into
things,” said Sahwah. “Here Mr. Smalley made such elaborate efforts to
find that record, using up more energy and ingenuity than it would take
to dig up the whole farm and hunt for the gas well; and he didn’t find
it in the end; and all I did was drop in on top of it without even
suspecting its existence.”
“There must be a special destiny that guides us,” said Migwan. “Perhaps
we possess an enchanted goblet, like the ‘Luck of Edenhall,’ only it’s
‘The Luck of the Winnebagos.’”
“Cheer for the ‘Luck of the Winnebagos,’” said Sahwah, who never lost an
occasion to raise a cheer on any pretext. And at that Sahwah never
dreamed of the extent of the good fortune she had brought the Bartletts
by her lucky tumble. The vein of gas which was struck when they
subsequently drilled proved a sensation even in that notable gas region
and made millionaires of its owners. And the reward which Sahwah
received for finding the record, and that which the others received
“just for living,” as Migwan expressed it—for though they had not found
the sub-cellar themselves it was due to their game that Sahwah had found
it—drove the memory of their fright from their heads. But we are getting
a little ahead of our story. There is one more chapter yet to the Luck
of the Winnebagos before that remarkable summer came to an end.
After the departure of Abner Smalley things grew so quiet at Onoway
House that Migwan, who had declared before that she would be a wreck if
the excitement did not cease soon, was now complaining that things
seemed flat and she wished the mystery hadn’t been cleared up because it
robbed them of their chief topic of conversation.
“Well, I’m go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quiet atmosphere and
straighten out my bureau drawers,” said Nyoda. “I haven’t been able to
put my mind to it with all this excitement going on. And they’re a sight
since you girls went rummaging for things for the Thieves’ Market.” In
doing this she came upon that strange creation of Uncle Peter’s brain,
the plan for the “Wasted Minute Saving Machine.” She showed it to the
girls and they examined it wonderingly.
“What is this on the other side?” asked Migwan. “It’s a will!” she
cried, reading it through. “It says, ‘I, Adam Smalley, give and
bequeathe my farm on the Centerville Road to my son Jim, as Abner has
already had his share in cash.’”
“Let me see!” cried Calvin. “It’s the latest one!” he shouted, reading
the date. “It’s dated 1902 and the one Uncle Abner found was 1900. The
farm is mine after all! Uncle Peter had this will in his possession and
didn’t know it! How can I thank you girls for what you’ve done for me?”
“It was all Migwan’s fault,” said Hinpoha. “She insisted upon going to
see whether the old man was all right after the storm.”
Migwan declared that she ha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t; it was the Luck
of the Winnebagos that had given her the inspiration. But Calvin knew
well that in this case the Luck of the Winnebagos was only Migwan’s own
thoughtfulness.
CHAPTER XIV.—GOOD-BYE TO ONOWAY HOUSE.
By the first of September Migwan had made enough money from the sale of
canned tomatoes to more than pay her way through college the first year.
“It’s Mother Nature who has been my fairy godmother,” she said to the
girls. “I asked her for the money to go to college and she put her hand
deep into her earth pocket and brought it out for me. It’s like the
magic gardens in the fairy tales where the money grew on the bushes.”
“What a summer this has been, to be sure,” said Hinpoha, who was in a
reflective mood. They were all sitting in the orchard, busy with various
sorts of handwork. The day was hot and drowsy and the shade of the trees
most inviting. “Migwan and I thought we would have such a quiet time
together, just we two. She was going to write a book and I was going to
illustrate it, when we weren’t working in the garden. And how
differently it all turned out! One by one you other girls came—I’ll
never forget how funny Gladys and Nyoda looked when they came out that
night, and how surprised Sahwah was to find you here when she arrived.
Then Gladys brought Ophelia, I mean Beatrice, and after that we never
had a quiet moment. Then the mystery began and kept up all summer.
Instead of these three months being a quiet rest they’ve been the most
thrilling time of my life.”
“It seems to have agreed with you, though,” said Sahwah, mischievously,
whereupon there was a general laugh, for Hinpoha, instead of growing
thin with all the worry and excitement, had actually gained five pounds.
“As much worry as it caused me,” said Migwan, “I’m glad everything
happened as it did. The summer I had looked forward to would have been
horribly dull and uninteresting, but now I feel that I’ve had some real
experiences. I’ve got enough ideas for stories to last for years to
come.”
“And for moving picture plays,” said Hinpoha. “But,” she added, “if you
go in for that sort of thing seriously, where am I coming in? You know
we made a compact; I was to illustrate everything you wrote, and how am
I going to illustrate moving picture plays?”
There was a ripple of amusement at her perplexity. “You’ll have to
illustrate them by acting them out,” said Gladys. They all agreed
Hinpoha would make a hit as a motion picture actress, all but Sahwah,
who dropped her eyes to her lap when Migwan began to talk about moving
pictures, and presently went into the house to fetch something she
needed for her work. When she came out again the subject had been
changed and was no longer embarrassing to her.
“What will the Bartletts say when they hear the peach crop was ruined by
the wind storm?” asked Hinpoha.
“That’s the only thing about our summer experience that I really
regret,” answered Migwan. “I wrote and told them about it, of course,
when I told them about the gas well, and Mrs. Bartlett said we shouldn’t
worry about it and that we ourselves were a crop of peaches.”
“The dear thing!” said Gladys. “I should love to see the Bartletts again
some time; they were so friendly to us last summer, and it is all due to
them that we have had such a glorious time this summer.”
Scarcely had she spoken when an automobile entered the drive and stopped
beside the house. Migwan ran out to see who it was. The next moment she
had her arms around the neck of a pretty little woman. “Oh, Mrs.
Bartlett!” she cried. “Did the fairies bring you? We just made a wish to
see you.”
Soon the girls were all flocking around the car, shaking hands with Mr.
and Mrs. Bartlett, and making a fuss over little Raymond. How the
Bartletts did sit up in astonishment when all the events of the summer
were told in detail! “Well, you certainly are trumps for sticking it
out,” said Mr. Bartlett, admiringly. “Nobody but a bunch of Camp Fire
Girls would have done it.” At which the Winnebagos glowed with pride.
Now that the Bartletts had come to stay at Onoway House, Migwan decided
she would go home a week earlier than she had planned, as there was not
enough room for so many people there. Aunt Phœbe and the Doctor were in
town again, so Hinpoha could go home if she wished; and Sahwah’s mother
had also returned. They were a little sorry to break up so abruptly when
they had planned quite a few things for that last week to celebrate the
finishing of the canning, but all agreed tha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it
was the best thing they could do.
“I really need a week at home,” said Migwan with a twinkle in her eye,
“to rest up from my vacation. There I’ll get the peace and quiet that I
came here to seek.” Take care, O Migwan, how you talk! Once before you
predicted peace and quiet, and see what happened!
Before they went, however, they must have one more big time altogether,
Mrs. Bartlett insisted, and she went into town on purpose to bring out
Nakwisi and Chapa and Medmangi. Close behind them came another car which
also stopped at Onoway House, and out of it stepped Mr. and Mrs. Evans
and Aunt Beatrice and Uncle Lynn and little Beatrice, the latter dressed
up in wonderful new clothes and already subtly changed, but still eager
to romp with the girls and tag after Sahwah.
“See here,” said Mr. Evans, when they were all talking about going home
the next day, “you girls have been working pretty hard this summer, and
haven’t had a real vacation yet, why don’t you go for an automobile trip
the last week? Gladys has her car; that is, if it came through all the
excitement alive, and mother and I would be willing to let you take the
other one. Go on a run of say a thousand miles or so, and see a few
cities. The change will do you good.”
“Oh, papa!” cried Gladys, clapping her hands in rapture. “That will be
wonderful!” And the other girls fell in love with the idea on the spot.
As this was to be their last night at Onoway House nothing was left
undone that would make the occasion a happy one. The evening was fine
and warm and the stars hung in the sky like great jeweled lamps. With
one accord they all sought the garden and the orchard, where Gladys
danced on the grass in the moonlight like a real fairy. Then all the
girls danced together, until Mrs. Evans declared that they looked like
the dancing nymphs in the Corot picture. And Beatrice, who had been
taught those same things during the summer, broke away from her mother
and joined in the dance, as light and graceful as Gladys herself. It was
plain to see that she had the gift which ran in the family, and as her
mother watched her with a thrill of pride her heart overflowed anew in
thankfulness to the girls who had restored her daughter to her.
“On such a night,” quoted Migwan, looking up at the moon, “Leander swam
the Hellespont——”
“The river!” cried Sahwah, immediately, “we must go out on the river
once more. Oh, how can I say good-bye to the Tortoise-Crab?” And she
shed imaginary tears into her handkerchief.
“Let’s go for one more float,” cried all the girls.
The grown-ups strolled down to the river bank and sat on the grassy
slope, watching with indulgent interest what the girls were going to do
next. They saw them coming far up the river and heard their song as it
was wafted down on the scented breeze. Slowly and majestically the raft
approached, with Sahwah standing up and guiding it with the pole. When
it had come nearer the onlookers saw a romantic spectacle indeed. Gladys
reposed on a bed of flowers and leaves, under a canopy of branches and
vines, a ravishingly lovely Cleopatra. Beside her knelt Antony,
otherwise Migwan, holding out to her a big white water lily. The other
Winnebagos, as slave maidens, sat on the raft and wove flower wreaths or
fanned their lovely mistress with leaf fans. It was the slaves who were
doing the singing and their clear voices rang out with wonderful harmony
on the enchanted air. On they came, past the spot where Sahwah had been
hidden on the afternoon of the moving pictures; past the Lorelei Rock,
where they had held that other pageant which had frightened Calvin so;
past the spot where they lay concealed and watched the strange manœuvers
of the supposed Venoti gang. Each rock and tree along the stream was
pregnant with memories of that eventful summer, and they could hardly
believe that they were saying good-bye to it all.
Now they were opposite the watchers on the bank and the murmurs of
admiration reached their ears as they floated past. “What lovely
voices——”
“What wonderful imaginations those girls have——”
“How beautifully they work together——”
Calvin looked on in speechless admiration, his eyes for the most part on
Migwan. Never in his life had he regretted anything so much as he did
the fact that these jolly friends of his were going away. He was to stay
on his farm after all and now the prospect suddenly seemed empty.
The voices of the onlookers blended in the ears of the boaters with the
murmur of the river as it flowed over the stones, and with the sighing
of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as the raft passed on.
And here let us leave the Winnebagos for a time as we love best to see
them, all together on the water, their voices raised in the wonder song
of youth as they float down the river under the spell of the magic
moonlight.
THE END.
The next volume in this series is entitled: The Camp Fire Girls Go
Motoring; or, Along the Road that Leads the Way.
* * * * *
The Camp Fire Girls Series
By HILDEGARD G. FREY. The only series of stories for Camp Fire Girls
endorsed by the officials of the Camp Fire Girls Organization.
PRICE, 40 CENTS PER VOLUME
THE CAMP FIRE GIRLS IN THE MAINE WOODS; or,
The Winnebagos go Camping.
This lively Camp Fire group and their Guardian go back to Nature in a
camp in the wilds of Maine and pile up more adventures in one summer
than they have had in all their previous vacations put together. Before
the summer is over they have transformed Gladys, the frivolous boarding
school girl, into a genuine Winnebago.
THE CAMP FIRE GIRLS AT SCHOOL; or,
The Wohelo Weavers.
It is the custom of the Winnebagos to weave the events of their lives
into symbolic bead bands, instead of keeping a diary. All commendatory
doings are worked out in bright colors, but every time the Law of the
Camp Fire is broken it must be recorded in black. How these seven live
wire girls strive to infuse into their school life the spirit of Work,
Health and Love and yet manage to get into more than their share of
mischief, is told in this story.
THE CAMP FIRE GIRLS AT ONOWAY HOUSE; or,
The Magic Garden.
Migwan is determined to go to college, and not being strong enough to
work indoors earns the money by raising fruits and vegetables. The
Winnebagos all turn a hand to help the cause along and the “goings-on”
at Onoway House that summer make the foundations shake with laughter.
THE CAMP FIRE GIRLS GO MOTORING; or,
Along the Road That Leads the Way.
The Winnebagos take a thousand mile auto trip. The “pinching” of Nyoda,
the fire in the country inn, the runaway girl and the dead-earnest hare
and hound chase combine to make these three weeks the most exciting the
Winnebagos have ever experienced.
For sale by all booksellers, or sent postpaid on receipt of price by the
publishers. A. L. BURT COMPANY, 114-120 East 23d Street, New York.
* * * * *
The Blue Grass Seminary Girls Series
By CAROLYN JUDSON BURNETT
Handsome Cloth Binding
Price, 40c. per Volume
_Splendid Stories of the Adventures of a Group of Charming Girls_
THE BLUE GRASS SEMINARY GIRLS’ VACATION ADVENTURES;
or, Shirley Willing to the Rescue.
THE BLUE GRASS SEMINARY GIRLS’ CHRISTMAS HOLIDAYS;
or, A Four Weeks’ Tour with the Glee Club.
THE BLUE GRASS SEMINARY GIRLS IN THE MOUNTAINS;
or, Shirley Willing on a Mission of Peace.
THE BLUE GRASS SEMINARY GIRLS ON THE WATER;
or, Exciting Adventures on a Summer’s Cruise Through the
Panama Canal.
* * * * *
The Mildred Series
By MARTHA FINLEY
Handsome Cloth Binding
Price, 40c. per Volume
_A Companion Series to the Famous “Elsie” Books by the Same Author_
MILDRED KEITH
MILDRED AT ROSELANDS
MILDRED AND ELSIE
MILDRED’S NEW DAUGHTER
MILDRED’S MARRIED LIFE
MILDRED AT HOME
MILDRED’S BOYS AND GIRLS
For sale by all booksellers, or sent postpaid on receipt of price by the
publishers. A. L. BURT COMPANY, 114-120 East 23d Street, New York.
* * * * *
The Girl Chum’s Series
ALL AMERICAN AUTHORS.
ALL COPYRIGHT STORIES.
A carefully selected series of books for girls, written by popular
authors. These are charming stories for young girls, well told and full
of interest. Their simplicity, tenderness, healthy, interesting motives,
vigorous action, and character painting will please all girl readers.
Gladys appeared, felt of all their pulses and gave each a dose out of a
bottle, whereupon they all straightened up, lost their symptoms of
distress, and capered for joy.
“Cure,” said Migwan. The players shook their heads.
“Heal,” shouted Hinpoha, and Gladys acknowledged it.
In the last syllable Gladys went around and demanded payment for her
services, but in each case was met with a promise to pay at some future
time.
“Owe,” said Chapa, which was pronounced right. “O heal woe, what’s
that?” she asked.
“You’re twisted,” said Nyoda, “it’s ‘Wohelo.’ That really was too easy.
Let’s not divide them into syllables after this,” she suggested, “it’s
no contest of wits that way. Let’s act out the word all at once.” The
alteration was accepted with enthusiasm.
Hinpoha came out alone for her side. “Word of two syllables,” she said.
Taking a blanket she spread it over a bushy weed and tucked the corners
under until it looked not unlike a large stone. Then she retired from
the scene. Soon Nyoda came along and paused in front of the blanket,
which looked like an inviting seat.
“What a lovely rock to rest on!” she exclaimed, and seated herself upon
it. Of course, it flattened down under her weight and she was borne down
to the ground.
A moment of silence followed this performance as the guessers racked
their brains for the meaning. “Is it ‘Landsdowne?’” asked Gladys.
“It might be, but it isn’t,” said Nyoda, laughing.
“I know,” said Sahwah, starting up, “it’s ‘shamrock.’”
“You are sharper than I thought,” said Nyoda, rising from her seat.
“Nobody down yet. Now, fire your broadside at us. No word under three
syllables. Anything less would be unworthy of our giant intellects.”
“Third round!” cried Calvin.
Sahwah walked down to the water’s edge, holding in her hand a large key.
Leaning over, she moved the key as if it were walking in the water. This
proved a puzzler, and cries of ‘Milwaukee,’ ‘Nebrasky,’ and ‘turnkey’
were all met with a triumphant shake of the head.
“It looks as if we would have to give up,” said Hinpoha.
Just then Nyoda sprang up with a shout. “Why didn’t I think of it
before?” she cried. “It’s ‘Keewaydin,’ key-wade-in. What else could you
expect from Sahwah?”
“That’s it,” said Sahwah. “You must be a mind reader.”
“Here’s where we finish you off,” said Nyoda, as her side came out
again. “We’ve taken a word of four syllables this time.” The whole team
advanced in single file, Indian fashion, keeping closely in step. Round
and round they marched, back and forth, never slackening their speed,
until one by one they tumbled to the ground from sheer exhaustion and
stiffened out lifelessly. The guessers looked at each other, puzzled.
“Do it again,” said Sahwah. The strenuous march was repeated, and the
marchers succumbed as before. Still no light came to the onlookers.
Sahwah whispered something to Gladys.
“Would you just as soon do it again?” asked Gladys. Again the file wound
round the trees and tumbled to the turf. Nyoda made a triumphant grimace
as no guess was forthcoming. Sahwah’s eyes began to sparkle.
“Would you please do it once more?” she pleaded.
“Have mercy on the performers,” groaned Nyoda, but they went through it
again, and this time they were too spent to rise from the ground when
the acting was done. “Do you give up?” called Nyoda.
“No,” answered Gladys.
“You have five seconds to produce the answer, then,” said Nyoda.
“It’s diapason,” said Gladys, “die-a-pacin.”
“Really!” said Nyoda, falling back in astonishment.
“We knew it all the while!” cried Sahwah and Gladys. “We just kept you
doing it over and over again because we liked to see you work.”
The laugh was on Nyoda and her team all the way around. “We do this to
each other!” called Sahwah, using the Indian form of taunt when one has
played a successful trick on another.
“Tie the villains to a tree, and let them perish of mosquito bites,”
Nyoda commanded in an awful tone. “I’ll get even with you for that, Miss
Sahwah,” she said, darkly, as the other side trooped off to cook up a
new poser.
“Hadn’t you better stop playing now?” inquired Mrs. Gardiner. “You know
we wanted to get home before dark.”
“Oh, let’s do one more,” pleaded Migwan. If they had only stopped
playing when Mrs. Gardiner suggested it and gone home early they might
have been in time to prevent the thing which occurred, but they were
bent on seeing one side or the other go down, and Gladys’s side prepared
another charade.
“We’ve played up to your own game,” said Gladys, who was introducing the
new charade, “and have increased the number to five syllables.” The
actors were Mrs. Gardiner, Betty and Tom Gardiner. Mrs. Gardiner was
scolding the children and emphasized her remarks by a sharp pinch on
Tom’s arm. Betty, seeing the maternal hand also extended in her
direction, promptly climbed a tree and sat in safety, while her mother
shook her finger at her and cried warningly, “I’ll attend to you after
awhile.”
“What on earth?” said Nyoda, scratching her head in perplexity. But
scratch as she might, no answer came, and the rest of her team had
nothing to offer either. After holding out for fully fifteen minutes
they were compelled to give it up.
“It’s ‘manipulator,’” cried the winning side, in chorus.
“‘Ma-nip-you-later!’” And they stood around to condole while Nyoda’s
side prepared supper. Then it was that Calvin, basely deserting the team
he had helped so far, went over to the side of the enemy and helped
Migwan fetch wood for the fire. Both sides stopped often to jeer at each
other, so it took them twice as long to get the meal ready as it would
have ordinarily. They loitered and sang along the way home, letting the
horses take their time, and it was quite late when they reached Onoway
House.
The first thing that greeted them was the sight of Mr. Bob, the cocker
spaniel, rolling on the front lawn in great distress, and giving every
sign of being poisoned. They hastily administered an antidote and, after
a time of suspense were confident that the effect of the poison had been
counteracted. So far they had only been in the kitchen, but when the
excitement about the dog was over they moved toward the sitting-room to
rest awhile and drink lemonade before going to bed. When the light was
lit they all stopped in astonishment. In the sitting-room there was an
old-fashioned combination desk and bookcase, the bookcase part set on
top of the desk and reaching nearly to the ceiling. It belonged to the
house, and the desk was closed and locked. Now, however, it stood open,
and all the drawers were pulled out, while the top of the desk and the
floor before it were strewn with papers in great disorder.
“Burglars!” cried Migwan. “The house has been robbed!” They immediately
looked through the house to see what had been taken. Up-stairs in the
room occupied by the two boys there was a desk similar to the one in the
sitting-room. This had also been broken open and the drawers searched
through, although the disorder of papers was not so great as it was
down-stairs. Half afraid of what they should find, the whole family went
from room to room, but nothing else seemed to have been disturbed, and
as far as they could see nothing had been stolen. The silver in the
sideboard drawer was untouched, but then, this was only plate, and worn
at that. But in full view on the dining-room table lay Sahwah’s
Firemaker Bracelet, which she had laid there a few moments before
starting for the picnic, and then, with her customary forgetfulness,
neglected to pick up again. This was solid silver and worth stealing.
Further than that, she had also forgotten to wear her watch, and it was
still safe in her top bureau drawer. It was a riddle, and as they talked
it over they could only come to one conclusion, and that was that the
burglar had thought there were large sums of money hidden in the two
desks and had passed over the small articles in the hope of getting a
bigger harvest, or else was leaving those other things to the last. He
ransacked the up-stairs desk, having broken the lock, and then went
through the one down-stairs. While looking through the papers in the
sitting-room he had evidently been frightened away by something, for
there was one drawer that had not been disturbed. This also accounted
for the fact that nothing else had been taken. What had frightened him
was probably the barking of the dog, who, although he was on the
outside, had become aware of the presence of someone in the house. He
had fed the dog poison, probably poisoned meat, for they had found a
small piece of meat on the porch. Evidently the poison had begun to act
before Mr. Bob had it all eaten, and he left that piece. But before the
dog was dead the burglar had heard the family returning along the road,
singing, and made his escape. The whole thing must have happened not
long before, for the dog had not had the poison long enough to take
deadly effect. It was then that they regretted having lingered so long
over the game of charades and delayed their homecoming.
“If we had only been half an hour sooner, we might have found out who it
was,” said Mrs. Gardiner.
“Thank Heaven we weren’t half an hour later,” said Hinpoha, “or Mr. Bob
would have been dead.” She would have felt worse about losing Mr. Bob
than about having all her possessions stolen.
“How about sleeping in the tepee to-night?” asked Gladys. There was not
enough room in the house for so many people and the eight Winnebagos had
made their beds in the tepee while the three girls from town were there,
both to solve the question of sleeping quarters and for the fun of the
thing. It was just like camping out to sleep on the ground, all the
eight girls in a circle around the little watch fire in the middle of
the tepee.
“Oh, I’ll be afraid to,” said Hinpoha.
“I don’t know but what it would be just as safe as sleeping in the
house,” said Nyoda. “I doubt if anyone would think of people sleeping
out in that thing. It’s a rather novel idea in this neighborhood. And at
any rate there’s nothing out there to steal and consequently nothing to
tempt a thief.”
So, their fears having vanished, the Winnebagos went to bed in the tepee
just as they had planned. Nyoda took the precaution of putting her
pistol under her pillow. The girls really enjoyed the air of suppressed
excitement. When did youth and high spirits ever fail to respond to the
thrill of danger, either real or fancied? This attempted burglary was
the most exciting thing that had ever happened to most of the girls and
they were getting as much thrill out of it as possible. It amused them
to see Tom and Calvin parading the front lawn armed with bird guns,
swelled up with importance at having to guard a houseful of women.
Instead of hoping that the burglar had been scared away for good they
wished fervently that he would return and give them a chance to shoot.
They would have stayed there all night if Mrs. Gardiner had not ordered
them to bed.
One by one the girls in the tepee dropped off to slumber, worn out with
the varied events of the day. But Nyoda could not sleep. She had a
throbbing headache from the glare of the sun on the water while she sat
fishing. The little fire, in the center of the bare circle of earth
which prevented it from spreading, died down and subsided to glowing
embers, then one by one these turned black and left the tepee in
darkness. There was not a spark left. Nyoda was sure of this, for she
sat up several times in an effort to make herself comfortable, and when
she took a drink from the pail of well water which stood nearby she
emptied the dipper over the spot where the fire had been, to make doubly
sure. Still sleep would not come. She stared out of the doorway of the
tepee into the darkness. A group of beech trees with their light grey
bark loomed up ghostlike before the door. She began to think of the
ghost which had appeared to her that other night in that very doorway,
and tried to connect the incidents which had taken place afterwards with
that. One thing was sure—someone was getting into Onoway House every few
days. Why nothing was taken was a mystery to her. It seemed to her now
that it was not so much an attempt at burglary as an effort to annoy and
frighten the family. Possibly it was someone who had a grudge against
them—she could not imagine why—and was indulging in these pranks to
satisfy a spite. She thought she saw a glimmer of light on the subject.
Farmer Landsdowne had once told her that when it became known that Mr.
Mitchell was going to give up the care of the place, several farmers of
the Centerville Road district had applied for the position of caretaker,
but wishing to assist Migwan, the Bartletts had refused their offers and
given the place over to the Winnebagos. That must be it. Someone wanted
that job badly and was wreaking his disappointment on the people who had
kept him from getting it. The more she thought of it the more probable
it seemed. Possibly more than one were involved in the plot.
Then another thought struck her. Could it be the crazy man who lived
alone in the little house among the trees? Calvin had stated that he
never left the house, but who could account for the inspirations of an
unbalanced mind? That nothing had been taken from the house seemed to
indicate a want of fixed purpose in the mind of the housebreaker—to go
to all that trouble for nothing. This idea also seemed worth
considering.
As she lay turning these things over in her mind she thought she heard a
stealthy footstep in the grass outside of the tepee. Thinking that the
ghost was coming to pay another visit, she drew the pistol from under
her pillow and turning over, face downward, lay with it pointed toward
the doorway. There would be no outcry when he appeared in the doorway.
The first intimation the ghost would have that he was observed would be
a shot in the leg that would prevent him from running away and would
solve the mystery. In tense silence she waited, one; two; three minutes,
but nothing appeared. Then suddenly she smelled smoke, and turning
around swiftly saw that the side of the tepee toward which she had had
her back was in flames.
“Fire!” she called at the top of her voice. “Sahwah! Hinpoha! Gladys!
Migwan! Wake up!” And seizing the pail of water she dashed it against
the side of the tepee. The water sizzled as it fell, but the canvas
covering was burning like tinder. Thus rudely awakened the girls sprang
up in alarm. The place was filling with dense smoke, and through it they
groped their way to the opening, dragging out their blankets. Hardly had
the last girl got out when the whole thing was one roaring blaze, which
lit up the scenery a long way around.
Nyoda, paying no attention to the flames that were mounting skyward from
the burning canvas, looked intently for a lurking figure among the
trees, for she thought it hardly possible that whoever had set the tepee
afire could have gotten outside of the range of light in that short
time. It was possible to see as far as the road on the one side and
across the river on the other. But nowhere was there a man or the shadow
of a man. The folks came running out of Onoway House half dressed and in
terror that the girls had not escaped from the burning tent in time, and
the farmers all the way down the road, seeing the glare, rushed to offer
their assistance, for a fire in the country is a serious thing where
there is no water pressure. Farmer Landsdowne came on a dead run,
carrying a water bucket. Even Abner Smalley appeared in the midst of the
crowd. He gave a scowling look at Calvin, but said nothing, and soon
took his departure when the danger was over, as it was directly, for it
did not take long to reduce that canvas covering to a black mass, and
buckets of water thrown all around on the ground and the trees kept the
fire from spreading.
For the second time that night the family gathered in the sitting-room
and faced each other over an exciting happening. “I told you if you
built a fire in that tepee you would burn it down,” said Mrs. Gardiner.
“I never felt easy when you had one.”
“But it didn’t catch fire from our little fire,” declared Nyoda, and
told the events of the night, from the going out of the fire to the
footsteps outside the tepee when the canvas had suddenly blazed up when
she was lying in wait for the ghost with a pistol. The circle of faces
paled with fear as she told her tale. Who could this mysterious visitor
be, who seemed determined to do them some harm? The girls finished the
night in the house, three in a bed, but none of them closed their eyes
to sleep.
CHAPTER XI.—THE WELL DIGGER’S GHOST.
The next morning Mrs. Gardiner sent Mr. Landsdowne to interview the
police force of the township in which the Centerville Road belonged, and
he brought the whole force back with him. He had to bring the whole
force if he brought any for it embraced only one man and he was well
along in years, but he had a uniform and a helmet and a club and a gun,
and presented an imposing appearance as he strutted up and down the
yard, before which an evil doer might be moved to pause. The three girls
from town had departed and Nakwisi had left her spy glass behind in the
excitement, and this was a source of great entertainment to the rural
gendarme. He spent a great deal of time sliding the lens back and forth
to fit his eye and peering up the road into the distance, or looking up
into the air, as if he expected to see the burglar approaching in an
airship. He was very talkative and fond of recounting the captures he
had made single handed, and declared solemnly that the man in this case
was as good as caught already, for no one had ever escaped yet when Dave
Beeman had started out to get him.
Nyoda, who was fond of seeing her theories worked out, still held to the
idea that the mysterious visitor was someone who wanted the job of
caretaker, and inquired closely of Farmer Landsdowne who the men were
who had applied for the position. When it came down to fact there was
only one who had really wanted the job very badly, although several
others had mentioned the fact that they wouldn’t mind doing it, and that
man had found a similar situation immediately afterward and left the
neighborhood. So her theory did not seem to be inclined to hold water.
She had another idea, however, and wrote to Mr. Mitchell, asking if he
had ever heard strange noises in the attic while he lived there. Mr.
Mitchell answered and said that not only had he heard strange noises in
the attic, but also in the cellar and in the barn, and that pieces of
furniture had apparently moved themselve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it was on this account that he had left the place, as it made his
wife so nervous she became ill. This fact put a new face on the matter.
The hostility, then, was not directed against themselves personally, but
against the tenants of the house, no matter who they were. But this idea
left them more in the dark than ever, and they lost a good deal of sleep
over it without reaching any solution.
After a few days of zealous watching, during which time nothing
happened, the police force of Centerville township gave it up as a bad
job and relaxed its vigilance, declaring that the firebug must have
gotten out of the country, for that was the only way he could hope to
escape his eagle eye. “If he was still in the country, I’d a’ had him by
this time”, Dave Beeman asserted confidently. “So as long as he’s gone
that far you don’t need to worry any more.” And he took himself off,
eager to get back to the quiet game of pinochle in Gus Wurlitzer’s
grocery store, which Farmer Landsdowne had interrupted several days ago.
It was just about this time that Migwan had her biggest order for canned
tomatoes—from a fashionable private sanitarium a few miles distant, and
the rush of canning gradually took their minds off the mysterious
intruder. Migwan, picking her finest and ripest tomatoes to fill this
order, noticed that a number of the vines were drooping and turning
yellow. The half ripe tomatoes were falling to the ground and rotting.
One whole end of the bed seemed to be affected. She looked carefully for
insects and found none. Some of the leaves seemed worse shrivelled than
others. In perplexity she called Mr. Landsdowne over to look at them. He
looked closely at the plants and also seemed puzzled as to the cause of
the mysterious blight. “It isn’t rot,” he said, “because the bed is high
and dry and the plants have never stood in water.” Upon looking closely
he discovered that the affected plants were covered with a fine white
coating. He gave a smothered exclamation. “Do you know what that is?” he
asked. “It’s lime! Somebody has sprayed your plants with a solution of
lime. Are you sure you didn’t do it yourself?” he asked, quizzically.
Migwan shook her head. “I haven’t sprayed those plants with anything for
a month,” she asserted, “and neither has anyone else in the house.”
“Somebody outside of the house has done it, then,” said Mr. Landsdowne.
The work of the mysterious visitor again! It struck dismay into the
breasts of the whole household. They never knew when and where that hand
was going to strike next. And so silently, so mysteriously, without ever
leaving a trace behind!
There was nothing left to do but dig up the dead plants and throw them
away. Migwan almost stopped breathing when she thought that the rest of
the bed might be treated in the same way, and the source of her revenue
cut off. But why was all this happening? What could anyone possibly have
against the peaceful dwellers at Onoway House?
A guard was set over the tomato bed both day and night for a week and
the big order for the sanitarium was filled as fast as the tomatoes
ripened. Nothing at all happened during this time and the vigilance was
relaxed. A large dog was turned loose in the garden at night and they
felt secure in his protection. This dog belonged to Calvin Smalley. When
he had left his uncle’s house he had to leave Pointer behind, as he did
not know what else to do with him, but now that the Gardiners were
willing to have him he went over and got him when he knew his uncle was
away from the house, so he would not have to meet him. Pointer was
overjoyed at seeing his young master again and attached himself to the
household at once, and never made the slightest effort to go back to his
old home. He had a deep, heavy bark which could not fail to rouse the
house at once. With the coming of Pointer the girls breathed easily
again.
One day when Migwan had gone over to see the Landsdownes, Mr. Landsdowne
had given her a treasure for her garden. This was a plant of a rare
species called Titania Gloria, which a friend had brought from Bermuda.
It was a first year growth and so would not bloom until the following
summer. Migwan planted it along the fence beside the mint bed and
treasured it like gold, for the blossom of the Titania Gloria was a
wonderful shade of blue and was considered a prize by fanciers, who paid
high prices for cuttings of the plant. In the excitement over the tepee
and the tomato plants, however, she forgot to tell the other girls about
it, so she was the only one who knew what a precious thing that little
bed of leaves was.
The weather was so fine that week that Migwan decided to have a garden
party and invite a number of friends from town. Gladys promised to dance
and the boys cleared a circle for her in the grass under the trees,
picking up every stick that lay on the ground. Mrs. Landsdowne, hearing
about the party, offered to make ice cream for them in her freezer. Just
before the guests arrived Migwan and Calvin went over after it. They
took the raft, because they thought that would be the easiest way of
transporting the heavy tub. Migwan rode on the raft and supported the
tub and Calvin walked along the bank and pulled the tow line. His
eagerness to help with the festivity was somewhat pathetic. Never, to
his knowledge, had there been a party at the Smalley House. The way
these girls planned a party out of a clear sky and carried out their
plans without delay was nothing short of marvelous to him. They were
always at their ease with company, while it was a fearful ordeal for him
to meet strangers. He liked to be a part of such doings; but was at a
loss how to act. Migwan, with her fine understanding of things beneath
the surface, saw that this boy was lonesome in the crowd, not knowing
how to mix in and have a glorious time on his own account, and she
always saw to it that his part was mapped out for him in all their
doings. Therefore she chose him to help her bring the ice cream over.
Calvin, happy at being useful, towed the raft carefully and turned his
head whenever Migwan spoke, so as to give strict attention to her words.
Doing this, he fell over the branch of a tree in the path and jerked the
rope violently. The raft tipped up and both Migwan and the tub of ice
cream went into the river. Migwan climbed out on the bank before Calvin
was up from the ground. He was aghast at what he had done. He had been
so eager to help with the party and now he had spoiled it! That he would
be instantly expelled from Onoway House he was sure, and he felt that he
deserved it. Migwan, at least, would never speak to him again.
Speechless, he turned piteous eyes to where she sat on the bank
dripping. To his surprise she was doubled up with laughter. “What are
you laughing at?” he asked, startled.
“Because you upset the raft and the ice cream fell into the river!”
giggled Migwan. Calvin gasped. The very thing that was nearly killing
him with chagrin was the cause of her mirth! It was the first time he
had ever seen anyone make light of a calamity. Her mirth was so
contagious that he began to laugh himself. Still laughing, he brought
the tub out of the river and set it on the bank. The water had washed
away the packing of ice, but the lid on the inner can was providentially
tight and the ice cream was unharmed. That little incident crystallized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After that he was Migwan’s slave. A girl
who could be thrown into the river without getting vexed was a friend
worth having. Dripping, they returned to the house, where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party were at their height, to be laughed at
immoderately and christened the “Water Babies.”
To Hinpoha the Artistic had been entrusted the setting of the tables.
Her decorations were water lilies from the river, and when she had
finished it looked as if a feast had been spread for the river nymphs.
Around the edges of the platter she put bunches of bright mint leaves.
Her artistic efforts called out so much praise from the guests that she
was in a continual state of blushing as she waited on the table.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r hand?” asked Migwan, noticing that she was
passing things around left handedly.
“Nothing,” said Hinpoha, “nothing much. I slipped when I was getting the
lilies and fell on my wrist and it feels lame, that’s all.”
“Is it sprained?” asked Migwan.
“Oh, no,” said Hinpoha, “I don’t think so.”
“It’s all swelled up,” said Migwan, holding up the injured wrist. “Let
me paint it with iodine and tie it up for you.”
Hinpoha maintained that it was nothing serious, but Migwan insisted.
“Where is the iodine, mother?” she asked.
“On the pantry shelf,” answered Mrs. Gardiner. Migwan got the bottle and
painted Hinpoha’s wrist before the party could proceed. Hinpoha surveyed
the brown stripe around her arm rather disgustedly. It was for this very
reason that she had said nothing about the wrist before. She did not
want it painted up for the party. It offended her artistic eye and she
would rather suffer in silence.
While the guests were sitting at the tables Gladys danced on the lawn
for their entertainment. The merry laughter was hushed in surprise and
delight at her fairylike movements. In the silence which reigned at this
time the thing which happened was distinctly heard by everyone.
Apparently from the depths of the earth there came a muffled thud, thud,
as of a pick striking against hard ground. It kept up for a few minutes
and then ceased, to be renewed again after a short interval. The
dwellers at Onoway House looked at each other. Into each mind there
sprang the story of the Deacon’s well, and the words of Farmer
Landsdowne, “_Superstitious folks say you can still hear the buried well
digger striking with his pick against the ground that covers him._” It
was the most mysterious sound, far away and faint, yet seemingly right
under their very feet. Gladys heard it and paused in her dancing.
Pointer and Mr. Bob both heard it and began to bark. In a little while
the thudding noise ceased and was heard no more, and the company were
all left wondering if they could have been the victims of imagination.
“Maybe it’s somebody down cellar,” said Calvin, and taking Pointer with
him, went down. Tom followed him. But there was no sign of anyone down
there. Pointer ran around with his nose to the ground as if he were
smelling for footsteps, but his tail kept wagging all the while. They
were all familiar footsteps he scented. Nothing was out of place in the
cellar except that a basket of potatoes was thrown over and the potatoes
had rolled out on the cement floor. The boys noticed this without
thinking anything of it. The mystery of the well digger’s ghost remained
unsolved.
In the cool of the early evening after her guests had departed, Migwan
wandered down into the garden to look at her various plants and flowers.
It occurred to her that she had not paid her Titania Gloria a visit for
several days. But what a sight met her eyes when she reached the spot
where the precious thing had been planted! Not a single bit was left.
The clean cut stalks showed where they had been clipped off close to the
ground. Migwan started up with a cry of dismay which brought the other
girls running to her side. “My Titania Gloria!” gasped Migwan. “Look!
The mysterious visitor has been at work again!” And she told them about
the valuable cuttings that had disappeared so uncannily.
“We never hear that ghost but what something happens after it!” said
Gladys, in an awestruck tone. The girls peered apprehensively into the
shadows of the tall trees surrounding the garden.
“What’s up?” asked Hinpoha, joining the group. Migwan pointed to the
devastated bed. “What’s the matter with it?” asked Hinpoha.
“My Titania Gloria!” said Migwan. “It’s been clipped off at the roots.”
“Your what?” asked Hinpoha. Migwan explained about the rare plant Farmer
Landsdowne had given her. Hinpoha gave a sudden start and exclamation.
“What did you say it was?” she asked.
“A Titania Gloria,” answered Migwan.
“Well, girls, I’m the guilty one, then,” said Hinpoha, “for I cut those
plants off thinking they were mint. That was what I decorated the
platters with this afternoon. Do anything you like with me, Migwan, beat
me, hang me to a tree, put my feet in stocks, or anything, and I’ll make
no resistance.” She was absolutely frozen to the spot when she realized
what she had done.
Migwan, grieved as she was over the loss of her cherished Titania, yet
had to laugh at the depths of Hinpoha’s mortification. “You old goose!”
she said, putting her arms around her, “don’t take it so to heart! It’s
my fault, not yours at all, because I didn’t tell anyone what that plant
was. And the leaves do look just like mint.” Thus she comforted the
discomfited Hinpoha.
“Migwan,” said her mother, when they had returned to the house, “where
did you get that iodine with which you painted Hinpoha’s wrist this
afternoon?”
“On the pantry shelf, just where you told me,” answered Migwan.
“Well,” said her mother, “I told you wrong. The iodine is up on my
wash-stand.”
“Then what was in the brown bottle on the pantry shelf?” asked Migwan.
The bottle was produced.
“Why,” said Mrs. Gardiner, “that’s walnut stain, guaranteed not to wear
off!”
Then there was a laugh at Migwan’s expense!
“Old Migwan Hubbard
She went to the cupboard,
To get iodine in a phial,
But she couldn’t read plain,
And brought walnut stain,
And now her poor patient looks vile!”
chanted Sahwah.
“You’re even now,” said Gladys, “you’ve each scored a trick.”
“‘_We do this to each other!_’” said Migwan and Hinpoha in the same
breath, and locked fingers and made a wish according to the time-honored
custom.
CHAPTER XII.—OPHELIA FINDS A FAIRY GODMOTHER.
As the summer progressed, the girls had more than one conference as to
what was to become of Ophelia when they left Onoway House. To let her go
back to her life in the slums was unthinkable. So far, Old Grady had
made no effort to get her back, possibly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she
did not know where the child was. They did not even know whether or not
she had a legal claim on Ophelia. All Ophelia knew about the business
was that Old Grady had taken her from the orphan asylum when she was
seven years old. Where she had lived before she went to the orphan
asylum she could not remember, so she must have been very young when she
came there. They were equally unwilling that she should return to the
asylum.
“If we could only find someone to adopt her,” said Hinpoha. That would
be the best thing, they all agreed, although there was a lingering doubt
in the mind of each one as to whether anyone would want to adopt
Ophelia. Grammar was to her a totally unnecessary accomplishment, and
the amount of slang she knew was unending. By dint of hard labor they
had succeeded in making her say “you” instead of “yer,” and “to” instead
of “ter,” and discard some of her more violent slang phrases, but she
was still obviously a child of the streets and the tenement, and that
life had left its brand upon her. It showed itself constantly in her
speech. They had better success in teaching her table manners, for with
a child’s gift of imitation she soon fell into the ways of those around
her.
But having had so much excitement in her short life she still pined for
it. While the life in the country was pleasant in the extreme it was far
too quiet to suit her and she longed to be back in the crowded tenement
where there was something happening every hour out of the twenty-four;
where people woke to life instead of going to bed when darkness fell and
the lamps were lighted; where street cars clanged and wagons rattled and
fire engines rumbled by; where the harsh voices of newsboys rang out
above the loud conversation of the women on the doorsteps and the
wailing of the babies. The zigging of the grasshoppers and the swishing
of the wind in the Balm of Gilead tree and the murmur of the river had
for her a mournful and desolate sound, and she often covered up her ears
so as not to hear it. When she first came to Onoway House she was so
interested in the new life that it kept her busy all day long finding
out new things; but gradually the novelty wore off. At first she had
been as mischievous as a monkey; always up to some prank or other. She
teased Tom and was teased by him in return; she put burrs in Mr. Bob’s
long ears; she climbed trees and threw things down on the heads of
unsuspecting persons underneath; she startled the girls out of their
wits by lying unseen under the couch in the sitting-room and grabbing
their ankles unexpectedly. Always she was doing something, and always
merry and full of life; so that she made the girls feel that they had
done a fine thing by bringing her to Onoway House.
But of late a change had come over her. She began to droop, and to sit
silent by herself at times. The girls did their best to keep her amused,
but they were very busy with the continual canning, and Betty, who had
more time than the others, did not like her and would not play with her.
So she grew more and more homesick for the big, noisy city and the
playmates of other days. Then had come the time when she was so
sunburned and she had developed the fondness for Sahwah. After that she
was less lonesome, for Sahwah was such a lively person to be attached to
that one had always to be on the lookout for surprises. Sahwah taught
her to swim and dive and ride a bicycle; she had the boys make a swing
for her under the big tree, and Ophelia blossomed once more into
happiness. At Sahwah’s instigation she played more tricks on the other
girls than before.
But Ophelia was a shrewd little person, and she knew that the summer
would come to a close and the girls would not live together any more.
She often heard them discussing their plans. What was to become of her
then? The happy family life at Onoway House stirred in her a desire to
have a home too, and a mother of her own. She began to grow wistful
again and at times her eyes would have a strange far-away look. The
scandals of the streets which were once the breath of life to her and
which she repeated with such relish, began to lose their charm, and she
developed a taste for fairy tales. “Tell me the story about the fairy
godmother,” she would say to Sahwah, and would listen attentively to the
end. “Are you sure I’ve got one somewhere?” she would ask eagerly.
“You surely have,” Sahwah would answer, to satisfy her.
And then, “What _are_ we going to do with Ophelia when the summer is
over?” Sahwah would ask the girls after Ophelia was in bed. And Hinpoha
would think of Aunt Phœbe and knew she would never adopt such a child as
Ophelia was; and Migwan knew that it would be out of the question in her
family; and Sahwah knew that her mother would not let her come and live
with them; and Gladys thought of her delicate mother and sighed. Nyoda
could not make a home for her, because she had none of her own and a
boarding house was no place for a child.
“It’s a shame,” Sahwah would declare vehemently, “that there aren’t
fathers and mothers enough in this world to go round. Here’s Ophelia
will have to go into an institution more than likely, and grow up
without any especial interest being taken in her, while we have had so
much done for us. It isn’t fair.”
“There’s something curious about Ophelia,” said Gladys, musingly. “While
she came from the tenements and is as wild and untrained as any little
street gamin, she has the appearance of a child of a much higher class.
Have you ever noticed how small and perfect her hands and feet are? And
what beautiful almond shaped fingernails she has? And what delicate
features? Have you seen how erectly she carries herself, and how
graceful she is when she dances? In spite of her name, I don’t believe
she is Irish; and I don’t think her people could have been low class.
There’s an indefinable something about her which spells quality.”
“Probably a princess in disguise,” said Sahwah, in a tone of amusement.
“Leave it to Gladys to scent ‘quality.’”
But the others had noticed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in Ophelia and were
inclined to agree with Gladys on the subject.
“But what about the strange spot of light hair on her head?” asked
Sahwah. “Would you call that a mark of quality?” But to this there was
no answer. They had never seen or heard of anything like it before. Thus
the summer days slipped by and Onoway House continued to shelter two
homeless orphans, neither of whom knew what the future held in store for
them.
One afternoon when the girls had planned to go for a long walk to the
woods Gladys read in the paper that a balloonist was to make an
ascension over the lake. For some unaccountable reason she took a fancy
that she would like to see the performance. “Oh, Gladys,” said Sahwah,
impatiently, “you’ve seen balloonists before and you’ll see plenty yet;
come with us this afternoon.” But Gladys held out, even while she
wondered to herself why she was so eager to see this not uncommon sight.
Half offended at her, the other girls departed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woods. Gladys climbed high up in the Balm of Gilead tree, from which she
could look over the country for miles around and easily see the lake and
the distant amusement park from which the balloonist was to ascend.
The newspaper said three o’clock, but evidently the performance was
delayed, for although Gladys was on the lookout since before that time
nothing seemed to be happening. To aid her in seeing she took Nakwisi’s
spy glass up into the tree with her, and while she was waiting for the
parachute spectacle she amused herself by focusing the glass on far away
objects on the land and bringing them right before her eyes, as it
seemed. She could look right into the back door of a distant farm house
and see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doorway and chickens walking up and down
the steps; she could see the men working in the fields; she could see
the yachts out on the lake and the smoky trail of a freight steamer.
Somewhere in the middle of her range of vision were the gleaming rails
of the car tracks. She looked at them idly; they were like long streaks
of light in the sun. She saw two men, evidently tramps, come out of the
bushes along the road and bend over the rails. Somewhere along that
stretch of track there was a derailing switch and it seemed to Gladys
that it was at this point where the men were. Gladys looked at the pair,
suspiciously, for a second and then decided they were track testers. One
had an iron bar in his hand and he seemed to be turning the switch.
Suddenly the other man pointed up the road and then the two jumped
quickly backward into the bushes. Gladys looked in the direction the man
had pointed. Far off down the track she could see the red body of the
“Limited” approaching at a tremendous rate. The stretch of country past
the Centerville Road was flat and even; the track was perfect and there
was no traffic to block the way, and the cars made great speed along
here. Something told Gladys that the men had had no business at the
switch; that they meant to derail and wreck the Limited. Gladys had
learned to think and act quickly since she had become a Camp Fire Girl,
and scarcely had the idea entered her head that the Limited was in
danger, than she conceived the plan of heading it off. Before the car
reached the switch it must pass the Centerville Road. Being the Limited,
it did not stop there. So Gladys planned to run the automobile down the
Centerville Road and flag the car. She flung herself from the tree in
haste, got the machine out of the barn and started down the road with
wide-open throttle.
Trees and fences whirled dizzily by, obscured in the cloud of dust she
was raising. Across the stillness of the fields she could hear the
Limited pounding down the track. A hundred yards from the end of the
road the automobile engine snorted, choked and went dead. Without
waiting to investigate the trouble, Gladys jumped out and proceeded on
foot. Could she make it? She could see the red monster through the
trees, rushing along to certain destruction. With an inward prayer for
the speed of Antelope Boy, the Indian runner, she darted forward like an
arrow from the bow. Breathless and spent she came out on the car track
just a moment ahead of the thundering car, and waved the scarlet
Winnebago banner, which she had snatched from the wall on the way out.
With a quick jamming of the emergency brakes that shook the car from end
to end it came to a standstill just beyond the Centerville Road, and
only fifty feet from the switch.
“What’s the matter?” asked the motorman, coming out.
“Look at the switch!” panted Gladys, sinking down beside the road,
unable to say more.
The motorman looked at the switch. “My God,” he said, mopping his
forehead, “if we’d ever run into that thing going at such a rate there
wouldn’t have been anyone left to tell the tale.”
The passengers were pouring from the car, eager to find out the reason
for the sudden stoppage. “What’s the matter?” was heard on every side.
“You’ve got that girl to thank,” said the motorman, moving back toward
his vestibule, “that you’re not lying in a heap of kindling wood.”
Gladys, much abashed and still hardly able to breathe, laid her head on
her knee and sobbed from sheer nervousness and relief.
“Gladys!” suddenly said a voice above the murmurings of the throng of
passengers.
Gladys raised her head. “Papa!” she cried, staggering to her feet. “Were
you on that car?”
Another figure detached itself from the crowd and hastened forward.
“Mother!” cried Gladys. “Oh, if I hadn’t been able to stop it—” and at
the horror of the idea her strength deserted her and she slipped quietly
to the ground at her parents’ feet.
When she came to the car had gone on and she was lying in the grass by
the roadside with her head in her mother’s lap. “Cheer up, you’re all
right,” said her mother a little unsteadily, smiling down at her. Gladys
now became aware of two other figures that were standing in the road.
“Aunt Beatrice!” she cried. “And Uncle Lyn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e all came out to surprise you,” said her father. “We got back from
the West last night; sooner than we expected, and decided we would run
out without any warning and see what kind of farmers you were. The
automobile is being overhauled so we came on the interurban. We didn’t
know it didn’t stop at your road.”
Then, Gladys suddenly remembered her own disabled car standing in the
road, and they all moved toward it. With a little tinkering it
condescended to run and they were soon at Onoway House, telling the
exciting tale to Mrs. Gardiner, who held up her hands in horror at the
thought of the fate which the newcomers had so narrowly escaped. Aunt
Beatrice, not being strong, was much agitated, and developed a
palpitation of the heart, and had to lie in the hammock on the porch and
be doctored, so Gladys had her hands full until the girls came back.
They were much surprised at the houseful of company and very glad to see
Mr. and Mrs. Evans, who were very good friends of the Winnebagos indeed.
They looked with interest when Aunt Beatrice was introduced, for they
all remembered the tragic story Gladys had told them about the loss of
her baby in the hotel fire. Aunt Beatrice felt well enough to get up
then and acknowledge the introductions with a sweet but infinitely sad
smile that went straight to their hearts, and brought tears to the eyes
of the soft-hearted Hinpoha.
Ophelia came in last, having loitered on the lawn to play with Pointer
and Mr. Bob. She had taken off her hat and was swinging it around in her
hand when she came up on the porch. “And this is the little sister of
the Winnebagos,” said Nyoda, drawing her forward. Aunt Beatrice looked
down at the dust-streaked little face, with her sad smile, but her eyes
rested there only an instant. She was gazing as if fascinated at the
strange ring of light hair on her head. She became very pale and her
eyes widened until they seemed to be the biggest part of her face.
“Lynn!” she gasped in a choking voice, “Lynn! Look!” and she sank on the
floor unconscious. “It can’t be! It can’t be!” she kept saying faintly
when they revived her. “Beatrice died in the fire. But Beatrice had that
ring of light hair on her head! It can’t be! But there never were two
such birthmarks!”
What a hubbub arose when this startling possibility was uttered!
Ophelia, the lost Beatrice? Could it possibly be true? Uncle Lynn lost
no time in finding out. Taking Ophelia with him he hunted up Old Grady.
She knew nothing more save that she had gotten her from an orphan
asylum, which she named. At the asylum he learned what he wanted to
know. The superintendent remembered about Ophelia on account of the
strange ring of light hair. The child had been brought to the
institution when she was about a year old. There was a babies’
dispensar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lace, and into this a weak, haggard
girl of about eighteen had staggered one day carrying a baby. The baby
was sick and she begged them to make it well. While she sat waiting for
the nurse to look at the baby the girl collapsed. She died in a charity
hospital a few days later. On her death-bed she confessed that she had
run away from a large hotel with the baby which had been left in her
care, intending to hide it and get money from the parents for its
recovery. But she feared this would lead her into trouble and left town
with the child and never troubled the parents as she had intended, and
kept the baby with her until it fell sick, when she had become
frightened and sought the dispensary. She apparently never knew that the
hotel had burned and covered up the traces of her flight. The baby was
kept at the orphan asylum and named Ophelia. Her last name had never
been known. Thence Old Grady had adopted her, but her right could be
taken away from her as it was clear that she was no fit person to have
the child.
“It’s just like a fairy tale!” said Hinpoha, when it was established
beyond a doubt that the abused street waif Gladys had brought home in
the goodness of her heart was her own cousin.
“Didn’t I tell you you’d find your fairy godmother if you only waited
long enough?” said Sahwah. And Ophelia, from the depths of her mother’s
arms, nodded rapturously.
CHAPTER XIII.—A GAME OF HIDE-AND-SEEK.
“Oh, Gladys, do you have to go home, now that your mother and father are
back?” asked Migwan, anxiously.
“Not unless you want to, Gladys,” said Mrs. Evans. “If you would rather
stay out here until school opens, you may. Father and I are going to
Boston in a few days, you know.”
So there was no breaking up of the group before they all went home, with
the exception of Ophelia, or rather Beatrice, as we will have to call
her from now on, for, of course, she was to go with her mother.
“What must it be like, anyway,” said Hinpoha, “not to have any last name
until you’re nine years old and then be introduced to yourself? To
answer to the name of Ophelia one and ‘Miss Beatrice Palmer’ the next?
It must be rather confusing.”
Little Beatrice went to Boston with her mother and father and uncle and
aunt and Onoway House missed her rather sorely. Calvin Smalley also got
a measure of happiness out of the restoration of the lost child, for
Uncle Lynn was so beside himself with joy over the event that he was
ready to bestow favors on anyone connected with Onoway House, and
promised to see that Calvin got through school and college. He would
give him a place to work in his office Saturdays and vacations.
For several days now there had been no sign of the mysterious visitor,
and the well digger’s ghost had also apparently been laid to rest. Then
one morning they woke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unseen agency had been
at work again. Pinned on the front door was a piece of paper on which
was scrawled,
“_If you folks know what’s good for you you’ll get out of that
house._”
“We’ll do no such thing!” said Migwan, with unexpected spirit “I’ve
started out to earn money to go to college by canning tomatoes, and I’m
going to stay here until they’re canned; I don’t care who likes it or
doesn’t.”
“That’s it, stand up for your rights,” applauded Sahwah.
“But what possible motive could anyone have for wanting us to get out of
the house?” asked Migwan. Of course, there was no answer to this.
“Do you suppose the house will be burned down as the tepee was?” asked
Gladys, in rather a scared voice. This suggestion sent a shiver through
them all.
“We must get the policeman back again to watch,” said Mrs. Gardiner.
Accordingly, the redoubtable constable was brought on the scene again.
“Well, well, well,” he said, fingering the mysterious note. “Thought
he’d come back again now that the coast was clear, did he? You notice,
though, that he didn’t make no effort while I was here. You can bet your
life he won’t get busy again while I’m here now. You ladies just rest
easy and go on with your peeling.”
Scarcely had he finished speaking, when from the bowels of the earth and
apparently under his very feet, there came the strange sound as of blows
being struck on hard earth or stone. The expression on Dave Beeman’s
face was such a mixture of surprise and alarm that the girls could not
keep from laughing, disturbed as they were at the return of the sounds.
“By gum,” said the constable, looking furtively around, “this is
certainly a queer business.” He had heard the story of the well digger’s
ghost and it was very strong in his mind just now. “Maybe it’s just as
well not to meddle,” he said under his breath.
Off and on through the day they heard the same sounds issuing from the
ground, and at dusk the weird moaning began again. The constable showed
strong signs of wishing himself elsewhere. When darkness fell the noises
ceased and were heard no more that night. But another sort of moaning
had taken its place. This was the wind, which had been blowing strongly
all day, and early in the evening increased to the proportions of a
hurricane. With wise forethought Sahwah and Nyoda brought the raft and
the rowboat up on land. Leaves, small twigs and thick dust filled the
air. Windows rattled ominously; doors slammed with jarring crashes.
Migwan, foreseeing a devastating storm, set all the girls to picking
tomatoes as fast as they could, whether they were ripe or not, to save
them from being dashed to the ground. They could ripen off the vines
later.
At last the sandstorm drove them into the house, blinded. Then there
came such a wind as none of them had ever experienced. Trees in the yard
broke like matches; the Balm of Gilead roared like an ocean in a
tempest. There was a constant rattle of pebbles and small objects
against the window panes; then one of the windows in the dining-room was
broken by a branch being hurled against it, and let in a miniature
tempest. Papers blew around the room in great confusion. Migwan rolled
the high topped sideboard in front of the broken pane to keep the wind
out of the room. At times it seemed as if the very house must be coming
down on top of their heads, and they stood with frightened faces in the
front hall ready to dash out at a moment’s notice. A crash sounded on
the roof and they thought the time had come, but in a moment they
realized that it was only the chimney falling over. The bricks went
sliding and bumping down the slope of the roof and fell to the ground
over the edge.
“I pity anybody who’s caught in this out in the open,” said Migwan. “I
believe the wind is strong enough to blow a horse over. I wonder where
Calvin is now.” Calvin had gone to the city with Farmer Landsdowne on
business and intended to remain all night.
“He’s probably all right if he has reached those friends of the
Landsdownes’,” said Hinpoha.
“The Smalleys are out, too,” said Sahwah. “I saw them drive past after
dark, going toward town, just before it began to blow so terribly. Oh,
listen! What do you suppose that was?” A crash in the yard told them
that something had happened to the barn. Gladys was in great distress
about the car, and had to be restrained forcibly from running out to see
if it was all right. The wind continue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night
and nobody thought of going to bed. By morning it had spent its force.
Then they looked out on a scene of destruction. The garden was piled
with branches and trunks of trees, and strewn with clothes that had been
hanging on wash-lines somewhere along the road. Up against the porch lay
a wicker chair which they recognized as belonging to a house some
distance away. Everywhere around they could see the corn and wheat lying
flat on the ground, as if trodden by some giant foot. The roof of the
barn had been torn off on one side and reposed on the ground, more or
less shattered. The car was uninjured except that it was covered with a
thick coating of yellow dust. It was well that they had thought to pick
the tomatoes, for the vines and the frames which supported them were
demolished. All the telephone wires were down as far as they could see.
Calvin was not to return until night, and they felt no great anxiety
about him, but often during the day a disquieting thought came to
Migwan. This was about Uncle Peter, the man who lived in the cottage
among the trees. Suppose something had happened to him? From Sahwah’s
report, the house was very old and frail. She watched the Red House
closely for signs of life, but apparently the Smalleys had not returned.
The doors were shut and there was no smoke coming out of the kitchen
chimney.
“Nyoda,” said Migwan, finally, “I’m going over and see if that old man
is all right. I can’t rest until I know.”
“All right,” said Nyoda, “I’m going with you.” Sahwah was over at Mrs.
Landsdowne’s, but they remembered her description of the approach to the
cottage, and made the detour around the field where the bull was and the
marsh beyond it, coming up to the cottage from the other side. It was
still standing, although the big tree beside it had been blown over and
lay across the roof.
“Would you ever think,” said Migwan, “that there was anyone living in
there? I could pass it a dozen times and swear it was empty, if I didn’t
know about it.”
“Well,” said Nyoda, the house is still standing, “so I suppose the old
man is all right.”
“I wonder,” said Migwan. “He may have been frightened sick, and he may
have nothing to eat or drink, now that the Smalleys are kept away. We’d
better have a look. He can’t hurt us. If Sahwah spent the whole
afternoon with him we needn’t be afraid.”
They tried the door, but, of course, found it locked, and were obliged
to resort to the same means of entrance as Sahwah had employed. They saw
the key in the other door just as Sahwah had and turned it and opened
the door. The old man was sitting by the table in just the position
Sahwah had described. Apparently he was neither frightened nor hurt. He
looked up when he saw them in the doorway and motioned them to come in.
There was nothing extraordinary in his appearance; he was simply an old
man with mild blue eyes. Obeying the same impulse of adventure which had
led Sahwah across the threshold, they stepped in and sat down. The room
was just as Sahwah had told them. The table was littered with wheels and
rods which the old man was fitting together. As they expected, he worked
away without taking any notice of them.
“Did you mind the storm?” asked Nyoda.
“Storm?” said the old man. “What storm?”
“He never noticed it!” said Migwan, in an aside to Nyoda.
“What are you making?” asked Migwan, wishing to hear from his own lips
the explanation he had given Sahwah.
After his customary interval he spoke. “It’s a machine that reclaims
wasted moments,” he explained. “Every moment that isn’t made good use of
goes down through this little trap door, and when there are enough to
make an hour they join hands and climb up on the face of the clock
again.”
Migwan and Nyoda exchanged glances. The ingenious imagination of the old
man surpassed anything they had ever heard. They stayed awhile, amusing
themselves by looking at the books and clocks in the cabinets, and then
rose, intending to slip away quietly when he was absorbed in his work,
as Sahwah had done. A dish of apples standing on one of the cabinets
indicated that he was not without food and their minds were now at rest
about his welfare. But when they moved toward the door he turned and
looked at them.
“What do you think of it?” he asked.
By “it” they figured that he meant the machine he was working on. “It’s
a very good one indeed,” said Nyoda, “very interesting.”
“Do you want to buy the rights?” asked the old man, taking off his hat
and putting it on again.
“He thinks he’s talking to some capitalist!” whispered Migwan.
“We’ll talk over the plans first among ourselves and let you know our
decision,” said Nyoda, not knowing what to say and wishing to appear
politely interested. This speech would give them an opportunity to get
away. But to her surprise Uncle Peter drew a sheet of paper from among
those on the table and gravely handed it to her.
“Here are the plans,” he said. “Take them and look them over and let me
know in a week.” Then he fell to work and forgot their presence. Holding
the paper in her hands Nyoda walked out of the room, followed by Migwan.
They left the house as they had entered it and returned by a roundabout
way to Onoway House. Nyoda put the plans of the remarkable machine away
in her room, intending to keep it as a curiosity. Soon afterward they
saw the Smalleys driving into the yard of the Red House.
The weepers continued their weeping in the second syllable, and then
Gladys appeared, felt of all their pulses and gave each a dose out of a
bottle, whereupon they all straightened up, lost their symptoms of
distress, and capered for joy.
“Cure,” said Migwan. The players shook their heads.
“Heal,” shouted Hinpoha, and Gladys acknowledged it.
In the last syllable Gladys went around and demanded payment for her
services, but in each case was met with a promise to pay at some future
time.
“Owe,” said Chapa, which was pronounced right. “O heal woe, what’s
that?” she asked.
“You’re twisted,” said Nyoda, “it’s ‘Wohelo.’ That really was too easy.
Let’s not divide them into syllables after this,” she suggested, “it’s
no contest of wits that way. Let’s act out the word all at once.” The
alteration was accepted with enthusiasm.
Hinpoha came out alone for her side. “Word of two syllables,” she said.
Taking a blanket she spread it over a bushy weed and tucked the corners
under until it looked not unlike a large stone. Then she retired from
the scene. Soon Nyoda came along and paused in front of the blanket,
which looked like an inviting seat.
“What a lovely rock to rest on!” she exclaimed, and seated herself upon
it. Of course, it flattened down under her weight and she was borne down
to the ground.
A moment of silence followed this performance as the guessers racked
their brains for the meaning. “Is it ‘Landsdowne?’” asked Gladys.
“It might be, but it isn’t,” said Nyoda, laughing.
“I know,” said Sahwah, starting up, “it’s ‘shamrock.’”
“You are sharper than I thought,” said Nyoda, rising from her seat.
“Nobody down yet. Now, fire your broadside at us. No word under three
syllables. Anything less would be unworthy of our giant intellects.”
“Third round!” cried Calvin.
Sahwah walked down to the water’s edge, holding in her hand a large key.
Leaning over, she moved the key as if it were walking in the water. This
proved a puzzler, and cries of ‘Milwaukee,’ ‘Nebrasky,’ and ‘turnkey’
were all met with a triumphant shake of the head.
“It looks as if we would have to give up,” said Hinpoha.
Just then Nyoda sprang up with a shout. “Why didn’t I think of it
before?” she cried. “It’s ‘Keewaydin,’ key-wade-in. What else could you
expect from Sahwah?”
“That’s it,” said Sahwah. “You must be a mind reader.”
“Here’s where we finish you off,” said Nyoda, as her side came out
again. “We’ve taken a word of four syllables this time.” The whole team
advanced in single file, Indian fashion, keeping closely in step. Round
and round they marched, back and forth, never slackening their speed,
until one by one they tumbled to the ground from sheer exha
Gladys appeared, felt of all their pulses and gave each a dose out of a
bottle, whereupon they all straightened up, lost their symptoms of
distress, and capered for joy.
“Cure,” said Migwan. The players shook their heads.
“Heal,” shouted Hinpoha, and Gladys acknowledged it.
In the last syllable Gladys went around and demanded payment for her
services, but in each case was met with a promise to pay at some future
time.
“Owe,” said Chapa, which was pronounced right. “O heal woe, what’s
that?” she asked.
“You’re twisted,” said Nyoda, “it’s ‘Wohelo.’ That really was too easy.
Let’s not divide them into syllables after this,” she suggested, “it’s
no contest of wits that way. Let’s act out the word all at once.” The
alteration was accepted with enthusiasm.
Hinpoha came out alone for her side. “Word of two syllables,” she said.
Taking a blanket she spread it over a bushy weed and tucked the corners
under until it looked not unlike a large stone. Then she retired from
the scene. Soon Nyoda came along and paused in front of the blanket,
which looked like an inviting seat.
“What a lovely rock to rest on!” she exclaimed, and seated herself upon
it. Of course, it flattened down under her weight and she was borne down
to the ground.
A moment of silence followed this performance as the guessers racked
their brains for the meaning. “Is it ‘Landsdowne?’” asked Gladys.
“It might be, but it isn’t,” said Nyoda, laughing.
“I know,” said Sahwah, starting up, “it’s ‘shamrock.’”
“You are sharper than I thought,” said Nyoda, rising from her seat.
“Nobody down yet. Now, fire your broadside at us. No word under three
syllables. Anything less would be unworthy of our giant intellects.”
“Third round!” cried Calvin.
Sahwah walked down to the water’s edge, holding in her hand a large key.
Leaning over, she moved the key as if it were walking in the water. This
proved a puzzler, and cries of ‘Milwaukee,’ ‘Nebrasky,’ and ‘turnkey’
were all met with a triumphant shake of the head.
“It looks as if we would have to give up,” said Hinpoha.
Just then Nyoda sprang up with a shout. “Why didn’t I think of it
before?” she cried. “It’s ‘Keewaydin,’ key-wade-in. What else could you
expect from Sahwah?”
“That’s it,” said Sahwah. “You must be a mind reader.”
“Here’s where we finish you off,” said Nyoda, as her side came out
again. “We’ve taken a word of four syllables this time.” The whole team
advanced in single file, Indian fashion, keeping closely in step. Round
and round they marched, back and forth, never slackening their speed,
until one by one they tumbled to the ground from sheer exhaustion and
stiffened out lifelessly. The guessers looked at each other, puzzled.
“Do it again,” said Sahwah. The strenuous march was repeated, and the
marchers succumbed as before. Still no light came to the onlookers.
Sahwah whispered something to Gladys.
“Would you just as soon do it again?” asked Gladys. Again the file wound
round the trees and tumbled to the turf. Nyoda made a triumphant grimace
as no guess was forthcoming. Sahwah’s eyes began to sparkle.
“Would you please do it once more?” she pleaded.
“Have mercy on the performers,” groaned Nyoda, but they went through it
again, and this time they were too spent to rise from the ground when
the acting was done. “Do you give up?” called Nyoda.
“No,” answered Gladys.
“You have five seconds to produce the answer, then,” said Nyoda.
“It’s diapason,” said Gladys, “die-a-pacin.”
“Really!” said Nyoda, falling back in astonishment.
“We knew it all the while!” cried Sahwah and Gladys. “We just kept you
doing it over and over again because we liked to see you work.”
The laugh was on Nyoda and her team all the way around. “We do this to
each other!” called Sahwah, using the Indian form of taunt when one has
played a successful trick on another.
“Tie the villains to a tree, and let them perish of mosquito bites,”
Nyoda commanded in an awful tone. “I’ll get even with you for that, Miss
Sahwah,” she said, darkly, as the other side trooped off to cook up a
new poser.
“Hadn’t you better stop playing now?” inquired Mrs. Gardiner. “You know
we wanted to get home before dark.”
“Oh, let’s do one more,” pleaded Migwan. If they had only stopped
playing when Mrs. Gardiner suggested it and gone home early they might
have been in time to prevent the thing which occurred, but they were
bent on seeing one side or the other go down, and Gladys’s side prepared
another charade.
“We’ve played up to your own game,” said Gladys, who was introducing the
new charade, “and have increased the number to five syllables.” The
actors were Mrs. Gardiner, Betty and Tom Gardiner. Mrs. Gardiner was
scolding the children and emphasized her remarks by a sharp pinch on
Tom’s arm. Betty, seeing the maternal hand also extended in her
direction, promptly climbed a tree and sat in safety, while her mother
shook her finger at her and cried warningly, “I’ll attend to you after
awhile.”
“What on earth?” said Nyoda, scratching her head in perplexity. But
scratch as she might, no answer came, and the rest of her team had
nothing to offer either. After holding out for fully fifteen minutes
they were compelled to give it up.
“It’s ‘manipulator,’” cried the winning side, in chorus.
“‘Ma-nip-you-later!’” And they stood around to condole while Nyoda’s
side prepared supper. Then it was that Calvin, basely deserting the team
he had helped so far, went over to the side of the enemy and helped
Migwan fetch wood for the fire. Both sides stopped often to jeer at each
other, so it took them twice as long to get the meal ready as it would
have ordinarily. They loitered and sang along the way home, letting the
horses take their time, and it was quite late when they reached Onoway
House.
The first thing that greeted them was the sight of Mr. Bob, the cocker
spaniel, rolling on the front lawn in great distress, and giving every
sign of being poisoned. They hastily administered an antidote and, after
a time of suspense were confident that the effect of the poison had been
counteracted. So far they had only been in the kitchen, but when the
excitement about the dog was over they moved toward the sitting-room to
rest awhile and drink lemonade before going to bed. When the light was
lit they all stopped in astonishment. In the sitting-room there was an
old-fashioned combination desk and bookcase, the bookcase part set on
top of the desk and reaching nearly to the ceiling. It belonged to the
house, and the desk was closed and locked. Now, however, it stood open,
and all the drawers were pulled out, while the top of the desk and the
floor before it were strewn with papers in great disorder.
“Burglars!” cried Migwan. “The house has been robbed!” They immediately
looked through the house to see what had been taken. Up-stairs in the
room occupied by the two boys there was a desk similar to the one in the
sitting-room. This had also been broken open and the drawers searched
through, although the disorder of papers was not so great as it was
down-stairs. Half afraid of what they should find, the whole family went
from room to room, but nothing else seemed to have been disturbed, and
as far as they could see nothing had been stolen. The silver in the
sideboard drawer was untouched, but then, this was only plate, and worn
at that. But in full view on the dining-room table lay Sahwah’s
Firemaker Bracelet, which she had laid there a few moments before
starting for the picnic, and then, with her customary forgetfulness,
neglected to pick up again. This was solid silver and worth stealing.
Further than that, she had also forgotten to wear her watch, and it was
still safe in her top bureau drawer. It was a riddle, and as they talked
it over they could only come to one conclusion, and that was that the
burglar had thought there were large sums of money hidden in the two
desks and had passed over the small articles in the hope of getting a
bigger harvest, or else was leaving those other things to the last. He
ransacked the up-stairs desk, having broken the lock, and then went
through the one down-stairs. While looking through the papers in the
sitting-room he had evidently been frightened away by something, for
there was one drawer that had not been disturbed. This also accounted
for the fact that nothing else had been taken. What had frightened him
was probably the barking of the dog, who, although he was on the
outside, had become aware of the presence of someone in the house. He
had fed the dog poison, probably poisoned meat, for they had found a
small piece of meat on the porch. Evidently the poison had begun to act
before Mr. Bob had it all eaten, and he left that piece. But before the
dog was dead the burglar had heard the family returning along the road,
singing, and made his escape. The whole thing must have happened not
long before, for the dog had not had the poison long enough to take
deadly effect. It was then that they regretted having lingered so long
over the game of charades and delayed their homecoming.
“If we had only been half an hour sooner, we might have found out who it
was,” said Mrs. Gardiner.
“Thank Heaven we weren’t half an hour later,” said Hinpoha, “or Mr. Bob
would have been dead.” She would have felt worse about losing Mr. Bob
than about having all her possessions stolen.
“How about sleeping in the tepee to-night?” asked Gladys. There was not
enough room in the house for so many people and the eight Winnebagos had
made their beds in the tepee while the three girls from town were there,
both to solve the question of sleeping quarters and for the fun of the
thing. It was just like camping out to sleep on the ground, all the
eight girls in a circle around the little watch fire in the middle of
the tepee.
“Oh, I’ll be afraid to,” said Hinpoha.
“I don’t know but what it would be just as safe as sleeping in the
house,” said Nyoda. “I doubt if anyone would think of people sleeping
out in that thing. It’s a rather novel idea in this neighborhood. And at
any rate there’s nothing out there to steal and consequently nothing to
tempt a thief.”
So, their fears having vanished, the Winnebagos went to bed in the tepee
just as they had planned. Nyoda took the precaution of putting her
pistol under her pillow. The girls really enjoyed the air of suppressed
excitement. When did youth and high spirits ever fail to respond to the
thrill of danger, either real or fancied? This attempted burglary was
the most exciting thing that had ever happened to most of the girls and
they were getting as much thrill out of it as possible. It amused them
to see Tom and Calvin parading the front lawn armed with bird guns,
swelled up with importance at having to guard a houseful of women.
Instead of hoping that the burglar had been scared away for good they
wished fervently that he would return and give them a chance to shoot.
They would have stayed there all night if Mrs. Gardiner had not ordered
them to bed.
One by one the girls in the tepee dropped off to slumber, worn out with
the varied events of the day. But Nyoda could not sleep. She had a
throbbing headache from the glare of the sun on the water while she sat
fishing. The little fire, in the center of the bare circle of earth
which prevented it from spreading, died down and subsided to glowing
embers, then one by one these turned black and left the tepee in
darkness. There was not a spark left. Nyoda was sure of this, for she
sat up several times in an effort to make herself comfortable, and when
she took a drink from the pail of well water which stood nearby she
emptied the dipper over the spot where the fire had been, to make doubly
sure. Still sleep would not come. She stared out of the doorway of the
tepee into the darkness. A group of beech trees with their light grey
bark loomed up ghostlike before the door. She began to think of the
ghost which had appeared to her that other night in that very doorway,
and tried to connect the incidents which had taken place afterwards with
that. One thing was sure—someone was getting into Onoway House every few
days. Why nothing was taken was a mystery to her. It seemed to her now
that it was not so much an attempt at burglary as an effort to annoy and
frighten the family. Possibly it was someone who had a grudge against
them—she could not imagine why—and was indulging in these pranks to
satisfy a spite. She thought she saw a glimmer of light on the subject.
Farmer Landsdowne had once told her that when it became known that Mr.
Mitchell was going to give up the care of the place, several farmers of
the Centerville Road district had applied for the position of caretaker,
but wishing to assist Migwan, the Bartletts had refused their offers and
given the place over to the Winnebagos. That must be it. Someone wanted
that job badly and was wreaking his disappointment on the people who had
kept him from getting it. The more she thought of it the more probable
it seemed. Possibly more than one were involved in the plot.
Then another thought struck her. Could it be the crazy man who lived
alone in the little house among the trees? Calvin had stated that he
never left the house, but who could account for the inspirations of an
unbalanced mind? That nothing had been taken from the house seemed to
indicate a want of fixed purpose in the mind of the housebreaker—to go
to all that trouble for nothing. This idea also seemed worth
considering.
As she lay turning these things over in her mind she thought she heard a
stealthy footstep in the grass outside of the tepee. Thinking that the
ghost was coming to pay another visit, she drew the pistol from under
her pillow and turning over, face downward, lay with it pointed toward
the doorway. There would be no outcry when he appeared in the doorway.
The first intimation the ghost would have that he was observed would be
a shot in the leg that would prevent him from running away and would
solve the mystery. In tense silence she waited, one; two; three minutes,
but nothing appeared. Then suddenly she smelled smoke, and turning
around swiftly saw that the side of the tepee toward which she had had
her back was in flames.
“Fire!” she called at the top of her voice. “Sahwah! Hinpoha! Gladys!
Migwan! Wake up!” And seizing the pail of water she dashed it against
the side of the tepee. The water sizzled as it fell, but the canvas
covering was burning like tinder. Thus rudely awakened the girls sprang
up in alarm. The place was filling with dense smoke, and through it they
groped their way to the opening, dragging out their blankets. Hardly had
the last girl got out when the whole thing was one roaring blaze, which
lit up the scenery a long way around.
Nyoda, paying no attention to the flames that were mounting skyward from
the burning canvas, looked intently for a lurking figure among the
trees, for she thought it hardly possible that whoever had set the tepee
afire could have gotten outside of the range of light in that short
time. It was possible to see as far as the road on the one side and
across the river on the other. But nowhere was there a man or the shadow
of a man. The folks came running out of Onoway House half dressed and in
terror that the girls had not escaped from the burning tent in time, and
the farmers all the way down the road, seeing the glare, rushed to offer
their assistance, for a fire in the country is a serious thing where
there is no water pressure. Farmer Landsdowne came on a dead run,
carrying a water bucket. Even Abner Smalley appeared in the midst of the
crowd. He gave a scowling look at Calvin, but said nothing, and soon
took his departure when the danger was over, as it was directly, for it
did not take long to reduce that canvas covering to a black mass, and
buckets of water thrown all around on the ground and the trees kept the
fire from spreading.
For the second time that night the family gathered in the sitting-room
and faced each other over an exciting happening. “I told you if you
built a fire in that tepee you would burn it down,” said Mrs. Gardiner.
“I never felt easy when you had one.”
“But it didn’t catch fire from our little fire,” declared Nyoda, and
told the events of the night, from the going out of the fire to the
footsteps outside the tepee when the canvas had suddenly blazed up when
she was lying in wait for the ghost with a pistol. The circle of faces
paled with fear as she told her tale. Who could this mysterious visitor
be, who seemed determined to do them some harm? The girls finished the
night in the house, three in a bed, but none of them closed their eyes
to sleep.
CHAPTER XI.—THE WELL DIGGER’S GHOST.
The next morning Mrs. Gardiner sent Mr. Landsdowne to interview the
police force of the township in which the Centerville Road belonged, and
he brought the whole force back with him. He had to bring the whole
force if he brought any for it embraced only one man and he was well
along in years, but he had a uniform and a helmet and a club and a gun,
and presented an imposing appearance as he strutted up and down the
yard, before which an evil doer might be moved to pause. The three girls
from town had departed and Nakwisi had left her spy glass behind in the
excitement, and this was a source of great entertainment to the rural
gendarme. He spent a great deal of time sliding the lens back and forth
to fit his eye and peering up the road into the distance, or looking up
into the air, as if he expected to see the burglar approaching in an
airship. He was very talkative and fond of recounting the captures he
had made single handed, and declared solemnly that the man in this case
was as good as caught already, for no one had ever escaped yet when Dave
Beeman had started out to get him.
Nyoda, who was fond of seeing her theories worked out, still held to the
idea that the mysterious visitor was someone who wanted the job of
caretaker, and inquired closely of Farmer Landsdowne who the men were
who had applied for the position. When it came down to fact there was
only one who had really wanted the job very badly, although several
others had mentioned the fact that they wouldn’t mind doing it, and that
man had found a similar situation immediately afterward and left the
neighborhood. So her theory did not seem to be inclined to hold water.
She had another idea, however, and wrote to Mr. Mitchell, asking if he
had ever heard strange noises in the attic while he lived there. Mr.
Mitchell answered and said that not only had he heard strange noises in
the attic, but also in the cellar and in the barn, and that pieces of
furniture had apparently moved themselve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it was on this account that he had left the place, as it made his
wife so nervous she became ill. This fact put a new face on the matter.
The hostility, then, was not directed against themselves personally, but
against the tenants of the house, no matter who they were. But this idea
left them more in the dark than ever, and they lost a good deal of sleep
over it without reaching any solution.
After a few days of zealous watching, during which time nothing
happened, the police force of Centerville township gave it up as a bad
job and relaxed its vigilance, declaring that the firebug must have
gotten out of the country, for that was the only way he could hope to
escape his eagle eye. “If he was still in the country, I’d a’ had him by
this time”, Dave Beeman asserted confidently. “So as long as he’s gone
that far you don’t need to worry any more.” And he took himself off,
eager to get back to the quiet game of pinochle in Gus Wurlitzer’s
grocery store, which Farmer Landsdowne had interrupted several days ago.
It was just about this time that Migwan had her biggest order for canned
tomatoes—from a fashionable private sanitarium a few miles distant, and
the rush of canning gradually took their minds off the mysterious
intruder. Migwan, picking her finest and ripest tomatoes to fill this
order, noticed that a number of the vines were drooping and turning
yellow. The half ripe tomatoes were falling to the ground and rotting.
One whole end of the bed seemed to be affected. She looked carefully for
insects and found none. Some of the leaves seemed worse shrivelled than
others. In perplexity she called Mr. Landsdowne over to look at them. He
looked closely at the plants and also seemed puzzled as to the cause of
the mysterious blight. “It isn’t rot,” he said, “because the bed is high
and dry and the plants have never stood in water.” Upon looking closely
he discovered that the affected plants were covered with a fine white
coating. He gave a smothered exclamation. “Do you know what that is?” he
asked. “It’s lime! Somebody has sprayed your plants with a solution of
lime. Are you sure you didn’t do it yourself?” he asked, quizzically.
Migwan shook her head. “I haven’t sprayed those plants with anything for
a month,” she asserted, “and neither has anyone else in the house.”
“Somebody outside of the house has done it, then,” said Mr. Landsdowne.
The work of the mysterious visitor again! It struck dismay into the
breasts of the whole household. They never knew when and where that hand
was going to strike next. And so silently, so mysteriously, without ever
leaving a trace behind!
There was nothing left to do but dig up the dead plants and throw them
away. Migwan almost stopped breathing when she thought that the rest of
the bed might be treated in the same way, and the source of her revenue
cut off. But why was all this happening? What could anyone possibly have
against the peaceful dwellers at Onoway House?
A guard was set over the tomato bed both day and night for a week and
the big order for the sanitarium was filled as fast as the tomatoes
ripened. Nothing at all happened during this time and the vigilance was
relaxed. A large dog was turned loose in the garden at night and they
felt secure in his protection. This dog belonged to Calvin Smalley. When
he had left his uncle’s house he had to leave Pointer behind, as he did
not know what else to do with him, but now that the Gardiners were
willing to have him he went over and got him when he knew his uncle was
away from the house, so he would not have to meet him. Pointer was
overjoyed at seeing his young master again and attached himself to the
household at once, and never made the slightest effort to go back to his
old home. He had a deep, heavy bark which could not fail to rouse the
house at once. With the coming of Pointer the girls breathed easily
again.
One day when Migwan had gone over to see the Landsdownes, Mr. Landsdowne
had given her a treasure for her garden. This was a plant of a rare
species called Titania Gloria, which a friend had brought from Bermuda.
It was a first year growth and so would not bloom until the following
summer. Migwan planted it along the fence beside the mint bed and
treasured it like gold, for the blossom of the Titania Gloria was a
wonderful shade of blue and was considered a prize by fanciers, who paid
high prices for cuttings of the plant. In the excitement over the tepee
and the tomato plants, however, she forgot to tell the other girls about
it, so she was the only one who knew what a precious thing that little
bed of leaves was.
The weather was so fine that week that Migwan decided to have a garden
party and invite a number of friends from town. Gladys promised to dance
and the boys cleared a circle for her in the grass under the trees,
picking up every stick that lay on the ground. Mrs. Landsdowne, hearing
about the party, offered to make ice cream for them in her freezer. Just
before the guests arrived Migwan and Calvin went over after it. They
took the raft, because they thought that would be the easiest way of
transporting the heavy tub. Migwan rode on the raft and supported the
tub and Calvin walked along the bank and pulled the tow line. His
eagerness to help with the festivity was somewhat pathetic. Never, to
his knowledge, had there been a party at the Smalley House. The way
these girls planned a party out of a clear sky and carried out their
plans without delay was nothing short of marvelous to him. They were
always at their ease with company, while it was a fearful ordeal for him
to meet strangers. He liked to be a part of such doings; but was at a
loss how to act. Migwan, with her fine understanding of things beneath
the surface, saw that this boy was lonesome in the crowd, not knowing
how to mix in and have a glorious time on his own account, and she
always saw to it that his part was mapped out for him in all their
doings. Therefore she chose him to help her bring the ice cream over.
Calvin, happy at being useful, towed the raft carefully and turned his
head whenever Migwan spoke, so as to give strict attention to her words.
Doing this, he fell over the branch of a tree in the path and jerked the
rope violently. The raft tipped up and both Migwan and the tub of ice
cream went into the river. Migwan climbed out on the bank before Calvin
was up from the ground. He was aghast at what he had done. He had been
so eager to help with the party and now he had spoiled it! That he would
be instantly expelled from Onoway House he was sure, and he felt that he
deserved it. Migwan, at least, would never speak to him again.
Speechless, he turned piteous eyes to where she sat on the bank
dripping. To his surprise she was doubled up with laughter. “What are
you laughing at?” he asked, startled.
“Because you upset the raft and the ice cream fell into the river!”
giggled Migwan. Calvin gasped. The very thing that was nearly killing
him with chagrin was the cause of her mirth! It was the first time he
had ever seen anyone make light of a calamity. Her mirth was so
contagious that he began to laugh himself. Still laughing, he brought
the tub out of the river and set it on the bank. The water had washed
away the packing of ice, but the lid on the inner can was providentially
tight and the ice cream was unharmed. That little incident crystallized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After that he was Migwan’s slave. A girl
who could be thrown into the river without getting vexed was a friend
worth having. Dripping, they returned to the house, where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party were at their height, to be laughed at
immoderately and christened the “Water Babies.”
To Hinpoha the Artistic had been entrusted the setting of the tables.
Her decorations were water lilies from the river, and when she had
finished it looked as if a feast had been spread for the river nymphs.
Around the edges of the platter she put bunches of bright mint leaves.
Her artistic efforts called out so much praise from the guests that she
was in a continual state of blushing as she waited on the table.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r hand?” asked Migwan, noticing that she was
passing things around left handedly.
“Nothing,” said Hinpoha, “nothing much. I slipped when I was getting the
lilies and fell on my wrist and it feels lame, that’s all.”
“Is it sprained?” asked Migwan.
“Oh, no,” said Hinpoha, “I don’t think so.”
“It’s all swelled up,” said Migwan, holding up the injured wrist. “Let
me paint it with iodine and tie it up for you.”
Hinpoha maintained that it was nothing serious, but Migwan insisted.
“Where is the iodine, mother?” she asked.
“On the pantry shelf,” answered Mrs. Gardiner. Migwan got the bottle and
painted Hinpoha’s wrist before the party could proceed. Hinpoha surveyed
the brown stripe around her arm rather disgustedly. It was for this very
reason that she had said nothing about the wrist before. She did not
want it painted up for the party. It offended her artistic eye and she
would rather suffer in silence.
While the guests were sitting at the tables Gladys danced on the lawn
for their entertainment. The merry laughter was hushed in surprise and
delight at her fairylike movements. In the silence which reigned at this
time the thing which happened was distinctly heard by everyone.
Apparently from the depths of the earth there came a muffled thud, thud,
as of a pick striking against hard ground. It kept up for a few minutes
and then ceased, to be renewed again after a short interval. The
dwellers at Onoway House looked at each other. Into each mind there
sprang the story of the Deacon’s well, and the words of Farmer
Landsdowne, “_Superstitious folks say you can still hear the buried well
digger striking with his pick against the ground that covers him._” It
was the most mysterious sound, far away and faint, yet seemingly right
under their very feet. Gladys heard it and paused in her dancing.
Pointer and Mr. Bob both heard it and began to bark. In a little while
the thudding noise ceased and was heard no more, and the company were
all left wondering if they could have been the victims of imagination.
“Maybe it’s somebody down cellar,” said Calvin, and taking Pointer with
him, went down. Tom followed him. But there was no sign of anyone down
there. Pointer ran around with his nose to the ground as if he were
smelling for footsteps, but his tail kept wagging all the while. They
were all familiar footsteps he scented. Nothing was out of place in the
cellar except that a basket of potatoes was thrown over and the potatoes
had rolled out on the cement floor. The boys noticed this without
thinking anything of it. The mystery of the well digger’s ghost remained
unsolved.
In the cool of the early evening after her guests had departed, Migwan
wandered down into the garden to look at her various plants and flowers.
It occurred to her that she had not paid her Titania Gloria a visit for
several days. But what a sight met her eyes when she reached the spot
where the precious thing had been planted! Not a single bit was left.
The clean cut stalks showed where they had been clipped off close to the
ground. Migwan started up with a cry of dismay which brought the other
girls running to her side. “My Titania Gloria!” gasped Migwan. “Look!
The mysterious visitor has been at work again!” And she told them about
the valuable cuttings that had disappeared so uncannily.
“We never hear that ghost but what something happens after it!” said
Gladys, in an awestruck tone. The girls peered apprehensively into the
shadows of the tall trees surrounding the garden.
“What’s up?” asked Hinpoha, joining the group. Migwan pointed to the
devastated bed. “What’s the matter with it?” asked Hinpoha.
“My Titania Gloria!” said Migwan. “It’s been clipped off at the roots.”
“Your what?” asked Hinpoha. Migwan explained about the rare plant Farmer
Landsdowne had given her. Hinpoha gave a sudden start and exclamation.
“What did you say it was?” she asked.
“A Titania Gloria,” answered Migwan.
“Well, girls, I’m the guilty one, then,” said Hinpoha, “for I cut those
plants off thinking they were mint. That was what I decorated the
platters with this afternoon. Do anything you like with me, Migwan, beat
me, hang me to a tree, put my feet in stocks, or anything, and I’ll make
no resistance.” She was absolutely frozen to the spot when she realized
what she had done.
Migwan, grieved as she was over the loss of her cherished Titania, yet
had to laugh at the depths of Hinpoha’s mortification. “You old goose!”
she said, putting her arms around her, “don’t take it so to heart! It’s
my fault, not yours at all, because I didn’t tell anyone what that plant
was. And the leaves do look just like mint.” Thus she comforted the
discomfited Hinpoha.
“Migwan,” said her mother, when they had returned to the house, “where
did you get that iodine with which you painted Hinpoha’s wrist this
afternoon?”
“On the pantry shelf, just where you told me,” answered Migwan.
“Well,” said her mother, “I told you wrong. The iodine is up on my
wash-stand.”
“Then what was in the brown bottle on the pantry shelf?” asked Migwan.
The bottle was produced.
“Why,” said Mrs. Gardiner, “that’s walnut stain, guaranteed not to wear
off!”
Then there was a laugh at Migwan’s expense!
“Old Migwan Hubbard
She went to the cupboard,
To get iodine in a phial,
But she couldn’t read plain,
And brought walnut stain,
And now her poor patient looks vile!”
chanted Sahwah.
“You’re even now,” said Gladys, “you’ve each scored a trick.”
“‘_We do this to each other!_’” said Migwan and Hinpoha in the same
breath, and locked fingers and made a wish according to the time-honored
custom.
CHAPTER XII.—OPHELIA FINDS A FAIRY GODMOTHER.
As the summer progressed, the girls had more than one conference as to
what was to become of Ophelia when they left Onoway House. To let her go
back to her life in the slums was unthinkable. So far, Old Grady had
made no effort to get her back, possibly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she
did not know where the child was. They did not even know whether or not
she had a legal claim on Ophelia. All Ophelia knew about the business
was that Old Grady had taken her from the orphan asylum when she was
seven years old. Where she had lived before she went to the orphan
asylum she could not remember, so she must have been very young when she
came there. They were equally unwilling that she should return to the
asylum.
“If we could only find someone to adopt her,” said Hinpoha. That would
be the best thing, they all agreed, although there was a lingering doubt
in the mind of each one as to whether anyone would want to adopt
Ophelia. Grammar was to her a totally unnecessary accomplishment, and
the amount of slang she knew was unending. By dint of hard labor they
had succeeded in making her say “you” instead of “yer,” and “to” instead
of “ter,” and discard some of her more violent slang phrases, but she
was still obviously a child of the streets and the tenement, and that
life had left its brand upon her. It showed itself constantly in her
speech. They had better success in teaching her table manners, for with
a child’s gift of imitation she soon fell into the ways of those around
her.
But having had so much excitement in her short life she still pined for
it. While the life in the country was pleasant in the extreme it was far
too quiet to suit her and she longed to be back in the crowded tenement
where there was something happening every hour out of the twenty-four;
where people woke to life instead of going to bed when darkness fell and
the lamps were lighted; where street cars clanged and wagons rattled and
fire engines rumbled by; where the harsh voices of newsboys rang out
above the loud conversation of the women on the doorsteps and the
wailing of the babies. The zigging of the grasshoppers and the swishing
of the wind in the Balm of Gilead tree and the murmur of the river had
for her a mournful and desolate sound, and she often covered up her ears
so as not to hear it. When she first came to Onoway House she was so
interested in the new life that it kept her busy all day long finding
out new things; but gradually the novelty wore off. At first she had
been as mischievous as a monkey; always up to some prank or other. She
teased Tom and was teased by him in return; she put burrs in Mr. Bob’s
long ears; she climbed trees and threw things down on the heads of
unsuspecting persons underneath; she startled the girls out of their
wits by lying unseen under the couch in the sitting-room and grabbing
their ankles unexpectedly. Always she was doing something, and always
merry and full of life; so that she made the girls feel that they had
done a fine thing by bringing her to Onoway House.
But of late a change had come over her. She began to droop, and to sit
silent by herself at times. The girls did their best to keep her amused,
but they were very busy with the continual canning, and Betty, who had
more time than the others, did not like her and would not play with her.
So she grew more and more homesick for the big, noisy city and the
playmates of other days. Then had come the time when she was so
sunburned and she had developed the fondness for Sahwah. After that she
was less lonesome, for Sahwah was such a lively person to be attached to
that one had always to be on the lookout for surprises. Sahwah taught
her to swim and dive and ride a bicycle; she had the boys make a swing
for her under the big tree, and Ophelia blossomed once more into
happiness. At Sahwah’s instigation she played more tricks on the other
girls than before.
But Ophelia was a shrewd little person, and she knew that the summer
would come to a close and the girls would not live together any more.
She often heard them discussing their plans. What was to become of her
then? The happy family life at Onoway House stirred in her a desire to
have a home too, and a mother of her own. She began to grow wistful
again and at times her eyes would have a strange far-away look. The
scandals of the streets which were once the breath of life to her and
which she repeated with such relish, began to lose their charm, and she
developed a taste for fairy tales. “Tell me the story about the fairy
godmother,” she would say to Sahwah, and would listen attentively to the
end. “Are you sure I’ve got one somewhere?” she would ask eagerly.
“You surely have,” Sahwah would answer, to satisfy her.
And then, “What _are_ we going to do with Ophelia when the summer is
over?” Sahwah would ask the girls after Ophelia was in bed. And Hinpoha
would think of Aunt Phœbe and knew she would never adopt such a child as
Ophelia was; and Migwan knew that it would be out of the question in her
family; and Sahwah knew that her mother would not let her come and live
with them; and Gladys thought of her delicate mother and sighed. Nyoda
could not make a home for her, because she had none of her own and a
boarding house was no place for a child.
“It’s a shame,” Sahwah would declare vehemently, “that there aren’t
fathers and mothers enough in this world to go round. Here’s Ophelia
will have to go into an institution more than likely, and grow up
without any especial interest being taken in her, while we have had so
much done for us. It isn’t fair.”
“There’s something curious about Ophelia,” said Gladys, musingly. “While
she came from the tenements and is as wild and untrained as any little
street gamin, she has the appearance of a child of a much higher class.
Have you ever noticed how small and perfect her hands and feet are? And
what beautiful almond shaped fingernails she has? And what delicate
features? Have you seen how erectly she carries herself, and how
graceful she is when she dances? In spite of her name, I don’t believe
she is Irish; and I don’t think her people could have been low class.
There’s an indefinable something about her which spells quality.”
“Probably a princess in disguise,” said Sahwah, in a tone of amusement.
“Leave it to Gladys to scent ‘quality.’”
But the others had noticed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in Ophelia and were
inclined to agree with Gladys on the subject.
“But what about the strange spot of light hair on her head?” asked
Sahwah. “Would you call that a mark of quality?” But to this there was
no answer. They had never seen or heard of anything like it before. Thus
the summer days slipped by and Onoway House continued to shelter two
homeless orphans, neither of whom knew what the future held in store for
them.
One afternoon when the girls had planned to go for a long walk to the
woods Gladys read in the paper that a balloonist was to make an
ascension over the lake. For some unaccountable reason she took a fancy
that she would like to see the performance. “Oh, Gladys,” said Sahwah,
impatiently, “you’ve seen balloonists before and you’ll see plenty yet;
come with us this afternoon.” But Gladys held out, even while she
wondered to herself why she was so eager to see this not uncommon sight.
Half offended at her, the other girls departed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woods. Gladys climbed high up in the Balm of Gilead tree, from which she
could look over the country for miles around and easily see the lake and
the distant amusement park from which the balloonist was to ascend.
The newspaper said three o’clock, but evidently the performance was
delayed, for although Gladys was on the lookout since before that time
nothing seemed to be happening. To aid her in seeing she took Nakwisi’s
spy glass up into the tree with her, and while she was waiting for the
parachute spectacle she amused herself by focusing the glass on far away
objects on the land and bringing them right before her eyes, as it
seemed. She could look right into the back door of a distant farm house
and see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doorway and chickens walking up and down
the steps; she could see the men working in the fields; she could see
the yachts out on the lake and the smoky trail of a freight steamer.
Somewhere in the middle of her range of vision were the gleaming rails
of the car tracks. She looked at them idly; they were like long streaks
of light in the sun. She saw two men, evidently tramps, come out of the
bushes along the road and bend over the rails. Somewhere along that
stretch of track there was a derailing switch and it seemed to Gladys
that it was at this point where the men were. Gladys looked at the pair,
suspiciously, for a second and then decided they were track testers. One
had an iron bar in his hand and he seemed to be turning the switch.
Suddenly the other man pointed up the road and then the two jumped
quickly backward into the bushes. Gladys looked in the direction the man
had pointed. Far off down the track she could see the red body of the
“Limited” approaching at a tremendous rate. The stretch of country past
the Centerville Road was flat and even; the track was perfect and there
was no traffic to block the way, and the cars made great speed along
here. Something told Gladys that the men had had no business at the
switch; that they meant to derail and wreck the Limited. Gladys had
learned to think and act quickly since she had become a Camp Fire Girl,
and scarcely had the idea entered her head that the Limited was in
danger, than she conceived the plan of heading it off. Before the car
reached the switch it must pass the Centerville Road. Being the Limited,
it did not stop there. So Gladys planned to run the automobile down the
Centerville Road and flag the car. She flung herself from the tree in
haste, got the machine out of the barn and started down the road with
wide-open throttle.
Trees and fences whirled dizzily by, obscured in the cloud of dust she
was raising. Across the stillness of the fields she could hear the
Limited pounding down the track. A hundred yards from the end of the
road the automobile engine snorted, choked and went dead. Without
waiting to investigate the trouble, Gladys jumped out and proceeded on
foot. Could she make it? She could see the red monster through the
trees, rushing along to certain destruction. With an inward prayer for
the speed of Antelope Boy, the Indian runner, she darted forward like an
arrow from the bow. Breathless and spent she came out on the car track
just a moment ahead of the thundering car, and waved the scarlet
Winnebago banner, which she had snatched from the wall on the way out.
With a quick jamming of the emergency brakes that shook the car from end
to end it came to a standstill just beyond the Centerville Road, and
only fifty feet from the switch.
“What’s the matter?” asked the motorman, coming out.
“Look at the switch!” panted Gladys, sinking down beside the road,
unable to say more.
The motorman looked at the switch. “My God,” he said, mopping his
forehead, “if we’d ever run into that thing going at such a rate there
wouldn’t have been anyone left to tell the tale.”
The passengers were pouring from the car, eager to find out the reason
for the sudden stoppage. “What’s the matter?” was heard on every side.
“You’ve got that girl to thank,” said the motorman, moving back toward
his vestibule, “that you’re not lying in a heap of kindling wood.”
Gladys, much abashed and still hardly able to breathe, laid her head on
her knee and sobbed from sheer nervousness and relief.
“Gladys!” suddenly said a voice above the murmurings of the throng of
passengers.
Gladys raised her head. “Papa!” she cried, staggering to her feet. “Were
you on that car?”
Another figure detached itself from the crowd and hastened forward.
“Mother!” cried Gladys. “Oh, if I hadn’t been able to stop it—” and at
the horror of the idea her strength deserted her and she slipped quietly
to the ground at her parents’ feet.
When she came to the car had gone on and she was lying in the grass by
the roadside with her head in her mother’s lap. “Cheer up, you’re all
right,” said her mother a little unsteadily, smiling down at her. Gladys
now became aware of two other figures that were standing in the road.
“Aunt Beatrice!” she cried. “And Uncle Lyn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e all came out to surprise you,” said her father. “We got back from
the West last night; sooner than we expected, and decided we would run
out without any warning and see what kind of farmers you were. The
automobile is being overhauled so we came on the interurban. We didn’t
know it didn’t stop at your road.”
Then, Gladys suddenly remembered her own disabled car standing in the
road, and they all moved toward it. With a little tinkering it
condescended to run and they were soon at Onoway House, telling the
exciting tale to Mrs. Gardiner, who held up her hands in horror at the
thought of the fate which the newcomers had so narrowly escaped. Aunt
Beatrice, not being strong, was much agitated, and developed a
palpitation of the heart, and had to lie in the hammock on the porch and
be doctored, so Gladys had her hands full until the girls came back.
They were much surprised at the houseful of company and very glad to see
Mr. and Mrs. Evans, who were very good friends of the Winnebagos indeed.
They looked with interest when Aunt Beatrice was introduced, for they
all remembered the tragic story Gladys had told them about the loss of
her baby in the hotel fire. Aunt Beatrice felt well enough to get up
then and acknowledge the introductions with a sweet but infinitely sad
smile that went straight to their hearts, and brought tears to the eyes
of the soft-hearted Hinpoha.
Ophelia came in last, having loitered on the lawn to play with Pointer
and Mr. Bob. She had taken off her hat and was swinging it around in her
hand when she came up on the porch. “And this is the little sister of
the Winnebagos,” said Nyoda, drawing her forward. Aunt Beatrice looked
down at the dust-streaked little face, with her sad smile, but her eyes
rested there only an instant. She was gazing as if fascinated at the
strange ring of light hair on her head. She became very pale and her
eyes widened until they seemed to be the biggest part of her face.
“Lynn!” she gasped in a choking voice, “Lynn! Look!” and she sank on the
floor unconscious. “It can’t be! It can’t be!” she kept saying faintly
when they revived her. “Beatrice died in the fire. But Beatrice had that
ring of light hair on her head! It can’t be! But there never were two
such birthmarks!”
What a hubbub arose when this startling possibility was uttered!
Ophelia, the lost Beatrice? Could it possibly be true? Uncle Lynn lost
no time in finding out. Taking Ophelia with him he hunted up Old Grady.
She knew nothing more save that she had gotten her from an orphan
asylum, which she named. At the asylum he learned what he wanted to
know. The superintendent remembered about Ophelia on account of the
strange ring of light hair. The child had been brought to the
institution when she was about a year old. There was a babies’
dispensar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lace, and into this a weak, haggard
girl of about eighteen had staggered one day carrying a baby. The baby
was sick and she begged them to make it well. While she sat waiting for
the nurse to look at the baby the girl collapsed. She died in a charity
hospital a few days later. On her death-bed she confessed that she had
run away from a large hotel with the baby which had been left in her
care, intending to hide it and get money from the parents for its
recovery. But she feared this would lead her into trouble and left town
with the child and never troubled the parents as she had intended, and
kept the baby with her until it fell sick, when she had become
frightened and sought the dispensary. She apparently never knew that the
hotel had burned and covered up the traces of her flight. The baby was
kept at the orphan asylum and named Ophelia. Her last name had never
been known. Thence Old Grady had adopted her, but her right could be
taken away from her as it was clear that she was no fit person to have
the child.
“It’s just like a fairy tale!” said Hinpoha, when it was established
beyond a doubt that the abused street waif Gladys had brought home in
the goodness of her heart was her own cousin.
“Didn’t I tell you you’d find your fairy godmother if you only waited
long enough?” said Sahwah. And Ophelia, from the depths of her mother’s
arms, nodded rapturously.
CHAPTER XIII.—A GAME OF HIDE-AND-SEEK.
“Oh, Gladys, do you have to go home, now that your mother and father are
back?” asked Migwan, anxiously.
“Not unless you want to, Gladys,” said Mrs. Evans. “If you would rather
stay out here until school opens, you may. Father and I are going to
Boston in a few days, you know.”
So there was no breaking up of the group before they all went home, with
the exception of Ophelia, or rather Beatrice, as we will have to call
her from now on, for, of course, she was to go with her mother.
“What must it be like, anyway,” said Hinpoha, “not to have any last name
until you’re nine years old and then be introduced to yourself? To
answer to the name of Ophelia one and ‘Miss Beatrice Palmer’ the next?
It must be rather confusing.”
Little Beatrice went to Boston with her mother and father and uncle and
aunt and Onoway House missed her rather sorely. Calvin Smalley also got
a measure of happiness out of the restoration of the lost child, for
Uncle Lynn was so beside himself with joy over the event that he was
ready to bestow favors on anyone connected with Onoway House, and
promised to see that Calvin got through school and college. He would
give him a place to work in his office Saturdays and vacations.
For several days now there had been no sign of the mysterious visitor,
and the well digger’s ghost had also apparently been laid to rest. Then
one morning they woke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unseen agency had been
at work again. Pinned on the front door was a piece of paper on which
was scrawled,
“_If you folks know what’s good for you you’ll get out of that
house._”
“We’ll do no such thing!” said Migwan, with unexpected spirit “I’ve
started out to earn money to go to college by canning tomatoes, and I’m
going to stay here until they’re canned; I don’t care who likes it or
doesn’t.”
“That’s it, stand up for your rights,” applauded Sahwah.
“But what possible motive could anyone have for wanting us to get out of
the house?” asked Migwan. Of course, there was no answer to this.
“Do you suppose the house will be burned down as the tepee was?” asked
Gladys, in rather a scared voice. This suggestion sent a shiver through
them all.
“We must get the policeman back again to watch,” said Mrs. Gardiner.
Accordingly, the redoubtable constable was brought on the scene again.
“Well, well, well,” he said, fingering the mysterious note. “Thought
he’d come back again now that the coast was clear, did he? You notice,
though, that he didn’t make no effort while I was here. You can bet your
life he won’t get busy again while I’m here now. You ladies just rest
easy and go on with your peeling.”
Scarcely had he finished speaking, when from the bowels of the earth and
apparently under his very feet, there came the strange sound as of blows
being struck on hard earth or stone. The expression on Dave Beeman’s
face was such a mixture of surprise and alarm that the girls could not
keep from laughing, disturbed as they were at the return of the sounds.
“By gum,” said the constable, looking furtively around, “this is
certainly a queer business.” He had heard the story of the well digger’s
ghost and it was very strong in his mind just now. “Maybe it’s just as
well not to meddle,” he said under his breath.
Off and on through the day they heard the same sounds issuing from the
ground, and at dusk the weird moaning began again. The constable showed
strong signs of wishing himself elsewhere. When darkness fell the noises
ceased and were heard no more that night. But another sort of moaning
had taken its place. This was the wind, which had been blowing strongly
all day, and early in the evening increased to the proportions of a
hurricane. With wise forethought Sahwah and Nyoda brought the raft and
the rowboat up on land. Leaves, small twigs and thick dust filled the
air. Windows rattled ominously; doors slammed with jarring crashes.
Migwan, foreseeing a devastating storm, set all the girls to picking
tomatoes as fast as they could, whether they were ripe or not, to save
them from being dashed to the ground. They could ripen off the vines
later.
At last the sandstorm drove them into the house, blinded. Then there
came such a wind as none of them had ever experienced. Trees in the yard
broke like matches; the Balm of Gilead roared like an ocean in a
tempest. There was a constant rattle of pebbles and small objects
against the window panes; then one of the windows in the dining-room was
broken by a branch being hurled against it, and let in a miniature
tempest. Papers blew around the room in great confusion. Migwan rolled
the high topped sideboard in front of the broken pane to keep the wind
out of the room. At times it seemed as if the very house must be coming
down on top of their heads, and they stood with frightened faces in the
front hall ready to dash out at a moment’s notice. A crash sounded on
the roof and they thought the time had come, but in a moment they
realized that it was only the chimney falling over. The bricks went
sliding and bumping down the slope of the roof and fell to the ground
over the edge.
“I pity anybody who’s caught in this out in the open,” said Migwan. “I
believe the wind is strong enough to blow a horse over. I wonder where
Calvin is now.” Calvin had gone to the city with Farmer Landsdowne on
business and intended to remain all night.
“He’s probably all right if he has reached those friends of the
Landsdownes’,” said Hinpoha.
“The Smalleys are out, too,” said Sahwah. “I saw them drive past after
dark, going toward town, just before it began to blow so terribly. Oh,
listen! What do you suppose that was?” A crash in the yard told them
that something had happened to the barn. Gladys was in great distress
about the car, and had to be restrained forcibly from running out to see
if it was all right. The wind continue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night
and nobody thought of going to bed. By morning it had spent its force.
Then they looked out on a scene of destruction. The garden was piled
with branches and trunks of trees, and strewn with clothes that had been
hanging on wash-lines somewhere along the road. Up against the porch lay
a wicker chair which they recognized as belonging to a house some
distance away. Everywhere around they could see the corn and wheat lying
flat on the ground, as if trodden by some giant foot. The roof of the
barn had been torn off on one side and reposed on the ground, more or
less shattered. The car was uninjured except that it was covered with a
thick coating of yellow dust. It was well that they had thought to pick
the tomatoes, for the vines and the frames which supported them were
demolished. All the telephone wires were down as far as they could see.
Calvin was not to return until night, and they felt no great anxiety
about him, but often during the day a disquieting thought came to
Migwan. This was about Uncle Peter, the man who lived in the cottage
among the trees. Suppose something had happened to him? From Sahwah’s
report, the house was very old and frail. She watched the Red House
closely for signs of life, but apparently the Smalleys had not returned.
The doors were shut and there was no smoke coming out of the kitchen
chimney.
“Nyoda,” said Migwan, finally, “I’m going over and see if that old man
is all right. I can’t rest until I know.”
“All right,” said Nyoda, “I’m going with you.” Sahwah was over at Mrs.
Landsdowne’s, but they remembered her description of the approach to the
cottage, and made the detour around the field where the bull was and the
marsh beyond it, coming up to the cottage from the other side. It was
still standing, although the big tree beside it had been blown over and
lay across the roof.
“Would you ever think,” said Migwan, “that there was anyone living in
there? I could pass it a dozen times and swear it was empty, if I didn’t
know about it.”
“Well,” said Nyoda, the house is still standing, “so I suppose the old
man is all right.”
“I wonder,” said Migwan. “He may have been frightened sick, and he may
have nothing to eat or drink, now that the Smalleys are kept away. We’d
better have a look. He can’t hurt us. If Sahwah spent the whole
afternoon with him we needn’t be afraid.”
They tried the door, but, of course, found it locked, and were obliged
to resort to the same means of entrance as Sahwah had employed. They saw
the key in the other door just as Sahwah had and turned it and opened
the door. The old man was sitting by the table in just the position
Sahwah had described. Apparently he was neither frightened nor hurt. He
looked up when he saw them in the doorway and motioned them to come in.
There was nothing extraordinary in his appearance; he was simply an old
man with mild blue eyes. Obeying the same impulse of adventure which had
led Sahwah across the threshold, they stepped in and sat down. The room
was just as Sahwah had told them. The table was littered with wheels and
rods which the old man was fitting together. As they expected, he worked
away without taking any notice of them.
“Did you mind the storm?” asked Nyoda.
“Storm?” said the old man. “What storm?”
“He never noticed it!” said Migwan, in an aside to Nyoda.
“What are you making?” asked Migwan, wishing to hear from his own lips
the explanation he had given Sahwah.
After his customary interval he spoke. “It’s a machine that reclaims
wasted moments,” he explained. “Every moment that isn’t made good use of
goes down through this little trap door, and when there are enough to
make an hour they join hands and climb up on the face of the clock
again.”
Migwan and Nyoda exchanged glances. The ingenious imagination of the old
man surpassed anything they had ever heard. They stayed awhile, amusing
themselves by looking at the books and clocks in the cabinets, and then
rose, intending to slip away quietly when he was absorbed in his work,
as Sahwah had done. A dish of apples standing on one of the cabinets
indicated that he was not without food and their minds were now at rest
about his welfare. But when they moved toward the door he turned and
looked at them.
“What do you think of it?” he asked.
By “it” they figured that he meant the machine he was working on. “It’s
a very good one indeed,” said Nyoda, “very interesting.”
“Do you want to buy the rights?” asked the old man, taking off his hat
and putting it on again.
“He thinks he’s talking to some capitalist!” whispered Migwan.
“We’ll talk over the plans first among ourselves and let you know our
decision,” said Nyoda, not knowing what to say and wishing to appear
politely interested. This speech would give them an opportunity to get
away. But to her surprise Uncle Peter drew a sheet of paper from among
those on the table and gravely handed it to her.
“Here are the plans,” he said. “Take them and look them over and let me
know in a week.” Then he fell to work and forgot their presence. Holding
the paper in her hands Nyoda walked out of the room, followed by Migwan.
They left the house as they had entered it and returned by a roundabout
way to Onoway House. Nyoda put the plans of the remarkable machine away
in her room, intending to keep it as a curiosity. Soon afterward they
saw the Smalleys driving into the yard of the Red House.
one called ‘Jerry’s Sister.’ But you have really spoiled it in the
development. It takes a person familiar with the production of a film to
direct the movements of the actors intelligently. If Mr. Larue, for
example, had developed that piece it would be a very good one. Would you
be willing to sell just the idea, if Mr. Larue thinks he can use it?”
Migwan had never thought of this before. “Why, yes,” she said, “I
suppose I would. It’s certainly no good to me as it is.”
“Let me take it to Mr. Larue,” said Miss Mortimer. “I’m sure he will see
the possibilities in it just as I have.” Migwan was in a transport of
delight to think that her idea at least had found favor with Miss
Mortimer. Miss Mortimer was as good as her word and showed the play to
Mr. Larue and he agreed with her that it could be developed into a
side-splitting farce comedy. Migwan was more intoxicated with that first
sale of the labors of her pen than she was at any future successes,
however great. Deeply inspired by this recognition of her talent, she
evolved an exciting plot from the incidents which had just occurred,
namely, the mistaking of the moving picture company for the Venoti gang.
She kept it merely in plot form, not trying to develop it, and Mr. Larue
accepted this one also. After this second success, even though the price
she received for the two plots was not large, the future stretched out
before Migwan like a brilliant rainbow, with a pot of gold under each
end.
Miss Mortimer soon discovered that the Winnebagos were a group of Camp
Fire Girls, and she immediately had an idea. When “The Honor of a
Soldier” was finished Mr. Larue was going to produce a piece which
called for a larger number of people than the company contained, among
them a group of Camp Fire Girls. He intended hiring a number of “supers”
for this play. “Why not hire the Winnebagos?” said Miss Mortimer. And so
it was arranged. Medmangi and Nakwisi and Chapa, the other three
Winnebagos, were notified to join the ranks, and excitement ran high. To
be in a real moving picture! It is true that they had nothing special to
do, just walk through the scene in one place and sit on the ground in a
circle in another, but there was not a single girl who did not hope that
her conduct on that occasion would lead Mr. Larue into hiring her as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company.
Especially Sahwah. The active, strenuous life of a motion picture
actress attracted her more than anything just now. She longed to be in
the public eye and achieve fame by performing thrilling feats. She saw
herself in a thousand different positions of danger, always the heroine.
Now she was diving for a ring dropped into the water from the hand of a
princess; now she was trapped in a burning building; now she was riding
a wild horse. But always she was the idol of the company, and the idol
of the moving picture audiences, and the envy of all other actresses.
She would receive letters from people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her
picture would be in the papers and in the magazines, and her name would
be featured on the colored posters in front of the theatres. Managers
would quarrel over her and she would be offered a fabulous salary. All
this Sahwah saw in her mind’s eye as the future which was waiting for
her, for since meeting Miss Mortimer she really meant to be a motion
picture actress when she was through school. She felt in her heart that
she could show people a few things when it came to feats of action. She
simply could not wait for the day when the Winnebagos were to be in the
picture. When the play was produced in the city theatres her friends
would recognize her, and Oh joy!—here her thoughts became too gay to
think.
The play in question was staged, not on the Centerville road, but in one
of the city parks, where there were hills and formal gardens and an
artificial lake, which were necessary settings. The day arrived at last.
News had gone abroad that a motion picture play was to be staged in that
particular park and a curious crowd gathered to watch the proceedings.
Sahwah felt very splendid and important as she stood in the company of
the actors. She knew that the crowd did not know that she was just in
that one play as a filler-in; to them she was really and truly a member
of this wonderful company—a real moving picture actress. Gazing over the
crowd with an air of indifference, she suddenly saw one face that sent
the blood racing to her head. That was Marie Lanning, the girl whom
Sahwah had defeated so utterly in the basketball game the winter before,
and who had tried such underhand means to put her out of the game.
Sahwah felt that her triumph was complete. Marie was just the kind of
girl who would nearly die of envy to see her rival connected with
anything so conspicuous.
The picture began; progressed; the time came for the march of the Camp
Fire Girls down the steep hill. Sahwah stood straight as a soldier; the
supreme moment had come. Now Mr. Larue would see that she stood out from
all the other girls in ability to act; that moment was to be the making
of her fortune. She glanced covertly at Marie Lanning. Marie had
recognized her and was staring at her with unbelieving, jealous eyes.
The march began. Sahwah held herself straighter still, if that were
possible, and began the descent. It was hard going because it was so
steep, but she did not let that spoil her upright carriage. She was just
in the middle of the line, which was being led by Nyoda, and could see
that the girls in front of her were getting out of step and breaking the
unity of the line in their efforts to preserve their balance. Not so
Sahwah. She saw Mr. Larue watching her and she knew he was comparing her
with the rest. Her fancy broke loose again and she had a premonition of
her future triumphs. The sight of the camera turned full on her gave her
a sense of elation beyond words. It almost intoxicated her. Halfway down
the hill Sahwah, with her head full of day-dreams, stepped on a loose
stone which turned under her foot, throwing her violently forward. She
fell against Hinpoha, who was in front of her. Hinpoha, utterly
unprepared for this impetus from the rear, lost her balance completely
and crashed into Gladys. Gladys was thrown against Nyoda, and the whole
four of them went down the hill head over heels for all the world like a
row of dominoes.
Down at the bottom of the hill stood the hero and heroine of the piece,
namely, Miss Mortimer and Chambers, the leading man, and as the
landslide descended it engulfed them and the next moment there was a
heap of players on the ground in a tangled mass. It took some minutes to
extricate them, so mixed up were they. Mr. Larue hastened to the spot
with an exclamation of very excusable impatience. Several dozen feet of
perfectly good film had been spoiled and valuable time wasted. The
players got to their feet again unhurt, and the watching crowd shouted
with laughter. Sahwah was ready to die of chagrin and mortification. She
had spoiled any chances she had ever had of making a favorable
impression on Mr. Larue; but this was the least part of it. There in the
crowd was Marie Lanning laughing herself sick at this fiasco of Sahwah’s
playing. Good-natured Mr. Chambers was trying to soothe the
embarrassment of the Winnebagos and make them laugh by declaring he had
lost his breath when he was knocked over and when he got it back he
found it wasn’t his, but Sahwah refused to be comforted. She had
disgraced herself in the public eye. Breaking away from the group she
ran through the crowd with averted face, in spite of calls to come back,
and kept on running until she had reached the edge of the park and the
street car line. Boarding a car, she went back to Onoway House, wishing
miserably that she had never been born, or had died the winter before in
the coasting accident. Her ambition to be a motion picture actress died
a violent death right then and there. So the march of the Camp Fire
Girls had to be done over again without Sahwah, and was consummated this
time without accident.
When Sahwah reached Onoway House she wished with all her heart that she
hadn’t come back there. She had done it mechanically, not knowing where
else to go. At the time her only thought had been to get away from the
crowd and from Mr. Larue; now she hated to face the Winnebagos. She was
glad that no one was at home, for Mrs. Gardiner had taken Betty and Tom
and Ophelia to see the play acted. As she went around the back of the
house she came face to face with Mr. Smalley, who was just going up on
the back porch. He seemed just as surprised to see her as she was to see
him, so Sahwah thought, but he was friendly enough and asked if the
Gardiners were at home. When Sahwah said no, he said, “Then possibly
they wouldn’t mind if you gave me what I wanted. I came over to see if
they would lend me their wheel hoe, as mine is broken and will have to
be sent away to be fixed, and I have a big job of hoeing that ought to
be done to-day.” Sahwah knew that Migwan would not refuse to do a
neighborly kindness like that as long as they were not using the tool
themselves, and willingly lent it to him.
She was still in great distress of mind over the ridiculous incident of
the morning and did not want to see the other girls when they came home.
So taking a pillow and a book, she wandered down the river path to a
quiet shady spot among the willows and spent the afternoon in solitude.
When the other girls returned home Sahwah was nowhere to be found. This
did not greatly surprise them, however, for they were used to her
impetuous nature and knew she was hiding somewhere. Hinpoha and Gladys
were up-stairs removing the dust of the road from their faces and hands
when they heard a stealthy footstep overhead. “She’s hiding in the
attic!” said Hinpoha.
“She’ll melt up there,” said Gladys, “it must be like an oven. Let’s
coax her down and don’t any of us say a word about the play. She must
feel terrible about it.”
So it was agreed among the girls that no mention of Sahwah’s mishap
should be made, and Hinpoha went to the foot of the attic stairs and
called up: “Come on down, Sahwah, we’re all going out on the river.”
There was no answer. Hinpoha called again: “Please come, Sahwah, we need
you to steer the raft.” Still no answer. Hinpoha went up softly. She
thought she could persuade Sahwah to come down if none of the others
were around. But when she reached the top of the stairs there was no
sign of Sahwah anywhere. The place was stifling, and Hinpoha gasped for
breath. Sahwah must be hiding among the old furniture. Hinpoha moved
things about, raising clouds of dust that nearly choked her, and calling
to Sahwah. No answer came, and she did not find Sahwah hidden among any
of the things. Gladys came up to see what was going on, followed by
Migwan.
“She doesn’t seem to be up here after all,” said Hinpoha, pausing to
take breath. “It’s funny; I certainly thought I heard someone up here.”
“Don’t you remember the time I thought I heard someone up here in the
night and you said it was the noise made by rats or mice?” asked Migwan.
“It was probably that same thing again.”
“It must have been,” said Hinpoha.
“Maybe it was the ghost of that Mrs. Waterhouse, who died before she had
her attic cleaned, and comes back to move the furniture,” said Gladys.
In spite of its being daylight an unearthly thrill went through the
veins of the girls. The whole thing was so mysterious and uncanny.
Migwan was looking around the attic. “Who broke that window?” she asked,
suddenly. The side window, the one near the Balm of Gilead tree, was
shattered and lay in pieces on the floor.
“It wasn’t broken the day we brought Miss Mortimer up,” said Gladys. “It
must have happened since then.”
“There must have been someone up here to-day,” said Migwan. “Do you
suppose—” here she stopped.
“Suppose what?” asked Hinpoha.
“Do you suppose,” continued Migwan, “that Sahwah was up here and broke
it accidentally and is afraid to show herself on account of it?”
“Maybe,” said Hinpoha, “but Sahwah’s not the one to try to cover up
anything like that. She’d offer to pay for the damage and it wouldn’t
worry her five minutes.”
“It may have been broken the night of the storm,” said Nyoda, who had
arrived on the scene. “If I remember rightly, we opened it when Miss
Mortimer was up here, and as it is only held up by a nail and a rope
hanging down from the ceiling, it could easily have been torn loose in
such a wind as that and slammed down against the casement and broken. We
were so excited trying to cover up the plants that we did not hear the
crash, if indeed, we could have heard it in that thunder at all.”
This seemed such a plausible explanation that the girls accepted it
without question and dismissed the matter from their minds. Descending
from the hot attic they went out on the river on the raft. As it drew
near supper time they feared that Sahwah would stay away and miss her
supper, and they knew that she would have to show herself sometime, so
they determined to have it over with so Sahwah could eat her supper in
peace. On the path along the river they found her handkerchief and knew
that she was somewhere near the water. They called and called, but she
did not answer. “I know what will bring her from her hiding-place,” said
Nyoda. She unfolded her plan and the girls agreed. They poled the raft
back to the landing-place and got on shore. Then they set Ophelia on the
raft all alone and sent it down-stream, telling her to scream at the top
of her voice as if she were frightened. Ophelia obeyed and set up such a
series of ear-splitting shrieks as she floated down the river that it
was hard to believe that she was not in mortal terror. The scheme worked
admirably. Sahwah heard the screams and peered through the bushes to see
what was happening. She saw Ophelia alone on the raft and no one else in
sight, and thought, of course, that she was afraid and ran out to
reassure her. She took hold of the tow line and pulled the raft back to
the landing-place.
“Whatever made you so scared?” she asked, as Ophelia stepped on terra
firma.
“Pooh, I wasn’t scared at all,” said Ophelia, grandly. “They told me to
scream so you’d come out.” So Sahwah knew the trick that had been
practised on her, but instead of being pleased to think that the girls
wanted her with them so badly she was more irritated than before. There
was no further use of hiding; she had to go into the house now and eat
her supper with the rest. The meal was not such a trial for her as she
had anticipated, because no one mentioned the subject of moving
pictures, or acted as if anything had happened at all. After supper
Nyoda brought out a magazine showing pictures of the Rocky Mountains and
the girls gave this their strict attention. Nyoda read aloud the
descriptions that went with the pictures. In one place she read: “The
barren aspect of the hillside is due to a landslide which swept
everything before it.”
At this Migwan’s thoughts went back to the scene on the hillside that
day, when the human landslide was in progress. Now Migwan, in spite of
her serious appearance, had a sense of humor which at times got the
upper hand of her altogether. The memory of those figures rolling down
the hill was too much for her and she dissolved abruptly into hysterical
laughter. She vainly tried to control it and buried her face in her
handkerchief, but it was no use. The harder she tried to stop laughing
the harder she laughed. “Oh,” she gasped, “I never saw anything so funny
as when you rolled against Miss Mortimer and Mr. Chambers and knocked
them off their feet.”
After Migwan’s hysterical outburst the rest could not restrain their
laughter either, and Sahwah became the butt of all the humorous remarks
that had been accumulating in the minds of the rest. If it had been
anyone else but Migwan who had started them off, Sahwah would possibly
have forgiven that one, but since selling her two plots to Mr. Larue
Migwan had been holding her head pretty high. That Migwan had succeeded
in her end of the motion picture business when she had failed in hers
galled Sahwah to death and she fancied that Migwan was trying to “rub it
in.”
“I hope everything I do will cause you as much pleasure,” she said
stiffly. “I suppose nothing could make you happier than to see me do
something ridiculous every day.” Sahwah had slipped off her balance
wheel altogether.
Migwan sobered up when she heard Sahwah’s injured tone. She never
dreamed Sahwah had taken the occurrence so much to heart. It was not her
usual way. “Please don’t be angry, Sahwah,” she said, contritely. “I
just couldn’t help laughing. You know how light headed I am.”
But Sahwah would have none of her apology. “I’ll leave you folks to have
as much fun over it as you please,” she said coldly, rising and going
up-stairs.
Migwan was near to tears and would have gone after her, but Nyoda
restrained her. “Let her alone,” she advised, “and she’ll come out of it
all the sooner.”
Sahwah was herself again in the morning as far as the others were
concerned, but she still treated Migwan somewhat coldly and it was
evident that she had not forgiven her.
CHAPTER VIII.—A CANNING EPISODE.
Three times every week Migwan had been making the trip to town with a
machine-load of vegetables, which was disposed of to an ever growing
list of customers. Thanks to the early start the garden had been given
by Mr. Mitchell, and the constant care it received at the hands of
Migwan and her willing helpers, Migwan always managed to bring out her
produce a day or so in advance of most of the other growers in the
neighborhood and so could command a better price at first than she could
have if she had arrived on the scene at flood tide. After every trip
there was a neat little sum to put in the old cocoa can which Migwan
used as a bank until there was enough accumulated to make a real bank
deposit. The asparagus had passed beyond its vegetable days and had
grown up in tall feathery shoots that made a pretty sight as they stood
in a long row against the fence. The new strawberry plants had taken
root and were growing vigorously; the cucumbers were thriving like fat
babies. The squashes and melons were running a race, as Sahwah said, to
see which could hold up the most fruit on their vines; the corn-stalks
stood straight and tall, holding in their arms their firstborn, silky
tassel-capped children, like proud young fathers.
But it was the tomato bed in which Migwan’s dearest hopes were bound up.
The frames sagged with exhaustion at the task of holding up the weight
of crimsoning globes that hung on the vines. Migwan tended this bed as a
mother broods over a favorite child, fingering over the leaves for
loathsome tomato worms, spraying the plants to keep away diseases, and
cultivating the ground around the roots. All suckers were ruthlessly
snipped off as soon as they grew, so that the entire strength of the
plants could go into the ripening of tomatoes. For it was on that tomato
bed that Migwan’s fortune depended. While the proceeds from the
remainder of the garden were gratifying, they were not great enough to
make up the sum which Migwan needed to go to college, as the vegetables
were not raised in large enough quantities. Migwan carefully estimated
the amount she would realize from the sale of the tomatoes and found
that it would not be large enough, and decided she could make more out
of them by canning them. At Nyoda’s advice the Winnebagos formed
themselves into a Canning Club, which would give them the right to use
the 4H label, which stood for Head, Hand, Health and Heart, and was
recognized by dealers in various places. According to the methods of the
Canning Club they canned the tomatoes in tin cans, with tops neatly
soldered on. After an interview with various hotels and restaurants in
the city Nyoda succeeded in establishing a market for Migwan’s goods,
and the canning went on in earnest. The whole family were pressed into
service, and for days they did nothing but peel from morning until
night.
“I’m getting to be such an expert peeler,” said Hinpoha, “that I
automatically reach out in my sleep and start to peel Migwan.”
Nyoda made up a gay little song about the peeling. To the tune of
“Comrades, comrades, ever since we were boys,” she sang, “Peeling,
peeling, ever since 6 A.M.”
Several places had asked for homemade ketchup and Migwan prepared to
supply the demand. Never did a prize housekeeper, making ketchup for a
county fair, take such pains as Migwan did with hers. She took care to
use only the best spices and the best vinegar; she put in a few peach
leaves from the tree to give it a finer flavor; she stood beside the big
iron preserving kettle and stirred the mixture all the while it was
boiling to be sure that it would not settle and burn. Everyone in the
house had to taste it to be sure it found favor with a number of
critical palates. “Wouldn’t you like to put a few bay leaves into it?”
asked her mother. “There are some in the glass jar in the pantry. They
are all crumbled and broken up fine, but they are still good.” Migwan
put a spoonful of the broken leaves into the ketchup; then she put
another.
“Oh, I never was so tired,” she sighed, when at last it had boiled long
enough and she shoved it back.
“Let’s all go out on the river,” proposed Nyoda, “and forget our toil
for awhile.” Sahwah was the last out of the kitchen, having stopped to
drink a glass of water, and while she was drinking her eye roved over
the table and caught sight of half a dozen cloves that had spilled out
of a box. Gathering them up in her hand she dropped them into the
ketchup. Just then Migwan came back for something and the two went out
together.
“And now for the bottling,” said Migwan, when the supper dishes were put
away, and she set several dozen shining glass bottles on the table.
After she had been dipping up the ketchup for awhile she paused in her
work to sit down for a few moments and count up her expected profits.
“Let’s see,” she said, “forty bottles at fifteen cents a bottle is six
dollars. That isn’t so bad for one day’s work. But I hope I don’t have
many days of such work,” she added. “My back is about broken with
stirring.” About thirty of the bottles were filled and sealed when she
took this little breathing spell.
“Let me have a taste,” said Hinpoha, eyeing the brown mixture longingly.
“Help yourself,” said Migwan. Hinpoha took a spoonful. Her face drew up
into the most frightful puckers. Running to the sink she took a hasty
drink of water. “What’s the matter?” said Migwan, viewing her in alarm.
“Did you choke on it?”
“Taste it!” cried Hinpoha. “It’s as bitter as gall.”
Migwan took a taste of the ketchup and looked fit to drop. “Whatever is
the matter with it?” she gasped. One after another the girls tasted it
and voiced their mystification. “It couldn’t have spoiled in that short
time,” said Migwan.
Then she suddenly remembered having seen Sahwah drop something into the
kettle as it stood on the back of the stove. Could it be possible that
Sahwah was seeking revenge for having been made fun of? “Sahwah,” she
gasped, unbelievingly, “did you put anything into the ketchup that made
it bitter?”
“I did not,” said Sahwah, the indignant color flaming into her face. She
had already forgotten the incident of the cloves. She saw Nyoda and the
other girls look at her in surprise at Migwan’s words. Her temper rose
to the boiling point. “I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she said, fiercely.
“You think I did something to the ketchup to get even with Migwan, but I
didn’t, so there. I don’t know any more about it than you do.”
“I take it all back,” said Migwan, alarmed at the tempest she had set
astir, and bursting into tears buried her head on her arms on the
kitchen table. All that work gone for nothing!
Sahwah ran from the room in a fearful passion. Nyoda tried to comfort
Migwan. “It’s a lucky thing we found it before the stuff was sold,” she
said, “or your trade would have been ruined.” She and the other girls
threw the ketchup out and washed the bottles.
“Whatever could have happened to it?” said Gladys, wonderingly.
Migwan lifted her face. “I want to tell you something, Nyoda,” she said.
“I suppose you wonder why I asked Sahwah if she had put anything in.
Well, when I went back into the kitchen after my hat when we were going
out on the river, Sahwah was there, and she was dropping something into
the kettle.”
“You don’t mean it?” said Nyoda, incredulously. Nyoda understood
Sahwah’s blind impulses of passion, and she could not help noticing for
the last few days that Sahwah was still nursing her wrath at Migwan for
laughing at her, and she wondered if she could have lost control of
herself for an instant and spoiled the ketchup.
Meanwhile Sahwah, up-stairs, had cooled down almost as rapidly as she
had flared up, and began to think that she had been a little hasty in
her outburst. She, therefore, descended the back stairs with the idea of
making peace with the family and helping to wash the bottles. But
halfway down the stairs she happened to hear Migwan’s remark and Nyoda’s
answer, and the long silence which followed it. Immediately her fury
mounted again to think that they suspected her of doing such an
underhand trick. “They don’t trust me!” she cried, over and over again
to herself. “They don’t believe what I said; they think I did it and
told a lie about it.” All night she tossed and nursed her sense of
injury and by morning her mind was made up. She would leave this place
where everyone was against her, and where even Nyoda mistrusted her.
That was the most unkind cut of all.
When she did not appear at the breakfast table the rest began to wonder.
Betty reported that Sahwah had not been in bed when she woke up, which
was late, and she thought she had risen and dressed and gone down-stairs
without disturbing her. There was no sign of her in the garden or on the
river. Both the rowboat and the raft were at the landing-place. There
was an uncomfortable restraint at the breakfast table. Each one was
thinking of something and did not want the others to see it. That thing
was that Sahwah had a guilty conscience and was afraid to face the
girls. Migwan’s eyes filled with tears when she thought how her dear
friend had injured her. A blow delivered by the hand of a friend is so
much worse than one from an enemy. The table was always set the night
before and the plates turned down.
“What’s this sticking out under Sahwah’s plate?” asked Gladys. It was a
note which she opened and read and then sat down heavily in her chair.
The rest crowded around to see. This was what they read: “As long as you
don’t trust me and think I do underhand things you will probably be glad
to get rid of me altogether. Don’t look for me, for I will never come
back. You may give my place in the Winnebagos to someone else.” It was
signed “Sarah Ann Brewster,” and not the familiar “Sahwah.”
“Sahwah’s run away!” gasped Migwan in distress, and the girls all ran up
to her room. Her clothes were gone from their hooks and her suit-case
was gone from under the bed. The girls faced each other in
consternation.
“Do you think she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ketchup, after all?” asked
Gladys, thoughtfully. “It was so unlike her to do anything of that
kind.”
“Then why did she run away?” asked Migwan, perplexed.
The morning passed miserably. They missed Sahwah at every turn. Several
times the girls forgot themselves and sang out “O Sahwah!” Nyoda did not
doubt for a moment that Sahwah had gone to her own home, but she thought
it best not to go after her immediately. Sahwah’s hot temper must cool
before she would come to herself. Nyoda was puzzled at her conduct. If
she had nothing to be ashamed of why had she run away? That was the
question which kept coming up in her mind. Nothing went right in the
house or the garden that day. Everyone was out of sorts. Migwan
absent-mindedly pulled up a whole row of choice plants instead of weeds;
Gladys ran the automobile into a tree and bent up the fender; Hinpoha
slammed the door on her finger nail; Nyoda burnt her hand. Ophelia was
just dressed for the afternoon in a clean, starched white dress when she
fell into the river and had to be dressed over again from head to foot.
The whole household was too cross for words. The departure of Sahwah was
the first rupture that had ever occurred in the closely linked ranks of
the Winnebagos and they were all broken up over it.
When Mrs. Gardiner was cooking beef for supper she told Migwan to get
her some bay leaf to flavor it with. Migwan brought out the glass jar of
crushed leaves. “That’s not the bay leaf,” said her mother, and went to
look for it herself. “Here it is,” she said, bringing another glass jar
down from a higher shelf.
“Then what’s this?” asked Migwan, indicating the first jar.
“I haven’t the slightest idea,” said Mrs. Gardiner. “It was in the
pantry when we came.”
“But this was what I put into the ketchup,” said Migwan. Hastily
unscrewing the top she shook out some of the contents and tasted them.
Her mouth contracted into a fearful pucker. Never in her life had she
tasted anything so bitter.
“I did it myself,” she said, in a dazed tone. “I spoiled the ketchup
myself.” At her shout the girls came together in the kitchen to hear the
story of the mistaken ingredient.
“What can that be?” they all asked. Nobody knew. It was some dried herb
that had been left by the former mistress of the house, and a powerful
one. The girls looked at each other blankly.
“And I accused Sahwah of doing it,” said Migwan, remorsefully. “No
wonder she flared up and left us, I don’t blame her a bit. I wouldn’t
thank anyone for accusing me wrongfully of anything like that.”
“We’ll have to go after her this very evening,” said Gladys, “and bring
her back.”
“If she’ll come,” said Hinpoha, knowing Sahwah’s proud spirit.
“Oh, I’m quite willing to grovel in the dust at her feet,” said Migwan.
Gladys drove them all into town with her and they sped to the Brewster
house. It was all dark and silent. Sahwah was evidently not there. They
tried the neighbors. They all denied that she had been near the house.
They finally came to this conclusion themselves, for in the light of the
street lamp just in front of the house they could see that the porch was
covered with a month’s accumulation of yellow dust which bore no
footmarks but their own.
Here was a new problem. They had come expecting to offer profuse
apologies to Sahwah and carry her back with them to Onoway House
rejoicing, and it was a shock to find her gone. The thought of letting
her go on believing that they mistrusted her was intolerable, but how
were they going to clear matters up? Sahwah had no relatives in town,
and, of course, they did not know all her friends, so it would be hard
to find her. That is, if she had ever reached town at all. Something
might have happened to her on the way—Nyoda and Gladys sought each
other’s eyes and each thought of what had happened to them on the way to
Bates Villa.
With heavy hearts they rode back to Onoway House. The days went by
cheerlessly. A week passed since Sahwah had run away, but no word came
from her. Nyoda interviewed the conductors on the interurban car line to
find out if Sahwah had taken the car into the city. No one remembered a
girl of that description on the day mentioned. Sahwah had only one hat—a
conspicuous red one—and she would not fail to attract attention.
Thoroughly alarmed, Nyoda decided on a course of action. She called up
the various newspapers in town and asked them to print a notice to the
effect that Sahwah had disappeared. If Sahwah were in town she would see
it and knowing that they were worried about her would let them know
where she was. The notice came out in the papers, and a day or two
passed, but there was no word from Sahwah. Nyoda and Gladys made a
hurried trip to town to put the police on the track. Just before they
got to the city limits they had a blowout and were delayed some time
before they could go on. As they waited in the road another machine came
along and the driver stopped and offered assistance. Nyoda recognized a
friend of hers in the machine, a Miss Barnes, teacher in a local
gymnasium.
“Hello, Miss Kent,” she called, cheerfully, “I haven’t seen you for an
age. Where have you been keeping yourself?”
“Where have you been keeping yourself?” returned Nyoda.
“I, Oh, I’m working this summer,” replied Miss Barnes. “I’m just in town
on business. I’m helping to conduct a girls’ summer camp on the lake
shore. I thought possibly you would bring your Camp Fire group out there
this summer. One of your girls is out there now.”
“Which one?” asked Nyoda, thinking of Chapa and Nakwisi, whom she had
heard talking about going.
“One by the name of Brewster,” said Miss Barnes, “a regular mermaid in
the water. She has the girls out there standing open-mouthed at her
swimming and diving. Why, what’s the matter?” she asked, as Nyoda gave a
sigh of relief that seemed to come from her boots.
“Nothing,” replied Nyoda, “only we’ve been scouring the town for that
very girl.”
“You have?” asked Miss Barnes, with interest. “Would you like to come
out and visit her?”
“Could I?” asked Nyoda.
“Certainly,” said Miss Barnes, “come right out with me now. I’m going
back.”
And so Sahwah’s mysterious disappearance was cleared up. When the
Winnebagos, lined up in the road, saw the automobile approaching, and
that Sahwah was in it, they welcomed her back into their midst with a
rousing Winnebago cheer that warmed her to the heart. All the clouds had
been rolled away by Nyoda’s explanations and this was a triumphant
homecoming. A regular feast was spread for her, and as she ate she
related her adventures since leaving the house early that other morning.
Without forming any plan of where she was going she had walked up the
road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of the car line and then a farmer had
come along on a wagon and given her a lift. He had taken her all the way
to the other car line, three miles below Onoway House. She had come into
the city by this route. She did not want to go home for fear they would
come after her, so she went to the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As she sat in the rest room wondering what she should do next she heard
two girls talking about registering for camp. This seemed to her a
timely suggestion, and she followed them to the registration desk and
registered for two weeks. She went out that same day. When she arrived
there she did such feats in the water that they asked her if she would
not stay all summer and help teach the girls to swim. She said she
would, and so saw a very easy way out of her difficulty. The reason they
had not heard from her when they put the notice in the papers was
because they did not get the city papers in camp.
Sahwah surveyed the faces around the table with a beaming countenance.
After all, she could only be entirely happy with the Winnebagos. Migwan
and she were once more on the best of terms.
“But tell us,” said Hinpoha, now that this was safe ground to tread
upon, “what it was you put into the ketchup.”
“Oh,” said Sahwah, who now remembered all about it, “those were a couple
of cloves that were lying on the table.”
And so the last bit of mystery was cleared up.
CHAPTER IX.—OPHELIA DANCES THE SUN DANCE.
Among the other books at Onoway House there was a Manual of the
Woodcraft Indians which belonged to Sahwah, and which she was very fond
of quoting and reading to the other girls when they were inclined to
hang back at some of the expeditions she proposed. One night she read
aloud the chapter about “dancing the sun dance,” that is, becoming
sunburned from head to foot without blistering. On a day not long after
this Ophelia might have been seen standing beside the river clad only in
a thin, white slip. Stepping from the bank, she immersed herself in the
water, then stood in the sun, holding out her arms and turning up her
face to its glare. When the blazing August sunlight began to feel
uncomfortably warm on her body she plunged into the cooling flood and
then came up to stand on the bank again. She did this straight through
for two hours, and then began to investigate the result. Her arms were a
beautiful brilliant red, and the length of leg that extended out from
the slip was the same shade. She felt wonderfully pleased, and dipped in
the water again and again to cool off and then returned to the burning
process. When the dinner bell rang she returned to the house, eager to
show her achievement. But she did not feel so enthusiastic now as when
she first beheld her scarlet appearance. Something was wrong. It seemed
as if she were on fire from head to foot. She looked at her arms. They
were no longer such a pretty red; they had swelled up in large, white
blisters. So had her legs. She could hardly see out of her eyes.
“Ophelia!” gasped the girls, when she came into the house. “What has
happened? Have you been scalded?”
“I’ve been doing your old Sun Dance,” said Ophelia, painfully.
Never in all their lives had they seen such a case of sunburn. Every
inch of her body was covered with blisters as big as a hand. The sun had
burned right through the flimsy garment she wore. There was a pattern
around her neck where the embroidery had left its trace. She screamed
every time they tried to touch her. Nyoda worked quickly and deftly and
the luckless sun dancer was wrapped from head to foot in soft linen
bandages until she looked like a mummy.
Sahwah sought Nyoda in tribulation. “Was it my fault,” she asked, “for
reading her that book? She never would have thought of it if I hadn’t
given her the idea.”
“No,” answered Nyoda, “it wasn’t your fault. It said emphatically in the
book that the coat of tan should be acquired gradually. You couldn’t
foresee that she would stand in the sun that way. So don’t worry about
it any longer.”
“Still, I feel in a measure responsible,” said Sahwah, “and I ought to
be the one to take care of her. Let me sleep in the room with her
to-night and get up if she wants anything.” Sahwah’s desire to help was
so sincere that she insisted upon being allowed to do it, and took upon
herself all the care of the sunburned Ophelia, which was no small job,
for the pain from the blisters made her frightfully cross.
Nyoda was surprised to see Sahwah keeping at it with such persistent
good nature and apparent success, for as a rule she was not a good one
to take care of the sick; she was in too much of a hurry. She would
generally spill the water when she was trying to give a drink to her
patient, or fall over the rug, or drop dishes; and the effect she
produced was irritating rather than soothing. But in this case she
seemed to be making a desperate effort to do things correctly so she
would be allowed to continue, and fetched and carried all the afternoon
in obedience to Ophelia’s whims. She read her stories to while away the
painful hours and when supper time came made her a wonderful egg salad
in the form of a water lily, and cut sandwiches into odd shapes to
beguile her into eating them. When evening came and Ophelia was restless
and could not go to sleep she sang to her in her clear, high voice,
songs of camp and firelight. One by one the Winnebagos drifted in and
joined their voices to hers in a beautifully blended chorus.
“Gee, that’s what it must be like in heaven,” sighed the child of the
streets, as she listened to them. The Winnebagos smiled tenderly and
sang on until she dropped off to sleep.
Sahwah slept with one eye open listening for a call from Ophelia. She
heard her stirring restlessly in the night and went over and sat beside
her. “Can’t you sleep?” she asked.
“No,” complained Ophelia. “Say, will you tell me that story again?”
Sahwah began,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little girl and she had a
fairy godmother——”
“What’s a fairy godmother?” interrupted Ophelia.
“Oh,” said Sahwah, “it’s somebody who looks after you especially and is
very good to you and grants all your wishes, and always comes when
you’re in trouble——”
“Who’s my fairy godmother?” demanded Ophelia.
“I don’t know,” said Sahwah.
“I bet I haven’t got any!” said Ophelia, suspiciously. “I didn’t have a
father and mother like the rest of the kids and I bet I haven’t got any
fairy godmother either.”
“Oh, yes, you have,” said Sahwah to soothe her, “you have one only you
haven’t seen her yet. Wait and she’ll appear.” But Ophelia lay with her
face to the wall and said no more. “Would you like me to bring you a
drink?” asked Sahwah, a few minutes later. Ophelia replied with a nod
and Sahwah went down to the kitchen. There was no drinking water in
sight and Sahwah hesitated about going out to the well at that time of
the night. Then she remembered that a pail of well water had been taken
down cellar that evening to keep cool. Taking a light she descended the
cellar stairs. When she was nearly to the bottom she heard a subdued
crash, like a basket of something being thrown over, followed by a
series of small bumping sounds. She stood stock still, afraid to move
off the step.
Then, summoning her voice, she cried, “Who is down there?” No answer
came from the darkness below. After that first crash there was not
another sound. Sahwah was not naturally timid, and her one explanation
for all night noises in a house was rats. Besides, she had started after
water for Ophelia, and she meant to get it. She went down stairs and
looked all around with her light. She soon found the thing which had
made the noise. It was a basket of potatoes which had fallen over and as
the potatoes rolled out on the cement floor they had made those odd
little after noises which had puzzled her. Satisfied that nobody was in
the house she took her pail of water and went up-stairs, glad that she
had not roused the house and brought out a laugh against herself.
She gave Ophelia the drink, and being feverish she drank it eagerly and
murmured gratefully, “I guess you’re my fairy godmother.” As Sahwah
turned to go to bed Ophelia thrust out a bandaged hand and caught hold
of her gown. “Stay with me,” she said, and Sahwah sat down again beside
the bed until Ophelia fell asleep. Sahwah felt pleased and elated at
being chosen by Ophelia as the one she wanted near her. It was not often
that a child singled Sahwah out from the group as an object of
affection; they usually went to Gladys or Hinpoha. So she responded
quickly to the advances made by Ophelia and thenceforth made a special
pet of her, taking her part on all occasions.
Soon after Ophelia’s experience with sunburn a rainy spell set in which
lasted a week. Every day they were greeted by grey skies and a steady
downpour, fine for the parched garden, but hard on amusements. They
played card games until they were weary of the sight of a card; they
played every other game they knew until it palled on them, and on the
fifth day of rain they surrounded Nyoda and clamored for something new
to do. Nyoda scratched her head thoughtfully and asked if they would
like to play Thieves’ Market.
“Play what?” asked Gladys.
“Thieves’ Market,” said Nyoda. “You know in Mexico there is an
institution known as the Thieves’ Market, where stolen goods are sold to
the public. We will not discuss the moral aspect of the business, but I
thought we could make a game out of it. Let’s each get a hold of some
possession of each one of the others’ without being seen and put a price
on it. The price will not be a money value, of course, but a stunt. The
owner of the article will have first chance at the stunt and if she
fails the thing will go to whoever can buy it. If anyone fails to get a
possession from each one of the rest to add to the collection she can’t
play, and if she is seen by the owner while ‘stealing’ it she will have
to put it back. We’ll hold the Thieves’ Market to-night after supper in
the parlor and I’ll be storekeeper.”
The Winnebagos, always on the lookout for something novel and
entertaining, seized on the idea with rapture. The rain was forgotten
that afternoon as they scurried around the house trying to seize upon
articles belonging to the oth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trying valiantly
to guard their own possessions. It was not hard to get Sahwah’s things,
for she had a habit of leaving them lying all over the house. Her red
hat had fallen a victim the first thing; likewise her shoes and tennis
racket. It was harder to get anything away from Nyoda, for she seemed to
be Argus eyed; but providentially she was called to the telephone, and
while she was talking they made their raid.
When opened, the Thieves’ Market presented such a conglomeration of
articles that at first the girls could only stand and wonder how those
things had ever been taken away from them without their knowing it, for
many of them were possessions which were usually hidden from sight while
the owners fondly believed that their existence was unknown. Migwan gave
a cry of dismay when she beheld her “Autobiography,” which she was
carefully keeping a secret from the rest, out in full view on the table.
“How did you ever find it?” she gasped. “It was folded up in my
clothes.”
But Migwan’s embarrassment was nothing compared to Nyoda’s when she
caught sight of a certain photograph. She blushed scarlet while the
girls teased her unmercifully. It was a picture of Sherry, the serenader
of the camp the summer before. Until they found the photograph the girls
did not know that Nyoda was corresponding with him. And the prices on
the various things were the funniest of all. The girls had come down
that evening dressed in their middies and bloomers for they had a
suspicion that there would be some acrobatic stunts taking place, and it
was well that they did. To redeem her hat Sahwah had to stand on her
head and to get her bedroom slippers Gladys had to jump through a hoop
from a chair. Hinpoha had to wrestle with Nyoda for the possession of
her paint box, and the price of Betty’s shoes was to throw them over her
shoulder into a basket. At the first throw she knocked a vase off the
table, but luckily it did not break, and she was warned that another
accident would result in her going shoeless. Migwan tremblingly
approached the Autobiography to find out the price. It was “Read one
chapter aloud.” “I won’t do it,” said Migwan, flatly.
“Next customer,” cried Nyoda, pounding with her hammer. “For the simple
price of reading aloud one chapter I will sell this complete
autobiography of a pious life, profusely illustrated by the author.”
Sahwah hastened up to “buy” the book, but Migwan headed her off in a
hurry and read the first chapter with as good grace as she could, amid
the cheers and applause of the other customers. Sahwah made a grimace
when she had to polish the shoes of everyone present to get her shoe
brush back.
Thus the various articles in the Thieves’ Market were disposed of amid
much laughter and merry-making, until there remained but one article, a
cold chisel. Nyoda went through the usual formula, offering it for sale,
but no one came to claim it. She redoubled her pleas, but with the same
result. “For the third and last time I offer this great bargain in a
cold chisel for the simple price of jumping over three chairs in
succession,” she said, with a flourish. Nobody appeared to be anxious to
redeem their property. “Whose is it?” she asked, mystified.
It apparently belonged to no one. “It’s yours, Gladys,” said Sahwah, “I
stole it from you.”
“Mine?” asked Gladys, in surprise. “I don’t own any chisel. Where did
you get it from?”
“Out of the automobile,” answered Sahwah.
“But it doesn’t belong there,” said Gladys. “There’s no chisel among the
tools. You’re joking, you found it somewhere else.”
“No, really,” said Sahwah, “I found it in the car this afternoon.”
“Mother,” called Migwan, “were there any tools left in the barn by Mr.
Mitchell?”
“Nothing but the garden tools,” answered her mother. Tom also denied any
knowledge of the chisel.
“Girls,” said Nyoda, seriously, “there is something going on here that I
do not understand. First Migwan thought she heard footsteps in the
attic; then a ghost appeared to me in the tepee; one night we saw a man
running out of the barn, and later on that night Migwan claims to have
run into a man in the garden. Soon afterward Hinpoha was sure she heard
footsteps in the attic, and when we went up we found the window broken.
Just a few nights ago a basket of potatoes was mysteriously knocked over
in the cellar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now we find a chisel in
the automobile which does not belong to us. It looks for all the world
as if somebody were trying to break into this house, in fact, has broken
in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
Migwan shrieked and covered up her ears. “A mystery!” said Sahwah,
theatrically. “How thrilling!” The interest in the Thieves’ Market died
out before this new and alarming idea.
“It may be only a remarkable series of co-incidences,” said Nyoda,
seeing the fright of the girls, “but it certainly looks suspicious. That
window may possibly have been broken by the wind during the storm, and
the footsteps may have been rats or Mrs. Waterhouse’s ghost, and the
ghost in the tepee may have been a practical joker, but baskets of
potatoes do not fall over of their own accord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cold chisels don’t grow in automobiles. There’s something wrong and
we ought to find out what it is.”
“Oh, I’ll never go up-stairs alone again,” shuddered Migwan. “Sahwah,
how did you ever dare go down cellar in the dark after you heard that
noise?” And she shivered violently at the very thought.
“Tom, can you handle a gun?” asked Nyoda.
“Yes,” answered Tom.
“I’m going to buy a little automatic pistol to-morrow,” said Nyoda, “and
teach everyone of you girls how to shoot it.”
“I wonder if we hadn’t better try to get Calvin Smalley to sleep in the
house,” said Migwan.
“I can take care of you,” said Tom, proudly. Nothing else was talked of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evening and when bed time came there was a
general reluctance to become separated from the rest of the household.
But, although they listened for footsteps in the attic they heard
nothing, and the night passed away peacefully.
The next night the ghost became active again. Whether it was the same
one or a different one they did not find out, however, for they did not
see it this time, only heard it. Just about bed time it was, a strange,
weird moaning sound that filled the house and echoed through the big
halls. Whether it proceeded from the basement or the attic they were
unable to make out; it seemed to come from everywhere and nowhere.
Migwan clung close to her mother and trembled. The sound rang out again,
more weird than before. It was bloodcurdling. Nyoda opened the window
and fired several shots into the air. The moaning sound stopped abruptly
and was heard no more that night, but sleep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The
girls were too excited and fearful. The next day Mrs. Gardiner advised
everybody to hide their valuables away. The peaceful life at Onoway
House was broken up. The household lived in momentary expectation of
something happening. “And this is the quiet of the country,” sighed
Migwan, “where I was to grow fat and strong. I’m worn to a frazzle
worrying about this mystery.”
“So’m I,” said Gladys.
“And I’m getting thin,” said Hinpoha, which brought out a general laugh.
“Not so you could notice it,” said Sahwah. Whereupon Hinpoha tried to
smother her with a pillow and the two rolled over on the bed,
struggling.
As if worrying about a burglar were not enough, Sahwah and Gladys had
another exciting experience one day that week. If we were to stretch a
point and trace things back to their beginnings it was the fault of the
Winnebagos themselves, for if they hadn’t gone horseback riding that
day—— Well, Farmer Landsdowne came over in the morning and said he had a
pair of horses which were not working and if they wanted to go horseback
riding now was their chance. The girls were delighted with the idea and
flew to don bloomers. None of them had ever ridden before and excitement
ran high. Naturally there were no saddles, for Farmer Landsdowne’s
horses were not ridden as a general rule, and the girls had to ride
bareback.
“It feels like trying to straddle a table,” said Migwan, marveling at
the width of the horse she was on. “My legs aren’t half long enough.”
She clung desperately to his mane as he began to trot and she began to
slide all over him. “He’s so slippery I can’t stick on,” she gasped. The
horse stopped abruptly as she jerked on the reins and she slid off as if
he had been greased, and landed in the soft grass beside the road.
“Here, let me try,” said Sahwah, impatient for her turn. “He isn’t
either slippery,” she said, when she got on, “he’s bony, horribly bony.
He’s just like knives.” She jolted up and down a few times on his hip
bones and an idea jolted into her head. Getting off she ran into the
house and came out again with a sofa pillow, which she proceeded to tie
on his back. Then she rode in comparative comfort, amid the laughter of
the girls.
Calvin Smalley, who happened to be working out in front and saw her ride
past, doubled up with laughter over his vegetable bed. “What next?” he
chuckled. “What next?” He was still thinking about this and laughing
over it when he went through the empty field which Sahwah had crossed
the time she had discovered the house among the trees, and where Abner
Smalley now pastured his bull. So absorbed was he in the memory of that
ridiculous pillow tied on the horse that he was not careful in putting
up the bars behind him when he left the field, and later in the
afternoon the bull wandered over in that direction and came through into
the next field. He found the river road and followed it and began to
graze in one of the unploughed fields belonging to Onoway House.
Sahwah, wearing her big, red hat, was bending low over the ground,
digging up some ferns which grew there, when all of a sudden she heard a
loud snort and looked up to see the bull charging down upon her. She
looked wildly around for a place of safety. Nothing was nearer than the
far-off hedge that surrounded the cultivated garden patch. Not a tree,
not a fence, in sight. Quick as light she bounded off toward the hedge,
although she knew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her to reach it before the
bull would be upon her.
Gladys, coming along the road in the automobile, heard a shriek and
looked up to see Sahwah tearing across the open field with the bull hard
after her. Without a moment’s hesitation Gladys turned the car into the
field and started after the bull at full speed. She let the car out
every notch and it whizzed dizzily over the hard turf. She sounded the
horn again and again with the hope of attract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bull, but he did not pause. Like lightning she bore down upon him,
passed to one side and slowed down for a second beside Sahwah, who
jumped on the running-board and was borne away to safety.
“This hum-drum, uneventful life,” said Sahwah, as she sat on the porch
half an hour afterward and tried to catch her breath, while the rest
fanned her with palm leaf fans, “is getting a little too much for me!”
CHAPTER X.—A BIRTHDAY PARTY
After Nyoda had fired the shots out of the window, nothing was heard or
seen of the ghost and the footsteps in the attic ceased. “It’s just as I
thought,” said Nyoda, “someone has been trying to frighten us with a
possible view of robbing the house at some time, thinking that a
houseful of women would be terror-stricken at the ghostly noises, but
when he found we had a gun and could shoot he thought better of the
plan.” Gradually the girls lost their fright, and the odd corners of
Onoway House regained their old charm. They were far too busy with the
canning to think of much else, for the tomatoes were ripening in such
large quantities that it was all they could do to dispose of them. The
4H brand found favor and the market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every week
Migwan had a goodly sum to deposit in the bank after the cost of the tin
cans had been deducted.
“I have to laugh when I think of that honor in the book,” said Migwan,
“can at least three cans of fruit,” and she pointed to the cans stacked
on the back porch ready to be packed into the automobile and taken to
town. “Why, hello, Calvin,” she said, as Calvin Smalley appeared at the
back door. “Come in.” Calvin came in and sat down. “What’s the matter?”
asked Migwan, for his face had a frightened and distressed look.
“Uncle Abner has turned me out!” said Calvin.
“Turned you out!” echoed the girls. “Why?”
“He showed me a will last night,” said Calvin, “a later one than that
which was found when my grandfather died, which left the farm to him
instead of to my father. He just found it last night when he was
rummaging among grandfather’s old papers. According to that I have been
living on his charity all these years instead of on my own property as I
supposed and now he says he can’t afford to keep me any longer. He
wanted me to sign a paper saying that I would work for him without pay
until I was thirty years old to make up for what I have had all these
years, and when I wouldn’t do it he told me to get out.”
“How can any man be so mean and stingy!” said Migwan, indignantly.
“And what do you intend to do now?” asked Mrs. Gardiner.
“I don’t know,” said Calvin, looking utterly downcast and discouraged.
“I had expected to go through school and then to agricultural college
and be a scientific farmer, but that’s out of the question now. I
haven’t a cent in the world. I could hire out to some of the farmers
around here, I suppose, but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they wouldn’t pay
me much because I’m a boy, but they would get a man’s work out of me and
it’s precious little time I’d have for school. I’ve always saved Uncle
Abner the cost of one hired man in return for what he gave me, so I
don’t feel under any obligations to him. I think I’ll give up farming
for a while and go to the city and work. The trouble is I have no
friends there and it might be hard for me to get into a good place.” His
honest eyes were clouded over with perplexity and trouble.
“My father could probably get you a job in the city,” said Gladys, “if
you can wait until he gets back. He’s out west now.”
“I tell you what to do,” said kind-hearted Mrs. Gardiner to Calvin, “you
stay here with us until Mr. Evans comes back. You can help the girls in
the garden, and we were wishing not long ago that we had another man in
the house.”
“You are very kind,” said Calvin, gratefully, “but I don’t want to put
you to any trouble.”
“No trouble at all,” Mrs. Gardiner assured him, “you can sleep with
Tom.” The girls all expressed pleasure at the prospect of having Calvin
stay at Onoway House and under the spell of their kindly hospitality his
drooping spirits revived. He shook the dust of his uncle’s house from
his feet, feeling no longer an outcast, since he had suddenly found such
kind friend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hedge.
Calvin lived in a perpetual state of wonder at the girls at Onoway
House. They made a frolic out of everything they did and were
continually thinking up new and amazing games to play. Calvin had never
done anything at home all his life but work, and work was a serious
business to him. He never knew before that work was fun. The long, weary
hours of peeling were enlivened with songs made up 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 Sahwah would look up from the pan over which she was bending,
and sing to the tune of “The Pope”:
“Our Migwan leads a jolly life, jolly life,
She peels tomatoes with her knife, with her knife,
And puts the pieces in the can,
And leaves the peelings in the pan, (Oh, tra la la).”
And then they would all start to sing at once,
“The tomatoes went in one by one,
(There’s one more bushel to peel),
Hinpoha she did cut her thumb,
(There’s one more bushel to peel).”
“The tomatoes went in two by two,
And Gladys and Sahwah fell into the stew.
The tomatoes went in three by three,
And Migwan got drowned a-trying to see.”
etc., etc., thus they made merry over the work until it was done.
“Do you know,” said Migwan, looking up from her peeling, “that it’s
Gladys’s birthday next Friday? We ought to have a celebration.”
“How about a picnic?” asked Nyoda. “We haven’t had a real one yet. Have
the rest of the Winnebagos come out from town and all of us sleep in the
tepee as we had planned on the Fourth of July. Then we’ll get a horse
and wagon and drive along the roads until we come to a place beside the
river where we want to stop and cook our dinner and just spend the day
like gypsies.” The girls entered into the plan with enthusiasm, both for
the sake of celebrating Gladys’s birthday and cheering up Calvin, who
had been rather quiet and pensive of late. It was a great disappointment
to him to have to give up his plans for going to college, and his
uncle’s unfriendly treatment of him had cut him to the heart.
Medmangi and Chapa and Nakwisi arrived the day before the picnic and the
house echoed with the sound of voices and laughter, as the Winnebagos
bubbled over with joy at being all together. The morning of the picnic
was as fine as they could wish, and it was not long before they were
bumping over the road in one of Farmer Landsdowne’s wagons, behind the
very two horses which the girls had ridden the week before. It was a
wagon full. Sahwah sat up in front and drove like a veritable daughter
of Jehu, with Farmer Landsdowne up beside her to come to the rescue in
case the horses should run away, which was not at all likely, as it took
constant persuasion to keep them going even at an easy jog trot. Mrs.
Landsdowne, who, with her husband, had been invited to the picnic, sat
beside Mrs. Gardiner, in the back of the wagon, while Calvin Smalley
stayed next to Migwan, as he usually did. She was so quiet and gentle
and kind that he felt more at ease with her than with the rest of the
Winnebagos, who were such jokers. Ophelia, who was beginning to be
inseparable from Sahwah, squeezed herself in between her and Mr.
Landsdowne, and refused to move. Sahwah, of course, took her part and
let her stay, although she was a bit crowded for space. Hinpoha and
Gladys sat at the back of the wagon dangling their feet over the end,
where they could watch the yellow road unwinding like a ribbon beneath
them, while Nyoda sat between Betty and Tom to keep the peace.
“Where are we going?” asked Mrs. Gardiner, as they swung along the road.
“Oh,” replied Sahwah, “somewhere, anywhere, everywhere, nowhere. It’s
lots more romantic to start out without any idea where you’re going and
stop wherever it suits you than to start out for a certain place and
think you have to go there even if you pass nicer places o
one called ‘Jerry’s Sister.’ But you have really spoiled it in the
development. It takes a person familiar with the production of a film to
direct the movements of the actors intelligently. If Mr. Larue, for
example, had developed that piece it would be a very good one. Would you
be willing to sell just the idea, if Mr. Larue thinks he can use it?”
Migwan had never thought of this before. “Why, yes,” she said, “I
suppose I would. It’s certainly no good to me as it is.”
“Let me take it to Mr. Larue,” said Miss Mortimer. “I’m sure he will see
the possibilities in it just as I have.” Migwan was in a transport of
delight to think that her idea at least had found favor with Miss
Mortimer. Miss Mortimer was as good as her word and showed the play to
Mr. Larue and he agreed with her that it could be developed into a
side-splitting farce comedy. Migwan was more intoxicated with that first
sale of the labors of her pen than she was at any future successes,
however great. Deeply inspired by this recognition of her talent, she
evolved an exciting plot from the incidents which had just occurred,
namely, the mistaking of the moving picture company for the Venoti gang.
She kept it merely in plot form, not trying to develop it, and Mr. Larue
accepted this one also. After this second success, even though the price
she received for the two plots was not large, the future stretched out
before Migwan like a brilliant rainbow, with a pot of gold under each
end.
Miss Mortimer soon discovered that the Winnebagos were a group of Camp
Fire Girls, and she immediately had an idea. When “The Honor of a
Soldier” was finished Mr. Larue was going to produce a piece which
called for a larger number of people than the company contained, among
them a group of Camp Fire Girls. He intended hiring a number of “supers”
for this play. “Why not hire the Winnebagos?” said Miss Mortimer. And so
it was arranged. Medmangi and Nakwisi and Chapa, the other three
Winnebagos, were notified to join the ranks, and excitement ran high. To
be in a real moving picture! It is true that they had nothing special to
do, just walk through the scene in one place and sit on the ground in a
circle in another, but there was not a single girl who did not hope that
her conduct on that occasion would lead Mr. Larue into hiring her as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company.
Especially Sahwah. The active, strenuous life of a motion picture
actress attracted her more than anything just now. She longed to be in
the public eye and achieve fame by performing thrilling feats. She saw
herself in a thousand different positions of danger, always the heroine.
Now she was diving for a ring dropped into the water from the hand of a
princess; now she was trapped in a burning building; now she was riding
a wild horse. But always she was the idol of the company, and the idol
of the moving picture audiences, and the envy of all other actresses.
She would receive letters from people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her
picture would be in the papers and in the magazines, and her name would
be featured on the colored posters in front of the theatres. Managers
would quarrel over her and she would be offered a fabulous salary. All
this Sahwah saw in her mind’s eye as the future which was waiting for
her, for since meeting Miss Mortimer she really meant to be a motion
picture actress when she was through school. She felt in her heart that
she could show people a few things when it came to feats of action. She
simply could not wait for the day when the Winnebagos were to be in the
picture. When the play was produced in the city theatres her friends
would recognize her, and Oh joy!—here her thoughts became too gay to
think.
The play in question was staged, not on the Centerville road, but in one
of the city parks, where there were hills and formal gardens and an
artificial lake, which were necessary settings. The day arrived at last.
News had gone abroad that a motion picture play was to be staged in that
particular park and a curious crowd gathered to watch the proceedings.
Sahwah felt very splendid and important as she stood in the company of
the actors. She knew that the crowd did not know that she was just in
that one play as a filler-in; to them she was really and truly a member
of this wonderful company—a real moving picture actress. Gazing over the
crowd with an air of indifference, she suddenly saw one face that sent
the blood racing to her head. That was Marie Lanning, the girl whom
Sahwah had defeated so utterly in the basketball game the winter before,
and who had tried such underhand means to put her out of the game.
Sahwah felt that her triumph was complete. Marie was just the kind of
girl who would nearly die of envy to see her rival connected with
anything so conspicuous.
The picture began; progressed; the time came for the march of the Camp
Fire Girls down the steep hill. Sahwah stood straight as a soldier; the
supreme moment had come. Now Mr. Larue would see that she stood out from
all the other girls in ability to act; that moment was to be the making
of her fortune. She glanced covertly at Marie Lanning. Marie had
recognized her and was staring at her with unbelieving, jealous eyes.
The march began. Sahwah held herself straighter still, if that were
possible, and began the descent. It was hard going because it was so
steep, but she did not let that spoil her upright carriage. She was just
in the middle of the line, which was being led by Nyoda, and could see
that the girls in front of her were getting out of step and breaking the
unity of the line in their efforts to preserve their balance. Not so
Sahwah. She saw Mr. Larue watching her and she knew he was comparing her
with the rest. Her fancy broke loose again and she had a premonition of
her future triumphs. The sight of the camera turned full on her gave her
a sense of elation beyond words. It almost intoxicated her. Halfway down
the hill Sahwah, with her head full of day-dreams, stepped on a loose
stone which turned under her foot, throwing her violently forward. She
fell against Hinpoha, who was in front of her. Hinpoha, utterly
unprepared for this impetus from the rear, lost her balance completely
and crashed into Gladys. Gladys was thrown against Nyoda, and the whole
four of them went down the hill head over heels for all the world like a
row of dominoes.
Down at the bottom of the hill stood the hero and heroine of the piece,
namely, Miss Mortimer and Chambers, the leading man, and as the
landslide descended it engulfed them and the next moment there was a
heap of players on the ground in a tangled mass. It took some minutes to
extricate them, so mixed up were they. Mr. Larue hastened to the spot
with an exclamation of very excusable impatience. Several dozen feet of
perfectly good film had been spoiled and valuable time wasted. The
players got to their feet again unhurt, and the watching crowd shouted
with laughter. Sahwah was ready to die of chagrin and mortification. She
had spoiled any chances she had ever had of making a favorable
impression on Mr. Larue; but this was the least part of it. There in the
crowd was Marie Lanning laughing herself sick at this fiasco of Sahwah’s
playing. Good-natured Mr. Chambers was trying to soothe the
embarrassment of the Winnebagos and make them laugh by declaring he had
lost his breath when he was knocked over and when he got it back he
found it wasn’t his, but Sahwah refused to be comforted. She had
disgraced herself in the public eye. Breaking away from the group she
ran through the crowd with averted face, in spite of calls to come back,
and kept on running until she had reached the edge of the park and the
street car line. Boarding a car, she went back to Onoway House, wishing
miserably that she had never been born, or had died the winter before in
the coasting accident. Her ambition to be a motion picture actress died
a violent death right then and there. So the march of the Camp Fire
Girls had to be done over again without Sahwah, and was consummated this
time without accident.
When Sahwah reached Onoway House she wished with all her heart that she
hadn’t come back there. She had done it mechanically, not knowing where
else to go. At the time her only thought had been to get away from the
crowd and from Mr. Larue; now she hated to face the Winnebagos. She was
glad that no one was at home, for Mrs. Gardiner had taken Betty and Tom
and Ophelia to see the play acted. As she went around the back of the
house she came face to face with Mr. Smalley, who was just going up on
the back porch. He seemed just as surprised to see her as she was to see
him, so Sahwah thought, but he was friendly enough and asked if the
Gardiners were at home. When Sahwah said no, he said, “Then possibly
they wouldn’t mind if you gave me what I wanted. I came over to see if
they would lend me their wheel hoe, as mine is broken and will have to
be sent away to be fixed, and I have a big job of hoeing that ought to
be done to-day.” Sahwah knew that Migwan would not refuse to do a
neighborly kindness like that as long as they were not using the tool
themselves, and willingly lent it to him.
She was still in great distress of mind over the ridiculous incident of
the morning and did not want to see the other girls when they came home.
So taking a pillow and a book, she wandered down the river path to a
quiet shady spot among the willows and spent the afternoon in solitude.
When the other girls returned home Sahwah was nowhere to be found. This
did not greatly surprise them, however, for they were used to her
impetuous nature and knew she was hiding somewhere. Hinpoha and Gladys
were up-stairs removing the dust of the road from their faces and hands
when they heard a stealthy footstep overhead. “She’s hiding in the
attic!” said Hinpoha.
“She’ll melt up there,” said Gladys, “it must be like an oven. Let’s
coax her down and don’t any of us say a word about the play. She must
feel terrible about it.”
So it was agreed among the girls that no mention of Sahwah’s mishap
should be made, and Hinpoha went to the foot of the attic stairs and
called up: “Come on down, Sahwah, we’re all going out on the river.”
There was no answer. Hinpoha called again: “Please come, Sahwah, we need
you to steer the raft.” Still no answer. Hinpoha went up softly. She
thought she could persuade Sahwah to come down if none of the others
were around. But when she reached the top of the stairs there was no
sign of Sahwah anywhere. The place was stifling, and Hinpoha gasped for
breath. Sahwah must be hiding among the old furniture. Hinpoha moved
things about, raising clouds of dust that nearly choked her, and calling
to Sahwah. No answer came, and she did not find Sahwah hidden among any
of the things. Gladys came up to see what was going on, followed by
Migwan.
“She doesn’t seem to be up here after all,” said Hinpoha, pausing to
take breath. “It’s funny; I certainly thought I heard someone up here.”
“Don’t you remember the time I thought I heard someone up here in the
night and you said it was the noise made by rats or mice?” asked Migwan.
“It was probably that same thing again.”
“It must have been,” said Hinpoha.
“Maybe it was the ghost of that Mrs. Waterhouse, who died before she had
her attic cleaned, and comes back to move the furniture,” said Gladys.
In spite of its being daylight an unearthly thrill went through the
veins of the girls. The whole thing was so mysterious and uncanny.
Migwan was looking around the attic. “Who broke that window?” she asked,
suddenly. The side window, the one near the Balm of Gilead tree, was
shattered and lay in pieces on the floor.
“It wasn’t broken the day we brought Miss Mortimer up,” said Gladys. “It
must have happened since then.”
“There must have been someone up here to-day,” said Migwan. “Do you
suppose—” here she stopped.
“Suppose what?” asked Hinpoha.
“Do you suppose,” continued Migwan, “that Sahwah was up here and broke
it accidentally and is afraid to show herself on account of it?”
“Maybe,” said Hinpoha, “but Sahwah’s not the one to try to cover up
anything like that. She’d offer to pay for the damage and it wouldn’t
worry her five minutes.”
“It may have been broken the night of the storm,” said Nyoda, who had
arrived on the scene. “If I remember rightly, we opened it when Miss
Mortimer was up here, and as it is only held up by a nail and a rope
hanging down from the ceiling, it could easily have been torn loose in
such a wind as that and slammed down against the casement and broken. We
were so excited trying to cover up the plants that we did not hear the
crash, if indeed, we could have heard it in that thunder at all.”
This seemed such a plausible explanation that the girls accepted it
without question and dismissed the matter from their minds. Descending
from the hot attic they went out on the river on the raft. As it drew
near supper time they feared that Sahwah would stay away and miss her
supper, and they knew that she would have to show herself sometime, so
they determined to have it over with so Sahwah could eat her supper in
peace. On the path along the river they found her handkerchief and knew
that she was somewhere near the water. They called and called, but she
did not answer. “I know what will bring her from her hiding-place,” said
Nyoda. She unfolded her plan and the girls agreed. They poled the raft
back to the landing-place and got on shore. Then they set Ophelia on the
raft all alone and sent it down-stream, telling her to scream at the top
of her voice as if she were frightened. Ophelia obeyed and set up such a
series of ear-splitting shrieks as she floated down the river that it
was hard to believe that she was not in mortal terror. The scheme worked
admirably. Sahwah heard the screams and peered through the bushes to see
what was happening. She saw Ophelia alone on the raft and no one else in
sight, and thought, of course, that she was afraid and ran out to
reassure her. She took hold of the tow line and pulled the raft back to
the landing-place.
“Whatever made you so scared?” she asked, as Ophelia stepped on terra
firma.
“Pooh, I wasn’t scared at all,” said Ophelia, grandly. “They told me to
scream so you’d come out.” So Sahwah knew the trick that had been
practised on her, but instead of being pleased to think that the girls
wanted her with them so badly she was more irritated than before. There
was no further use of hiding; she had to go into the house now and eat
her supper with the rest. The meal was not such a trial for her as she
had anticipated, because no one mentioned the subject of moving
pictures, or acted as if anything had happened at all. After supper
Nyoda brought out a magazine showing pictures of the Rocky Mountains and
the girls gave this their strict attention. Nyoda read aloud the
descriptions that went with the pictures. In one place she read: “The
barren aspect of the hillside is due to a landslide which swept
everything before it.”
At this Migwan’s thoughts went back to the scene on the hillside that
day, when the human landslide was in progress. Now Migwan, in spite of
her serious appearance, had a sense of humor which at times got the
upper hand of her altogether. The memory of those figures rolling down
the hill was too much for her and she dissolved abruptly into hysterical
laughter. She vainly tried to control it and buried her face in her
handkerchief, but it was no use. The harder she tried to stop laughing
the harder she laughed. “Oh,” she gasped, “I never saw anything so funny
as when you rolled against Miss Mortimer and Mr. Chambers and knocked
them off their feet.”
After Migwan’s hysterical outburst the rest could not restrain their
laughter either, and Sahwah became the butt of all the humorous remarks
that had been accumulating in the minds of the rest. If it had been
anyone else but Migwan who had started them off, Sahwah would possibly
have forgiven that one, but since selling her two plots to Mr. Larue
Migwan had been holding her head pretty high. That Migwan had succeeded
in her end of the motion picture business when she had failed in hers
galled Sahwah to death and she fancied that Migwan was trying to “rub it
in.”
“I hope everything I do will cause you as much pleasure,” she said
stiffly. “I suppose nothing could make you happier than to see me do
something ridiculous every day.” Sahwah had slipped off her balance
wheel altogether.
Migwan sobered up when she heard Sahwah’s injured tone. She never
dreamed Sahwah had taken the occurrence so much to heart. It was not her
usual way. “Please don’t be angry, Sahwah,” she said, contritely. “I
just couldn’t help laughing. You know how light headed I am.”
But Sahwah would have none of her apology. “I’ll leave you folks to have
as much fun over it as you please,” she said coldly, rising and going
up-stairs.
Migwan was near to tears and would have gone after her, but Nyoda
restrained her. “Let her alone,” she advised, “and she’ll come out of it
all the sooner.”
Sahwah was herself again in the morning as far as the others were
concerned, but she still treated Migwan somewhat coldly and it was
evident that she had not forgiven her.
CHAPTER VIII.—A CANNING EPISODE.
Three times every week Migwan had been making the trip to town with a
machine-load of vegetables, which was disposed of to an ever growing
list of customers. Thanks to the early start the garden had been given
by Mr. Mitchell, and the constant care it received at the hands of
Migwan and her willing helpers, Migwan always managed to bring out her
produce a day or so in advance of most of the other growers in the
neighborhood and so could command a better price at first than she could
have if she had arrived on the scene at flood tide. After every trip
there was a neat little sum to put in the old cocoa can which Migwan
used as a bank until there was enough accumulated to make a real bank
deposit. The asparagus had passed beyond its vegetable days and had
grown up in tall feathery shoots that made a pretty sight as they stood
in a long row against the fence. The new strawberry plants had taken
root and were growing vigorously; the cucumbers were thriving like fat
babies. The squashes and melons were running a race, as Sahwah said, to
see which could hold up the most fruit on their vines; the corn-stalks
stood straight and tall, holding in their arms their firstborn, silky
tassel-capped children, like proud young fathers.
But it was the tomato bed in which Migwan’s dearest hopes were bound up.
The frames sagged with exhaustion at the task of holding up the weight
of crimsoning globes that hung on the vines. Migwan tended this bed as a
mother broods over a favorite child, fingering over the leaves for
loathsome tomato worms, spraying the plants to keep away diseases, and
cultivating the ground around the roots. All suckers were ruthlessly
snipped off as soon as they grew, so that the entire strength of the
plants could go into the ripening of tomatoes. For it was on that tomato
bed that Migwan’s fortune depended. While the proceeds from the
remainder of the garden were gratifying, they were not great enough to
make up the sum which Migwan needed to go to college, as the vegetables
were not raised in large enough quantities. Migwan carefully estimated
the amount she would realize from the sale of the tomatoes and found
that it would not be large enough, and decided she could make more out
of them by canning them. At Nyoda’s advice the Winnebagos formed
themselves into a Canning Club, which would give them the right to use
the 4H label, which stood for Head, Hand, Health and Heart, and was
recognized by dealers in various places. According to the methods of the
Canning Club they canned the tomatoes in tin cans, with tops neatly
soldered on. After an interview with various hotels and restaurants in
the city Nyoda succeeded in establishing a market for Migwan’s goods,
and the canning went on in earnest. The whole family were pressed into
service, and for days they did nothing but peel from morning until
night.
“I’m getting to be such an expert peeler,” said Hinpoha, “that I
automatically reach out in my sleep and start to peel Migwan.”
Nyoda made up a gay little song about the peeling. To the tune of
“Comrades, comrades, ever since we were boys,” she sang, “Peeling,
peeling, ever since 6 A.M.”
Several places had asked for homemade ketchup and Migwan prepared to
supply the demand. Never did a prize housekeeper, making ketchup for a
county fair, take such pains as Migwan did with hers. She took care to
use only the best spices and the best vinegar; she put in a few peach
leaves from the tree to give it a finer flavor; she stood beside the big
iron preserving kettle and stirred the mixture all the while it was
boiling to be sure that it would not settle and burn. Everyone in the
house had to taste it to be sure it found favor with a number of
critical palates. “Wouldn’t you like to put a few bay leaves into it?”
asked her mother. “There are some in the glass jar in the pantry. They
are all crumbled and broken up fine, but they are still good.” Migwan
put a spoonful of the broken leaves into the ketchup; then she put
another.
“Oh, I never was so tired,” she sighed, when at last it had boiled long
enough and she shoved it back.
“Let’s all go out on the river,” proposed Nyoda, “and forget our toil
for awhile.” Sahwah was the last out of the kitchen, having stopped to
drink a glass of water, and while she was drinking her eye roved over
the table and caught sight of half a dozen cloves that had spilled out
of a box. Gathering them up in her hand she dropped them into the
ketchup. Just then Migwan came back for something and the two went out
together.
“And now for the bottling,” said Migwan, when the supper dishes were put
away, and she set several dozen shining glass bottles on the table.
After she had been dipping up the ketchup for awhile she paused in her
work to sit down for a few moments and count up her expected profits.
“Let’s see,” she said, “forty bottles at fifteen cents a bottle is six
dollars. That isn’t so bad for one day’s work. But I hope I don’t have
many days of such work,” she added. “My back is about broken with
stirring.” About thirty of the bottles were filled and sealed when she
took this little breathing spell.
“Let me have a taste,” said Hinpoha, eyeing the brown mixture longingly.
“Help yourself,” said Migwan. Hinpoha took a spoonful. Her face drew up
into the most frightful puckers. Running to the sink she took a hasty
drink of water. “What’s the matter?” said Migwan, viewing her in alarm.
“Did you choke on it?”
“Taste it!” cried Hinpoha. “It’s as bitter as gall.”
Migwan took a taste of the ketchup and looked fit to drop. “Whatever is
the matter with it?” she gasped. One after another the girls tasted it
and voiced their mystification. “It couldn’t have spoiled in that short
time,” said Migwan.
Then she suddenly remembered having seen Sahwah drop something into the
kettle as it stood on the back of the stove. Could it be possible that
Sahwah was seeking revenge for having been made fun of? “Sahwah,” she
gasped, unbelievingly, “did you put anything into the ketchup that made
it bitter?”
“I did not,” said Sahwah, the indignant color flaming into her face. She
had already forgotten the incident of the cloves. She saw Nyoda and the
other girls look at her in surprise at Migwan’s words. Her temper rose
to the boiling point. “I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she said, fiercely.
“You think I did something to the ketchup to get even with Migwan, but I
didn’t, so there. I don’t know any more about it than you do.”
“I take it all back,” said Migwan, alarmed at the tempest she had set
astir, and bursting into tears buried her head on her arms on the
kitchen table. All that work gone for nothing!
Sahwah ran from the room in a fearful passion. Nyoda tried to comfort
Migwan. “It’s a lucky thing we found it before the stuff was sold,” she
said, “or your trade would have been ruined.” She and the other girls
threw the ketchup out and washed the bottles.
“Whatever could have happened to it?” said Gladys, wonderingly.
Migwan lifted her face. “I want to tell you something, Nyoda,” she said.
“I suppose you wonder why I asked Sahwah if she had put anything in.
Well, when I went back into the kitchen after my hat when we were going
out on the river, Sahwah was there, and she was dropping something into
the kettle.”
“You don’t mean it?” said Nyoda, incredulously. Nyoda understood
Sahwah’s blind impulses of passion, and she could not help noticing for
the last few days that Sahwah was still nursing her wrath at Migwan for
laughing at her, and she wondered if she could have lost control of
herself for an instant and spoiled the ketchup.
Meanwhile Sahwah, up-stairs, had cooled down almost as rapidly as she
had flared up, and began to think that she had been a little hasty in
her outburst. She, therefore, descended the back stairs with the idea of
making peace with the family and helping to wash the bottles. But
halfway down the stairs she happened to hear Migwan’s remark and Nyoda’s
answer, and the long silence which followed it. Immediately her fury
mounted again to think that they suspected her of doing such an
underhand trick. “They don’t trust me!” she cried, over and over again
to herself. “They don’t believe what I said; they think I did it and
told a lie about it.” All night she tossed and nursed her sense of
injury and by morning her mind was made up. She would leave this place
where everyone was against her, and where even Nyoda mistrusted her.
That was the most unkind cut of all.
When she did not appear at the breakfast table the rest began to wonder.
Betty reported that Sahwah had not been in bed when she woke up, which
was late, and she thought she had risen and dressed and gone down-stairs
without disturbing her. There was no sign of her in the garden or on the
river. Both the rowboat and the raft were at the landing-place. There
was an uncomfortable restraint at the breakfast table. Each one was
thinking of something and did not want the others to see it. That thing
was that Sahwah had a guilty conscience and was afraid to face the
girls. Migwan’s eyes filled with tears when she thought how her dear
friend had injured her. A blow delivered by the hand of a friend is so
much worse than one from an enemy. The table was always set the night
before and the plates turned down.
“What’s this sticking out under Sahwah’s plate?” asked Gladys. It was a
note which she opened and read and then sat down heavily in her chair.
The rest crowded around to see. This was what they read: “As long as you
don’t trust me and think I do underhand things you will probably be glad
to get rid of me altogether. Don’t look for me, for I will never come
back. You may give my place in the Winnebagos to someone else.” It was
signed “Sarah Ann Brewster,” and not the familiar “Sahwah.”
“Sahwah’s run away!” gasped Migwan in distress, and the girls all ran up
to her room. Her clothes were gone from their hooks and her suit-case
was gone from under the bed. The girls faced each other in
consternation.
“Do you think she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ketchup, after all?” asked
Gladys, thoughtfully. “It was so unlike her to do anything of that
kind.”
“Then why did she run away?” asked Migwan, perplexed.
The morning passed miserably. They missed Sahwah at every turn. Several
times the girls forgot themselves and sang out “O Sahwah!” Nyoda did not
doubt for a moment that Sahwah had gone to her own home, but she thought
it best not to go after her immediately. Sahwah’s hot temper must cool
before she would come to herself. Nyoda was puzzled at her conduct. If
she had nothing to be ashamed of why had she run away? That was the
question which kept coming up in her mind. Nothing went right in the
house or the garden that day. Everyone was out of sorts. Migwan
absent-mindedly pulled up a whole row of choice plants instead of weeds;
Gladys ran the automobile into a tree and bent up the fender; Hinpoha
slammed the door on her finger nail; Nyoda burnt her hand. Ophelia was
just dressed for the afternoon in a clean, starched white dress when she
fell into the river and had to be dressed over again from head to foot.
The whole household was too cross for words. The departure of Sahwah was
the first rupture that had ever occurred in the closely linked ranks of
the Winnebagos and they were all broken up over it.
When Mrs. Gardiner was cooking beef for supper she told Migwan to get
her some bay leaf to flavor it with. Migwan brought out the glass jar of
crushed leaves. “That’s not the bay leaf,” said her mother, and went to
look for it herself. “Here it is,” she said, bringing another glass jar
down from a higher shelf.
“Then what’s this?” asked Migwan, indicating the first jar.
“I haven’t the slightest idea,” said Mrs. Gardiner. “It was in the
pantry when we came.”
“But this was what I put into the ketchup,” said Migwan. Hastily
unscrewing the top she shook out some of the contents and tasted them.
Her mouth contracted into a fearful pucker. Never in her life had she
tasted anything so bitter.
“I did it myself,” she said, in a dazed tone. “I spoiled the ketchup
myself.” At her shout the girls came together in the kitchen to hear the
story of the mistaken ingredient.
“What can that be?” they all asked. Nobody knew. It was some dried herb
that had been left by the former mistress of the house, and a powerful
one. The girls looked at each other blankly.
“And I accused Sahwah of doing it,” said Migwan, remorsefully. “No
wonder she flared up and left us, I don’t blame her a bit. I wouldn’t
thank anyone for accusing me wrongfully of anything like that.”
“We’ll have to go after her this very evening,” said Gladys, “and bring
her back.”
“If she’ll come,” said Hinpoha, knowing Sahwah’s proud spirit.
“Oh, I’m quite willing to grovel in the dust at her feet,” said Migwan.
Gladys drove them all into town with her and they sped to the Brewster
house. It was all dark and silent. Sahwah was evidently not there. They
tried the neighbors. They all denied that she had been near the house.
They finally came to this conclusion themselves, for in the light of the
street lamp just in front of the house they could see that the porch was
covered with a month’s accumulation of yellow dust which bore no
footmarks but their own.
Here was a new problem. They had come expecting to offer profuse
apologies to Sahwah and carry her back with them to Onoway House
rejoicing, and it was a shock to find her gone. The thought of letting
her go on believing that they mistrusted her was intolerable, but how
were they going to clear matters up? Sahwah had no relatives in town,
and, of course, they did not know all her friends, so it would be hard
to find her. That is, if she had ever reached town at all. Something
might have happened to her on the way—Nyoda and Gladys sought each
other’s eyes and each thought of what had happened to them on the way to
Bates Villa.
With heavy hearts they rode back to Onoway House. The days went by
cheerlessly. A week passed since Sahwah had run away, but no word came
from her. Nyoda interviewed the conductors on the interurban car line to
find out if Sahwah had taken the car into the city. No one remembered a
girl of that description on the day mentioned. Sahwah had only one hat—a
conspicuous red one—and she would not fail to attract attention.
Thoroughly alarmed, Nyoda decided on a course of action. She called up
the various newspapers in town and asked them to print a notice to the
effect that Sahwah had disappeared. If Sahwah were in town she would see
it and knowing that they were worried about her would let them know
where she was. The notice came out in the papers, and a day or two
passed, but there was no word from Sahwah. Nyoda and Gladys made a
hurried trip to town to put the police on the track. Just before they
got to the city limits they had a blowout and were delayed some time
before they could go on. As they waited in the road another machine came
along and the driver stopped and offered assistance. Nyoda recognized a
friend of hers in the machine, a Miss Barnes, teacher in a local
gymnasium.
“Hello, Miss Kent,” she called, cheerfully, “I haven’t seen you for an
age. Where have you been keeping yourself?”
“Where have you been keeping yourself?” returned Nyoda.
“I, Oh, I’m working this summer,” replied Miss Barnes. “I’m just in town
on business. I’m helping to conduct a girls’ summer camp on the lake
shore. I thought possibly you would bring your Camp Fire group out there
this summer. One of your girls is out there now.”
“Which one?” asked Nyoda, thinking of Chapa and Nakwisi, whom she had
heard talking about going.
“One by the name of Brewster,” said Miss Barnes, “a regular mermaid in
the water. She has the girls out there standing open-mouthed at her
swimming and diving. Why, what’s the matter?” she asked, as Nyoda gave a
sigh of relief that seemed to come from her boots.
“Nothing,” replied Nyoda, “only we’ve been scouring the town for that
very girl.”
“You have?” asked Miss Barnes, with interest. “Would you like to come
out and visit her?”
“Could I?” asked Nyoda.
“Certainly,” said Miss Barnes, “come right out with me now. I’m going
back.”
And so Sahwah’s mysterious disappearance was cleared up. When the
Winnebagos, lined up in the road, saw the automobile approaching, and
that Sahwah was in it, they welcomed her back into their midst with a
rousing Winnebago cheer that warmed her to the heart. All the clouds had
been rolled away by Nyoda’s explanations and this was a triumphant
homecoming. A regular feast was spread for her, and as she ate she
related her adventures since leaving the house early that other morning.
Without forming any plan of where she was going she had walked up the
road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of the car line and then a farmer had
come along on a wagon and given her a lift. He had taken her all the way
to the other car line, three miles below Onoway House. She had come into
the city by this route. She did not want to go home for fear they would
come after her, so she went to the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As she sat in the rest room wondering what she should do next she heard
two girls talking about registering for camp. This seemed to her a
timely suggestion, and she followed them to the registration desk and
registered for two weeks. She went out that same day. When she arrived
there she did such feats in the water that they asked her if she would
not stay all summer and help teach the girls to swim. She said she
would, and so saw a very easy way out of her difficulty. The reason they
had not heard from her when they put the notice in the papers was
because they did not get the city papers in camp.
Sahwah surveyed the faces around the table with a beaming countenance.
After all, she could only be entirely happy with the Winnebagos. Migwan
and she were once more on the best of terms.
“But tell us,” said Hinpoha, now that this was safe ground to tread
upon, “what it was you put into the ketchup.”
“Oh,” said Sahwah, who now remembered all about it, “those were a couple
of cloves that were lying on the table.”
And so the last bit of mystery was cleared up.
CHAPTER IX.—OPHELIA DANCES THE SUN DANCE.
Among the other books at Onoway House there was a Manual of the
Woodcraft Indians which belonged to Sahwah, and which she was very fond
of quoting and reading to the other girls when they were inclined to
hang back at some of the expeditions she proposed. One night she read
aloud the chapter about “dancing the sun dance,” that is, becoming
sunburned from head to foot without blistering. On a day not long after
this Ophelia might have been seen standing beside the river clad only in
a thin, white slip. Stepping from the bank, she immersed herself in the
water, then stood in the sun, holding out her arms and turning up her
face to its glare. When the blazing August sunlight began to feel
uncomfortably warm on her body she plunged into the cooling flood and
then came up to stand on the bank again. She did this straight through
for two hours, and then began to investigate the result. Her arms were a
beautiful brilliant red, and the length of leg that extended out from
the slip was the same shade. She felt wonderfully pleased, and dipped in
the water again and again to cool off and then returned to the burning
process. When the dinner bell rang she returned to the house, eager to
show her achievement. But she did not feel so enthusiastic now as when
she first beheld her scarlet appearance. Something was wrong. It seemed
as if she were on fire from head to foot. She looked at her arms. They
were no longer such a pretty red; they had swelled up in large, white
blisters. So had her legs. She could hardly see out of her eyes.
“Ophelia!” gasped the girls, when she came into the house. “What has
happened? Have you been scalded?”
“I’ve been doing your old Sun Dance,” said Ophelia, painfully.
Never in all their lives had they seen such a case of sunburn. Every
inch of her body was covered with blisters as big as a hand. The sun had
burned right through the flimsy garment she wore. There was a pattern
around her neck where the embroidery had left its trace. She screamed
every time they tried to touch her. Nyoda worked quickly and deftly and
the luckless sun dancer was wrapped from head to foot in soft linen
bandages until she looked like a mummy.
Sahwah sought Nyoda in tribulation. “Was it my fault,” she asked, “for
reading her that book? She never would have thought of it if I hadn’t
given her the idea.”
“No,” answered Nyoda, “it wasn’t your fault. It said emphatically in the
book that the coat of tan should be acquired gradually. You couldn’t
foresee that she would stand in the sun that way. So don’t worry about
it any longer.”
“Still, I feel in a measure responsible,” said Sahwah, “and I ought to
be the one to take care of her. Let me sleep in the room with her
to-night and get up if she wants anything.” Sahwah’s desire to help was
so sincere that she insisted upon being allowed to do it, and took upon
herself all the care of the sunburned Ophelia, which was no small job,
for the pain from the blisters made her frightfully cross.
Nyoda was surprised to see Sahwah keeping at it with such persistent
good nature and apparent success, for as a rule she was not a good one
to take care of the sick; she was in too much of a hurry. She would
generally spill the water when she was trying to give a drink to her
patient, or fall over the rug, or drop dishes; and the effect she
produced was irritating rather than soothing. But in this case she
seemed to be making a desperate effort to do things correctly so she
would be allowed to continue, and fetched and carried all the afternoon
in obedience to Ophelia’s whims. She read her stories to while away the
painful hours and when supper time came made her a wonderful egg salad
in the form of a water lily, and cut sandwiches into odd shapes to
beguile her into eating them. When evening came and Ophelia was restless
and could not go to sleep she sang to her in her clear, high voice,
songs of camp and firelight. One by one the Winnebagos drifted in and
joined their voices to hers in a beautifully blended chorus.
“Gee, that’s what it must be like in heaven,” sighed the child of the
streets, as she listened to them. The Winnebagos smiled tenderly and
sang on until she dropped off to sleep.
Sahwah slept with one eye open listening for a call from Ophelia. She
heard her stirring restlessly in the night and went over and sat beside
her. “Can’t you sleep?” she asked.
“No,” complained Ophelia. “Say, will you tell me that story again?”
Sahwah began,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little girl and she had a
fairy godmother——”
“What’s a fairy godmother?” interrupted Ophelia.
“Oh,” said Sahwah, “it’s somebody who looks after you especially and is
very good to you and grants all your wishes, and always comes when
you’re in trouble——”
“Who’s my fairy godmother?” demanded Ophelia.
“I don’t know,” said Sahwah.
“I bet I haven’t got any!” said Ophelia, suspiciously. “I didn’t have a
father and mother like the rest of the kids and I bet I haven’t got any
fairy godmother either.”
“Oh, yes, you have,” said Sahwah to soothe her, “you have one only you
haven’t seen her yet. Wait and she’ll appear.” But Ophelia lay with her
face to the wall and said no more. “Would you like me to bring you a
drink?” asked Sahwah, a few minutes later. Ophelia replied with a nod
and Sahwah went down to the kitchen. There was no drinking water in
sight and Sahwah hesitated about going out to the well at that time of
the night. Then she remembered that a pail of well water had been taken
down cellar that evening to keep cool. Taking a light she descended the
cellar stairs. When she was nearly to the bottom she heard a subdued
crash, like a basket of something being thrown over, followed by a
series of small bumping sounds. She stood stock still, afraid to move
off the step.
Then, summoning her voice, she cried, “Who is down there?” No answer
came from the darkness below. After that first crash there was not
another sound. Sahwah was not naturally timid, and her one explanation
for all night noises in a house was rats. Besides, she had started after
water for Ophelia, and she meant to get it. She went down stairs and
looked all around with her light. She soon found the thing which had
made the noise. It was a basket of potatoes which had fallen over and as
the potatoes rolled out on the cement floor they had made those odd
little after noises which had puzzled her. Satisfied that nobody was in
the house she took her pail of water and went up-stairs, glad that she
had not roused the house and brought out a laugh against herself.
She gave Ophelia the drink, and being feverish she drank it eagerly and
murmured gratefully, “I guess you’re my fairy godmother.” As Sahwah
turned to go to bed Ophelia thrust out a bandaged hand and caught hold
of her gown. “Stay with me,” she said, and Sahwah sat down again beside
the bed until Ophelia fell asleep. Sahwah felt pleased and elated at
being chosen by Ophelia as the one she wanted near her. It was not often
that a child singled Sahwah out from the group as an object of
affection; they usually went to Gladys or Hinpoha. So she responded
quickly to the advances made by Ophelia and thenceforth made a special
pet of her, taking her part on all occasions.
Soon after Ophelia’s experience with sunburn a rainy spell set in which
lasted a week. Every day they were greeted by grey skies and a steady
downpour, fine for the parched garden, but hard on amusements. They
played card games until they were weary of the sight of a card; they
played every other game they knew until it palled on them, and on the
fifth day of rain they surrounded Nyoda and clamored for something new
to do. Nyoda scratched her head thoughtfully and asked if they would
like to play Thieves’ Market.
“Play what?” asked Gladys.
“Thieves’ Market,” said Nyoda. “You know in Mexico there is an
institution known as the Thieves’ Market, where stolen goods are sold to
the public. We will not discuss the moral aspect of the business, but I
thought we could make a game out of it. Let’s each get a hold of some
possession of each one of the others’ without being seen and put a price
on it. The price will not be a money value, of course, but a stunt. The
owner of the article will have first chance at the stunt and if she
fails the thing will go to whoever can buy it. If anyone fails to get a
possession from each one of the rest to add to the collection she can’t
play, and if she is seen by the owner while ‘stealing’ it she will have
to put it back. We’ll hold the Thieves’ Market to-night after supper in
the parlor and I’ll be storekeeper.”
The Winnebagos, always on the lookout for something novel and
entertaining, seized on the idea with rapture. The rain was forgotten
that afternoon as they scurried around the house trying to seize upon
articles belonging to the oth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trying valiantly
to guard their own possessions. It was not hard to get Sahwah’s things,
for she had a habit of leaving them lying all over the house. Her red
hat had fallen a victim the first thing; likewise her shoes and tennis
racket. It was harder to get anything away from Nyoda, for she seemed to
be Argus eyed; but providentially she was called to the telephone, and
while she was talking they made their raid.
When opened, the Thieves’ Market presented such a conglomeration of
articles that at first the girls could only stand and wonder how those
things had ever been taken away from them without their knowing it, for
many of them were possessions which were usually hidden from sight while
the owners fondly believed that their existence was unknown. Migwan gave
a cry of dismay when she beheld her “Autobiography,” which she was
carefully keeping a secret from the rest, out in full view on the table.
“How did you ever find it?” she gasped. “It was folded up in my
clothes.”
But Migwan’s embarrassment was nothing compared to Nyoda’s when she
caught sight of a certain photograph. She blushed scarlet while the
girls teased her unmercifully. It was a picture of Sherry, the serenader
of the camp the summer before. Until they found the photograph the girls
did not know that Nyoda was corresponding with him. And the prices on
the various things were the funniest of all. The girls had come down
that evening dressed in their middies and bloomers for they had a
suspicion that there would be some acrobatic stunts taking place, and it
was well that they did. To redeem her hat Sahwah had to stand on her
head and to get her bedroom slippers Gladys had to jump through a hoop
from a chair. Hinpoha had to wrestle with Nyoda for the possession of
her paint box, and the price of Betty’s shoes was to throw them over her
shoulder into a basket. At the first throw she knocked a vase off the
table, but luckily it did not break, and she was warned that another
accident would result in her going shoeless. Migwan tremblingly
approached the Autobiography to find out the price. It was “Read one
chapter aloud.” “I won’t do it,” said Migwan, flatly.
“Next customer,” cried Nyoda, pounding with her hammer. “For the simple
price of reading aloud one chapter I will sell this complete
autobiography of a pious life, profusely illustrated by the author.”
Sahwah hastened up to “buy” the book, but Migwan headed her off in a
hurry and read the first chapter with as good grace as she could, amid
the cheers and applause of the other customers. Sahwah made a grimace
when she had to polish the shoes of everyone present to get her shoe
brush back.
Thus the various articles in the Thieves’ Market were disposed of amid
much laughter and merry-making, until there remained but one article, a
cold chisel. Nyoda went through the usual formula, offering it for sale,
but no one came to claim it. She redoubled her pleas, but with the same
result. “For the third and last time I offer this great bargain in a
cold chisel for the simple price of jumping over three chairs in
succession,” she said, with a flourish. Nobody appeared to be anxious to
redeem their property. “Whose is it?” she asked, mystified.
It apparently belonged to no one. “It’s yours, Gladys,” said Sahwah, “I
stole it from you.”
“Mine?” asked Gladys, in surprise. “I don’t own any chisel. Where did
you get it from?”
“Out of the automobile,” answered Sahwah.
“But it doesn’t belong there,” said Gladys. “There’s no chisel among the
tools. You’re joking, you found it somewhere else.”
“No, really,” said Sahwah, “I found it in the car this afternoon.”
“Mother,” called Migwan, “were there any tools left in the barn by Mr.
Mitchell?”
“Nothing but the garden tools,” answered her mother. Tom also denied any
knowledge of the chisel.
“Girls,” said Nyoda, seriously, “there is something going on here that I
do not understand. First Migwan thought she heard footsteps in the
attic; then a ghost appeared to me in the tepee; one night we saw a man
running out of the barn, and later on that night Migwan claims to have
run into a man in the garden. Soon afterward Hinpoha was sure she heard
footsteps in the attic, and when we went up we found the window broken.
Just a few nights ago a basket of potatoes was mysteriously knocked over
in the cellar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now we find a chisel in
the automobile which does not belong to us. It looks for all the world
as if somebody were trying to break into this house, in fact, has broken
in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
Migwan shrieked and covered up her ears. “A mystery!” said Sahwah,
theatrically. “How thrilling!” The interest in the Thieves’ Market died
out before this new and alarming idea.
“It may be only a remarkable series of co-incidences,” said Nyoda,
seeing the fright of the girls, “but it certainly looks suspicious. That
window may possibly have been broken by the wind during the storm, and
the footsteps may have been rats or Mrs. Waterhouse’s ghost, and the
ghost in the tepee may have been a practical joker, but baskets of
potatoes do not fall over of their own accord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cold chisels don’t grow in automobiles. There’s something wrong and
we ought to find out what it is.”
“Oh, I’ll never go up-stairs alone again,” shuddered Migwan. “Sahwah,
how did you ever dare go down cellar in the dark after you heard that
noise?” And she shivered violently at the very thought.
“Tom, can you handle a gun?” asked Nyoda.
“Yes,” answered Tom.
“I’m going to buy a little automatic pistol to-morrow,” said Nyoda, “and
teach everyone of you girls how to shoot it.”
“I wonder if we hadn’t better try to get Calvin Smalley to sleep in the
house,” said Migwan.
“I can take care of you,” said Tom, proudly. Nothing else was talked of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evening and when bed time came there was a
general reluctance to become separated from the rest of the household.
But, although they listened for footsteps in the attic they heard
nothing, and the night passed away peacefully.
The next night the ghost became active again. Whether it was the same
one or a different one they did not find out, however, for they did not
see it this time, only heard it. Just about bed time it was, a strange,
weird moaning sound that filled the house and echoed through the big
halls. Whether it proceeded from the basement or the attic they were
unable to make out; it seemed to come from everywhere and nowhere.
Migwan clung close to her mother and trembled. The sound rang out again,
more weird than before. It was bloodcurdling. Nyoda opened the window
and fired several shots into the air. The moaning sound stopped abruptly
and was heard no more that night, but sleep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The
girls were too excited and fearful. The next day Mrs. Gardiner advised
everybody to hide their valuables away. The peaceful life at Onoway
House was broken up. The household lived in momentary expectation of
something happening. “And this is the quiet of the country,” sighed
Migwan, “where I was to grow fat and strong. I’m worn to a frazzle
worrying about this mystery.”
“So’m I,” said Gladys.
“And I’m getting thin,” said Hinpoha, which brought out a general laugh.
“Not so you could notice it,” said Sahwah. Whereupon Hinpoha tried to
smother her with a pillow and the two rolled over on the bed,
struggling.
As if worrying about a burglar were not enough, Sahwah and Gladys had
another exciting experience one day that week. If we were to stretch a
point and trace things back to their beginnings it was the fault of the
Winnebagos themselves, for if they hadn’t gone horseback riding that
day—— Well, Farmer Landsdowne came over in the morning and said he had a
pair of horses which were not working and if they wanted to go horseback
riding now was their chance. The girls were delighted with the idea and
flew to don bloomers. None of them had ever ridden before and excitement
ran high. Naturally there were no saddles, for Farmer Landsdowne’s
horses were not ridden as a general rule, and the girls had to ride
bareback.
“It feels like trying to straddle a table,” said Migwan, marveling at
the width of the horse she was on. “My legs aren’t half long enough.”
She clung desperately to his mane as he began to trot and she began to
slide all over him. “He’s so slippery I can’t stick on,” she gasped. The
horse stopped abruptly as she jerked on the reins and she slid off as if
he had been greased, and landed in the soft grass beside the road.
“Here, let me try,” said Sahwah, impatient for her turn. “He isn’t
either slippery,” she said, when she got on, “he’s bony, horribly bony.
He’s just like knives.” She jolted up and down a few times on his hip
bones and an idea jolted into her head. Getting off she ran into the
house and came out again with a sofa pillow, which she proceeded to tie
on his back. Then she rode in comparative comfort, amid the laughter of
the girls.
Calvin Smalley, who happened to be working out in front and saw her ride
past, doubled up with laughter over his vegetable bed. “What next?” he
chuckled. “What next?” He was still thinking about this and laughing
over it when he went through the empty field which Sahwah had crossed
the time she had discovered the house among the trees, and where Abner
Smalley now pastured his bull. So absorbed was he in the memory of that
ridiculous pillow tied on the horse that he was not careful in putting
up the bars behind him when he left the field, and later in the
afternoon the bull wandered over in that direction and came through into
the next field. He found the river road and followed it and began to
graze in one of the unploughed fields belonging to Onoway House.
Sahwah, wearing her big, red hat, was bending low over the ground,
digging up some ferns which grew there, when all of a sudden she heard a
loud snort and looked up to see the bull charging down upon her. She
looked wildly around for a place of safety. Nothing was nearer than the
far-off hedge that surrounded the cultivated garden patch. Not a tree,
not a fence, in sight. Quick as light she bounded off toward the hedge,
although she knew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her to reach it before the
bull would be upon her.
Gladys, coming along the road in the automobile, heard a shriek and
looked up to see Sahwah tearing across the open field with the bull hard
after her. Without a moment’s hesitation Gladys turned the car into the
field and started after the bull at full speed. She let the car out
every notch and it whizzed dizzily over the hard turf. She sounded the
horn again and again with the hope of attract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bull, but he did not pause. Like lightning she bore down upon him,
passed to one side and slowed down for a second beside Sahwah, who
jumped on the running-board and was borne away to safety.
“This hum-drum, uneventful life,” said Sahwah, as she sat on the porch
half an hour afterward and tried to catch her breath, while the rest
fanned her with palm leaf fans, “is getting a little too much for me!”
CHAPTER X.—A BIRTHDAY PARTY
After Nyoda had fired the shots out of the window, nothing was heard or
seen of the ghost and the footsteps in the attic ceased. “It’s just as I
thought,” said Nyoda, “someone has been trying to frighten us with a
possible view of robbing the house at some time, thinking that a
houseful of women would be terror-stricken at the ghostly noises, but
when he found we had a gun and could shoot he thought better of the
plan.” Gradually the girls lost their fright, and the odd corners of
Onoway House regained their old charm. They were far too busy with the
canning to think of much else, for the tomatoes were ripening in such
large quantities that it was all they could do to dispose of them. The
4H brand found favor and the market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every week
Migwan had a goodly sum to deposit in the bank after the cost of the tin
cans had been deducted.
“I have to laugh when I think of that honor in the book,” said Migwan,
“can at least three cans of fruit,” and she pointed to the cans stacked
on the back porch ready to be packed into the automobile and taken to
town. “Why, hello, Calvin,” she said, as Calvin Smalley appeared at the
back door. “Come in.” Calvin came in and sat down. “What’s the matter?”
asked Migwan, for his face had a frightened and distressed look.
“Uncle Abner has turned me out!” said Calvin.
“Turned you out!” echoed the girls. “Why?”
“He showed me a will last night,” said Calvin, “a later one than that
which was found when my grandfather died, which left the farm to him
instead of to my father. He just found it last night when he was
rummaging among grandfather’s old papers. According to that I have been
living on his charity all these years instead of on my own property as I
supposed and now he says he can’t afford to keep me any longer. He
wanted me to sign a paper saying that I would work for him without pay
until I was thirty years old to make up for what I have had all these
years, and when I wouldn’t do it he told me to get out.”
“How can any man be so mean and stingy!” said Migwan, indignantly.
“And what do you intend to do now?” asked Mrs. Gardiner.
“I don’t know,” said Calvin, looking utterly downcast and discouraged.
“I had expected to go through school and then to agricultural college
and be a scientific farmer, but that’s out of the question now. I
haven’t a cent in the world. I could hire out to some of the farmers
around here, I suppose, but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they wouldn’t pay
me much because I’m a boy, but they would get a man’s work out of me and
it’s precious little time I’d have for school. I’ve always saved Uncle
Abner the cost of one hired man in return for what he gave me, so I
don’t feel under any obligations to him. I think I’ll give up farming
for a while and go to the city and work. The trouble is I have no
friends there and it might be hard for me to get into a good place.” His
honest eyes were clouded over with perplexity and trouble.
“My father could probably get you a job in the city,” said Gladys, “if
you can wait until he gets back. He’s out west now.”
“I tell you what to do,” said kind-hearted Mrs. Gardiner to Calvin, “you
stay here with us until Mr. Evans comes back. You can help the girls in
the garden, and we were wishing not long ago that we had another man in
the house.”
“You are very kind,” said Calvin, gratefully, “but I don’t want to put
you to any trouble.”
“No trouble at all,” Mrs. Gardiner assured him, “you can sleep with
Tom.” The girls all expressed pleasure at the prospect of having Calvin
stay at Onoway House and under the spell of their kindly hospitality his
drooping spirits revived. He shook the dust of his uncle’s house from
his feet, feeling no longer an outcast, since he had suddenly found such
kind friend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hedge.
Calvin lived in a perpetual state of wonder at the girls at Onoway
House. They made a frolic out of everything they did and were
continually thinking up new and amazing games to play. Calvin had never
done anything at home all his life but work, and work was a serious
business to him. He never knew before that work was fun. The long, weary
hours of peeling were enlivened with songs made up 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 Sahwah would look up from the pan over which she was bending,
and sing to the tune of “The Pope”:
“Our Migwan leads a jolly life, jolly life,
She peels tomatoes with her knife, with her knife,
And puts the pieces in the can,
And leaves the peelings in the pan, (Oh, tra la la).”
And then they would all start to sing at once,
“The tomatoes went in one by one,
(There’s one more bushel to peel),
Hinpoha she did cut her thumb,
(There’s one more bushel to peel).”
“The tomatoes went in two by two,
And Gladys and Sahwah fell into the stew.
The tomatoes went in three by three,
And Migwan got drowned a-trying to see.”
etc., etc., thus they made merry over the work until it was done.
“Do you know,” said Migwan, looking up from her peeling, “that it’s
Gladys’s birthday next Friday? We ought to have a celebration.”
“How about a picnic?” asked Nyoda. “We haven’t had a real one yet. Have
the rest of the Winnebagos come out from town and all of us sleep in the
tepee as we had planned on the Fourth of July. Then we’ll get a horse
and wagon and drive along the roads until we come to a place beside the
river where we want to stop and cook our dinner and just spend the day
like gypsies.” The girls entered into the plan with enthusiasm, both for
the sake of celebrating Gladys’s birthday and cheering up Calvin, who
had been rather quiet and pensive of late. It was a great disappointment
to him to have to give up his plans for going to college, and his
uncle’s unfriendly treatment of him had cut him to the heart.
Medmangi and Chapa and Nakwisi arrived the day before the picnic and the
house echoed with the sound of voices and laughter, as the Winnebagos
bubbled over with joy at being all together. The morning of the picnic
was as fine as they could wish, and it was not long before they were
bumping over the road in one of Farmer Landsdowne’s wagons, behind the
very two horses which the girls had ridden the week before. It was a
wagon full. Sahwah sat up in front and drove like a veritable daughter
of Jehu, with Farmer Landsdowne up beside her to come to the rescue in
case the horses should run away, which was not at all likely, as it took
constant persuasion to keep them going even at an easy jog trot. Mrs.
Landsdowne, who, with her husband, had been invited to the picnic, sat
beside Mrs. Gardiner, in the back of the wagon, while Calvin Smalley
stayed next to Migwan, as he usually did. She was so quiet and gentle
and kind that he felt more at ease with her than with the rest of the
Winnebagos, who were such jokers. Ophelia, who was beginning to be
inseparable from Sahwah, squeezed herself in between her and Mr.
Landsdowne, and refused to move. Sahwah, of course, took her part and
let her stay, although she was a bit crowded for space. Hinpoha and
Gladys sat at the back of the wagon dangling their feet over the end,
where they could watch the yellow road unwinding like a ribbon beneath
them, while Nyoda sat between Betty and Tom to keep the peace.
“Where are we going?” asked Mrs. Gardiner, as they swung along the road.
“Oh,” replied Sahwah, “somewhere, anywhere, everywhere, nowhere. It’s
lots more romantic to start out without any idea where you’re going and
stop wherever it suits you than to start out for a certain place and
think you have to go there even if you pass nicer places o
what would happen next, but nothing did. The house stood blank and
silent and apparently as empty as ever. Not a glimmer of light was
visible anywhere. Sahwah and Nyoda were just on the point of getting
into the rowboat, which had been tied on behind the raft, and towing the
other girls back home, when their ears caught the sound of a faint
splashing, like the sound made by the dipping of an oar. They were
completely hidden from sight either up or down the river, for just at
this point a portion of the bank had caved in, and the water filling up
the hole had made a deep indentation in the shore line, and into this
miniature bay the Tortoise-Crab had been steered. The thick willows
along the bank formed a screen between them and the stream above and
below. But they could look between the branches and see what was coming
up stream, from the direction of the lake. It was a rowboat, containing
two persons. The scudding clouds parted at intervals and the moon shone
through, and by its fitful light they could see that one of these
persons was a woman. When the rowboat was almost directly behind the
house it came to a halt, only a few yards from the place where the
Winnebagos lay concealed.
“This is the house,” said the man.
“I told you the water was deep enough up this far,” said the woman, in a
tone of satisfaction. Just then the moon shone out for a brief instant,
and the Winnebagos looked at each other in surprise. The woman, or
rather the girl, in the rowboat was Miss Mortimer, who had been their
guest only that day. The next moment she spoke. “We might as well go
back now. There isn’t anything more we can do. I just wanted to prove to
you that it could be towed up the river this far without danger.”
“All right, Belle,” replied the man, and at the sound of his voice
Migwan pricked up her ears. There was something vaguely familiar about
it; something which eluded her at the moment. The rowboat turned in the
river and proceeded rapidly down-stream. The Winnebagos returned home,
full of excitement and wonder.
The barn at Onoway House stood halfway between the house and the river.
As they landed from the raft and were tying it to the post they saw a
man come out of the barn and disappear among the bushes that grew
nearby. It was too dark to see him with any degree of distinctness.
Gladys’s thought leaped immediately to her car, which was left in the
barn. “Somebody’s trying to steal the car!” she cried, and they all
hastened to the barn. The automobile stood undisturbed in its place.
They made a hasty search with lanterns, but as far as they could see,
none of the gardening tools were missing. Satisfied that no damage had
been done, they went into the house.
“Probably a tramp,” said Mrs. Gardiner, when the facts were told her.
“He evidently thought he would sleep in the barn, and then changed his
mind for some reason or other.”
Migwan lay awake a long time trying to place the voice of the man in the
rowboat. Just as she was sinking off to sleep it came to her. The voice
she had heard in the darkness had a slightly foreign accent, and was the
voice of the man who had used the telephone that morning.
Sometime during the night Onoway House was wakened by the sounds of a
terrific thunder storm. The girls flew around shutting windows. After a
few minutes of driving rain against the window panes the sound changed.
It became a sharp clattering. “Hail!” said Sahwah.
“Oh, my young plants!” cried Migwan. “They will be pounded to pieces.”
“Cover them with sheets and blankets!” suggested Nyoda. With their
accustomed swiftness of action the Winnebagos snatched up everything in
the house that was available for the purpose and ran out into the
garden, and spread the covers over the beds in a manner which would keep
the tender young plants from being pounded to pieces by the hailstones.
Migwan herself ran down to the farthest bed, which was somewhat
separated from the others. As she raced to save it from destruction she
suddenly ran squarely into someone who was standing in the garden. She
had only time to see that it was a man, when, with a muffled exclamation
of alarm he disappeared into space. Disappeared is the only word for it.
He did not run, he never reached the cover of the bushes; he simply
vanished off the face of the earth. One moment he was and the next
moment he was not. Much excited, Migwan ran back to the others and told
her story, only to be laughed at and told she was seeing things and had
lurking men on the brain. The thing was so queer and uncanny that she
began to wonder herself if she had been fully awake at the time, and if
she might not possibly have dreamed the whole thing.
The morning dawned fresh and fair after the shower, green and gold with
the sun on the garden, and Migwan’s delight at finding the tender little
plants unharmed, thanks to their timely covering, was inclined to thrust
the mysterious goings-on at the empty house the night before into
secondary place in her mind. But she was not allowed to forget it, for
it was the sole topic of conversation at the breakfast table. Gladys,
with her nose buried in the morning paper, suddenly looked up. “Listen
to this,” she said, and then began to read: “Another dynamite plot
unearthed. Society for the purpose of assassinating men prominent in
affairs and dynamiting large buildings discovered in attempt to blow up
the Court House. An attempt to blow up the new Court House was
frustrated yesterday when George Brown, one of the custodians, saw a man
crouching in the engine room and ordered him out. A search revealed the
fact that dynamite had been placed on the floor and attached to a fuse.
On being arrested the man confessed that he was a member of the famous
Venoti gang, operating in the various large cities. The man is being
held without bail, but the head of the gang, Dante Venoti, is still at
large, and so is his wife, Bella, who aids him in all his activities. No
clue to their whereabouts can be found.”
“Do you suppose,” said Gladys, laying the paper down, “that those men we
saw last night could belong to that gang? You remember how carefully
they carried the keg into the house, as if it contained some explosive.
They couldn’t have any business there or they wouldn’t have come at
night. And they called the woman in the boat ‘Belle,’ or it might have
been ‘Bella.’”
“And that man in the boat was the same one who came here and used the
telephone yesterday morning,” said Migwan. “I couldn’t help noticing his
foreign accent. He said, ‘We are going to do it on the Centerville Road.
There is a river near.’ What are they going to do on the Centerville
Road?”
The garden work was neglected while the girls discussed the matter. “And
the man we saw coming out of the barn when we came home,” said Sahwah,
“he probably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it, too.”
“And the man I saw in the garden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said
Migwan.
“If you _did_ see a man,” said Nyoda, somewhat doubtfully. Migwan did
not insist upon her story. What was the use, when she had no proof, and
the thing had been so uncanny?
They were all moved to real grief over the fact that the delightful Miss
Mortimer should have a hand in such a dark business—in fact, was
undoubtedly the famous Bella Venoti herself. “I can’t believe it,” said
Migwan, “she was so jolly and friendly, and was so charmed with Onoway
House.”
“I wonder why she wanted to go through it from attic to cellar,” said
Sahwah, shrewdly. “Could she have had some purpose? _Migwan!_” she
cried, jumping up suddenly, “don’t you remember that she said, ‘How near
that tree is to the window’? Could she have been thinking that it would
be easy to climb in there? And when she asked how we ever moved about
with all that furniture up there, you said, ‘We never come up here’!
Don’t you see what we’ve done? We’ve given her a chance to look the
house over and find a place where people could hide if they wanted to,
and as much as told her that they would be safe up here because we never
came up.”
Consternation reigned at this speech of Sahwah’s. The girls remembered
the incident only too well. “I’ll never be able to trust anyone again,”
said Migwan, near to tears, for she had conceived a great liking for the
young woman she had known as “Miss Mortimer.”
“Do you remember,” pursued Sahwah, “how she took the pole of the raft
and found out how deep the water was all along, and then afterwards she
said to the man in the boat, ‘I told you it was deep enough.’ Everything
she did at our house was a sort of investigation.”
“But it was only by accident that she got to Onoway House in the first
place,” said Gladys. “All she did was ask me to tell her where she could
get a team of horses to tow her to a garage. She didn’t know I belonged
to Onoway House. It was I who brought her here, and she only stayed
because we asked her to. It doesn’t look as if she had any serious
intentions of investigating the neighborhood. She said she was in a
hurry to go on.” Migwan brightened visibly at this. She clutched eagerly
at any hope that Miss Mortimer might be innocent after all.
“How do you know that that breakdown in the road was accidental?” asked
Nyoda. “And how can you be sure that she didn’t know you came from
Onoway House? She may have been looking for a pretense to come here and
you played right into her hands by offering to tow her into the barn.”
Migwan’s hope flickered and went out.
“And the man in the barn,” said Sahwah, knowingly, “he might have come
to look the automobile over and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way the barn
door opened, so he could get into the car and drive away in a hurry if
he wanted to get away.” Taken all in all, there was only one conclusion
the girls could come to, and that was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suspicious going on in the neighborhood, and it looked very much as if
the Venoti gang were hiding explosives in the empty house and were
planning to bring something else; what it was they could not guess. At
all events, something must be done about it. Nyoda called up the police
in town and told briefly what they had seen and heard, and was told that
plain clothes men would be sent out to watch the empty house. When she
described the man who had called and used the telephone, the police
officer gave an exclamation of satisfaction.
“That description fits Venoti closely,” he said. “He used to have a
mustache, but he could very easily have shaved it off. It’s very
possible that it was he. He’s done that trick before; asked to use
people’s telephones as a means of getting into the house.”
The girls thrilled at the thought of having seen the famous anarchist so
close. “Hadn’t we better tell the Landsdownes about it?” asked Migwan.
“They are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watch that house from their windows
than we are.”
“You’re right,” said Nyoda. “And we ought to tell the Smalleys, too, so
they will be on their guard and ready to help the police if it is
necessary.”
“I hate to go over there,” said Migwan, “I don’t like Mr. Smalley.”
“Tha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it,” said Nyoda, firmly. “The fact that he
is fearfully stingy and grasping has no bearing on this case. He has a
right to know it if his property is in danger.” And she proceeded
forthwith to the Red House.
Mr. Smalley was inclined to pooh-pooh the whole affair as the
imagination of a houseful of women. “Saw a man running out of your barn,
did you?” he asked, showing some interest in this part of the tale.
“Well now, come to think of it,” he said, “I saw someone sneaking around
ours too, last night. But I didn’t think much of it. That’s happened
before. It’s usually chicken thieves. I keep a big dog in the barn and
they think twice about breaking in after they hear him bark, and you
haven’t any chickens, that’s why nothing was touched.” It was a very
simple explanation of the presence of the man in the barn, but still it
did not satisfy Nyoda. She could not help connecting it in some way with
the occurrences in the vacant house.
Mr. Landsdowne was very much interested and excited at the story when it
was told to him. “There’s probably a whole lot more to it than we know,”
he said, getting out his rifle and beginning to clean it. “There’s more
going on in this country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affairs than most
people dream of. You have notified the police? That’s good; I guess
there won’t be many more secret doings in the empty house.”
As Nyoda and Migwan went home from the Landsdownes they passed a
telegraph pole in the road on which a man was working. Silhouetted
against the sky as he was they could see his actions clearly. He was
holding something to his ear which looked like a receiver, and with the
other hand he was writing something down in a little book. Migwan looked
at him curiously; then she started. “Nyoda,” she said, in a whisper,
“that is the same man who used our telephone. That is Dante Venoti
himself.” As if conscious that they were looking at him, the man on the
pole put down the pencil, and drawing his cap, which had a large visor,
down over his face, he bent his head so they could not get another look
at his features. “That’s the man, all right,” said Migwan. “What do you
suppose he is doing?”
“It looks,” said Nyoda, judicially, “as if he were tapping the wires for
messages that are expected to pass at this time. Possibly you did not
notice it, but I began to look at that man as soon as we stepped into
the road from Landsdowne’s, and I saw him look at his watch and then
hastily put the receiver to his ear.”
“Oh, I hope the police from town will come soon,” said Migwan, hopping
nervously up and down in the road.
“Until they do come we had better keep a close watch on what goes on
around here,” said Nyoda. Accordingly the Winnebagos formed themselves
into a complete spy system. Migwan and Gladys and Betty and Tom took
baskets and picked the raspberries that grew along the road as an excuse
for watching the road and the front of the house, while Nyoda and Sahwah
and Hinpoha took the raft and patrolled the river. As the girls in the
road watched, the man climbed down from the pole, walked leisurely past
them, went up the path to the empty house and seated himself calmly on
the front steps, fanning himself with his hat, apparently an innocent
line man taking a rest from the hot sun at the top of his pole.
“He’s afraid to go in with us watching him,” whispered Migwan. Just then
a large automobile whirled by, stirring up clouds of dust, which
temporarily blinded the girls. When they looked again toward the house
the “line man” had vanished from the steps. “He’s gone inside!” said
Migwan, when they saw without a doubt that he was nowhere in sight
outdoors.
Meanwhile the girls on the raft, who had been keeping a sharp lookout
down-stream with a pair of opera glasses, saw something approaching in
the distance which arrested their attention. For a long time they could
not make out what it was—it looked like a shapeless black mass. Then as
they drew nearer they saw what was coming, and an exclamation of
surprise burst from each one. It was a structure like a portable garage
on a raft, towed by a launch. As it drew nearer still they could make
out with the opera glasses that the person at the wheel was a woman, and
that woman was Bella Venoti.
The hasty arrival of an automobile full of armed men who jumped out in
front of the “vacant” house frightened the girls in the road nearly out
of their wits, until they realized that these were the plain clothes men
from town. After sizing up the house from the outside the men went up
the path to the porch. The girls were watching them with a fascinated
gaze, and no one saw the second automobile that was coming up the road
far in the distance. One of the plain clothes men, who seemed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group, rapped sharply on the door of the house. There was
no answer. He rapped again. This time the door was flung wide open from
the inside. The girls could see that the man in the doorway was Dante
Venoti. The officer of the law stepped forward. “Your little game is up,
Dante Venoti,” he said, quietly, “and you are under arrest.”
Dante Venoti looked at him in open-mouthed astonishment. “Vatevaire do
you mean?” he gasped. “I am under arrest? Has ze law stop ze production?
Chambers, Chambers,” he called over his shoulder, “come here queek. Ze
police has stop’ ze production!”
A tall, lanky, decidedly American looking individual appeared in the
doorway behind him. “What the deuce!” he exclaimed, at the sight of all
the men on the porch. At this moment the second automobile drove up,
followed by a third and a fourth. A large number of men and women
dismounted and ran up the path to the house.
“Caruthers! Simpson! Jimmy!” shouted Venoti, excitedly to the latest
arrivals, “ze police has stop ze production!”
“What do you know about it!” exclaimed someone in the crowd of
newcomers, evidently one of those addressed. “Where’s Belle?”
“She is bringing zeze caboose! Up ze rivaire!” cried the black haired
man, wringing his hands in distress.
The plain clothes men looked over the band of people that stood around
him. There was nothing about them to indicate their desperate character.
Instead of being Italians as they had expected, they seemed to be mostly
Americans. The leader of the policemen suddenly looked hard at Venoti.
“Say,” he said, “you look like a Dago, but you don’t talk like one. Who
are you, anyway?”
“I am Felix Larue,” said the black haired man, “I am ze director of ze
Great Western Film Company, and zeze are all my actors. We have rent zis
house and farm for ze production of ze war play ‘Ze Honor of a Soldier.’
Last night we bring some of ze properties to ze house; zey are very
valuable, and Chambers and Bushbower here zey stay in ze house wiz zem.”
The plain clothes men looked at each other and started to grin. Migwan
and Gladys, who had joined the company on the porch, suddenly felt
unutterably foolish. “But what were you doing on top of the pole?”
faltered Migwan.
Mr. Larue turned his eyes toward her. He recognized her as the girl who
had allowed him to use her telephone the day before, and favored her
with a polite bow. “Me,” he said, “I play ze part of ze spy in ze
piece—ze villain. I tap ze wire and get ze message. I was practice for
ze part zis morning.” He turned beseechingly to the policeman who had
questioned him. “Zen you will not stop ze production?” he asked.
“Heavens, no,” answered the policeman. “We were going to arrest you for
an anarchist, that’s all.”
The company of actors were dissolving into hysterical laughter, in which
the plain clothes men joined sheepishly. Just then a young woman came
around the house from the back, followed at a short distance by Nyoda,
Sahwah and Hinpoha. Seeing the crowd in front she stopped in surprise.
Larue went to the edge of the porch and called to her reassuringly.
“Come on, Belle,” he called, gaily. When she was up on the porch he took
her by the hand and led her forward. “Permit me to introduce my fellow
conspirator,” he said, in a theatrical manner and with a low bow. “Zis
is Belle Mortimer, ze leading lady of ze Great Western Film Company!”
CHAPTER VII.—MOVING PICTURES.
The Winnebagos looked at each other speechlessly. Belle Mortimer, the
famous motion picture actress, whom they had seen on the screen dozens
of times, and for whom Migwan had long entertained a secret and
devouring adoration! Not Bella Venoti at all! “Did you ever?” gasped
Sahwah.
“No, I never,” answered the Winnebagos, in chorus.
Miss Mortimer recognized her hostesses of the day before and greeted
them warmly. “My kind friends from Onoway House,” she called them. The
Winnebagos were embarrassed to death to have to explain how they had
spied on the vacant house and thought the famous Venoti gang was at
work, and were themselves responsible for the presence of the policemen.
“I never _heard_ of anything so funny,” she said, laughing until the
tears came. “I _never_ heard of anything so funny!” The plain clothes
men departed in their automobile, disappointed at not having made the
grand capture they had expected to. “Would you like to stay with us for
the day and watch us work?” asked Miss Mortimer.
“Oh, could we?” breathed Migwan. She was in the seventh heaven at the
thought of being with Belle Mortimer so long. Then followed a day of
delirious delight. To begin with, the Winnebagos were introduced to the
whole company, many of whose names were familiar to them. Felix Larue,
having gotten over the fright he had received when he thought the piece
was going to be suppressed by the police for some unaccountable reason,
was all smiles and amiability, and explained anything the girls wanted
to know about. The piece was a very exciting one, full of thrilling
incidents and danger, and the girls were held spellbound at the physical
feats which some of those actors performed. The house on the raft was
explained as the play progressed. It was filled with soldiers and towed
up the river, to all appearances merely a garage being moved by its
owner. But when a dispatch bearer of the enemy, whose family lived in
the house, stopped to see them while he was carrying an important
message, the soldiers rushed out from the garage, sprang ashore, seized
the man along with the message and carried him away in the launch, which
had been cut away from the raft while the capture was being made. Migwan
thought of the tame little plots she had written the winter before and
was filled with envy at the creator of this stirring play.
It took a whole week to make the film of “The Honor of a Soldier” and in
that time the girls saw a great deal of Miss Mortimer. And one blessed
night she stayed at Onoway House with them, instead of motoring back to
the city with the rest of the company. Just as Migwan was dying of
admiration for her, so she was attracted by this dreamy-eyed girl with
the lofty brow. In a confidential moment Migwan confessed that she had
written several motion picture plays the winter before, all of which had
been rejected. “Do you mind if I see them?” asked Miss Mortimer. Much
embarrassed, Migwan produced the manuscripts, written in the form
outlined in the book she had bought. Miss Mortimer read them over
carefully, while Migwan awaited her verdict with a beating heart.
“Well?” she asked, when Miss Mortimer had finished reading them.
“Who told you to put them in this form?” asked Miss Mortimer.
“I learned it from a book,” answered Migwan.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m?” she asked, impatient for Miss Mortimer’s opinion.
hastily, blushing a little, and stretching out her hand to receive it.
“Oh, miss!” said he, returning it carelessly, “I hope there’s no offence.
I meant but to serve you, that’s all. Such a rare piece of china-work
has no cause to go a-begging,” added he. Then, putting the Flora
deliberately into the case, and turning the key with a jerk, he let it
drop into his pocket; when, lifting up his box by the leather straps, he
was preparing to depart.
“Oh, stay one minute!” said Cecilia, in whose mind there had passed a
very warm conflict during the peddler’s harangue. “Louisa would so like
this Flora,” said she, arguing with herself. “Besides, it would be so
generous in me to give it to her instead of that ugly mandarin; that
would be doing only common justice, for I promised it to her, and she
expects it. Though, when I come to look at this mandarin, it is not even
so good as hers was. The gilding is all rubbed off, so that I absolutely
must buy this for her. Oh, yes! I will, and she will be so delighted!
and then everybody will say it is the prettiest thing they ever saw, and
the broken mandarin will be forgotten for ever.”
Here Cecilia’s hand moved, and she was just going to decide: “Oh, but
stop,” said she to herself, “consider—Leonora gave me this box, and it is
a keepsake. However, we have now quarrelled, and I dare say that she
would not mind my parting with it. I’m sure that I should not care if
she was to give away my keepsake, the smelling-bottle, or the ring which
I gave her. Then what does it signify? Besides, is it not my own? and
have I not a right to do what I please with it?”
At this moment, so critical for Cecilia, a party of her companions opened
the door. She knew that they came as purchasers, and she dreaded her
Flora’s becoming the prize of some higher bidder. “Here,” said she,
hastily putting the box into the peddler’s hand, without looking at it;
“take it, and give me the Flora.” Her hand trembled, though she snatched
it impatiently. She ran by, without seeming to mind any of her
companions.
Let those who are tempted to do wrong by the hopes of future
gratification, or the prospect of certain concealment and impunity,
remember that, unless they are totally depraved, they bear in their own
hearts a monitor, who will prevent their enjoying what they ill obtained.
In vain Cecilia ran to the rest of her companions, to display her
present, in hopes that the applause of others would restore her own
self-complacency; in vain she saw the Flora pass in due pomp from hand to
hand, each vying with the other in extolling the beauty of the gift and
the generosity of the giver. Cecilia was still displeased with herself,
with them, and even with their praise. From Louisa’s gratitude, however,
she yet expected much pleasure, and immediately she ran upstairs to her
room.
In the meantime, Leonora had gone into the hall to buy a bodkin; she had
just broken hers. In giving her change, the peddler took out of his
pocket, with some halfpence, the very box which Cecilia had sold to him.
Leonora did not in the least suspect the truth, for her mind was above
suspicion; and besides, she had the utmost confidence in Cecilia.
“I should like to have that box,” said she, “for it is like one of which
I was very fond.”
The peddler named the price, and Leonora took the box. She intended to
give it to little Louisa. On going to her room she found her asleep, and
she sat softly down by her bedside. Louisa opened her eyes.
“I hope I didn’t disturb you,” said Leonora.
“Oh, no. I didn’t hear you come in; but what have you got there?”
“Only a little box; would you like to have it? I bought on purpose for
you, as I thought perhaps it would please you, because it’s like that
which I gave Cecilia.”
“Oh, yes! that out of which she used to give me Barbary drops. I am very
much obliged to you; I always thought that exceedingly pretty, and this,
indeed, is as like it as possible. I can’t unscrew it; will you try?”
Leonora unscrewed it. “Goodness!” exclaimed Louisa, “this must be
Cecilia’s box. Look, don’t you see a great L at the bottom of it?”
Leonora’s colour changed. “Yes,” she replied calmly, “I see that; but it
is no proof that it is Cecilia’s. You know that I bought this box just
now of the peddler.”
“That may be,” said Louisa; “but I remember scratching that L with my own
needle, and Cecilia scolded me for it, too. Do go and ask her if she has
lost her box—do,” repeated Louisa, pulling her by the ruffle, as she did
not seem to listen.
Leonora, indeed, did not hear, for she was lost in thought. She was
comparing circumstances, which had before escaped her attention. She
recollected that Cecilia had passed her as she came into the hall,
without seeming to see her, but had blushed as she passed. She
remembered that the peddler appeared unwilling to part with the box, and
was going to put it again in his pocket with the halfpence. “And why
should he keep it in his pocket, and not show it with his other things?”
Combining all these circumstances, Leonora had no longer any doubt of the
truth, for though she had honourable confidence in her friends, she had
too much penetration to be implicitly credulous.
“Louisa,” she began, but at this instant she heard a step, which, by its
quickness, she knew to be Cecilia’s, coming along the passage. “If you
love me, Louisa,” said Leonora, “say nothing about the box.”
“Nay, but why not? I daresay she had lost it.”
“No, my dear, I’m afraid she has not.” Louisa looked surprised. “But I
have reasons for desiring you not to say anything about it.”
“Well, then, I won’t, indeed.”
Cecilia opened the door, came forward smiling, as if secure of a good
reception, and taking the Flora out of the case, she placed it on the
mantlepiece, opposite to Louisa’s bed. “Dear, how beautiful!” cried
Louisa, starting up.
“Yes,” said Cecilia, “and guess who it’s for.”
“For me, perhaps!” said the ingenuous Louisa.
“Yes, take it, and keep it, for my sake. You know that I broke your
mandarin.”
“Oh, but this is a great deal prettier and larger than that.”
“Yes, I know it is; and I meant that it should be so. I should only have
done what I was bound to do if I had only given you a mandarin.”
“Well,” replied Louisa, “and that would have been enough, surely; but
what a beautiful crown of roses! and then that basket of flowers! they
almost look as if I could smell them. Dear Cecilia, I’m very much
obliged to you; but I won’t take it by way of payment for the mandarin
you broke; for I’m sure you could not help that, and, besides, I should
have broken it myself by this time. You shall give it to me entirely;
and as your keepsake, I’ll keep it as long as I live.”
Louisa stopped short and coloured; the word keepsake recalled the box to
her mind, and all the train of ideas which the Flora had banished.
“But,” said she, looking up wistfully in Cecilia’s face, and holding the
Flora doubtfully, “did you—”
Leonora, who was just quitting the room, turned her head back, and gave
Louisa a look, which silenced her.
Cecilia was so infatuated with her vanity, that she neither perceived
Leonora’s sign nor Louisa’s confusion, but continued showing off her
present, by placing it in various situations, till at length she put it
into the case, and laying it down with an affected carelessness upon the
bed, “I must go now, Louisa. Good-bye,” said she, running up and kissing
her; “but I’ll come again presently,” then, clapping the door after her
she went. But as soon as the formentation of her spirits subsided, the
sense of shame, which had been scarcely felt when mixed with so many
other sensations, rose uppermost in her mind. “What!” said she to
herself, “is it possible that I have sold what I promised to keep for
ever? and what Leonora gave me? and I have concealed it too, and have
been making a parade of my generosity. Oh! what would Leonora, what
would Louisa—what would everybody think of me, if the truth were known?”
Humiliated and grieved by these reflections, Cecilia began to search in
her own mind for some consoling idea. She began to compare her conduct
with that of others of her own age; and at length, fixing her comparison
upon her brother George, as the companion of whom, from her infancy, she
had been habitually the most emulous, she recollected that an almost
similar circumstance had once happened to him, and that he had not only
escaped disgrace, but had acquired glory, by an intrepid confession of
his fault. Her father’s word to her brother, on the occasion, she also
perfectly recollected.
“Come to me, George,” he said holding out his hand, “you are a generous,
brave boy: they who dare to confess their faults will make great and good
men.”
These were his words; but Cecilia, in repeating them to herself, forgot
to lay that emphasis on the word _men_, which would have placed it in
contradistinction to the word women. She willingly believed that the
observation extended equally to both sexes, and flattered herself that
she should exceed her brother in merit if she owned a fault, which sh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so much more difficult to confess. “Yes, but,”
said she, stopping herself, “how can I confess it? This very evening, in
a few hours, the prize will be decided. Leonora or I shall win it. I
have now as good a chance as Leonora, perhaps a better; and must I give
up all my hopes—all that I have been labouring for this month past? Oh,
I never can! If it were but to-morrow, or yesterday, or any day but
this, I would not hesitate; but now I am almost certain of the prize, and
if I win it—well, why then I will—I think I will tell all—yes I will; I
am determined,” said Cecilia.
Here a bell summoned them to dinner. Leonora sat opposite to her, and
she was not a little surprised to see Cecilia look so gay and
unconstrained. “Surely,” said she to herself, “if Cecilia had done that
which I suspect, she would not, she could not, look as she does.” But
Leonora little knew the cause of her gaiety. Cecilia was never in higher
spirits, or better pleased with herself, than when she had resolved upon
a sacrifice or a confession.
“Must not this evening be given to the most amiable? Whose, then, will
it be?” All eyes glanced first at Cecilia, and then at Leonora. Cecilia
smiled; Leonora blushed. “I see that it is not yet decided,” said Mrs.
Villars; and immediately they ran upstairs, amidst confused whisperings.
Cecilia’s voice could be distinguished far above the rest. “How can she
be so happy!” said Leonora to herself. “Oh Cecilia, there was a time
when you could not have neglected me so! when we were always together the
best of friends and companions; our wishes, tastes, and pleasures the
same! Surely she did once love me,” said Leonora; “but now she is quite
changed. She has even sold my keepsake; and she would rather win a
bracelet of hair from girls whom she did not always think so much
superior to Leonora, than have my esteem, my confidence, and my
friendship for her whole life—yes, for her whole life, for I am sure she
will be an amiable woman. Oh, that this bracelet had never been thought
of, or that I were certain of her winning it; for I am sure that I do not
wish to win it from her. I would rather—a thousand times rather—that we
were as we used to be than have all the glory in the world. And how
pleasing Cecilia can be when she wishes to please!—how candid she is!—how
much she can improve herself! Let me be just, though she has offended
me; she is wonderfully improved within this last month. For one fault,
and _that_ against myself, shall I forget all her merits?”
As Leonora said these last words, she could but just hear the voices of
her companions. They had left her alone in the gallery. She knocked
softly at Louisa’s door. “Come in,” said Louisa; “I’m not asleep. Oh,”
said she, starting up with the Flora in her hand, the instant that the
door was opened; “I’m so glad you are come, Leonora, for I did so long to
hear what you all were making such a noise about. Have you forgot that
the bracelet—”
“Oh, yes! is this the evening?” inquired Leonora.
“Well, here’s my white shell for you,” said Louisa. “I’ve kept it in my
pocket this fortnight; and though Cecilia did give me this Flora, I still
love you a great deal better.”
“I thank you, Louisa,” said Leonora, gratefully. “I will take your
shell, and I shall value it as long as I live; but here is a red one, and
if you wish to show me that you love me, you will give this to Cecilia.
I know that she is particularly anxious for your preference, and I am
sure that she deserves it.”
“Yes, if I could I would choose both of you,” said Louisa, “but you know
I can only choose which I like the best.”
“If you mean, my dear Louisa,” said Leonora, “that you like me the best,
I am very much obliged to you, for, indeed, I wish you to love me; but it
is enough for me to know it in private. I should not feel the least more
pleasure at hearing it in public, or in having it made known to all my
companions, especially at a time when it would give poor Cecilia a great
deal of pain.”
“But why should it give her pain?” asked Louisa; “I don’t like her for
being jealous of you.”
“Nay, Louisa, surely you don’t think Cecilia jealous? She only tries to
excel, and to please; she is more anxious to succeed than I am, it is
true, because she has a great deal more activity, and perhaps more
ambition. And it would really mortify her to lose this prize—you know
that she proposed it herself. It has been her object for this month
past, and I am sure she has taken great pains to obtain it.”
“But, dear Leonora, why should you lose it?”
“Indeed, my dear, it would be no loss to me; and, if it were, I would
willingly suffer it for Cecilia; for, though we seem not to be such good
friends as we used to be, I love her very much, and she will love me
again—I’m sure she will; when she no longer fears me as a rival, she will
again love me as a friend.”
Here Leonora heard a number of her companions running along the gallery.
They all knocked hastily at the door, calling “Leonora! Leonora! will you
never come? Cecilia has been with us this half-hour.”
Leonora smiled. “Well, Louisa,” said she, smiling, “will you promise
me?”
“Oh, I am sure, by the way they speak to you, that they won’t give you
the prize!” said the little Louisa, and the tears started into her eyes.
“They love me, though, for all that,” said Leonora; “and as for the
prize, you know whom I wish to have it.”
“Leonora! Leonora!” called her impatient companions; “don’t you hear us?
What are you about?”
“Oh, she never will take any trouble about anything,” said one of the
party; “let’s go away.”
“Oh, go, go! make haste!” cried Louisa; “don’t stay; they are so angry.”
“Remember, then, that you have promised me,” said Leonora, and she left
the room.
During all this time, Cecilia had been in the garden with her companions.
The ambition which she had felt to win the first prize—the prize of
superior talents and superior application—was not to be compared to the
absolute anxiety which she now expressed to win this simple testimony of
the love and approbation of her equals and rivals.
To employ her exuberant activity, Cecilia had been dragging branches of
lilacs and laburnums, roses and sweet briar, to ornament the bower in
which her fate was to be decided. It was excessively hot, but her mind
was engaged, and she was indefatigable. She stood still at last to
admire her works. Her companions all joined in loud applause. They were
not a little prejudiced in her favour by the great eagerness which she
expressed to win their prize, and by the great importance which she
seemed to affix to the preference of each individual. At last, “Where is
Leonora?” cried one of them; and immediately, as we have seen, they ran
to call her.
Cecilia was left alone. Overcome with heat and too violent exertion, she
had hardly strength to support herself; each moment appeared to her
intolerably long. She was in a state of the utmost suspense, and all her
courage failed her. Even hope forsook her; and hope is a cordial which
leaves the mind depressed and enfeebled.
“The time is now come,” said Cecilia; “in a few moments all will be
decided. In a few moments—goodness! How much do I hazard? If I should
not win the prize, how shall I confess what I have done? How shall I beg
Leonora to forgive me? I, who hoped to restore my friendship to her as
an honour! They are gone to seek for her. The moment she appears I
shall be forgotten. What—what shall I do?” said Cecilia, covering her
face with her hands.
Such was Cecilia’s situation when Leonora, accompanied by her companions,
opened the hall door. They most of them ran forwards to Cecilia. As
Leonora came into the bower, she held out her hand to Cecilia. “We are
not rivals, but friends, I hope,” said she. Cecilia clasped her hand;
but she was in too great agitation to speak.
The table was now set in the arbour—the vase was now placed in the
middle. “Well!” said Cecilia, eagerly, “who begins?” Caroline, one of
her friends, came forward first, and then all the others successively.
Cecilia’s emotion was hardly conceivable. “Now they are all in! Count
them, Caroline!”
“One, two, three, four; the numbers are both equal.” There was a dead
silence. “No, they are not,” exclaimed Cecilia, pressing forward, and
putting a shell into a vase. “I have not given mine, and I give it to
Leonora.” Then, snatching the bracelet, “It is yours, Leonora,” said
she; “take it, and give me back your friendship.” The whole assembly
gave one universal clap and a general shout of applause.
“I cannot be surprised at this from you, Cecilia,” said Leonora; “and do
you then still love me as you used to do?”
“Oh, Leonora, stop! don’t praise me; I don’t deserve this,” said she,
turning to her loudly applauding companions. “You will soon despise me.
Oh, Leonora, you will never forgive me! I have deceived you; I have
sold—”
At this instant, Mrs. Villars appeared. The crowd divided. She had
heard all that passed, from her window. “I applaud your generosity,
Cecilia,” said she, “but I am to tell you that, in this instance it is
unsuccessful. You have not it in your power to give the prize to
Leonora. It is yours. I have another vote to give to you. You have
forgotten Louisa.”
“Louisa!” exclaimed Cecilia; “but surely, ma’am, Louisa loves Leonora
better than she does me.”
“She commissioned me, however,” said Mrs. Villars, “to give you a red
shell; and you will find it in this box.”
Cecilia started, and turned as pale as death; it was the fatal box!
Mrs. Villars produced another box. She opened it; it contained the
Flora. “And Louisa also desired me,” said she, “to return to you this
Flora.” She put it into Cecilia’s hand. Cecilia trembled so that she
could not hold it. Leonora caught it.
“Oh, madam! Oh, Leonora!” exclaimed Cecilia; “now I have no hope left.
I intended—I was just going to tell—”
“Dear Cecilia,” said Leonora, “you need not tell it me; I know it
already; and I forgi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Yes, I can prove to you,” said Mrs. Villars, “that Leonora has forgiven
you. It is she who has given you the prize; it was she who persuaded
Louisa to give you her vote. I went to see her a little while ago; and
perceiving, by her countenance, that something was the matter, I pressed
her to tell me what it was.
“‘Why, madam,’ said she, ‘Leonora has made me promise to give my shell to
Cecilia. Now I don’t love Cecilia half so well as I do Leonora.
Besides, I would not have Cecilia think I vote for her because she gave
me a Flora.’ Whilst Louisa was speaking,” continued Mrs. Villars, “I saw
this silver box lying on the bed. I took it up, and asked if it was not
yours, and how she came by it. ‘Indeed, madam,’ said Louisa, ‘I could
have been almost certain that it was Cecilia’s; but Leonora gave it me,
and she said that she bought it of the peddler this morning. If anybody
else had told me so, I could not have believed them, because I remember
the box so well; but I can’t help believing Leonora.’ But did not you
ask Cecilia about it? said I. ‘No, madam,’ replied Louisa; ‘for Leonora
forbade me. I guessed her reason.’ Well, said I, give me the box, and I
will carry your shell in it to Cecilia. ‘Then, madam,’ said she, ‘if I
must give it her, pray do take the Flora, and return it to her first,
that she may not think it is for that I do it.’”
“Oh, generous Louisa!” exclaimed Cecilia; “but, indeed, Leonora, I cannot
take your shell.”
“Then, dear Cecilia, accept of mine instead of it! you cannot refuse it;
I only follow your example. As for the bracelet,” added Leonora, taking
Cecilia’s hand, “I assure you I don’t wish for it, and you do, and you
deserve it.”
“No,” said Cecilia, “indeed, I do not deserve it. Next to you, surely
Louisa deserves it best.”
“Louisa! oh, yes, Louisa,” exclaimed everybody with one voice.
“Yes,” said Mrs. Villars, “and let Cecilia carry the bracelet to her; she
deserves that reward. For one fault I cannot forget all your merits,
Cecilia, nor, I am sure, will your companions.”
“Then, surely, not your best friend,” said Leonora, kissing her.
Everybody present was moved. They looked up to Leonora with respectful
and affectionate admiration.
“Oh, Leonora, how I love you! and how I wish to be like you!” exclaimed
Cecilia—“to be as good, as generous!”
“Rather wish, Cecilia,” interrupted Mrs. Villars, “to be as just; to be
as strictly honourable, and as invariably consistent. Remember, that
many of our sex are capable of great efforts—of making what they call
great sacrifices to virtue or to friendship; but few treat their friends
with habitual gentleness, or uniformly conduct themselves with prudence
and good sense.”
THE LITTLE MERCHANTS.
CHAPTER I.
_Chi di gallina nasce_, _convien che rozole_.
As the old cock crows, so crows the young.
THOSE who have visited Italy give us an agreeable picture of the cheerful
industry of the children of all ages in the celebrated city of Naples.
Their manner of living and their numerous employments are exactly
described in the following “Extract from a Traveller’s Journal.” {301}
“The children are busied in various ways. A great number of them bring
fish for sale to town from Santa Lucia; others are very often seen about
the arsenals, or wherever carpenters are at work, employed in gathering
up the chips and pieces of wood; or by the sea-side, picking up sticks,
and whatever else has drifted ashore, which, when their basket is full,
they carry away.
“Children of two or three years old, who can scarcely crawl along upon
the ground, in company with boys of five or six, are employed in this
pretty trade. Hence they proceed with their baskets into the heart of
the city, where in several places they form a sort of little market,
sitting round with their stock of wood before them. Labourers, and the
lower order of citizens, buy it of them to burn in the tripods for
warming themselves, or to use in their scanty kitchens.
“Other children carry about for sale the water of the sulphurous wells,
which, particularly in the spring season, is drunk in great abundance.
Others again endeavour to turn a few pence by buying a small matter of
fruit, of pressed honey, cakes, and comfits, and then, like little
peddlers, offer and sell them to other children, always for no more
profit than that they may have their share of them free of expense.
[Picture: The Little Merchants]
“It is really curious to see how an urchin, whose whole stock and
property consist in a board and a knife, will carry about a water-melon,
or a half roasted gourd, collect a troup of children round him, set down
his board, and proceed to divide the fruit into small pieces among them.
“The buyers keep a sharp look out to see that they have enough for their
little piece of copper; and the Lilliputian tradesmen act with no less
caution as the exigencies of the case may require, to prevent his being
cheated out of a morsel.”
The advantages of truth and honesty, and the value of a character for
integrity, are very early felt amongst these little merchants in their
daily intercourse with each other. The fair dealer is always sooner or
later seen to prosper. The most cunning cheat is at last detected and
disgraced.
Numerous instances of the truth of this common observation were remarked
by many Neapolitan children, especially by those who were acquainted with
the characters and history of Piedro and Francisco, two boys originally
equal in birth, fortune and capacity, but different in their education,
and consequently in their habits and conduct. Francisco was the son of
an honest gardener, who, from the time he could speak, taught him to love
to speak the truth, showed him that liars are never believed—that cheats
and thieves cannot be trusted, and that the shortest way to obtain a good
character is to deserve it.
Youth and white paper, as the proverb says, take all impressions. The
boy profited much by his father’s precepts, and more by his example; he
always heard his father speak the truth, and saw that he dealt fairly
with everybody. In all his childish traffic, Francisco, imitating his
parents, was scrupulously honest, and therefore all his companions
trusted him—“As honest as Francisco,” became a sort of proverb amongst
them.
“As honest as Francisco,” repeated Piedro’s father, when he one day heard
this saying. “Let them say so; I say, ‘As sharp as Piedro’; and let us
see which will go through the world best.” With the idea of making his
son _sharp_ he made him cunning. He taught him, that to make a _good
bargain_ was to deceive as to the value and price of whatever he wanted
to dispose of; to get as much money as possible from customer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ir ignorance or of their confidence. He often repeated
his favourite proverb—“The buyer has need of a hundred eyes; the seller
has need but of one.” {302} And he took frequent opportunities of
explaining the meaning of this maxim to his son. He was a fisherman; and
as his gains depended more upon fortune than upon prudence, he trusted
habitually to his good luck. After being idle for a whole day, he would
cast his line or his nets, and if he was lucky enough to catch a fine
fish, he would go and show it in triumph to his neighbour the gardener.
“You are obliged to work all day long for your daily bread,” he would
say. “Look here; I work but five minutes, and I have not only daily
bread, but daily fish.”
Upon these occasions, our fisherman always forgot, or neglected to count,
the hours and days which were wasted in waiting for a fair wind to put to
sea, or angling in vain on the shore.
Little Piedro, who used to bask in the sun upon the sea-shore beside his
father, and to lounge or sleep away his time in a fishing-boat, acquired
habits of idleness, which seemed to his father of little consequence
whilst he was _but a child_.
“What will you do with Piedro as he grows up, neighbour?” said the
gardener. “He is smart and quick enough, but he is always in mischief.
Scarcely a day has passed for this fortnight but I have caught him
amongst my grapes. I track his footsteps all over my vineyard.”
“_He is but a child_ yet, and knows no better,” replied the fisherman.
“But if you don’t teach him better now he is a child, how will he know
when he is a man?” said the gardener.
“A mighty noise about a bunch of grapes, truly!” cried the fisherman: “a
few grapes more or less in your vineyard, what does it signify?”
“I speak for your son’s sake, and not for the sake of my grapes,” said
the gardener; “and I tell you again, the boy will not do well in the
world, neighbour, if you don’t look after him in time.”
“He’ll do well enough in the world, you will find,” answered the
fisherman, carelessly. “Whenever he casts my nets, they never come up
empty. ‘It is better to be lucky than wise.’” {303a}
This was a proverb which Piedro had frequently heard from his father, and
to which he most willingly trusted, because it gave him less trouble to
fancy himself fortunate than to make himself wise.
“Come here, child,” said his father to him, when he returned home after
the preceding conversation with the gardener; “how old are you, my
boy?—twelve years old, is not it?”
“As old as Francisco, and older by six months,” said Piedro.
“And smarter and more knowing by six years,” said his father. “Here,
take these fish to Naples, and let us see how you’ll sell them for me.
Venture a small fish, as the proverb says, to catch a great one. {303b}
I was too late with them at the market yesterday, but nobody will know
but what they are just fresh out of the water, unless you go and tell
them.”
“Not I; trust me for that; I’m not such a fool,” replied Piedro,
laughing; “I leave that to Francisco. Do you know, I saw him the other
day miss selling a melon for his father by turning the bruised side to
the customer, who was just laying down the money for it, and who was a
raw servant-boy, moreover—one who would never have guessed there were two
sides to a melon, if he had not, as you say, father, been told of it?”
“Off with you to market. You are a droll chap,” said his father, “and
will sell my fish cleverly, I’ll be bound. As to the rest, let every man
take care of his own grapes. You understand me, Piedro?”
“Perfectly,” said the boy, who perceived that his father was indifferent
as to his honesty, provided he sold fish at the highest price possible.
He proceeded to the market, and he offered his fish with assiduity to
every person whom he thought likely to buy it, especially to those upon
whom he thought he could impose. He positively asserted to all who
looked at his fish, that they were just fresh out of the water. Good
judges of men and fish knew that he said what was false, and passed him
by with neglect; but it was at last what he called _good luck_ to meet
with the very same young raw servant-boy who would have bought the
bruised melon from Francisco. He made up to him directly, crying, “Fish!
Fine fresh fish! fresh fish!”
“Was it caught to-day?” said the boy.
“Yes, this morning; not an hour ago,” said Piedro, with the greatest
effrontery.
The servant-boy was imposed upon; and being a foreigner, speaking the
Italian language but imperfectly, and not being expert at reckoning the
Italian money, he was no match for the cunning Piedro, who cheated him
not only as to the freshness, but as to the price of the commodity.
Piedro received nearly half as much again for his fish as he ought to
have done.
On his road homewards from Naples to the little village of Resina, where
his father lived, he overtook Francisco, who was leading his father’s
ass. The ass was laden with large panniers, which were filled with the
stalks and leaves of cauliflowers, cabbages, broccoli, lettuces, etc.—all
the refuse of the Neapolitan kitchens, which are usually collected by the
gardeners’ boys, and carried to the gardens round Naples, to be mixed
with other manure.
“Well filled panniers, truly,” said Piedro, as he overtook Francisco and
the ass. The panniers were indeed not only filled to the top, but piled
up with much skill and care, so that the load met over the animal’s back.
“It is not a very heavy load for the ass, though it looks so large,” said
Francisco. “The poor fellow, however, shall have a little of this
water,” added he, leading the ass to a pool by the roadside.
“I was not thinking of the ass, boy; I was not thinking of any ass, but
of you, when I said, ‘Well filled panniers, truly!’ This is your
morning’s work, I presume, and you’ll make another journey to Naples
to-day, on the same errand, I warrant, before your father thinks you have
done enough?”
“Not before _my father_ thinks I have done enough, but before I think so
myself,” replied Francisco.
“I do enough to satisfy myself and my father, too,” said Piedro, “without
slaving myself after your fashion. Look here,” producing the money he
had received for the fish; “all this was had for asking. It is no bad
thing, you’ll allow, to know how to ask for money properly.”
“I should be ashamed to beg, or borrow either,” said Francisco.
“Neither did I get what you see by begging, or borrowing either,” said
Piedro, “but by using my wits; not as you did yesterday, when, like a
novice, you showed the bruised side of your melon, and so spoiled your
market by your wisdom.”
“Wisdom I think it still,” said Francisco.
“And your father?” asked Piedro.
“And my father,” said Francisco.
“Mine is of a different way of thinking,” said Piedro. “He always tells
me that the buyer has need of a hundred eyes, and if one can blind the
whole hundred, so much the better. You must know, I got off the fish
to-day that my father could not sell yesterday in the market—got it off
for fresh just out of the river—got twice as much as the market price for
it; and from whom, think you? Why, from the very booby that would have
bought the bruised melon for a sound one if you would have let him.
You’ll allow I’m no fool, Francisco, and that I’m in a fair way to grow
rich, if I go on as I have begun.”
“Stay,” said Francisco; “you forgot that the booby you took in to-day
will not be so easily taken in to-morrow. He will buy no more fish from
you, because he will be afraid of your cheating him; but he will be ready
enough to buy fruit from me, because he will know I shall not cheat
him—so you’ll have lost a customer, and I gained one.”
“With all my heart,” said Piedro. “One customer does not make a market;
if he buys no more from me, what care I? there are people enough to buy
fish in Naples.”
“And do you mean to serve them all in the same manner?” asked Francisco.
“If they will be only so good as to give me leave,” said Piedro,
laughing, and repeating his father’s proverb, “‘Venture a small fish to
catch a large one.’” {306} He had learned to think that to cheat in
making bargains was witty and clever.
“And you have never considered, then,” said Francisco, “that all these
people will, one after another, find you out in time?”
“Ay, in time; but it will be some time first. There are a great many of
them, enough to last me all the summer, if I lose a customer a day,” said
Piedro.
“And next summer,” observed Francisco, “what will you do?”
“Next summer is not come yet; there is time enough to think what I shall
do before next summer comes. Why, now, suppose the blockheads, after
they had been taken in and found it out, all joined against me, and would
buy none of our fish—what then? Are there no trades but that of a
fisherman? In Naples, are there not a hundred ways of making money for a
smart lad like me? as my father says. What do you think of turning
merchant, and selling sugar-plums and cakes to the children in their
market? Would they be hard to deal with, think you?”
“I think not,” said Francisco; “but I think the children would find out
in time if they were cheated, and would like it as little as the men.”
“I don’t doubt them. Then _in time_ I could, you know, change my
trade—sell chips and sticks in the wood-market—hand about the lemonade to
the fine folks, or twenty other things. There are trades enough, boy.”
“Yes, for the honest dealer,” said Francisco, “but for no other; for in
all of them you’ll find, as _my_ father says, that a good character is
the best fortune to set up with. Change your trade ever so often, you’ll
be found out for what you are at last.”
“And what am I, pray?” said Piedro, angrily. “The whol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Francisco, that you envy my good luck, and can’t bear to hear
this money jingle in my hand. Ay, stroke the long ears of your ass, and
look as wise as you please. It’s better to be lucky than wise, as _my_
father says. Good morning to you. When I am found out for what I am, or
when the worst comes to the worst, I can drive a stupid ass, with his
panniers filled with rubbish, as well as you do now, _honest Francisco_.”
“Not quite so well. Unless you were _honest Francisco_, you would not
fill his panniers quite so readily.”.
This was certain, that Francisco was so well known for his honesty
amongst all the people at Naples with whom his father was acquainted,
that everyone was glad to deal with him; and as he never wronged anyone,
all were willing to serve him—at least, as much as they could without
loss to themselves: so that after the market was over, his panniers were
regularly filled by the gardeners and others with whatever he wanted.
His industry was constant, his gains small but certain, and he every day
had more and more reason to trust to his father’s maxim—That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The foreign servant lad, to whom Francisco had so honestly, or, as Piedro
said, so sillily, shown the bruised side of the melon, was an Englishman.
He left his native country, of which he was extremely fond, to attend
upon his master, to whom he was still more attached. His master was in a
declining state of health, and this young lad waited on him a little more
to his mind than his other servants. We must, in consideration of his
zeal, fidelity and inexperience, pardon him for not being a good judge of
fish. Though he had simplicity enough to be easily cheated once, he had
too much sense to be twice made a dupe. The next time he met Piedro in
the market, he happened to be in company with several English gentlemen’s
servants, and he pointed Piedro out to them all as an arrant knave. They
heard his cry of “Fresh fish! fresh fish! fine fresh fish!” with
incredulous smiles, and let him pass, but not without some expressions of
contempt, though uttered in English, he tolerably well understood; for
the tone of contempt is sufficiently expressive in all languages. He
lost more by not selling his fish to these people than he had gained the
day before by cheating the _English booby_. The market was well
supplied, and he could not get rid of his cargo.
“Is not this truly provoking?” said Piedro, as he passed by Francisco,
who was selling fruit for his father. “Look, my basket is as heavy as
when I left home and look at ’em yourself, they really are fine fresh
fish to-day and yet, because that revengeful booby told how I took him in
yesterday, not one of yonder crowd would buy them; and all the time they
really are fresh to-day!”
“So they are,” said Franscisco, “but you said so yesterday, when they
were not; and he that was duped then, is not ready to believe you to-day.
How does he know that you deserve it better?”
“He might have looked at the fish,” repeated Piedro; “they are fresh
to-day. I am sure he need not have been afraid.”
“Ay,” said Francisco; “but as my father said to you once—the scalded dog
fears cold water.” {308}
Here their conversation was interrupted by the same English lad, who
smiled as he came up to Francisco, and taking up a fine pine-apple, he
said, in a mixture of bad Italian and English—“I need not look at the
other side of this; you will tell me if it is not as good as it looks.
Name your price; I know you have but one, and that an honest one; and as
to the rest, I am able and willing to pay for what I buy; that is to say,
my master is, which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I wish your fruit could
make him well, and it would be worth its weight in gold to me, at least.
We must have some of your grapes for him.”
“Is he not well?” inquired Francisco. “We must, then, pick out the best
for him,” at the same time singling out a tempting bunch. “I hope he
will like these; but if you could some day come as far as Resina (it is a
village but a few miles out of town, where we have our vineyard), you
could there choose for yourself, and pluck them fresh from the vines for
your poor master.”
“Bless you, my good boy; I should take you for an Englishman, by your way
of dealing. I’ll come to your village. Only write me down the name; for
your Italian names slip through my head. I’ll come to the vineyard if it
was ten miles off; and all the time we stay in Naples (may it not be so
long as I fear it will!), with my master’s leave, which he never refuses
me to anything that’s proper, I’ll deal with you for all our fruit, as
sure as my name’s Arthur, and with none else, with my good will. I wish
all your countrymen would take after you in honesty, indeed I do,”
concluded the Englishman, looking full at Piedro, who took up his unsold
basket of fish, looking somewhat silly, and gloomily walked off.
Arthur, the English servant, was as good as his word. He dealt
constantly with Francisco, and proved an excellent customer, buying from
him during the whole season as much fruit as his master wanted. His
master, who was an Englishman of distinction, was invited to take up his
residence, during his stay in Italy, at the Count de F.’s villa, which
was in the environs of Naples—an easy walk from Resina. Francisco had
the pleasure of seeing his father’s vineyard often full of generous
visitors, and Arthur, who had circulated the anecdote of the bruised
melon, was, he said, “proud to think that some of this was his doing, and
that an Englishman never forgot a good turn, be it from a countryman or
foreigner.”
“My dear boy,” said Francisco’s father to him, whilst Arthur was in the
vineyard helping to tend the vines, “I am to thank you and your honesty,
it seems, for our having our hands so full of business this season. It
is fair you should have a share of our profits.”
“So I have, father, enough and enough, when I see you and mother going on
so well. What can I want more?”
“Oh, my brave boy, we know you are a grateful, good son; but I have been
your age myself; you have companions, you have little expenses of your
own. Here; this vine, this fig-tree, and a melon a week next summer
shall be yours. With these make a fine figure amongst the little
Neapolitan merchants; and all I wish is that you may prosper as well, and
by the same honest means, in managing for yourself, as you have done
managing for me.”
“Thank you, father; and if I prosper at all, it shall be by those means,
and no other, or I should not be worthy to be called your son.”
Piedro the cunning did not make quite so successful a summer’s work as
did Francisco the honest. No extraordinary events happened, no singular
instance of bad or good luck occurred; but he felt, as persons usually
do, the natural consequences of his own actions. He pursued his scheme
of imposing, as far as he could, upon every person he dealt with; and the
consequence was, that at last nobody would deal with him.
“It is easy to outwit one person, but impossible to outwit all the
world,” said a man {309} who knew the world at least as well as either
Piedro or his father.
Piedro’s father, amongst others, had reason to complain. He saw his own
customers fall off from him, and was told, whenever he went into the
market, that his son was such a cheat there was no dealing with him. One
day, when he was returning from the market in a very bad humour, in
consequence of these reproaches, and of his not having found customers
for his goods, he espied his _smart_ son Piedro at a little merchant’s
fruit-board devouring a fine gourd with prodigious greediness. “Where,
glutton, do you find money to pay for these dainties?” exclaimed his
father, coming close up to him, with angry gestures. Piedro’s mouth was
much too full to make an immediate reply, nor did his father wait for
any, but darting his hand into the youth’s pocket, pulled forth a handful
of silver.
“The money, father,” said Piedro, “that I got for the fish yesterday, and
that I meant to give you to-day, before you went out.”
“Then I’ll make you remember it against another time, sirrah!” said his
father. “I’ll teach you to fill your stomach with my money. Am I to
lose my customers by your tricks, and then find you here eating my all?
You are a rogue, and everybody has found you out to be a rogue; and the
worst of rogues I find you, who scruples not to cheat his own father.”
Saying these words, with great vehemence he seized hold of Piedro, and in
the very midst of the little fruit-market gave him a severe beating.
This beating did the boy no good; it was vengeance not punishment.
Piedro saw that his father was in a passion, and knew that he was beaten
because he was found out to be a rogue, rather than for being one. He
recollected perfectly that his father once said to him: “Let everyone
take care of his own grapes.”
Indeed it was scarcely reasonable to expect that a boy who had been
educated to think that he might cheat every customer he could in the way
of trade, should be afterwards scrupulously honest in his conduct towards
the father whose proverbs encouraged his childhood in cunning.
Piedro writhed with bodily pain as he left the market after his drubbing,
but his mind was not in the least amended. On the contrary, he was
hardened to the sense of shame by the loss of reputation. All the little
merchants were spectators of this scene, and heard his father’s words:
“You _are_ a rogue, and the worst of rogues, who scruples not to cheat
his own father.”
These words were long remembered, and long did Piedro feel their effects.
He once flattered himself that, when his trade of selling fish failed
him, he could readily engage in some other; but he now found, to his
mortification, that what Francisco’s father said proved true: “In all
trades the best fortune to set up with is a good character.”
Not one of the little Neapolitan merchants would either enter into
partnership with him, give him credit, or even trade with him for ready
money. “If you would cheat your own father, to be sure you will cheat
us,” was continually said to him by these prudent little people.
Piedro was taunted and treated with contempt at home and abroad. His
father, when he found that his son’s smartness was no longer useful in
making bargains, shoved him out of his way whenever he met him. All the
food or clothes that he had at home seemed to be given to him grudgingly,
and with such expressions as these: “Take that; but it is too good for
you. You must eat this, now, instead of gourds and figs—and be thankful
you have even this.”
Piedro spent a whole winter very unhappily. He expected that all his old
tricks, and especially what his father had said of him in the
market-place, would be soon forgotten; but month passed after month, and
still these things were fresh in the memory of all who had known them.
It is not easy to get rid of a bad character. A very great rogue {311}
was once heard to say, that he would, with all his heart, give ten
thousand pounds for a good character, because he knew that he could make
twenty thousand by it.
Something like this was the sentiment of our cunning hero when he
experienced the evils of a bad reputation, and when he saw the numerous
advantages which Francisco’s good character procured. Such had been
Piedro’s wretched education, that even the hard lessons of experience
could not alter its pernicious effects. He was sorry his knavery had
been detected, but he still thought it clever to cheat, and was secretly
persuaded that, if he had cheated successfully, he should have been
happy. “But I know I am not happy now,” said he to himself one morning,
as he sat alone disconsolate by the sea-shore, dressed in tattered
garments, weak and hungry, with an empty basket beside him. His
fishing-rod, which he held between his knees, bent over the dry sands
instead of into the water, for he was not thinking of what he was about;
his arms were folded, his head hung down, and his ragged hat was slouched
over his face. He was a melancholy spectacle.
Francisco, as he was coming from his father’s vineyard with a large dish
of purple and white grapes upon his head, and a basket of melons and figs
hanging upon his arm, chanced to see Piedro seated in this melancholy
posture. Touched with compassion, Francisco approached him softly; his
footsteps were not heard upon the sands, and Piedro did not perceive that
anyone was near him till he felt something cold touch his hand; he then
started, and, looking up, saw a bunch of grapes, which Francisco was
holding over his head.
“Eat them: you’ll find them very good, I hope,” said Francisco, with a
benevolent smile.
“They are excellent—most excellent, and I am much obliged to you,
Francisco,” said Piedro. “I was very hungry, and that’s what I am now,
without anybody’s caring anything about it. I am not the favourite I was
with my father, but I know it is all my own fault.”
“Well, but cheer up,” said Francisco; “my father always says, ‘One who
knows he has been in fault, and acknowledges it, will scarcely be in
fault again.’ Yes, take as many figs as you will,” continued he; and
held his basket closer to Piedro, who, as he saw, cast a hungry eye upon
one of the ripe figs.
“But,” said Piedro, after he had taken several, “shall not I get you into
a scrape by taking so many? Won’t your father be apt to miss them?”
“Do you think I would give them to you if they were not my own?” said
Francisco, with a sudden glance of indignation.
“Well, don’t be angry that I asked the question; it was only from fear of
getting you into disgrace that I asked it.”
“It would not be easy for anybody to do that, I hope,” said Francisco,
rather proudly.
“And to me less than anybody,” replied Piedro, in an insinuating tone,
“_I_, that am so much obliged to you!”
“A bunch of grapes, and a few figs, are no mighty obligation,” said
Francisco, smiling; “I wish I could do more for you. You seem, indeed,
to have been very unhappy of late. We never see you in the markets as we
used to do.”
“No; ever since my father beat me, and called me rogue before all the
children there, I have never been able to show my face without being
gibed at by one or t’other. If you would but take me along with you
amongst them, and only just _seem_ my friend, for a day or two, or so, it
would quite set me up again; for they all like you.”
“I would rather _be_ than seem your friend, if I could,” said Francisco.
“Ay, to be sure; that would be still better,” said Piedro, observing that
Francisco, as he uttered his last sentence, was separating the grapes and
other fruits into two equal divisions. “To be sure I would rather you
would _be_ than _seem_ a friend to me; but I thought that was too much to
ask at first, though I have a notion, notwithstanding I have been so
_unlucky_ lately—I have a notion you would have no reason to repent of
it. You would find me no bad hand, if you were to try, and take me into
partnership.”
“Partnership!” interrupted Francisco, drawing back alarmed; “I had no
thoughts of that.”
“But won’t you? can’t you?” said Piedro, in a supplicating tone; “_can’t_
you have thoughts of it? You’d find me a very active partner.”
Franscisco still drew back, and kept his eyes fixed upon the ground. He
was embarrassed; for he pitied Piedro, and he scarcely knew how to point
out to him that something more is necessary in a partner in trade besides
activity, and that is honesty.
“Can’t you?” repeated Piedro, thinking that he hesitated from merely
mercenary motives. “You shall have what share of the profits you
please.”
“I was not thinking of the profits,” said Francisco; “but without meaning
to be ill-natured to you, Piedro, I must say that I cannot enter into any
partnership with you at present; but I will do what, perhaps, you will
like as well,” said he, taking half the fruit out of his basket; “you are
heartily welcome to this; try and sell it in the children’s fruit market.
I’ll go on before you, and speak to those I am acquainted with, and tell
them you are going to set up a new character, and that you hope to make
it a good one.”
“Hey, shall I! Thank you for ever, dear Francisco,” cried Piedro,
seizing his plentiful gift of fruit. “Say what you please for me.”
“But don’t make me say anything that is not true,” said Francisco,
pausing.
“No, to be sure not,” said Piedro; “I _do_ mean to give no room for
scandal. If I could get them to trust me as they do you, I should be
happy indeed.”
“That is what you may do, if you please,” said Francisco. “Adieu, I wish
you well with all my heart; but I must leave you now, or I shall be too
late for the market.”
CHAPTER II.
_Chi va piano va sano_, _e anché lontano_.
Fair and softly goes far in a day.
PIEDRO had now an opportunity of establishing a good character. When he
went into the market with his grapes and figs, he found that he was not
shunned or taunted as usual. All seemed disposed to believe in his
intended reformation, and to give him a fair trial.
These favourable dispositions towards him were the consequence of
Francisco’s benevolent representations. He told them that he thought
Piedro had suffered enough to cure him of his tricks, and that it would
be cruelty in them, because he might once have been in fault, to banish
him by their reproaches from amongst them, and thus to prevent him from
the means of gaining his livelihood honestly.
Piedro made a good beginning, and gave what several of the younger
customers thought excellent bargains. His grapes and figs were quickly
sold, and with the money that he got for them he the next day purchased
from a fruit dealer a fresh supply; and thus he went on for some time,
conducting himself with scrupulous honesty, so that he acquired some
credit among his companions. They no longer watched him with suspicious
eyes. They trusted to his measures and weights, and they counted less
carefully the change which they received from him.
The satisfaction he felt from this alteration in their manners was at
first delightful to Piedro; but in proportion to his credit, his
opportunities of defrauding increased; and these became temptations which
he had not the firmness to resist. His old manner of thinking recurred.
“I make but a few shillings a day, and this is but slow work,” said he to
himself. “What signifies my good character, if I make so little by it?”
Light gains, and frequent, make a heavy purse, {314} was one of
Francisco’s proverbs. But Piedro was in too great haste to get rich to
take time into his account. He set his invention to work, and he did not
want for ingenuity, to devise means of cheating without running the risk
of detection. He observed that the younger part of the community were
extremely fond of certain coloured sugar plums, and of burnt almonds.
With the money he had earned by two months’ trading in fruit he laid in a
large stock of what appeared to these little merchants a stock of almonds
and sugar-plums, and he painted in capital gold coloured letters upon his
board, “Sweetest, largest, most admirable sugar-plums of all colours ever
sold in Naples, to be had here; and in gratitude to his numerous
customers, Piedro adds to these, ‘Burnt almonds gratis.’”.
This advertisement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ll who could read; and
many who could not read heard it repeated with delight. Crowds of
children surrounded Piedro’s board of promise, and they all went away the
first day amply satisfied. Each had a full measure of coloured
sugar-plums at the usual price, and along with these a burnt almond
gratis. The burnt almond had such an effect upon the public judgment,
that it was universally allowed that the sugar-plums were, as the
advertisement set forth, the largest, sweetest, most admirable ever sold
in Naples; though all the time they were, in no respect, better than any
other sugar-plums.
It was generally reported that Piedro gave full measure—fuller than any
other board in the city. He measured the sugar-plums in a little cubical
tin box; and this, it was affirmed, he heaped up to the top, and pressed
down before he poured out the contents into the open hands of his
approving customers. This belief, and Piedro’s popularity, continued
longer even than he had expected; and, as he thought his sugar-plums had
secured their reputation with the _generous public_, he gradually
neglected to add burnt almonds gratis.
One day a boy of about ten years old passed carelessly by, whistling as
he went along, and swinging a carpenter’s rule in his hand. “Ha! what
have we here?” cried he, stopping to read what was written on Piedro’s
board. “This promises rarely. Old as I am, and tall of my age, which
makes the matter worse, I am still as fond of sugar-plums as my little
sister, who is five years younger than I. Come, Signor, fill me quick,
for I’m in haste to taste them, two measures of the sweetest, largest,
most admirable sugar-plums in Naples—one measure for myself and one for
my little Rosetta.”
“You’ll pay for yourself and your sister, then,” said Piedro, “for no
credit is given here.”
“No credit do I ask,” replied the lively boy; “when I told you I loved
sugar-plums, did I tell you I loved them, or even my sister, so well as
to run in debt for them? Here’s for myself, and here’s for my sister’s
share,” said he, laying down his money; “and now for the burnt almonds
gratis, my good fellow.”
“They are all out; I have been out of burnt almonds this great while,”
said Piedro.
“Then why are they in your advertisement here?” said Carlo.
“I have not had time to scratch them out of the board.”
“What! not when you have, by your own account, been out of them a great
while? I did not know it required so much time to blot out a few
words—let us try”; and as he spoke, Carlo, for that was the name of
Piedro’s new customer, pulled a bit of white chalk out of his pocket, and
drew a broad score across the line on the board which promised burnt
almonds gratis.
“You are most impatient,” said Piedro; “I shall have a fresh stock of
almonds to-morrow.”
“Why must the board tell a lie to-day?”
“It would ruin me to alter it,” said Piedro.
“A lie may ruin you, but I could scarcely think the truth could.”
“You have no right to meddle with me or my board,” said Piedro, put off
his guard, and out of his usual soft voice of civility, by this last
observation. “My character, and that of my board, are too firmly
established now for any chance customer like you to injure.”
“I never dreamed of injuring you or anyone else,” said Carlo—“I wish,
moreover, you may not injure yourself. Do as you please with your board,
but give me my sugar-plums, for I have some right to meddle with those,
having paid for them.”
“Hold out your hand, then.”
“No, put them in here, if you please; put my sister’s, at least, in here;
she likes to have them in this box: I bought some for her in it
yesterday, and she’ll think they’ll taste the better out of the same box.
But how is this? your measure does not fill my box nearly; you give us
very few sugar-plums for our money.”
“I give you full measure, as I give to everybody.”
“The measure should be an inch cube, I know,” said Carlo; “that’s what
all the little merchants have agreed to, you know.”
“True,” said Piedro, “so it is.”
“And so it is, I must allow,” said Carlo, measuring the outside of it
with the carpenter’s rule which he held in his hand. “An inch every way;
and yet by my eye—and I have no bad one, being used to measuring
carpenter’s work for my father—by my eye I should think this would have
held more sugar-plums.”
“The eye often deceives us;” said Piedro. “There’s nothing like
measuring, you find.”
“There’s nothing like measuring, I find, indeed,” replied Carlo, as he
looked closely at the end of his rule, which, since he spoke last, he had
put into the cube to take its depth in the inside. “This is not as deep
by a quarter of an inch, Signor Piedro, measured within as it is measured
without.”
Piedro changed colour terribly, and seizing hold of the tin box,
endeavoured to wrest it from the youth who measured so accurately. Carlo
held his prize fast, and lifting it above his head, he ran into the midst
of the square where the little market was held, exclaiming, “A discovery!
a discovery! that concerns all who love sugar-plums. A discovery! a
discovery that concerns all who have ever bought the sweetest, and most
admirable sugar-plums ever sold in Naples.”
The crowd gathered from all parts of the square as he spoke.
“We have bought,” and “We have bought of those sugar-plums,” cried
several little voices at once, “if you mean Piedro’s.”
“The same,” continued Carlo—“he who, out of gratitude to his numerous
customers, gives, or promises to give, burnt almonds gratis.”
“Excellent they were!” cried several voices. “We all know Piedro well;
but what’s your discovery?”
“My discovery is,” said Carlo, “that you, none of you, know Piedro. Look
you here; look at this box—this is his measure; it has a false bottom—it
holds only three-quarters as much as it ought to do; and his numerous
customers have all been cheated of one-quarter of every measure of the
admirable sugar-plums they have bought from him. ‘Think twice of a good
bargain,’ says the proverb.”
“So we have been finely duped, indeed,” cried some of the bystanders,
looking at one another with a mortified air. “Full of courtesy, full of
craft!” {317} “So this is the meaning of his burnt almonds gratis,”
cried others; all joined in an uproar of indignation, except one, who, as
he stood behind the rest, expressed in his countenance silent surprise
and sorrow.
“Is this Piedro a relation of yours?” said Carlo, going up to this silent
person. “I am sorry, if he be, that I have published his disgrace, for I
would not hurt _you_. You don’t sell sugar-plums as he does, I’m sure;
for my little sister Rosetta has often bought from you. Can this Piedro
be a friend of yours?”
“I wished to have been his friend; but I see I can’t,” said Francisco.
“He is a neighbour of ours, and I pitied him; but since he is at his old
tricks again, there’s an end of the matter. I have reason to be obliged
to you, for I was nearly taken in. He has behaved so well for some time
past, that I intended this very evening to have gone to him, and to have
told him that I was willing to do for him what he has long begged of me
to do—to enter into partnership with him.”
“Francisco! Francisco!—your measure, lend us your measure!” exclaimed a
number of little merchants crowding round him. “You have a measure for
sugar-plums; and we have all agreed to refer to that, and to see how much
we have been cheated before we go to br
conduct. “Why could not you, any of you, stay one minute to help me?”
said he.
“We did not hear you call,” answered one.
“I was so frightened,” said another, “I would not have turned back for
the whole world.”
“And you, Tarlton?”
“I,” said Tarlton; “had not I enough to do to take care of myself, you
blockhead? Everyone for himself in this world!”
“So I see,” said Loveit, gravely.
“Well, man! is there anything strange in that?”
“Strange! why, yes; I thought you all loved me!”
“Lord love you, lad! so we do; but we love ourselves better.”
“Hardy would not have served me so, however,” said Loveit, turning away
in disgust. Tarlton was alarmed. “Pugh!” said he; “what nonsense have
you taken into your brain! Think no more about it. We are all very
sorry, and beg your pardon; come, shake hands, forgive and forget.”
Loveit gave his hand, but gave it rather coldly. “I forgive it with all
my heart,” said he; “but I cannot forget it so soon!”
“Why, then, you are not such a good humoured fellow as we thought you
were. Surely you cannot bear malice, Loveit.” Loveit smiled, and
allowed that he certainly could not bear malice. “Well, then, come; you
know at the bottom we all love you, and would do anything in the world
for you.” Poor Loveit, flattered in his foible, began to believe that
they did love him at the bottom, as they said, and even with his eyes
open consented again to be duped.
“How strange it is,” thought he, “that I should set such value upon the
love of those I despise! When I’m once out of this scrape, I’ll have no
more to do with them, I’m determined.”
Compared with his friend Hardy, his new associates did indeed appear
contemptible; for all this time Hardy had treated him with uniform
kindness, avoided to pry into his secrets, yet seemed ready to receive
his confidence, if it had been offered.
After school in the evening, as he was standing silently beside Hardy,
who was ruling a sheet of paper for him, Tarlton, in his brutal manner,
came up, and seizing him by the arm, cried, “Come along with me, Loveit,
I’ve something to say to you.”
“I can’t come now,” said Loveit, drawing away his arm.
“Ah, do come now,” said Tarlton, in a voice of persuasion.
“Well, I’ll come presently.”
“Nay, but do, pray; there’s a good fellow, come now, because I have
something to say to you.”
“What is it you’ve got to say to me? I wish you’d let me alone,” said
Loveit; yet at the same time he suffered himself to be led away.
Tarlton took particular pains to humour him and bring him into temper
again; and even though he was not very apt to part with his playthings,
went so far as to say, “Loveit, the other day you wanted a top; I’ll give
you mine if you desire it.”
Loveit thanked him, and was overjoyed at the thought of possessing this
top. “But what did you want to say to me just now?”
“Ay, we’ll talk of that presently; not yet—when we get out of hearing.”
“Nobody is near us,” said Loveit.
“Come a little farther however,” said Tarlton, looking round
suspiciously.
“Well now, well?”
“You know the dog that frightened us last night?”
“Yes.”
“It will never frighten us again.”
“Won’t it? how so?”
“Look here,” said Tarlton, drawing something from his pocket wrapped in a
blue handkerchief.
“What’s that?” Tarlton opened it. “Raw meat!” exclaimed Loveit. “How
came you by it?”
“Tom, the servant boy, Tom got it for me; and I’m to give him sixpence.”
“And is it for the dog?”
“Yes; I vowed I’d be revenged on him, and after this he’ll never bark
again.”
“Never bark again! What do you mean? Is it poison?” exclaimed Loveit,
starting back with horror.
“Only poison for _a dog_,” said Tarlton, confused; “you could not look
more shocking if it was poison for a Christian.”
Loveit stood for nearly a minute in profound silence. “Tarlton,” said he
at last, in a changed tone and altered manner, “I did not know you; I
will have no more to do with you.”
“Nay, but stay,” said Tarlton, catching hold of his arm, “stay; I was
only joking.”
“Let go my arm—you were in earnest.”
“But then that was before I knew there was any harm. If you think
there’s any harm?”
“_If_,” said Loveit.
“Why, you know, I might not know; for Tom told me it’s a thing that’s
often done. Ask Tom.”
“I’ll ask nobody! Surely we know better what’s right and wrong than Tom
does.”
“But only just ask him, to hear what he’ll say.”
“I don’t want to hear what he’ll say,” cried Loveit, vehemently: “the dog
will die in agonies—in agonies! There was a dog poisoned at my
father’s—I saw him in the yard. Poor creature! He lay and howled and
writhed himself!”
“Poor creature! Well, there’s no harm done now,” cried Tarlton, in a
hypocritical tone. But though he thought fit to dissemble with Loveit,
he was thoroughly determined in his purpose.
Poor Loveit, in haste to get away, returned to his friend Hardy; but his
mind was in such agitation, that he neither talked nor moved like
himself; and two or three times his heart was so full that he was ready
to burst into tears.
“How good-natured you are to me,” said he to Hardy, as he was trying
vainly to entertain him; “but if you knew—” Here he stopped short, for
the bell for evening prayer rang, and they all took their places, and
knelt down. After prayers, as they were going to bed, Loveit stopped
Tarlton,—“_Well_!” asked he, in an inquiring manner, fixing his eyes upon
him.
“_Well_!” replied Tarlton, in an audacious tone, as if he meant to set
his inquiring eye at defiance.
“What do you mean to do to-night?”
“To go to sleep, as you do, I suppose,” replied Tarlton, turning away
abruptly, and whistling as he walked off.
“Oh, he has certainly changed his mind!” said Loveit to himself, “else he
could not whistle.”
About ten minutes after this, as he and Hardy were undressing, Hardy
suddenly recollected that he had left his new kite out upon the grass.
“Oh,” said he, “it will be quite spoiled before morning!”
“Call Tom,” said Loveit, “and bid him bring it in for you in a minute.”
They both went to the top of the stairs to call Tom; no one answered.
They called again louder, “Is Tom below?”
“I’m here,” answered he at last, coming out of Tarlton’s room with a look
of mixed embarrassment and effrontery. And as he was receiving Hardy’s
commission, Loveit saw the corner of the blue handkerchief hanging out of
his pocket. This excited fresh suspicions in Loveit’s mind; but, without
saying one word, he immediately stationed himself at the window in his
room, which looked out towards the lane; and, as the moon was risen, he
could see if anyone passed that way.
“What are you doing there?” said Hardy, after he had been watching some
time; “why don’t you come to bed?” Loveit returned no answer, but
continued standing at the window. Nor did he watch long in vain.
Presently he saw Tom gliding slowly along a by-path, and get over the
gate into the lane.
“He’s gone to do it!” exclaimed Loveit aloud, with an emotion which he
could not command.
“Who’s gone? to do what?” cried Hardy, starting up.
“How cruel! how wicked!” continued Loveit.
“What’s cruel—what’s wicked? speak out at once!” returned Hardy, in that
commanding tone which, in moments of danger, strong minds feel themselves
entitled to assume towards weak ones. Loveit instantly, though in an
incoherent manner, explained the affair to him. Scarcely had the words
passed his lips, when Hardy sprang up, and began dressing himself without
saying one syllable.
“For God’s sak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said Loveit, in great
anxiety. “They’ll never forgive me! don’t betray me! they’ll never
forgive! pray, speak to me! only say you won’t betray us.”
“I will not betray you, trust to me,” said Hardy: and he left the room,
and Loveit stood in amazement; while, in the meantime, Hardy, in hopes of
overtaking Tom before the fate of the poor dog was decided, ran with all
possible speed across the meadow, then down the lane. He came up with
Tom just as he was climbing the bank into the old man’s garden. Hardy,
too much out of breath to speak, seized hold of him, dragged him down,
detaining him with a firm grasp, whilst he panted for utterance.
“What, Master Hardy, is it you? what’s the matter? what do you want?”
“I want the poisoned meat that you have in your pocket.”
“Who told you that I had any such thing?” said Tom, clapping his hand
upon his guilty pocket.
“Give it me quietly, and I’ll let you off.”
“Sir, upon my word I haven’t! I didn’t!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said Tom, trembling, though he was by far the stronger of the two.
“Indeed,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You do,” said Hardy, with great indignation: and a violent struggle
immediately commenced.
The dog, now alarmed by the voices, began to bark outrageously. Tom was
terrified lest the old man should come out to see what was the matter;
his strength forsook him, and flinging the handkerchief and meat over the
hedge, he ran away with all his speed. The handkerchief fell within
reach of the dog, who instantly snapped at it; luckily it did not come
untied. Hardy saw a pitchfork on a dunghill close beside him, and,
seizing upon it, stuck it into the handkerchief. The dog pulled, tore,
growled, grappled, yelled; it was impossible to get the handkerchief from
between his teeth; but the knot was loosed, the meat, unperceived by the
dog, dropped out, and while he dragged off the handkerchief in triumph,
Hardy, with inexpressible joy, plunged the pitchfork into the poisoned
meat, and bore it away.
Never did hero retire with more satisfaction from a field of battle.
Full of the pleasure of successful benevolence, Hardy tripped joyfully
home, and vaulted over the window sill, when the first object he beheld
was Mr. Power, the usher, standing at the head of the stairs, with his
candle in his hand.
“Come up, whoever you are,” said Mr. William Power, in a stern voice. “I
thought I should find you out at last. Come up, whoever you are!” Hardy
obeyed without reply.—“Hardy!” exclaimed Mr. Power, starting back with
astonishment; “is it you, Mr. Hardy?” repeated he, holding the light to
his face. “Why, sir,” said he, in a sneering tone, “I’m sure if Mr.
Trueman was here he wouldn’t believe his own eyes; but for my part I saw
through you long since; I never liked saints, for my share. Will you
please to do me the favour, sir, if it is not too much trouble, to empty
your pockets.” Hardy obeyed in silence. “Heyday! meat! raw meat! what
next?”
“That’s all,” said Hardy, emptying his pockets inside out.
“This is _all_,” said Mr. Power, taking up the meat.
“Pray, sir,” said Hardy, eagerly, “let that meat be burned, it is
poisoned.”
“Poisoned!” cried Mr. William Power, letting it drop out of his fingers;
“you wretch!” looking at him with a menacing air: “what is all this?
Speak.” Hardy was silent. “Why don’t you speak?” cried he, shaking him
by the shoulder impatiently. Still Hardy was silent. “Down upon your
knees this minute and confess all: tell me where you’ve been, what you’ve
been doing, and who are your accomplices, for I know there is a gang of
you; so,” added he, pressing heavily upon Hardy’s shoulder, “down upon
your knees this minute, and confess the whole, that’s your only way now
to get off yourself. If you hope for _my_ pardon, I can tell you it’s
not to be had without asking for.”
“Sir,” said Hardy, in a firm but respectful voice, “I have no pardon to
ask, I have nothing to confess; I am innocent; but if I were not, I would
never try to get off myself by betraying my companions.”
“Very well, sir! very well! very fine! stick to it, stick to it, I advise
you, and we shall see. And how will you look to-morrow, Mr. Innocent,
when my uncle, the doctor, comes home?”
“As I do now, sir,” said Hardy, unmoved.
His composure threw Mr. Power into a rage too great for utterance.
“Sir,” continued Hardy, “ever since I have been at school, I never told a
lie, and therefore, sir, I hope you will believe me now. Upon my word
and honour, sir, I have done nothing wrong.”
“Nothing wrong? Better and better! what, when I caught you going out at
night?”
“_That_, to be sure, was wrong,” said Hardy, recollecting himself; “but
except that—”
“Except that, sir! I will except nothing. Come along with me, young
gentleman, your time for pardon is past.”
Saying these words, he pulled Hardy along a narrow passage to a small
closet, set apart for desperate offenders, and usually known by the name
of the _Black Hole_. “There, sir, take up your lodging there for
to-night,” said he, pushing him in; “to-morrow I’ll know more, or I’ll
know why,” added he, double locking the door, with a tremendous noise,
upon his prisoner, and locking also the door at the end of the passage,
so that no one could have access to him. “So now I think I have you
safe!” said Mr. William Power to himself, stalking off with steps which
made the whole gallery resound, and which made many a guilty heart
tremble.
The conversation which had passed between Hardy and Mr. Power at the head
of the stairs had been anxiously listened to; but only a word or two here
and there had been distinctly overheard.
The locking of the black hole door was a terrible sound—some knew not
what it portended, and others knew _too well_. All assembled in the
morning with faces of anxiety. Tarlton and Loveit’s were the most
agitated: Tarlton for himself, Loveit for his friend, for himself, for
everybody. Every one of the party, and Tarlton at their head, surrounded
him with reproaches; and considered him as the author of the evils which
hung over them. “How could you do so? and why did you say anything to
Hardy about it? when you had promised, too! Oh! what shall we all do?
what a scrape you have brought us into, Loveit, it’s all your fault!”
“All my fault!” repeated poor Loveit, with a sigh; “well, that is hard.”
“Goodness! there’s the bell,” exclaimed a number of voices at once. “Now
for it!” They all stood in a half circle for morning prayers. They
listened—“Here he is coming! No—Yes—Here he is!” And Mr. William Power,
with a gloomy brow, appeared and walked up to his place at the head of
the room. They knelt down to prayers, and the moment they rose, Mr.
William Power, laying his hand upon the table, cried, “Stand still,
gentlemen, if you please.” Everybody stood stock still; he walked out of
the circle; they guessed that he was gone for Hardy, and the whole room
was in commotion. Each with eagerness asked each what none could answer,
“_Has he told_?” “_What_ has he told?” “Who has he told of?” “I hope
he has not told of me,” cried they.
“I’ll answer for it he has told of all of us,” said Tarlton.
“And I’ll answer for it he has told of none of us,” answered Loveit, with
a sigh.
“You don’t think he’s such a fool, when he can get himself off,” said
Tarlton.
At this instant the prisoner was led in, and as he passed through the
circle, every eye was fixed upon him. His eye fell upon no one, not even
upon Loveit, who pulled him by the coat as he passed—everyone felt almost
afraid to breathe.
“Well, sir,” said Mr. Power, sitting down in Mr. Trueman’s elbow-chair,
and placing the prisoner opposite to him; “well, sir, what have you to
say to me this morning?”
“Nothing, sir,” answered Hardy, in a decided, yet modest manner; “nothing
but what I said last night.”
“Nothing more?”
“Nothing more, sir.”
“But I have something more to say to you, sir, then; and a great deal
more, I promise you, before I have done with you;” and then, seizing him
in a fury, he was just going to give him a severe flogging, when the
schoolroom door opened, and Mr. Trueman appeared, followed by an old man
whom Loveit immediately knew. He leaned upon his stick as he walked, and
in his other hand carried a basket of apples. When they came within the
circle, Mr. Trueman stopped short. “Hardy!” exclaimed he, with a voice
of unfeigned surprise, whilst Mr. William Power stood with his hand
suspended.—“Ay, Hardy, sir,” repeated he. “I told him you’d not believe
your own eyes.”
Mr. Trueman advanced with a slow step. “Now, sir, give me leave,” said
the usher, eagerly drawing him aside, and whispering.
“So, sir,” said Mr. T. when the whisper was done, addressing himself to
Hardy, with a voice and manner which, had he been guilty, must have
pierced him to the heart, “I find I have been deceived in you; it is but
three hours ago that I told your uncle I never had a boy in my school in
whom I placed so much confidence; but, after all this show of honour and
integrity, the moment my back is turned, you are the first to set an
example of disobedience of my orders. Why do I talk of disobeying my
commands—you are a thief!”
“I, sir?” exclaimed Hardy, no longer able to repress his feelings.
“You, sir,—you and some others,” said Mr. Trueman, looking round the room
with a penetrating glance—“you and some others.”
“Ay, sir,” interrupted Mr. William Power, “get that out of him if you
can—ask him.”
“I will ask him nothing; I shall neither put his truth nor his honour to
the trial; truth and honour are not to be expected amongst thieves.”
“I am not a thief! I have never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thieves,” cried
Hardy, indignantly.
“Have you not robbed this old man? Don’t you know the taste of these
apples?” said Mr. Trueman, taking one out of the basket.
“No, sir; I do not. I never touched one of that old man’s apples.”
“Never touched one of them! I suppose this is some vile equivocation;
you have done worse, you have had the barbarity, the baseness, to attempt
to poison his dog; the poisoned meat was found in your pocket last
night.”
“The poisoned meat was found in my pocket, sir; but I never intended to
poison the dog—I saved his life.”
“Lord bless him!” said the old man.
“Nonsense—cunning!” said Mr. Power. “I hope you won’t let him impose
upon you, sir.”
“No, he cannot impose upon me; I have a proof he is little prepared for,”
said Mr. Trueman, producing the blue handkerchief in which the meat had
been wrapped.
Tarlton turned pale; Hardy’s countenance never changed.
“Don’t you know this handkerchief, sir?”
“I do, sir.”
“Is it not yours?”
“No, sir.”
“Don’t you know whose it is?” cried Mr. Power. Hardy was silent.
“Now, gentlemen,” said Mr. Trueman, “I am not fond of punishing you; but
when I do it, you know, it is always in earnest. I will begin with the
eldest of you; I will begin with Hardy, and flog you with my own hands
till this handkerchief is owned.”
“I’m sure it’s not mine,” and “I’m sure it’s none of mine,” burst from
every mouth, whilst they looked at each other in dismay; for none but
Hardy, Loveit and Tarlton knew the secret. “My cane,” said Mr. Trueman,
and Mr. Power handed him the cane. Loveit groaned from the bottom of his
heart. Tarlton leaned back against the wall with a black countenance.
Hardy looked with a steady eye at the cane.
“But first,” said Mr. Trueman, laying down the cane, “let us see.
Perhaps we may find out the owner of this handkerchief another way,”
examining the corners. It was torn almost to pieces; but luckily the
corner that was marked remained.
“J. T.!” cried Mr. Trueman. Every eye turned upon the guilty Tarlton,
who, now as pale as ashes and trembling in every limb, sank down upon his
knees, and in a whining voice begged for mercy. “Upon my word and
honour, sir, I’ll tell you all; I’d never have thought of stealing the
apples if Loveit had not first told me of them; and it was Tom who first
put the poisoning the dog into my head. It was he that carried the meat,
_wasn’t it_?” said he, appealing to Hardy, whose word he knew must be
believed. “Oh, dear sir!” continued he as Mr. Trueman began to move
towards him, “do let me off; pray do let me off this time! I’m not the
only one, indeed, sir! I hope you won’t make me an example for the rest.
It’s very hard I’m to be flogged more than they!”
“I’m not going to flog you.”
“Thank you, sir,” said Tarlton, getting up and wiping his eyes.
“You need not thank me,” said Mr. Trueman. “Take your handkerchief—go
out of this room—out of this house; let me never see you more.”
“If I had any hopes of him,” said Mr. Trueman, as he shut the door after
him;—“if I had any hopes of him, I would have punished him;—but I have
none. Punishment is meant only to make people better; and those who have
any hopes of themselves will know how to submit to it.”
At these words Loveit first, and immediately all the rest of the guilty
party, stepped out of the ranks, confessed their fault, and declared
themselves ready to bear any punishment their master thought proper.
“Oh, they have been punished enough,” said the old man; “forgive them,
sir.”
Hardy looked as if he wished to speak. “Not because you ask it,” said
Mr. Trueman to the guilty penitents, “though I should be glad to oblige
you—it wouldn’t be just; but there,” pointing to Hardy, “there is one who
has merited a reward; the highest I can give him is that of pardoning his
companions.”
Hardy bowed and his face glowed with pleasure, whilst everybody present
sympathized in his feelings.
“I am sure,” thought Loveit, “this is a lesson I shall never forget.”
“Gentlemen,” said the old man, with a faltering voice, “it wasn’t for the
sake of my apples that I spoke; and you, sir,” said he to Hardy, “I thank
you for saving my dog. If you please, I’ll plant on that mount, opposite
the window, a young apple-tree, from my old one. I will water it, and
take care of it with my own hands for your sake, as long as I am able.
And may God bless you!” laying his trembling hand on Hardy’s head; “may
God bless you—I’m sure God _will_ bless all such boys as you are.”
THE BASKET-WOMAN.
“Toute leur étude était de se complaire et de s’entr’aider.” {365a}
PAUL ET VIRGINIE.
AT the foot of a steep, slippery, white hill, near Dunstable, in
Bedfordshire, called Chalk Hill, there is a hut, or rather a hovel, which
travellers could scarcely suppose could be inhabited, if they did not see
the smoke rising from its peaked roof. An old woman lives in this hovel,
{365b} and with her a little boy and girl, the children of a beggar who
died, and left these orphans perishing with hunger. They thought
themselves very happy when the good old woman first took them into her
hut and bid them warm themselves at her small fire, and gave them a crust
of mouldy bread to eat. She had not much to give, but what she had she
gave with good-will. She was very kind to these poor children, and
worked hard at her spinning-wheel and at her knitting, to support herself
and them. She earned money also in another way. She used to follow all
the carriages as they went up Chalk Hill, and when the horses stopped to
take breath or to rest themselves, she put stones behind the carriage
wheels to prevent them from rolling backwards down the steep, slippery
hill.
The little boy and girl loved to stand beside the good natured old
woman’s spinning-wheel when she was spinning, and to talk to her. At
these times she taught them something, which, she said, she hoped they
would remember all their lives. She explained to them what is meant by
telling the truth, and what it is to be honest. She taught them to
dislike idleness, and to wish that they could be useful.
One evening, as they were standing beside her, the little boy said to
her, “Grandmother,” for that was the name by which she liked that these
children should call her—“grandmother, how often you are forced to get up
from your spinning-wheel, and to follow the chaises and coaches up that
steep hill, to put stones underneath the wheels, to hinder them from
rolling back! The people who are in the carriages give you a halfpenny
or a penny for doing this, don’t they?”
“Yes, child.”
“But it is very hard work for you to go up and down that hill. You often
say that you are tired, and then you know that you cannot spin all that
time. Now if we might go up the hill, and put the stones behind the
wheels, you could sit still at your work, and would not the people give
us the halfpence? and could not we bring them all to you? Do, pray, dear
grandmother, try us for one day—to-morrow, will you?”
“Yes,” said the old woman; “I will try what you can do; but I must go up
the hill along with you for the first two or three times, for fear you
should get yourselves hurt.”
So, the next day, the little boy and girl went with their grandmother, as
they used to call her, up the steep hill; and she showed the boy how to
prevent the wheels from rolling back, by putting stones behind them; and
she said, “This is called scotching the wheels;” and she took off the
boy’s hat and gave it to the little girl, to hold up to the
carriage-windows, ready for the halfpence.
When she thought that the children knew how to manage by themselves, she
left them, and returned to her spinning-wheel. A great many carriages
happened to go by this day, and the little girl received a great many
halfpence. She carried them all in her brother’s hat to her grandmother
in the evening; and the old woman smiled, and thanked the children. She
said that they had been useful to her, and that her spinning had gone on
finely, because she had been able to sit still at her wheel all day.
“But, Paul my boy,” said she, “what is the matter with your hand?”
“Only a pinch—only one pinch that I got, as I was putting a stone behind
a wheel of a chaise. It does not hurt me much, grandmother; and I’ve
thought of a good thing for to-morrow. I shall never be hurt again, if
you will only be so good as to give me the old handle of the broken
crutch, grandmother, and the block of wood that lies in the
chimney-corner, and that is of no use. I’ll make it of some use, if I
may have it.”
“Take it then, dear,” said the old woman; “and you’ll find the handle of
the broken crutch under my bed.”
Paul went to work immediately, and fastened one end of the pole into the
block of wood, so as to make something like a dry-rubbing brush. “Look,
grandmamma, look at my _scotcher_. I call this thing my _scotcher_,”
said Paul, “because I shall always scotch the wheels with it. I shall
never pinch my fingers again; my hands, you see, will be safe at the end
of this long stick; and, sister Anne, you need not be at the trouble of
carrying any more stones after me up the hill; we shall never want stones
any more. My scotcher will do without anything else, I hope. I wish it
was morning, and that a carriage would come, that I might run up the
hill, and try my scotcher.”
“And I wish that as many chaises may go by to-morrow as there did to-day,
and that we may bring you as many halfpence, grandmother,” said the
little girl.
“So do I, my dear Anne,” said the old woman; “for I mean that you and
your brother shall have all the money that you get to-morrow. You may
buy some gingerbread for yourselves, or some of those ripe plums that you
saw at the fruit-stall the other day, which is just going into Dunstable.
I told you then that I could not afford to buy such things for you; but
now that you can earn halfpence for yourselves, children, it is fair
should taste a ripe plum and bit of gingerbread for once and a way in
your lives.”
“We’ll bring some of the gingerbread home to her, shan’t we, brother?”
whispered little Anne. The morning came; but no carriages were heard,
though Paul and his sister had risen at five o’clock, that they might be
sure to be ready for early travellers. Paul kept his scotcher poised
upon his shoulder, and watched eagerly at his station at the bottom of
the hill. He did not wait long before a carriage came. He followed it
up the hill; and the instant the postillion called to him, and bid him
stop the wheels, he put his scotcher behind them, and found that it
answered the purpose perfectly well.
Many carriages went by this day, and Paul and Anne received a great many
halfpence from the travellers.
When it grew dusk in the evening, Anne said to her brother—“I don’t think
any more carriages will come by to-day. Let us count the halfpence, and
carry them home now to grandmother.”
“No, not yet,” answered Paul, “let them alone—let them lie still in the
hole where I have put them. I daresay more carriages will come by before
it is quite dark, and then we shall have more halfpence.”
Paul had taken the halfpence out of his hat, and he had put them into a
hole in the high bank by the roadside; and Anne said she would not meddle
with them, and that she would wait till her brother liked to count them;
and Paul said—“If you will stay and watch here, I will go and gather some
blackberries for you in the hedge in yonder field. Stand you hereabouts,
half-way up the hill, and the moment you see any carriage coming along
the road, run as fast as you can and call me.”
Anne waited a long time, or what she thought a long time; and she saw no
carriage, and she trailed her brother’s scotcher up and down till she was
tired. Then she stood still, and looked again, and she saw no carriage;
so she went sorrowfully into the field, and to the hedge where her
brother was gathering blackberries, and she said, “Paul, I’m sadly tired,
_sadly tired_!” said she, “and my eyes are quite strained with looking
for chaises; no more chaises will come to-night; and your scotcher is
lying there, of no use, upon the ground. Have not I waited long enough
for to-day, Paul?”
“Oh, no,” said Paul; “here are some blackberries for you; you had better
wait a little bit longer. Perhaps a carriage might go by whilst you are
standing here talking to me.”
Anne, who was of a very obliging temper, and who liked to do what she was
asked to do, went back to the place where the scotcher lay; and scarcely
had she reached the spot, when she heard the noise of a carriage. She
ran to call her brother, and to their great joy, they now saw four
chaises coming towards them. Paul, as soon as they went up the hill,
followed with his scotcher; first he scotched the wheels of one carriage,
then of another; and Anne was so much delighted with observing how well
the scotcher stopped the wheels, and how much better it was than stones,
that she forgot to go and hold her brother’s hat to the travellers for
halfpence, till she was roused by the voice of a little rosy girl, who
was looking out of the window of one of the chaises. “Come close to the
chaise-door,” said the little girl; “here are some halfpence for you.”
Anne held the hat; and she afterwards went on to the other carriages.
Money was thrown to her from each of them; and when they had all gotten
safely to the top of the hill, she and her brother sat down upon a large
stone by the roadside, to count their treasure. First they began by
counting what was in the hat—“One, two, three, four halfpence.”
“But, oh, brother, look at this!” exclaimed Anne; “this is not the same
as the other halfpence.”
“No, indeed, it is not,” cried Paul, “it is no halfpenny; it is a guinea,
a bright golden guinea!”
“Is it?” said Anne, who had never seen a guinea in her life before, and
who did not know its value; “and will it do as well as a halfpenny to buy
gingerbread? I’ll run to the fruit-stall, and ask the woman; shall I?”
“No, no,” said Paul, “you need not ask any woman, or anybody but me; I
can tell you all about it, as well as anybody in the whole world.”
“The whole world! Oh, Paul, you forgot. Not so well as my grandmother.”
“Why, not so well as my grandmother, perhaps, but, Anne, I can tell you
that you must not talk yourself, Anne, but you must listen to me quietly,
or else you won’t understand what I am going to tell you, for I can
assure you that I don’t think I quite understood it myself, Anne, the
first time my grandmother told it to me, though I stood stock still
listening my best.”
Prepared by this speech to hear something very difficult to be
understood, Anne looked very grave, and her brother explained to her,
that, with a guinea, she might buy two hundred and fifty-two times as
many plums as she could get for a penny.
“Why, Paul, you know the fruit-woman said she would give us a dozen plums
for a penny. Now, for this little guinea, would she give us two hundred
and fifty-two dozen?”
“If she has so many, and if we like to have so many, to be sure she
will,” said Paul, “but I think we should not like to have two hundred and
fifty-two dozen of plums; we could not eat such a number.”
“But we could give some of them to my grandmother,” said Anne.
“But still there would be too many for her, and for us, too,” said Paul,
“and when we had eaten the plums, there would be an end to all the
pleasure. But now I’ll tell you what I am thinking of, Anne, that we
might buy something for my grandmother, that would be very useful to her
indeed, with the guinea—something that would last a great while.”
“What, brother? What sort of thing?”
“Something that she said she wanted very much last winter, when she was
so ill with the rheumatism—something that she said yesterday, when you
were making her bed, she wished she might be able to buy before next
winter.”
“I know, I know what you mean!” said Anne—“a blanket. Oh, yes, Paul,
that will be much better than plums; do let us buy a blanket for her; how
glad she will be to see it! I will make her bed with the new blanket,
and then bring her to see it. But, Paul, how shall we buy a blanket?
Where are blankets to be got?”
“Leave that to me, I’ll manage that. I know where blankets can be got.
I saw one hanging out of a shop the day I went last to Dunstable.”
“You have seen a great many things at Dunstable, brother.”
“Yes, a great many; but I never saw anything there or anywhere else, that
I wished for half so much as I did for the blanket for my grandmother.
Do you remember how she used to shiver with the cold last winter? I’ll
buy the blanket to-morrow. I’m going to Dunstable with her spinning.”
“And you’ll bring the blanket to me, and I shall make the bed very
neatly, that will be all right—all happy!” said Anne, clapping her hands.
“But stay! Hush! don’t clap your hands so, Anne; it will not be all
happy, I’m afraid,” said Paul, and his countenance changed, and he looked
very grave. “It will not be all right, I’m afraid, for there is one
thing we have neither of us thought of, but that we ought to think about.
We cannot buy the blanket, I’m afraid.”
“Why, Paul, why?”
“Because I don’t think this guinea is honestly ours.”
“Nay, brother, but I’m sure it is honestly ours. It was given to us, and
grandmother said all that was given to us to-day was to be our own.”
“But who gave it to you, Anne?”
“Some of the people in those chaises, Paul. I don’t know which of them,
but I daresay it was the little rosy girl.”
“No,” said Paul, “for when she called you to the chaise door, she said,
‘Here’s some halfpence for you.’ Now, if she gave you the guinea, she
must have given it to you by mistake.”
“Well, but perhaps some of the people in the other chaises gave it to me,
and did not give it to me by mistake, Paul. There was a gentleman
reading in one of the chaises and a lady, who looked very good-naturedly
at me, and then the gentleman put down his book and put his head out of
the window, and looked at your scotcher, brother, and he asked me if that
was your own making; and when I said yes, and that I was your sister he
smiled at me, and put his hand into his waistcoat pocket, and threw a
handful of halfpence into the hat, and I daresay he gave us the guinea
along with them because he liked your scotcher so much.”
“Why,” said Paul, “that might be, to be sure, but I wish I was quite
certain of it.”
“Then, as we are not quite certain, had not we best go and ask my
grandmother what she thinks about it?”
Paul thought this was excellent advice; and he was not a silly boy, who
did not like to follow good advice. He went with his sister directly to
his grandmother, showed her the guinea, and told her how they came by it.
“My dear, honest children,” said she, “I am very glad you told me all
this. I am very glad that you did not buy either the plums or the
blanket with this guinea. I’m sure it is not honestly ours. Those who
threw it you gave it you by mistake, I warrant; and what I would have you
do is, to go to Dunstable, and try if you can, at either of the inns find
out the person who gave it to you. It is now so late in the evening that
perhaps the travellers will sleep at Dunstable, instead of going on the
next stage; and it is likely that whosoever gave you a guinea instead of
a halfpenny has found out their mistake by this time. All you can do is
to go and inquire for the gentleman who was reading in the chaise.”
“Oh!” interrupted Paul, “I know a good way of finding him out. I
remember it was a dark green chaise with red wheels: and I remember I
read the innkeeper’s name upon the chaise, ‘_John Nelson_.’ (I am much
obliged to you for teaching me to read, grandmother.) You told me
yesterday, grandmother, that the names written upon chaises are the
innkeepers to whom they belong. I read the name of the innkeeper upon
that chaise. It was John Nelson. So Anne and I will go to both the inns
in Dunstable, and try to find out this chaise—John Nelson’s. Come, Anne;
let us set out before it gets quite dark.”
Anne and her brother passed with great courage the tempting stall that
was covered with gingerbread and ripe plums, and pursued their way
steadily through the streets of Dunstable; but Paul, when he came to the
shop where he had seen the blanket, stopped for a moment, and said, “It
is a great pity, Anne, that the guinea is not ours. However, we are
doing what is honest, and that is a comfort. Here, we must go through
this gateway, into the inn-yard; we are come to the ‘Dun Cow.’”
“Cow!” said Anne, “I see no cow.”
“Look up, and you’ll see the cow over your head,” said Paul—“the sign—the
picture. Come, never mind looking at it now; I want to find out the
green chaise that has John Nelson’s name upon it.”
The next morning Loveit could not help reproaching the party with their
conduct. “Why could not you, any of you, stay one minute to help me?”
said he.
“We did not hear you call,” answered one.
“I was so frightened,” said another, “I would not have turned back for
the whole world.”
“And you, Tarlton?”
“I,” said Tarlton; “had not I enough to do to take care of myself, you
blockhead? Everyone for himself in this world!”
“So I see,” said Loveit, gravely.
“Well, man! is there anything strange in that?”
“Strange! why, yes; I thought you all loved me!”
“Lord love you, lad! so we do; but we love ourselves better.”
“Hardy would not have served me so, however,” said Loveit, turning away
in disgust. Tarlton was alarmed. “Pugh!” said he; “what nonsense have
you taken into your brain! Think no more about it. We are all very
sorry, and beg your pardon; come, shake hands, forgive and forget.”
Loveit gave his hand, but gave it rather coldly. “I forgive it with all
my heart,” said he; “but I cannot forget it so soon!”
“Why, then, you are not such a good humoured fellow as we thought you
were. Surely you cannot bear malice, Loveit.” Loveit smiled, and
allowed that he certainly could not bear malice. “Well, then, come; you
know at the bottom we all love you, and would do anything in the world
for you.” Poor Loveit, flattered in his foible, began to believe that
they did love him at the bottom, as they said, and even with his eyes
open consented again to be duped.
“How strange it is,” thought he, “that I should set such value upon the
love of those I despise! When I’m once out of this scrape, I’ll have no
more to do with them, I’m determined.”
Compared with his friend Hardy, his new associates did indeed appear
contemptible; for all this time Hardy had treated him with uniform
kindness, avoided to pry into his secrets, yet seemed ready to receive
his confidence, if it had been offered.
After school in the evening, as he was standing silently beside Hardy,
who was ruling a sheet of paper for him, Tarlton, in his brutal manner,
came up, and seizing him by the arm, cried, “Come along with me, Loveit,
I’ve something to say to you.”
“I can’t come now,” said Loveit, drawing away his arm.
“Ah, do come now,” said Tarlton, in a voice of persuasion.
“Well, I’ll come presently.”
“Nay, but do, pray; there’s a good fellow, come now, because I have
something to say to you.”
“What is it you’ve got to say to me? I wish you’d let me alone,” said
Loveit; yet at the same time he suffered himself to be led away.
Tarlton took particular pains to humour him and bring him into temper
again; and even though he was not very apt to part with his playthings,
went so far as to say, “Loveit, the other day you wanted a top; I’ll give
you mine if you desire it.”
Loveit thanked him, and was overjoyed at the thought of possessing this
top. “But what did you want to say to me just now?”
“Ay, we’ll talk of that presently; not yet—when we get out of hearing.”
“Nobody is near us,” said Loveit.
“Come a little farther however,” said Tarlton, looking round
suspiciously.
“Well now, well?”
“You know the dog that frightened us last night?”
“Yes.”
“It will never frighten us again.”
“Won’t it? how so?”
“Look here,” said Tarlton, drawing something from his pocket wrapped in a
blue handkerchief.
“What’s that?” Tarlton opened it. “Raw meat!” exclaimed Loveit. “How
came you by it?”
“Tom, the servant boy, Tom got it for me; and I’m to give him sixpence.”
“And is it for the dog?”
“Yes; I vowed I’d be revenged on him, and after this he’ll never bark
again.”
“Never bark again! What do you mean? Is it poison?” exclaimed Loveit,
starting back with horror.
“Only poison for _a dog_,” said Tarlton, confused; “you could not look
more shocking if it was poison for a Christian.”
Loveit stood for nearly a minute in profound silence. “Tarlton,” said he
at last, in a changed tone and altered manner, “I did not know you; I
will have no more to do with you.”
“Nay, but stay,” said Tarlton, catching hold of his arm, “stay; I was
only joking.”
“Let go my arm—you were in earnest.”
“But then that was before I knew there was any harm. If you think
there’s any harm?”
“_If_,” said Loveit.
“Why, you know, I might not know; for Tom told me it’s a thing that’s
often done. Ask Tom.”
“I’ll ask nobody! Surely we know better what’s right and wrong than Tom
does.”
“But only just ask him, to hear what he’ll say.”
“I don’t want to hear what he’ll say,” cried Loveit, vehemently: “the dog
will die in agonies—in agonies! There was a dog poisoned at my
father’s—I saw him in the yard. Poor creature! He lay and howled and
writhed himself!”
“Poor creature! Well, there’s no harm done now,” cried Tarlton, in a
hypocritical tone. But though he thought fit to dissemble with Loveit,
he was thoroughly determined in his purpose.
Poor Loveit, in haste to get away, returned to his friend Hardy; but his
mind was in such agitation, that he neither talked nor moved like
himself; and two or three times his heart was so full that he was ready
to burst into tears.
“How good-natured you are to me,” said he to Hardy, as he was trying
vainly to entertain him; “but if you knew—” Here he stopped short, for
the bell for evening prayer rang, and they all took their places, and
knelt down. After prayers, as they were going to bed, Loveit stopped
Tarlton,—“_Well_!” asked he, in an inquiring manner, fixing his eyes upon
him.
“_Well_!” replied Tarlton, in an audacious tone, as if he meant to set
his inquiring eye at defiance.
“What do you mean to do to-night?”
“To go to sleep, as you do, I suppose,” replied Tarlton, turning away
abruptly, and whistling as he walked off.
“Oh, he has certainly changed his mind!” said Loveit to himself, “else he
could not whistle.”
About ten minutes after this, as he and Hardy were undressing, Hardy
suddenly recollected that he had left his new kite out upon the grass.
“Oh,” said he, “it will be quite spoiled before morning!”
“Call Tom,” said Loveit, “and bid him bring it in for you in a minute.”
They both went to the top of the stairs to call Tom; no one answered.
They called again louder, “Is Tom below?”
“I’m here,” answered he at last, coming out of Tarlton’s room with a look
of mixed embarrassment and effrontery. And as he was receiving Hardy’s
commission, Loveit saw the corner of the blue handkerchief hanging out of
his pocket. This excited fresh suspicions in Loveit’s mind; but, without
saying one word, he immediately stationed himself at the window in his
room, which looked out towards the lane; and, as the moon was risen, he
could see if anyone passed that way.
“What are you doing there?” said Hardy, after he had been watching some
time; “why don’t you come to bed?” Loveit returned no answer, but
continued standing at the window. Nor did he watch long in vain.
Presently he saw Tom gliding slowly along a by-path, and get over the
gate into the lane.
“He’s gone to do it!” exclaimed Loveit aloud, with an emotion which he
could not command.
“Who’s gone? to do what?” cried Hardy, starting up.
“How cruel! how wicked!” continued Loveit.
“What’s cruel—what’s wicked? speak out at once!” returned Hardy, in that
commanding tone which, in moments of danger, strong minds feel themselves
entitled to assume towards weak ones. Loveit instantly, though in an
incoherent manner, explained the affair to him. Scarcely had the words
passed his lips, when Hardy sprang up, and began dressing himself without
saying one syllable.
“For God’s sak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said Loveit, in great
anxiety. “They’ll never forgive me! don’t betray me! they’ll never
forgive! pray, speak to me! only say you won’t betray us.”
“I will not betray you, trust to me,” said Hardy: and he left the room,
and Loveit stood in amazement; while, in the meantime, Hardy, in hopes of
overtaking Tom before the fate of the poor dog was decided, ran with all
possible speed across the meadow, then down the lane. He came up with
Tom just as he was climbing the bank into the old man’s garden. Hardy,
too much out of breath to speak, seized hold of him, dragged him down,
detaining him with a firm grasp, whilst he panted for utterance.
“What, Master Hardy, is it you? what’s the matter? what do you want?”
“I want the poisoned meat that you have in your pocket.”
“Who told you that I had any such thing?” said Tom, clapping his hand
upon his guilty pocket.
“Give it me quietly, and I’ll let you off.”
“Sir, upon my word I haven’t! I didn’t!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said Tom, trembling, though he was by far the stronger of the two.
“Indeed,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You do,” said Hardy, with great indignation: and a violent struggle
immediately commenced.
The dog, now alarmed by the voices, began to bark outrageously. Tom was
terrified lest the old man should come out to see what was the matter;
his strength forsook him, and flinging the handkerchief and meat over the
hedge, he ran away with all his speed. The handkerchief fell within
reach of the dog, who instantly snapped at it; luckily it did not come
untied. Hardy saw a pitchfork on a dunghill close beside him, and,
seizing upon it, stuck it into the handkerchief. The dog pulled, tore,
growled, grappled, yelled; it was impossible to get the handkerchief from
between his teeth; but the knot was loosed, the meat, unperceived by the
dog, dropped out, and while he dragged off the handkerchief in triumph,
Hardy, with inexpressible joy, plunged the pitchfork into the poisoned
meat, and bore it away.
Never did hero retire with more satisfaction from a field of battle.
Full of the pleasure of successful benevolence, Hardy tripped joyfully
home, and vaulted over the window sill, when the first object he beheld
was Mr. Power, the usher, standing at the head of the stairs, with his
candle in his hand.
“Come up, whoever you are,” said Mr. William Power, in a stern voice. “I
thought I should find you out at last. Come up, whoever you are!” Hardy
obeyed without reply.—“Hardy!” exclaimed Mr. Power, starting back with
astonishment; “is it you, Mr. Hardy?” repeated he, holding the light to
his face. “Why, sir,” said he, in a sneering tone, “I’m sure if Mr.
Trueman was here he wouldn’t believe his own eyes; but for my part I saw
through you long since; I never liked saints, for my share. Will you
please to do me the favour, sir, if it is not too much trouble, to empty
your pockets.” Hardy obeyed in silence. “Heyday! meat! raw meat! what
next?”
“That’s all,” said Hardy, emptying his pockets inside out.
“This is _all_,” said Mr. Power, taking up the meat.
“Pray, sir,” said Hardy, eagerly, “let that meat be burned, it is
poisoned.”
“Poisoned!” cried Mr. William Power, letting it drop out of his fingers;
“you wretch!” looking at him with a menacing air: “what is all this?
Speak.” Hardy was silent. “Why don’t you speak?” cried he, shaking him
by the shoulder impatiently. Still Hardy was silent. “Down upon your
knees this minute and confess all: tell me where you’ve been, what you’ve
been doing, and who are your accomplices, for I know there is a gang of
you; so,” added he, pressing heavily upon Hardy’s shoulder, “down upon
your knees this minute, and confess the whole, that’s your only way now
to get off yourself. If you hope for _my_ pardon, I can tell you it’s
not to be had without asking for.”
“Sir,” said Hardy, in a firm but respectful voice, “I have no pardon to
ask, I have nothing to confess; I am innocent; but if I were not, I would
never try to get off myself by betraying my companions.”
“Very well, sir! very well! very fine! stick to it, stick to it, I advise
you, and we shall see. And how will you look to-morrow, Mr. Innocent,
when my uncle, the doctor, comes home?”
“As I do now, sir,” said Hardy, unmoved.
His composure threw Mr. Power into a rage too great for utterance.
“Sir,” continued Hardy, “ever since I have been at school, I never told a
lie, and therefore, sir, I hope you will believe me now. Upon my word
and honour, sir, I have done nothing wrong.”
“Nothing wrong? Better and better! what, when I caught you going out at
night?”
“_That_, to be sure, was wrong,” said Hardy, recollecting himself; “but
except that—”
“Except that, sir! I will except nothing. Come along with me, young
gentleman, your time for pardon is past.”
Saying these words, he pulled Hardy along a narrow passage to a small
closet, set apart for desperate offenders, and usually known by the name
of the _Black Hole_. “There, sir, take up your lodging there for
to-night,” said he, pushing him in; “to-morrow I’ll know more, or I’ll
know why,” added he, double locking the door, with a tremendous noise,
upon his prisoner, and locking also the door at the end of the passage,
so that no one could have access to him. “So now I think I have you
safe!” said Mr. William Power to himself, stalking off with steps which
made the whole gallery resound, and which made many a guilty heart
tremble.
The conversation which had passed between Hardy and Mr. Power at the head
of the stairs had been anxiously listened to; but only a word or two here
and there had been distinctly overheard.
The locking of the black hole door was a terrible sound—some knew not
what it portended, and others knew _too well_. All assembled in the
morning with faces of anxiety. Tarlton and Loveit’s were the most
agitated: Tarlton for himself, Loveit for his friend, for himself, for
everybody. Every one of the party, and Tarlton at their head, surrounded
him with reproaches; and considered him as the author of the evils which
hung over them. “How could you do so? and why did you say anything to
Hardy about it? when you had promised, too! Oh! what shall we all do?
what a scrape you have brought us into, Loveit, it’s all your fault!”
“All my fault!” repeated poor Loveit, with a sigh; “well, that is hard.”
“Goodness! there’s the bell,” exclaimed a number of voices at once. “Now
for it!” They all stood in a half circle for morning prayers. They
listened—“Here he is coming! No—Yes—Here he is!” And Mr. William Power,
with a gloomy brow, appeared and walked up to his place at the head of
the room. They knelt down to prayers, and the moment they rose, Mr.
William Power, laying his hand upon the table, cried, “Stand still,
gentlemen, if you please.” Everybody stood stock still; he walked out of
the circle; they guessed that he was gone for Hardy, and the whole room
was in commotion. Each with eagerness asked each what none could answer,
“_Has he told_?” “_What_ has he told?” “Who has he told of?” “I hope
he has not told of me,” cried they.
“I’ll answer for it he has told of all of us,” said Tarlton.
“And I’ll answer for it he has told of none of us,” answered Loveit, with
a sigh.
“You don’t think he’s such a fool, when he can get himself off,” said
Tarlton.
At this instant the prisoner was led in, and as he passed through the
circle, every eye was fixed upon him. His eye fell upon no one, not even
upon Loveit, who pulled him by the coat as he passed—everyone felt almost
afraid to breathe.
“Well, sir,” said Mr. Power, sitting down in Mr. Trueman’s elbow-chair,
and placing the prisoner opposite to him; “well, sir, what have you to
say to me this morning?”
“Nothing, sir,” answered Hardy, in a decided, yet modest manner; “nothing
but what I said last night.”
“Nothing more?”
“Nothing more, sir.”
“But I have something more to say to you, sir, then; and a great deal
more, I promise you, before I have done with you;” and then, seizing him
in a fury, he was just going to give him a severe flogging, when the
schoolroom door opened, and Mr. Trueman appeared, followed by an old man
whom Loveit immediately knew. He leaned upon his stick as he walked, and
in his other hand carried a basket of apples. When they came within the
circle, Mr. Trueman stopped short. “Hardy!” exclaimed he, with a voice
of unfeigned surprise, whilst Mr. William Power stood with his hand
suspended.—“Ay, Hardy, sir,” repeated he. “I told him you’d not believe
your own eyes.”
Mr. Trueman advanced with a slow step. “Now, sir, give me leave,” said
the usher, eagerly drawing him aside, and whispering.
“So, sir,” said Mr. T. when the whisper was done, addressing himself to
Hardy, with a voice and manner which, had he been guilty, must have
pierced him to the heart, “I find I have been deceived in you; it is but
three hours ago that I told your uncle I never had a boy in my school in
whom I placed so much confidence; but, after all this show of honour and
integrity, the moment my back is turned, you are the first to set an
example of disobedience of my orders. Why do I talk of disobeying my
commands—you are a thief!”
“I, sir?” exclaimed Hardy, no longer able to repress his feelings.
“You, sir,—you and some others,” said Mr. Trueman, looking round the room
with a penetrating glance—“you and some others.”
“Ay, sir,” interrupted Mr. William Power, “get that out of him if you
can—ask him.”
“I will ask him nothing; I shall neither put his truth nor his honour to
the trial; truth and honour are not to be expected amongst thieves.”
“I am not a thief! I have never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thieves,” cried
Hardy, indignantly.
“Have you not robbed this old man? Don’t you know the taste of these
apples?” said Mr. Trueman, taking one out of the basket.
“No, sir; I do not. I never touched one of that old man’s apples.”
“Never touched one of them! I suppose this is some vile equivocation;
you have done worse, you have had the barbarity, the baseness, to attempt
to poison his dog; the poisoned meat was found in your pocket last
night.”
“The poisoned meat was found in my pocket, sir; but I never intended to
poison the dog—I saved his life.”
“Lord bless him!” said the old man.
“Nonsense—cunning!” said Mr. Power. “I hope you won’t let him impose
upon you, sir.”
“No, he cannot impose upon me; I have a proof he is little prepared for,”
said Mr. Trueman, producing the blue handkerchief in which the meat had
been wrapped.
Tarlton turned pale; Hardy’s countenance never changed.
“Don’t you know this handkerchief, sir?”
“I do, sir.”
“Is it not yours?”
“No, sir.”
“Don’t you know whose it is?” cried Mr. Power. Hardy was silent.
“Now, gentlemen,” said Mr. Trueman, “I am not fond of punishing you; but
when I do it, you know, it is always in earnest. I will begin with the
eldest of you; I will begin with Hardy, and flog you with my own hands
till this handkerchief is owned.”
“I’m sure it’s not mine,” and “I’m sure it’s none of mine,” burst from
every mouth, whilst they looked at each other in dismay; for none but
Hardy, Loveit and Tarlton knew the secret. “My cane,” said Mr. Trueman,
and Mr. Power handed him the cane. Loveit groaned from the bottom of his
heart. Tarlton leaned back against the wall with a black countenance.
Hardy looked with a steady eye at the cane.
“But first,” said Mr. Trueman, laying down the cane, “let us see.
Perhaps we may find out the owner of this handkerchief another way,”
examining the corners. It was torn almost to pieces; but luckily the
corner that was marked remained.
“J. T.!” cried Mr. Trueman. Every eye turned upon the guilty Tarlton,
who, now as pale as ashes and trembling in every limb, sank down upon his
knees, and in a whining voice begged for mercy. “Upon my word and
honour, sir, I’ll tell you all; I’d never have thought of stealing the
apples if Loveit had not first told me of them; and it was Tom who first
put the poisoning the dog into my head. It was he that carried the meat,
_wasn’t it_?” said he, appealing to Hardy, whose word he knew must be
believed. “Oh, dear sir!” continued he as Mr. Trueman began to move
towards him, “do let me off; pray do let me off this time! I’m not the
only one, indeed, sir! I hope you won’t make me an example for the rest.
It’s very hard I’m to be flogged more than they!”
“I’m not going to flog you.”
“Thank you, sir,” said Tarlton, getting up and wiping his eyes.
“You need not thank me,” said Mr. Trueman. “Take your handkerchief—go
out of this room—out of this house; let me never see you more.”
“If I had any hopes of him,” said Mr. Trueman, as he shut the door after
him;—“if I had any hopes of him, I would have punished him;—but I have
none. Punishment is meant only to make people better; and those who have
any hopes of themselves will know how to submit to it.”
At these words Loveit first, and immediately all the rest of the guilty
party, stepped out of the ranks, confessed their fault, and declared
themselves ready to bear any punishment their master thought proper.
“Oh, they have been punished enough,” said the old man; “forgive them,
sir.”
Hardy looked as if he wished to speak. “Not because you ask it,” said
Mr. Trueman to the guilty penitents, “though I should be glad to oblige
you—it wouldn’t be just; but there,” pointing to Hardy, “there is one who
has merited a reward; the highest I can give him is that of pardoning his
companions.”
Hardy bowed and his face glowed with pleasure, whilst everybody present
sympathized in his feelings.
“I am sure,” thought Loveit, “this is a lesson I shall never forget.”
“Gentlemen,” said the old man, with a faltering voice, “it wasn’t for the
sake of my apples that I spoke; and you, sir,” said he to Hardy, “I thank
you for saving my dog. If you please, I’ll plant on that mount, opposite
the window, a young apple-tree, from my old one. I will water it, and
take care of it with my own hands for your sake, as long as I am able.
And may God bless you!” laying his trembling hand on Hardy’s head; “may
God bless you—I’m sure God _will_ bless all such boys as you are.”
THE BASKET-WOMAN.
“Toute leur étude était de se complaire et de s’entr’aider.” {365a}
PAUL ET VIRGINIE.
AT the foot of a steep, slippery, white hill, near Dunstable, in
Bedfordshire, called Chalk Hill, there is a hut, or rather a hovel, which
travellers could scarcely suppose could be inhabited, if they did not see
the smoke rising from its peaked roof. An old woman lives in this hovel,
{365b} and with her a little boy and girl, the children of a beggar who
died, and left these orphans perishing with hunger. They thought
themselves very happy when the good old woman first took them into her
hut and bid them warm themselves at her small fire, and gave them a crust
of mouldy bread to eat. She had not much to give, but what she had she
gave with good-will. She was very kind to these poor children, and
worked hard at her spinning-wheel and at her knitting, to support herself
and them. She earned money also in another way. She used to follow all
the carriages as they went up Chalk Hill, and when the horses stopped to
take breath or to rest themselves, she put stones behind the carriage
wheels to prevent them from rolling backwards down the steep, slippery
hill.
The little boy and girl loved to stand beside the good natured old
woman’s spinning-wheel when she was spinning, and to talk to her. At
these times she taught them something, which, she said, she hoped they
would remember all their lives. She explained to them what is meant by
telling the truth, and what it is to be honest. She taught them to
dislike idleness, and to wish that they could be useful.
One evening, as they were standing beside her, the little boy said to
her, “Grandmother,” for that was the name by which she liked that these
children should call her—“grandmother, how often you are forced to
inn-yard. There was a great noise and bustle. The hostlers were
carrying in luggage. The postillions were rubbing down the horses, or
rolling the chaises into the coach-house.
“What now! What business have you here, pray?” said a waiter, who almost
ran over Paul, as he was crossing the yard in a great hurry to get some
empty bottles from the bottle-rack. “You’ve no business here, crowding
up the yard. Walk off, young gentleman, if you please.”
“Pray give me leave, sir,” said Paul, “to stay a few minutes, to look
amongst these chaises for one dark green chaise with red wheels, that has
Mr. John Nelson’s name written upon it.”
“What’s that he says about a dark green chaise?” said one of the
postillions.
“What should such a one as he is know about chaises?” interrupted the
hasty waiter, and he vas going to turn Paul out of the yard; but the
hostler caught hold of his arm and said, “Maybe the child has some
business here; let’s know what he has to say for himself.”
The waiter was at this instant luckily obliged to leave them to attend
the bell; and Paul told his business to the hostler, who as soon as he
saw the guinea and heard the story, shook Paul by the hand, and said,
“Stand steady, my honest lad; I’ll find the chaise for you, if it is to
be found here; but John Nelson’s chaises almost always drive to the
‘Black Bull.’”
After some difficulty, the green chaise, with John Nelson’s name upon it,
and the postillion who drove that chaise, were found; and the postillion
told Paul that he was just going into the parlour to the gentleman he had
driven, to be paid, and that he would carry the guinea with him.
“No,” said Paul, “we should like to give it back ourselves.”
“Yes,” said the hostler; “that they have a right to do.”
The postillion made no reply, but looked vexed, and went towards the
house, desiring the children would wait in the passage till his return.
In the passage there was standing a decent, clean, good natured looking
woman, with two huge straw baskets on each side of her. One of the
baskets stood a little in the way of the entrance. A man who was pushing
his way in, and carried in his hand a string of dead larks hung to a
pole, impatient at being stopped, kicked down the straw basket, and all
its contents were thrown out. Bright straw hats, and boxes, and
slippers, were all thrown in disorder upon the dirty ground.
“Oh, they will be trampled upon! They will be all spoiled!” exclaimed
the woman to whom they belonged.
“We’ll help you to pick them up if you will let us,” cried Paul and Anne;
and they immediately ran to her assistance.
When the things were all safe in the basket again, the children expressed
a desire to know how such beautiful things could be made of straw; but
the woman had not time to answer before the postillion came out of the
parlour, and with him a gentleman’s servant, who came to Paul, and
clapping him upon the back, said, “So, my little chap, I gave you a
guinea for a halfpenny, I hear; and I understand you’ve brought it back
again; that’s right, give me hold of it.”
“No, brother,” said Anne, “this is not the gentleman that was reading.”
“Pooh, child, I came in Mr. Nelson’s green chaise. Here’s the postillion
can tell you so. I and my master came in that chaise. I and my master
that was reading, as you say, and it was he that threw the money out to
you. He is going to bed; he is tired and can’t see you himself. He
desires that you’ll give me the guinea.”
He pushed them towards the door; but the basket-woman whispered to them
as they went out, “Wait in the street till I come to you.”
“Pray, Mrs. Landlady,” cried this gentleman’s servant, addressing himself
to the landlady, who just then came out of a room where some company were
at supper, “Pray, Mrs. Landlady, please to let me have roasted larks for
my supper. You are famous for larks at Dunstable; and I make it a rule
to taste the best of everything wherever I go; and, waiter, let me have a
bottle of claret. Do you hear?”
“Larks and claret for his supper,” said the basket-woman to herself, as
she looked at him from head to foot. The postillion was still waiting,
as if to speak to him; and she observed them afterwards whispering and
laughing together. “_No bad hit_,” was a sentence which the servant
pronounced several times.
Now it occurred to the basket-woman that this man had cheated the
children out of the guinea to pay for the larks and claret; and she
thought that perhaps she could discover the truth. She waited quietly in
the passage.
“Waiter! Joe! Joe!” cried the landlady, “why don’t you carry in the
sweetmeat-puffs and the tarts here to the company in the best parlour?”
“Coming, ma’am,” answered the waiter; and with a large dish of tarts and
puffs, the waiter came from the bar; the landlady threw open the door of
the best parlour, to let him in; and the basket-woman had now a full view
of a large cheerful company, and amongst them several children, sitting
round a supper-table.
“Ay,” whispered the landlady, as the door closed after the waiter and the
tarts, “there are customers enough, I warrant, for you in that room, if
you had but the luck to be called in. Pray, what would you have the
conscience, I wonder now, to charge me for these here half-dozen little
mats to put under my dishes?”
“A trifle, ma’am,” said the basket-woman. She let the landlady have the
mats cheap, and the landlady then declared she would step in and see if
the company in the best parlour had done supper. “When they come to
their wine,” added she, “I’ll speak a good word for you, and get you
called in afore the children are sent to bed.”
The landlady, after the usual speech of, “_I hope the supper and
everything is to your liking_, _ladies and gentlemen_,” began with, “If
any of the young gentlemen or ladies would have a _cur’osity_ to see any
of our famous Dunstable straw-work, there’s a decent body without would,
I daresay, be proud to show them her pincushion-boxes, and her baskets
and slippers, and her other _cur’osities_.”
The eyes of the children all turned towards their mother; their mother
smiled, and immediately their father called in the basket-woman, and
desired her to produce her _curiosities_. The children gathered round
her large pannier as it opened, but they did not touch any of her things.
“Ah, papa!” cried a little rosy girl, “here are a pair of straw slippers
that would just fit you, I think; but would not straw shoes wear out very
soon? and would not they let in the wet?”
“Yes, my dear,” said her father, “but these slippers are meant—”
“For powdering-slippers, miss,” interrupted the basket-woman.
“To wear when people are powdering their hair,” continued the gentleman,
“that they may not spoil their other shoes.”
“And will you buy them, papa?”
“No, I cannot indulge myself,” said her father, “in buying them now. I
must make amends,” said he, laughing, “for my carelessness; and as I
threw away a guinea to-day, I must endeavour to save sixpence at least?”
“Ah, the guinea that you threw by mistake into the little girl’s hat as
we were coming up Chalk Hill. Mamma, I wonder that the little girl did
not take notice of its being a guinea, and that she did not run after the
chaise to give it back again. I should think, if she had been an honest
girl, she would have returned it.”
“Miss!—ma’am!—sir!” said the basket-woman, “if it would not be
impertinent, may I speak a word? A little boy and girl have just been
here inquiring for a gentleman who gave them a guinea instead of a
halfpenny by mistake; and not five minutes ago I saw the boy give the
guinea to a gentleman’s servant, who is there without, and who said his
master desired it should be returned to him.”
“There must be some mistake, or some trick in this,” said the gentleman.
“Are the children gone? I must see them—send after them.”
“I’ll go for them myself,” said the good natured basket-woman; “I bid
them wait in the street yonder, for my mind misgave me that the man who
spoke so short to them was a cheat, with his larks and his claret.”
Paul and Anne were speedily summoned, and brought back by their friend
the basket-woman; and Anne, the moment she saw the gentleman, knew that
he was the very person who smiled upon her, who admired her brother’s
scotcher, and who threw a handful of halfpence into the hat; but she
could not be certain, she said, that she received the guinea from him;
she only thought it most likely that she did.
“But I can be certain whether the guinea you returned be mine or no,”
said the gentleman. “I marked the guinea; it was a light one; the only
guinea I had, which I put into my waistcoat pocket this morning.” He
rang the bell, and desired the waiter to let the gentleman who was in the
room opposite to him know that he wished to see him.
“The gentleman in the white parlour, sir, do you mean?”
“I mean the master of the servant who received a guinea from this child.”
“He is a Mr. Pembroke, sir,” said the waiter.
Mr. Pembroke came; and as soon as he heard what had happened, he desired
the waiter to show him to the room where his servant was at supper. The
dishonest servant, who was supping upon larks and claret, knew nothing of
what was going on; but his knife and fork dropped from his hand, and he
overturned a bumper of claret as he started up from the table, in great
surprise and terror, when his master came in with a face of indignation,
and demanded “_The guinea_—the _guinea_, _sir_! that you got from this
child; that guinea which you said I ordered you to ask for from this
child.”
The servant, confounded and half intoxicated, could only stammer out that
he had more guineas than one about him, and that he really did not know
which it was. He pulled his money out, and spread it upon the table with
trembling hands. The marked guinea appeared. His master instantly
turned him out of his service with strong expressions of contempt.
“And now, my little honest girl,” said the gentleman who had admired her
brother’s scotcher, turning to Anne, “and now tell me who you are, and
what you and your brother want or wish for most in the world.”
In the same moment Anne and Paul exclaimed, “The thing we wish for the
most in the world is a blanket for our grandmother.”
“She is not our grandmother in reality, I believe, sir,” said Paul; “but
she is just as good to us, and taught me to read, and taught Anne to
knit, and taught us both that we should be honest—so she has; and I wish
she had a new blanket before next winter, to keep her from the cold and
the rheumatism. She had the rheumatism sadly last winter, sir; and there
is a blanket in this street that would be just the thing for her.”
“She shall have it, then; and,” continued the gentleman, “I will do
something more for you. Do you like to be employed or to be idle best?”
“We like to have something to do always, if we could, sir,” said Paul;
“but we are forced to be idle sometimes, because grandmother has not
always things for us to do that we _can_ do well.”
“Should you like to learn how to make such baskets as these?” said the
gentleman, pointing to one of the Dunstable straw-baskets. “Oh, very
much!” said Paul. “Very much!” said Anne.
“Then I should like to teach you how to make them,” said the
basket-woman; “for I’m sure of one thing, that you’d behave honestly to
me.”
The gentleman put a guinea into the good natured basket-woman’s hand, and
told her that he knew she could not afford to teach them her trade for
nothing. “I shall come through Dunstable again in a few months,” added
he; “and I hope to see that you and your scholars are going on well. If
I find that they are, I will do something more for you.”
“But,” said Anne, “we must tell all this to grandmother, and ask her
about it; and I’m afraid—though I’m very happy—that it is getting very
late, and that we should not stay here any longer.”
“It is a fine moonlight night,” said the basket-woman; “and is not far.
I’ll walk with you, and see you safe home myself.”
The gentleman detained them a few minutes longer, till a messenger whom
he had dispatched to purchase the much wished for blanket returned.
“Your grandmother will sleep well upon this good blanket, I hope,” said
the gentleman, as he gave it into Paul’s opened arms. “It has been
obtained for her by the honesty of her adopted children.”
FOOTNOTES
{2} A hard-hearted man.
{5} “The proper species of rush,” says White, in his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seems to be the Juncus effusus, or common soft rush, which is
to be found in moist pastures, by the sides of streams, and under hedges.
These rushes are in best condition in the height of summer, but may be
gathered so as to serve the purpose well quite on to autumn. The largest
and longest are the best. Decayed labourers, women, and children make it
their business to procure and prepare them. As soon as they are cut,
they must be flung into water, and kept there; for otherwise they will
dry and shrink, and the peel will not run. When these junci are thus far
prepared, they must lie out on the grass to be bleached and take the dew
for some nights, and afterwards be dried in the sun. Some address is
required in dipping these rushes in the scalding fat or grease; but this
knack is also to be attained by practice. A pound of common grease may
be procured for fourpence, and about six pounds of grease will dip a
pound of rushes and one pound of rushes may be bought for one shilling;
so that a pound of rushes, medicated and ready for use, will cost three
shillings.”
{7} The author has seen a pair of shoes, such as here described, made in
a few hours.
{12a} _Goody_ is not a word used in Ireland. _Collyogh_ is the Irish
appellation of an old woman: but as _Collyogh_ might sound strangely to
English ears, we have translated it by the word Goody.
{12b} What are in Ireland called moats, are, in England, called Danish
mounds, or barrows.
{12c} Near Kells, in Ireland, there is a round tower, which was in
imminent danger of being pulled down by an old woman’s rooting at its
foundation, in hopes of finding treasure.
{77} This is a true anecdote.
{139} _Salt_, the cant name given by the Eton lads to the money
collected at Montem.
{151} Young noblemen at Oxford wear yellow tufts at the tops of their
caps. Hence their flatterers are said to be dead-shots at
yellow-hammers.
{155} From beginning to end.
{167} This is the name of a country dance.
{181} It is necessary to observe that this experiment has never been
actually tried upon raspberry-plants.
{194} _Vide_ “Priestley’s History of Vision,” chapter on coloured
shadows.
{222} Lobe.
{236} This atrocious practice is now happily superseded by the use of
sweeping machines.
{256} This custom of “BARRING OUT” was very general (especially in the
northern parts of England)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and it has
been fully described by Brand and other antiquarian writers.
Dr. Johnson mentions that Addison, while under the tuition of Mr. Shaw,
master of the Lichfield Grammar School, led, and successfully conducted,
“a plan for _barring out_ his master. A disorderly privilege,” says the
doctor, “which, in his time, prevailed in the principal seminaries of
education.”
In the _Gentleman’s Magazine_ of 1828, Dr. P. A. Nuttall, under the
signature of H. A. N., has given a spirited sketch of a “BARRING OUT” at
the Ormskirk Grammar School, which has since been republished at length
(though without acknowledgment), by Sir Henry Ellis, in Bohn’s recent
edition of Brand’s “Popular Antiquities.” This operation took place
early in the present century, and is interesting from its being, perhaps,
the last attempt on record, and also from the circumstance of the writer
himself having been one of the juvenile leaders in the daring adventure,
“quo rum pars magna fuit.”—ED.
{262} Lucifer matches were then unknown.—Ed.
{301} Varieties of Literature, vol. i. p. 299.
{302} Chi compra ha bisogna di cent’ occhi; chi vende n’ha assai di uno.
{303a} E meglio esser fortunato che savio.
{303b} Butta una sardella per pigliar un luccio.
{306} _see anted_.
{308} Il cane scottato dell’ acqua calda ha paura poi della fredda.
{309} The Duke de Rochefoucault.—“On peut être puls fin qu’un autre,
mais pas plus fin que tous les autres.”
{311} Chartres.
{314} Poco e spesso empie il l’orsetto.
{317} Chi te fa piu carezza che non vuole,
O ingannato t’ha, o inganuar et vuole.
{318} This word comes from two Italian words, _bunco rotto_—broken
bench. Bankers and merchants used formerly to count their money, and
write their bills of exchange upon benches in the streets; and when a
merchant or banker lost his credit, and was unable to pay his debts, his
bench was broken.
{326} We must give those of our young English readers who may not be
acquainted with the ancient city of Herculaneum, some idea of it. None
can be ignorant that near Naples is the celebrated volcanic mountain of
Vesuvius;—that, from time to time, there happen violent eruptions from
this mountain; that is to say, flames and immense clouds of smoke issue
from different openings, mouths, or _craters_, as they are called, but
more especially from the summit of the mountain, which is distinguished
by the name of _the_ crater. A rumbling, and afterwards a roaring noise
is heard within, and prodigious quantities of stones and minerals burnt
into masses (scoriæ), are thrown out of the crater, sometimes to a great
distance. The hot ashes from Mount Vesuvius have often been seen upon
the roofs of the houses of Naples, from which it is six miles distant.
Streams of lava run down the sides of the mountains during the time of an
eruption, destroying everything in their way, and overwhelm the houses
and vineyards which are in the neighbourhood.
About 1700 years ago,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Roman Emperor Titus, there
happened a terrible eruption of Mount Vesuvius; and a large city called
Herculaneum, which was situated at about four miles’ distance from the
volcano, was overwhelmed by the streams of lava which poured into it,
filled up the streets, and quickly covered over the tops of the houses,
so that the whole was no more visible. It remained for many years
buried. The lava which covered it became in time fit for vegetation,
plants grew there, a new soil was formed, and a new town called Portici
was built over this place where Herculaneum formerly stood. The little
village of Resina is also situated near the spot. About fifty years ago,
in a poor man’s garden at Resina, a hole in a well about thirty feet
below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was observed. Some persons had the
curiosity to enter into this hole, and, after creeping underground for
some time, they came to the foundations of houses. The peasants,
inhabitants of the village, who had probably never heard of Herculaneum,
were somewhat surprised at their discovery. {327} About the same time,
in a pit in the town of Portici, a similar passage underground was
discovered, and, by orders of the King of Naples, workmen were employed
to dig away the earth, and clear the passage. They found, at length, the
entrance into the town, which, during the reign of Titus, was buried
under lava. It was about eighty-eight Neapolitan palms (a palm contains
near nine inches) below the top of the pit. The workmen, as they cleared
the passages, marked their way with chalk when they came to any turning,
lest they should lose themselves. The streets branched out in many
directions, and, lying across them, the workmen often found large pieces
of timber, beams, and rafters; some broken in the fall, others entire.
These beams and rafters are burned quite black like charcoal, except
those that were found in moist places, which have more the colour of
rotten wood, and which are like a soft paste, into which you might run
your hand. The walls of the houses slant, some one way, some another,
and some are upright. Several magnificent buildings of brick, faced with
marble of different colours, are partly seen, where the workmen have
cleared away the earth and lava with which they were encrusted. Columns
of red and white marble, and flights of steps, are seen in different
places; and out of the ruins of the palaces some very fine statues and
pictures have been dug. Foreigners who visit Naples are very curious to
see this subterraneous city, and are desirous to carry with them into
their own country some proofs of their having examined this wonderful
place.
{327}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vol. ix. p. 440.
{332} Tutte le volpi si trovano in pellicera.
{333a} Assai ben balla a chi fortuna suona.
{333b} Odi, vedi, taci, se vuoi viver in pace.
{334} La vita il fine,—e di loda la sera.
“Compute the morn and evening of their day.”—POPE.
{336} Vien presto consumato l’ingiustamente acquistato.
{337} I fatti sono maschii, le parole femmine.
{338a} Phil. Trans. vol. ix.
{338b} These facts are mentioned in Sir William Hamilton’s account of an
eruption of Mount Vesuvius.—See Phil. Trans. 1795, first part.
{342} La mala compagnia è quella che mena uomini a la forca.
{343} Pescar col hamo d’argento.
{365a} “Their whole study was how to please and to help one another.”
{365b} This was about the close of the 18th century.
***END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THE PARENT'S ASSISTANT***
******* This file should be named 3655-0.txt or 3655-0.zip *******
This and all associated files of various formats will be found in:
http://www.gutenberg.org/dirs/3/6/5/3655
Updated editions will replace the previous one--the old editions will
be renamed.
Creating the works from print edition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means that no one owns a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in these works,
so the Foundation (and you!) can copy and distribute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ermission and without paying copyright
royalties. Special rules, set forth in the General Terms of Use part
of this license, apply to copying and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ncept and trademark.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may not be used if you charge for the eBooks, unless you receive
specific permission. If you do not charge anything for copies of this
eBook, complying with the rules is very easy. You may use this eBook
for nearly any purpose such as creation of derivative works, reports,
performances and research. They may be modified and printed and given
away--you may do practically ANYT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eBoo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Redistribution is subject to the
trademark license, especially commercial redistribution.
START: FULL LICENS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PLEASE READ THIS BEFORE YOU DISTRIBUTE OR USE THIS WORK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by using or distributing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you agree to comply with all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available with this file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license.
Section 1. General Terms of Use and Re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1.A. By reading or using any part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you indicate that you have read, understand, agree to
and accept all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mark/copyright) agreement. If you do not agree to abide by all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cease using and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n your
possession. If you paid a fee for obtaining a copy of or access to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and you do not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ay obtain a refund from the
person or entity to whom you paid the fee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8.
used on or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an electronic work by people who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you can do with most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even without complying with the full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See
paragraph 1.C below.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do with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f you follow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and help preserve free future access to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See paragraph 1.E below.
1.C.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or PGLAF), owns a compilation copyright in the collec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Nearly all the individual
works in the collection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an individual work is un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are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do not
claim a right to prevent you from copying, distributing, performing,
display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e work as long as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are removed. Of course, we hope
that you will suppor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mission of promoting
free access to electronic works by freely sharing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keep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 You can easily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y keeping this work in the
same format with its attached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when
you share it without charge with others.
1.D.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located also govern
what you can do with this work. Copyright laws in most countries ar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change. If you ar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check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in addition to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efore downloading, copy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distribut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is work or any
other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The Foundation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concerning the copyright status of any work in any
country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1.E. Unless you have removed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1.E.1. The following sentence, with active links to, or othe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must appear
prominently whenever any copy of a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any work
on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ppears, or with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is associated) is accessed, displayed,
performed, viewed, copied or distributed: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If you are not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ll have to check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where you
are located before using this ebook.
1.E.2.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is
derived from text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does not
contain a notice indicating that it is pos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the work can be copied and distributed to an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aying any fees or charges. If you are
redistributing or providing access to a work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ssociated with or appearing on the work, you must comply
either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or
obtain permission for the use of the work and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s 1.E.8 or 1.E.9.
1.E.3.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i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your use and distribution
must comply with both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and any
additional terms impos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 Additional terms
will be linked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for all work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f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work.
1.E.4. Do not unlink or detach or remov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terms from this work, or any files containing a part of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with Project Gutenberg-tm.
1.E.5. Do not copy, display, perform, distribute or redistribute this
electronic work, or any part of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out
prominently displaying the sentence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1 with
active links o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1.E.6. You may convert to and distribute this work in any binary,
compressed, marked up, nonproprietary or proprietary form, including
any word processing or hypertext form. However, if you provide access
to or distribute copies of a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in a format
other than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at used in the official
version posted on the official Project Gutenberg-tm web site
(www.gutenberg.org), you must, at no additional cost, fee or expense
to the user, provide a copy, a means of exporting a copy, or a means
of obtaining a copy upon request, of the work in its original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 Any alternate format must includ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a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1.E.1.
1.E.7. Do not charge a fee for access to, view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copying or distributing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unless you comply with paragraph 1.E.8 or 1.E.9.
1.E.8. You may charge a reasonable fee for copies of or providing
access to or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provided that
* You pay a royalty fee of 20% of the gross profits you derive from
the use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
you already use to calculate your applicable taxes. The fee is owed
to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but he has
agreed to donate royalties under this paragraph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Royalty payments must be paid
within 60 days following each date on which you prepare (or are
legally required to prepare) your periodic tax returns. Royalty
payments should be clearly marked as such and sent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t the address specified in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 You provide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by a user who notifies
you in writing (or by e-mail) within 30 days of receipt that s/he
does not agree to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You must require such a user to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the works possessed in a physical medium and discontinue
all use of and all access to other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 You provide,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F.3,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for a work or a replacement copy, if a defect in the
electronic work is discovered and reported to you within 90 days of
receipt of the work.
* You comply with all other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free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1.E.9. If you wish to charge a fee or distribute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or group of works on different terms than
are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obtain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both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LLC,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Contact the Foundation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3 below.
1.F.
1.F.1. Project Gutenberg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expend considerable
effort to identify, do copyright research on, transcribe and proofread
wor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in creat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llection. Despite these efforts,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and the medium on which they may be stored, may
contain "Defect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incomplete, inaccurate
or corrupt data, transcription errors, a copyrigh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a defective or damaged disk or
other medium, a computer virus, or computer codes that damage or
cannot be read by your equipment.
1.F.2. LIMITED WARRANTY, DISCLAIMER OF DAMAGES - Except for the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F.3,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and any other party distributing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under this agreement, disclaim all
liability to you for damages,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YOU AGREE THAT YOU HAVE NO REMEDIES FOR NEGLIGENCE, STRICT
LIABILITY, BREACH OF WARRANTY OR BREACH OF CONTRACT EXCEPT THOSE
PROVIDED IN PARAGRAPH 1.F.3. YOU AGREE THAT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D ANY DISTRIBUTOR UNDER THIS AGREEMENT WILL NOT BE
LIABLE TO YOU FOR ACTUAL, DIRECT, INDIRECT, CONSEQUENTIAL, PUNITIVE OR
INCIDENTAL DAMAGES EVEN IF YOU GIVE NOTICE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1.F.3.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 If you discover a
defect in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in 90 days of receiving it, you can
receive a refund of the money (if any) you paid for it by sending a
written explanation to the person you received the work from.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on a physical medium, you must return the medium
with your written explanation. The person or entity that provided you
with the defective work may elect to provide a replacement cop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the person
or entity providing it to you may choose to give you a second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the second copy is also defective, you may demand a refund in writing
without further opportunities to fix the problem.
1.F.4. Except for the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F.3, this work is provided to you 'AS-IS', WITH NO
OTHER WARRANTIES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NY PURPOSE.
1.F.5. Some states do not allow disclaimers of certain implied
warranties or the exclusion or limitation of certain types of
damages. If any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violates the law of the state applicable to this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shall be interpreted to make the maximum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permitted by the applicable state law. The invalidity or
unenforceability of any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void the
remaining provisions.
1.F.6. INDEMNITY - You agree to indemnify and hold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y agent or employee of the Foundation, anyone
providing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greement, and any volunteer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promo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harmless from all liability,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that ari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any of
the following which you do or cause to occur: (a) distribution of this
or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b) alteration, modification, or
additions or deletions to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and (c) any
Defect you cause.
Section 2. Information about the Miss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Project Gutenberg-tm is synonymous with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in formats readable by the widest variety of
computers including obsolete, old, middle-aged and new computers. It
exists because of the efforts of hundreds of volunteers and donations
from people in all walks of life.
Volunteers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vide volunteers with the
assistance they need are critical to reaching Project Gutenberg-tm's
goals and ensuring tha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llection will
remain freely available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In 2001,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was created to provide a secure
and permanent future for Project Gutenberg-tm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how your efforts and donations can help, see
Sections 3 and 4 and the Foundation information page at
www.gutenberg.org
Section 3.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is a non profit
501(c)(3)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nd granted tax exempt status by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The Foundation's EIN or 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is 64-6221541.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re tax deductible to the full extent permitted by
U.S. federal laws and your state's laws.
The Foundation's principal office is in Fairbanks, Alaska, with the
mailing address: PO Box 750175, Fairbanks, AK 99775, but its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are scattered throughout numerous
locations. Its business office is located at 809 North 1500 West, Salt
Lake City, UT 84116, (801) 596-1887. Email contact links and up to
date contac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the Foundation's web site and
official page at www.gutenberg.org/contact
For additional contact information:
Dr. Gregory B. Newby
Chief Executive and Director
[email protected]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Project Gutenberg-tm depends upon and cannot survive without wide
spread public support and donations to carry out its mission of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ublic domain and licensed works that can be
freely distributed in machine readable form accessible by the widest
array of equipment including outdated equipment. Many small donations
($1 to $5,000)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aintaining tax exempt
status with the IRS.
The Foundation is committed to complying with the laws regulating
charities and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all 50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are not uniform and it takes a
considerable effort, much paperwork and many fees to meet and keep up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We do not solicit donations in locations
where we have not received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compliance. To SEND
DONATIONS or determine the status of compliance for any particular
state visit www.gutenberg.org/donate
While we cannot and do not solicit contributions from states where we
have not met the solicitation requirements, we know of no prohibition
against accepting unsolicited donations from donors in such states who
approach us with offers to donate.
International donations are gratefully accepted, but we cannot make
any statements concerning tax treatment of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U.S. laws alone swamp our small staff.
Please check the Project Gutenberg Web pages for current donation
methods and addresses. Donations are accepted in a number of other
ways including checks, online payments and credit card donations. To
donate, please visit: www.gutenberg.org/donate
Section 5.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Professor Michael S. Hart was the originato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ncept of a library of electronic works that could be
freely shared with anyone. For forty years, he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Project Gutenberg-tm eBooks with only a loose network of
volunteer support.
Project Gutenberg-tm eBooks are often created from several printed
editions, all of which are confirmed as not protected by copyright in
the U.S. unless a copyright notice is included. Thus, we do not
necessarily keep eBooks in compliance with any particular paper
edition.
Most people start at our Web site which has the main PG search
facility: www.gutenberg.org
This Web site includes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tm,
including how to make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how to help produce our new eBooks, and how to
subscribe to our email newsletter to hear about new eBooks.
used on or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an electronic work by people who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you can do with most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even without complying with the full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See
paragraph 1.C below.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do with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f you follow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and help preserve free future access to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See paragraph 1.E below.
1.C.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or PGLAF), owns a compilation copyright in the collec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Nearly all the individual
works in the collection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an individual work is un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are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do not
claim a right to prevent you from copying, distributing, performing,
display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e work as long as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are removed. Of course, we hope
that you will suppor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mission of promoting
free access to electronic works by freely sharing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keep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 You can easily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y keeping this work in the
same format with its attached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when
you share it without charge with others.
1.D.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located also govern
what you can do with this work. Copyright laws in most countries ar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change. If you ar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check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in addition to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efore downloading, copy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distribut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is work or any
other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The Foundation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concerning the copyright status of any work in any
country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1.E. Unless you have removed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1.E.1. The following sentence, with active links to, or othe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must appear
prominently whenever any copy of a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any work
on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ppears, or with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is associated) is accessed, displayed,
performed, viewed, copied or distributed: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If you are not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ll have to check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where you
are located before using this ebook.
1.E.2.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is
derived from text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does not
contain a notice indicating that it is pos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the work can be copied and distributed to an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aying any fees or charges. If you are
redistributing or providing access to a work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ssociated with or appearing on the work, you must comply
either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or
obtain permission for the use of the work and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s 1.E.8 or 1.E.9.
1.E.3.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i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your use and distribution
must comply with both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and any
additional terms impos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 Additional terms
will be linked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for all work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f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work.
1.E.4. Do not unlink or detach or remov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terms from this work, or any files containing a part of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with Project Gutenberg-tm.
1.E.5. Do not copy, display, perform, distribute or redistribute this
electronic work, or any part of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out
prominently displaying the sentence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1 with
active links o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1.E.6. You may convert to and distribute this work in any binary,
compressed, marked up, nonproprietary or proprietary form, including
any word processing or hypertext form. However, if you provide access
to or distribute copies of a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in a format
other than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at used in the official
version posted on the official Project Gutenberg-tm web site
(www.gutenberg.org), you must, at no additional cost, fee or expense
to the user, provide a copy, a means of exporting a copy, or a means
of obtaining a copy upon request, of the work in its original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 Any alternate format must includ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a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1.E.1.
1.E.7. Do not charge a fee for access to, view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copying or distributing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unless you comply with paragraph 1.E.8 or 1.E.9.
1.E.8. You may charge a reasonable fee for copies of or providing
access to or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provided that
* You pay a royalty fee of 20% of the gross profits you derive from
the use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
you already use to calculate your applicable taxes. The fee is owed
to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but he has
agreed to donate royalties under this paragraph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Royalty payments must be paid
within 60 days following each date on which you prepare (or are
legally required to prepare) your periodic tax returns. Royalty
payments should be clearly marked as such and sent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t the address specified in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 You provide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by a user who notifies
you in writing (or by e-mail) within 30 days of receipt that s/he
does not agree to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You must require such a user to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the works possessed in a physical medium and discontinue
all use of and all access to other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 You provide,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F.3,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for a work or a replacement copy, if a defect in the
electronic work is discovered and reported to you within 90 days of
receipt of the work.
* You comply with all other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free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1.E.9. If you wish to charge a fee or distribute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or group of works on different terms than
are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obtain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both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LLC,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Contact the Foundation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3 below.
1.F.
1.F.1. Project Gutenberg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expend considerable
effort to identify, do copyright research on, transcribe and proofread
wor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in creat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llection. Despite these efforts,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and the medium on which they may be stored, may
contain "Defect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incomplete, inaccurate
or corrupt data, transcription errors, a copyrigh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a defective or damaged disk or
other medium, a computer virus, or computer codes that damage or
cannot be read by your equipment.
1.F.2. LIMITED WARRANTY, DISCLAIMER OF DAMAGES - Except for the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F.3,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and any other party distributing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under this agreement, disclaim all
liability to you for damages,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YOU AGREE THAT YOU HAVE NO REMEDIES FOR NEGLIGENCE, STRICT
LIABILITY, BREACH OF WARRANTY OR BREACH OF CONTRACT EXCEPT THOSE
PROVIDED IN PARAGRAPH 1.F.3. YOU AGREE THAT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D ANY DISTRIBUTOR UNDER THIS AGREEMENT WILL NOT BE
LIABLE TO YOU FOR ACTUAL, DIRECT, INDIRECT, CONSEQUENTIAL, PUNITIVE OR
INCIDENTAL DAMAGES EVEN IF YOU GIVE NOTICE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1.F.3.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 If you discover a
defect in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in 90 days of receiving it, you can
receive a refund of the money (if any) you paid for it by sending a
written explanation to the person you received the work from.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on a physical medium, you must return the medium
with your written explanation. The person or entity that provided you
with the defective work may elect to provide a replacement cop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the person
or entity providing it to you may choose to give you a second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the second copy is also defective, you may demand a refund in writing
without further opportunities to fix the problem.
1.F.4. Except for the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F.3, this work is provided to you 'AS-IS', WITH NO
OTHER WARRANTIES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NY PURPOSE.
1.F.5. Some states do not allow disclaimers of certain implied
warranties or the exclusion or limitation of certain types of
damages. If any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violates the law of the state applicable to this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shall be interpreted to make the maximum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permitted by the applicable state law. The invalidity or
unenforceability of any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void the
remaining provisions.
1.F.6. INDEMNITY - You agree to indemnify and hold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y agent or employee of the Foundation, anyone
providing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greement, and any volunteer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promo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harmless from all liability,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that ari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any of
the following which you do or cause to occur: (a) distribution of this
or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b) alteration, modification, or
additions or deletions to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and (c) any
Defect you cause.
Section 2. Information about the Miss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Project Gutenberg-tm is synonymous with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in formats readable by the widest variety of
computers including obsolete, old, middle-aged and new computers. It
exists because of the efforts of hundreds of volunteers and donations
from people in all walks of life.
Volunteers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vide volunteers with the
assistance they need are critical to reaching Project Gutenberg-tm's
goals and ensuring tha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llection will
remain freely available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In 2001,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was created to provide a secure
and permanent future for Project Gutenberg-tm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how your efforts and donations can help, see
Sections 3 and 4 and the Foundation information page at
www.gutenberg.org
Section 3.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is a non profit
501(c)(3)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nd granted tax exempt status by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The Foundation's EIN or 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is 64-6221541.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re tax deductible to the full extent permitted by
U.S. federal laws and your state's laws.
The Foundation's principal office is in Fairbanks, Alaska, with the
mailing address: PO Box 750175, Fairbanks, AK 99775, but its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are scattered throughout numerous
locations. Its business office is located at 809 North 1500 West, Salt
Lake City, UT 84116, (801) 596-1887. Email contact links and up to
date contac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the Foundation's web site and
official page at www.gutenberg.org/contact
For additional contact information:
Dr. Gregory B. Newby
Chief Executive and Director
[email protected]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Project Gutenberg-tm depends upon and cannot survive without wide
spread public support and donations to carry out its mission of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ublic domain and licensed works that can be
freely distributed in machine readable form accessible by the widest
array of equipment including outdated equipment. Many small donations
($1 to $5,000)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aintaining tax exempt
status with the IRS.
The Foundation is committed to complying with the laws regulating
charities and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all 50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are not uniform and it takes a
considerable effort, much paperwork and many fees to meet and keep up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We do not solicit donations in locations
where we have not received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compliance. To SEND
DONATIONS or determine the status of compliance for any particular
state visit www.gutenberg.org/donate
While we cannot and do not solicit contributions from states where we
have not met the solicitation requirements, we know of no prohibition
against accepting unsolicited donations from donors in such states who
approach us with offers to donate.
International donations are gratefully accepted, but we cannot make
any statements concerning tax treatment of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U.S. laws alone swamp our small staff.
Please check the Project Gutenberg Web pages for current donation
methods and addresses. Donations are accepted in a number of other
ways including checks, online payments and credit card donations. To
donate, please visit: www.gutenberg.org/donate
Section 5.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Professor Michael S. Hart was the originato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ncept of a library of electronic works that could be
freely shared with anyone. For forty years, he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Project Gutenberg-tm eBooks with only a loose network of
volunteer support.
Project Gutenberg-tm eBooks are often created from several printed
editions, all of which are confirmed as not protected by copyright in
the U.S. unless a copyright notice is included. Thus, we do not
necessarily keep eBooks in compliance with any particular paper
edition.
Most people start at our Web site which has the main PG search
facility: www.gutenberg.org
This Web site includes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tm,
including how to make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how to help produce our new eBooks, and how to
subscribe to our email newsletter to hear about new eBooks.
Антиглобалист
------
Те всички са спестявали от закуски :)
И от прокуратурата -също
трябва да отнеме на този общински законотворец Стефчо Колеф и личен паж на кмета даже и прослувутото колело Ферари за което се похвали и на което вие лично му направихте реклама във Флагман!!!
Може би шампион на Вицеевропа?
А какво е тогава европейски вицешампион, драги журналисти?